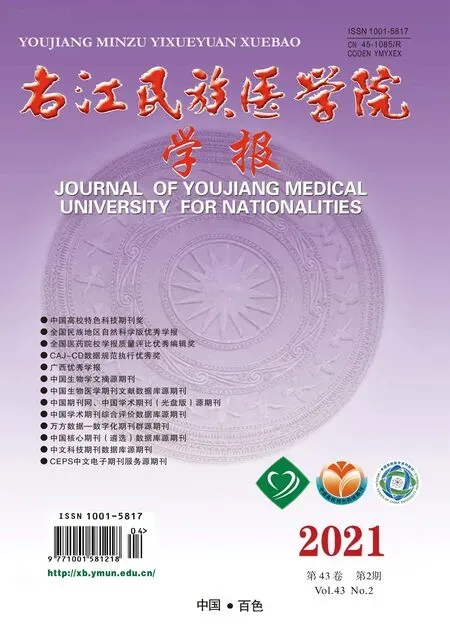結直腸癌標本經自然腔道取出術對患者氧化應激及免疫功能影響
邢玉龍,劉剛,吳澤暉,史良會
(皖南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胃腸外科,安徽 蕪湖 241000)
結直腸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全球高發的消化道惡性腫瘤之一,由于中國經濟發展和飲食條件的改善,其發病率較從前增加顯著[1]。多數患者早期并未發現異樣,確診時多以中晚期為主,目前仍是以手術為主,術后輔助以放化療。腹腔鏡技術的發展引領了外科的革命,傳統腹腔鏡手術仍保留腹部約5 mm切口,切口損傷的存在仍會導致患者術后免疫功能的異常,影響機體功能恢復,增加術后切口感染及后期切口疝等并發癥的發生率[2],全腹腔鏡結直腸癌經自然腔道取標本手術(natural orifice specimen extraction surgery,NOSES)僅留有腹部戳卡瘢痕,手術標本經肛門或女性陰道取出,避免了切口相關并發癥。考慮經陰道取出的二次傷害及性別限制,本研究目的在于比較腹腔鏡輔助結直腸癌根治術與全腹腔鏡NOSES術(經肛門拖出)對患者體內氧化應激及免疫微環境的影響,為結直腸癌患者治療方案提供選擇依據。
1 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年9月—2020年7月皖南醫學院弋磯山醫院胃腸三科收治的高位直腸癌和乙狀結腸癌且可搜集完整住院資料的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回顧性研究,分為NOSES組(觀察組22例)和腹腔鏡輔助結直腸切除術(LACR)組(對照組26例)。均行標準手術治療,NOSES組患者年齡38~83歲,平均年齡(61.11±11.70)歲,男性10例,女性12例,乙狀結腸癌9例,直腸癌13例;LACR組年齡35~80歲,平均年齡(61.80±11.50)歲,男性13例,女性13例,乙狀結腸癌13例,直腸癌13例。
1.2 納入條件 ①腸鏡下病理確診為乙狀結腸或高位直腸癌;②腫瘤分期≤T3期,腫瘤最大直徑<5 cm且環腸周直徑≤3 cm;③術前無明顯手術禁忌證;④術前均告知患者病情及手術風險,簽訂手術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術前行放、化療及免疫等相關治療;②術后復發結直腸癌或合并其他惡性腫瘤患者;③因其他疾病已行手術治療。治療方案:均由同一組手術醫師完成,遵守其標準化術式進行。
1.2.1 NOSES組 取臍上穿刺建立氣腹,放入腹腔鏡鏡頭,五孔法置入Trocar并置入腹腔鏡器械,清掃腸系膜下動脈根部淋巴結,向下分離至腹膜折返水平;用強生腔鏡切割閉合器于腹膜折返水平離斷直腸,擴肛,經肛門碘伏沖洗直腸;遠端直腸切開一小口,置入標本保護套,經肛托出,再經肛側保護套開口將吻合器底釘座送入腹腔;采用反穿刺法置入吻合器底釘座,用線性切割閉合器離斷結腸,將標本裝入保護套內,經肛取出,重新閉合遠端直腸;經肛門置入吻合器出體,從直腸切斷線中點穿出中心杠,腔鏡引導下與底釘座對接并完成吻合。
1.2.2 LACR組 取臍上穿刺建立氣腹,放置腹腔鏡鏡頭,五孔法置入Trocar并置入腹腔鏡器械,將乙狀結腸向上提起,向下分離至直腸中段水平;用強生腔鏡切割閉合器于直腸中段離斷直腸;取右下腹經腹直肌切口5 cm,使用切口保護套,選擇腫瘤近端5 cm離斷降結腸,近端荷包縫合,置入吻合器底釘座,收緊荷包線接扎,放回腹腔;重建氣腹,擴肛后,經肛置入吻合器主體,經切緣戳出中心桿,腔鏡下于近端底釘座對接后吻合,退出吻合器。
1.3 觀察指標及相關檢測方式 記錄總手術時長,術中總出血量,淋巴結清掃數目,術前1天(D1)及術后第2天(D2)、術后第7天(D3)分別以比色法檢測超氧化物歧化酶(SOD)、TBA法檢測丙二醛(MDA)及流式細胞學檢測T細胞(CD3+、CD4+、CD8+、CD4+/CD8+)和免疫濁度法檢測免疫球蛋白(IgA、IgM、IgG)和免疫比濁法檢測補體(C3、C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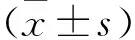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術前相關資料及手術結果的比較 兩組患者性別、年齡、BMI、手術時間、腫瘤位置、腫瘤直徑及T分期,術中總出血量、淋巴結清掃數目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術前相關資料及手術結果
2.2 細胞免疫學檢測(CD3+、CD4+、CD8+、CD4+/CD8+)結果 兩組患者組內比較D2時CD3+、CD4+、CD4+/CD8+值均明顯低于D1時(P<0.05),D3均升高,僅兩組 CD4+/CD8+值升高及LACR組CD3+、CD4+值高于D2時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組間比較D1時CD3+、CD4+、CD8+、CD4+/CD8+值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D2時NOSES組CD3+、CD4+、CD4+/CD8+值均較LACR組高(P<0.05),D3時NOSES組僅CD4+/CD8+值仍高于LACR組(P<0.05),見表2。

表2 兩種不同手術方式對患者T淋巴細胞不同亞群的影響
2.3 體液免疫(IgA、IgM、IgG)及補體系統(C3、C4)檢測結果 兩組患者組內比較D2時IgM、IgG、C3值均明顯低于D1時(P<0.05),D3時三者檢測值均高于D2(P<0.05),僅LACR組D2時IgA值低于D1時(P<0.05)。兩組患者組間比較D1時免疫球蛋白及補體(IgA、IgM、IgG、C3、C4)差異比較無統計學意義(P>0.05),D2時NOSES組IgM、IgG、IgA值均較LACR組高,D3時NOSES組僅IgG值仍高于LACR組(P<0.05),見表3。

表3 兩種不同手術方式對患者體液免疫的影響 單位:g/L
2.4 氧化應激反應(SOD、MDA)檢測結果 兩組患者組內比較D2時SOD值低于D1時(P<0.05),LACR組中D3時SOD值高于D2時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D2時MDA均高于D1(P<0.05),D3時MDA值均較D2時低(P<0.05)。兩組患者組間比較D1時MDA、SOD值差異比較無統計學意義(P>0.05),D2、D3時NOSES組SOD值較對照組高,MDA值明顯低于LACR組(P<0.05),見表4。

表4 兩種不同手術方式對患者機體氧化應激的影響
3 討論
現代微創外科的不斷發展,結直腸癌經自然腔道內鏡手術摒棄了傳統的腹部切口,減少了腹腔對外界的暴露和手術后切口的創傷,Karagul S等[3]研究發現 NOSE 完全腹腔鏡根治性手術并發癥總發生率明顯低于傳統腹腔鏡手術,但標準化根治術對患者的傷害仍不可避免,應激反應是機體受到外界傷害是內環境的自我調節,當手術創傷超過機體可調節范圍,則引起全身各器官的功能障礙,氧化應激是氧化劑與抗氧化防御系統之間的平衡失調,似乎是許多慢性疾病的病理生理中的一個共同因素,氧化應激系統可能參與到結直腸癌的發病機制當中,當體內促氧化劑超過機體微環境抗氧化能力,則會破壞組織細胞的DNA,增加細胞癌變的風險[4-5],有趣的是研究發現其可能降低了腫瘤遠處轉移的可能性[6],SOD是抗氧化系統的重要物質,MDA是應激后自由基作用于脂質發生氧化反應產生,本研究中術后第2天及第7天SOD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MDA均上升,但NOSES組患者體內SOD仍高于LACR組,MDA組間比較低于LACR組,提示減少腹部手術切口,明顯降低了術后體內氧化應激反應,對患者組織細胞的創傷可能有一定的保護作用。
手術、麻醉時間越長,對機體的免疫功能抑制越大,它們在抵御惡性腫瘤和抑制轉移中起著重要作用,免疫抑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早期癌細胞發生免疫逃逸的潛在風險[7-8],且研究發現腫瘤患者由于瘤體生長作用不同程度地抑制機體的免疫能力,本研究發現,兩種手術術后第2天患者CD3+、CD4+、CD4+/CD8+水平較水平均明顯下降,但NOSES組高于LACR組患者,術后第7天均恢復至術前相當的水平,說明傳統腹腔鏡直腸癌根治術對患者短期細胞免疫功能的抑制作用更強,張小軍[ 9]研究發現傳統腹腔鏡手術較開腹手術而言,其術后T淋巴細胞水平明顯高于開腹組,隨訪2~3年后發現其生存率也高于開腹手術,說明術后完整的細胞免疫功能與患者預后密切相關。在Ordemann J等[10]研究的腹腔鏡輔助和開腹手術中發現,表達CD4+和CD8+的淋巴細胞亞群的數量在腹腔鏡手術和常規手術中均無變化,判斷手術切口對免疫功能無影響,該研究中腹腔鏡組手術平均用時為(210±45) min,開放手術為(149±49) min,可能由于手術醫師對腹腔鏡器械掌握的熟練程度,增加了手術時長及麻醉藥物的使用,可能是導致比較結果的無差異性的最大因素。免疫球蛋白作為體液免疫的主要物質,在術后抗感染方面體現重要的作用[11],本研究發現術后第2天兩組患者IgM、IgG均出現下降,NOSES組高于LACR組,且術后第7天LACR組IgG仍處于較低水平,說明減少腹部切口和腸道暴露有利于體液免疫功能的保護。SIgA在腸道黏膜免疫中占有重要地位,LACR組患者術后第2天IgA出現減少,可能與腹部切口及腸道暴露于外界有關,但第7天便迅速恢復,且經短期住院觀察未發現兩組患者出現重大免疫相關疾病及嚴重的感染癥狀,這與抗生素的預防性使用、術中降低創傷和免疫功能保護及加速康復外科理念相結合不無關系。補體系統是輔助機體免疫的調節因子,參與免疫反應,在某些類型的癌癥中發現補體可能也參與其發生[12-13],本研究發現行NOSES組患者術后短期C3水平較高,且兩組患者術后第7天便恢復至術前水平,C4術前與術后均無明顯差異,說明增加腹部切口對補體調節系統影響較小。
綜上發現兩種手術均會導致術后的應激損傷及免疫功能被抑制。腹腔鏡結直腸癌NOSES可較好地減輕患者術后機體微環境中組織的氧化應激損傷,且可以更加完整地保護術后免疫功能,可能對癌癥進一步的治療有前期輔助作用,但腫瘤分期越差,腹腔沖洗液檢出腫瘤細胞陽性率越高[14],對于NOSES患者的選擇需嚴格把握適應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