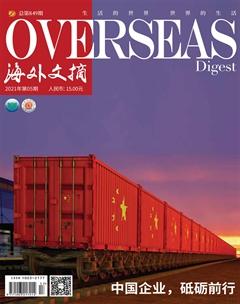平衡木上的噩夢
安特耶·文特曼 小妮子

德國體操運動員波琳·舍費爾和妹妹海倫在開姆尼茨體操中心的訓練室
23歲的波琳·舍費爾時常想起在開姆尼茨體操訓練中心平衡木上練習的那些日子:17歲的她自以為動作完成得不錯,但教練總在指責她,甚至對她說:“看到你,我就忍不住咆哮。”回憶往事,舍費爾總是忍不住流淚:“每天都被侮辱的話,總會在性格中留下痕跡。”
7次德國冠軍,2015年世錦賽平衡木項目季軍,2017年世界冠軍——波琳·舍費爾是近30年來德國成就最高的藝術體操運動員。而現在,她決定公開自己的遭遇。開姆尼茨體操訓練中心由國家資助,致力于培養有天賦的體操選手。舍費爾稱,那里的教練加布里勒·弗雷塞多年來對她百般刁難和折磨,超出了正常人所能承受的極限。除她之外,還有幾個年輕運動員也指責弗雷塞的高壓讓她們受到了精神虐待,不得不服用強止痛劑,或是患上了厭食癥、貪食癥等進食障礙。
| 控制 |
一切都是為了成功,最大限度的成功。弗雷塞的前教練同事雷納特·克呂格爾也證實了這些控訴。“我親眼看到她是如何在精神上控制這些女孩的。”克呂格爾說。那時,她曾多次向上級反映這一情況,但從未得到重視。
四年前,在美國的運動員性侵丑聞曝光后,英國、荷蘭和瑞士的一些運動員也公開了多年來遭受的身心折磨。舍費爾等人受到了國外同病相憐者的鼓舞,但她們和教練相處的時間甚至長過和她們自己的母親,要對教練提起控訴,實屬不易。好在動力戰勝了恐懼,她們希望能讓每個體操訓練室都成為安全的地方,不再有孩子和她們一樣因為熱愛體操而身心受損。
舍費爾說,剛開始她認為弗雷塞是在關心自己,“學業、牙醫預約、贊助合同等等都是她在為我辦。”訓練很苦,但她從不覺得累,“我只做她讓我做的事情。”然而漸漸地,小小的“體操機器人”成長為一個年輕的女人,有了自己的想法,比如她會追問,為何總是這樣訓練而不嘗試其他方法,兩人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有時候我會反駁說,我才是最了解自己身體的人,但加比(譯注:加布里勒的昵稱)完全無法接受。”
對弗雷塞來說,最重要的是馴養和秩序。“她試圖剝奪所有人的行為能力,確保自身處于支配地位,以便實現自我意志。”有人這樣說道。“她的惡毒評論并非未經思索就脫口而出的,她是在故意貶低我。”舍費爾這樣認為。盡管如此,那時她仍試圖相信弗雷塞所言非虛。為控制體重,她曾有一周時間只喝檸檬水,其他什么都不吃。
| 體重 |
13歲時轉到開姆尼茨訓練的麗莎·赫爾也說:“我到這里的第一周,加比就告訴我必須注意保持體重。”當時她每周都會被叫到弗雷塞的辦公室接受訓誡多次。“她一再指責我是個大麻煩,我甚至因此而厭惡自己。”赫爾說。她患上了神經性貪食癥,有時每天要吐兩次。弗雷塞得知后送她去看兒童心理醫生。“她似乎認為,這樣問題就解決了。”赫爾說。

教練加布里勒·弗雷塞
那時,赫爾幾乎無法從體操訓練中獲得任何快樂,直到18歲時到了另一個訓練營地后,她才意識到自己的厭惡情緒并非針對體操本身。“加比不在我身邊時,我就感覺訓練過程非常愉快。”赫爾說。
回到開姆尼茨后,她要求不再跟著弗雷塞訓練,否則就放棄體操運動。由于赫爾是重點培養對象,她的愿望實現了。但她提出要求后,弗雷塞對她的惡劣態度開始變本加厲。赫爾說:“那時我過得非常糟糕,甚至想過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赫爾說,新教練對她的態度和弗雷塞截然不同,“他把我當人看,給我價值感。”隨后,她的貪食癥也慢慢改善了。
| 疼痛 |
除了體重,女孩們還要面對另一個永恒的主題——疼痛。她們常常會達到訓練的極限,肌肉、骨骼和關節都得承受痛苦。“大部分時候,即使疼痛難忍,我們也不敢說,因為教練會告訴我們:咬牙堅持,因為其他人都在堅持。”舍費爾說。
弗雷塞制定出幾乎精確到分鐘的訓練計劃,規定哪個女孩、何時、在何種器械上、以何種頻率、做哪個動作。“女孩們匆匆忙忙地從一種器械趕往另一種器械。”弗雷塞的一位前教練同事說。女孩們認為,能在國家資助的營地訓練是一種榮耀。她們很多都還是十幾歲的少女,卻都以征戰奧運會為目標,愿意為此付出一切。
如果疼痛持續得太久,弗雷塞就會帶舍費爾去看醫生,但每次都以服用止痛藥布洛芬告終。弗雷塞會給她600到800毫克的藥片,每天兩次,服用一到兩周。那么,她的父母對此怎么說?舍費爾疲憊地笑著說:“如果我告訴家里,我為練習體操而服藥,我媽會把整個訓練中心給拆了,或者至少也會打電話給加比,而那之后,她可能會將從我媽那里收獲的郁悶三倍奉還給我。”和很多其他女孩一樣,她決定保持沉默。問題是,一旦停藥,疼痛就會卷土重來,而弗雷塞會說“你還不夠努力”“你太懶了”“你只是不想訓練”。“于是我開始自己買止痛藥。”舍費爾說,“我對藥物產生了依賴。”需要時刻保持良好身體狀況的壓力對她來說實在太大了。
| 傷病 |
2015—2018年間,索菲爾·斯托伊在開姆尼茨接受訓練。一天,她的頭撞到了平衡木上。這個如今16歲的女孩這樣描述弗雷塞的反應:“我疼痛難忍,但加比認為沒有那么嚴重,我不應該哭得那么大聲。”那時,她才13歲。

體操運動員麗莎·赫爾:“她一再指責我是個大麻煩,我甚至因此而厭惡自己。”

體操運動員索菲爾·斯托伊:“我全身都疼。”
體操是一項危險的運動,一瞬間的走神就可能致命或終生致殘,比如藝術體操選手羅尼·齊斯梅爾就在訓練中摔斷了頸椎導致癱瘓。根據克呂格爾的描述,有一次,只因為一個動作沒做到位,弗雷塞就讓一個年輕的體操運動員不斷重復一套完整的地板練習動作直到精疲力盡。“那個女孩沒有力氣了,但她必須繼續訓練,直到我說,如果還不停止,我就馬上離開訓練室,一切才結束。”
如今24歲的羅薩·史密茨在開姆尼茨訓練了五年。一天,13歲的她告訴教練,她右胳膊疼,但訓練基地的醫生說并不嚴重。所以,她又咬緊牙關回去訓練了,甚至還參加了比賽,直到某天早上,她都沒法自己梳頭了,才被母親接回家。照X光后,醫生發現,她的胳膊已經斷了。
| 高壓 |
曾在開姆尼茨訓練中心工作的教練蘇珊娜·溫特爾說,弗雷塞有兩副面孔,有時表現得極其友好,但更常冰冷如鐵,她給運動員們最嚴厲的懲罰是忽視,可能連續多日不理睬一個女孩。
25歲的大學生伊薩貝爾·馬考德回憶起自己在開姆尼茨的經歷:“因為我不夠聽話,弗雷塞就要其他女孩離我遠點。有一次,她們被叫進加比的辦公室,排著隊指出我有多差勁。”晚上回去的時候,女孩們向她道了歉。馬考德認為這種做法非常殘忍,因為她將一起訓練的小伙伴視為姐妹。
另外,弗雷塞還讓她做眼線。“我得盯著其他女孩吃了什么,是否私藏了巧克力。”她說。實際上,偷吃巧克力的女孩往往十分痛苦。一個女孩說:“我總想催吐出來,但太難了。”她們還在宿舍用其他方式自我懲罰,比如用尖銳物品割傷自己。
克呂格爾說:“我發現,這些女孩從來都沒有安全感,天天如此,個個如是。”幾年后,她也辭職了。“我經常想告發加比,”她說,“但如果受害者并不認為自己遭受了精神暴力,我要如何證明?這些孩子相信一切都是自己的問題,大多是如今回想起來才意識到問題所在。”
2016年,美國隊醫拉里·納薩爾性侵多名體操運動員多年的丑聞曝光后,弗雷塞也受到了媒體問詢。她解釋道,這里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但他們以后會更加關注這個問題。對于女孩們的指控,弗雷塞表現得非常吃驚。她的律師回應道,指控中包含大量毫無根據的不實信息。
開姆尼茨奧運訓練基地主任托馬斯·維斯說:“運動員們感到不滿,是因為她們的成績不夠優異或訓練太過艱苦,因為教練的要求太過嚴格或交流風格過于嚴厲。但是,這些都是她們的主觀視角。體操訓練日又不是小孩子的生日。”他表示不可能存在藥物濫用的情況。“這里的大部分運動員都還未成年,必須得到父母和醫生的書面許可才能開到藥。”他宣稱,“能積極訓練、有效提高成績的運動員,從來不會抱怨。”
[編譯自德國《明鏡周刊》]
編輯: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