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性減排政策與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
徐圓 陳曦 郭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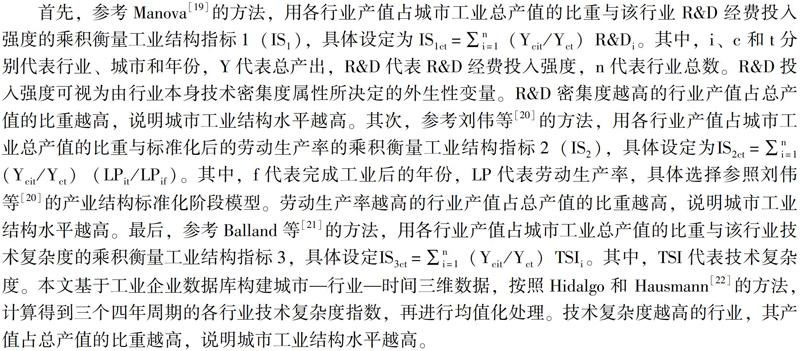


摘 要:基于手工收集的中國230個地級市的強制性減排強度數(shù)據(jù),本文以民營企業(yè)為研究對象,利用雙重差分模型分析“十一五”規(guī)劃中的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的影響及機制。研究結(jié)果顯示,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具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并且這種促進作用會隨著環(huán)境績效考核政策的實施得以強化。考慮到內(nèi)生性問題,本文進一步采用工具變量法、三重差分檢驗法等進行檢驗,均表明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具有顯著促進作用。機制研究表明,強制性減排政策通過對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的抑制效應(yīng)、對民營企業(yè)進入和退出的影響以及對民營企業(yè)創(chuàng)新行為的補償效應(yīng)等途徑促進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本文的研究結(jié)論表明強制性減排政策和環(huán)境績效考核政策是中國實現(xiàn)經(jīng)濟增長與污染治理雙贏的有效手段,如何進一步完善上述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關(guān)鍵詞:強制性減排;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民營企業(yè);環(huán)境績效考核;污染治理
中圖分類號:F421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1)02-0042-11
一、問題的提出
在高質(zhì)量發(fā)展道路上,如何探索經(jīng)濟增長與環(huán)境改善的雙贏之路,是擺在各國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理論上,波特假說和逐優(yōu)競爭假說均指出雙贏之路可以實現(xiàn),前者認(rèn)為適當(dāng)?shù)沫h(huán)境規(guī)制設(shè)計可以通過創(chuàng)新補償效應(yīng)和先發(fā)優(yōu)勢效應(yīng)增強特定行業(yè)的競爭力[1],后者強調(diào)地區(qū)間環(huán)境規(guī)制的逐優(yōu)趨勢會推動整個行業(yè)的標(biāo)準(zhǔn)向上并帶來競爭優(yōu)勢[2]。圍繞此命題,學(xué)者們開展了大量的實證研究[3],然而并沒有得出一致結(jié)論,尤其是對“強式波特假說”的檢驗還缺乏有力證據(jù),但也體現(xiàn)出在追求綠色發(fā)展過程中,協(xié)調(diào)好環(huán)境與經(jīng)濟的可持續(xù)性發(fā)展,關(guān)鍵在于有效且適當(dāng)?shù)沫h(huán)境規(guī)制手段。
中國的環(huán)境規(guī)制體系建設(shè)歷經(jīng)數(shù)次改革,自1983年將環(huán)境保護列為基本國策以來,前后制定了29部相關(guān)法律[4]。僅從立法數(shù)量上來看,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環(huán)境法治大國,但即便如此,不斷惡化的污染形勢依舊嚴(yán)峻。究其原因,很多學(xué)者認(rèn)為其中的關(guān)鍵癥結(jié)置于“財政分權(quán)、政治集權(quán)”的制度背景下,中國環(huán)境治理體制存在中央集權(quán)與地方分權(quán)的二元對立模式[5]。以短期經(jīng)濟增長而非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為目標(biāo)的地方政府,會選擇性地執(zhí)行自上而下的環(huán)境治理政策,甚至在激烈的地方競爭中為追求招商引資,不惜以忽略環(huán)境保護政策的執(zhí)行為代價,換取較高的經(jīng)濟增長速度,出現(xiàn)環(huán)境規(guī)制“向底線賽跑”的趨勢[6]。可見,將環(huán)境治理作為基本公共服務(wù)供給下放到地方政府而建立起來的分權(quán)型環(huán)境管理體制存在明顯的制度缺陷。因此,在追求經(jīng)濟增長與環(huán)境改善的雙贏之路上,對中國而言,制定有效且合適的環(huán)境規(guī)制政策首先需要打破這種中央與地方的二元對立模式。
事實上,這也是過去20年來中國環(huán)境政策的一次巨大改變。為平衡經(jīng)濟增長與環(huán)境保護的雙重目標(biāo),中央政府不斷推進環(huán)境管理目標(biāo)責(zé)任制,在“十一五”規(guī)劃中首次明確主要污染物(化學(xué)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目標(biāo)的約束性量化指標(biāo)(即國務(wù)院向全國人大進行政府報告時,承諾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需要達(dá)到的預(yù)期目標(biāo)),并于2007年出臺《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監(jiān)測辦法》,將減排約束性指標(biāo)分解到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本文將該政策稱為強制性減排政策。2009年9月,中央為進一步加強地方黨政領(lǐng)導(dǎo)班子與領(lǐng)導(dǎo)干部隊伍建設(shè),制定《地方黨政領(lǐng)導(dǎo)班子和領(lǐng)導(dǎo)干部綜合考核評價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考核試行辦法》),1996年國務(wù)院發(fā)布《關(guān)于環(huán)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本轄區(qū)環(huán)境質(zhì)量負(fù)責(zé),2005年又發(fā)布《國務(wù)院關(guān)于落實科學(xué)發(fā)展觀加強環(huán)境保護的決定》,指出要把環(huán)境保護納入領(lǐng)導(dǎo)班子和領(lǐng)導(dǎo)干部考核的重要內(nèi)容,并將考核情況作為干部選拔任用和獎懲的依據(jù)之一。然而,由于這些政策并沒有沒有明確的考核辦法和量化指標(biāo),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環(huán)境績效還只是停留 “紙上談兵”,以至于國家“十五”規(guī)劃執(zhí)行情況中,污染減排是唯一未達(dá)標(biāo)項目,而且工業(yè)二氧化硫排放依舊還上升。而2009年出臺的《地方黨政領(lǐng)導(dǎo)班子和領(lǐng)導(dǎo)干部綜合考核評價辦法(試行)》,是中央層面,由中組部印發(fā),主要目的就是改革和完善發(fā)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jīng)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文件中在“地方黨政領(lǐng)導(dǎo)班子實績分析、民意調(diào)查評價要點”中明確節(jié)能減排與環(huán)境保護、生態(tài)建設(shè)與耕地資源保護等可持續(xù)發(fā)展內(nèi)容。與之前文件相比,從出臺機構(gòu)來說對地方官員更具威懾力,從內(nèi)容上來說也更加具體和可量化。,再次明確將節(jié)能減排和環(huán)境保護列入地方黨政領(lǐng)導(dǎo)班子的政績中,并要求各級地方政府進一步完善評價制度,破除“唯GDP”傾向,由此抑制地方政府為經(jīng)濟利益而忽視生態(tài)利益的狹隘做法,本文將該政策稱為環(huán)境績效考核政策。
隨著強制性減排政策和環(huán)境績效考核政策的實施,以排污費稅率、查處環(huán)境違法企業(yè)數(shù)量和政府環(huán)境支出衡量的環(huán)境規(guī)制指標(biāo),都在2006年后表現(xiàn)出顯著的上升趨勢。環(huán)境規(guī)制趨于嚴(yán)格所帶來的污染治理效應(yīng)被諸多研究所證實[7]。“十一五”規(guī)劃中強制性減排政策是近年來中國環(huán)境質(zhì)量改善的重要推動力,后續(xù)的一系列研究也揭示出該制度的深層次影響機制,發(fā)現(xiàn)在不斷趨嚴(yán)的環(huán)境約束下,污染密集型企業(yè)的空間分布會傾向往減排目標(biāo)壓力較小的中西部地區(qū)轉(zhuǎn)移。龍文濱[10]則發(fā)現(xiàn),地方政府會基于城市空間地理特征作出減排策略的特征性安排,導(dǎo)致“邊界污染效應(yīng)”。
遺憾的是,雖然中國環(huán)境治理模式這一轉(zhuǎn)折性變化帶來的影響,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關(guān)注,雖然中國環(huán)境治理模式開始受到越來越多學(xué)者的關(guān)注,但現(xiàn)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規(guī)制—污染”的單一影響。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嚴(yán)格的環(huán)境規(guī)制能夠有效遏制污染只是目標(biāo)之一,實現(xiàn)環(huán)境改善與經(jīng)濟增長的雙贏才是最終目的。因此,本文以民營企業(yè)為研究對象,探討“十一五”規(guī)劃中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的影響。選擇民營企業(yè)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如下:(1)民營企業(yè)的重要性。截至2018年,中國民營企業(yè)數(shù)量超過2 700萬家,創(chuàng)造全國60%以上的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和70%以上的新技術(shù)、新產(chǎn)品。作為協(xié)調(diào)經(jīng)濟高質(zhì)量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的關(guān)鍵路徑之一,產(chǎn)業(yè)優(yōu)化升級能否順利進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民營企業(yè)[8]。(2)民營企業(yè)轉(zhuǎn)型升級壓力更為緊迫。一般認(rèn)為,隨著環(huán)境規(guī)制的趨嚴(yán),中小企業(yè)的合規(guī)成本遠(yuǎn)高于大企業(yè)[9]。因此,實力較弱、技術(shù)單一的民營企業(yè)更容易受到環(huán)境規(guī)制影響的外部沖擊,進而加速污染大、效率低的企業(yè)退出市場,促進整體結(jié)構(gòu)升級。民營企業(yè)通過研究環(huán)境目標(biāo)約束對民營企業(yè)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的影響,不僅能為實現(xiàn)經(jīng)濟增長和環(huán)境保護的雙贏提供可供參考的政策建議,也對民營經(jīng)濟高質(zhì)量發(fā)展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本文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1)在研究內(nèi)容上,本文系統(tǒng)考察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的宏觀作用和微觀機制。已有文獻(xiàn)大都圍繞環(huán)境規(guī)制與企業(yè)的經(jīng)營績效、出口活動、創(chuàng)新行為展開,缺乏從宏觀層面探討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的整體影響,以及從微觀層面尋找環(huán)境規(guī)制促進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的微觀機制。早期文獻(xiàn)大都存在環(huán)境規(guī)制變量的內(nèi)生性和不可觀測因素帶來的經(jīng)驗分析估計偏差,本文以“十一五”規(guī)劃中污染物減排目標(biāo)設(shè)定,這一事前監(jiān)管措施政策,作為環(huán)境規(guī)制變量,利用DID和DDD模型最大可能地避免內(nèi)生性問題。(2)在研究數(shù)據(jù)上,本文構(gòu)建城市層面強制性減排指標(biāo)更真實和科學(xué)。自“十一五”規(guī)劃將特定污染物排放目標(biāo)量化為約束性指標(biāo)后,國務(wù)院通過出臺《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辦法》將目標(biāo)任務(wù)分解到省級政府,省級政府再以此分解到下一級地方政府。已有文獻(xiàn)雖然以地級市為研究對象,但強制性減排指標(biāo)要么以省級數(shù)據(jù)進行替代,要么按各地級市實際排放比重對省級目標(biāo)進行分解估算。這兩種方法都會導(dǎo)致強制性減排指標(biāo)在省內(nèi)城市間并沒有差異,但事實上,以江蘇為例,“十一五”期間國家對江蘇SO2排放目標(biāo)是削減18%,省級政府又將任務(wù)分解到十三個地級市,其中,要求徐州削減53.6%,但鹽城的任務(wù)只有3%。可見,城市間強制性減排強度存在巨大差異。之前研究中以省級數(shù)據(jù)的替代和估計都會導(dǎo)致偏差。因此,本文盡可能地通過手工收集各省級政府部門下達(dá)的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在城市層面得到更真實和科學(xué)的污染物減排目標(biāo)強度,使得研究結(jié)論更加可信(3)在研究對象上,本文在減排目標(biāo)約束的基礎(chǔ)上聯(lián)合環(huán)境績效考核,綜合考察兩者對民營以民營企業(yè)為研究對象,考察強制性減排政策和環(huán)境績效考核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的影響。雖然“十一五”規(guī)劃中首次將主要污染減排目標(biāo)定義為約束性指標(biāo),但在中國特殊的晉升錦標(biāo)賽機制下,地方政府能否完成上級下達(dá)的環(huán)境政治任務(wù)與對其評價體系是息息相關(guān)的。然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單一分析減排目標(biāo)約束的作用[10],但事實上官員考核制度的改變有可能使得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民營企業(yè)的影響更大。,而忽略這點,研究結(jié)論將失去對環(huán)境治理核心關(guān)鍵制度設(shè)計的啟示意義。
二、制度背景與研究假設(shè)
(一)制度背景
作為中央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在執(zhí)行環(huán)境政策時出現(xiàn)嚴(yán)重的目標(biāo)偏離,這啟發(fā)中央政府意識到問題來源于政治激勵的錯位。因此,為抓住矛盾的本質(zhì),中央政府不僅開始將環(huán)境指標(biāo)納入五年規(guī)劃的約束性任務(wù),還不斷提升其干部考核指標(biāo)體系中的權(quán)重[7]。其實,早上20世紀(jì)80年代末,國務(wù)院召開第三次環(huán)境保護會議時就提出,要積極推行深化環(huán)境管理的目標(biāo)責(zé)任制。到2005年《關(guān)于落實科學(xué)發(fā)展觀加強環(huán)境保護的決定》時,再次明確要把環(huán)境保護納入領(lǐng)導(dǎo)班子和領(lǐng)導(dǎo)干部考核的重要內(nèi)容,并將考核情況作為干部選拔任用和獎懲的依據(jù)之一。但在當(dāng)時,由于沒有明確的考核辦法和量化指標(biāo),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環(huán)境目標(biāo)約束還只是停留在“紙上談兵”。
轉(zhuǎn)折出現(xiàn)在2006年“十一五”規(guī)劃綱要首次明確將污染物排放目標(biāo)量化為約束性指標(biāo),其中在全國層面要求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2007年出臺《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監(jiān)測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huán)境保護部將10%的減排目標(biāo)具體量化到削減化學(xué)需氧量571萬噸、二氧化硫673萬噸,并通過簽訂目標(biāo)責(zé)任書逐一分解落實到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和電力集團公司。各省級政府隨后又將減排指標(biāo)、減排工程和減排措施分解落實到地市和重點排污單位,從而實現(xiàn)環(huán)保考核的可操作性。減排目標(biāo)成為可量化的約束性指標(biāo),必然有利于各級政府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在衡量經(jīng)濟增長和環(huán)境保護之間矛盾時增加對后者的權(quán)重,而中央政府通過約束性指標(biāo)的強制力來實現(xiàn)對各地區(qū)的有效監(jiān)督,有利于糾正過去偏離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行為。
2009年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修訂實施《考核試行辦法》,其中涉及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有環(huán)境保護、資源消耗與安全生產(chǎn)、耕地等資源保護三個細(xì)分評價要點,強調(diào)要把民生改善、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等作為考核評價重要內(nèi)容,加大資源消耗、環(huán)境保護、消化產(chǎn)能過剩等指標(biāo)的權(quán)重。雖然,中組部在2006年就印發(fā)《體現(xiàn)科學(xué)發(fā)展觀要求的地方黨政領(lǐng)導(dǎo)班子和領(lǐng)導(dǎo)干部綜合考核評價試行辦法》,但由于缺乏的具體環(huán)境考核權(quán)重指標(biāo),地方組織部門需要據(jù)此自行設(shè)計方案。據(jù)北京政通境和節(jié)能研究所的調(diào)研,《考核試行辦法》中的三個要點在各省百分制的實際考核中平均只占不到10分的分值,而排在前3項的經(jīng)濟指標(biāo)一般占35分以上。
由此可見,從“十一五”規(guī)劃的實施開始,在強制性減排和環(huán)境績效考核的壓力下,“唯 GDP 論”開始被打破,地方政府從單純追求GDP增長轉(zhuǎn)變?yōu)椤盀楹椭C而競爭”。無論是地方政府對污染治理的財政支出,還是環(huán)境規(guī)制綜合指數(shù),環(huán)境規(guī)制綜合指數(shù),本文參考沈坤榮等[6]的方法,在城市層面基于二氧化硫去除率、工業(yè)煙(粉)塵去除率,采用線性加權(quán)和法進行測算。與強制性減排強度的回歸系數(shù)都在2006年后表現(xiàn)出迅速增長趨勢。這表明“十一五”規(guī)劃中強制性減排政策的實施,使得地方政府官員在不同的目標(biāo)考核壓力下,會對轄區(qū)內(nèi)的環(huán)境治理進行權(quán)衡,導(dǎo)致對污染治理的財政支出越來越多,也帶動本地環(huán)境規(guī)制不斷趨向嚴(yán)格。
(二)研究假設(shè)
盡管環(huán)境規(guī)制的目標(biāo)在于減少污染排放并加強環(huán)境治理,但由于企業(yè)成本和產(chǎn)品價格的變化,它對經(jīng)濟活動的結(jié)構(gòu)和空間分布有都具有間接影響[11]。在強制性減排和環(huán)境績效考核的雙重壓力下,中國環(huán)境規(guī)制不斷趨嚴(yán),不具備政治優(yōu)勢的民營企業(yè)將比其他所有制企業(yè)更早一步和更大程度受到成本壓力[12]。早期具有代表性的“遵循成本說”指出,環(huán)境規(guī)制的實施會增加企業(yè)的生產(chǎn)成本,降低生產(chǎn)效率[13]。因此,日漸嚴(yán)格的環(huán)境規(guī)制引致的額外成本上升以不同方式和渠道作用于民營企業(yè),這種倒逼機制促使民營企業(yè)進入重要的轉(zhuǎn)型升級時期。
首先,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會直接受到環(huán)境規(guī)制成本效應(yīng)的沖擊而承受更高的生產(chǎn)成本。由于技術(shù)的復(fù)雜性和設(shè)備的特殊性,污染密集型行業(yè)進行生產(chǎn)能力的調(diào)整更為困難。當(dāng)環(huán)境規(guī)制趨嚴(yán)時,污染密集型企業(yè)不得不增加非生產(chǎn)性投入以抵消環(huán)境監(jiān)管成本,這將導(dǎo)致資源分配出現(xiàn)扭曲,進而阻礙企業(yè)的發(fā)展甚至生存。相反,清潔行業(yè)會在環(huán)境規(guī)制趨嚴(yán)時增大研發(fā)投入強度,從技術(shù)渠道避免環(huán)境監(jiān)管成本,導(dǎo)致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激勵效應(yīng)和溢出效應(yīng),并最終帶動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其次,環(huán)境規(guī)制通過形成隱形的綠色行業(yè)壁壘,推動經(jīng)濟發(fā)達(dá)地區(qū)獲得發(fā)展清潔型產(chǎn)品的優(yōu)質(zhì)生態(tài)環(huán)境,能在產(chǎn)業(yè)群組中進行基于外力實施的正向清洗,從而限制高污染、粗放落后、低端低效企業(yè)的進入。同時,由于環(huán)境規(guī)制在產(chǎn)業(yè)鏈中的成本傳導(dǎo)機制,會提升整個區(qū)域企業(yè)進入的市場門檻,通過優(yōu)勝劣汰的作用機制,將低生產(chǎn)率企業(yè)清理出去,并引導(dǎo)經(jīng)營能力更強的高生產(chǎn)率企業(yè)進入,由此推動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優(yōu)化升級。不同于環(huán)境規(guī)制直接作用于低效率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非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也將由于自身的產(chǎn)業(yè)鏈下游地位而受到上游壟斷企業(yè)采取抬高定價策略以抵消環(huán)境規(guī)制額外成本這一行為的間接影響[14],因而所有民營企業(yè)都不得不進行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以應(yīng)對市場清洗,即強制性減排政策對民營企業(yè)產(chǎn)生了低效率企業(yè)退出和高效率企業(yè)進入的過濾效應(yīng)。對于低效率企業(yè)而言,環(huán)境規(guī)制引致的額外成本對企業(yè)研發(fā)支出產(chǎn)生擠出效應(yīng),抑制了技術(shù)創(chuàng)新能力,不利的競爭地位使得大批企業(yè)逐漸退出市場;對于高效率企業(yè)而言,全面推行的環(huán)境績效約束使得中小民營企業(yè)的低價競爭行為不再被允許,給予了早期就已踏上遵循環(huán)保政策道路的部分高效率企業(yè)更充足的發(fā)展空間。最后,正如圍繞波特假說展開的傳統(tǒng)觀點認(rèn)為,雖然環(huán)境規(guī)制早短期會增加企業(yè)治污的額外成本,但從長期來看會成為企業(yè)研發(fā)創(chuàng)新的內(nèi)在激勵[15]。嚴(yán)格的環(huán)境規(guī)制使得發(fā)展相對處于劣勢的民營企業(yè)加快研發(fā)創(chuàng)新投入以扭轉(zhuǎn)自身發(fā)展受阻的不利局面,而發(fā)展相對處于優(yōu)勢的民營企業(yè)也將在原有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水平上進一步增加研發(fā)投入以維持自身的優(yōu)勢地位,環(huán)境規(guī)制激發(fā)了民營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補償效應(yīng),在抵消遵循成本損耗的同時產(chǎn)生了技術(shù)擴散和結(jié)構(gòu)升級效應(yīng)[16]。
可見,強制性減排政策使地方政府加強了環(huán)境規(guī)制的執(zhí)行和監(jiān)管力度,提高了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的成本投入,并由于產(chǎn)業(yè)鏈的成本傳導(dǎo)機制,通過優(yōu)勝劣汰的市場作用將低生產(chǎn)率民營企業(yè)清理出去,引導(dǎo)經(jīng)營能力更強的高生產(chǎn)率民營企業(yè)進入,由此推動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優(yōu)化升級。不僅如此,環(huán)境規(guī)制引致的額外成本還將對民營企業(yè)產(chǎn)生一定的創(chuàng)新補償效應(yīng),促使民營企業(yè)向更高級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
綜上所述,筆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設(shè):
H1:“十一五”規(guī)劃中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具有一定的正向促進作用,并且這種作用會隨著2009年環(huán)境績效考核政策的實施得以強化。
H2:強制性減排和環(huán)境績效考核帶來環(huán)境規(guī)制不斷趨嚴(yán),通過對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的抑制效應(yīng)、對民營企業(yè)進入和退出的影響以及對民營企業(yè)創(chuàng)新行為的補償效應(yīng)促進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
三、研究設(shè)計
(一)數(shù)據(jù)來源與說明
本文的主要來源于中國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該數(shù)據(jù)庫統(tǒng)計了全部國有企業(yè)和主營業(yè)務(wù)收入超過500萬元的非國有企業(yè),涵蓋國民經(jīng)濟行業(yè)分類的6—46大類(除去12和38類)。考慮到原始數(shù)據(jù)存在樣本匹配混亂、測度誤差明顯和變量大小異常等問題,本文參照聶輝華[21]的方法,對數(shù)據(jù)作出如下處理:首先,對出現(xiàn)變量定義變動的指標(biāo)按2002年的國家標(biāo)準(zhǔn)(GBT/4757)進行一致性轉(zhuǎn)換處理。其次,刪除關(guān)鍵變量(總產(chǎn)出、總資產(chǎn)、企業(yè)類型、省地縣碼、控股類型等)缺失的觀察值;刪除明顯不符合邏輯關(guān)系的觀察值,如企業(yè)總產(chǎn)出為負(fù)、企業(yè)各項投入(固定資產(chǎn)原值、固定資產(chǎn)凈值、職工總數(shù)、中間品投入)為負(fù)、總資產(chǎn)小于企業(yè)固定資產(chǎn)凈值、總資產(chǎn)小于企業(yè)流動資產(chǎn)、固定資產(chǎn)累計折舊小于當(dāng)期折舊;刪除成立時間在1949年之間的企業(yè);刪除企業(yè)注冊類型錯誤的樣本(如企業(yè)注冊類型小于代碼3,或大于代碼340)。最后,根據(jù)企業(yè)的法人代碼、企業(yè)名稱、省地縣碼、法人姓名、主要產(chǎn)品逐一進行不同年份間企業(yè)的識別和匹配。本文主要研究對象聚焦于民營企業(yè),因而在數(shù)據(jù)識別上,按照《中國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中的企業(yè)注冊類型對民營企業(yè)進行挑選。在數(shù)據(jù)處理上,城市層面的民營工業(yè)行業(yè)總產(chǎn)值等數(shù)據(jù)通過對微觀企業(yè)數(shù)據(jù)加總構(gòu)建城市—年份—行業(yè)的三維數(shù)據(jù)得到。
中國230個地級市的污染物排放量數(shù)據(jù)來自于各年度的《城市統(tǒng)計年鑒》,包括工業(yè)SO2和工業(yè)廢水。國家對特定污染物排放目標(biāo)中并沒有工業(yè)廢水,但包含工業(yè)廢水主要污染物—化學(xué)需氧量(COD),因此,對于城市層面的污染減排強度指標(biāo)構(gòu)建采用SO2和COD,其中,COD減排強度按各市工業(yè)廢水排放比例進行測算。分行業(yè)的工業(yè)污染物排放強度是2005年、2010年、2015年三年的平均值,數(shù)據(jù)來自于《中國環(huán)境統(tǒng)計年鑒》。分行業(yè)的R&D強度數(shù)據(jù)來自于國家統(tǒng)計局的第二次全國R&D資源清查主要數(shù)據(jù)公報。其他城市特征變量數(shù)據(jù),主要來自于各年份的《城市統(tǒng)計年鑒》。
本文研究對象為民營企業(yè),數(shù)據(jù)來自于中國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參考聶輝華等[17]的方法,對原始數(shù)據(jù)進行一系列異常值處理。最終通過對微觀企業(yè)數(shù)據(jù)的加總得到城市—年份—行業(yè)三維民營工業(yè)數(shù)據(jù)。各行業(yè)的污染物排放強度數(shù)據(jù)來自《中國環(huán)境統(tǒng)計年鑒》,城市層面控制變量數(shù)據(jù)來自《城市統(tǒng)計年鑒》,民營上市企業(yè)數(shù)據(jù)來自Wind數(shù)據(jù)庫。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工業(yè)結(jié)構(gòu)指標(biāo)
一般而言,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表現(xiàn)為各行業(yè)比例關(guān)系的改變和技術(shù)含量的提升,通常指從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再到知識技術(shù)密集型的轉(zhuǎn)換,或由低附加值產(chǎn)業(yè)到高附加值產(chǎn)業(yè)的轉(zhuǎn)變,或由初級產(chǎn)品產(chǎn)值占優(yōu)勢向制造中間產(chǎn)品、最終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占優(yōu)勢的轉(zhuǎn)換等[18]。本文從工業(yè)各行業(yè)R&D投入密度、勞動生產(chǎn)率和技術(shù)復(fù)雜度三個方面構(gòu)建工業(yè)結(jié)構(gòu)指標(biāo)。
首先,參考Manova[19]的方法,用各行業(yè)產(chǎn)值占城市工業(yè)總產(chǎn)值的比重與該行業(yè)R&D經(jīng)費投入強度的乘積衡量工業(yè)結(jié)構(gòu)指標(biāo)1(IS1),具體設(shè)定為IS1ct=∑ni=1(Ycit/Yct)R&Di。其中,i、c和t分別代表行業(yè)、城市和年份,Y代表總產(chǎn)出,R&D代表R&D經(jīng)費投入強度,n代表行業(yè)總數(shù)。R&D投入強度數(shù)據(jù)來源于全國第二次R&D清查,與城市和時間都無關(guān),可視為由行業(yè)本身技術(shù)密集度屬性所決定的外生性變量。R&D密集度越高的行業(yè)產(chǎn)值占總產(chǎn)值的比重越高,說明城市工業(yè)結(jié)構(gòu)水平越高。
其次,參考劉偉等[20]的方法,用各行業(yè)產(chǎn)值占城市工業(yè)總產(chǎn)值的比重與標(biāo)準(zhǔn)化后的勞動生產(chǎn)率的乘積衡量工業(yè)結(jié)構(gòu)指標(biāo)2(IS2),具體設(shè)定為IS2ct=∑ni=1(Ycit/Yct)(LPit/LPif)。其中,f代表完成工業(yè)后的年份,LP代表勞動生產(chǎn)率,具體選擇參照劉偉等[20]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標(biāo)準(zhǔn)化階段模型。勞動生產(chǎn)率越高的行業(yè)產(chǎn)值占總產(chǎn)值的比重越高,說明城市工業(yè)結(jié)構(gòu)水平越高。
最后,參考Balland等 [21]的方法,用各行業(yè)產(chǎn)值占城市工業(yè)總產(chǎn)值的比重與該行業(yè)技術(shù)復(fù)雜度的乘積衡量工業(yè)結(jié)構(gòu)指標(biāo)3,具體設(shè)定IS3ct=∑ni=1(Ycit/Yct)TSIi。其中,TSI代表技術(shù)復(fù)雜度。本文基于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構(gòu)建城市—行業(yè)—時間三維數(shù)據(jù),按照Hidalgo和 Hausmann[22]的方法,計算得到三個四年周期的各行業(yè)技術(shù)復(fù)雜度指數(shù),再進行均值化處理。技術(shù)復(fù)雜度越高的行業(yè),其產(chǎn)值占總產(chǎn)值的比重越高,說明城市工業(yè)結(jié)構(gòu)水平越高。
2.解釋變量:強制性減排強度
本文城市層面的數(shù)據(jù)通過手工收集和信息公開申請等方式由各省級、市級政府部門的相關(guān)政策文件得到,具體用SO2減排強度(RTSO2)和COD減排強度(RTCOD)來衡量。環(huán)境規(guī)制的內(nèi)生性是相關(guān)研究中的難點問題之一,在中國一般在省級層面采用地區(qū)單位排污費、工業(yè)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等事后監(jiān)管變量衡量地區(qū)環(huán)境規(guī)制強度。本文采用強制性減排強度作為環(huán)境規(guī)制變量的優(yōu)勢在于,它可以被視為一個事前變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內(nèi)生性問題。因為強制性減排強度由國家統(tǒng)一提前制定,不太可能受到相關(guān)企業(yè)采取改變生產(chǎn)活動等手段來應(yīng)對環(huán)境規(guī)制的影響。
3.控制變量
市場化程度(lnmarket),用私營及個體就業(yè)人數(shù)占總就業(yè)人數(shù)比重的自然對數(shù)來衡量;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lngdp),用人均GDP的自然對數(shù)來衡量;服務(wù)業(yè)占比(lnservice),用服務(wù)業(yè)占地區(qū)GDP比重的自然對數(shù)來衡量,服務(wù)業(yè)通過推進專業(yè)化分工、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知識溢出,對制造業(yè)升級有正向作用;金融深化(lnfindev),用金融機構(gòu)貸款余額占地區(qū)GDP比重的自然對數(shù)來衡量,以反映金融體系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的融資支持;開放度(lnopen),用限額以上外商投資工業(yè)企業(yè)總產(chǎn)值占工業(yè)企業(yè)工業(yè)總產(chǎn)值比重的自然對數(shù)來衡量,外商投資還具有顯著的技術(shù)溢出效應(yīng),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具有推動作用;人力資本水平(lnhumcap),用每萬人高等學(xué)校在校生人數(shù)的自然對數(shù)來衡量。
(三)模型設(shè)定
城市間減排目標(biāo)約束的差異和“十一五”規(guī)劃實施2009年《考核試行辦法》實施前后的變化,為采用雙重差分(DID)模型分析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民營工業(yè)結(jié)構(gòu)的影響提供了條件。本文構(gòu)建如下基準(zhǔn)計量模型:
本文采用雙重差分(DID)模型分析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的影響,基準(zhǔn)模型如下:
其中,i、c和t分別代表行業(yè)、城市和年份;Postt是時間虛擬變量,具體表示“十一五”規(guī)劃中強制性減排政策的實施或2009年環(huán)境績效考核政策的實施,當(dāng)t≥2006時,Post2006取值為1,否則為0;當(dāng)t≥2009時,Post2009取值為1,否則為0;RTct×Postt代表強制性減排強度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X代表上述一系列控制變量;γc和δi分別代表地區(qū)固定效應(yīng)和時間固定效應(yīng);εct為隨機誤差項。為了消除潛在的異質(zhì)性和序列相關(guān)性,此模型在城市層面聚類標(biāo)準(zhǔn)誤。
為彌補DID模型可能存在的雙向因果關(guān)系,同時避免一些隨時間變化的城市特征變量與自變量、解釋變量同時相關(guān)的可能性,本文構(gòu)建三重差分(DDD)模型解決估計偏誤問題。嚴(yán)格的環(huán)境法規(guī)所產(chǎn)生的成本效應(yīng)不僅會影響污染密集型行業(yè),還會對非污染密集型企業(yè)造成成本壓力。美中貿(mào)易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指出,有29%的成員公司將不斷上升的環(huán)境合規(guī)視為2018年最主要的成本問題。這是因為,從宏觀層面來看,環(huán)境規(guī)制具有產(chǎn)業(yè)鏈的成本傳遞機制,這會給非污染密集型企業(yè)造成間接影響。嚴(yán)格的環(huán)境規(guī)制使處于較高層次行業(yè)的企業(yè)具有更大空間進行污染成本控制,而處于較低層次行業(yè)的企業(yè)可能因為無法吸收環(huán)境成本而退出市場,因而環(huán)境規(guī)制可視為工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的新動力。鑒于此,環(huán)境規(guī)制對處于不同結(jié)構(gòu)層次的行業(yè)具有差異性的影響,從而具有構(gòu)建DDD模型的基礎(chǔ)。具體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R&Di代表研發(fā)投入強度;RTct×Postt×R&Di代表強制性減排強度、時間虛擬變量與研發(fā)投入強度的交互項;γct、δit和μci分別代表時間—地區(qū)固定效應(yīng)、行業(yè)—時間固定效應(yīng)和地區(qū)—行業(yè)固定效應(yīng);εict為隨機誤差項。本文關(guān)注三重交互項系數(shù)α21的符號,如果為正,表明強制性減排強度越大的城市,高層次行業(yè)產(chǎn)出增加越多,間接驗證環(huán)境規(guī)制有利于推動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不同于DID模型,DDD模型不僅有助于控制所有易隨時間變化和不易隨時間變化的城市特征變量,還有助于控制所有易隨時間變化和不易隨時間變化的行業(yè)特征變量。
表1是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
四、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基準(zhǔn)回歸結(jié)果
本文基于中國230個城市的面板數(shù)據(jù),考察環(huán)境目標(biāo)約束對民營工業(yè)結(jié)構(gòu)的影響。模型(1)的回歸結(jié)果如表2和表3是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影響的回歸結(jié)果,其中,表2探討2006年強制性減排政策實施前后的差異,表3探討2009年環(huán)境考核績效政策實施前后的差異。
工業(yè)結(jié)構(gòu)指標(biāo)的回歸結(jié)果均顯著為正,表明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具有正向推動作用。對比表2和表3的回歸系數(shù)可以發(fā)現(xiàn),后者是前者的2.75—5.47倍,表明在強制性減排和環(huán)境績效考核的雙重壓力下,環(huán)境規(guī)制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的影響更加強烈,H1得到驗證。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十一五”規(guī)劃中主要污染物減排目標(biāo)經(jīng)層層分解落實到地方政府時,還需明確的環(huán)境績效考核作為保證才能被有效執(zhí)行。“十一五”期間未被納入約束性目標(biāo)的污染物排放量依舊持續(xù)增加,如工業(yè)廢水和一般工業(yè)固體廢物。隨著2009年環(huán)境考核績效政策的實施,地方政府開始明確考核辦法和量化指標(biāo),除了考核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biāo)完成情況外,還將環(huán)境治理改善和環(huán)境保護重點任務(wù)完成情況等指標(biāo)量化并納入考核,甚至增加公眾滿意程度等指標(biāo),這會推動地方政府落實環(huán)保主體責(zé)任,進一步加強環(huán)境規(guī)制。
(二)年度動態(tài)效應(yīng)
DID估計存在一個潛在問題——2006年后強制性減排政策驅(qū)動的環(huán)境質(zhì)量改善可能源自之前政府所作的努力,而2006年后工業(yè)結(jié)構(gòu)的變化實際上是由預(yù)先存在的趨勢造成。事實上,“十一五”規(guī)劃是從2006年開始執(zhí)行,直到2007年各省級政府才陸續(xù)制定本省的減排方案,并逐級向下級地方政府傳達(dá)。如果民營企業(yè)在“十一五”規(guī)劃實施之前就已經(jīng)開始采用清潔生產(chǎn)技術(shù)或改變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則會改變樣本的平行趨勢,使得DID估計產(chǎn)生偏誤。同時,基準(zhǔn)模型回歸結(jié)果反映的是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的平均影響,并沒有反映在不同時段內(nèi)這一影響的差異。為考察這種時間變化趨勢,本文參考Chen等[23]的做法,將強制性減排政策實施的2006年作為基準(zhǔn)年設(shè)立虛擬變量納入基本模型,通過時間變化趨勢檢驗來識別強制性減排政策的敏感性,據(jù)此構(gòu)建模型(3):
其中,YearDummy t是取值為0和1的虛擬變量,當(dāng)t=2002年時,YearDummy 2002取值為1,其他年份均取值為0;當(dāng)t=2003年時,YearDummy 2003取值為1,其他年份均取值為0,并以此類推至2013年。
表4是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動態(tài)效應(yīng)的回歸結(jié)果。結(jié)果顯示,在強制性減排政策實施之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并沒有呈現(xiàn)出顯著性影響,但在2006年之后,α31系數(shù)開始表現(xiàn)出顯著性正相關(guān),并隨著年份增加而不斷增大。證實中央政府在“十一五”期間明確主要污染物的減排目標(biāo)后,民營企業(yè)開始進行轉(zhuǎn)型升級且力度逐年遞增。
(三)穩(wěn)健性檢驗
限于篇幅,穩(wěn)健性檢驗結(jié)果和安慰劑檢驗圖形未在文中列出,留存?zhèn)渌鳌?/p>
1.工具變量
雖然采用強制性減排強度作為環(huán)境規(guī)制的代理變量能夠最大可能地克服之前研究中出現(xiàn)的內(nèi)生性問題,但地方官員對環(huán)境治理的實際努力還不能完全由城市所下達(dá)的強制性減排強度所涵蓋。同時,以環(huán)境績效考核為代表的弱排名激勵也可能存在形式上滿足外在科層要求,實質(zhì)上可在內(nèi)部作出調(diào)整。為解決低合規(guī)強制性減排強度可能錯誤地衡量實際監(jiān)管嚴(yán)格性的問題,本文參照Chen等[10]選取政府工作報告中與“環(huán)境”有關(guān)詞匯出現(xiàn)的頻次作為強制性減排強度的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回歸。政府工作報告是依法行政和執(zhí)行權(quán)力機關(guān)決定、決議的綱要,是指導(dǎo)政府工作的綱領(lǐng)性文件。因此,政府工作報告中與環(huán)境相關(guān)詞匯出現(xiàn)頻數(shù)能夠反映出地方政府對環(huán)境治理的重視和力度。同時,由于地方政府報告一般在年初對外公布,當(dāng)年度的實際經(jīng)濟行為無法反向影響政府報告,可以緩解模型中潛在的內(nèi)生性問題。工具變量法的回歸結(jié)果顯示,雖然“十一五”規(guī)劃開始執(zhí)行的COD減排強度的系數(shù)不顯著,但2009年《考核試行辦法》出臺后,其在1%水平下顯著。SO2減排強度與基準(zhǔn)模型回歸結(jié)果一致。弱識別檢驗統(tǒng)計值和識別不足檢驗統(tǒng)計值均拒絕工具變量與強制性減排強度不相關(guān)和相關(guān)性較弱的假定。同時過度識別檢驗中的Hanson J統(tǒng)計值的P值不顯著,說明工具變量與誤差項不相關(guān),能夠滿足外生性假定的條件。
2.排除其他因素干擾
任何政策的實施不可避免地受到突發(fā)事件的外部沖擊及其他政策的影響,從而對政策實施效果評估造成偏誤。鑒于此,本文需要排除在研究樣本期間內(nèi)一系列可能產(chǎn)生影響的政策沖擊。具體包括:一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為兌現(xiàn)北京奧運會的“藍(lán)天承諾”,2007—2008年中國政府對北京周邊高污染排放的工業(yè)企業(yè)實施一系列強制性措施。按照He等[24]的研究,受到影響的地區(qū)還包括天津、山西、內(nèi)蒙古和遼寧。為防止這一事件對研究穩(wěn)健性的影響,將2007—2008年相應(yīng)地區(qū)的城市從研究樣本中剔除,結(jié)果顯示強制性減排強度的系數(shù)在1%的水平下均顯著為正。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世界經(jīng)濟和中國經(jīng)濟造成巨大沖擊,故在樣本中剔除2008年和2009年,結(jié)果顯示強制性減排強度的系數(shù)在1%的水平下均顯著為正。,說明即使考慮到一系列潛在影響民營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策或者事件后,環(huán)境績效約束仍然能夠顯著促進民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提升,從而研究結(jié)論的可靠性得到進一步驗證。此外,考慮到北京和上海兩個直轄市的特殊性和服務(wù)業(yè)占地區(qū)GDP比重較大的現(xiàn)實情況,本文剔除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的樣本數(shù)據(jù),結(jié)果顯示強制性減排強度的系數(shù)在1%的水平下依舊均顯著為正,與基準(zhǔn)回歸結(jié)果沒有顯著差異,表明本文結(jié)論穩(wěn)健。
(四)三重差分模型回歸結(jié)果
為彌補雙重差分模型的不足,本文利用三重差分模型進一步分析。由模型(2)可知,需要重點關(guān)注RTct×Postt×R&Di的系數(shù)α21,若α21大于0,則說明2006年后隨著環(huán)境規(guī)制的不斷趨嚴(yán),強制性減排強度越高的城市中的高層次行業(yè)產(chǎn)值規(guī)模呈現(xiàn)出增長趨勢;反之,則說明強制性減排強度越高,城市中的高層次行業(yè)產(chǎn)值規(guī)模不斷萎縮,從而間接驗證強制性減排強度通過促進高層次行業(yè)增長和抑制低層次行業(yè)規(guī)模,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具有促進作用。表5是三重差分模型的回歸結(jié)果,“十一五”規(guī)劃后SO2減排強度有利于民營工業(yè)中R&D密集型行業(yè)的增長,并且在2009年環(huán)境績效考核政策實施后,影響強度有所加深。COD強制性減排強度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對高R&D強度行業(yè)和低R&D強度行業(yè)的影響差異并沒有立刻顯現(xiàn),但在2009年后開始變得顯著。
五、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影響的機制分析
(一)強制性減排政策對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的抑制效應(yīng)
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污染物減排任務(wù)經(jīng)層層分解給地方政府帶來了高強度的環(huán)保壓力,再加之考核指標(biāo)中環(huán)境績效的確認(rèn),這無疑會嚴(yán)格環(huán)境規(guī)制,增加民營企業(yè)的排污成本,即大量早期文獻(xiàn)中提到的“遵循成本”。相比較于清潔產(chǎn)業(yè),強制性減排政策對污染密集型行業(yè)中的民營企業(yè)具有更明顯的負(fù)面影響。一方面,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需要引進價格高昂的排污設(shè)備,并投入大量的生產(chǎn)資源用于處理污染物;另一方面,在原本已經(jīng)難以消化的額外生產(chǎn)成本基礎(chǔ)之上,強制性減排政策使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無法投入足夠的資金進行研發(fā)創(chuàng)新,企業(yè)競爭力被逐步削弱。根據(jù)工業(yè)污染物排放強度指標(biāo),SO2排放密集型行業(yè)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非金屬及金屬制品、礦物采選業(yè)等,COD排放強度較高的行業(yè)包括石油化工、紡織、紙制品等。污染密集型行業(yè)的技術(shù)層次通常不高,一般處于價值鏈中下游,在環(huán)境規(guī)制的作用下,這些行業(yè)中的民營企業(yè)生存壓力增大,產(chǎn)值規(guī)模和增長趨勢都可能受到抑制。本文利用不同污染密集程度的行業(yè)對環(huán)境規(guī)制的反應(yīng)存在差異的事實,構(gòu)建DDD模型,研究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在強制性減排強度下可能發(fā)生的抑制效應(yīng)。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INTi代表污染密集程度,主要選取SO2密集程度和COD密集程度來衡量;RTct×Postt×INTi代表強制性減排強度、時間虛擬變量與污染密集程度的交互項。
本文關(guān)注的是三重交互項回歸系數(shù),如果結(jié)果為負(fù),表明污染物減排強度越大城市的高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產(chǎn)出減少得越多,由此驗證環(huán)境目標(biāo)約束會抑制污染密集型企業(yè)增長。表6是強制性減排政策對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抑制效應(yīng)的回歸結(jié)果,列(1)和列(2)不顯著,列(3)和列(4)均顯著為負(fù),意味著在環(huán)境績效考核政策實施后,當(dāng)“十一五”規(guī)劃中的強制性減排任務(wù)完全轉(zhuǎn)化成地方官員的晉升壓力后,在強制性減排強度越大的城市,污染密集型行業(yè)中的民營產(chǎn)出開始受到抑制。如果我們把民營企業(yè)樣本縮小到低生產(chǎn)率企業(yè)的范圍,結(jié)果如列(5)—列(8)所示,可以看到,對于本來生產(chǎn)率就較低的民營企業(yè)而言,由于承擔(dān)環(huán)境成本的空間有限,在2006年開始實施規(guī)定后,污染密集程度越高的低效率企業(yè)產(chǎn)出規(guī)模明顯萎縮,顯示出強制性減排政策對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具有較強的抑制效應(yīng)。因此,H2部分得到驗證。
(二)強制性減排政策對民營企業(yè)進入和退出的影響
對于非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來說,即便能夠在短期內(nèi)避免由環(huán)保高壓帶來的成本增加而產(chǎn)出下降,但也難以擺脫上下游關(guān)聯(lián)以及價格傳導(dǎo)機制造成的間接影響。強制性減排政策通過清洗作用[25]推動工業(yè)結(jié)構(gòu)進一步升級,主要表現(xiàn)為低層次企業(yè)退出和高層次企業(yè)進入。環(huán)境績效約束對所有產(chǎn)業(yè)和民營企業(yè)都產(chǎn)生了一種強制性清洗作用[29],正是這種“過濾效應(yīng)”推動民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進一步升級。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低層次企業(yè)退出。由于無法在內(nèi)外交困的生存夾縫中進行生產(chǎn)效率的提高和生產(chǎn)方式的轉(zhuǎn)變,也未能增加研發(fā)投入以創(chuàng)新效應(yīng)沖抵成本沖擊的負(fù)面影響,無論是否處于污染密集度行業(yè),部分低層次民營企業(yè)將被市場淘汰。二是高層次企業(yè)進入。由于上下游供應(yīng)鏈的傳導(dǎo)機制,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整體生產(chǎn)成本隨之增加,減排目標(biāo)約束和環(huán)境績效考核將提升新進民營企業(yè)的市場門檻,為高技術(shù)密集度的清潔型企業(yè)發(fā)展提供更為優(yōu)越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從而優(yōu)化民營企業(yè)流入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本文通過構(gòu)建DDD模型(5)來驗證不同R&D投入強度的行業(yè)在環(huán)境規(guī)制下對民營企業(yè)進入和退出的影響。,以此證明民營企業(yè)中存在著低技術(shù)層次企業(yè)退出和高技術(shù)層次企業(yè)進入的事實,從而推動了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
其中,NumberEnter/Exitict表示進入或退出民營企業(yè)數(shù)量占行業(yè)總企業(yè)數(shù)量的百分比。
表7是強制性減排政策對民營企業(yè)進入和退出影響的回歸結(jié)果,列(1)—列(4)是進入情況的回歸結(jié)果,三重交互項RTct×Postt×R&Di的系數(shù)顯著為正,說明強制性減排強度越大的城市,越能在R&D投入強度的行業(yè)中吸引新進入的民營企業(yè),驗證強制性減排政策使得市場門檻有所提升,民營企業(yè)若想要進入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較高而減排壓力較大的城市時,生產(chǎn)類型需要偏向于R&D投入強度較高的行業(yè)。表7列(5)—列(8)是退出情況的回歸結(jié)果,三重交互項RTct×Postt×R&Di的系數(shù)均顯著為負(fù),說明強制性減排強度越大的城市,在R&D投入強度小的行業(yè)中退出的企業(yè)數(shù)量越多,處于低技術(shù)密集度層次的民營企業(yè)會被迫退出市場。因此,H2部分得到驗證。
(三)強制性減排政策對民營企業(yè)創(chuàng)新行為的補償效應(yīng)
為彌補環(huán)保高壓下合規(guī)成本激增帶來的負(fù)面影響,企業(yè)需要依賴技術(shù)創(chuàng)新轉(zhuǎn)變生產(chǎn)方式、提高生產(chǎn)率,即波特假說中的創(chuàng)新補償效應(yīng)[1]。然而,從靜態(tài)的角度來看,現(xiàn)有的產(chǎn)業(yè)生態(tài)、技術(shù)環(huán)境和分工組織會對企業(yè)的經(jīng)營模式產(chǎn)生鎖定作用,當(dāng)引入環(huán)境規(guī)制時只會增加企業(yè)的生產(chǎn)成本,因此,環(huán)境規(guī)制對企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凈效應(yīng),由創(chuàng)新補償效應(yīng)和合規(guī)成本效應(yīng)的大小決定。此外,技術(shù)推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通常導(dǎo)致創(chuàng)新補償效應(yīng)落后于合規(guī)成本效應(yīng)。在短期內(nèi),環(huán)境法規(guī)將抑制企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但從長遠(yuǎn)來看,環(huán)境監(jiān)管將刺激企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對處于相對發(fā)展劣勢的民營企業(yè)來說,面臨強制性減排政策壓力時,唯有技術(shù)創(chuàng)新是促進長久發(fā)展的唯一路徑。為驗證強制性減排政策是否對民營企業(yè)創(chuàng)新行為有補償效應(yīng),從而間接推動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本文構(gòu)建了DID模型如下:
其中,Innovfct代表專利申請數(shù)量。X代表一系列企業(yè)和地區(qū)層面的控制變量,企業(yè)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yè)年齡(lnage)、規(guī)模(lnsacle,使用企業(yè)總資產(chǎn)對數(shù)表示)、企業(yè)現(xiàn)金資產(chǎn)比率(ncfoa,使用現(xiàn)金資產(chǎn)占企業(yè)總資產(chǎn)比率作為代理變量),城市層面的控制變量與模型(1)相同。表8是強制性減排政策對民營企業(yè)創(chuàng)新行為補償效應(yīng)的回歸結(jié)果,2006年強制性減排政策和2009年環(huán)境績效考核政策的實施對上市民營企業(yè)的發(fā)明專利申請數(shù)量和R&D經(jīng)費投入強度均表現(xiàn)出正向作用,且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強制性減排政策對民營企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水平的提高具有較強的解釋力。為了彌補環(huán)境規(guī)制成本和提升競爭力,民營企業(yè)加大了研發(fā)投入的力度,強制性減排政策的創(chuàng)新補償效應(yīng)發(fā)揮出重大作用,具體體現(xiàn)在企業(yè)所獲專利數(shù)量得到明顯提升,同時企業(yè)的技術(shù)密集度也在逐漸增大,民營企業(yè)趨向于向更高層次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發(fā)展。因此,H2部分得到驗證。
六、研究結(jié)論與政策建議
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fā)展理念,建設(shè)美麗中國依賴于環(huán)境治理體系的制度保障。自“十一五”規(guī)劃以來實施的強制性減排政策和2009年實施的環(huán)境績效考核政策打破了長久以來中國環(huán)境治理體系的中央與地方二元對立模式,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持續(xù)改善具有重大意義,也對各類經(jīng)濟活動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在環(huán)境規(guī)制受到綠色績效而產(chǎn)生的約束性日益增強的現(xiàn)實情況之下,這一制度性改革能否成為協(xié)調(diào)經(jīng)濟增長和環(huán)境保護的關(guān)鍵路徑需要進一步檢驗。為此,本文通過手工收集“十一五”規(guī)劃以來中國230個地級市強制性減排強度數(shù)據(jù),以民營企業(yè)為研究對象,運用雙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工具變量法以及一系列穩(wěn)健性檢驗,實證分析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的影響及機制。研究結(jié)果顯示:首先,強制性減排政策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有正向促進作用,并且這種促進作用會隨著環(huán)境績效考核政策的實施得以強化。其次,與“十一五”規(guī)劃中強制性減排政策的制定相比,2009年環(huán)境績效考核政策的實施對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的影響更為明顯。最后,強制性減排政策通過對污染密集型民營企業(yè)的抑制效應(yīng)、對民營企業(yè)進入和退出的影響以及對民營企業(yè)創(chuàng)新行為的補償效應(yīng)等途徑促進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
基于上述研究結(jié)論,筆者提出如下建議:首先,建立環(huán)境監(jiān)管垂直管理制度,給予地方環(huán)保部門管理獨立性,增強強制性減排政策實際效果。本文的實證結(jié)論證實,2006年后不斷完善的環(huán)境績效制度是一種能改善環(huán)境質(zhì)量并倒逼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的雙贏工具,因此為確保環(huán)境績效制度的有效性,需不斷減少地方政府對環(huán)境規(guī)制實施的行政干預(yù),給予地方環(huán)保部門獨立執(zhí)法權(quán)力。其次,強化對民營企業(yè)的環(huán)保專項資金支持,鼓勵民營企業(yè)取得先動優(yōu)勢。增加對民營企業(yè)環(huán)保項目的財政支持,鼓勵民營企業(yè)開展自愿型環(huán)保投入,采取高于環(huán)境規(guī)制標(biāo)準(zhǔn)所要求的污染防治措施,從而面對趨嚴(yán)的環(huán)境規(guī)制形成先動優(yōu)勢。最后,促使生產(chǎn)要素充分流動,利用環(huán)境規(guī)制倒逼工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的關(guān)鍵在于為民營企業(yè)創(chuàng)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保證生產(chǎn)要素跨部門的充分流動,并對民營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行為給予支持。
參考文獻(xiàn):
[1] Porter, M. E.,Van Der Linde, C. Towards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4(4):97-118.
[2] Vogel, D. Trading up and Governing Across: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997, 4(4):556-571.
[3] Lanoie, P., Laurent-Lucchetti, J., Johnstone, 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New Insights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J].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11, 20(3):803-842.
[3] Rubashkina, Y., Galeotti, M., Verdolini, 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 From European Manufacturing Sectors[J]. Energy Policy, 2015, 83(8):288-300.
[4] 包群,邵敏,楊大利.環(huán)境管制抑制了污染排放嗎?[J].經(jīng)濟研究,2013,(12):13-28.
[5] 李勝蘭,初善冰,申晨. 地方政府競爭、環(huán)境規(guī)制與區(qū)域生態(tài)效率[J]. 世界經(jīng)濟,2014,(4):88-110.
[6] 沈坤榮,金剛,方嫻. 環(huán)境規(guī)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轉(zhuǎn)移嗎? [J]. 經(jīng)濟研究,2017,(5):44-59.
[7] 王紅建,湯泰劼,宋獻(xiàn)中. 誰驅(qū)動了企業(yè)環(huán)境治理:官員任期考核還是五年規(guī)劃目標(biāo)考核[J]. 財貿(mào)經(jīng)濟,2017,(11):147-160.[9] 龍文濱,胡珺. 節(jié)能減排規(guī)劃、環(huán)保考核與邊界污染[J]. 財貿(mào)經(jīng)濟,2018,(12):128-143.
[16] Levinson, A., Taylor, M. S. Unmasking the Pollution Haven Effect[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8, 49():223-254.
[7] 鄭石明. 政治周期、五年規(guī)劃與環(huán)境污染——以工業(yè)二氧化硫排放為例[J]. 政治學(xué)研究,2016,(2):80-94.
[8] 金碚. 關(guān)于“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經(jīng)濟學(xué)研究[J]. 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2018,(4):5-18.
[9] 龍小寧,萬威.環(huán)境規(guī)制、企業(yè)利潤率與合規(guī)成本規(guī)模異質(zhì)性[J].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2017,(6):155-174.
[10] Chen, Z., Kahn, M. E., Liu, Y. The Consequences of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Water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China[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8, 88(5):468-485.
[11] Burton, D. M., Gomez, I. A., Love, H. A.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st and Industry Structure Changes[J]. Land Economics, 2011, 87(3):545-557.
[12] Wang, H., Nlandu, M., Susmita, D., et al.Incomplete Enforcement of Pollution Regulation:Bargaining Power of Chinese Factories[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2.
[13] 傅京燕,李麗莎. 環(huán)境規(guī)制、要素稟賦與產(chǎn)業(yè)國際競爭力的實證研究——基于中國制造業(yè)的面板數(shù)據(jù)[J].管理世界,2010,(10):87-98.
[14] 劉瑞明,石磊. 國有企業(yè)的雙重效率損失與經(jīng)濟增長[J]. 經(jīng)濟研究,2010,(1):127-137.
[15] Acemoglu, D., Aghion, P., Bursztyn, L.,et al.The Environment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1):131-166.
[16] 張平,張鵬鵬,蔡國慶. 不同類型環(huán)境規(guī)制對企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影響比較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2016,6(4):8-13.
[17] 聶輝華,江艇,楊汝岱. 中國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的使用現(xiàn)狀和潛在問題[J]. 世界經(jīng)濟,2012,(5):142-158.
[18] 韓永輝,黃亮雄,王賢彬. 產(chǎn)業(yè)政策推動地方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了嗎?——基于發(fā)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論解釋與實證檢驗[J].經(jīng)濟研究,2017,(8):33-48.
[19] Manova, K.Credit Constraints, Equity Market Liberal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76(2):33-47.
[20] 劉偉,張輝,黃澤華. 中國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度與工業(yè)化進程和地區(qū)差異的考察[J]. 經(jīng)濟學(xué)動態(tài), 2008,(11):4-8.
[21] Balland, P., Boschma, R., Crespo, J.,et al.Smart Specialization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Relatedness, Knowledge Complexity and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J]. Regional Studies, 2019, 53(9):1252-1268.
[22] Hidalgo, C. A., Hausmann, R. The Building Blocks of Economic Complexity[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 106(26):10570-10575.
[23] Chen, L., Xu, L., Xu, Q.,et al.Optimization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Under the Low-Carbon Goal and the Water Constraints:A Case in Dalian,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6,114(2):323-333.
[24] He, G., Fan, M., Zhou, M. Th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Mortality in China:Evidence From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6, 79(9):18-39.
[25] 武建新,胡建輝. 環(huán)境規(guī)制、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與綠色經(jīng)濟增長——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證檢驗[J]. 經(jīng)濟問題探索, 2018,(3):7-17.
(責(zé)任編輯:孫 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