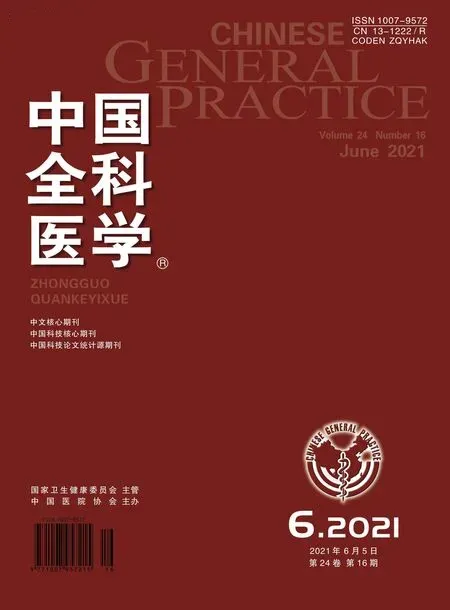中國流動人口就醫行為選擇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張檢,蔡金龍,黃元英,何中臣,唐貴忠*
我國仍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人口流動遷移持續活躍,2017年流動人口規模達2.445億,并由快速增長期逐漸進入調整期[1]。《“十三五”全國流動人口衛生計生服務管理規劃》中指出,加強流動人口衛生計生服務管理,是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內在要求,也是增強流動人口獲得感的迫切需要[2]。長期以來,流動人口醫療衛生服務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結構性不合理,其健康權益和醫療需求無法得到充分滿足[3-4]。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促使區域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問題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現階段,學界針對流動人口醫療衛生服務均等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不平等性與異質性分析,針對流動人口醫療衛生服務需求與實際滿足之間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5-6]。就醫行為泛指人們在有病感或出現某種癥狀時尋求醫療幫助的社會行動,是反映醫療衛生服務需求、供給、利用水平的綜合指標[7-8]。本研究利用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分析了我國流動人口就醫行為選擇及其影響因素,旨在為提高流動人口基本醫療服務可及性提供決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于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1]。該調查采用分層、三階段、與規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樣方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PPS),以在流入地居住1個月及以上、非本區(縣、市)戶口的15周歲及以上流動人口為調查對象,累計調查了全國3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169 989例流動人口。調查內容涵蓋家庭成員與收支情況、就業情況、流動及居留意愿、健康與公共服務、社會融合5個部分。因覆蓋面廣、樣本量大,調查數據已廣泛應用于流動人口公共服務、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等領域研究,被證實具備較高的代表性與可靠性[1-2,5]。本研究申請獲得數據。
1.2 研究方法 2020年7月,基于研究目的對監測調查數據進行提取、整理與分析。本研究將流動人口兩周患病的就醫行為選擇作為因變量。第一步,依據健康與公共服務部分“您本人是否有患病(負傷)或身體不適的情況?”,共篩選出10 996例兩周內患病的流動人口;第二步,依據“最近一次患病(負傷)或身體不適時,您首先去哪里看的病/傷?”對就醫行為選擇進行歸類和整理,將“哪也沒去,沒治療”和“本地藥店”合并為“自我治療”,“本地社區衛生站(中心/街道衛生院)”和“個體診所”合并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本地綜合/專科醫院”不做處理,“在老家治療”和“本地和老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合并為“老家/外地就醫”。
基于Andersen醫療衛生服務利用模型,結合流動人口流動行為特征選取以下4方面14項指標構建分析框架:(1)傾向特征,指流動人口選擇不同就醫行為所具備的個性特征,包括人口學特征(性別、年齡)和社會結構特征(文化程度);(2)流動特征,指個體流動行為所具備的可能影響公共服務利用的特征,包括流動范圍、流動時間和落戶意愿;(3)使能資源,指促進或阻礙個人衛生服務可得性的因素,包括地區、城鄉、到最近醫療機構時長、家庭人均年收入和醫療保險;(4)需求因素,指影響個人衛生服務利用的最直接因素,包括自評健康、慢性病患病和健康檔案建檔情況[9]。
1.3 相關概念界定 (1)流動范圍與流動時間,均指最近一次流動行為,其中進入流入地期間離開不超過1個月,再次返回時不作為一次新的流動;(2)地區與城鄉,均指現居住地(流入地),而非戶籍所在地(流出地);(3)到最近醫療機構時長(min),以自身最易獲得的交通方式到最近的醫療服務機構(包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村居醫務室、醫院等)需要的時長;(4)慢性病患病,經醫生確診患有高血壓、2型糖尿病兩類最常見慢性病;(5)健康檔案,未建立健康檔案包括明確回答“未建立”和在流入地居住不足6個月的流動人口。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軟件進行數據整理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相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及方差齊性以(±s)表示。采用逐步回歸法構建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影響流動人口就醫行為選擇的因素。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流動人口兩周患病率為6.47%(10 996/169 989)。其中,女5 873例(53.41%),男5 123例(46.59%);年齡16~95歲,平均年齡(37.9±12.2)歲;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2 562例(23.30%),初中4 611例(41.93%),高中/中專2 177例(19.80%),大專996例(9.06%),本科及以上650例(5.91%);流動范圍為跨省流動5 136例(46.71%),省內跨市3 728例(33.90%),市內跨縣2 132例(19.39%);流動時間≤2年3 424例(31.14%),3~5年2 565例(23.33%),6~10年2 575例(23.42%),>10年2 432例(22.12%);4 184例有在流入地落戶的意愿(38.05%);流入地區為東部4 209例(38.28%)、中部1 729例(15.72%)、西部4 181例(38.02%)和東北877例(7.98%);居住在城市8 017例(72.91%),農村2 979例(27.09%),城鄉人口比為2.69∶1。
2.2 流動人口就醫行為選擇現況 共4 467例選擇自我治療,兩周患病未就診率為40.62%(4 467/10 996)。共6 529例選擇各類醫療衛生機構就診,兩周患病就診率為59.38%(6 529/10 996),其中選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者占比65.46%(4 274/6 529),選擇綜合/專科醫院者占比32.06%(2 093/6 529),選擇老家/外地就醫者占比2.48%(162/6 529)。
2.3 不同流動行為特征的流動人口就醫行為選擇的比較 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流動范圍、流動時間、落戶意愿、地區、城鄉、到最近醫療機構時長、家庭人均年收入、醫療保險、自評健康、慢性病患病、健康檔案情況的流動人口就醫行為選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不同流動行為特征的流動人口就醫行為選擇的比較〔n(%)〕Table 1 Choices of healthcare utilization in floating population by personal factors

(續表1)
2.4 影響流動人口就醫行為選擇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將流動人口就醫行為選擇作為因變量(賦值:自我治療=0,基層醫療衛生機構=1,綜合/專科醫院=2,老家/外地就醫=3),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14項指標作為自變量并依次賦值,采用逐步回歸法(α入=0.05,α出=0.10)構建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多重共線性診斷結果顯示,所有方差膨脹因子VIF<10(VIFmax=1.448),提示數據中不存在多重共線性。Cox及Snell、Nagelkerke、McFadden三個偽R系數分別為0.192、0.203和0.144,提示模型擬合狀況良好。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分析框架中所包含的傾向特征(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流動特征(流動范圍、流動時間、落戶意愿)、使能資源(地區、城鄉、到最近醫療機構時長、家庭人均年收入、醫療保險)和需求因素(自評健康、慢性病患病、健康檔案)4方面14項指標均會對流動人口的就醫行為選擇產生影響(P<0.05,見表2)。

表2 影響流動人口就醫行為選擇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Table 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oice of healthcare utiliz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3 討論
3.1 流動人口就醫主動性整體較差,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就診率偏高 流動人口兩周患病就診率僅為59.38%,遠低于“第五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中我國常住人口兩周患病就診率84.5%[10],略低于“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中農村勞動力兩周患病就診率62.61%[11],提示流動人口就醫主動性整體較差,衛生服務利用不足。機構選擇上,流動人口基層就診率達65.47%,明顯高于《2017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就診率54.2%[12]。就醫主動性低下伴隨的基層就診率偏高,一方面反映出流動人口健康意識淡薄,對自身健康關注不夠;另一方面反映出我國異地就醫政策在結算模式、報銷依據、行為引導等方面的窘境,導致流動人口患者由于流入地就醫自付比例高、次均費用高而喪失支付能力,繼而放棄就醫或“就低不就高”[13]。針對流動人口主動利用和被動利用均較低的現況,應加快完善流動人口衛生服務供給體系的頂層設計,從體制、制度和技術3個層面優化異地就醫實時結算政策,并大量開展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項目,以引導其合理就醫并理性選擇就醫機構[14]。
3.2 不同社會人口學特征、流動特征流動人口的就醫行為選擇存在差異 研究再次證實了性別、年齡、文化程度3項社會人口學特征是影響就醫行為選擇的共性因素,與既往研究一致[15],文化程度較低者更傾向于基層就診,而女性、>60歲、本科及以上流動人口更傾向于選擇綜合/專科醫院就醫。需要指出的是,學歷低者、高齡老人作為流動人口中兩類弱勢群體,其就醫行為應給予重點引導。流動特征方面,由于自身分散性大、流動頻繁等特點,流動人口與流入地戶籍人口在醫療服務利用方面存在一定差距[4-5]。本研究中,跨省和省內跨市流動人口的就醫主動性更差,而流動時間>10年和有落戶意愿的流動人口更傾向于選擇綜合/專科醫院就醫。究其原因,流動人口流動方式、在流入地的居住時間和居住條件等,都會對其生活幸福感和定居意愿產生顯著作用,而有定居意愿的流動人口更可能主動地尋求與戶籍人口同質化的公共服務[16]。上述結論也提示,強化流動與戶籍人口在日常生活方式、社會交往/參與、地方文化等多維度的社會融合,有助于提升區域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
3.3 醫療服務可及性是影響流動人口就醫行為選擇的關鍵因素 醫療服務的距離與費用可負擔性是影響居民就醫行為選擇的關鍵因素[17]。文獻復習發現,從醫療保險覆蓋率、住院服務利用率等評價指標看,東北地區流動人口醫療服務供給與利用水平明顯低于其他經濟區域,本研究中東北地區流動人口兩周患病就診率僅為47.66%,低于東、中、西部地區,且相比經濟較發達省市的差距更為明顯,如湖北省和廣州市(72.8%和55.0%)[18]。此外,農村流動人口基層就醫可能性更大,而到最近醫療衛生機構時長超過30 min的流動人口選擇老家/外地就醫的可能性更大,這與李冬冬等[19]研究發現一致。鑒于此,應注重醫療衛生資源配置與使用的科學性和協調性,尤其在東北地區、農村地區和流動人口密集區域,建議縮短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半徑以構建距離科學合理的就醫格局。
費用可負擔性方面,較高的經濟收入易于解除居民對就醫成本的敏感性,擴大醫療選擇權,繼而帶來就醫行為的正向改變,本研究證實,高收入者更傾向于選擇綜合/專科醫院、老家/外地就醫。此外,醫療保險作為一種疾病風險共擔的有效機制,是流動人口享有基本醫療服務的前提和保障[20],本研究中流動人口參保率僅為90.92%,低于我國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95.1%[10],其中只在戶籍地參保占比達到63.78%。較低的流入地醫保覆蓋率和異地就醫政策的不完善制約了流動人口的就醫行為,繼而誘發“小病不就醫”和“大病回鄉醫”,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流入地和戶籍地兩地都參保、只在流入地參保的流動人口更傾向于選擇綜合/專科醫院就醫。鑒于上述,應進一步提高醫療保險的統籌層次,充分做好異地就醫結算服務及醫療保險關系轉移接續的相關手續辦理工作,為更好地促進和改善流動人口就醫行為提供經濟基礎。
3.4 個體健康需求是影響流動人口就醫行為選擇的最直接因素 對軀體健康狀況的自我評價反映出個體就醫行為選擇時對就醫需求的評估,本研究中,自我評價不健康的流動人口就醫主動性更強,且更可能選擇綜合/專科醫院、老家/外地就醫,這與多項研究一致[4,7,11,17]。同樣,患有慢性病的流動人口更可能選擇綜合/專科醫院就醫,這與關云琦等[18]研究發現不同,但與李海洋等[21]吻合,可能解釋是流動人口是經過健康選擇的群體,所患病種多為癥狀輕微或病程緩慢的疾病,而患有慢性病的流動人口往往只在慢性病急性發作期才會前往診療水平更佳的綜合/專科醫院就診。此外,已建立健康檔案的流動人口選擇基層就診的可能性是未建立者的1.612倍,從側面印證了完善健康檔案制度對提高衛生服務利用、推進基層首診制度落實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22]。鑒于上述,應夯實慢性病管理、健康檔案等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在流動人口中的落實,引導其積極開展自我健康管理,規范就醫行為和就醫秩序。
3.5 本研究的局限與不足 首先,受限于已有的數據庫,既往研究所證實的疾病嚴重程度、交通便利度、醫療服務滿意度等重要因素[23]未納入分析框架;其次,就醫行為選擇“老家/外地就醫”組別的流動人口較少,可能對分析結果的穩定性有一定的影響,且尚未考慮自變量間的中介作用與調節作用,亟待未來研究中進一步深入。
作者貢獻:張檢、蔡金龍、黃元英負責研究設計、統計學處理、結果分析與解釋、論文撰寫與修訂;何中臣、唐貴忠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審校和監督管理,對文章整體負責。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