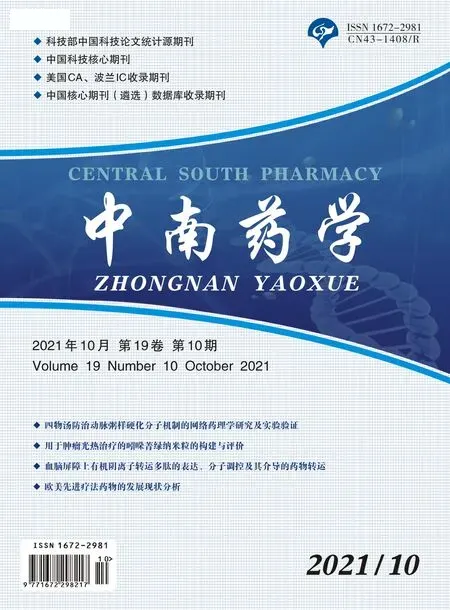補體在肝臟損傷與再生中的作用
陳海霞,黃少杰,陳錦儀,梁瑞敏,趙佳鑫,段佳林*,王婧雯*(1. 陜西中醫藥大學 藥學院,陜西 咸陽 71046;. 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 藥劑科,西安 71003)
補體系統是機體固有免疫和獲得性免疫的橋梁,是機體針對致病性感染的一線防御體系,由30多個不同的血漿蛋白及膜蛋白組成,形成了蛋白酶級聯反應體系[1]。其組成包括可被級聯激活的固有組分、補體調節蛋白及補體受體等[2]。補體與肝臟的關系十分緊密,血漿中80%~90%的補體成分在肝臟合成,補體是一把雙刃劍,在維持宿主內穩態和防御微生物中起著關鍵的作用,然而,激活不足或刺激過度都可能對宿主造成危害,引起微生物易感性增加或者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生[3]。現就補體在肝損傷與再生中的作
用進行綜述,為其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
1 補體系統
補體可識別“自我”和“非我”成分,是機體免疫的重要因子。補體系統可通過經典途徑、旁路途徑和凝集素途徑激活,在C3上匯集形成C3轉化酶,將C3裂解為C3a和C3b。過敏毒素C3a和C5a與C3aR和C5aR受體結合后,啟動下游介質的產生,誘發急性炎癥反應,推動促炎性介質的釋放[4]。C5b募集C6、C7、C8 及C9到靶細胞表面,形成C5b-9(通常稱為TCC),插入膜或釋放到流體相,則形成膜攻擊復合物(membrane attack complex,MAC)[5-6]。它們激活共同的終末途徑,裂解靶細胞,釋放促炎因子,識別并清除入侵微生物,使免疫細胞聚集到炎癥發生部位,這些效應的級聯作用使補體在機體的防御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
2 肝臟損傷與再生
肝臟發生損傷時,一系列信號通路被激活,擴張剩余肝組織,刺激肝臟再生[7-8]。肝再生主要包括三個階段:①啟動階段(G0~G1):白介素-6(interleukin 6,IL-6)和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TNF-α)共同啟動肝臟再生,協同激活G0期肝細胞,使肝細胞由G0期進入G1期[9]。TNF-α與TNF-αⅠ型受體結合后,順序誘導NFκB→IL-6→STAT3,影響核內眾多基因的表達,使肝臟啟動再生功能[10-11]。
②增殖階段(G1~S期):影響肝細胞周期的主要為TNF-α、表皮生長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肝細胞生長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和轉化生長因子-α(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alpha,TGF-α)等促有絲分裂的生長因子[12-13]。當肝葉部分切除或其他原因產生殘缺肝細胞后,剩余的肝實質細胞及非實質細胞會有序地進入增殖狀態,以此來補充肝細胞的數量及維持肝臟的功能[8]。
③終止階段(G1~G0期):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與TGF-β受體相互作用從而參與有絲分裂的終止,誘導細胞凋亡,使大多數肝細胞恢復到靜止狀態[14]。
3 補體對不同原因所致肝損傷與再生的調節
3.1 補體與肝部分切除術
大鼠2/3肝切除模型(partial hepatectomy,PH)為肝再生機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礎,是應用最多、最廣的再生研究模型。肝損傷后,病原通過血流激活再生起始因子TNF-α和IL-6的釋放,活化轉錄激活因子NF-κB和STAT-3,上調再生效應因子EGF、TGF-α和HGF的表達,最終啟動肝臟的再生[15]。許多研究結果顯示補體系統參與了切除后肝再生過程,且其中的關鍵組分C3和C5對于肝再生的啟動至關重要。
小鼠肝切除模型中,C3、C5及其受體的阻斷可造成嚴重的再生障礙,有較高的死亡率和明顯的肝實質損傷。C3、C5基因共敲除小鼠,表現出更加嚴重的肝損傷和肝衰竭現象,但及時在術前或術后給予過敏毒素C3a和C5a,病變則可以部分逆轉[15-16]。C3缺失小鼠術后死亡率、壞死和病變程度更高,這是因為C3作為補體系統的中心組分,不僅影響C3a活化產物的生成,還阻礙其下游級聯反應[17]。C3 缺失小鼠術后死亡率、壞死和病變程度更高,這是因為C3作為補體系統的中心組分,不僅影響C3a活化產物的生成,還阻礙其下游級聯反應,如C5的活化和作用等,因此,C3缺失對于動物肝再生的影響較C5缺失更為嚴重,但C3和C5基因共敲除鼠中肝受損的疊加效果說明C5依然具有相對獨立的作用,這應該與其在庫普弗細胞上的受體(C5aR)相互作用有關[17]。可見,C3和C5這兩種補體成分,在肝再生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3.2 補體與化學性肝損傷
化學性肝損傷是指化學性肝毒性物質所造成的肝損傷,常用的模型是CCl4急性肝損傷模型[18],能造成肝實質的凋亡和損傷[19]。CCl4通過細胞色素P450 2E1(cytochrome P450 2E1,CYP2E1)在肝中代謝,產生三氯甲基自由基,干擾肝中的氧化還原穩態,引起氧化應激,促進脂質過氧化,最終造成肝細胞損傷[20]。在毒性肝損傷過程中,補體促進肝再生功能同樣存在。
C5缺失小鼠CCl4毒性損傷后,肝臟嚴重受損,出現持續性、彌散性的實質損傷和壞死,肝細胞進入S期明顯延遲,而給予小鼠C5或C5a后能顯著恢復肝細胞再生[21]。C3與C5一樣,對CCl4毒性肝損傷的再生也有影響,C3經歷兩次激活,分別于2 h和48 h達到峰值。C3缺失小鼠CCl4損傷后肝再生受損,凋亡和壞死細胞清除延遲,補充C3a則可以恢復[16]。因此,C3、C5以及先天免疫應答中的促炎因子C3a和C5a都可能是毒性損傷后肝再生的重要條件,結合它們在肝切除后所起的相似作用,說明它們在兩種模型中具有相似的肝再生調節作用。
3.3 補體與酒精性肝損傷
酒精性肝病是一種發病率高的肝臟疾病,酒精的急、慢性作用都能夠抑制肝再生[22-23],其機制可能與乙醇代謝產生自由基,引起脂質過氧化以及抗氧化劑的耗竭有關,繼而引起肝損傷和炎癥反應[24],最終導致疾病發生[25]。補體作為免疫防御的重要組分,其活化及其介導的免疫調節和效應放大,會加劇酒精肝損傷的作用。
C3缺失小鼠可耐受或顯著減輕酒精誘導的急性或慢性肝臟脂肪變性,表現出肝臟保護作用[26]。C5缺失小鼠則沒有表現出保肝作用,但血清中谷丙轉氨酶(ALT)和肝臟炎癥反應均下降[27]。補體調節蛋白CD55/DAF,抑制激活C3,減輕三酰甘油聚集,延緩酒精性肝病的病程,而CD55/DAF功能的缺失則會增強酒精誘導肝脂肪變性,加劇肝臟損傷和炎癥反應[27]。也有研究發現C3激活產物C3a和Asp(C3a-des-Arg)在肝臟脂肪變性的發生發展中起關鍵作用,通過CYP2E1調節甘氨酸轉移tRNA(Gly-tRF)的表達,揭示了補體介導的Gly-tRFs促進脂肪生成和抑制脂肪酸β氧化的新機制[28]。
因此,需要進一步探究補體各組分在疾病過程中的機制和作用,為酒精性肝臟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提供依據。值得注意的是,C3活化的補體抑制劑和Gly-tRF抑制劑治療可能是酒精性脂肪肝潛在的治療方法。
3.4 補體與病毒性肝損傷
病毒性肝炎是由多種病毒引起的肝臟炎癥,具有高發病率和強傳染性的特點。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構成急性肝炎的主體,是發展為慢性肝病、肝硬化和肝癌的重要誘因[29]。盡管其機制尚不明確,但免疫應激及其導致的損傷發揮了重要作用[30]。近年來,關于補體與病毒性肝病的關系也有一些報道。
在研究病毒性肝炎自身防御的實驗中發現,部分HCV病毒表面能夠表達補體調節蛋白CD59,CD59通過抑制MAC的生成,使病毒逃避補體系統的攻擊,而CD59功能的喪失會增強補體對HCV病毒的破壞[31]。另有研究發現,HCV核心蛋白引發的炎癥、脂肪變性、纖維化等病變與補體(C3)的上調有關,注射補體調節因子CD55可抑制炎癥[32]。同時,補體C4、C5的血清濃度與肝纖維化程度也顯著相關,可作為評價肝纖維化的指標,此外,C4也可作為評價干擾素和利巴韋林治療HCV感染的指標[33-34]。
Qu等[30]研究發現,在HBV轉基因動物肝臟中補體調節因子CD59水平明顯下降,HBV感染患者肝臟中也存在同樣現象,提示補體活化在HBV感染過程中具有致病效應。乙型肝炎核心抗原(hepatitis B core antigen,HBcAg)是一種病毒衣殼蛋白,誘導HBV感染肝細胞中固有免疫蛋白toll樣受體2(toll-like receptor 2,TLR2)的改變[35],抑制IL-6、IL-12和TNF等基因的表達,影響HBV感染肝細胞的生理功能[36-38]。HBcAg與補體系統相關的膜分子CD59相互作用,下調其表達,增加肝細胞對補體的敏感性,最終促使慢性HBV感染期間肝損傷的發生[39]。因此,抑制HBc-CD59的相互作用可以預防HBV感染引起的炎癥性肝病的發生,阻斷這一過程可能是對抗這些疾病的潛在途徑。
3.5 補體與肝缺血再灌注損傷
肝缺血再灌注損傷(hepatic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HIRI)是肝臟手術的主要并發癥,包括肝移植、肝切除和創傷手術[40]。缺血是由于供氧不足導致血流中斷,擾亂細胞代謝所致。再灌注可恢復血流、氧傳遞和組織pH值,從而加劇缺氧或缺氧引起的細胞損傷[41-42]。肝臟損傷后,補體系統被激活,中性粒細胞聚集,增加血管通透性,引發炎癥,造成細胞損傷[43]。因此,補體可以減輕大鼠HIRI,提高肝臟的再生能力。
可溶性補體受體1(soluble complement receptor,sCR1)的治療可有效降低C3活化,改善微血管循環,減少黏附性白細胞[43]。PMX53是C5aR1拮抗劑,它能降低HIRI后肝酶水平,減少嗜中性粒細胞浸潤,使全HIRI的死亡率下降[44]。使用融合蛋白CR2-CD59靶向抑制補體,在小鼠HIRI模型中也有顯著的治療效果[45],它既保護宿主免疫又能提高生物利用度,但CR2-CD59的抑制作用對C3和C5并沒有影響,這使得C5a和C3a在HIRI局部繼續發揮作用[45]。CR2-CD59不同于其他目前可用的補體抑制劑,是一種很有前途的無毒治療方法,可在多種臨床環境下保護肝臟免受損傷并促進再生[46]。因此,在HIRI中,補體的激活平衡了損傷和保護之間的微調效應,但這種相互作用機制需進一步研究。
3.6 補體與自身免疫性肝病
自身免疫性肝病(autoimmune liver diseases,AILDs)是自身免疫介導的肝細胞和/或膽管上皮細胞慢性炎癥損傷性疾病[47],主要包括自身免疫性肝炎[48](autoimmune hepatitis,AIH)、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PSC)及其重疊綜合征等,其發病機制與免疫反應關系密切。補體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有著重要作用,但在自身免疫性肝病中的作用并不明確。
有研究發現,與健康人和對照小鼠相比,AIH小鼠模型和AIH患者血漿中的C3水平均升高,83%的兒科AIH患者中存在C4d沉積[49],在乙型肝炎患者中也同樣發現了C4d沉積[26],而尚無補體在成人AIH患者中作用的報道。研究發現,PBC患者血漿中C3和C4水平較健康對照組升高[50],在酒精性肝炎和病毒性肝炎中也存在同樣的情況,但在肝硬化PBC患者中C3和C4水平則下降。在PSC患者和膽總管結石患者的血漿中C3水平較健康對照組升高,而PSC和健康對照組之間的C4水平則沒有發現差異,提示炎癥可能是導致C3水平升高的原因之一[51]。綜上所述,盡管補體系統參與了各種自身免疫性疾病和一些肝臟疾病,但補體在AIH、PBC和PSC中的作用似乎有限。
4 結果與討論
肝臟是最能發揮補體作用的器官,它不僅是補體蛋白的主要來源,對補體的攻擊也有極強的耐受性。補體系統是機體內先天免疫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組織防御外來侵害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充分闡明補體在各種免疫介導疾病中的確切作用是開發有效治療性補體調節藥物的巨大挑戰。
近年來補體藥物領域的研究飛速發展,自2007年首個C5抑制單抗批準上市之后,已有數十種在研藥物用于不同適應證的開發。2007年,FDA批準了補體領域第一個藥物——依庫珠單抗(eculizumab,Soliris,Alexion Pharm),其為針對C5的補體特異性藥物,用于治療罕見病突發性睡眠性血紅蛋白尿癥(PNH),并隨后將適應證擴展為非典型溶血尿毒綜合征(aHUS),乙酰膽堿受體自身抗體陽性的廣泛性重癥肌無力(gMG),以及水通道蛋白AQP4自身抗體陽性的視神經脊髓炎譜系障礙(NMOSD)。2008年,重組血漿絲氨酸C1脂酶抑制劑C1-INH(Cinryze)獲批用于遺傳性血管水腫,盡管C1-INH不是一種嚴格的補體特異性藥物,但其發現推動了幾項針對經典激活和凝集素激活途徑的聯合靶向臨床試驗治療。
目前臨床開發的補體藥物種類主要為多肽和單克隆抗體,個別為小分子和SiRNA,其中絕大多數適應證為罕見病。但是否能擴展至常規免疫用藥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到目前為止,補體領域臨床獲批藥物僅有一款Soliris,包括其優化后的長效版本raculizumab(Ultomiris,Alexion Pharm),顯然不能滿足臨床需求。在未來,大型肝臟手術后,補體調節藥物可能有助于預防補體介導的肝臟損傷,促進肝臟再生。雖然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隨著科技的迅速發展,補體可能成為在各種臨床環境中優化肝臟獨特生理特征的關鍵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