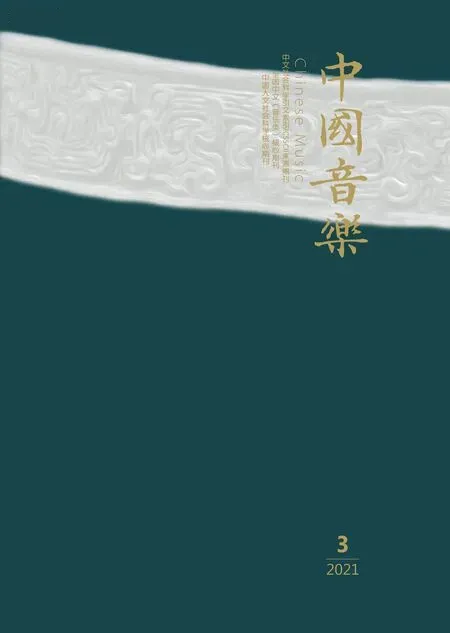唐代琵琶巫卜風俗考
○ 陳岸汀
唐代琵琶藝術發(fā)展輝煌。琵琶廣泛活躍于社會各階層,存見于不同的社會文化領域。在漢唐琵琶音樂文化功能的變遷中,琵琶不僅以樂器身份逸響于殿堂、宅院,播之茶肆、酒樓,活躍在權貴、精英、百姓的音樂生活中在某些條件下,琵琶也成為民間巫卜活動中的通靈器物,通過彈奏琵琶占卜算命、招魂續(xù)命,同時,琵琶也在民間信俗迎神賽會中棖棖作響,娛樂神人,形成了有琵琶參與的唐代巫卜風俗亞文化現(xiàn)象。
本文主要關注唐代筆記小說、詩歌等文獻史料中的琵琶占卜、巫術和民間信仰崇拜活動,就唐代琵琶巫卜風俗的內容、特點、功能與文化內涵等進行音樂學分析。
一、民間卜算類——以琵琶為卜器占卜算命
中國傳統(tǒng)的占卜算命,一般以易卦卜筮為主流,但也有其他方式。南北朝劉敬叔的小說《異苑》中,就記錄有一件以琵琶占卜吉兇的事例。①[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六“靈侯”,黃益元校點,載《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49頁。小說中提到,東晉時有蠻岳在姑蘇彈琵琶為人占卜吉兇。其占卜方式是“每占吉兇,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即一邊彈奏琵琶、一邊言說,道出占卜結果。求卜之人是為算仕途,問的是“遷官”之事。按劉敬叔于“予為國郎中,親領此土”判斷,他曾在當?shù)赜H自了解過蠻岳的占卜行為。不過,雖當?shù)貍餮耘谜疾方Y果“事事有驗”,但從“荊州俗諺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來看,除了姑蘇蠻岳卜算者外,當時大眾似乎尚不會將彈奏琵琶與知吉兇聯(lián)系起來,因此解釋為:或曰鬼附身,或曰名為靈侯的老鼠作法等。
時至唐代,在民間卜算行業(yè)中,興起了通過彈琵琶占卜算命、預測吉兇的卜算風俗。唐代張《朝野僉載》中,分別記錄有何婆、阿來婆的琵琶占卜事例。
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數(shù)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弦柱,和聲氣曰:“個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年得三品,更后年得四品。”郭曰:“阿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后年減三品,更后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②[唐]張:《朝野僉載》,恒鶴校點,《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7頁。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琵琶曲調豐富,彈前需調弦,這一舉動原本是琵琶演奏環(huán)節(jié)中的常態(tài)。而在占卜時,卜者是如何將調弦的行為內涵與一般性演奏琵琶的調弦相區(qū)隔,原文記錄沒有做出說明。但是,如果對何婆“調弦柱”占卜行為的關注確有必要,是否可以推測,占卜者或是根據(jù)所卜之人、事,選彈特定的調式樂曲,作為一種方法的運用來進行占卜,也未可知。
在當時長安城中,也有權貴參與以琵琶測吉兇的卜算活動,并且還在“琵琶卜”活動中產生出一位名滿朝廷的琵琶占卜師——居住在長安城崇仁坊的阿來婆。
阿來婆的占卜儀式過程比何婆要詳細、復雜。主要包括三大儀程和七個小步驟。三大儀程:一是請局、二是請神、三是卜算。具體步驟有:(1)卜問者付卜資(一匹綢綾),請局;(2)占卜者彈琵琶;(3)焚香;(4)閉眼向四方神靈唱禱;(5)請卜者禮拜;(6)陳述卜問事項;(7)占卜者察算后給出卜問結果。其中,彈琵琶是在阿來婆焚香、告請神靈的請神行為一列,此時具體事項的卜算尚未開始。從這一點看,先行彈琵琶意味著樂音能上達神靈,與冥冥之中的神靈產生溝通,進而引動神靈示降,卜問的事項也由此可獲得神意。按此,琵琶在卜算中應具有溝通神靈的功能。不過,阿來婆在后續(xù)的“望細看”“決疑惑”卜算過程中,是否為一邊彈琵琶一邊唱出占卜結果,尚不得而知。總之,阿來婆以琵琶巫卜之術聞名長安權貴圈。按《唐兩京城坊考》“崇仁坊”條之“師婆阿來宅”注,阿來婆因“專行厭魅”④“厭魅”指用迷信的方法祈禱鬼神或詛咒。《辭源》“厭魅”條:“陳書后主沈皇后傅附張貴妃:又好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后主。”《辭源》,北京:商務印出館,2009年,第442頁。參與韋氏之亂,最終在宮廷政治斗爭中死于非命。
就事例的代表性與普遍性而言,至遲于唐中宗時期,唐代琵琶占卜已是一項專門化的職業(yè)活動,出現(xiàn)有專職以琵琶算命的“師婆”一行。琵琶作為卜器參與民間占卜,一是承擔請神、溝通獲得神諭的功能;一是用于占卜吉兇、求算仕途。李賀長詩《惱公》中“跳脫看年命,琵琶道吉兇。王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⑤[唐]李賀:《惱公》,《全唐詩》第十二冊卷三百九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4410頁。,記述了詩中女子通過琵琶卜算丈夫仕途之事。可以說,以“琵琶道吉兇”應當是唐代社會的一種較為常見的現(xiàn)象,散落在民間的琵琶卜算從業(yè)人員應當不會太少。至于在民間神祠中,專門由女巫進行琵琶卜算獲取神意的風俗,將于下文從民間信仰崇拜活動的角度再作說明。
二、民間巫術類——以琵琶為法器行巫作法
用琵琶作法,進行招魂、驅邪、續(xù)命等巫術活動,其性質屬于民間巫術范疇。
宋代李昉等編纂的《太平廣記》中,收錄有幾例唐人彈琵琶行巫作法的故事。主要包含為孩童、病人驅邪、招魂,為亡人鬼魂行巫招魂之事。
《太平廣記》“巫”記:“唐郎中白行簡,太和初,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行簡如其言擲之,小兒便驚啼悶絕。店婦曰:‘孩兒中惡。’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彈琵琶召請曰:‘無他故,小魍魎為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為祟。可速作饤饦,取酒。’逡巡陳設。巫者拜謁,二人與行簡就坐,食飽而起。小兒復如故……”⑥[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三“白行簡”,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2258頁。
《太平廣記》“神”記:“……(裴度)后為太原節(jié)度使,家人病,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倒良久,蹶然而起曰……”⑦[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七“裴度”,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2434頁。
兩例故事雖然虛誕,卻含有唐代社會風俗中涉及“驅邪”“招魂”的一般知識。從其所述之事及其判斷、處理來看,符合唐代“琵琶卜”通常的認知和行為方式。如白行簡一例,認為小孩子驚嚇昏厥可能是撞上不干凈的東西(“中惡”)而失魂,處理方式是為其驅邪招魂。驅邪招魂需要請女巫,其行為過程是“焚香,彈琵琶”,結果是“小兒復如故”。裴度一例與此相類。裴度家人生病,請了女巫查看,女巫行的是驅邪之事,行為過程是“彈胡琴,顛倒良久”。“彈胡琴”是行巫中的儀程,女巫以樂音上達神靈、溝通神人,由此道出為裴度家人看病的結果,并讓裴度擇日祭拜神靈。
其中,唐代文獻中有“胡琴”指“琵琶”的情況,如劉景復《夢為吳泰伯作勝兒歌》記載:“歲乙丑,有以輕綃畫侍婢捧胡琴者,名為勝兒,貌踰舊繪,巫方獻舞……奉邀作胡琴一曲以寵之。”⑧[唐]劉景復:《夢為吳泰伯作勝兒歌》,載《全唐詩》第二十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9832–9833頁。實際勝兒所彈是琵琶,詩中用“繁弦”“邏娑撥”“四弦攏撚”“大聲嘈嘈”“小弦切切”等關鍵提法描繪了其琵琶演奏。李賀《感春》有“胡琴今日恨,急語向檀槽”⑨[唐]李賀:《感春》,載《全唐詩》第十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4418頁。、王仁裕《荊南席上詠胡琴妓(一作奉使荊南高從誨筵上聽彈胡琴)》有“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朱弦四十條”⑩[唐]王仁裕:《荊南席上詠胡琴妓》,載《全唐詩》第二十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8401頁。等,“檀槽”或“紫檀槽”“朱弦四十條”都指琵琶的結構特征。白居易《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唐]白居易:《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載《全唐詩》第十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4968頁。、劉禹錫《和楊師皋給事傷小姬英英》?[唐]劉禹錫:《和楊師皋給事傷小姬英英》,載《全唐詩》第十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4066頁。中,“胡琴錚鏦指撥剌”“撚弦花下呈新曲”點出了琵琶的演奏特征;李咸用《昭君》“千秋青冢骨,留怨在胡琴”?[唐]李咸用:《昭君》,載《全唐詩》第十九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7388頁。體現(xiàn)出唐人對琵琶有“胡樂”淵源、用于表達“邊塞情”的音樂意識等。以此,按唐代文獻常見的、一般性的提法,從唐人對“琵琶”淵源、演奏、音樂特質等的認識,包括“彈胡琴”之“彈”的運用,裴度一例中,“彈胡琴”仍有可能指的是“彈琵琶”。
另外,《靈異記》中還有許至雍見亡妻鬼魂的故事。其中,請巫師招魂的過程描述得比較詳細:“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為土人所敬伏,皆趙生之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許生乃知符其妻之說也……乃計其所費之直,果三貫六百耳。遂擇良日,于其內灑掃焚香,施床幾于西壁下,于檐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三更,忽聞庭際有人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吁嗟數(shù)四,應云:‘是。’”?[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三“許至雍”,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2259頁。
這是由男巫實施的招魂活動。按故事所記,巫師收三貫六百錢,為亡人作招魂,即“今召死魂,又今生人見之”。具體行為包括擇良日、焚香、結壇場、彈胡琴。此處“彈胡琴”同樣可能指彈琵琶。
總之,不論招魂結果如何,從文獻所反映的唐人認識來看,唐代民間的巫術活動中,琵琶是巫師用于作法的工具,彈琵琶成為一些民間招魂巫術活動中的特定儀程,巫師通過彈琵琶方式進行驅邪招魂活動。
三、民間信仰崇拜活動中的琵琶
唐代琵琶與民間廟宇神祠的相關性主要發(fā)生在兩個層面:一是在神祠中由巫者彈琵琶宣示神意、卜命吉兇;一是在祀神賽會活動、民俗活動中以琵琶音樂娛樂神人。
1.巫師彈琵琶溝通神靈
在民間信俗活動方面,除了歲時祭祀外,平時百姓到某祠廟進香,也可能遇見持抱琵琶的女巫。廟中女巫為上香的客人彈奏琵琶祈神,從而知兇吉、獲神佑。
女巫遮客買神盤,爭取琵琶廟里彈。聞有馬蹄生拍樹,路人來去向南看。自移西岳門長鎖,一個行人一遍開。?[唐]王建:《華岳廟》,載《全唐詩》第九冊卷三〇一,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430頁。
王建《華岳廟》詩中描述,廟門未開的情況下,女巫們要引香客來廟,會主動在路上攔客,即“女巫遮客買神盤”。事實上,唐代華岳之上所建祠廟較多,眾女巫遮道攔客應為普遍現(xiàn)象,這在白行簡《三夢記》中也有記載。對應“買神盤”的行為,在引香客來廟后,女巫們在廟里為上香者彈琵琶,即“爭取琵琶廟里彈”。“一個行人一遍開”,說明華山上祠廟(或殿堂)的門一般是關上的,只有香客給錢后,才開門讓香客逐一進去。這或許是神靈前女巫彈琵琶與香客祈愿,祠廟方所提供的一對一的特定服務。
可以說,此時的琵琶不是宮廷或城鎮(zhèn)流行音樂空間中追逐演奏技藝的音樂藝術,而是以祠廟環(huán)境為依托,由巫師彈琵琶做巫卜活動,功能在溝通神靈,用以卜命吉兇、獲得神佑。反映琵琶是祠廟活動中溝通媒介的,還有如王叡《祠神歌》詩:“棖棖山響答琵琶,酒濕清莎肉飼鴉。樹葉無聲神去后,紙錢灰出木棉花。”?[唐]王叡:《祠神歌》,載《全唐詩》第十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4361頁。
應當說,類似華岳眾廟巫女彈琵琶的行為活動,已然成為唐代的一種風俗。唐人筆記小說多載士人赴華岳廟求問前程之事。賈竦在未及第時,也曾赴華岳廟求問。在他的敘述中,華岳廟上眾巫覡活動已然成風,“因循作風俗,相與成舊溺”。?[唐]賈竦:《謁華岳廟》,載王重民等《全唐詩外編》“補逸卷之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00頁。
總之,在特定的祠廟環(huán)境中,通過人物身份、場景、涵義,共同構筑了區(qū)別于一般演奏娛樂場合中的琵琶及其音樂功能,體現(xiàn)并加深著唐人對特定的琵琶樂音通靈的認識觀,擴充了唐代琵琶在民間信仰崇拜活動中的生存空間。
2.樂者彈琵琶娛樂神人
傳統(tǒng)社會的民間宗教信仰活動中,比較突出的是地方各路雜神廟宇舉行的迎神賽會、歲時祭祀。到了唐代,民間祀神賽會活動中琵琶的地位被凸顯出來,彈琵琶是這類活動中娛神的重要形式。
王建《賽神曲》詩中描述有民間賽神活動:“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聽神語。新婦上酒勿辭勤,使爾舅姑無所苦。椒漿湛湛桂座新,一雙長箭系紅巾。但愿牛羊滿家宅,十月報賽南山神。青天無風水復碧,龍馬上鞍牛服軛。紛紛醉舞踏衣裳,把酒路旁勸行客。”?[唐]王建:《賽神曲》,載《全唐詩》第九冊卷二九八,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377頁。
此處所述的賽神活動應是請神出廟沿路巡游。據(jù)詩意,賽神隊巡游至某家門前,伴隨著男子彈琵琶女子跳舞,家中主人前來敬拜神靈、“聽神語”,主婦向諸人敬酒,并祈禱。這類琵琶歌舞是屬于賽神巡游的隊伍,還是由某家門中主人所備,難以判斷。行樂人是樂人還是巫覡,也難以查證。能夠明確的是:(1)琵琶和歌舞并置;(2)唱跳演奏發(fā)生在家中主人敬拜神靈、“聽神語”之前;(3)家門夫婦的行為活動核心在獲得神佑而非占卜、驅邪,男子主要是拜聽神語,女子主要是敬酒、祈愿;(4)琵琶音樂不具備獲取神諭的功能。由此,整體判斷琵琶歌舞更偏向于音樂行為,承擔的應當是吸引神靈、娛樂神人的功能。從彈琵琶的人物身份、目的、活動內容來看,與上文所述的各類請巫師結場、焚香、彈琵琶,行巫卜之事有所不同。這是一例唐代民間以琵琶娛神的祀神賽會活動。
此外還有段安節(jié)《樂府雜錄》所記康昆侖與段善本琵琶斗樂一例。此事發(fā)生于唐德宗貞元年間,背景是長安大旱、設壇祈雨時,由東西兩市專門請琵琶大師段善本與康昆侖在長安天門街彈琵琶斗樂,活動的舉辦屬于民間祀神賽會內容。從本文論題的角度:(1)彈琵琶是祀神賽會活動中的一環(huán),琵琶承擔了娛樂神人的功能。這說明了唐人認可琵琶在民間信仰崇拜活動中的地位作用,有著以琵琶娛神的信俗特色。(2)彈琵琶者受祀神活動主持方的邀請而來,一為宮廷琵琶名手,一為寺院中的僧人,二人不是巫覡。所奏樂曲是世俗社會流行曲目。就此而言,娛神時,神靈與琵琶之間存在的是社會活動形式上的關聯(lián)。彈奏者及其琵琶音樂,沒有超現(xiàn)實的神秘色彩,不具有通靈性,這與卜筮、招魂有所不同。唯有文獻中所錄“鄰舍女巫授一品弦調”一事,透露了從事“琵琶卜”女巫的存在,同時也透露了這類女巫中,確有身懷較強琵琶演奏技藝并傳授他人一類人物的存在。
總 結
唐代形成了特有的琵琶巫卜風俗亞文化現(xiàn)象。唐代琵琶從不同角度、以多種方式參與社會的巫卜信仰活動。按其所參與活動的內容特點,大體可分為民間卜算類、民間巫術類和在神祠中舉行的民間信仰活動類三種。
其中的琵琶,就其器用功能而言,有樂器和巫卜用器之分。在民間信仰崇拜活動方面,尤其是賽神祈愿活動中,由樂人彈奏的琵琶,其功能是在請神、拜神或祈愿中娛神。彈琵琶以娛神的行為,肯定了琵琶樂感天人的認識。究其前源,這既與華夏傳統(tǒng)的樂感天人認識相通,也或與南北朝以來世俗社會以琵琶歌舞“種種伎樂供養(yǎng)佛”?釋迦牟尼:“若佛生處、大會處、菩提大會處、轉法輪大會、五年大會,作種種伎樂供養(yǎng)佛。”《摩訶僧衹律》卷三十三,載《中華大藏經》第三十七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40頁。的信俗認識相連。
從卜算的角度,包含民間及祠廟中的占卜吉兇,師婆、巫覡等彈奏琵琶,是將琵琶用作溝通神人之器,其樂音上達神靈是為獲得神諭。究其前源,當與以樂器占卜、聽音樂知吉兇的傳統(tǒng)巫卜行為、觀念有關。在巫術活動中結場、焚香、彈琵琶,有些已是行巫中的特定儀程,琵琶也成了行巫的法器,承擔著招魂、驅邪等巫術功能。
巫卜琵琶,可以說是一種具有久遠傳統(tǒng)、在唐代社會具有普遍影響,并在音樂和非音樂文化領域相互滲透的歷史景象。南北朝的有關史料就已提到宮廷中人既善彈琵琶又行左道?左道:“邪門旁道。封建統(tǒng)治階級多用以指斥未經官府認可的巫蠱、方術等。”《辭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958頁。,也提到地方“土人”彈琵琶占卜,這至少反映出自南北朝以來,琵琶已與巫卜活動產生聯(lián)系。而康昆侖琵琶技藝的啟蒙來自鄰舍女巫一例,也補充說明了這種聯(lián)系。唐代具有廣泛的、跨民族的琵琶風俗文化,涉及漢族、少數(shù)民族和中原、西域的音樂活動。琵琶能夠突破宴飲及胡樂歌舞的音樂身份,在民間信俗領域廣為傳播,是和南北朝至隋唐琵琶跨民族、泛文化的社會傳播分不開的。唐代巫師中不乏精于琵琶者,且能教習傳承其琵琶技藝。唐人主動選擇以琵琶娛神或溝通神人,某種程度上也是唐代琵琶音樂深入社會、琵琶藝術得到普及、發(fā)展,具有更大受眾面的一種體現(xiàn)。雖然目前無法求證巫師彈琵琶的演奏技法相關內容,但是,巫師的琵琶技藝,顯然也離不開唐代琵琶藝術演奏、娛人、傳播的大背景。
另外,就巫卜琵琶的藝術特點而言,巫卜琵琶的演奏實踐不同于伎樂琵琶,在巫卜行為的神秘文化心理氛圍中,巫師會將自身的感受與行巫氣氛傳遞到“琵琶卜”的行為與傳承中,如段善本指稱康昆侖琵琶樂音中有“邪聲”,恰恰是從另一角度說明,當時像段、康這樣的琵琶高手,能夠判斷出具不同文化功能、在不同文化場合中應用的琵琶音樂,與其所屬文化氛圍和應用領域,在演奏風格和所彈奏的曲調等關系上,存在有一定的區(qū)別。就此而言,從文化的多元化和特殊的文化樣態(tài)來講,唐代琵琶巫卜風俗的活躍,對于當時琵琶藝術特別是民俗琵琶的生存與發(fā)展,是一個應予關注和重視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