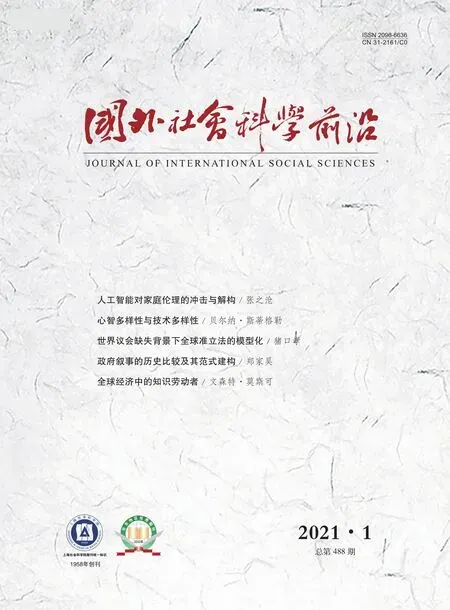阿甘本“生命—形式”范式的建構邏輯 *
劉 黎
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生命政治理論表達了對世界政治再次遭遇“奧斯維辛”到來的擔憂,他認為要躲過這場世界性的浩劫不是求助于某種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引領,比如上帝、耶穌、救世主,也不是訴諸某種具有革命潛能的倫理主體或主權邏輯的徹底變更,亦或等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解體與崩潰。相反,他的救贖計劃既具有濃烈的宗教色彩又具有政治本體論的意蘊,既表達了對彌賽亞事件的期待,又設想了一種“即將來臨的共同體”亦或“即將來臨的政治”。無論是彌賽亞事件還是即將到來的共同體,阿甘本認為,歸根結底還是要回歸到主權活動來思考躲避生命政治裝置的控制,即思考一種生命與其形式不相分離的生命—形式(form-of-life)。正是由于生命與其形式的緊密相連,致使主權邏輯無法再生產出赤裸生命,無法再迫使自然生命與政治生命、bios 與zoē 相分離。因此,“任何不以主權邏輯為基礎的未來政治必須使用這種生命概念,即不是基于自然生命與政治生命,zoē與bios 的司法分離,也不是從赤裸生命中涌現出來的生命。相反,而是,必須使這種分離變得不可能。這就是生命—形式(form-of-life),在那里,生命的神圣性是被阻止的……不是要在共同體中建立司法包容性,這種結果無一例外是排斥的和暴力的……取而代之的是在神圣和褻瀆之間的區分變得無效,不起作用,以至于神圣不再被用作于排斥機制。”①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s.),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72.
一、“生命—形式”結構體的語義內涵
生活形式(form of life)是歐陸哲學與科學哲學中的傳統技術術語,該術語經常為20 世紀的分析哲學大師維特根斯坦所用,它的語義內涵不同于20 世紀初反實證主義社會思潮的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的“生活風格”概念,“生活風格”概念常被運用于文化哲學、精神、心理學方面。維特根斯坦與阿甘本在哲學興趣與研究方向上存在很大差異,維特根斯坦哲學主要關注于邏輯學與語言哲學問題,而阿甘本對傳統政治哲學、美學、宗教、倫理學、傳統本體論問題感興趣,但是維特根斯坦在阿甘本哲學研究道路上,尤其在阿甘本神圣人計劃后期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阿甘本的核心術語“生命—形式”范疇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維特根斯坦的啟發,除此之外,維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學中對遵循規則、“用”的重要性的強調,也對阿甘本能夠在圣方濟各會的隱修制度與生活方式中討論反“有”的“用”的生命—形式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維特根斯坦對于其生活形式(form of life)概念并沒有進行詳細而又具體的界定,與其說他試圖明確地定義其概念,還不如說他更加強調概念的使用過程。對于維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首先我們需要明確兩個基本點:第一,生活形式概念在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過程中并不是一個高頻率詞匯,而且德語Lebensform 、Lebensformen、Form des Lebens(生活形式)中的Leben 具有雙重意義,這有點類似于阿甘本對生命(life)bios 與zoē 的區分。Leben 既可以表達為中文中的“生命”概念亦可指示“生活”概念。這兩個相異的Leben 內涵,維特根斯坦并沒有對它們進行具體的考古學式的界定,因此,將其理解為中文語境中的“生活”是有缺陷的,而是應該在“生活”與“生命”的兩層意義上來把握維特根斯坦的Lebensform 范疇;第二,維特根斯坦不主張對概念進行定義,而強調應該在具體實踐過程、具體使用背景中來把握其本質性的特征。對于生活形式,他將其置于語言分析過程中,生活形式概念在其著作中出現得寥寥可數,然而卻在很多場合下是被應用于語言之中。因此,語言是理解維特根斯坦生活形式概念的主要基礎,也是維特根斯坦生活形式的最重要的理解方式。維特根斯坦認為“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像一種生活形式(a form of life)”;“語言的述說乃是一種活動,或是一種生活形式的一個部分”;等等 。①[奧地利]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李步樓譯,商務印書館,2000 年,第12、17 頁。這是維特根斯坦對語言和生活形式關系的直接描述。維特根斯坦對語言的考察集中于語言與生命之間的關系、語言對世界的展現,但這不是一種抽象的、靜態的、形而上學式的語言分析,而是一種在日常社會生活實踐過程中的語言游戲問題,即人在語言游戲中如何表現其主體性、如何對語言做出相應的反應,人的諸種情感、行為如何與語言游戲交織在一起。這就是說,語言不再是作為純粹的交流的工具,也可以是人類實踐活動、生活形式的表達與描述,語言需要脫離對詞、命題、句子、意義、本質的固守,從而轉向在人類生活不同語境、背景、環境中的運用與使用。費迪南·費爾曼(Ferdinand Fellmann)認為維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指的就是“‘使用’,……說明了通過運用和習慣穩定下來的內部的行為和態度方式。這里沒有產生出形式,也沒有預給形式,而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通過形式得到了私人情感的多變性并為這種多變性增加了一種內心的、可以設想的態度行為方式。”②[德]費迪南·費爾曼:《生命哲學》,李健鳴譯,華夏出版社,2000 年,第194 頁。換言之,語言在使用過程中可以呈現出多變性,在必須遵守相應游戲規則的前提下,又可以在這種多變性與規則中衍生出另一種或多種意義,這也就是生活形式的演變過程。既可以促使某種行為方式得到保留,又可以在陳舊的行為方式中創造出全新的行為方式,生活形式也就預示著諸種可能性。維特根斯坦生活形式雖然存在著諸多類型的解讀方式,但是最明顯的就是,他在論述其生活形式過程中將其與語言游戲交織在一起,是在語言游戲中探尋生活的內容與生命的意義,這對于阿甘本而言也是如此。阿甘本對語言與生命問題的關注一直貫穿于其整個思想研究過程。
對于生命—形式結構體,阿甘本在意大利語中有兩種表達方式,“forme di vita”與“Forma-di-vita”,在英語、法語中一般將其轉譯為form-of-life,或者Forme-de-vie。生命—形式(form-of-life),阿甘本將其視為赤裸生命的對立面,一種具有完全意義的生命,一種司法政治無法捕獲的生命,一種純粹的人類生命,一種擺脫法律掌控的生命。從書寫形式上來看,生命—形式(form-of-life)中的生命與形式之間以連字符形式書寫,以強調生命與形式之間的親密關系,這明顯地體現了海德格爾的表達風格。從內容上來看,阿甘本與維特根斯坦對生活形式的模糊定義不同,他將其界定為“一種不可能與其形式相分離的生命,一種永遠不可能隔離出某種類似于赤裸生命的生命。”③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 2000, pp. 3-4.從語言差異的角度來看,生命—形式(form-of-life)異于生活形式( forma vivendi)、生命形式(forma vitae)、生命或法則(vita vel regula),生命—形式既不是生命的形式,也不是諸種生命形式,它是以單數形式而存在的生命—形式。“生命—形式(form-of-life)對立于以捕獲zoē 為主要目標的生命的諸種形式(forms of life)……生命的諸種形式(forms of life)描述的是權力裝置界定和控制生命的諸種方式。這種復數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確認了主權權力對生命的斷裂與控制的多種方式。然而,生命—形式(form-of-life),是一種單一的生命,一旦分裂生命變得無效,那么這種單一的生命就會涌現出來。”①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s.),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2.生命的諸種形式呈現的是主權邏輯與生命范疇之間的捕獲、控制關系,亦或是主權權力模式萃取生命內容的各種迥異的方式,它最終指涉的是主權對生命的否定關系。而至于生命—形式,雖然阿甘本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其是以抵御zoē 的政治化為目標,反抗bios 與zoē 之間的任何分離,但是阿甘本并沒有賦予其任何具體性的內容,而是在與赤裸生命的對立關系之中來確認此種生命。因此,它只能通過其對立面來獲得自身的內涵與指向,這也就意味著它通常是以一種潛在的、不在場的方式存在于其對立關系之中,只有當其對立面變得無效、變得不再起作用時,它才會露出真實面貌。生命—形式也就成為了阿甘本對那些誤認為其是悲觀主義者的反擊,它也是阿甘本對人類生命擺脫生命政治法律邏輯控制的有力探討。如果西方政治無法再離析出生物性存在的赤裸生命的話,那么,這就是一種嶄新的政治與倫理學的到來,這就是即將來臨的政治哲學的基礎,這也就是一種幸福生活,“一種絕對世俗的‘充足生活’,這種生活使其自身的力量與可交流性達到了完美境地——一種凌駕于主權之上的生活,一種主權不再具備掌控生命權利的生活。”②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 2000, pp. 114-115.生命—形式也就預示著一種“幸福生活”的到來。在如何發現生命—形式的問題上,阿甘本很抽象地言說道:“只有在某種生命的形式的事實性與物性中存在一種思想時,某種生命的形式才會轉變為生命—形式,即在其中絕不可能離析出某種類似于赤裸生命的東西。”③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 2000, p. 9.阿甘本預設了生命—形式存在的前提條件,即思想。思想是生命的諸種形式轉變為生命—形式的媒介、中介,某種單一的生命的形式可以轉變為生命—形式。因為思想本身具有“一種體驗,一種實驗”,而在這種體驗與實驗中,“它把生命以及人類智力的潛能特性視為其對象。”④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 2000 , p. 9.這是但丁意義上的思想權力,該種思想權力即是“使生命不斷地與其形式重新聯合,或不斷地阻止生命與其形式的分離。”⑤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 2000, p. 11.“ 思想即是生命—形式,這種生命不能與其形式相分離;這種親近的不可分離的生命可以出現在物質過程和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的物質性中的任何地方,在那里,只存在思想,在理論中也是如此。這種思想,這種生命—形式……必將成為即將來臨的政治的指導性概念與統一的中心。”①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 2000, pp. 11-12.阿甘本并沒有完全停留在對生命—形式的簡略而又抽象的分析上,他設定了一種生命—形式的典范,即圣方濟各會的隱修生活形式,從而開啟了從權力形式向生命—形式的政治神學思考。在圣方濟各會的隱修生活與制度形式中,重要的“不是規則,而是生命,不是宣稱信奉這種或那種信條的能力,而是以某種方式生活的能力,即愉快而又公開地過著某種生活形式的能力。”②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3.阿甘本強調的是圣方濟各會的生命與生命—形式,而不是某種單一的規則或形式,這是反抗生命政治邏輯的巔峰體現,而圣方濟各會隱修規則中的“最高的貧困”與“使用”的生活方式即是對抗資本主義的另一種具體的生命—形式。
二、生命—形式的典范:“最高的貧困”
阿甘本生命—形式最基本的特征即是不受法律的控制,不是規范應用于生活或生命之中,而是生活或生命被應用于規范之中,在規范之中生存,或者說,形式、生命、規則進入了無差異的門檻地帶。因此,“這并不是一個把某種形式(或規范)應用于生命的問題,而是按照那種形式去生活的問題,這就是生命的形式,接下來,讓生命本身成為形式,并與之相一致。”③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9.至于此種生命—形式類型的體現,阿甘本將其追溯到了基督教的文化傳統中,而且他直接地將圣方濟各會中的隱修規則及其僧侶生活方式視為生命—形式的典范,認為圣方濟各會中的法外生活規則為人類行為方式、追求“幸福生活”指明了方向。
與福柯晚期轉向苦行傳統類似,阿甘本對基督教隱修制度的探討旨在“通過隱修生活的典型例子的研究——構建出一種生命—形式,也就是說,一種與其形式聯系得如此緊密的生命,以致于這種生命與其形式無法分離。”修道院中僧侶們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與必須遵循的諸種規則是思考阿甘本意義上生命—形式的核心,“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研究首先面對的問題是規則與生命之間的關系,這個關系界定了一種裝置,通過這種裝置修道士們藉此來實現他們共同生活形式的理想。”④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xi.因此,阿甘本認為正是隱修生活方式中對僧侶們的最細微、最直接的生命調節,使得規則、法律、儀式、生命之間變得模糊,使得僧侶們的生活實踐成為“無差異領域”,世俗法律的禁止界限與修道院中對僧侶們生活的塑造變得不再可分,隱修規則脫離了其原初的禁止與懲罰的設定而演變為對僧侶們生活方式的最精細的關照。阿甘本試圖通過對中世紀圣方濟各會運動中僧侶們的共同生活的分析而努力探尋逃離現代政治法律機制對生命捕獲與控制的機會,思索避免淪為赤裸生命命運的出口,最終擺脫主權權力與生命權力相一致的陷阱,走出生命政治趨向死亡政治學的邏輯框架。阿甘本對基督教早期隱修制度或圣方濟各會的生命與形式之間的關系問題持有這樣的立場,他們在努力地追求生命與其形式的統一,“堅持不懈地接近它的實現”,但是又“一直在錯過它。”①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xii.雖然圣方濟各會最終失敗了,沒有實現其生命與形式的完全統一,但這不會對阿甘本將其視為生命—形式的典范造成阻礙,仍然可以從中汲取力量。阿甘本對圣方濟各會禁欲傳統的描述集中關注了其貧窮狀態,這不是從司法政治角度出發,也不是從政治經濟學批判角度來看待貧窮問題,而是認為貧窮言說著一種生命狀態,一種存在狀態。因而,阿甘本試圖從宗教、哲學角度出發來重新審視基督教生活模式,思考圣方濟各會的行為方式。在這里,他主要強調的是他們自愿選擇貧困,他們的貧窮是一種“至上的貧窮”,“最高的貧窮”,不擁有任何權利,不占有任何東西,這就是圣方濟各會的典型的生命—形式,也是對羅馬教廷的強烈反抗。
對于“貧窮”概念的理解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出發:第一,從修道院修道士的穿著習慣(habitus)角度來看,他們并不需要光鮮靚麗、絢麗多彩的衣物與裝飾,但也不至于衣衫襤褸,他們有著自身的一套服飾規則,傾向于簡潔、樸素的著裝。阿甘本認為習慣(habitus)一詞“最初指的是一種‘存在方式或行為方式’,在斯多葛學派那里,習慣變成了美德的同義詞……似乎越來越多意味著穿著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引導自己的方式’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②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在修道院隱修制度中,習慣漸漸地演變為一種著裝習慣、生存狀態,并與行為品德、指導自我的方式變得密切相關,這種裝束習慣“已經呈現為一種教化過程,使得他們成為一種美德和生活方式的象征或寓言。正因為如此,對外在著裝的描述,就等同于揭示了內在的存在方式。”③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4.阿甘本認為外在修飾的素雅、簡單也就意味著個體內心存在的單純、天真。在這個意義上,修道士的“貧窮”指涉的是服飾習慣的簡單化與純潔化對生命內部活動的隱喻,“貧窮”也是修道士形成此種生活習慣的前提條件,而不只是對著裝簡陋、材質粗糙的表達。“因此,僧人們日夜穿戴的小兜帽是讓其‘不斷保持小孩的純真和天真’的訓誡。亞麻長袍的短袖‘暗示了他們已經中斷了這個世界的行為和工作’。穿過腋下的細羊毛繩使衣服緊緊地貼在修士的身上,表示他們已經為所有的體力勞動做好了準備。他們披在衣領和肩膀上的小披風或外套象征著謙卑。手杖提醒著他們‘他們絕不能在眾多的惡犬中赤手空拳地走出去’。他們腳上穿的涼鞋代表著‘我們靈魂之足……必須時刻為精神上的競技做好準備’。”④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4-15.修道院生活習俗把服飾轉變成了一種生活習慣,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生存樣態,即著裝與生活方式的不可分離。而且,“只有在修道院生活中,我們才可以目睹到服飾的各個要素被徹底教化。”①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7.因此,在阿甘本看來,隱修制度中穿著習慣的“貧窮”既是修道士們共同堅持的生活規則,也是事實上的窮困狀態,這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在這種貧窮中,他們能夠獲得一種純真的、單純的生活模式,這是貧窮造成的結果,也是趨向美德的前提條件,與此同時,也能夠使其獲得圓滿的教化過程。換言之,在修道院服飾習慣中,貧窮并不意味著生活拮據的消極意義,而應看到貧窮帶來的肯定性內涵。除此之外,貧窮在這方面也類似于福柯在其晚期著作中對關照自我的生存美學的探討,比如,福柯極力倡導將生活塑造成一種具有創造性的藝術品,使生活成為藝術。早期修道院修道士的服飾內容也是一種對藝術與美的追求,它促使修道士生活在單純、天真、純粹的生活之中,這不是根據某種隱修規則而實現的,而是以這種生活方式而存在,抑或說,生命與規則相互滲透而使其不可區分。從倫理學與美學角度來看,貧窮也意味著一種生存美學,生活藝術,指向對自我的不斷完善。在這個方面,修道士服飾習慣與其生活方式的不可分離,即是阿甘本意義上的生命—形式,這不是在赤裸生命語境中談論生命—形式的內容,而是在規則與生命,教義、教制與生命關系中言說生命與其形式的不可分離。
第二,從法律角度來看圣方濟各會的“貧窮”問題,圣方濟各會沒有任何財產所有權概念。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與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認為,“圣方濟各派的信徒推崇‘教會法’——‘根據自然法,全部事物屬于所有人’,‘根據神法,所有的事物都是共同的’。”圣方濟各派反對財治,反對財產共和國,支持共享制度,共同體建基在共同財富基礎上,②[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34~35 頁。從根本上來看,這不是“所有權社會”而是一種共產主義形式。亦可說,圣方濟各會一無所有,然而又“無所不有”,他們不占有、不擁有任何東西,沒有財產,沒有所有權,沒有專屬于自身的東西,但是,卻能在共同中產生使用行為,這只是一種事實上的使用,而不是法律上所指示的使用權。“財產和所有的人類法律都始于人類的墮落和該隱之城的建設……在純真狀態下,人類使用了東西,但是沒有所有權,在圣方濟各會那里也是如此,以基督耶穌和使徒們為榜樣,圣方濟各會放棄了所有的財產權但保留了對事物事實上的使用……放棄權利(abdicatio iuris,這意味著回到墮落之前的自然狀態)以及所有權與使用的分離構成了圣方濟各會常常從專業角度界定他們所謂的‘貧窮’的特殊條件的基本裝置。”③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13.早期圣方濟各會宣稱要對權力、制度提出激進的批判,抵抗世俗世界的法律與權利,最激進的批判即是反對私有財產,反對個人所有物,反對對他人勞動的占有。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圣方濟各會反對任何占有,反對任何私有物,拒絕擁有任何東西,這就是圣方濟各會“最高的貧困”,亦即“至高的清貧”,這是一種自愿接受而讓人無限向往的生活方式,這也是一種“符合放棄所有權利(abdicatio omnis iuris)原則的實踐,也就是說,人在法律之外而又沒有任何權利而存在的可能性”。①Daniel McLoughlin (ed.) , Agamben and Radical Poli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38-39.用阿甘本的話來說,“圣方濟各會必須堅持貧窮的‘征用’性……‘最高的貧困……是征用的,因為它不能占有任何共同的或個人的東西,既不能占有兄弟的東西也不能占有整個團體的東西’,并拒絕小修道會的任何占有意圖(animus possidendi)。”②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9.從對所有權的放棄角度來看,這也就意味著對創造經濟價值、經濟利潤的私有財產的拒絕,也就無法生產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剩余勞動或剩余價值,也就避免了對勞動者的剝削與壓榨,這種生命體驗,即是圣方濟各會生命—形式的主要體現。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圣方濟各會宣稱要放棄任何權利,不擁有任何東西,不是通過廢除既定的社會法律與規則來實現。相反,與其說是一種倡導取消現定法律與權利,不如說是一種逃離,一種不服從,一種對既定法律與權利的無視,從而使其自身處于法律、權利之外,使法律與權利自動失效,不再起作用,這也就是一種至高的貧困。因此,圣方濟各會的“貧困”,既是一種生活習慣上的簡樸,又是一種法律上對物權的舍棄,這不是根據某種世俗法律規定而生活,而是使其融入生活之中,成為自身的生活形式、生活內容,使此種生活形式與自身的生命存在融為一體,不可分離,因為“這種形式不是一種強加在生命之上的規范,而是在追隨基督生活過程中,給予自身一種形式并使自身成為一種形式去生活。”③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05.阿甘本將圣方濟各會的“最高的貧困”視為一種拒絕任何形式所有權的生活方式,這是他建構其生命與其形式不可分離的生命—形式的一面,而其另一面則是“貧困的使用”,對“使用”問題的探討反映了生命—形式具體操作的可能性,因此,是阿甘本構建“生命—形式”范式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三、“使用(Use)”理論
阿甘本在生命政治理論中構建了主權、法律、規則對生命的控制與捕獲,使得生命淪為了沒有任何活力、激情、創造性、主體性的赤裸生命,為了擺脫主權權力邏輯與例外狀態的全面束縛,使生命從法律、權力的禁錮中解脫出來,他將之訴諸生命—形式的創造。與阿甘本將生命政治的典范鎖定在集中營的做法類似,他將走出生命政治邏輯框架鎖定在圣方濟各會運動中,把圣方濟各會的生活方式視為走向未來幸福生活的范例。圣方濟各會運動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法律、規則與生命之間的關系變得十分模糊,這兩個明顯充滿差異的領域變得不可區分,成為“無差異地帶”,從而切斷了法律、權力、主權對生命控制與操縱的可能性。阿甘本認為法律概念之所以會在圣方濟各會運動中失效,是在于他們對所有權的放棄,不再占有任何物的所有權,不再成為權利的主體,這是對傳統羅馬法律的反抗,以具有反“有”特征的“最高的貧困”的存在模式為抵抗武器。個體以“一無所有”的方式而生活,沒有占有任何物的意志,這并不意味著沒有財產或所有權,不是自權人就不能生存。圣方濟各會雖然不占有任何財產,但是,他們堅持共同使用任何物,使用任何共同物。“使用”范疇的革新,是圣方濟各會生活方式得以進行的前提條件,它體現的是法律、生命、所有權、權利之間關系的變革,因此,阿甘本意義上的生命—形式可能得益于“使用”理論的重新塑造。
從思想發展脈絡角度來看,阿甘本在20 世紀70 年代就提及過“使用”概念,這是基于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來探討商品的神秘性。顯然,他不是為了在馬克思基礎上來延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來繼續分析商品是如何從簡單而又平凡的東西,普通而又可感覺的物轉化為“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88 頁。。他關注的既不是商品的使用價值或價值,也不是商品形式的物化與物象化過程,而是一種作為景觀的商品秘密,“可見而不可見之物”對一切生命的全面統治。阿甘本認為當“商品容貌轉變成著了魔的物體時,這是交換價值開始超過商品使用價值的標志。”②Giorgio Agamben, Stanzas: Word and Phantasm in Western Culture, Translated by Ronald L. Martinez,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38.對此,杰西卡·懷特(Jessica Whyte)解釋道,“雖然阿甘本早期將之解釋為對使用可能性的腐蝕,但它依然是以克服使用價值的懷舊,挑戰其潛在的功利主義預設為導向的。阿甘本對使用概念的最早解釋考慮的是與物之間新關系的可能性,這種新關系既不是使用的功利主義概念,也不是交換邏輯。”③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s.),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94.阿甘本確實想要擺脫功利主義與交換邏輯的話語,不過,在這里他并不是想要在馬克思基礎上重新思考“使用”范疇,或建構某種具體的“使用”理論。他談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的論述,主要是為了將馬克思塑造為景觀批判的先鋒,而不是重申馬克思主義經濟拜物教批判方式。因此,在此階段,阿甘本談論“使用”問題,更傾向于展現資本主義世界的景觀統治,交換價值對使用價值的超越,以至于最終成為操縱生命的絕對權威。與其說這是阿甘本對“使用”問題的最初解釋,還不如說是他對資本主義景觀社會批判的肯定。因為在20 世紀90 年代,阿甘本再一次回到了這個主題,高度贊揚了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觀社會批判,并進一步討論了“使用”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問題。根據阿甘本在資本主義極端階段,即資本主義以景觀展示其自身的社會,“一切使用都變得不可能并將一直不可能。”④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 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 2007, p. 81.這是阿甘本對“使用”概念的實際應用,以分析資本主義在大眾消費社會通過景觀影像、資本影像對人類生活的全新操控。這也就預示了阿甘本對“使用”概念的運用要異質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對商品使用價值的分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阿甘本對資本主義領域“使用”問題的思考,是他在宗教領域中對圣方濟各會生活形式分析的現實運用與延伸。換言之,要想更清楚地理解與掌握阿甘本的“使用”概念、“使用”理論的最根本特征,或作為一種生命—形式的“使用”范疇,就必須回到中世紀宗教領域中,回到圣方濟各會運動中,回到生命—形式的典范之中,回到圣方濟各會的“最高的貧困”之中。
具體而言,阿甘本構建的“使用”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使用與所有權的對立,以建構一種生命—形式為目標。“在圣方濟各會對‘最高的貧困’的倡導中,他們宣稱一種完全被移出法律領域的使用是可能的,為把這種使用與用益權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使用權區分開來,他們把這種使用稱作事實上的使用(usus facti),實際使用(de facto use)(使用事實)。”①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 2007, p. 82.這是異于物權法中的用益權、所有權的純粹事實上的使用,這種純粹的使用“是某種人們永遠不可能擁有、也永遠不可能把它當做所有物來占有的東西。換言之,使用通常指涉的是與某種不可能被占有的東西之間的關系;使用指涉的是那些不能成為占有對象的物。”②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 2007, p. 83.事實上的使用,亦或使用事實,強調的不是使用價值而是單純的使用事實,即使用不是法律或權利問題而是事實、功能問題。與此同時,這又是一種“貧困的使用”,是一種實踐行為與事實,是圣方濟各會的生活形式,以“貧困的使用”來展示圣方濟各會的最初的生活方式。簡言之,圣方濟各會最核心的主張就是反對財產所有權,拒絕任何形式的所有權,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并以此與世俗社會相聯系。在這種“使用”范疇中,不是去鑒定“使用”本身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看到“使用”是作為一種生活實踐行為,并使此種生活形式融入實踐過程中,從而又可以生成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生命—形式。因此,阿甘本強調,“在這里,使用不再意味著純粹而又簡單的放棄法律,而是把這種放棄建構成一種形式,一種生活方式。”③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42.也就是說,使用既是圣方濟各會修道士們的具體實踐,也是他們生命—形式的體現。第二,使用相異于使用權,使用即是沒有權利的使用。在這方面,阿甘本受惠于13 世紀圣方濟各會的哲學家與神學家彼埃爾·讓·奧利維(Pierre Jean Olivi) 的“使用”概念。在圣方濟各會的隱修制度之中,他們所呼吁的“最高的貧困”,不只是放棄擁有物的權利,還必須放棄使用物的權利,即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同時放棄。在奧利維看來,“使用和權利不是一回事:我們可以用某個東西,但沒有所有權或使用權,正如奴隸用他主人的東西,卻沒有任何所有權和用益權一樣。”④[意]吉奧喬·阿甘本:《剩余的時間》,錢立卿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 年,第35 頁。圣方濟各會修士們踐行的是不占有任何物,不擁有獨屬于自身的任何東西,而是共同使用。在這里,使用不表示任何價值內涵,也不隸屬于法律范疇,而是一種純粹以使用為目的的使用。這是一種短暫的擁有,這種擁有除了表達使用的單純行為不代表任何意義,也不是倫理或道德上的要求。因而,從這個角度來看,使用表現的是一種共享行為,一種生活方式。他們被允許使用,但是不具有使用權,與奧卡姆(Guillelmus de Ockham)所言類似,“他們放棄了所有財產,放棄了所有占有的能力,但是并沒有放棄使用的自然權利,因為它是一種不可放棄的自然權利。”①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4-115.純粹事實上的使用實踐是個體本身具有的內在屬性,是自然賦予的不可剝奪或放棄的權利。阿甘本試圖努力地將圣方濟各會的“使用”概念激進化,從而延伸奧利維與奧卡姆等圣方濟各會理論家們對“使用”范疇的界定。在阿甘本看來,圣方濟各會的失敗在于“使用的事實性本身不足以保證法律的外在性,因為所有事實都可以轉化為權利,正如所有權利都暗示著事實方面。……以這種方式他們又將他們自己越來越多地糾纏在司法概念中,通過這些司法概念他們最后將會被顛覆和擊敗。”換而言之,圣方濟各會修道士們正“全神貫注地用司法術語來建構使用的正當性”②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9.。圣方濟各會對處于法律、權利范圍之外的訴求是一種純粹地、絕對地放棄,這只是一種表面上的否定性,最終無法避免再次陷入司法領域。因此,圣方濟各會最終受到了羅馬教廷的強勢打壓以失敗而告終。阿甘本在圣方濟各會運動中看到了其失敗的原因,為了擺脫圣方濟各會運動中遭遇到的法律困境,他認為“與律法的沖突——或更確切地說,試圖使法律失效,通過使用讓法律不再起作用,也同樣處于純粹存在層面上,在那里律法與儀式在有效運作。生活形式是純粹的存在現實,這種純粹的存在現實必須要從律法和職責或義務的封印中解放出來。”③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6.從這個方面來看,阿甘本看到了避免與法律發生沖突,逃離法律的可能性,那就是轉向對圣保羅的思考,走向圣保羅對彌賽亞生活的界定。這也就是阿甘本“使用”理論的第三個特征,圣保羅彌賽亞的真正“使用”,使法律失效,使其不再發揮作用,以“要像不”(“好像不”)的方式來重新發現“使用”理論。以“要像不”使用的態度與立場來對待使用過程,而不是采取抵抗法律或違背法律的激進行為,旨在“創造一個脫離權力和法律掌控的空間,不和它們沖突,卻能使它們停止運作。”④[意]吉奧喬·阿甘本:《剩余的時間》,錢立卿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 年,第36 頁。以“要像不”的方式讓渡法律、權利、所有權、社會身份、特權,以“要像不”的使用方式而生活,“以‘要像不’的形式而生活,意味著喪失所有司法的和社會的所有權。”⑤Giorgio Agamben, The Use of Bodies, Homo Sacer IV, 2,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74.這也就意味著阿甘本對生命—形式的建構,從司法領域轉向了宗教神學領域或經濟神學領域,意味著阿甘本的政治旨趣并不是要創造或生成一個全新的共同體,而是能夠如此的共同體,“這并不是另一個樣子或另一個世界;它就是這個世界的樣子的逝去。”①[意]吉奧喬·阿甘本:《剩余的時間》,錢立卿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 年,第31 頁。
四、結 語
在福柯生命政治理論背景下,阿甘本試圖在對人類生存境況的探索中發現嶄新的世界和生活方式。阿甘本一方面以主權權力、例外狀態為核心構建了政治權力生產赤裸生命的生命政治圖景,這是他對西方現代政治的病理診斷。另一方面,又試圖在消除zoē 與bios,生命與形式的分割中創制與其形式不再分離的生命—形式,并將其作為抵抗生命政治捕獲和控制生命的最高手段以及解決現代政治困境的有效路徑。生命—形式不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意義上創造一切的純粹生命,也不是奈格里、哈特意義上能夠開展政治斗爭的革命主體。在阿甘本這里,生命—形式不僅預示一種全新的生命存在樣態的出現、幸福生活的到來,更意味著主權權力運作邏輯的失效、生命政治裝置的終結。人不再是現實的或潛在的赤裸生命,而是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純粹潛能。然而,在生命與其形式中涌現的生命—形式卻是源于對政治神學傳統的思考,以宗教神學話語批判方式代替現代政治的現實批判,這使得生命—形式難以克服神秘而虛幻的末世論基調。這嚴重損害了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論邏輯布展和思想建構的效力與深刻性,從而使得這種思考淪為個人苦惱與焦慮的展現,與此同時,這也表明了現代西方左翼激進政治確實面臨難以解決的現實難題,只能屈從于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