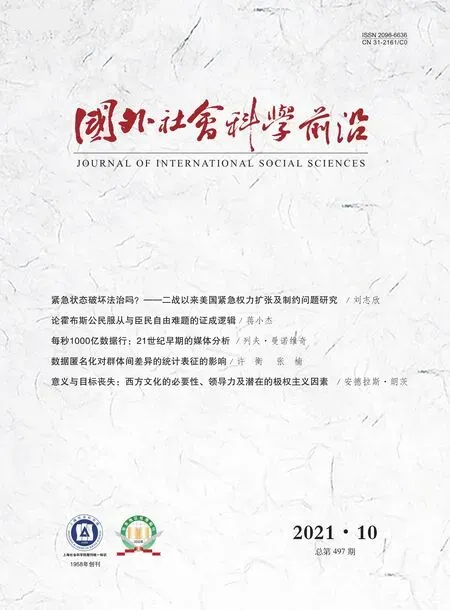論霍布斯公民服從與臣民自由難題的證成邏輯 *
蔣小杰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的提出
霍布斯政治哲學的核心目標是證成絕對的主權權威,為了公共的和平與安全,公民承擔有服從主權者的絕對義務。但我們也發現,他在證成主權權威的絕對性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沒有放棄自由的先在性和自衛的正當性,他甚至還把此保留為國家狀態下“真正的臣民自由”。這似乎意味著公民對絕對主權權威的服從只具有相對性。學者們藉此認定,霍布斯確有自由主義者這一面向。例如,施特勞斯就曾明確地說過:“倘若我們把自由主義稱之為這樣一種政治學說,它將與義務判然有別的人的權利視為基本的政治事實,并認為國家的職能在于保衛或維護那些權利,那么,我們必須說自由主義的創立者乃是霍布斯。”1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181-182.艾倫?瑞安更是直言不諱:霍布斯的自由觀開啟了西方現代自由主義的先河,并由此“被廣泛稱為現代個人主義的創始人、個人主義之父”2Alan Ryan, Hobbes and Individualism, in G. A. J. Rogers and Alan Ryan (eds.), Perspective on Thomas Hobbe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p. 81.。即便是政治保守主義者的奧克肖特也認為,“霍布斯雖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他那里的自由主義哲學比多數自稱為自由主義的捍衛者更多。”3奧克肖特:《〈利維坦〉導讀》,應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0頁。國內學者吳增定通過對“權力”概念的梳理,最后認定,“霍布斯所建構出來的這種無目的、可計算、可量化、可分離、可組合的權力概念,在此后近四百年的時間里,一直貫穿著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演變進程”,雖然霍布斯本人并無意于自由主義的建構,但他對權力問題的看法客觀上為現代自由主義提供了基本的前提。4吳增定:《霍布斯與自由主義的“權力之惡”問題》,《浙江學刊》2006年第3期。
但與此同時,也有研究者不以為然,而是認為:我們不應當對霍布斯所提出的臣民自由進行過多的自由主義拔高,即便霍布斯提出并論證了臣民自由,但他的這一論證對其絕對主權學說的證成而言并沒有構成實質性的挑戰,甚至霍布斯對臣民自由論證會沖擊到其政治哲學體系的自洽性。例如,格倫?伯吉斯認為,霍布斯在《利維坦》第21章中所推論出來的臣民相對服從主權者的那些權利根本就是無足輕重的,它們并“沒有什么實際的政治意義,甚至可能會讓他自己理論的邏輯內涵變得尷尬無比,因為霍布斯實際上本想把他的這一推論給掩蓋起來”。5Glenn Burgess, On Hobbesian Resistance Theory, Political Studies, vol. 42, no. 1, 1994, p. 69.同樣,喬治?卡夫卡也將霍布斯對臣民自由的闡述看作是“不精確的主張和孱弱無力的論點”。6Gregory S. Kavka, Hobbesian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19.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只要我們補充以新的解釋原則就能彌合霍布斯論證的缺陷。例如蘇姍?斯雷德哈爾就提出了理解社會契約的“合理預期原則”“忠實原則”和“必要性原則”,認為只要我們能夠遵從這些原則,那么霍布斯對臣民真正自由的論證不僅不會顯得怪異而且還會變得有意義,并呈現為一個連貫的體系。7Susanne Sreedhar, Hobbes on Resistance: Defying the Leviath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4.
霍布斯既然一方面闡發并始終強調主權權威與公民服從的絕對性,另一方面卻又認真地保留了臣民自由,并認為他們只是承擔相對的服務義務。那么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是:如何理解霍布斯在主權權威和臣民自由兩者之間所做的如此安排?他對公民相對服從義務的論證是否與其絕對主權權威的論證存在著內在的沖突,真就如批評者所說的那樣根本上就是邏輯不相容的?抑或如支持者所言,需要引入新的解釋原則才能使得這一論證實現邏輯自洽?本文嘗試對以上問題做出梳理并給出相應的回答。
二、契約-授權的有限性與絕對性
通常而言,把霍布斯作為權威主義者的直接依據在于,自然人在簽訂社會契約過程中所轉讓的權利內容涵蓋了他們全部的自然自由。作為授權方,自然人放棄了獨立的自然人格,而作為受托方,主權者在保留自身完整自然人之人格的同時又全盤接收了其他自然人授權而來的人造人之人格,最終成為不受其他力量約制的最高權力或絕對權威。簡言之,在主權的絕對性和授權的無限性之間存在著同一性關系。
但通過仔細的文本辨析可以發現,霍布斯在道明主權權威絕對性的同時,對權利的轉讓范圍卻持有相當謹慎的態度,這兩者之間并不就具有完全的同一性。根據契約程序的第一步,為了能夠“保全自己的生命”,人們“指定一個人或一個由多人組成的集體來代表他們的人格,每一個人都承認授權于如此承當本身人格的人在有關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為、或命令他人做出的行為”。1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31頁。以下簡寫L,并置于正文以括號標示。文內部分譯文根據英文原本有所改動。英文本參見Thomas Hobbes,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 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London: printed for Andrew Crooke, at the Green Dragon in St. Pauls Churchyard, 1651。在此,霍布斯并沒有說自然人對自己全部的人格都做了授權,而只是說他們承認代理人在“有關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可以做出任何命令行為,這也就對主權者的權力效用范圍做出了比較明確的限制。那么基于此,契約程序的第二步,“在這種行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從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斷服從于他的判斷”和第三步驟“這就不僅是同意或協調,而是全體真正統一于唯一人格之中”(L131),自然人所具有的自然人格被主權者所具有的人造人格所吸納之時,也就僅限于“有關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除此之外的權利事項,特別是“保全自己生命”的自由,自然人既沒有向代理人進行授權,也沒有放棄其自然人格的行使,因此主權者對此并不能做出任意的命令。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霍布斯會這樣說:“臣民對于主權者的義務應理解為只存在于主權者能用以保衛他們的權力持續存在的時期。因為在沒有其他人能保衛自己時,人們的天賦自衛權利是不能根據信約放棄的。”(L172)他如此言說的目的也就在于,如果主權者做出命令破壞了公共的和平與安全,從而使得公民的生命不能得以保全,那么公民也就不再承擔對主權者命令的服從義務。公民未能放棄的天賦自衛權賦予了他們自身以抵抗主權者命令的權利,亦即“保全自己的生命”構成了公民自由權利的硬核,它為主權者基于其自身的自然人格的任性行為樹立了到此為止的界碑。
盡管如此,斷言霍布斯是權威主義者也始終有著充分的證據支撐。主權者在“有關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不僅擁有著支配臣民的絕對權利,同時還保留著完整的先發制人以及純粹征服的自由權利。霍布斯還做了諸多的足以使人產生聯想的表述:“但人們在這一點上也許會提出反對說:臣民的景況太可憐了,他們只能聽任具有無限權力的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的貪欲及其他不正常激情擺布。”(L141)盡管反對者會說“臣民只能聽憑主權者擺布”,但霍布斯并沒有對此反對意見予以任何的否定,反而有些犯忌諱地說到“主權……都是人們能想象得到使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像這種一種無限的權力,人們也許會覺得有許多不良的后果,但缺乏這種權力的后果卻是人人長久相互為戰,更比這壞多了。”(L162)在霍布斯看來,主權者即便做出了對臣民普遍的最大不利之行動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較之于自然狀態之下的相互為戰,主權之下的恐懼戰栗依然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較優選擇;與其整天惶恐于來自任何他者的暴力死亡恐懼,不若只驚懼于來自主權者這明確的單一主體的暴力死亡恐懼,較之于不確定的死亡恐懼,確定的死亡恐懼更能讓人接受——霍布斯的終極恐懼似乎不是對暴死本身的恐懼,而是對“不確定”的恐懼。不僅如此,在對主權的性質進行界定時,霍布斯還直接規定了主權作為“無限的權力”所具有的不可轉讓和不可分割的絕對性特質,這更是直接就讓人對霍布斯產生絕對權威主義者的印象。在列舉主權者所具有的12項權利之后,他直言不諱:“以上所說的就是構成主權要素的權利,……這些都是不可轉讓和不可分割的權利。”(L139)與此同時,霍布斯還不忘告誡主權者要時刻警惕如下觀念的產生:認為臣民同時也能夠分享主權,主張把主權割裂開來分屬于不同機構的混合政體,甚至讓臣民相信存在著超越主權之外“不可見權力”。
通過以上的解析,在此可以做出簡要的回答:契約的程序性確保了主權者行動的權威,但授權的有限性設定了主權者行動的范圍,亦即“有關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主權者在此行動的范圍內擁有絕對的權威,它樹立了臣民到此為止的界碑,任何個人或團體都不能對之進行挑戰,否則國家必將解體,重歸自然狀態。但在主權者絕對權威之下,公民“保全自我生命”這一硬核無論是建立國家前后都始終保留著,而此正是下文所說的“真正的臣民自由”和公民相對服從權利的理論籍資。
三、自由的分層、轉化與保留
無論是授權的內容還是主權的構成,兩者所指向的都是“自由”的問題,因此辨明主權者權威的效用范圍以及臣民自由的限度問題,都應從“自由”概念的辨析入手。霍布斯把“自由”看作是自然意義的存在,“所有的人都同樣地是生而自由的”(L168),這就意味著“自由”具有相對于主權國家的先在性。經由契約建構主權,自然自由轉化為公民自由,在此過程中只是部分的自由受到了特定的剝奪或限制,而相當多的自由則被霍布斯所完整地予以保留。正是基于此完整保留的自由,霍布斯才推論出了他所謂的“真正的臣民自由”以及“公民相對服從”這一結論。
在國家建立之前存在著的只是自然意義的自由,可以進一步區分為物體運動意義上的人身自由和作為自然權利的天賦自由。
1.人身自由(corporal liberty)。這是基于物體運動而來的自由,僅表明不存在外在阻礙的狀態,“自由這一語詞,按照其確切的意義說來,就是外界障礙不存在的狀態”,(L97)“自由一詞就其本義說來,指的是沒有阻礙的狀況,我所謂的阻礙,指的是運動的外界障礙”(L162)。(1)人身自由是事物本然意義上的狀態,具有較之于外在阻礙的先在性(former):“因為自由的本義如果指的是人身自由……人們顯然已經享有這種自由了,他們現在還像這樣喧嚷,要求這種自由就是非常荒謬的。”(L164-165)外在的障礙只是阻礙人身自由的實現,既不能取消、更不能剝奪人身自由。(2)人身自由是否定意義上的自由,它表明行為不受外在障礙的阻礙,即所謂的“自由不過是缺乏對運動的阻礙”。1Thomas Hobbes, On the Citiz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11.例如,被鎖住的動物和被河岸束縛的水流之所以被稱之為“缺乏自由”,只因為它們受到外部障礙的阻礙。因此,(3)人身自由的缺乏既不意味著本然意義上自由的缺失,也不意味著實現自由之內在力量的喪失,例如靜止的石頭和因疾病而動彈不得的人。(4)人身自由適用于所有的上帝造物,但落實在人類這一“有理性的造物”時就是霍布斯所說的與心靈(mind)相對應的身體(body)的自由:“因為自由的本義……也就是不受鎖鏈鎖禁和監禁的自由”。(L164-165)
2.天賦自由(natural liberty)。這是在力量和智慧所能及的范圍內做其想做之事的自由:“著作家們一般稱之為自然權利的,就是每一個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這種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斷和理性認為最適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L97)(1)天賦自由的核心是“保全自己的生命”,既包括消極意義上的禁止去做損毀自己的生命或剝奪保全生命的手段的事情,也包括積極意義上去做自己認為最有利于自己生命保全的事情。(2)天賦自由是接受“自我保全”所施加限度的自然權利,當人們具有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對適當的事情采取行動時,它必須只是作為自我保全的必要條件,否則就是超出限度的自由,例如純粹的以征服為樂。(3)天賦自由是具有必然性規定的自由,“自由與必然是相容的”(L163),出于自由的行為是來自人們意志的自愿行為,而人們的意志由于對自我保全的自覺而具有其必然性。(4)天賦自由是具有絕對性的自由,“如果一個君主為他自己和他的繼承人放棄主權時,臣民就恢復了絕對的天賦自由。”(L172)
3.自然意義自由的分層結構。無論是人身自由還是天賦自由,都是先在的本然自由,其內核便是“保全自己的生命”,包括不受殺死、傷害和監禁等內容構成。“保全生命”賦予自然權利以絕對性從而成為自由的硬核,無論是主權建構目的的證成還是真正臣民自由的證成,始終都是圍繞著這一硬核展開的;換言之,它構成了霍布斯政治哲學的拱頂石。即便在建立國家的過程中,臣民也“沒有將這一權利賦與主權者”(L241)。
根據這一“硬核”,我們可以辨析出霍布斯自然自由若干層次:(1)單純硬核的自由,也就是人們出于生命的保全而自己做出判斷并采取行動,這其中包含著不得對自己的生命施加侵害,例如不得自我傷害并防止他人侵害。(2)硬核之外的自由,因為無關于生命的保全,這也就不在霍布斯的處理范圍之內。(3)作為硬核之必要條件的自由,意即人們基于這一硬核因互相疑懼他人對自己可能之傷害(hurt)而采取的先發制人的行動。(4)侵害(injury)硬核的自由,即純粹的以征服為樂。依照霍布斯的論述,(2)和(3)都屬于限度之內的自由,是被允許的,但(4)屬于對自由的超限使用,則應當予以禁絕。(L77)但是無論是(3)還是(4),它們于外在行動上都對他人的生命造成了阻礙,引發戰爭狀態,因此在契約程序中是應當被予以放棄或轉讓的內容,意即應當予以限制的自由,這也就是霍布斯所謂的“管理自己的權利”(L131)。但由于(3)是基于自我保全的被動防衛,只有在侵害到自我保全這一硬核時才被激發而被允許臣民重新獲取,而(4)則是基于純粹征服的主動侵犯,直接指向他人的自我保全,因此這是必須要嚴格禁絕由個人來行使。
在國家建立之后自然意義的自由就轉化為公民意義的自由,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市民自由和作為政治成員的臣民自由,前者是與主權建構的目的無關的自由,后者則是與主權建構相關的自由,霍布斯稱之為“真正的臣民自由”。
1.市民自由(civil liberty)。即一般意義上的臣民自由(the liberty of subjects),意即“在法律未加規定的一切行為中,人們有自由去做自己的理性認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L164),意即在民約法不需要采取特別規定的情況下個人由完全自行決斷的自由,它是由“自我保全”這一硬核之外的天賦自由所轉化而來的自由。(1)市民自由是民約法可以保持“沉默”的領域,“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訂出足夠的法規來規定人們的一切言論和行為,這種事情是不可能辦到的;這樣就必然會得出一個結論說:在法律未加規定的一切行為中,人們有自由去做自己的理性認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L164)。(2)市民自由是主權建構目的所規定范圍之外的社會權利,“如買賣或其他契約行為的自由,選擇自己的住所、飲食、生業以及按自己認為適宜的方式教育子女的自由,等等”(L165),這些終究是無害于主權建構目的的,亦即市民所享有的那些廣泛社會自由。(3)市民自由是經由民約法過濾之后所保留下來的天賦自由,兩者外延并不相同,“人們很容易被自由的美名所欺騙,并由于缺乏斷判力不能加以區別,以致把只屬于公眾的權利當成了個人的遺產和與生俱來的權利”(L167),市民行使此種自由時要時刻記著“主權的權威”,“然而我們不能認為生殺與奪的主權由于這種自由而被取消或受到限制。”(L165)
2.真正的臣民自由(the true liberty of a subject)。亦即“雖然主權者命令,但臣民可以拒絕不做而不為不義”(L168)的自由。(1)臣民可以拒絕主權者特定命令的自由,意即臣民面對主權者的絕對權威時依然可以自我決斷的權利。(2)由臣民作為硬核的單純自我保全的天賦自由轉化而來的,人們因單純的自我保全而具有絕對的自衛權,這是不可轉讓也不可剝奪的自由。(3)被激發的自由,在國家狀態之下當主權者超出主權建構目的范圍去行動而侵害到公民的硬核自由時,單純自我保全的天賦自由就從休眠狀態被激活;其實質是臣民對主權者特定命令的抵抗權利,它表明公民出于主權建構目的的政治義務、繼而出于天賦自由而來的自然義務可以抵抗主權者。(4)公民在國家狀態下所保留的最后的自我保全方式。一般而言,在國家狀態下人們自我保全的唯一正當方式便是主權權威,意即民約法。真正的臣民自由被啟用,意味著人們開始棄用主權權威,開始運用自身的力量來實現自我保全;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可以任意地行使之前所放棄的先發制人的權利,更遑論純粹征服的權利。
3.公民意義自由的分層結構。很顯然,無論是無害的市民自由,還是真正的臣民自由,都不會是霍布斯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他真正的關注是主權者的權利,換言之,也就是主權者的自由。主權者的自由有著雙重構成:(1)作為人造人格的自由是建構出來的,也就是自然人相互約定所放棄的先發制人的自由和純粹征服的自由,經由契約程序和共同授權就就被轉化成“公共的和平與安全”。這是主權建構的目的之所在,從而構成了公民意義之自由的硬核,成為主權者絕對的權利領地;在此領地之內,主權者享有絕對的行動自由。(2)作為自然人格的自由則是由其自然意義的自由完整地轉化而來的,包括全部的人身自由和天賦自由,在臣民那里被放棄的先發制人的自由和純粹征服的自由,在主權者這里卻完整地被保留了下來。人造人格是抽象規定的公共人格,而自然人格則純粹是具象規定的私人人格,因此主權者的兩種自由可稱之為“公共自由”和“私人自由”。依照公共人格的邏輯規定,主權者應當完全地遵照主權建構的目的而行為,但主權者卻因為私人人格的保留(意即他們還擁有全部的天賦自由)而被允許采取完全單方面的意愿行為。(3)正是由于主權者完整地保留了其先發制人和純粹征服的自由,所以公民的硬核自由必然面臨著被主權者侵害的風險。當主權者的任性行為侵入到公民的自由硬核之時,就“真正的臣民自由”就會被激發。真正的臣民自由在國家狀態下并不是顯性存在的,只有當主權者的私人人格背離公共人格之時才會被激發。(4)市民自由雖然無涉國家狀態下的自由硬核,但其范圍和邊界因為主權者私人人格的存在,而始終是模糊的、變動的,他取決于主權者自身基于對自然法的理性良知而做出的自我克制程度。
四、公民服從的相對性及其證成
自然人對主權者的授權以及臣民對主權者的承認,并不意味他們對主權者自身先在性天賦自由進行了限制,“臣民對于主權者的承認包含在這樣一句話中:我授權于他的一切行為或對之負責。這里面對他自己原先具有的天賦自由并沒有任何限制”(L169)。因此,主權者完全有可能會基于他自己的天賦自由而發出違背主權建構目的的命令,造成臣民無法實現自我保全。霍布斯對真正臣民自由的認肯,他以否定的方式標示了主權者應當承擔基于主權建構之目的的公共義務,主權者基于私人人格的行為應當以不破壞公共人格為其底線。“自我保全”這一自然權利既為主權者絕對權威的正當性提供了證成,也為主權者的行動劃定了行動的邊界,一旦主權者突破如此底線而發出命令,臣民也就可以正當地啟用其天賦的權利來實現對其自由硬核的保護,“任何人都不因語詞本身的原因而有義務要殺死自己或任何其他人”(L169),這里的“語詞”當然指向的是主權者的命令。
霍布斯指出,公民對主權者的某些特別命令無論如何都是可以絕對抵抗的,換言之即便絕對抵抗會直接挑戰主權者的權威,公民依然能夠行使而不失為不義。在《利維坦》第21章的第11-13節給出三種的情況:(1)主權者命令其自殺(例如絕飲食、斷呼吸、摒醫藥)的自由;(2)主權者命令其自傷、自殘以及對人身攻擊不抵抗的自由;(3)主權者命令其自證其罪而得不到寬恕承諾的自由。另外根據人身自由還可添加(4)主權者命令其剝奪自己身體自由的自由(意即鎖拿和監禁),因為霍布斯幾乎總是把免于鎖拿和監禁的權利同避免傷害和死亡的權利相提并論。1第14章論述第一自然法時,在聲稱“如果有人以武力攻擊一個人,要奪去他的生命,他就不能放棄抵抗的權利”之后,霍布斯立馬就說,“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傷害、鎖鏈或監禁。”在這一章的后面,他說:“任何人都不能讓出或放棄自救于死亡、傷害或監禁的權利。”這里所提的問題是,這些絕對抵抗的權利在邏輯上應該如何從自我保全這一自然權利中充分地推論出來。第(1)項權利,即“違抗命令去做那些能使人死亡的事情的權利”,是對自我保全這一自然硬核的直接違背,對此無需做推論。第(2)項“抵抗傷害的權利”、第(3)項“反對自證其罪的權利”以及第(4)項“抵抗監禁的權利”需要推論,因為諸如“傷害”“自我控告”“監禁”等命令形式并不就直接導致死亡。即便我們能夠確定這些行為并不會必然導致死亡的這一結果,但霍布斯依然認為需要臣民保有這些方面抵制的權利。他給出的理由相當簡單:“如果有人以武力攻擊一個人,要奪去他的生命,他就不能放棄抵抗的權利……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傷害、枷鎖或監禁。”(L100)雖然“當一個人看見人們以暴力對待他時,不能預先估定他們是不是要置自己于死地”(L100),但在此時如果他放棄了抵抗傷害、鎖拿和監禁之命令的權利,實際上也就是把自己置于暴力死亡的潛在狀態之中;傷害總是會危及生命,當某人毫無戒備地袒露于他人的武力之下,他的安全就會受到威脅。正是基于對暴力死亡的合理預期,公民就有必要保留對來自主權者命令的絕對抵抗權利。只要公民真誠地認可自我保全的欲望和暴力死亡的恐懼,他們也就必然地會要求保留抵抗傷害的權利,即便是在國家狀態之下面對主權者的命令之時也不例外。對此,蘇姍就認為,只要基于合理的猜疑就能得出臣民保有絕對抵抗權利的必要性,雖然在公民社會中合理的期望原則通常而言是有效的。2Susanne Sreedhar, Hobbes on Resistance: Defying the Leviath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40-47.
但筆者認為,僅基于合理的預期不能就對公民的絕對抵抗作出充足的論證,這只能算是一個具有合情理的推理。因為,很顯然,公民能夠對主權者的命令進行“合理的猜疑”,就意味著公民在相互訂約、共同授權時并沒有把相互猜疑、先發制人的天賦自由給轉讓出去。事實上,霍布斯認為,自然人共同授權時就表明了他們信任主權者會在將來履行他們的所托,這就表明了霍布斯相信公民在國家狀態下已經全部讓出了對主權者進行猜疑的權利。本文認為,公民在這些不能直接導致死亡的事項上也應當保留絕對抵抗的權利,不僅是出于“支配自己身體”的需要,更是出于“更好的生活”的需要。在論述權利的讓出之時,霍布斯就提出了除“保全生命”之外更多的目的設定:“像這樣放棄權利、轉讓權利的動機與目的,無非是保障一個人使他的生命得到安全;并且保障他擁有既能保全生命,而又不對生命感覺厭倦的手段。”(L100)在《利維坦》第二部分“論國家”的開端,霍布斯便給出了國家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使得人類能夠“保全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更為滿意的生活”(L128)。換言之,人們進入社會不僅僅是出于保全自己生命的遠見,還有著得到更為舒適的生活的預期。國家有義務為人民提供安全,“所謂的安全還不單純是指保全性命,而且也包括每個人通過合法的勞動、在不危害國家的條件下可以獲得的生活上的一切其他的滿足。”(L260)只有如此安全的保障,才可以使人產生恐懼的合理理由不復存在,即只要他不冒犯別人,他就沒有合理的根據恐懼他們,而自然的狀態中“舉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進口商品的運用、舒適的建筑、移動與卸除須費巨大力量的物體的工具、地貌的知識、時間的記載、文藝、文學、社會等等”不得穩定、無法存在的這些舒適生活也將得到實現。(L94-95)。在政治國家中,財產法使人們能夠享受他們的勞動成果,因為只有當一個人的努力被認為是值得、并具有穩定預期的時候,幸福、滿足、享受才有可能。既然公民進入國家是基于對更好生活的希望:“使人們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對死亡的畏懼、對舒適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過自己的勤勞取得這一切的希望”(L96-97),那么“主權者為公民的幸福所能做的不過是使他們能享受由于他們的勤勞而為自己贏得的財產以及使他們免于內外戰爭的困擾”,1Thomas Hobbes, On the Citiz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44.于是公民也就完全有理由為著“更好的生活”而保留抵抗主權者命令其進行自我傷害、自我監禁或自我指控的權利,因為這些命令把他們置于暴力死亡的恐懼、美好生活的絕望以及勞動致富的幻滅之中。主權者所應提供的保護,不限于臣民的自由硬核,它還涵蓋著臣民想要的舒適生活,2Eleanor Curran, Can Rights Curb the Hobbesian Sovereign? Law and Philosophy, vol. 25, 2006, p. 250.主權被建構是不僅只是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且還為了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意即意味著生活得好。3Howard Warrender,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omas Hobb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81.
霍布斯還列舉了公民可視不同情境選擇是否服從主權者的特定命令。在《利維坦》第21章14-16節列出了四種情形:(1)主權者對臣民所下的自己殺死自己或殺死其他人的命令;(2)主權者對臣民所下的對自己有危險的命令;(3)主權者對臣民所下的去做顯得不榮耀之事的命令;(4)主權者對臣民所下的奉命殺敵的命令。由于(1)直接與主權建構的目的相背離無需討論,而(4)完全可以被(3)所吸納,因此這里只需要論證的是(2)和(3)。如上臣民自由被激發的條件,取決于主權者的命令是否會造成主權建構目的無法達至:“當我們拒絕服從就會使建立主權的目的無法達到時,我們便沒有自由拒絕,否則就有自由拒絕”(L169)。當然這一目的也就是“公共的和平與安全”。主權者命令做不榮耀或危險之事時臣民是否有義務服從,取決于如此行動是否會造成主權的終結;如果臣民遵照主權者命令去做如此之事會造成主權建構的目的無法實現,那么他們就被允許激發不服從的權利。
那么現在問題就轉化為,如何判定或誰來判定他們的相對服從是否會造成主權建構目的不可達至?霍布斯認為,只要公民能夠普遍性擁有足夠多的認知,那么判定就應當交付給公民來行使。(1)邏輯規定上應該由臣民自己做出判定。既然自然人決意通過契約授權的方式產生主權者,那么這實際上已經預設了他們已然知道契約行動的初衷和條件,據此也就需要他們自己做出判斷用以確定主權者的命令是否違背了主權建構的目的。“任何人都不能以對自然法的無知作為借口,因為每一個人達到運用理智的階段以后都應當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L211)(2)公民具有充分的理性認知,能夠做出正確的推理并得到明確的結論。相互約定、共同授權本身就是一個理性的行動,也就是意味著立約者亦即授權人已經是具有充分理性能力的存在,在國家狀態之下他們完全有能力做出正確的判定。因此,“應該由公民做出判斷”其實不是一個道德意義上的“應該”而是認知意義上“應該”。(3)公民具有理性反思能力,這表現在公民會承認存在著“自己的無知”從而做出錯誤的抵抗行動:“因為這一主權既是他為了自己的防衛而自行同意建立的,他就應當看到哪些事和主權不相容,并且應當看到這種與主權不相容的自由是由于對其惡果無知才被授予的。”(L235)只要公民具有理性判斷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那就應當交由公民自己來進行判斷。
當然,這并不是一個單方面的行動。在國家得以建構之后,主權者還承擔對公民實施政治教導的職責。實施主權義務教導的政務大臣,“有權教導或使他人教導人民認識其對主權者的義務,教導他們有關什么是正義和什么是不義的知識,因而使他們彼此之間能更加虔誠地、和平地生活并抵御共同敵人”(L188)。公民不僅會被教導要服從主權者,而且還會教導知曉服從的理由;換言之,他們將被教導國家得以建立的基本原則和理由,這些應該是他們公民義務的基礎。因此,公民在決定是否具有可以違抗主權者命令的權利之時,要先行確保公民能夠接受到充分的教導而具有做出正確判斷的能力。因此,在一個由英明的主權者治理的秩序井然的國家中,我們可以預期公民能夠就各種突發性的問題做出正確的判斷。
不過,在此可能依然會有人提出質疑:即便臣民受到了充分的公民教育,知曉了他們的政治義務及其理由,但他們依然可能會基于自私的理由來做出判斷;那么,如此一來豈不依然會導致公民各種的不服從,而且范圍還會無限地擴大?的確,擁有理性能力與作出正確判斷這兩者在事實上并不一致,主權者和公民完全有可能是僅出于“主觀的”意圖而做出判斷。但實際上霍布斯并不真的就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如果公民的不服從明顯地會使得主權建構的目的本身遭到重創、甚至否定,那么主權者完全可以憑借其絕對的權威來強迫臣民服從。此時無論公民是否出于“自私的理由”做出主觀判斷,面對主權者絕對的權威實際上都無關緊要。如果公民的相對服從并不會造成主權建構的目的本身無法達至,那么此時即便公民是出于“自私的理由”做出主觀的判斷,那又有什么關系呢?霍布斯只是假設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將會知道什么類型的自由可以被授予所有的人,從而作出他們自己的行動考量;至于是否是出于“自私的理由”而做出的主觀判斷,對于公民的相對服從的證成都沒有實質性的影響。與此同時,當霍布斯把自由完全界定在外在的運動之上而全然無涉內在的運動時,公民無論是否是出于內在主觀的自私理由,對于利維坦的運行來說都已然是不足道哉之事了。
五、結語:霍布斯的思想史使命
依據自由權利的先在性及絕對性、契約授權的有限性以及人民對更為美好生活的期待等,我們可以較為充分地推論出真正的臣民自由及公民相對服從,這足以改變霍布斯作為絕對權威主義者刻板印象。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霍布斯的這一推論始終都是以對主權的范圍做出嚴格的界定并貫穿始終為前提的,而且這一前提與主權者權威的絕對性之間始終是相容的。從實際呈現的效果來看,霍布斯所闡述的公民意義的自由,其內部本身的分層結構是比較復雜的,而且與自然意義自由的內部分層結構也不是簡單的同構關系,要想對此做出清晰的辨明并不容易,以至于諸如芬克爾斯坦等人對霍布斯的論證有效性保有高度的懷疑也情有可原。1Claire Finkelstein, A Puzzle about Hobbes’s Right of Self-Defense,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82, no. 3-4,2001, pp. 332-361.說到底,公民的自由包裹著自然的自由,不僅主權者全部的自然自由被完整保留,而且臣民硬核的自然自由也被得以保留,并且兩者因自由的先在性都具有絕對性的規定;這在客觀上必然導致政治自由內部的界線模糊甚至與外部自然自由之間的界線模糊。當然,這種模糊并不是霍布斯政治哲學自身的邏輯混亂,只要始終把握國家建立前后自由硬核的變化就能看出,霍布斯的政治哲學體系始終有著比較清晰的邏輯規定。蘇姍通過引入新的解釋原則以霍布斯的名義構建了反抗權理論,并且認為如果我們對霍布斯的絕對主權理論和反抗權理論都能夠加以正確理解的話,這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2Susanne Sreedha, Hobbes on Resistance: Defying the Leviath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69-170.但經辨析可以發現,其實我們沒有必要引入新的解釋原則,只要緊緊抓住自由的先在性、授權的有限性以及自由硬核轉化的規定性就可以推論出臣民自由和公民相對服從的結論。
盡管如此,因為主權者和臣民在“權力”擁有上是絕對不對等的,所以霍布斯所說的公民抵抗權理論的現實有效性是比較弱的,其現實效力是大打折扣的。霍布斯雖然道明了主權者應當接受自然法的限制,不應做不公道之事,“公道作為自然法的誡條來說,上自主權者、下至最卑賤的臣民,都同樣必須服從”(L268),“所有的主權者都要服從自然法,因為這種法是神設的,任何個人或國家都不能加以廢除。”(L253)但若主權者真的違背自然法而做了諸如“處死一個無辜的臣民”這樣直接傷害公民自由硬核的事情,霍布斯也認為并沒有對臣民構成侵害,這只是不合道義的事而不是不合正義的事(L165)。事實上,自然法所能限制的只是作為自然人格的主權者而非人造人格的主權者。但問題的實質在于,自然法只是具有“應然的力量”而缺乏“實然的力量”——自然法只是道德的誡命。主權者與臣民因為所擁有的權利、特別是權力上量的差異,在國家狀態下其地位必然地是絕對不對等的,主權者基于其代理人的身份可以做出任何的超限行動卻不受實質性的約束,但公民除了保留適度的不服從權利則別無他途,他們終不能自外于國家主權而尋求權利的保障。對于主權者而言,即便他們有著充分的理性良知愿意遵從自然法而行動,但這一良知意愿在人造人格所合法地賦予他們的真真切切的無限權力面前是脆弱不堪的。更何況在國家狀態下,主權者本人依然正當地保留了自身完整的自然人格,同時還加持了因人造人格而來的無限合法權力,因此臣民并不能懷著道德之愿而期待主權者自始至終都能自律地不為所欲為,做有德性的有為之君。霍布斯消除了臣民之間的自然狀態,但他卻在更高的層面上創造了自然狀態,也就是主權者與臣民之間始終處在潛在或顯在的戰爭之中,主權者實際上可以侵害臣民的自由硬核,這雖不合道義但卻不為不正義。只要主權者在擁有人造人格的同時保留著完整的自然人格,就不能寄希望他們單憑道德德性就能自我克制、公道高尚。由于霍布斯契約-授權程序的單向性,臣民并沒有要求主權者反向地與他們訂立任何以言辭標明的契約關系——所謂契約其實質是所有愿做臣民的那些自然人之間的相互約定而已,他們只是期望主權者具有良好的理性認知和公道良知,而此他們的硬核自由無論如何都得不到連貫一致的有效保證。沒有臣民反向地與主權者之間的制度建設,就不會有真正的臣民自由。如此的理論困境,相信進入知天命之年才寫就《利維坦》這一皇皇巨著的霍布斯絕不可能會懵懵然,但他依然信誓旦旦地做出臣民自由的推論,其真實的意圖就不得不令人懷疑。或許這只是霍布斯對其利維坦體系必然要面對挑戰和質疑的一種緩沖性處理手法,用于堵悠悠眾人之口,而他本人并非就是真的相信。事實上,只要不把維護自由權利確定為主權國家的至上性目的,并把主權者本人也納入契約的當事方,籍此從根本上消除其人造人格和自然人格的分裂,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臣民自由,公民也就沒有實質性的不服從權利。
基于霍布斯政治哲學體系的整體性來看,臣民自由和公民相對服從的推論盡管有著顯著的思想史價值,但我們依然可以判定這并不是霍布斯所要完成的目標任務。我們不應著急于用權威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的標簽來簡單地定位和解釋霍布斯。霍布斯對自由之先在性及絕對性的認肯始終貫穿在他的政治哲學始終。無論國家建立前后他對此都沒有進行否定,甚至還明確地提出了“人生而自由”這一自由主義的經典命題。但就歷史任務而言,霍布斯的主要工作并不在于要對此自由權利予以證成,而在于用以確保自由權利所必需的秩序應該是什么以及這一秩序如此才能夠有效地建構出來。換言之,霍布斯所看到的是,鑒于自然自由所具有的破壞性,需要我們做出何種行動以消除無序,他論證的目的指向的是“國家主權”這一自由必要保障條件的基礎性地位。有學者認為霍布斯建構利維坦的目的意在一種“擴展的保護”,意即“主權者必須為商業社會提供背景條件,推行穩定、簡單的法律秩序等政策,提高臣民取得和使用財產的能力”;因此,公民“服從的目的不僅是保護人,而且是保護財產及其使用,也就是說,保護舒適生活的機會”。1Christopher R. Hallenbrook, Leviathan No More: The Right of Nature and the Limits of Sovereignty in Hobbe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78, 2016, p. 179, p. 193.這顯然對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做出了過多的期待和過度的解讀。對自由權利的證成及其實現,在霍布斯這里即便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主要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固然可以承帶出“擴展的保護”,但他對國家所應當具有之任務的論爭意在“實現自然法”,而全部的自然法都意在落實“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然權利,這一結論是明確的。2王曦:《試論霍布斯法哲學思想之思維方式》,《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就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演進來看,霍布斯著力于對主權國家建構的論證,除卻有著理論規定上優先性——他對主權權威之絕對性的證成毋容置疑地優先于臣民自由的推論,還有著歷史生成意義上的優先性。霍布斯之后的洛克所著力論證的才是對自然自由的內涵與構成的闡述,他所做出的部分授權、有限政府、反抗暴政等方面的論證,其目的都在于用于確保自然自由的實現,特別是不受主權者的侵害。在此意義上,政治哲學史把洛克而不是霍布斯看作是自由主義的創始人的確是有其道理的。霍布斯的思想史使命在于,他固然看到了自由的重要性,但他更為看重的是秩序,沒有秩序的建構,任何的自由都免談,而秩序的建構則需要絕對的權威。因此,無論是邏輯規定意義上,還是歷史生成意義上,霍布斯在洛克之前都具有必然性。通過霍布斯的工作,洛克論證其自由主義學說時的前置性理論任務已經被解決,因此他的思想史的任務就在于確證和保障“自由”這一價值的至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