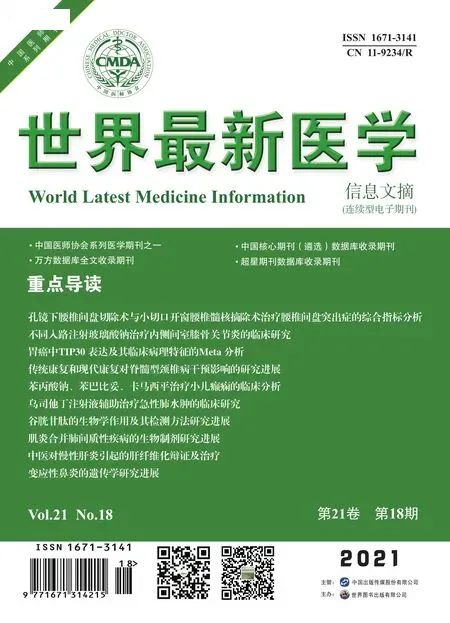外周血血小板和白細胞評估PD-1 抑制劑治療晚期非小細胞肺癌預后的價值
王衛杰,張麗麗,康馬飛
(桂林醫學院附屬醫院腫瘤內科,廣西 桂林 541001)
0 引言
肺癌是我國發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排第一位的惡性腫瘤,其中非小細胞肺癌(NSCLC)約占全部肺癌的80%,約70%的患者在診斷時已處于局部晚期或有遠處轉移,喪失了根治性手術機會,以含鉑類藥物為基礎的聯合化療在中晚期肺癌的療效已達到瓶頸[1,2]。分子靶向治療如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KI)在表皮生長受體(EGFR)基因敏感突變的病人的治療中有了巨大進步。近年來,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肺癌的治療中也進步很大,近年來在臨床治療和科研創新中都受到了廣泛關注成為腫瘤研究熱點[3]。一線pembrolizumab 單藥治療在未經治療的程序性細胞死亡配體1(PD-L1)表達≥50%的晚期NSCLC 患者中比化療有OS 優勢[4],在對PD-L1 陽性腫瘤的老年晚期NSCLC 患者的分析中,與化療相比,pembrolizumab改善了OS,具有更高的安全性[5]。目前公認的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療效有預測價值的生物學指標有PD-L1 高表達[6]、微衛星高度不穩定(MSI-H)[7]和腫瘤突變負荷(TMB)高[8]。那么,是否還有其他指標對評估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患者預后有意義呢?本研究分析血小板與白細胞比值(PWR)、血小板與淋巴細胞比值(PLR)和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LR)與接受PD-1 抑制劑治療的晚期NSCLC 患者的預后的關系,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8 年1 月至2020 年7 月20 日于桂林醫學院附屬醫院確診的中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臨床資料。入選標準:①年齡大于18 歲。②所有患者免疫治療前均接受胸部CT 等檢查,經過纖維支氣管鏡或CT 引導下肺穿刺取病理,證實為NSCLC。③按照美國癌癥聯合委員會第8 版腫瘤分期確定腫瘤的TNM 分期為Ⅲ-Ⅳ期。④無心、肝、腎等重要臟器嚴重并發癥。⑤ECOG 評分2 分及以下。⑥均在我院首次接受PD-1 抑制劑治療。⑦患者首次接受PD-1 抑制劑治療前兩周內均檢驗血常規指標。排除標準:①伴有其他惡性腫瘤。②SCLC 或非原發NSCLC 者。③存在出血或急慢性感染者。④存在肺栓塞、急性心肌梗死、腦血管疾病者。⑤臨床資料不全者。共收集486 份患者資料,其中符合入選標準者148 例,失訪14 例,入選134 例。納入的134 例患者年齡31~84 歲,男99例,女35 例;年齡<60 歲48 例,年齡≥60 歲76 例;腺癌55 例,鱗癌79 例,Ⅲ期58 例,Ⅳ期76 例。

表1 PWR、PLR、NLR 與134 例NSCLC 患者臨床特征之間的關系
1.2 信息采集
通過病案管理系統收集患者資料,包括性別、年齡、病理分型、發病部位、TNM 分期、遠處轉移個數、吸煙、飲酒和是否根治性手術。收集患者首次接受PD-1 抑制劑前兩周內血常規指標,包括中性粒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白細胞計數、血小板計數,計算PWR、PLR 和NLR。
1.3 隨訪
利用病案記錄,以患者首次接受PD-1 抑制劑治療前兩周內血常規指標作為觀察起點,對治療后出院的患者采用電話方式每3 個月隨訪1 次,隨訪截止時間為2020 年7 月20 日,隨訪率為90.5%。生存時間為首次接受PD-1 抑制劑治療日期至死亡日期或者至末次隨訪時間。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 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PWR、PLR 及NLR 與患者臨床及病理資料(性別、年齡、病理分型、發病部位、TNM 分期、遠處轉移個數、吸煙、飲酒、是否根治性手術)的關系采用χ2檢驗。采用Kaplan-Meier 法計算生存率,不同分組患者生存率的比較采用Log- rank 檢驗。采用多因素Cox 模型分析預后的獨立影響因素。檢驗水準為α=0.05,P<0.05 具有統計學差異。
2 結果
2.1 晚期NSCLC 患者PWR、PLR 及NLR 與患者臨床特征的關系
本研究以所有統計患者的PWR、PLR 及NLR 平均值作為截點,通過SPSS 22.0 軟件對全組患者進行描述性分析,統計得出PWR 的均值為41.64,PLR 均值為237.77,NLR 的均值為4.56。將PWR ≥41.64 定義為PWR 高值組,將PWR<41.64 定義為PWR 低值組;PLR ≥237.77 定義為PLR 高值組,PLR<237.77定義為PLR 低值組;將NLR ≥4.56 定義為NLR 高值組,將NLR<4.56 定義為NLR 低值組。對不同PWR 組、PLR 組和NLR組患者的性別、年齡、病理分型、發病部位、TNM 分期、遠處轉移個數、吸煙、飲酒和是否根治性手術進行比較。結果顯示,高PWR 組和低PWR 組患者在年齡(P=0.049)、M 分期(P=0.027)、TNM 分期(P=0.019)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高PLR 組和低PLR組患者在T 分期(P=0.040)、N 分期(P=0.044)、M 分期(P=0.028)、遠處轉移個數(P=0.019)、吸煙(P=0.011)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高NLR組和低NLR組患者在T分期(P=0.020)、M分期(P=0.030)、遠處轉移個數(P=0.038)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見表1。

圖1 高PLR 組與低PLR 組的OS 比較

圖2 高NLR 組與低NLR 組的OS 比較
2.2獲得隨訪的134 例晚期NSCLC 患者,截至2020 年7 月20 日,共計死亡25 例,中位存活時間為14.0 個月。其中,低PLR 組1、2 年生存率分別為72.5%和48.3%,高PLR 組分別為36.9%和18.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7);低NLR 組1、2 年生存率分別為66.5% 和44.3%;高NLR 組分別為33.6%和16.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2);PWR 高低兩組預測NSCLC 患者無顯著性差異(P=0.702)。不同分組的Kaplan-Meier 分析生存曲線見圖1、圖2 和圖3。
2.3 單因素分析
結 果 吸 煙(P=0.001)、T 分 期(P=0.006)、PLR(P=0.021)、NLR(P=0.037)是影響NSCLC 的PD-1 抑制劑治療患者生存時間的危險因素(表2)。COX 多因素分析顯示:在所有納入的自變量中只有吸煙(P=0.006)、T 分期(P=0.014)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表3)。
3 討論
外周血中評價全身系統性炎癥反應的指標包括格拉斯哥預后評分(GPS)、C 反應蛋白(CRP)、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LR)、血小板與淋巴細胞比值(PLR)和淋巴細胞與單核細胞比值(LMR)等,其中GPS 評分、CRP 的預后價值最為明確[9]。有研究表明,淋巴細胞的定量改變在癌癥患者中是常見的,并強烈影響預后和生存。免疫系統的狀態(如絕對淋巴細胞計數及其亞群、腫瘤CD8+T 細胞浸潤等)現在被認為是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療效的一個重要的生物標記之一[10]。NLR 與多種腫瘤預后相關,中性粒細胞數量在腫瘤組織中大量增多及淋巴細胞減少,局部免疫應答減弱時,往往提示腫瘤患者預后不良。研究表明,外周血NLR 與晚期NSCLC 的預后密切相關[11,12]。在接受PD-1/PD-L1 抑制劑治療的NSCLC 患者中,血NLR 升高與PFS 和OS 縮短相關,具有潛在的預測和預后價值[13]。本研究結果顯示,低NLR 組1、2 年生存率分別為66.5%和44.3%,顯著高于高NLR 組(分別為33.6%和16.8%),也說明低NLR 的患者生存明顯好于高NLR 患者,與上述研究結果相似。對于接受PD-1/PD-L1 阻斷的晚期惡性腫瘤患者,基線和治療期間的NLR 是預后指標。基線NLR ≤4 和治療期間較低的NLR 可能與疾病控制和治療反應相關,基線和縱向NLR可能作為一種獨特的生物標志物,對接受免疫治療的患者的臨床決策有幫助[14-15]。該指標不僅在肺癌的PD-1 抑制劑的治療中有預后評估價值,在其他腫瘤如黑色素瘤患者[16]的PD-1 抑制劑的治療中同樣有預后評估價值。

圖3 高PWR 組與低PWR 組的OS 比較

表2 影響NSCLC PD-1 治療患者生存時間的單因素分析

表3 影響NSCLC PD-1 治療患者生存時間的多因素分析
PLR 是血小板與淋巴細胞的比值,可以反映二者的相對變化,其升高反映了血小板計數相對增多或淋巴細胞計數相對減少,均可影響腫瘤患者的預后。研究證實,PLR 可影響EGFR突變的NSCLC 患者的預后[17]。PLR 和NLR 不僅代表外周血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和血小板計數,還可以反映腫瘤患者外周血粒細胞、淋巴細胞和血小板的失衡狀態。在接受nivolumab治療的轉移性NSCLC 患者中,治療前NLR 和PLR 升高與較短的OS 和PFS 以及較低的應答率相關,而與其他預后因素無關[18]。通過對使用PD-1 抑制劑治療的多種晚期腫瘤的治療結果分析,發現低PLR 組的中位PFS 和疾病控制率均顯著高于高PLR 組[19]。本研究結果顯示,低PLR 組1、2 年生存率顯著高于高PLR 組,與上述研究結果相似。
NLR 和PLR 雙指標也是評估PD-1 抑制劑治療患者的療效的有用指標,無論癌癥類型,基線高的NLR 或PLR(單獨或聯合)均與較差的免疫治療療效相關,與病情穩定或病情進展的患者相比,部分或完全緩解的患者治療后NLR 和PLR 顯著降低,這表明它們可能是免疫治療療效的一個不可知的標記[20]。此外,NLR 和PLR 雙指標也是評估PD-1 抑制劑治療患者的預后的有用指標。研究認為,NLR 和PLR 水平高的NSCLC 患者使用nivolumab 的預后可能較差。因此,在預后不良的亞組患者中,特別是在PD-L1 陰性的患者和/或存在其他不良預后因素的情況下,采用替代治療策略可能是一種有價值的選擇[21]。在肺癌研究中,都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即NLR、PLR 高值惡性肺癌患者的預后較差[22-25]。在肝細胞肝癌的免疫治療研究中,在治療后NLR 和PLR 的復合模型中,高NLR 和高PLR 的組合與死亡風險增加8 倍有關,認為NLR 和PLR 在PD-1 抑制劑治療的HCC 患者中具有很強的預測作用[26]。
本研究分析了接受PD-1 抑制劑治療的晚期NSCLC 患者不同PWR、PLR 和NLR 與臨床病理特征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生存分析,并進行了單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NLR、PLR為接受PD-1 抑制劑治療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預后的預后指標,PWR 對接受PD-1 抑制劑治療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預后無影響。吸煙、T 分期是影響接受PD-1 抑制劑治療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預后的獨立因素。利用NLR 和PLR,結合年齡、性別、是否吸煙、TNM 分期等因素,能夠更好地判斷進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晚期NSCLC 患者的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