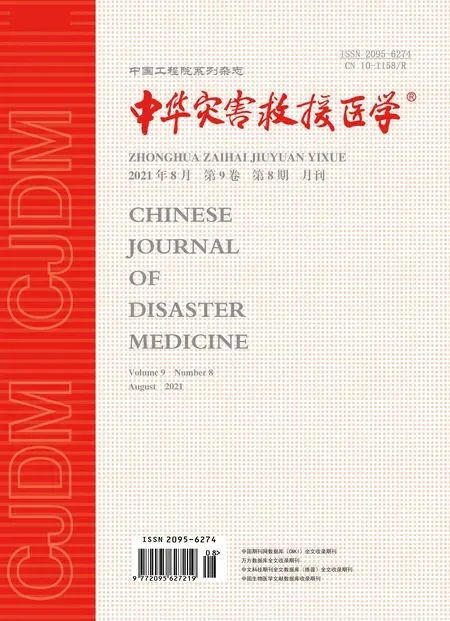便攜式超聲在戰場戰傷救治中應用與展望
張偉麗,彭碧波,李勝男,郭 靜,喻慧敏,席 梅
便攜式超聲診斷儀體積小、質量輕、移動靈活,攜帶方便,適合多種戰時環境的物理性能[1],自從1996年美國成功地研發可應用于戰場的便攜式超聲診斷儀,便攜式超聲應用于戰場、災害現場的探討與研究不斷增多[2]。本文首次系統綜述便攜式超聲在戰傷診斷以及便攜式超聲引導下急救操作兩個方面的價值,其中超聲檢查范圍包括胸部、腹部、顱腦、骨骼和軟組織;超聲引導下的急救操作包括,環甲膜切開、氣管插管,心包穿刺、動脈靜脈穿刺置管、腹腔穿刺操作等。總結便攜式超聲應用于戰傷診斷與救治的優缺點[3],以期為便攜式超聲在戰術區域推廣應用,提供參考。
1 便攜式超聲應用于戰傷救治中的理念提出與應用研究
1912年泰坦尼克號在大西洋中撞擊冰山發生沉船事故,激發了人們利用超聲波探測水下物體的想法。1916年,法國物理學家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領導的聲納技術研究小組,利用石英壓電晶體振動研制出能在水中傳播的超聲波,成功探測到水下潛艇并確定其位置[4]。1959年,Tom Brown發明首臺超聲相控陣檢測系統,并申請了專利。1964年,德國KK(Krautmer)公司成功研制小型超聲波檢測儀。1992年,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研制成功了數字式超聲相控陣實時成像系統。從1990年爆發的海灣戰爭到2001年爆發的阿富汗戰爭,美國與其北約盟國中有在野戰救護所使用便攜式超聲設備進行檢查的報道,但連級戰斗衛勤保障單元并無使用便攜式超聲檢查的報道[5]。Robert Magotti等人報道,在2010 年溫哥華冬季奧運會和殘奧會期間,使用袖珍超聲檢查設備,可以在室外狹小空間給傷病員做檢查[6]。
我國自1952年,由孫大雨、吳繩武等人自行設計電路,自行燒制鈦酸鋇壓電陶瓷,于1955年成功研制國產超聲波檢測儀,1988年國內第一臺數字化超聲波檢測儀的原理樣機研制成功[7]。2010年國內學者席梅首次報道了便攜式超聲儀在高原救災中的應用價值:玉樹地震災區的醫學救援。2016年國內學者呂發勤、黎檀實在國內首次提出戰場可直接應用便攜式超聲檢查的理念[8],首次論述便攜式超聲診斷在戰場的應用范圍與價值。
2 便攜式超聲在戰傷診斷的應用現況
2.1 便攜式超聲在腹部創傷中的應用子彈與炮彈碎片引起的腹部臟器破裂是戰傷救治面對重要損傷類型,包括穿透傷及鈍挫傷,其中脾臟破裂和肝臟破裂分別居腹部損傷的第一位與第二位。應用便攜式超聲,識別腹腔肝、脾、腎等內臟槍彈傷,非常方便,并對識別是否伴有骨盆或腹部實質器官損傷非常有幫助,早期發現是確定性治療的前提條件[9]。在沒有超聲診斷儀時,戰術區域只要懷疑有肝脾破裂時,除了加快后送,現場沒有止血方法,傷員死在轉送途中的比例高達1/3[10]。在沒有超聲檢查時,即使傷員后送到了野戰救護所,既往診斷肝脾破裂主要通過腹腔穿刺與灌洗液中發現大量紅細胞進行推理性診斷。
便攜式超聲診斷腹腔內臟出血,優勢明顯。腹部創傷超聲重點評估法(Focused Assessment with Sonography in Traumas,FAST)就是依靠超聲作為診斷設備,快速準確評估腹膜積血范圍,判斷傷者的嚴重程度[11]。Richards對808名腹部鈍性創傷患者進行FAST檢查,證實其在診斷腹腔內出血的敏感性為89%、特異性為99%,診斷準確性為99%[12]。
便攜式超聲可通過下腔靜脈或中心靜脈對血容量進行快速評估,通過下靜脈直徑和下靜脈坍塌指數(Inferior Vena Cava-Collapsible Index,IVC-CI)評估失血嚴重程度并對補液策略提供參考[13]。分別記錄復蘇后的中心靜脈壓(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下腔靜脈直徑值(Inferior Vena Cava-Diameter,IVCD),并計算出中心靜脈壓變化值,評估血容量非常準確。王志華等采用超聲評估腹部閉合性損傷患者休克狀態,證實IVC-CI可評估患者血容量狀況,且與休克指數呈正相關[14]。
腎絞痛、消化道穿孔以及膽囊炎等可以通過便攜式超聲快速、準確地診斷。在腎絞痛的診斷中,超聲可清楚顯示腎積水,結合腹痛和血尿等臨床表現,對腎絞痛的檢測敏感性為81~89%[15]。在膽道疾病的診斷中,膽石征象和墨菲征象陽性(超聲探頭推膽囊時有壓痛)是膽囊炎的簡易快速檢測方法。當這兩種結果同時存在時,急性膽囊炎的陽性預測值和陰性預測值分別為92%和95%[16]。
2.2 便攜式超聲在胸部創傷中的應用氣胸、胸腔積液、心包填塞是常見胸部戰創傷并發癥,便攜式超聲在胸部創傷中的早期診斷中顯示出很高的應用價值。便攜式超聲檢查胸膜腔通過“肺滑行”和“彗尾”征消失診斷氣胸,診斷敏感性和準確性遠高于X片,接近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CT)的效果[17]。Revzin 在對676例胸外傷患者的研究中發現,聽診檢測血氣胸的靈敏度在鈍挫傷患者為100%,在穿透性創傷患者僅為50%;超聲“肺滑行”和“彗尾”征氣胸的陰性預測值高達為99%,可以取代傳統的X線檢查。超聲還可篩查肺水腫,其診斷敏感性(100%)明顯高于肺部X線[18]。在高原作戰環境下配備超聲心臟矩陣探頭能監測患者左室收縮功能及瓣膜、室壁運動情況,可評估高原肺水腫嚴重程度與治療效果變化。
心臟穿透性損傷,心包積液和心包壓塞等急癥在戰現場環境中,體格檢查準確度很低,而便攜式超聲可清楚識別心包積液,其特異度為97%,靈敏度接近100%[19]。此外,超聲診斷上區分靠近心包的胸腔積液和心包積液非常有價值,有利于兩者的區別處理。
2.3 便攜式超聲在顱腦創傷中的應用便攜式超聲在顱腦創傷中的早期診斷中也顯示出很高的應用價值。顱內壓升高(Intracranial Pressure,ICP)提示顱內出血、血腫形成,甚至腦疝風險等,快速診斷和處理對閉合性顱腦損傷患者的生存至關重要,如未及時診斷,致死率高達90%[20]。神經系統檢查和體格檢查是ICP的常用手段,但其耗時較長且診斷價值不高。便攜式超聲檢查[21]視神經鞘5.2可提示顱內壓20 Hg,其靈敏度高達93.1%,特異性為74%,且腦脊液引流后視鞘直徑迅速下降[22]。高原腦水腫(High Altitude Cerebral Edem,HACE)是急性高山病的一種,具有較好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便攜式超聲測量視神經鞘直徑對顱內壓進行評估,可及時發現高原腦水腫[23]。
近紅外光譜(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NIRS)可直接穿透骨骼并深入組織下,可用于院前非侵入性顱內出血監測,顱內出血時,血腫內血紅蛋白的濃度顯著升高(濃度約為正常腦組織的10倍),血紅蛋白對NIRS吸光度大,因此血腫區域較正常腦組織對近紅外光譜的吸收更多,近紅外光譜檢查時透光性差的一側為顱內血腫。近紅外光譜配合便攜式超聲,聯合診斷顱內出血敏感性為91.18%,特異性為71.43%,與CT和MRI結果有較好的一致性[24]。
2.4 便攜式超聲在骨折中的應用戰場無法進行骨折X線檢查時,利用超聲檢查骨折具有重大意義。國內學者張宏波,韋福康2002年在《中國超聲醫學雜志》發文:骨折超聲顯像的實驗研究。汶川地震救援行動中,便攜式超聲在骨折診斷中的應用研究有大量文獻報道。最近幾年,便攜式超聲檢查骨折的聲像圖直接征象為骨折部位骨皮質強回聲帶連續性斷裂,相鄰斷端錯位或僅表現為輕微凹陷,間接征象為周圍軟組織增厚,回聲雜亂、不均勻[25]。葛永軍采用比格犬股骨骨折模型,證實在超聲引導下,指導骨折復位,復位時使用超聲指導有助于在夾板前確定復位的準確性。股骨骨折可獲得滿意的復位與固定,提示便攜式超聲儀可有效替代傳統X線機,尤其適合野戰環境下四肢骨折傷員的緊急救治[26]。Chartier等人通過Meta分析顯示,對2982名長骨骨折(包括肱骨,橈骨,尺骨,股骨,脛骨和腓骨)患者,超聲診斷骨折的敏感度為93.1%,特異度為92.9%[27]。此外,超聲對于X線平片難以診斷的隱匿性骨折,包括舟狀骨、肋骨、胸骨等具有更高的診斷價值。超聲診斷舟狀骨的敏感度為85.6%,特異度為83.3%,但相關研究均是在院內完成的,其在戰傷救治中的應用缺乏相關研究證實[28]。
3 超聲可視化技術輔助急救操作
3.1 超聲引導下環甲膜切開術在野戰救護室,環甲膜切開是侵入性氣道管理的首選方法。目前,緊急情況下使用超聲引導經皮環甲膜切開術仍有爭議,但Curtis等認為超聲引導經皮環甲膜切開術是一項快速、可靠的技術,在21例尸體標本上使用超聲引導經皮環甲膜切開,其中20例獲得成功,操作中位時間為26.2 s,該研究并未對比傳統觸診定位切開和超聲引導定位切開的操作時間。Siddiqui等在尸體標本上對比觸診定位和超聲引導定位經皮環甲膜切開,結果表明超聲引導定位能將導管植入成功率提高5.6倍,喉部和氣管損傷的發生率降至33%[29]。類似研究也發現,采用傳統觸診定位經皮環甲膜切開時氣管導管從環狀軟骨和第1氣管軟骨環之間置入(定位錯誤)的發生人數為5例(33%),氣管撕裂受損的人數為6例(43%),而超聲引導定位穿刺則分別為0例和4例(36%)。
3.2 超聲引導下氣管插管術便攜式超聲輔助下進行氣管插管,避免誤插入食管或單側支氣管的風險。超聲引導急診氣管插管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98%和94%,而無超聲引導的快速氣管插管的一次成功率為46~85%。此外,在氣管插管成功后,超聲檢查可以進一步觀察到胸膜滑動。當右側有胸膜滑動而左側無滑動時,可證實插入右側支氣管,靈敏度為95~100%,特異性接近100%。相比之下,呼氣末二氧化碳評估氣管插管的靈敏度為93%,特異性為97%,均低于便攜式超聲[30]。Zadel等對124例行院前緊急氣管插管的病例進行分析,在發生氣管導管誤入食管的13例(10.5%,13/124)患者中,通過視覺或聽診僅發現4例(30.8%,4/13),而超聲可確認氣管導管位置,其對導管位置判斷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均為100%,平均檢查時間為30[31]。
3.3 超聲引導下心包穿刺抽液術超聲檢查可望成為快速診斷心包積血和心包填塞的有效方法,并引導心包腔穿刺操作。對于已有癥狀的心包積血或心包填塞需緊急治療時,超聲引導下心包穿刺術將是一種安全、有效且易于操作的方法。一項多中心研究探討了超聲引導心包穿刺術的安全性[32],發現納入研究的各個醫療機構穿刺成功率均較高(91.7%~99%),并發癥的發生率也均較低,其中嚴重并發癥的發生率為1.2%,輕微并發癥的發生率為4.3%。對胸部或上腹部損傷的傷病員需及時進行心包腔的超聲檢查,以排除心包填塞風險,這對挽救傷病員的生命具有重要意義。
3.4 超聲引導下輔助動靜脈穿刺置管術超聲可視化技術可用于輔助深靜脈穿刺置管,如頸內靜脈、鎖骨下靜脈或股靜脈穿刺,可減少穿刺次數和穿刺置管時間,確定導管位置,降低靜脈導管誤入動脈、出血和氣胸等嚴重并發癥發生風險。一項隨機、前瞻性研究發現,通過體表標志定位的頸內靜脈置管成功率為78.5%,而超聲引導定位的頸內靜脈置管成功率為93.9%,成功穿刺置管的平均嘗試次數分別為1.6次和1.3次;此外,體表標志定位發生各種并發癥(包括血腫、動脈穿刺和氣胸)的發生率為16.9%,而超聲引導穿刺并發癥的發生率為4.6%[33]。有關體表標志定位和超聲引導頸內靜脈置管的meta分析發現,超聲可降低71%的并發癥發生率,減少了72%的誤入頸動脈的發生率和73%的血腫發生率,總體穿刺成功率增加12%。
3.5 超聲引導下神經阻滯麻醉超聲引導下區域神經阻滯是一種常見的麻醉技術,可在野戰醫院進行應用。區域神經阻滯通過阻斷外周神經傳導而緩解傷病員疼痛,且不影響傷病員意識、呼吸和循環,可減少阿片類藥物的使用,降低全身鎮痛藥物相關的不良反應,減輕醫療負擔。例如,超聲引導下股神經阻滯可有效緩解髖部骨折疼痛;超聲引導下腹橫肌平面神經阻滯是骨盆骨折緩解疼痛的有效方法,阻斷前腹壁神經可松弛腹肌,減少其對坐骨和恥骨的牽拉,而椎旁或肋間神經阻滯可用于肋骨骨折的鎮痛。在將傷病員送入后方醫療機構接受進一步救治前,可先對傷病員進行超聲引導下神經阻滯鎮痛治療,緩解疼痛。
3.6 超聲引導下輔助腹腔穿刺抽液術超聲可使穿刺部位可視化,保證穿刺的安全、有效。一項觀察性隊列研究探討了超聲對腹腔穿刺術后出血并發癥風險的影響,在69859例接受腹腔穿刺的患者中有0.8%(565例)的患者出現并發癥,而超聲可將出血并發癥風險降低68%[34],急診醫師分別使用超聲輔助和傳統方法進行腹腔穿刺成功率分別為95%和65%。
4 小結與展望
4.1 便攜超聲在戰傷診斷與救治中應用的潛能便攜式超聲在戰傷診斷與救治中具有多種潛能,但戰地使用便攜式超聲仍然需要進一步評估,等待軍隊戰傷救治規則修改后才可使用 盡管在連、營、團級作戰單元的醫療救治機構,便攜式超聲都具有應用潛能,但不能盲目擴大應用范圍。目前無論是外軍還是我軍,在連、營、團級作戰單元與醫療保障單元中,都沒有配備便攜式超聲診斷儀的許可性文件。美軍醫療救護手冊,也沒有把便攜式超聲應用連級戰斗單元的許可。在戰術區域使用便攜式超聲檢查,還需要充分論證,客觀評估,只有經過戰傷救護法規立法允許后才能使用。軍隊醫療后送遵循分級救治,階梯治療原則,只有在得到擴大救治范圍命令時,才允許擴大范圍。而在醫療轉送渠道暢通,不需擴大救治范圍時,就不必配置便攜式超聲檢查設備。另外,便攜式超聲在物理性能與機械設備方面,還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便攜式超聲為了減輕設備重量,一般只配備腹部探頭,因此檢查范圍較窄;超聲設備尤其是探頭怕碰怕摔,容易出現儀器故障;戰術一線非交火區中戰傷救治中,需處置傷員多、衛生人員少,未經過超聲操作訓練的衛生員,并未完全掌握超聲檢查技術;超聲圖像亮度低,灰階小,在普通日光照射下看不清圖像等缺點有待進一步解決。
4.2 便攜式超聲在戰傷救治中還有可以期待的更廣泛應用前景目前,便攜式超聲檢查與5G通信平臺相結合,可開展超聲遠程檢查,遠程傳送圖像,快速遠程會診,從而節省前方人員資源配置,減少高原、海島等遠距離人員投放的資源消耗。5G通信實時遠程傳遞圖像數據到后方醫院,由后方醫院人員進行診斷,從而降低了一線衛生人員的技術準入臺階,并提升診斷準確性。由于超聲診斷與急救的范圍拓展,軍隊一線醫療人員超聲操作技術應拓展到什么標準,值得進一步調研。
4.3 可穿戴超聲與醫療救援機器人的結合,將開啟機器人超聲診斷的新紀元便攜式超聲可智能化為可穿戴的超聲設備,可以由機器人搭載,成為超聲機器人,前伸部署到戰場或災害現場。超聲機器人可自主檢查,自主診斷,自主操作,戰場救護時擺脫對人工操作的依賴。加載有超聲診斷功能的智能機器人甚至要以具備超過人類的優勢,例如不怕疲勞,適應夜暗與惡劣的戰場環境、可在高原缺氧環境下持續工作,具備自動行駛、自動定位、自動識別路途障礙,代替人類進行傷員救治與后送,具有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