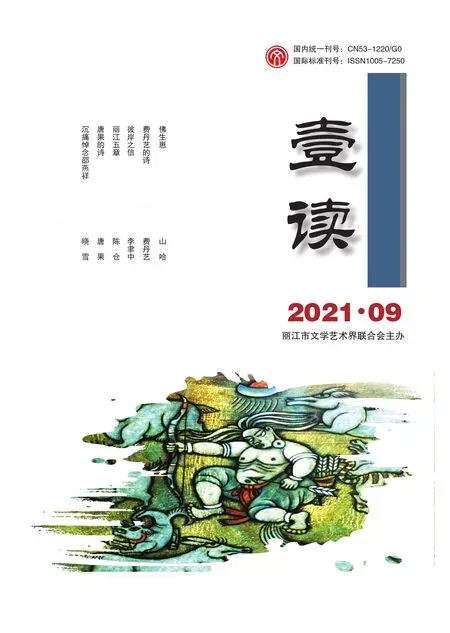河流上的野鴨
◆宗玉柱
一只雌性赤頸鴨脫單了,于春江中追逐著華麗得有點妖艷的雄鴛鴦。雄鴛鴦躲躲閃閃,一副被騷擾又無可奈何的樣子,母鴛鴦就沖上去與之纏斗。那纏斗也只是短暫的一撲,水花濺起的時候,遠處的綠頭鴨和鴛鴦們受到驚動,紛紛游過來,以為又有人在投食。
管理員不讓給綠頭鴨和鴛鴦投食,認為這樣會影響它們的胃口和野性。盡可能保持原始是目前對生態有效保護的觀念之一,相左的觀點認為,對于野生動物來說,接近人類或許更能夠有利于繁衍生存。事實上,野鴨鴛鴦等更喜歡被投食。鴛鴦也只是這幾年多起來,以前偶爾才見,并且離人很遠,遠到讓人失去興致。綠頭鴨就是常客了,往前數,大約能數到2004年,因為據科研者觀察,這年冬天,綠頭鴨突然不遷徙了。
不遷徙的綠頭鴨讓科學院的專家們感到驚奇,同時也知道這不能簡單地斷定是好事還是壞事。喜憂參半吧。經驗老道的專業人士,對事物的變化大都保持這種態度。
最初留下的綠頭鴨,在寒冷的江水中孤獨無助,它們大都聚集在奶頭河那片不結冰的水域,接受食肉動物,應該是水獺,還有人類的遴選。那時當地居民還沒有人認為綠頭鴨也需要保護。
2004年的水獺應該是在驚喜中度過冬天的,它們躲在水底仰看上面浮動的食物時,不知會發出怎樣的贊嘆。動植物的分類很科學,也復雜到很不好科普,有門、綱、目、科、屬、種等分類,還有什么亞門、亞科,除非專業,普通人看過也記不住。比方這水獺就是脊椎動物門、哺乳綱、食肉目、鼬科、水獺亞科、水獺屬、水獺。如此,其他已知動物都能找到它的譜系。
水獺的口糧主要是魚類,當然也抓河邊活動的小鳥、春秋時的哈什螞,有時也吃應季可口的植物。它最長用的手段是伏擊,尤其是冬天,常常躲在冰窟窿里,等待魚游過來透氣兒時突然沖上去捕食,估計“大快朵頤”這個詞和它沒啥關系,能解決溫飽就很不錯了。
奶頭河因為特殊地理位置,冬季不結冰。在寒冷的北方,河流不結冰的地方也不很多,奶頭河這一段比較著名。凜冬時節,大多數早晨,不結冰的河面上會生出霧氣,霧氣附著在岸邊的樹木上結成厚厚的冰晶,謂之霧凇。晨光透過升騰彌漫的霧氣,把冰晶映成五彩顏色,變幻莫測且神秘,就有人把這里取名為“魔界”。
攝影和旅游小眾的時候,魔界只有很少的人知曉,去過的人說起那里時,聽者會撇嘴道,還能有霧凇島好?盡管他未必去過吉林霧凇島,但名氣在那里。說魔界好的人如果也沒去過霧凇島,就只好閉嘴。
有一年冬末我在二道白河情人橋上遇到兩位沈陽來的大哥,他們看到我脖子上掛相機,就問我當地美景。那天正趕上大雪初停,樹枝上掛滿厚厚的雪團,陽光明媚,這雪即將被搖落,搖落后便不是攝影者想要的景色了。這二人意猶未盡,我看他倆面相和善,就隨口道,可以去魔界。
我們不熟悉地方,一路從雪鄉追著雪過來的,正要去,你能帶我們嗎?兩位滿是期待地看著我。好吧,明早我來賓館接你們。問明住處,我欣然答應。
第二天,我也是第一次領略了老魔界的早晨。從日未出時暗影幢幢,到日出后萬象綺麗,真當得上人間罕有的魔幻之地。
老魔界早晨很少看到綠頭鴨,綠頭鴨都隱匿在上游新魔界里,也就是現在的長白山魔界景區。多年后迷上拍星空,去被“更新”嚴重的老魔界拍過一次,林立的枯木消失殆盡,兩岸也因開發,自然叢林被綠化木置換,完全不是過去的樣子。受不了光污染,隨即就想到了新魔界。半夜九點左右來到河邊,設置好相機參數就開始靜等,偶爾,遠處干葦叢后傳來輕微的水聲和寒夜中的鴨叫。
聽著能有不少。我和同伴悄聲說。突然,撲啦啦,呷呷呷!翅膀撲擊水面的聲音,水鳥飛離時急速帶動空氣的聲音,驚恐而又茫然低啞鳴叫的聲音同時響起。
完,是水獺,拖走一只。同伴惋惜道。
水獺肯定是悄悄潛近,然后一口咬住綠頭鴨拖進水里。這家伙有獺貓、魚貓、水狗、水毛子、水猴等很多稱謂,除交配期以外,平時都單獨生活。我曾查過資料,水獺一年四季都能交配,每胎產1~5仔,生育能力強,暫時不會瀕危。所謂瀕危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種群數量降至臨界點,一個是致危因素仍在持續。綠頭鴨也不會,但前提是這東西既不好吃,也不值錢。水獺的保護級別是“近危”,綠頭鴨的保護級別是“低危”。“近危”者襲擊了“低危”者,在動物界屬自然,在人類社會也一直默認。
大約過了兩小時,又一陣水聲和綠頭鴨的驚叫聲響起。又拖走一只。我對同伴說。
黑暗中互相看不出表情,多少有點不舍。這一夜,水獺總共拖走三只綠頭鴨。這樣算起來,整個冬天要拖走幾百只,但顯然不會是這樣,要不然綠頭鴨很快就會從“低危”晉級為“近危”。那一夜大概是個案。
查看水獺百科時一如其他隨看隨忘,唯記住一句:“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這話是李時珍在介紹作為中藥時的水獺說的,因為熊和水獺都是長白山土著,所以對這句獨有興趣。劉建封《長白山江崗志略》中記載有老虎“食狗則醉,食豬則癱”,與此十分類似,后來有人證實,食豬則癱沒人見過,食狗則醉確有實例。1947年土改時,撫松縣北崗參農靳連學帶狗看參園,一虎闖入,吃掉狗后醉了一兩天,醒來后復入森林。由此可見古話切莫輕易否定,進而回味“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很有道理。
我對綠頭鴨有些許親近,相比那些對中華秋沙鴨情有獨鐘的攝友們,我對綠頭鴨的興趣多了些“土”氣,前者實屬“瀕危”,有“鳥類中的大熊貓”之稱,后來發現有著這一稱謂的鳥類居然很多,能夠列出的有震旦鴉雀、黑臉琵鷺、青頭潛鴨、朱鹮等,總之它們都是鳥類中的貴族。
有一次與作家胡冬林老師兄妹偶遇情人橋,也就是遇到兩位遼寧朋友的那個橋上。原本與他們相約第二天見,提前遇上也是欣喜。正說話間,河左岸一個年輕男子抱著孩子走向岸邊,后面跟著一只寵物狗。此刻岸邊一只綠頭鴨媽媽帶著十幾只鴨雛正覓食,受到驚擾開始迅速撤離,不料寵物狗猛沖到水邊,一邊狂吠,一邊沿著河岸上下奔走。鴨媽媽大驚,張開兩翅,拼命大叫著,隨寵物狗的跑動奮力游弋攔截。
青年喝止不住寵物狗,便做壁上觀。我們雖然有些不高興,但知道那狗就是虛張聲勢,并沒有危險,遂靜觀其變。不料遠處湖面沸騰起來,但見滿湖的綠頭鴨們高聲叫著齊向這邊飛速游來,分明是大隊人馬趕來增援。我們頭次看到這壯觀景象,震驚不已。寵物狗見勢不妙,竟丟下主人轉身逃之夭夭。過后我們都很惋惜沒帶設備,沒有記錄下這罕見的場面。
有一年春天,我在經過美人松林的公路上晨跑,遠遠看到五六個小黑點在路邊快速移動,跑近后看清,原來是才孵化出的鴨雛跟著鴨媽媽過路,路邊條石有點高,僅幾只鴨雛蹦上去,有六只還在尋找位置奮力翻越。鴨媽媽在路邊大聲鼓勁,見到有人來,慌忙鉆進草叢,片刻又鉆出來,勇敢地沖我叫,似威嚇,似求助。
見此情景我忍不住要施加援手,但卻低估了鴨雛的速度——既要小心鴨雛受傷,又要在快速奔跑中拿獲。幸好那時還算年輕腿腳靈便,等把鴨雛全部送上路邊,竟跑出一身汗。鴨媽媽帶著全部孩子很快消失在通往河邊的松林里。手掌中鴨雛毛茸茸的感覺還在,讓我心里也軟軟的,我覺得應該自豪一下,怎么說也算做了件好事,暢快之余,多次講給別人聽。
還有一年夏天,路過雙橋,橋下水花飛濺,一只綠頭鴨媽媽在使勁撞擊一只已經長的很大的鴨雛。我覺得奇怪,趴在橋欄看究竟,原來岸邊水中立有一張沾網,鴨雛的頭頸不小心鉆進網里無法掙脫。我趕緊攀著橋欄下到河邊,鴨媽媽退后幾米在我夠不著的地方焦急地叫著,我費了好大勁才把鴨雛從網上摘下來,然后放到河里。鴨雛一脫手就在水面拼命奔跑,瞬間沒了蹤影,看來是嚇得不輕。鴨媽媽沒有去追,而是靜靜地面對我輕輕連叫,半天沒有挪動,似乎是要記住我的長相。我揮揮手說,走吧走吧,趕緊去追孩子吧。那鴨媽媽這才轉身離去。
隨著環保理念深入人心,當地人大都以成為野生動物保護者為驕傲,在他們的溺愛下,如今二道白河的綠頭鴨已經以主人自居,它們有時會大搖大擺地在人行道上走,有時會摟著鴨雛們在河邊睡覺,任來往人等隨意拍攝。走在河邊廊橋上,橋下會有綠頭鴨和鴛鴦跟隨,這是夏天常見的風景。如果沒有什么表示,綠頭鴨會叫幾聲以示不滿和提醒。帶點面包餅干類的食品去河邊喂綠頭鴨,是接待遠來客人的必備節目,管理員們對此頭疼不已。如此方式親近自然,這在別處是很少見的,只能表示理解。
有兩個攝友來拍綠頭鴨和鴛鴦,出來時只帶了長焦鏡頭,等拍的時候就后悔了,距離太近,竟然一時間感覺困擾了。有天中午天太熱,我和幾個攝友坐在公園椅子上聊天,一只雄綠頭鴨飛落到幾米遠的樹蔭里,看了看我們,然后抬起一只腳掌呈獨立式,把頭轉向后背,扁嘴巴插在翅膀下睡起覺來。我們幾個互相看看均覺得這家伙也太囂張了吧。拿著相機比劃著要和它合張影,后來想還是算了,別打擾人家午休。
綠頭鴨和鴛鴦的關系一直是和諧的,當然也有例外。我曾見過一只綠頭鴨媽媽帶著寶寶們順流而下,一只鴛鴦媽媽帶著寶寶們逆流而上,狹路相逢時,綠頭鴨媽媽直沖上去,打的鴛鴦母子們四散奔逃。綠頭鴨母子過去后,雌鴛鴦立刻召集起寶寶們繼續前行。作為觀者,我竟沒覺得“霸凌”氣十足的綠頭鴨媽媽有多可惡,這種打斗原始而純粹。就假設人類若如此相遇,一定會互相夸贊對方的寶寶可愛,背對時便各自翻白眼——我在面對自然時的這種妄意推斷大概也反應出人類心理不健康的現狀,或者僅僅是我個人的現狀,自覺汗顏。
先前提到的赤頸鴨以及丑鴨、斑背潛鴨、鳳頭??等都是過客,它們只在春秋出現。中華秋沙鴨對人類還是保持高度警惕,一副老死不相往來的架勢。反觀綠頭鴨和鴛鴦,它們接納人類的樣子滿含著自然的溫度。梭羅在他的著作《種子的信仰》里引用古羅馬科學家普林尼的話:“自然于最卑微處最卓越。”最卑微處——那些非瀕危的,保護等級低以及不能列為保護的生命,它們的存在或許意義更大。如這些在近年來率性融入人類社會的綠頭鴨,它們以崇尚簡單直抵目的為真實,突破物候與物種界限,以身論證著生命何以繁衍承繼,同時也檢索出人類文明中盛贊平等卻按需構建重重束縛的虛偽——當我從書本里抬起頭的時候,我知道自己離走近自然還有很長很長一段距離。
我是務林人,與森林中的樹木花草和動物相伴半生,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理念有身在其中的理解。我曾經認為,只有人類全部搬離出來,才算是真正把萬物還歸自然,大自然當會按照自己的法則完成自我修復。近來卻想,假如這樣,修復的自然是不是與人類還能有聯系呢?人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與自然不可分割,人對自然應保持敬畏,而自然也當為人類提供必要的所需。
我還這樣想,人類的破壞在自然來看是無所謂的,放眼地球史,從上一個冰川期到下一個冰川期,很難說是因為什么生物破壞引起的,或許它就是一種自然的輪回。人類要做的是在下一個冰川期到來之前,通過對生態的保護,致力科技發展,為未來尋找到出路,為人類爭取繁衍生息下去的時間。如此,適合人類生存的自然是最理想的自然狀態,這個狀態需要長長久久地保持,它關乎人類未來,人類為此應盡的責任更大更艱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