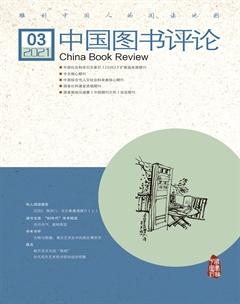后人類時代的電影本體論
吳明
【導??讀】首先以“事件性”為中介,搭建電影與愛之同構;再以Cinema的語義辨析,分析電影院作為驅力主體轉型的空間場域價值;最后從知覺后勤學,闡釋電影院賦予觀眾機器感知系統,實現主體的觸興式體驗。
【關鍵詞】愛??電影院??知覺后勤學
引?言
1975年,特呂弗熱情洋溢地寫下“明天的電影會是一種愛的行動”[1]18。此話的背景是,“‘新浪潮已經變成一個可以肆意侮辱的名詞”,特呂弗要捍衛這種更為個人化的作者電影,以此抵制那些“聰明卻毫無激情”的類型化操作。[1]14但如今回望,彼時電影并未遭遇真正的整體性衰落與危機,甚至正處在大師與佳作頻出的巔峰時代。但在今天,在電影死亡論已被數度提及的后電影時代,在技術控制論不斷操縱或取代主體情感的后人類時代,在各種媒介終端儼然取締影院正統性的流媒體時代,“愛”對于電影而言,除了作為愛情片的常規主題或迷影群體的儀式化感動之外,還能意味著什么?
吳冠軍的新作《愛、死亡與后人類:“后電影時代”重鑄電影哲學》(以下提及簡稱“《愛》”本書“書中”),正是在這一當代語境中,嘗試了一次電影哲學的特呂弗式書寫。他“要論證的核心觀點就是:電影所開啟的那個獨特的幽靈性場域,具有豐厚的潛能,使觀影者發生主體性變化。而后人類主義能夠在哲學層面進一步闡釋該變化的形成機制——這個變化正是電影場域內無數微觀但實質性的觸動與被觸動的最終疊加效應”[2]77-78。具體而言,這本書試圖從精神分析和新唯物主義兩個端點出發,合力捍衛電影與愛的同構性本體。前半部分以精神分析理論揭示了欲望主體向驅力主體躍升時釋放的巨大情感能量,由此解釋電影敘事機制得以形成的主體性成因;后半部分則從后人類視角和新唯物主義理論解釋,物如何對人形成量子化的糾纏疊加效應,機器如何實現對主體的“知覺后勤學”供給,引發主體的觸興/情動。“電影院”則是貫穿全書的哲學場域,是所有人—物、主體—機器、體驗—觀測等耦合共生體的聚能場,實現了電影本體論從“輸出方”向“接收方”的視域轉移。
一、事件性:電影與愛的同構基礎
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愛和電影的同構性,正是在于兩者都有潛能成為事件性的地點,使陷入該狀態中的人經歷實質性的主體性轉型。”[2]19這個觀點指向兩個層面:其一,“事件性”是搭建電影與愛之同構的哲學基礎;其二,這一同構的表現是促成主體性轉型。這里先談事件性的層面,“從定義上說,事件都帶有某種‘奇跡似的東西:它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也可以是一些更宏大甚至帶著神性的事情”[3]2。它是對穩定、平衡、秩序等一系列日神式概念的酒神性反叛與跳脫。事件性之所以成為電影與愛的同構基礎,就因為它們都以某種方式達成了對日常生活秩序的溢出。
《愛》中詳細比對了在電影狀態和愛戀狀態中,主體如何遭遇相似的“被拽出去”的體驗。在電影院里,“被符號(往往在日常生活中呈現為‘理智‘理性)壓制的真實(未被符號化、抵制符號化、無法形諸語言的殘余),在銀幕中獲得幽靈性的具象(以及游行性的聲音)。這些具象不斷刺出銀幕,‘涌向那黑暗封閉空間的每個座椅、每個角落……觀影者被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拽了出去,遭遇在生命中、但比生命本身更激烈的‘活,甚至很多時候會淚落紛紛,久久不能自已”[2]11。而熱戀中的人常常“犯傻變瘋”,就是因為“在愛中的主體——愛者——有潛能沖出‘理智之總體性框束,將自身拽出周而復始的日常狀態,而進入一種語言形容不出、然而極度激烈的存在性向度中”[2]12。因此,觀影者和愛者共同成為驅力主體,而“所有驅力根本上都是‘死亡驅力,都是溢出性的、執迷性的、重復性的,并且在極致意義上都是毀滅性的”[2]101。由此,電影、愛、死亡都成為“去—日常現實”的主體經驗,而“赴死之愛”也就成為電影中最常見的戲劇性高潮,就像書中反復提及的幾部影片:《泰坦尼克號》《色,戒》《古今大戰秦俑情》等。
但這些影片大多是類型片,難免令人產生這樣的疑問:這些生死愛戀不過是類型片的慣用模式,何來書中痛徹心扉的感動呢?類型片的程式化特征,對以事件性為基礎的“電影—愛”之同構提出了挑戰。其悖論性在于:類型片既是事件性的,又是反事件性的。它在視聽效果上制造奇觀,在情節內容上制造奇遇,這是其“事件性”的一面;但它同時又要把各種驚奇固定為模式化的類型元素反復使用,這是其“反事件性”的一面。愛情片中的愛是一種類型化的愛,這使愛、事件、電影之間的關系越發焦灼。但也正因如此,類型片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問題視域,切入“事件”與“愛”的悖論性特質,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愛與電影的同構性可能。
類型片是20世紀30—40年代美國大制片廠時代的產物,它首先不是一種藝術形式,而是一套商業制作模式,以吸引觀眾、賺取票房為目的。這意味著類型片對所有能夠引起觀眾的元素都感興趣:各種視聽奇觀、傳奇故事、捧腹笑料、催淚愛情、暴力色情……總之一切能引人入勝的事物,都會被類型片囊括其中;而在市場反饋中被證明特別有效的那些因素,則會被固定下來成為一套模式,被反復使用成為一種類型。湯姆·甘寧著名的“吸引力電影”概念就是指:“直接訴諸觀眾的注意力,通過令人興奮的奇觀——一個獨特的事件,無論虛構還是實錄,本身就很有趣——激起視覺上的好奇心,提供快感。”[4]即便在敘事電影日趨主流后,吸引力也仍然作為電影的媒介基因保留下來,尤其“在某些類型中(比如,歌舞片)表現得比其他類型更加突出”[4]。雖然甘寧的“吸引力”側重于視聽效果以區別于敘事元素,但在類型片中,兩者并不矛盾。各種傳奇、秘聞、懸疑、沖突、意外,都對觀眾構成巨大的吸引力,而曲折離奇的情節往往與極具震撼力的視聽效果相輔相成,甚至在某些技術更迭期,前者是為后者服務的,例如,歌舞片的情節推進常常要讓位于歌舞片段,就是為了滿足有聲片誕生之初,觀眾對電影聲音的奇觀化追求。簡言之,奇觀與奇遇共同構成了類型片的影像與敘事基石,這正是它最具事件性的一面。
奇遇與奇觀又構成兩種意義上的事件性:一種是生活本身的事件性在情節內容中得以揭示,另一種是感官效果或敘事結構的出其不意。《泰坦尼克號》作為災難片與愛情片的交叉類型,就體現了這兩種事件性。它“包含兩個截然不同的情節,一個是愛情故事,一個是對災難的描述。……從時間順序上看,它們幾乎是完全分離的。愛情故事部分在第100到194分鐘的時候達到高潮……緊接著,船突然撞上了冰山,然后電影的奇觀動作部分開始”[5]10。片名提醒我們,這部電影的真正主角不僅是杰克和露絲,更是那艘船。從1995年的2D版到2012年的3D版之間,詹姆斯·卡梅隆多次利用潛艇和水下探索機器人,潛入海底殘骸獲取一手資料,并集結來自物理學、建筑學、船舶學、歷史學、藝術學等多位頂尖級泰坦尼克號專家,借助計算機動態模擬,試圖還原真相。[6]重制3D版主要是加強巨輪沉沒的奇觀效應,以此紀念泰坦尼克號沉沒100周年。可以說,刻骨銘心的愛情是男女主角生命中的冒險與脫軌,是愛情之為“人生事件”的銀幕重構;但讓這段愛情超越于同類題材的決定性因素,則是這場驚心動魄的意外災難,是它以考古學和工程學般的嚴謹,使這部作品成為一個經典的“電影事件”。
而類型片之為“類型”,在其“反事件性”,即把意外和偶然變成了不斷重復的模式。它“被用來描述那些一再重復講述的電影故事,這些故事只有些微的不同,遵循著同樣的基本模式,具有相同的基本組成要素。場景、人物、情節(沖突和解決方式)、畫面、電影手法和慣例等,被認為在同一類型的不同影片之間幾乎可以互換”[7]。這種公式化的極致代表就是悉德·菲爾德的《電影劇本寫作基礎》。它刻板地強調“三幕劇”結構,重視設定“情節點”和構筑“故事線”,按照每分鐘對應一頁紙的計量方式,把120分鐘的電影分布在1∶2∶1的三段式結構中,亦即開端30頁、中段60頁、結局30頁的所謂“三幕劇”格式。[8]當代好萊塢的通行套路也依然是“在第25頁到第27頁之間和第85頁到第90頁之間一定要有轉折點出現”[9]。即便在《超越套路的劇作法》這樣的書中,所謂的“反傳統結構”也不過是把三幕變成兩幕或一幕[10],最后形成的仍舊是一套“法則”(Rules)。
類型片是“電影制作者和觀眾之間的默認的‘契約”,是作為“電影身份的慣例系統”。[11]例如,在歌舞片中,會唱歌的人才會相愛。只要觀眾記住這條規則,那么《雨中曲》和《音樂之聲》中的女主角無論遭遇了多么強大的情敵威脅——美貌、家世、教養——但只要那個女人不會唱歌,觀眾就會知道,平凡但歌聲甜美的女主角必是最后的真愛。類型敘事中的驚奇,主要是一種結構性的驚奇,就像“歡喜冤家”模式一定會先制造誤會和厭惡,如此才能結構性地凸顯相愛時的反轉力度。同理,《色,戒》就是“愛上敵人”[12]357模式的典型,在美貌女學生和魅力男反派之間,相愛只是一種結構性的必然。而頂級明星梁朝偉的出演,也是類型片對觀眾的契約化保證,他的出場已然毫無懸念地預示了王佳芝未來的倒戈。類型片的商業屬性將原本偶然性的事件,變成了反事件的程序化演繹,這似乎在動搖電影與愛的同構性基礎。
但本文更傾向于另一種思路,即借由類型片的“反事件性”重新思考“事件”本身的自反性悖論。齊澤克曾以基督降世與升天的奇跡,觸及過事件的結構性吊詭:“我們不能認為,倘若基督不降臨世間,就會是所有人的不幸;恰恰相反,如果沒有基督,就沒有人會遭到不幸。這意味著,為了基督能夠降臨并拯救一部分人類,所有人都必須先行墮落。”[3]51這正與愛情片的邏輯一致:不是為愛犧牲令人感動,而是為了制造感動必須令其犧牲。于是,事件與類型片正是在悖論性上達成同構:事件本就包含自身的反面,即為了成就一次突圍,則必須為其預先制造出可供突圍的秩序;類型片則為了制造傳奇,必須將傳奇模式化與常態化。那么,“愛”又如何被納入這一悖論性體系?這促迫我們重新思考,“愛”是否只有自由不羈的一面,而徹底絕緣于任何持久穩定的系統?書中提及愛的“程序性”可能,它“開啟了一個后事件的‘真理—程序,或者說,‘類性—程序(人類定義自身的程序):在相遇的事件之后,愛旨在馴服偶然性,在事件(偶然性)中建構真理(永恒性)。也正因此,愛要求忠誠”[2]16。“忠誠”正是巴迪歐對愛之偶然性與持存性的辯證法,它“是讓事件去繼續得以持存的主體性實踐——通過這種后事件的實踐,讓事件去擁有永恒的屬性”[2]16。巴迪歐固然強調愛是一種偶然,但也認為它是一種“持之以恒的建構”和“堅持到底的冒險”。[13]這就是為什么《敢愛就來》的男女主角始終不敢說出“我愛你”——這是自由個體難以承受的持存之重,他們不敢冒險“愛到底”。赴死固然是愛的高光時刻,但在單子化的后現代境遇下,攜手白頭的綿長人生未必不是另一種愛的奇跡。因此,電影與愛不僅在事件性上彼此相似,更在事件之悖論性上獲得了同構。
二、電影院:生成驅力主體的本體性場域
書中對愛情片的分析是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釋類型片最關鍵的問題:為何是這樣一套程式而非別的被固定為類型元素,其背后的主體性成因究竟是怎樣的?這一直是類型元素最神秘的地方,“它的呈現必然是某種潛意識欲望的扭曲呈現……哲學家將人們不能‘看見的現象歸入‘遮蔽‘混沌‘實在界,心理學家則稱之為‘潛意識‘力比多等,總而言之,這是一個人類觀察的‘死角,這也是人們不能明白確定類型電影之中的類型元素究竟是如何構成的根本原因”[12]5。因此,以事件性為基礎建立電影與愛的同構,其意義不止于靜態的相關性類比,而是要為欲望主體向驅力主體的轉型打開哲學通路。“驅力”是一種精神上的“溢出性殘余”[2]193,“主體通過‘死亡驅力而對符號性秩序進行的抵抗,被拉康稱作‘分離(separation)。……驅力便是‘分離的本體論根源,賦予‘分離實踐以動力,使得主體同日常現實的激進‘分離成為可能”[2]28-29。所以,電影具有把人從生活中“拽出來”,亦即從“理性—經濟人”的狀態中分離出來的驅力化能量。“這個拉康主義論旨呈現自身的最佳場域,不是現實,而是電影(電影院)。正是在這個獨特場域內,被符號壓制的真實,在銀幕上獲得幽靈性的具象。”[2]11這就巧妙地把主體性問題轉移到對空間場域的討論,并且將電影與電影院進行了本體論上的同位思考。觀眾產生的各種認知、情感、身體反應,都是由“電影院”這一布滿各種機器設備的體驗裝置所引發的,銀幕上的劇情演繹也是這個裝配系統中的一部分。這就把電影理論在內部研究(文本細讀)和外部研究(受眾分析)的長期分立,統合為空間系統(電影院)研究。
對于電影之死的擔憂,始終圍繞著電影院是否會消亡的討論,這在流媒體時代已經變成了有關電影本體的爭奪。格林納威認為:“作為媒介的電影沒死,但其支配性的形態(被動的觀影者被困陷在封閉影院的黑暗空間中)已死。格氏認為不應再用‘cinema這個詞來描述各種新的影像形態。”[2]202這不只是名稱問題,也無關乎觀影儀式的懷舊感作祟,而是基于電影的機器本性和吸引力基因嚴肅追問:產生于不同技術規格下的制作與放映系統,存在怎樣的物質性差異,以及這種差異對于觀影主體究竟產生怎樣的影響?換言之,為何主體的驅力化轉型只能發生在電影院里?
那么,Cinema究竟是什么?在英文中,Film、Movie、Cinema都可以指“電影”。“‘膠片(film)一詞指那種讓形象呈現和聲音被記錄的物質性的賽璐珞,而‘電影(movie)指在那種物質的放映中被我們作為敘事和奇觀來消費的圖像之流。”[5]5Cinema是最偏重電影本體性也最具有電影史色彩的一個,它源自法語詞cinématographe(電影放映),本意為電影院,常與theatre通用;后吸收了英語中cinematograph(電影攝影機)的語義,強調由視聽語言和技術制作所確立的藝術形式特性,其形容詞變體cinematic意為“具有電影感的”。因此,所謂的“電影感”本身就意味著“影院感”。2019年年底,馬丁·斯科塞斯聲稱漫威系列不是“電影”(cinema),更是把這個詞推上了風口浪尖。他心目中的Cinema“是關于啟示的——美學、情感和精神上的啟示。它是關于人物的——人的復雜性和他們矛盾的、有時是悖謬的本質,他們可以彼此傷害、彼此相愛、突然面對自己的方式”[14]。顯然,斯科塞斯對漫威的不滿主要是因為它不具備作為藝術形式的電影在美學層面應有的深度,而并非放映介質上的差異。畢竟,漫威系列的“主題公園”體質使其更加依賴于影院放映系統的高技術格式,僅就此而言,漫威系列是非常cinematic的,它甚至比作者電影更渴望捍衛電影院的存在。這不僅與斯科塞斯強調“大銀幕”之于電影的必要性并無抵觸,反而共同證明了,商業化的類型片和藝術化的作者電影,無論它們在美學追求上有多么巨大的差異,但正是對電影院的依賴使它們仍舊暫時同屬于一種被稱為“電影”的東西。當然,這種依賴是相對意義上的,并不是說個人電腦上播放的東西就不是電影,但那一定是體驗上有所折損的電影。當人們熱議《囧媽》拋棄院線轉投流媒體平臺可能會徹底改變中國電影業格局的時候,徐崢對幕后人員致歉,因為“很多部門的工作是為能達成大銀幕最佳視聽觀感”[15]而付出的努力。退居小屏幕觀影,我們將損失很多東西,而且很可能是最cinematic的部分。
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對電影院持有桑塔格般的“拜物教式迷影”[2]195,作為中國影迷尤其不該如此。因為我們不能一邊享受著流媒體平臺和個人終端設備帶來的豐富資源和便捷自由的觀影可能性,又一邊大聲斥責這種方式在毀滅電影。電影不會因為離開電影院就變得毫無價值,否則我們怎么解釋錄像廳對“第六代”導演的集體啟蒙?以及如何解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即便在2016年才發行藍光高清版,卻在此前十幾年的時間里僅憑幾百兆的劣質網絡資源,依然能讓無數電腦前的影迷們獲得靈魂洗禮般的震撼?那些黑黢黢的畫面,曾怎樣如同一道圣光照進我們心底,而這一切并不是電影院帶給我們的。我們當然不否認在嘈雜明亮的日常環境中,用臺式機、平板電腦、手機等個人終端設備看電影的弊端。“人們已沒有耐心在兩小時的時間—影像中遭遇另一個整體世界。……在現實中,時間被碎片化、生活被碎片化;而電影,才恰恰是在保證非碎片化。”[2]203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吳冠軍在后記中也說:“利用國慶長假,一個人插上耳機,在電腦里找出早已下載好的藍光版The?Time?Travelers?Wife,在黑暗的書房里慢慢消磨兩小時。”[2]245相信書中的很多影片,也曾在同樣的電腦上感動過作者。
所以,這里有兩種意義上的電影院:一種是物理意義上的觀影空間,另一種是哲學意義上的主體性經驗系統。書中所捍衛的并非前者,而是后者,畢竟現實中的電影院已經越來越令人失望了。一邊是,主流影院為了節約投影機燈泡耗損把亮度調暗,工作人員的失誤可能導致畫幅錯誤,片尾字幕一出便開燈趕人,旁邊觀眾長時間亮起手機屏幕、大聲聊天、孩子哭鬧、寵物逃竄,以及集體觀影時往往礙于旁人而羞于流淚痛哭……另一邊則是,電影節期間被迷影群體占據的影院,他們“倡導的‘電影中心主義建構了對電影及其至高無上的藝術身份的近乎專斷的獨裁式想象,這種精英主義的‘圈子文化締造了‘大電影意識,或者‘電影原教旨主義,它推崇‘電影院崇拜論,強調清教徒般的觀影禮儀,傳播對膠片的化學成像美感的迷戀”[16]。他們穿著印有各種觀影禮儀的T恤衫,發放寫著“你亮起的手機屏幕把沉浸在電影中的我殺死了”的驚悚警告牌,觀影時如果有人不慎看了一眼手機,或不留神踢到前面的座位,輕則被報以白眼,重則被厲聲謾罵,以致全場側目——看電影已然成為一件令人膽戰心驚的事。
而哲學意義上的電影院則是一個“將人變成‘非人的裝置。當進入電影院后,人從其熟悉的現實生活中被‘隔離出來,暫時性地進入一種幽靈性場域,在其中人具有更大的潛能遭遇拉康所說的真實,從而促發主體性的劇變而成為驅力主體”[2]65。可見,“隔離”才是電影院之為哲學概念的核心。特呂弗曾說:“我開始感覺到一種強烈的需要,想要‘進入電影之中。我坐得離銀幕越來越近,為的是可以忽略電影院里其他的人和事的存在。……我只知道我想離電影近一點,再近一點。”[1]2盡量屏蔽他人,使自己最大限度進入電影世界,這才是生成驅力主體的空間保障。它既可以是普通影院,也可以是一人包場的VIP廳,也可以是家庭影院或關起門的書房,甚至不必真的走進一間屋子,只要戴上一副VR眼鏡和耳機,坐在椅子上就能開啟你的個人影院。而這些形式的共性就在于,必須保證周邊的黑暗與安靜——使人從現實中抽離出來。只有這樣才能暫時忘我地卷入情節和各種視聽效果帶來的情感驅力。在今天,能夠產生這一驅力的地方,就是一個人的“電影院”。
三、觸興:知覺后勤學的情感能量
斯賓諾莎認為,人的身體不斷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和影響,“情感誕生于身體的感觸經驗”,以此反對笛卡兒的身心二元論——情感不再是孤立于身體的“心情”,而是由身體觸動和激發的反饋機制,這就是觸興/情動(Affect)的基本特征。[17]德勒茲強調其作為“情感流變”的動態屬性,馬蘇米則在“物質化”的維度上更凸顯了這個概念的后人類氣質,他“要將事物無中介地放回文化物質主義中,同時將看上去最物質有形的東西放回身體”[18]。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比斯賓諾莎的情感更強調“‘觸興是無—主體性的、非—意識性的、非符號化的并且未在符號性秩序中受到注冊的、強烈的”[2]82。在后人類語境下,觸興比情感更能凸顯人機耦合的主體經驗,因為它強調人與物的相互觸動與激發,強調感性經驗被轉化為力與能量的方式釋放或儲存。人工智能的發展正在昭示信息論和控制論對人的本質性前瞻:從賽博格到人機同質。人的感受越來越建基于機器的牽引與觸發,今天已經很難找到那種完全排除機器影響的“純粹主體”了,我們是在各種機器的功能效應中,獲得身體與心里的感受。
維利里奧考察了現代戰爭與電影的共性,認為“影像的補給變得等同于彈藥一類軍需品的補給”[19]前言,2,并由此提出“知覺后勤學”。它具體是指,在現代戰爭中,攝影機與武器越發合為一整個“視覺機器”,使得軍事威脅逐漸“去現實化、去物質化”,亦即“視覺化”。[19]30它使電影從根本上拒絕了藝術模仿論,而側重于強調它的機器本性,以及這種機器本性對人類感知的建構性功能。簡言之,機器規訓感知,攝影機和顯示器的各項參數指標,決定了我們對世界的判斷。世界對我們而言依舊可以是“眼見為實”的,但這個“眼”已不再是生物學上的肉眼,而是機器眼。德呂克的“上鏡頭性”和維爾托夫的“電影眼睛人”是它的理論源頭。前者是以光學鏡頭和大銀幕的機器屬性來規訓演員的臉:一種更為瘦削有凹凸感的臉龐輪廓能成為“電影臉”的原因,蓋因它能平衡不同焦段鏡頭和寬度不同的銀幕在將三維對象擠壓為二維影像時,必然損耗的立體感。電影演員的身體首先不是作為人的身體,而是滿足鏡頭與銀幕需求的機器化身體。東亞女演員們無休止的減肥噩夢和對歐美人種更具雕塑感的基因傾慕,其性別與種族上的自卑根源與其說是文化,不如說是機器。維爾托夫的“電影眼睛人”或許是最早的電影賽博格理論,“把電影攝影機當成比肉眼更完美的電影眼睛來使用,以探究充塞空間的那些混沌的視覺現象”。以運動的機器視點取代舞臺觀眾視點,“以一種與肉眼完全不同的方式收集并記錄各種印象”[20]。它在今天的意義不只是作為未來主義的機器美學,而是揭示了從解放攝影機運動,增強機器自動化,到以數字繪景徹底取代實景拍攝的一整條機器視覺電影史。通過光學鏡頭、數字傳感器、Photoshop、Maya、After?Effects等數字圖像/視頻處理軟件,觀眾的感知已然賽博格化了。
在觀影層面上,“競速觀看所深層次帶來的知覺場變異,會劇烈地改變觀影者的頭腦環境,從而改變其‘知覺的后勤。”[2]70鏡頭和屏幕疊加在眼睛上,耦合成我們的視覺感受器;環繞立體聲音響系統或降噪耳機疊加在耳朵上,耦合成我們的聽覺感受器。今天的電影院是各種頂級視聽設備裝配后的“觸興賦能艙”,供給驅力主體轉型所必需的物質條件。“主題公園”并非電影院的原罪,而是其機器本性的集中顯現,影院觀影區別于流媒體觀影的根本,正是基于“知覺后勤學”的觸興體驗。在杜比影院(Dolby?Cinema)看過《雙子殺手》的觀眾,會被摩托車追擊片段全面震撼:身體仿佛真的坐上摩托車震動飛奔起來,以至于無法分清那種眩暈的高速運動究竟是一種心理感覺,還是一種物理上實實在在的身體震動。事實上,兩者是混合交織在一起的。這個段落中巨大的聲音轟鳴通過杜比全景聲(Dolby?Atoms)音響系統環繞放大,對座椅產生了切實的聲音震動,這種輕微的物理震動雖然不像4D座椅那樣明顯,但配合眼前杜比視界(Dolby?Vision)120幀3D的超高清流暢畫面,足以令人產生身—心共振。這就是電影院賦予我們的觸興力量,不再只是依靠一種動態的暗示來引發視錯覺,而是真正地介入我們的身體感覺器官。
在更為注重私人空間與個人體驗的今天,電影院的核心價值已不再是分享型的社交機構,而是以放映系統的高技術格式為其立身之本。之所以被稱為“放映系統”,是因為它不只是有關放映環節的設備裝置,而是從攝影機、鏡頭、影片拷貝、放映機、銀幕、音響系統、3D眼鏡、座椅間距、傾斜度、弧度等全方位保障最終呈現效果的技術規格體系。IMAX廳、杜比影院、LUXE廳、CGS中國巨幕廳、CINITY廳等,都有不同的配套技術規格,而且每一項技術指標的改變都會影響其他技術效果的呈現。《雙子殺手》上映時,華夏CINITY號稱采用120幀、3D、4K的頂配放映系統,約130~250元的超高票價也使觀眾默認這是觀看這部電影的最佳影院配置。但絕大多數人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CINITY系統采用的是傳統圓偏振3D眼鏡,導致色彩和亮度明顯失真;而杜比影院采用的是特制分色3D眼鏡,保證左右眼分別接收到高亮度全彩色圖像。這使得2K分辨率的杜比影院,在整體影像質量上遠高于4K分辨率的CINITY系統。這就是強調作為“系統”的影院的意義所在,每一個局部技術的變動,都可能影響最終的呈現效果。
即便前文已述,哲學意義上的電影院才是這一概念的深層旨歸。但如果拋開各種現實考量(如省時、便捷、無他人干擾等),技術裝備高端的現實影院依然是目前所有電影的最佳歸宿。不是只有漫威式的商業大片才適合主題公園,阿巴斯式的藝術實驗也提供一種文雅的“爽”。我們只是沒有機會在IMAX或杜比影院觀看《假面》《大路》這樣的電影(假設存在為這兩套放映系統重新制作的修復版),但想象一下比比和麗芙的臉龐交疊出現在22米寬、16米高的巨幕上(甚至更大),那將是怎樣宏偉奔涌的臉之現象學;馬蹄敲擊石板路的神秘午夜、藏巴諾發動引擎遠去的大篷車、杰索米娜憂傷的小號曲,如果能在杜比全景聲系統里響起,從頂部揚聲器和環繞揚聲器中次第流淌出來的聲音,會不會令“心碎”真正獲得一種身體上的顫抖與疼痛感。今天的影院觀眾,其主體經驗本身就是機器化的結果,“在作為‘行動者—網絡的電影場域中,除了觀影者外,影片、銀幕、放映機、墻、音響、3D眼鏡、4D座椅,都是行動者——它們盡管不具有‘意識,但卻具有能動性,都是‘有生氣的。……一進入電影院,觀影者很快就被抽走自由移動的能力、隨便說話的能力、分心做其他事的能力……這使得電影場域成為一個典范性的能動性聚合體:觀影者們恰恰是和非人類事物一起,在封閉的電影院(聚合性的網絡)中獲得能動性”[2]77。而能夠抽走我們行動力的電影院,必須是一個高科技武器裝備間,是這些非人類的機器,讓我們瞬間套上黃金戰甲,獲得無所畏懼的死亡驅力,成為真正的能量聚集體,以至于走出影院的那一刻,每個人都仿佛解甲歸田、恍如隔世。
結??語
特呂弗曾表示:“我心目中的成功電影必須同時表達出一種世界觀和一種電影觀。”[1]4這揭示出電影與哲學的一種基本關系:不是用影像去轉譯某種哲學理論,而是說,好電影本身應該具有哲學性,亦即它潛藏著自身與世界的同構性特質。吳冠軍的新作正是在電影已然被深刻質疑的時代,不斷追問“電影是什么”以及“電影還能是什么”這一最根本問題,持續演繹它與世界的同構性關系。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后現代主義哲學發展路徑與新進展研究”(18ZDA017)階段性成果;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電影對中國畫視覺機制的傳承與創新研究”(2019BWY015)階段性成果。]
注釋
[1][法]弗朗索瓦·特呂弗.我生命中的電影·序言[M].黃淵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2]吳冠軍.愛、死亡與后人類:“后電影時代”重鑄電影哲學[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
[3][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事件[M].王師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
[4]湯姆·岡寧.吸引力電影:早期電影及其觀眾與先鋒派[J].范倍譯.電影藝術,2009(2).
[5][澳大利亞]理查德·麥特白.好萊塢電影:美國電影工業發展史[M].吳菁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
[6]紀錄片《詹姆斯·卡梅隆:再見泰坦尼克號》中對此進行了詳細介紹。
[7][美]約瑟夫·M.博格斯,丹尼斯·W.皮特里.看電影的藝術[M].張菁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428.
[8][美]悉德·菲爾德.電影劇本寫作基礎:悉德·菲爾德經典劇作教程1[M].鐘大豐等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2012:7.
[9][美]大衛·波德維爾.好萊塢的敘事方法[M].白可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11.
[10][美]肯·丹西格,杰夫·拉什.超越套路的劇作法[M].易智言等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2013:41-48.
[11][美]托馬斯·沙茨.好萊塢類型電影[M].馮欣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4.
[12]聶欣如.類型電影原理[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
[13][法]阿蘭·巴迪歐.愛的多重奏[M].鄧剛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63.
[14]Martin?Scorsese.I?Said?Marvel?Movies?Arent?Cinema.Let?Me?Explain.https://www.nytimes.com/2019/11/04/opinion/martin-scorsese-marvel.html?_ga=2.261513988.842084746.1581629411-1810503934.1581629411.
[15]https://m.weibo.cn/status/4464228934865198?.
[16]李洋.叢書總序[A].[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真實眼淚之可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III.
[17]汪民安.何謂“情動”?[J].外國文學,2017(2).
[18][加]布萊恩·馬蘇米.虛擬的寓言[M].嚴蓓雯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4.
[19][法]保羅·維利里奧.戰爭與電影[M].孟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20]李恒基,楊遠嬰.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修訂本)(上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216.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
(責任編輯?周雨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