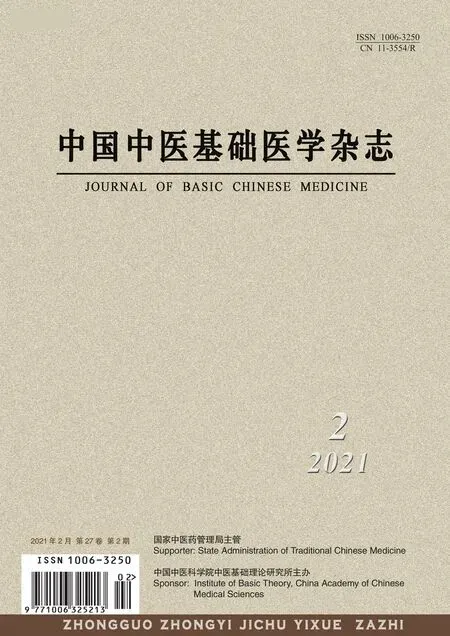腸道微生態在中醫藥領域的研究*
張佳緣,曹 劉,王云霞,晉瑜霞,肖 嘯,張 琦△
(1. 成都中醫藥大學, 成都 610072; 2. 四川省中西醫結合醫院,成都 610041)
中醫學歷經數千年的發展,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貢獻。由于其獨特的理論體系,現代醫學難以對其理論、療效的生物學機制進行本質性的詮釋。近現代中醫界乃至國際科研界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對中醫理論、診法、治法、方劑、中藥等各個方面不斷深入研究,試圖運用現代科學方法探索中醫學的科學內涵。隨著微生態學的興起,作為人體存在寄生生命最多的腸道微生態系統,逐漸成為全球的研究熱點。由于腸道微生態系統與中醫理論系統都體現了整體、平衡、動態變化等特點,因此中醫研究者不斷嘗試以腸道微生態系統為切入點,研究中醫學相關理論及方藥療效機制。本文將從證候研究、舌診研究、臟腑相關性理論研究、中醫治法方藥研究4個方面,分析基于腸道微生態的中醫藥相關研究,以求探索未來相關領域的發展方向。
1 腸道微生態與中醫藥理論
健康成年人的腸道內定殖著多達100萬億個微生物,至少包括30個屬500種細菌,是人體微生物棲息最多的部位,如此龐大數量的微生物及其生活的環境等構成了腸道微生態[1]。2007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首先提出人體微生物組計劃(human microbiome project,HMP)[2],腸道微生物開始成為國際科研界的焦點。經過不斷的研究發現,腸道微生態系統作為人體最大的互利共生有機統一體,參與人體物質代謝、免疫調節、信號傳導等重要生命活動[3]。目前腸道微生物的檢測方法主要包括分子生物學方法以及高通量測序技術兩大類[4]。運用傳統分子生物學方法檢測腸道微生物,可檢測的種類較少且只能針對已知的微生物進行分析。而高通量測序技術檢測微生物的范圍廣、種類多,且可進一步進行基因功能注釋,分析腸道菌群在宿主生命活動中的具體功用[5]。目前高通量測序技術已經廣泛應用于腸道微生態研究,腸道微生物宏基因組學的研究也已經成為國際科學界的前沿熱點。
有學者進行了純理論分析,認為腸道微生態恒動性、整體性等特點與中醫基礎理論中的整體觀、系統觀、恒動觀、平衡觀、陰陽理論、正邪理論、藏象理論等有相通之處[6-7]。19世紀80年代,我國微生態學創始人魏曦教授預言“微生態學很可能成為打開中醫奧秘大門的一把金鑰匙”[8],首次將微生態概念引入中醫藥領域的科學研究。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基于腸道微生態進行的中醫學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 基于腸道微生態的中醫藥研究
2.1 證候研究
脾胃為后天之本,運化水谷精微、生成氣血津液用于人體生命活動,這與現代醫學中腸道微生物參與食物消化吸收的功能相似,腸道菌群失調的癥狀與中醫脾胃虛弱的厭食、腹瀉等表現類似。危北海于1984年提出“系統而深入地分析腸道菌群狀態,是研究脾胃疾病的生理病理變化的一個重要途徑”[9]。因此,中醫藥領域基于腸道微生態開展得較早、較全面的研究集中于脾胃系統,如脾虛證型、濕熱證型的實質性研究。
2.1.1 脾虛證型 嚴梅楨等[10]較早地運用傳統培養法研究大黃水煎液灌胃制備的實驗性脾虛小鼠,發現脾虛模型小鼠出現了以雙歧桿菌、乳桿菌菌量下降為主要表現的腸道菌群紊亂。 劉晉生[11]等發現,脾氣虛證的胃和十二指腸疾病患者腸道致病菌的檢出率最高,因此脾虛證的部分生物學機制可能為腸道菌群的失衡。有研究[12]將脾虛模型大鼠與腎虛模型大鼠進行對比,發現脾虛模型大鼠糞便中革蘭氏陽性桿菌和霉菌的比例增加,革蘭氏陰性桿菌的比例下降,且優勢菌種以金黃色葡萄球菌、厭氧梭狀芽胞桿菌和白色念珠菌此類正常狀態下腸道含量極少的菌種為主,而腎虛模型大鼠未出現腸道菌群的改變。由此推斷,腸道菌群的改變可能是脾虛證的特異性生物學指標之一。后續運用類似傳統培養方法對脾虛證進行研究的結論可大致總結為腸道正常有益菌群的減少[13],或厭氧菌的減少[14-15],如雙歧桿菌、乳酸桿菌;條件致病菌的增多,如梭菌、葡萄球菌等[16]。由于傳統培養法檢測的菌群種類過少,研究范圍局限,其他分子生物學方法也被逐漸應用于脾虛證型的研究。王卓[17]通過分析對比番瀉葉煎劑制備的脾虛模型大鼠造模前后腸道菌群的腸道細菌基因間重復序列聚合酶鏈式反應(enterobacterial repetitive intergenic-consensus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ERIC-PCR)指紋圖譜發現,脾虛證型特異性表現的分子評價指標主要包括脾虛相關特征條帶390 bp的凈面積與豐度數值、ERIC-PCR指紋圖譜多樣性指數以及健康-脾虛Sorenson配對相似性系數。后續研究[18]在分析腸道菌群結構的同時觀察腸道微生物代謝產物短鏈脂肪酸的變化。劉佳[25]等對老年脾虛患者腸道菌群進行16S rDNA變性梯度凝膠電泳分析,發現脾虛患者與健康人指紋圖譜比較出現特征性變化[19]。
隨著高通量測序技術在腸道微生態領域的廣泛運用,中醫藥科研界也開始運用該技術研究脾虛證型腸道菌群的變化。李文艷運用16S rDNA技術[20]對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患者糞便標本進行研究,發現與健康受試者對比肝郁脾虛證患者腸道菌群中的柔膜菌門菌群相對豐度明顯降低,酸桿菌門綱目、腐生螺旋菌綱目、葡萄球菌科屬、紅螺菌科菌群豐度增高,說明該證型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患者的腸道菌群發生了獨特變化。有研究[21]運用高通量測序方法發現,脾虛濕困型痛風患者厚壁菌門、變形菌門所占比例較正常人明顯上升,而擬桿菌門、梭形桿菌則大幅下降。由此可知,實驗技術的發展,使研究逐漸由特定菌群轉變為整體多樣性及豐度等的研究,并開始與腸道微生物代謝產物如短鏈脂肪酸等逐漸結合。
總的來說,脾虛證基于腸道微生態的研究,既往主要采用傳統分離培養以及分子生物學方法,近年已經開始嘗試運用高通量測序技術進行研究。運用傳統培養方法進行的研究多針對脾虛證型狀態下腸道特定種類菌群的含量變化,早期研究針對的菌群單一(多研究以雙歧桿菌、乳酸桿菌等為代表的腸道益生菌),后續研究增加了菌群的種類,對比研究厭氧菌與需氧菌,腸道正常菌群與條件致病菌、致病菌。目前研究顯示,脾虛證型在腸道微生態的表現多為腸道益生菌的減少,或伴有腸道條件致病菌和(或)致病菌的增加;厭氧菌的減少,需氧菌的增加。基于分子生物學方法發現,脾虛證型腸道微生物的多樣性下降,與健康狀態腸道菌群結構的相似性下降。目前通過高通量測序技術研究脾虛證的報道相對較少,多為臨床研究,不同疾病過程中脾虛證型腸道微生態的表現不盡相同,未來需要多病種、多層次的深入研究了解脾虛證腸道菌群相對精確的表現趨勢。
2.1.2 濕熱證型 隨著對脾虛證研究的逐步開展,濕熱證型也逐漸引起研究者們的注意。江月斐等[22]通過傳統培養計數方法研究顯示,脾胃濕熱證腸易激綜合征患者腸道革蘭氏陽性桿菌比例明顯下降,而革蘭氏陰性桿菌及革蘭氏陽性球菌比例明顯上升,且與脾氣虛證比較革蘭陽性桿菌比例以及腸道菌群密度明顯升高。付消巖等[23]發現,慢性腹瀉脾胃濕熱證患者腸道中的需氧菌腸桿菌、腸球菌較脾虛證明顯增多,B/E(雙歧桿菌/大腸桿菌)比值高于脾虛證組,厭氧菌雙歧桿菌、乳桿菌亦高于脾虛證組,與脾虛證比較呈現出不同程度的菌群失調趨勢。吳宛蔚[24]對濕熱證型便秘患者的糞便進行分離培養發現,此類病人腸道雙歧菌、乳桿菌減少,腸球菌、霉菌增多。陳曉剛[25]運用實時熒光定量PCR技術(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RT-qPCR)研究發現,再發性腹痛脾胃濕熱證兒童與脾胃濕熱證對比,雙歧桿菌和腸桿菌含量顯著增加,B/E值升高。王婷等[26]運用RT-qPCR技術檢測不同濕熱動物模型腸道菌群,發現不同發病機制的濕熱證型腸道菌群表現不盡相同。脾陽虛為內濕基礎的濕熱證模型小鼠雙歧桿菌屬、乳桿菌屬含量減少,濕邪困擾為內濕基礎的濕熱證則表現為雙歧桿菌屬、乳桿菌屬含量增多。高通量測序研究[27]發現,潰瘍性結腸炎濕熱內蘊證、脾胃濕熱證以及脾胃氣虛證3種證型患者之間腸道菌群的差異性可能存在于厚壁菌門和變形菌門的構成比。
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可發現,濕熱證型與脾虛證型相較而言在腸道菌群結構方面的表現有以下趨勢:菌群密度及多樣性升高,腸道菌群條件致病菌和(或)致病菌增加,或伴有腸道厭氧菌的減少、B/E比值升高。除此之外,基于高通量測序技術的研究相對較少,多局限于潰瘍性結腸炎濕熱證,難以集中總結濕熱證在腸道菌群門、綱、目、科、屬、種的變化趨勢。
2.1.3 臟腑相關性理論研究 基于腸道微生態進行的臟腑相關性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肺大腸相表里”實質性研究。“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源于《黃帝內經》,肺與大腸在經絡結構、生理、病理上相互聯系,手太陰經屬肺絡大腸,手陽明經屬大腸絡肺。肺氣的肅降與腸道的功能密切相關。肺氣失于肅降可導致大腸傳導失司;腑氣不通、大腸傳導不暢亦可致肺氣壅塞。“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中的“肺”與現代醫學中的呼吸系統相關,而“大腸”與解剖器官腸道類似。近年來肺與大腸相互聯系機制的研究逐漸深入,如兩者組織結構同源性、內分泌機制等方面,而腸道微生態也是研究肺臟與腸道生物學聯系的重要切入點。總體而言,肺系疾病可以導致腸道菌群的變化,兩者可相互影響。進一步研究顯示,在肺系疾病(慢性支氣管炎)與腸系疾病模型(潰瘍性結腸炎)中,肺腸菌群部分存在同步規律性變化[28]。臨床研究發現,肺系疾病患者與其他系統疾病患者對比納差、便秘、便溏等癥狀的發生率較高,腸道存在明顯趨向異常的革蘭氏陽性球菌[29]。方騫等[30]發現,喘息性支氣管炎患兒在患病初期就出現了腸道菌群失調,表現為B/E值降低。除此之外,腸道菌群的變化亦可引起肺部微生物群的改變,可能導致肺部的病理損傷[31]。基于“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研究者通過汗法、宣肺利水法治療呼吸道感染、非小細胞肺癌,緩解病情的同時也觀察到腸道微生態的改變[32]。
“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與腸道微生態相關的生物學機制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當腸道菌群失調時,腸道中致病菌數量增加。這些致病菌可能通過消化道移行致口咽部,然后可能順行至呼吸道[33];由于腸道菌群失調時可能釋放腸源性內毒素進入血液循環,經下腔靜脈進入右心,經肺動脈和毛細血管最先到達肺臟[34];腸道菌群改變引起其一些可能參與免疫的代謝產物含量及種類發生變化,從而影響肺部的免疫環境[35]。
2.2 舌診研究
舌診是中醫診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辨證論治的重要依據。有研究認為,通過闡述舌苔菌群與腸道菌群的聯系,可以研究患者中醫體征與臟腑病變的物質聯系[36]。
膩苔作為一種常見的病理性舌苔,與腸道微生態的相關性研究相對較多。膩苔主濕邪、痰濁、食積,與胃腸道及脾胃系統密切相關。研究發現,膩苔的形成與腸道微生態的改變有相關性,脾虛濕盛泄瀉呈白膩苔的患者存在明顯的腸道微生態失調及舌部菌群改變,且兩者具有相關性[37]。由此推斷,腸道微生態的改變可能為膩苔的生物學表現之一,但仍需進一步大范圍的研究進行證實。
2.3 中醫治法方藥研究
2.3.1 健脾法及健脾方劑 隨著脾虛證腸道微生態相關生物學實質研究的拓展與深入,健脾治法及方劑作用機制的研究也逐漸開展。目前健脾法影響腸道微生態的研究多通過經典健脾方劑參苓白術散、四君子湯、七味白術散、理中湯等開展。研究發現,參苓白術散不僅能促進腸道益生菌的增殖[38-39],亦能修復腸黏膜,提高腸道局部的免疫能力[40]。如李姿慧[41]等發現,參苓白術散可以明顯改善脾虛濕困型潰瘍性結腸炎大鼠結腸組織中NF-κB p65蛋白表達,控制炎癥反應促進腸道黏膜的恢復。董開忠[42]等發現,抗生素誘導的腸道菌群失調小鼠服用參苓白術散后,腸道乳酸桿菌、雙歧桿菌等生理性細菌的增殖增加,而內毒素和P物質降低,說明參苓白術散不僅促進益生菌的增殖,還抑制了致病菌和條件致病菌的生長。四君子湯作用于腸道微生態,可促進腸道益生菌的增殖,提高腸道微生物多樣性,改善腸道局部的免疫狀態。孟良艷[43]較早運用16S rDNA測序技術發現,四君子湯可明顯提高脾虛大鼠腸道菌群的多樣性。分泌型免疫球蛋白(sIgA)是黏膜分泌的免疫球蛋白,反映著黏膜的局部免疫狀態,腸道sIgA的產生、分泌、功能與腸道菌群密切相關[44]。較多研究基于腸道組織中局部sIgA含量,分析四君子湯對于腸道局部免疫的作用。經過四君子湯治療后的脾虛泄瀉小鼠腸道菌群結構改善(乳酸桿菌增多,大腸桿菌量減少),回腸和盲腸sIgA含量增加[45]。運用中醫推拿聯合四君子湯[46]可改善β-內酰胺類抗菌藥物相關性腹瀉患兒的糞便球/桿菌比例、sIgA含量及血清二胺氧化酶、降鈣素原(PCT)、IgG、IgA等免疫、炎癥相關指標[46]。研究發現,理中湯可抑制肝硬化大鼠腸道腸桿菌、腸球菌、韋榮球菌,促進雙歧桿菌、乳酸桿菌、類桿菌增殖,降低血清內毒素及炎性因子水平,緩解肝臟纖維化,改善肝臟功能[47-48]。舒青龍[49]等運用16S rDNA高通量測序技術發現,理中湯可改善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模型小鼠的腸道菌群結構,增加腸道菌群的多樣性。
健脾法、健脾方劑相關的研究,一方面針對腸道菌群種類、結構、多樣性研究較多,另一方面對于腸道局部免疫的研究逐漸發展,已試圖進一步探索腸道菌群的改變對于腸道局部乃至整個機體免疫的影響。
2.3.2 單味中藥及中藥單體 不同于中醫復方的研究,中藥方面除了研究單味中藥對于腸道菌群結構的影響,還進行了中藥有效成分的探索,并且重視腸道菌群與中藥有效成分的相互作用。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研究者們逐漸開始研究中藥對微生物的作用[50],到目前為止,從腸道菌群切入進行研究的中藥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為清熱解毒藥,一類為補益藥,兩者對于菌群的作用也主要為促進腸道有益菌群的生長,抑制致病菌的增殖。如崔祥等[51]發現,黃連提取物可顯著抑制病原菌(腸桿菌、腸球菌)的生長,顯著促進益生菌(乳酸菌、雙歧桿菌)的生長。大黃對于腸道微生態的作用是雙向的,大劑量大黃可導致腸道菌群的紊亂,這也是制備脾虛動物模型的方法之一。而在膿毒癥、急性腎衰等疾病病理狀態下,大黃可調節失衡的腸道微生態[52-53]。孫立群[54]等發現,納米黃芪可改善潰瘍性結腸炎大鼠腸道菌群失調,使腸道雙歧桿菌﹑乳酸桿菌含量明顯上升,腸球菌﹑腸桿菌含量下降。有研究[55]發現,10~6kDa分子量的黃芪總多糖調節鹽酸林可霉素灌胃小鼠的腸道微生態效果最好。宋克玉等[56]同時研究黨參和茯苓(均為補益中藥)對小鼠腸道菌群的影響,發現高劑量的黨參能顯著提高腸道乳桿菌水平,并降低大腸桿菌水平,而高劑量的茯苓能顯著提高腸道雙歧桿菌水平。
中藥的給藥方式多以口服為主,均需經過胃腸道的消化吸收,離不開腸道菌群的作用,經腸道菌群代謝后的中藥成分才能成為最終的起效成分。因此基于腸道微生態的中藥藥物代謝學研究方向也成為目前中醫界的研究熱點之一。腸道微生物群與中藥兩者具有雙重效應,腸道微生物群豐富的代謝酶系可以對中藥成分的結構進行水解、氧化和還原、異構化等修飾反應,生成的代謝產物具有與其前體不同的生物利用度、生物活性和毒性,對中藥成分可能具有減毒或增效等效應。另一方面,中藥化學成分與腸道微生物群相互作用,可調節腸道微生物群的組成以恢復其穩態,從而改善其功能障礙以及相關的病理狀況[57]。附子主要成分為烏頭堿,有研究[58]發現,烏頭堿經人體腸道菌群作用后會發生酯化反應產生新的單酯型、雙酯型和脂類生物堿等,這些產物相對烏頭堿毒性較弱。番瀉葉本身的主要成分番瀉苷不具有瀉下活性,只有被腸道菌群轉化成為代謝產物大黃酸后,才能表現出瀉下的藥理活性[59]。
單位中藥及中藥單體的研究主要以動物模型為主,但是動物模型難以還原人體腸道微生態環境,這對研究成果最終的臨床適用性有一定的局限。中藥研究是腸道微生態在中藥領域應用的主要部分,多注重單藥有效成分的提取與研究,對于多味中藥、多種成分在腸道產生的具體生物化學效應研究較少,但中藥療效的產生往往基于多種化學成分、多種藥物,所以單一藥物、單一成分無法代表中藥與人體腸道微生態相互作用的實際情況。
3 前景與展望
由于中醫理論本身整體、動態變化等特點,以生態學角度研究中醫理論實質、中醫藥作用機制具有廣闊的研究前景。腸道微生態近年來已經成為國際研究熱點,研究技術也隨著現代分子生物學、生物信息學等飛速發展而不斷地更新換代,但總體來說目前基于腸道微生態進行的中醫藥研究相對落后。一方面研究成果集中在菌群變化方面,缺乏進一步分子生物機制的研究;另一方面,多數研究所采用的傳統培養研究腸道微生物的方法已經難以滿足對于腸道整體復雜菌群的研究要求。因此,未來基于腸道微生態的中醫藥生物學機制研究應利用宏基因組等前沿的方法,研究中醫藥理論在腸道微生態方面的生物學表現以及中醫藥對于腸道微生態結構與功能的具體影響,并進一步挖掘相關分子生物學作用通路與機制,揭示中醫藥通過腸道微生態產生作用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