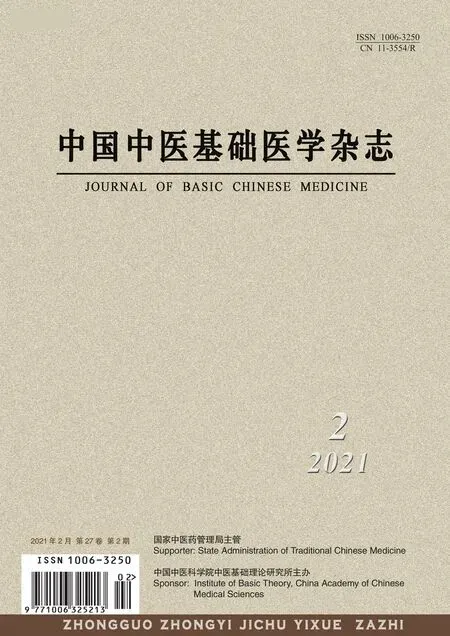論金元四大家治痹特點*
郝冬林,汪 悅,高忠恩△
(1. 南京中醫(yī)藥大學附屬蘇州市中醫(yī)醫(yī)院,江蘇 蘇州 215003; 2. 南京中醫(yī)藥大學附屬江蘇省中醫(yī)院,南京 210029)
溯自周秦之際,中醫(yī)學就有了對“痹證”的認識,最早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脈灸經(jīng)》中便有“疾畀”(痹)的記載,而《黃帝內經(jīng)》《傷寒論》《金匱要略》則奠定了痹證的理論基礎。迄至金元時代,史稱“金元四大家”的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朱丹溪摒棄宋以來醫(yī)家多默守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以“一方通治諸病”之弊,提出不同治病主張,開創(chuàng)后世中醫(yī)派別先河。正如《四庫全書》評價道:“儒之門戶分于宋,醫(yī)之門戶分于金元。”而金元四大家對痹證病因病機提出的不同觀點和治痹之法,進一步推動了痹病學的發(fā)展[1]。
1 劉完素——秉典創(chuàng)新,辨證論痹
1.1 秉承經(jīng)典,創(chuàng)立新說
劉完素臨床診治多秉承《黃帝內經(jīng)》思想:“蓋濟世者憑乎術,愈疾者仗乎法。故法之與術,悉出內經(jīng)之玄機”[2],并編撰了許多與《黃帝內經(jīng)》《傷寒論》相關著作,如《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內經(jīng)運氣要旨論》《傷寒直格》以及與《局方》并稱為“南局北方”的《素問宣明論方》等。他對痹證的認識中,秉承《黃帝內經(jīng)》“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及“風寒濕三氣偏盛”的學術思想,但又尊經(jīng)而不泥古,根據(jù)臨床實際創(chuàng)立新說,如以《素問·至真要大論篇》病機十九條為綱,創(chuàng)造性地增加了“諸澀枯涸,干勁皸揭,皆屬于火”的病機,認為“火灼真陰,血液衰少”可導致“皮膚皴揭而澀”,甚則“麻痹不仁”,對后世五淫痹之“燥痹”的病因病機有著指導意義[3];治療要“切忌辛溫大熱之烏附之輩”,應“通經(jīng)活絡,投以寒涼之品”,以達到“養(yǎng)陰退陽,血脈流通,陰津得布,肌膚得養(yǎng)”,并創(chuàng)立麥門冬飲子,成為目前臨床治療干燥綜合征的常用方劑;他認為“陽氣多,陰氣少,陽熱遭其陰寒”可發(fā)生熱痹,并出現(xiàn)“肌肉熱極……皮色變”的臨床表現(xiàn),主張犀角、羚羊角等寒涼之藥治療熱痹,為后世熱痹證型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1.2 治痹求本,辨證治痹
劉完素臨證治痹的首要之務當“明察病機”,“察病機之要理, 施品味之性用, 然后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 無以去深藏之大患”[2]15,只有把握風寒濕等邪氣之本質,明辨病機,才能為正確施治提供可靠保證。他雖主寒涼立法,但治痹卻非諸用寒涼之藥,而是講究辨證治痹。在《素問玄機原病式》中提到治痹之法:“大凡治病必求所在……病氣熱則除其熱,寒則退其寒,六氣同法。瀉實補虛,除邪養(yǎng)正,平則守常,醫(yī)之道也!豈可見病已熱,而反用熱藥,復言養(yǎng)水而勝心火者。[4]”其《素問宣明論方》列方348首, 據(jù)統(tǒng)計66%方劑多為寒熱并用,偏于溫熱的占21%, 而偏于寒涼的用方僅占13%;且首次將行痹、痛痹、著痹、熱痹等諸痹單獨列舉,依據(jù)不同證型特點辨證用方,如附子丸治療因陽氣少、陰氣多、氣血不行所致痹氣證;用附子湯治骨痹,防風湯治行痹,加減茯苓湯治痛痹,茯苓川芎湯治著痹,升麻湯治熱痹以及防風通圣湯治風熱走注疼痛麻痹。另對《黃帝內經(jīng)》首提“周痹”之病,不但豐富了其論述:“在血脈之中,隨上下,本痹不痛今能上下周身,故以名之”[5],而且提出用大豆蘗散以及針刺曲垣、膈俞、足臨泣、灸曲垣治之,其自創(chuàng)防風湯更是現(xiàn)代臨床常用治療痹證有效的代表方劑。觀其治痹所用方藥,處方靈活,寒涼溫熱,攻補兼施,各選其宜,隨證治之。
2 張從正——攻邪治痹,注重通陽
2.1 首提“濕熱”為痹證之源及痹證鑒別
張從正前從劉完素之學,后啟朱丹溪之論,在《儒門事親》中首次提出“痹證以濕熱為源,風寒濕為兼”的論點,認為濕熱也是致痹的主要原因之一,“所受之邪各有淺深,或痛或不痛,或仁或不仁,或筋屈而不能伸,或引而不縮,寒則蟲行,熱則縱緩,不相亂也”[6]。并用類比的方法詳細鑒別分析“風、痹、痿、厥”四證關系:“夫風痹痿厥四證,本自不同,而近世不能辨,一概作風冷治之……夫四末之疾,動而或勁者為風,不仁或痛者為痹,弱而不用者為痿,逆而寒熱者為厥,其狀未嘗同也,故其本源又復大異”[6]6。另外還指出,各種痹證致病特點不同,如行痹多旦劇夜靜,痛痹多旦靜夜甚,著痹多肌肉削而著骨,對后世臨床痹證之鑒別診斷具有實際意義。
2.2 善用汗、吐、下三法以通陽治痹
張從正善于根據(jù)病邪的性質、部位深淺,采用汗吐下三法使得邪祛則陽氣通達,氣血自暢,痹證自除。《儒門事親》云:“諸風寒之邪,結搏皮膚之間,藏于經(jīng)絡之內,留而不去,或發(fā)疼痛走注,麻痹不起及四肢腫癢拘攣,可汗而出之,風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濕固冷,熱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6]36”臨床常先用郁金散吐之,次服導水丸,輕寒之藥泄之,再以辛溫之劑發(fā)散汗出,如此涌吐以滌寒痰,蒸汗以疏經(jīng)絡,滲下分解濕滯,即“去邪以安正”,再用“當歸、芍藥、烏附,行經(jīng)和血之藥”才可事半功倍,痹病乃愈。他還指出風痹可用越婢加術附湯,輕則用防風湯加威靈仙、伸筋草等;寒痹則用烏頭湯或五積散,上肢痛甚加片姜黃,下肢痛甚加五加皮;濕痹用神效黃芪湯去蔓荊子,加防風、羌活、桂枝或用除濕蠲痹湯加薏苡仁、秦艽、防風之類;濕熱痹濕甚肢體煩痛、手足沉重用蠲痹湯;熱偏甚熱流四肢、諸節(jié)腫痛用千金犀角散,加秦艽、防己、酒黃柏等藥物。如其治痹:“陳下酒監(jiān)魏德新,因赴冬選,犯寒而行、真氣原衰,加之坐臥冷濕,飲食失節(jié),以冬遇此,遂作骨痹。腰之高骨壞而不用,兩胯似折,面黑如炭,前后兼痛,痿厥嗜臥。[6]8”此例以寒氣勝之痛痹,故以“玲瓏灶、用蒸氣法溫運通脈”,內服苓、術、官桂助脾土以制寒水之勢上凌,溫散寒濕而止痹痛,并針刺腎俞、太溪兩穴輔治,以宣暢少陰腎經(jīng)的陽氣,陽通則痹解,重視內外之法以治痹。
2.3 重視痹證恢復期調護:
此外,張從正還注重痹證恢復期飲食調攝及調暢情志。認為治病當論藥攻,但養(yǎng)生當論食補,將“谷肉果菜”比喻“君之德教”,謂之“梁肉”“汗下吐之法猶君之刑罰”,當“病之去也,粱肉補之”[7],強調食療對痹證后期恢復具有積極影響。并提出“悲可以治怒,以愴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謔浪褻狎之言娛之”[6]75,這對久痹不愈或因郁致病等產(chǎn)后痹具有一定的臨床指導意義。
3 李東垣——脾胃為本,升陽蠲痹
3.1 脾胃所傷,痹病由生
李東垣認為“人之一身,脾胃為主”,脾胃為氣血生化之源,元氣之本,陰陽氣機升降之樞紐,若脾胃功能正常則百病不生;若“脾胃一傷,五亂互作”,如遇風寒濕等邪氣,可致筋骨不堅,經(jīng)隧不暢,四肢不用,易生痹病。“脾病,體重節(jié)痛,為痛痹,為寒痹,為諸濕痹”[8],提出“脾胃所傷”為痹證主要發(fā)生原因之一,豐富了痹證的病因學說。
3.2 痹證論治,首辨外感內傷
在痹證辨證論治中李東垣強調首先要辨外感還是內傷:“若外傷風寒,是腎肝之氣已絕于內。腎主骨,為寒;肝主筋,為風……得病之日,便著床枕,非扶不起,筋骨為之疼痛,不能動搖,乃形質之傷”[9],說明外感風寒之邪癥狀表現(xiàn)多在體表,肌肉同筋骨相連,風寒外束,寒傷于形,致筋攣骨痛,臥床難以運動自如,這是外傷致痹的機理;“內傷等病是心肺之氣,已絕于外,必怠惰嗜臥,四肢沉困不收”[9]10。脾胃之氣受病,心肺精氣已絕,營衛(wèi)失據(jù),癥狀表現(xiàn)為少氣懶言、手足軟弱、沉困好睡、精神不振等,出現(xiàn)“骨消筋緩”的病理狀態(tài),成為內傷致痹的機理。
3.3 善用風藥,升陽蠲痹,分經(jīng)治痹
李東垣認為“諸風皆能勝濕”,善用風藥以勝濕散郁、升陽蠲痹。對外感痹證常用羌活、獨活、升麻、柴胡、防風、葛根等味薄清輕發(fā)散之藥物,既可祛風散寒除濕,又能升發(fā)脾之清陽,使得清陽以升,濁陰自降,諸癥可解,如羌活勝濕湯、通氣防風湯等;對于脾胃虛弱、風寒濕之邪乘虛而侮者,則用人參、黃芪、白術以補氣健脾益胃;蒼術、豬、茯苓及澤瀉淡滲利濕醒脾,再配以柴胡、升麻等風藥,使脾陽升清,氣機暢達,氣血充盈;對于陽氣被遏、日久化熱、濕熱蘊伏之熱痹,取“火郁發(fā)之”之意,用升麻、葛根之風藥,補益與升散并用,使陽氣得升,清氣上浮,郁火消散,氣機暢達,陰陽相濟,代表方劑如補中益氣湯、當歸拈痛湯、升陽散火湯等,現(xiàn)在當歸拈痛湯臨床常用于治療類風濕關節(jié)炎屬濕熱內蘊而兼風濕表證者。李東垣還根據(jù)不同引經(jīng)藥物治療痹痛,如升麻、白芷、葛根可用于“臂之前廉痛者,屬陽明經(jīng)”者;太陽經(jīng)者可用藁本、羌活;“屬少陽者”以柴胡行之;“內廉痛者,屬太陰經(jīng)”以升麻、白芷、蔥白行之;細辛、獨活可治少陰者。
4 朱丹溪——痰瘀論痹,滋陰療痹
4.1 首立“痛風”名,從痰瘀論痹
朱丹溪在對痹證認知中首立“痛風”之名,由于素人陰虛火盛,“血受熱自沸騰”,后因涉水遇冷,或久居濕地,或當風受涼,“寒涼外搏,熱血得寒,污濁凝澀”而成痹。認為“濕痰濁血流注”是其發(fā)生病機,在臨床實踐中以氣血痰郁為綱,以人的體質作為辨證論痹的客觀依據(jù),強調從痰瘀論痹。《丹溪心法》中載有:“肥人肢節(jié)痛,多是風濕與痰飲流注經(jīng)絡而痛,瘦人肢體痛,是血虛”[10],說明已關注到人的體質和痹證發(fā)病是相關的。另有記載“惡血入經(jīng)絡證,血受濕熱,久必凝濁,所下未盡,留滯隧道,所以作痛”[11],并在《金匱鉤玄》中指出“濕痰死血”可致“十指麻”,認為痰瘀之邪既是痹證發(fā)生原因又是痹證病理產(chǎn)物。若人嗜食肥甘厚味,易痰濕內生,阻礙脈道,氣血不通,發(fā)為痹證;痹證日久,氣血不暢,氣滯濕阻,聚而成痰,痰瘀互結,可加重痹證,這對于后世活血化瘀、祛痰化濁治療痹證有著深遠影響。已故國醫(yī)大師朱良春所創(chuàng)的泄?jié)峄觥㈩帽酝ńj法治療痛風深受其影響。
4.2 注重養(yǎng)血,滋陰療痹
朱丹溪治痹反對妄用溫燥,以免劫傷陰血,注重養(yǎng)血,滋陰療痹,常用補血滋陰之當歸、芍藥、龜甲、熟地黃、四物湯等,配以清熱、祛痰化瘀以調暢氣血。“因于濕者,蒼術、白術之類,佐以竹瀝;因于痰者,二陳湯加加酒炒黃芩、羌活、蒼術;因于血虛者,用芎歸之類,佐以紅花、桃仁”。“如瘦人肢節(jié)痛,是血虛,宜四物加防風、羌活。如瘦人性急躁而肢節(jié)痛,發(fā)熱,是血熱,宜四物湯加黃芩、酒炒黃柏”[10]181。并注重引經(jīng)藥物的使用:“凡治痛風,取薄桂味淡者,獨此能橫行手臂,領南星、蒼術等藥至痛處”。自創(chuàng)治痹代表方如上中下通用痛風方、二妙散、加味四物湯[12],均被后世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臨床常用方劑。其中上中下通用痛風方更能疏散風邪于上,清熱利濕于下,活血化痰、消滯和中,上中下痹皆宜用。
金元四大家治痹雖各有主張,但卻一脈相承,他們將各自學派學術特點用于痹證治療之中,開創(chuàng)了痹病學術百家爭鳴局面,豐富了痹證的理論基礎和實踐經(jīng)驗,對后世醫(yī)家治痹有著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