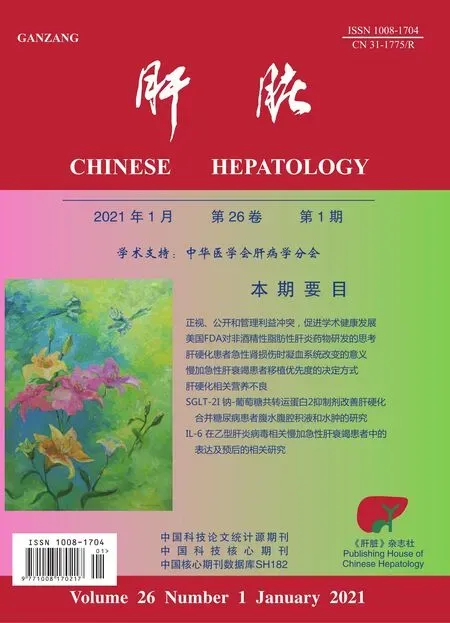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流行現狀
金倩 楊菁 范建高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是遺傳易感和胰島素抵抗引起的代謝功能障礙相關脂肪性肝病,肝臟特征性病變包括大泡性肝細胞脂肪變、小葉內炎癥、肝細胞氣球樣變以及肝纖維化[1]。隨著全球前所未有的工業化進程以及人類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21世紀以來NAFLD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現已成為全球第一大慢性肝病。考慮到始于兒童期的肥胖的持續流行、2型糖尿病患病率的不斷攀升以及人口老齡化等因素的影響,預計NAFLD的患病率以及進展期肝病患者的比例將繼續增加。與對照人群相比,進展至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和進展性纖維化的NAFLD患者肝病殘疾和死亡以及全因死亡風險顯著增加,給個人、家庭和醫療衛生系統帶來巨大社會經濟負擔。
目前,NAFLD的全球患病率估計為25%左右,僅在美國就有8 000余萬NAFLD患者。2016年發表的全球NAFLD流行病學系統綜述顯示,NAFLD患病率最高的地區是中東(32%),其次是南美洲(30%)和亞洲(27%),隨后是歐洲和北美(24%),非洲(13%)最低[2]。2019年一項系統綜述顯示,亞洲NAFLD總體患病率為30%,其中以印度尼西亞最高(51%),日本最低(22%)。新加坡、馬來西亞、伊朗、孟加拉、韓國和印度以及香港和臺灣地區NAFLD患病率都超過30%,中國大陸NAFLD患病率也接近30%[3]。鑒于NASH 需要通過肝活組織學檢查才能確診,目前只能根據少量的肝活檢資料估算普通人群NASH的患病率。基于現有的不完整數據,普通人群NASH的患病率估計為1.5%~6.45%,NAFLD患者NASH患病率為7%~30%。各個國家和地區肝活檢患者存在選擇偏倚,在亞洲的一項1 000余例肝活檢證實的NAFLD研究中NASH的檢出率為63.5%[2]。
過去40年間,全球肥胖癥的患病率增加了3倍。2016 年,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19億以上成年人超重,6.5 億以上成年人肥胖,每年因超重和肥胖并發癥而死亡的人口高達400萬[6]。香港的一項基于磁共振質譜分析普查脂肪肝的社區調查顯示,NAFLD患病率為28.8%,其中非肥胖者為19.3%,肥胖者為60.5%[7]。除肥胖以外,高脂血癥、2型糖尿病和胰島素抵抗等均為NAFLD發生發展的重要危險因素。隨著年齡的增長,NAFLD及其相關肝纖維化的患病率不斷增加。男性NAFLD患病率似乎高于女性,但是女性NAFLD患者NASH伴有進展性肝纖維化的比例可能高于男性。絕經后女性由于雌激素對代謝危險因素和肝纖維化保護作用的削弱,NAFLD患病率增長迅速,并且顯著肝纖維化的發生風險增加[4]。
隨著時間的推移,NAFLD發病率不斷增加。全球NAFLD發病率也存在地域差異,從以色列的28.01/1 000人年(95%置信區間19.34~40.57)至亞洲的52.34/1 000人年(95%置信區間28.31~96.77)[2]。預計2030年美國NAFLD患病人數將突破1億[8]。來自美國明尼蘇達州奧姆斯特德縣的一項基于人群的研究表明,自1997年以來診斷編碼確定的NAFLD發生率增加了5倍,以18~39歲的年輕人增加最為顯著[5]。NASH所致肝硬化日益增多,15%~20%的NASH患者終將發生肝硬化和HCC。在美國因HCC進行肝移植的患者中,NASH的占比從2.1%增至16.2%[10],NASH僅次于酒精性肝病是當前美國肝移植的第二大適應證[10]。NASH在歐洲肝移植患者中的占比高達8.4%,在2002年至2016年期間增長了7倍[11]。
與2015年相比,2030年NASH所致失代償期肝硬化和肝細胞癌(HCC)人數預計將分別增加168%和137%,肝臟相關死亡將增加178%[9]。與2016年相比,2030年中國NASH及其相關HCC患者數量將分別增加48%和82%[12]。此外,NAFLD還會伴發一系列肝外疾病,例如2型糖尿病、慢性腎病、心血管疾病、甲狀腺功能低下、多囊卵巢綜合征、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并增加結直腸腺癌等肝外癌癥的發病風險。
普通人群NAFLD患病率及其臨床表型和轉歸存在明顯差異,這些差異歸因于代謝合并癥、微生物組以及環境和遺傳或表觀遺傳等眾多因素,其中某些因素可解釋西班牙裔美國人NASH及其相關肝纖維化發病風險的增加[13]。既往認為西班牙裔是NAFLD的高危人群,最近研究發現墨西哥裔西班牙人NAFLD患病率為33%,而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后裔的患病率分別為18%和16%,提示PNPLA3基因多態性和出生地都與NAFLD的發病相關[14]。墨西哥人群攜帶PNPLA3基因多態性的相對頻率較高,日本、韓國等國家亦具有較高頻率的PNPLA3風險等位基因[15]。盡管非洲裔美國人代謝綜合征的發病率較高,但與白人和西班牙裔美國人相比,非洲裔美國人NAFLD和NASH并不常見,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因于非洲裔美國人PNPLA3攜帶率較低。然而,脂肪組織分布的差異也起一定作用[16],因非洲裔美國人的體型以外周型肥胖而不是中心型肥胖為主。此外,非洲裔美國人高甘油三酯血癥和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癥等血脂異常相對少見。這些研究結果提示,遺傳和環境因素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決定了不同人群NAFLD的患病率及嚴重程度[13]。
至今人們對于NAFLD自然史的理解主要基于回顧性隊列研究數據,通常無法控制關鍵混雜因素的影響。對于NAFLD短期自然史的了解始于藥物研發的2b/3期臨床試驗,NASH合并不同程度肝纖維化安慰劑對照組的再次肝活檢數據有助于前瞻性研究NASH的自然史。然而,這是嚴格挑選患者的隊列研究,研究結果未必真實代表NASH群體[13]。最近,一項涵蓋了NAFLD完整疾病譜的大規模前瞻性隊列研究顯示,高達46.9%的單純性脂肪肝患者在平均隨訪4.9年內進展為 NASH,30%的患者肝纖維化改善或進展[17]。
總之,隨著肥胖癥和2型糖尿病等代謝相關疾病的持續流行,NAFLD的患病率和發病率不斷增高,并且NAFLD和NASH至今尚無有效的治療藥物,NAFLD是危害人類健康的重要公共衛生問題。然而,許多國家缺乏基于人群的NAFLD研究數據,當前亟需嚴謹的大樣本的基于人群的流行病學調查,并需要進一步加大對NAFLD診治和預防的宣傳力度。提倡對高危人群篩查NAFLD,并進一步評估NAFLD患者的嚴重程度,及時采取針對性的生活方式干預和相關藥物治療,從而控制NAFLD的流行和有效防治NAFLD及其合并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