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邦短篇小說(shuō)的審丑性透視
付蘭梅,喬文東
(長(zhǎng)春理工大學(xué),吉林長(zhǎng)春,130022)
當(dāng)代河南作家劉慶邦自創(chuàng)作以來(lái)便立足于平民立場(chǎng),本著樸素的人道主義精神表現(xiàn)生活的真善美,揭露假惡丑,并通過(guò)對(duì)丑的揭露來(lái)達(dá)到喚醒美的深層目的。
劉慶邦的300余篇短篇小說(shuō)的風(fēng)格可大致分為“柔美”“酷烈”與兩極之外的其他風(fēng)格三類,其中以“柔美”風(fēng)格為主的作品有近百篇,如《梅妞放羊》(1998)、《鞋》(1997)、《小呀小姐姐》(1995)、《玉米地》(2008)、《眉豆花開(kāi)一串白》(2006)等,主要展現(xiàn)了對(duì)故園、人性美的眷戀。以“酷烈”風(fēng)格為主的不下百篇,如《走窯漢》(1985)、《鴿子》(2005)、《福利》(2005)、《兄妹》(1995)、《四季歌》(2007)、《做滿月》(2007)等作品,透視了社會(huì)的冷峻與人性的黑暗。以《大活人》(2003)以及“保姆在北京”的現(xiàn)實(shí)題材系列為代表的其他幾十篇小說(shuō),則“似乎從柔美與酷烈的兩個(gè)極致中走出來(lái),也是從民間的想象中走出來(lái),走進(jìn)現(xiàn)實(shí)的世界里”[1]。
學(xué)界對(duì)劉慶邦短篇小說(shuō)的關(guān)注多集中在審美層次上,對(duì)其審丑意義的研究則稍顯不足。評(píng)論界更多關(guān)注其作品柔美的一面,對(duì)其后者“酷烈”風(fēng)格作品的審丑層面上的關(guān)注則相對(duì)較少。“從主客體關(guān)系方面講,所謂審丑是非和諧的對(duì)象在主體(包括創(chuàng)作主體和接受主體)方面引起的否定性情感判斷和否定性價(jià)值判斷。從主體方面來(lái)講,審丑是指?jìng)€(gè)體對(duì)丑的否定性或作為否定性的丑的判斷、品評(píng)、鑒賞、批判、寬容、改造等各種能力的總和。從客體方面來(lái)講,審丑是指把握丑的否定性本質(zhì)及其形態(tài)在社會(huì)歷史中的演變和作用,其中包括作為否定性的客觀對(duì)象的審丑活動(dòng)本身。”[2]某種意義上,我們從審丑的維度來(lái)解讀劉慶邦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更能彰顯其短篇小說(shuō)的審美價(jià)值。
一、劉慶邦短篇小說(shuō)審丑的含混表達(dá)
“含混”(Ambiguity)一詞起源于拉丁文,本意為“更易”,自英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威廉·燕卜遜(Wil?liam Empson,1906—1984)發(fā)表《含混七型》后廣泛用于文學(xué)批評(píng)中,多表達(dá)為一種模糊性和多重闡釋性。在劉慶邦的短篇小說(shuō)中,作者對(duì)于涉及到人性丑的描寫也多采取多樣化的方式來(lái)表現(xiàn),除了直接表現(xiàn)以揭露存在的丑陋現(xiàn)象之外,更是以一種含混的方式去展現(xiàn)審丑的復(fù)雜與矛盾。
小說(shuō)《兄妹》中哥哥拿著妹妹出賣自己身體的錢去嫖娼,不以為恥,反倒以一句“興啥啥不丑”來(lái)欺人以自欺。同樣《三月春風(fēng)》(1995)中從農(nóng)村走出去的朱科在有了一定地位后禁不住某些不良風(fēng)氣的誘惑找了自己已為人婦的同學(xué)當(dāng)情人,對(duì)諸如此類的丑陋行徑的揭露都展現(xiàn)了劉慶邦在時(shí)代風(fēng)云變幻中不沉湎于對(duì)發(fā)展和美的贊頌,而更加重視對(duì)快速改革發(fā)展進(jìn)程中所存在的種種問(wèn)題進(jìn)行冷峻的思考并把這些丑的現(xiàn)象展現(xiàn)出來(lái)。在某種意義上說(shuō),審丑是作為審美的反題衍生出來(lái)的,無(wú)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在審丑的認(rèn)識(shí)上不一而足,在被認(rèn)可的脫離審美附庸之后的審丑又陷入了另一個(gè)難題,即從審丑維度去認(rèn)識(shí)事物時(shí),我們對(duì)于丑和美的古今認(rèn)識(shí)會(huì)出現(xiàn)一定的混淆,當(dāng)從一個(gè)視點(diǎn)認(rèn)定一個(gè)事物丑的同時(shí),又有人從另一個(gè)視點(diǎn)揭示它的美,這些視點(diǎn)多從心與物、形式與內(nèi)容、主觀與客觀、相對(duì)性與絕對(duì)性等不同角度對(duì)丑進(jìn)行正論與反論的辯證性分析。
如果說(shuō)以上的兩篇小說(shuō)是對(duì)丑的直接揭露,那么在《走窯漢》(1985)、《晚上十點(diǎn):一切正常》(1998)、《屠婦老塘》(1993)、《別讓我再哭了》(2002)、《響器》(2000)、《幸福票》(2001)等小說(shuō)中則充滿了作者對(duì)審丑的含混表達(dá)。在劉慶邦的成名短篇小說(shuō)《走窯漢》中,礦工馬海州的妻子被隊(duì)長(zhǎng)張清奸污以后,作為男性的馬海州,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在煤礦生存場(chǎng)域下男性的話語(yǔ)權(quán)而被人輕視,這與莫言所寫的民間的暴力與野性有一定的相似性,他們都在推崇一種來(lái)自民間的雄強(qiáng)美,而這種美是在游離于現(xiàn)代性之外所建立的。而從現(xiàn)代性視角來(lái)看,它無(wú)疑又是丑的,在美與丑、正義與邪惡之間表現(xiàn)了一種含混性。而后,毫無(wú)疑問(wèn),馬海州遵從了這種無(wú)規(guī)約的規(guī)約,沒(méi)有選擇報(bào)警和走法律途徑,而是自己拿刀捅了隊(duì)長(zhǎng)張清并因此坐牢。在這里又出現(xiàn)一對(duì)矛盾,馬海州選擇以一種不失去在煤礦作為男性的主體地位的方式拿刀捅了張清,此時(shí)他保住了他在煤礦生存場(chǎng)域下的男性話語(yǔ)地位,但卻因此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作為傷害者的張清由于被刺了一刀而成為了被害者,這種被害者身份的確立卻消隱了他的傷害者身份從而逃脫了法律的制裁,而只是被降了職。而此時(shí)作為最大受害者的田小娥卻沒(méi)有任何話語(yǔ)權(quán),甚至都沒(méi)有給予她應(yīng)有的人性關(guān)懷。在這里,作為民間“雄強(qiáng)美”代表的馬海州取得了權(quán)力占位,作為傷害者的張清的丑惡卻被作者有意遮蔽(這種有意被讀者發(fā)現(xiàn)的遮蔽反而更能引起讀者關(guān)注,從而使這個(gè)層面的審丑意義進(jìn)一步得到了強(qiáng)化),而作為男性絕對(duì)權(quán)威下的最大受害者田小娥的失聲同樣是作者有意遮蔽后對(duì)于絕對(duì)男權(quán)的審丑強(qiáng)化,以含混的形式表達(dá)文本的多義性。
在《晚上十點(diǎn):一切正常》中,煤礦的瓦斯爆炸看似是由于檢查員李順和溜號(hào)誤工去小煤窯背煤賺錢導(dǎo)致的,但是煤礦經(jīng)營(yíng)不善,幾個(gè)月發(fā)不出工資,大家都偷偷去小煤窯賺錢補(bǔ)貼家用,而李順和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盡管客觀來(lái)看他的行為和導(dǎo)致的后果是令人憤怒的,但考慮到實(shí)際情況和他的動(dòng)機(jī)與無(wú)奈,這種看似“丑”的行為也應(yīng)當(dāng)被適當(dāng)原諒。在《屠婦老塘》(1993)中,由于丈夫礦難去世,晏子一個(gè)人帶著未成年的兒子艱難生活,衣食無(wú)著,萬(wàn)般無(wú)奈。后來(lái)有幾個(gè)壞男人見(jiàn)她有幾分姿色便拿幾個(gè)錢來(lái)引誘她,迫于生活的艱難晏子便跟人睡了,以此來(lái)賺一些錢補(bǔ)貼家用,撫養(yǎng)孩子,從客觀上盡管晏子選擇通過(guò)做一些皮肉交易來(lái)賺錢的行為是丑陋的,但她在萬(wàn)般無(wú)奈之下為了家庭與孩子選擇犧牲自己去賺錢的方式便制造了一種審丑的含混表達(dá),使我們對(duì)晏子的行為在厭惡之余注入了一絲同情。而《鴿子》中的煤礦老板表面上逢迎領(lǐng)導(dǎo)、苛責(zé)曠工,而背后卻有著難言的苦衷并且不乏對(duì)礦工的關(guān)懷。《別讓我再哭了》(2002)塑造了一個(gè)靠哭來(lái)給礦上解決麻煩的工會(huì)主席孫寶川,但實(shí)際上他的哭是一種負(fù)責(zé)任的哭,是一種為工人解決實(shí)際問(wèn)題的策略,凡是難以解決的礦難,只要孫寶川出馬情真意切地大哭一場(chǎng)再加上動(dòng)之以情、曉之以理的一番說(shuō)辭,準(zhǔn)能解決問(wèn)題,這本來(lái)是講官僚主義及領(lǐng)導(dǎo)的不負(fù)責(zé),而當(dāng)讀完小說(shuō)后我們發(fā)現(xiàn),劉慶邦有意在文本中制造一種隱含意義,客觀上給我們展現(xiàn)了審丑的含混表達(dá)。類似這種審丑含混表達(dá)的小說(shuō)還有《響器》(2000)中高妮對(duì)理想不懈追求的執(zhí)著美與現(xiàn)實(shí)的冷峻殘酷;《福利》中礦老板表面上的冷酷實(shí)際卻減少了礦上的傷亡;《幸福票》(2001)中看似孟銀孩攢幸福票(礦主發(fā)的嫖妓的票券)的丑陋行為的背后,潛藏的是孟銀孩想用幸福票去換錢照顧家里的愿望;《看看誰(shuí)家有福》(1980)中通過(guò)集體的人心異變和個(gè)體中仍有人保持的原有的純真與善良的對(duì)比展現(xiàn)了審丑的含混之處。在《我和秀閨》(1981)、《地層下的笑聲》(1982)、《漢爺》(1991)、《女兒家》(2002)、《走新客》(2002)、《舍不了那閨女》(2004)、《游戲》(2006)、《遠(yuǎn)山》(2008)、《送禮》(2007)等一系列小說(shuō)中都呈現(xiàn)出審丑的含混表達(dá)。
只有透過(guò)劉慶邦短篇小說(shuō)審丑的含混表達(dá),并進(jìn)一步挖掘其審丑的含混表達(dá)背后的主觀意圖,才能對(duì)其作品的審丑意義做出更加全面的把握。
二、劉慶邦短篇小說(shuō)審丑的“心物二元”
法國(guó)哲學(xué)家勒內(nèi)·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認(rèn)為“心靈不是存在,物質(zhì)無(wú)思維,兩個(gè)相對(duì)實(shí)體獨(dú)立存在,互不干涉,彼此平行,構(gòu)成了兩個(gè)世界本原”[3],并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了“心物二元論”的哲學(xué)體系,在認(rèn)識(shí)過(guò)程中強(qiáng)調(diào)人的理性作用,存在過(guò)度唯理論而難以平衡物質(zhì)與心靈的弊端。如果說(shuō)我們把上文論及的含混表達(dá)視為審丑的客觀呈現(xiàn),而“心物二元”則可以看做這種客觀呈現(xiàn)背后的主觀意圖。
在《鴿子》中,黑色的煤礦與湯小明養(yǎng)的一群鴿子便在文本中形成鮮明的對(duì)照,同時(shí)也象征了煤礦雖黑、煤礦工人雖黑,但是煤礦本身和那些礦工的心靈就像鴿子一樣白,一樣純潔,這是作者以鴿子作比來(lái)從形式與內(nèi)容角度辨證地看美與丑。如煤礦老板牛礦本身想要保護(hù)自己的員工卻又不得不應(yīng)付那些手握權(quán)柄的官員們,不得不犧牲湯小明的鴿子去討好王所長(zhǎng),但沒(méi)想到遇到態(tài)度十分強(qiáng)硬的湯小明,不得不跑幾十里山路買了騾子肉又送錢給王所長(zhǎng)才算了事。在這里我們又看到一組對(duì)比,那些大權(quán)在握、頤指氣使的官老爺們看似威風(fēng)八面,實(shí)則乃是作者筆下丑惡的代表,是“心物二元”的正題。小說(shuō)結(jié)尾是點(diǎn)睛之筆,死活不愿賣出鴿子的湯小明以為得罪了礦長(zhǎng),被解雇了準(zhǔn)備要走,而礦長(zhǎng)的一句話“不回去還愣著干什么!袋子里裝的是不是鴿子?快把鴿子放開(kāi),那樣時(shí)間長(zhǎng)了會(huì)把鴿子悶壞的”[4]則更顯余味悠長(zhǎng),作為老板的牛礦在遇到這樣的員工后非但沒(méi)有處罰他,還出乎意料地關(guān)心鴿子,這就使得人物形象有了立體感與層次感,同時(shí)我們也可以看出心靈的美與外現(xiàn)的丑是可以對(duì)立并存的,即我們所說(shuō)的“心物二元”,但這種對(duì)立卻蘊(yùn)含著統(tǒng)一的美,在此基礎(chǔ)上我們對(duì)礦長(zhǎng)先入為主的審丑想象此刻也得到了消解。
《別讓我再哭了》這篇小說(shuō)重點(diǎn)描寫了工會(huì)副主席孫寶川以哭來(lái)處理礦難的過(guò)人之處,比如給礦難死去兒子的老兩口當(dāng)“兒子”照顧他們,比如被鄭師傅死后兒子女兒的困境所觸動(dòng),反倒哭求礦長(zhǎng)幫他們解決工作等。人的內(nèi)心與其所表現(xiàn)出的外在形象作為一種對(duì)立狀態(tài)但卻并不矛盾,作為官僚塞責(zé)態(tài)度代表的丑的形象反而使人產(chǎn)生崇高感。
在《福利》中礦主在礦工下井的井口擺上他給礦工準(zhǔn)備的福利——棺材,表現(xiàn)出一種誰(shuí)出事死了直接就能拉走的冷漠態(tài)度,礦主的冷漠及行為看似是“丑”的,然而從另一個(gè)層面看,煤礦工人這個(gè)職業(yè)本身便具有極大的危險(xiǎn)性,盡管如此危險(xiǎn)還是有一些礦工不遵守規(guī)矩帶違禁物品下井,這給煤礦安全帶來(lái)極大的隱患,而礦主的這種做法客觀上反而時(shí)刻在給工人提著醒——死亡,就在你身邊,客觀上促使工人更加遵守煤礦的規(guī)章制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安全,具有了“美”的意味。在《幸福票》中劉慶邦塑造了一個(gè)勤勞、善良、顧家的主人公孟銀孩,他拼命地工作掙錢,也掙“幸福票”,看似努力掙“幸福票”這一行為是丑陋的、不堪的,但我們沒(méi)想到的是別的礦工拿到“幸福票”都去“消費(fèi)”了,而孟銀孩卻想著拿“幸福票”去找小姐換成現(xiàn)金補(bǔ)貼家里,他的這一主觀行為與客觀表現(xiàn)所形成的反差表現(xiàn)了一個(gè)善良的小伙子盡管表面做了令人不解的事卻無(wú)法掩蓋其內(nèi)心的善良,促成了審丑的含混表達(dá)。《屠婦老塘》中晏子為了照顧沒(méi)了父親的孩子和家庭,不得已出賣了自己的身體,而這種外在的丑卻一點(diǎn)沒(méi)有掩蓋她作為一個(gè)偉大母親的光輝。《晚上十點(diǎn):一切正常》中李順和的溜號(hào)本應(yīng)被斥責(zé),但背后流露出缺失家庭生活的難以為繼的不得已而為之的無(wú)奈,內(nèi)心的想法與客觀的結(jié)果出現(xiàn)了矛盾,但這種主觀上的矛盾客觀上造成了審丑的含混表達(dá)。
此外,在《都走吧》(2006)、《送禮》(2007)、《四季歌》(2007)、《遠(yuǎn)山》(2008)、《捉對(duì)》、《血?jiǎng)拧贰ⅰ段逶铝窕ā返纫幌盗凶髌分校沁@種主觀上的“心物二元”,才使得劉慶邦短篇小說(shuō)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審丑的含混表達(dá)。
三、劉慶邦短篇小說(shuō)審丑背后的美學(xué)意義
我們?cè)谟懻摮蟮臅r(shí)候往往是以美作為對(duì)照,丑與美相伴而生,審丑與審美也相互依存。在劉慶邦的短篇小說(shuō)中往往存在諸多丑的現(xiàn)象,但作家給我們展現(xiàn)丑卻不僅僅將其作為一種外在表現(xiàn)去揭露,去控訴。往深處看,我們往往讀到他深層次的對(duì)美的渴望,對(duì)善良與正義的向往。所以,當(dāng)我們讀劉慶邦的審丑小說(shuō)時(shí),“不是為審丑而審丑,審丑不是目的,而是策略。它為真美提供了可資的對(duì)立參照,并適時(shí)形成一種張力完滿、真實(shí)人性的建立,多元、共生的存在開(kāi)始奠定勃發(fā)的價(jià)值土壤”[5]。在某種意義上,它不僅重新強(qiáng)化了審美的價(jià)值,還豐富了審丑的意義。
我們?cè)谏衔膶?duì)劉慶邦短篇小說(shuō)審丑的含混表達(dá)及其主觀上的“心物二元”進(jìn)行了探討,在某種程度上,無(wú)論是前者還是后者,作家都以審丑為基點(diǎn)傾注了自己的美學(xué)追求,將丑展現(xiàn)出來(lái),讓我們發(fā)現(xiàn)他筆下的丑并非單純的丑,而是向美而生的丑,二者成為彼此的對(duì)照和共生的土壤。正如我們上文談到的《鴿子》《福利》一樣,作家在“鴿子”“福利”中都注入了美好的象征意義,而在文本中展現(xiàn)的卻是老板逢迎領(lǐng)導(dǎo)和礦主的無(wú)情與冷漠,這本是一種丑的存在,但隨即在后文中老板的面狠心善與礦主主觀的冷漠卻在客觀上減少了傷亡,丑行丑態(tài)得以消解,美由此而生。我們?cè)谏衔乃摷暗摹秳e讓我再哭了》《走窯漢》《晚上十點(diǎn):一切正常》《草帽》《幸福票》等都在客觀的審丑的含混表達(dá)和主觀的“心物二元”的交織中綻放出審美之花。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shuō)劉慶邦短篇小說(shuō)的審丑的含混表達(dá)甚至具有獨(dú)立的審美意義,這一點(diǎn)是毋庸置疑的。
總的來(lái)說(shuō),在對(duì)劉慶邦短篇小說(shuō)的審丑進(jìn)行觀照時(shí)我們發(fā)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審丑應(yīng)該是多視角、多層次、多元化的,甚至是含混的。這樣的審丑表達(dá)帶來(lái)的強(qiáng)烈的審美陌生化效果,使小說(shuō)之美更加絢爛多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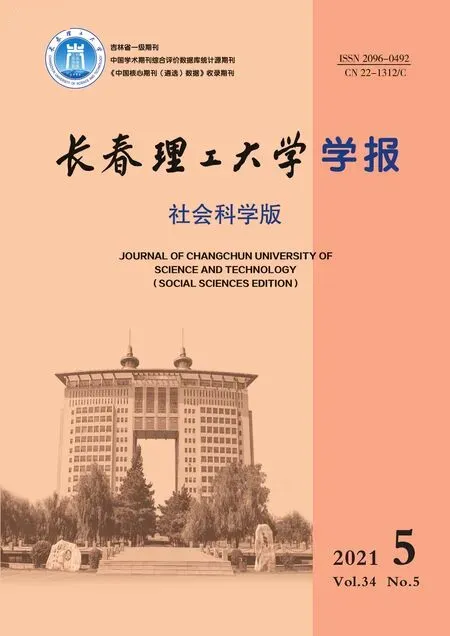 長(zhǎng)春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年5期
長(zhǎng)春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年5期
- 長(zhǎng)春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基于論元結(jié)構(gòu)理論的現(xiàn)代漢語(yǔ)“割”字義項(xiàng)分布情況研究
- 交叉學(xué)科類課程教學(xué)中的心智模型養(yǎng)成研究
- 優(yōu)化營(yíng)商環(huán)境會(huì)促進(jìn)居民消費(fèi)嗎?
——基于國(guó)內(nèi)30個(gè)省市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分析 - 教育財(cái)政支出的農(nóng)村減貧效應(yīng)研究
——基于空間溢出視角的分析 - 鄉(xiāng)村振興與新型城鎮(zhèn)化耦合協(xié)調(diào)度測(cè)算及時(shí)空變遷
- 國(guó)家治理體系視角下提升淮河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帶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質(zhì)量路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