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罪”意識
陳嫣婧

谷崎潤一郎(1886-1965)
隨著國內(nèi)大量谷崎潤一郎作品的譯介,人們似乎漸漸發(fā)現(xiàn)這位日本近現(xiàn)代文壇舉足輕重的人物實在是一名趣味橫生、各種題材與類型都涉獵甚廣的作家。確實,閱讀谷崎的門檻看似并不高,他的幻想、懸疑、驚悚、犯罪小說往往和他的情感倫理小說一樣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其情節(jié)的引人入勝及敘事語言的委婉曉暢十分不同于其他許多讀起來晦澀艱深的現(xiàn)代派小說。谷崎潤一郎的敘事能力是卓越的,他對小說的傳統(tǒng)有著近乎執(zhí)著的追求,對職業(yè)小說家的身份和所需要的“手藝”也十分看重。但若只將這些小說作為“類型”小說的一種去對待,對創(chuàng)作主體意識極其強大的谷崎潤一郎來說,又實在是委屈他了。筆者不愿意拘泥于這些作品各自的素材類型,并希望通過對作者獨特風格和思想的把握,從整體上理解其創(chuàng)作上的主要特征。
谷崎潤一郎的作品有兩個標志是為人所迷戀的,其一是他“惡魔主義”的創(chuàng)作觀,其二則是其在作品里流淌出來的“東洋古典之美”。他的創(chuàng)作以“惡魔主義”為始末,早期的《刺青》《襤褸之光》和晚期的《瘋癲老人日記》《夢之浮橋》是其中之代表作。特別到了晚年,谷崎對一切創(chuàng)作中所蘊藏的“惡魔本性”有了近于完全的了悟,這種對常態(tài)美的全然倒錯,對官能美的全然依賴,使之對“惡之花”的追求推往極致。《瘋癲老人日記》的魅力在于它展現(xiàn)出了一種癡迷狀態(tài),在這個狀態(tài)之下,只有文學的,沒有倫理的;而《夢之浮橋》則通過極為古雅的語言試著將悖德引入日常秩序之中,使人在不經(jīng)意間與“魔鬼”相遇而渾然不知。
雖然文學史家慣于將作家的創(chuàng)作通過階段的劃分來加以梳理,但就文本而論,谷崎潤一郎的風格可謂自始至終都高度統(tǒng)一,即便是《細雪》這樣貌似“溫和”的作品,仍然以兩性間隱約的反常態(tài)關(guān)系作為其底色。而其在構(gòu)思方面最為復雜的《鑰匙》和《卍》,則從人際關(guān)系的角度解構(gòu)了傳統(tǒng)倫理的穩(wěn)定性。兩部作品的敘事基礎(chǔ)都由三人關(guān)系構(gòu)成,并試圖彰顯個人存在與三人關(guān)系的本質(zhì)矛盾性,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巨大張力。谷崎深諳人的孤獨屬性,人與人終究是有隔閡的,但正因為如此,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也可能衍生出無限的可能,這并非建立在倫理基礎(chǔ)上,而是建立在人的惡之本性的基礎(chǔ)上,而其中最顯在的表現(xiàn),便是官能。雖然晚年谷崎刪繁就簡,仍然選用更為簡單也更直接的二人關(guān)系構(gòu)筑了《瘋癲老人日記》的基本結(jié)構(gòu),但《鑰匙》與《卍》的問世,卻起到重要的勾連作用,也可幫助人們更連貫地理解谷崎的小說。當然,這兩部小說本身所呈現(xiàn)出的層巒疊嶂的閱讀感覺,也給人以朦朧玄幽的美感,對人物心理的深切把握以及小說敘事手段的高超讓人讀之倍感痛快。
至于那沉淀著“東洋古典之美”的美學風格,大概所有讀過谷崎小說的讀者都能毫不費勁地體會到其中的“日本味”吧。撇開借著翻譯《源氏物語》產(chǎn)生的靈感從而寫出的《細雪》不談,《春琴抄》和《夢之浮橋》亦可說是個中代表。雖依然頂著“惡魔主義”的頭銜,但作品本身卻又是美的,且是傳統(tǒng)的日本式的寂寥、凄清,充滿了對逝去時間的悼念。日本傳統(tǒng)的美學概念“物哀”,看上去是一種主觀情緒,實際上這情緒卻是帶著對時間的感受力而產(chǎn)生的。如同櫻花迅疾地凋謝飄落,“物哀”的深層心理來自面對時間和特定時間中的個體生命的無力感,當這種無力感與由作品情節(jié)反射出來的叛逆極端雜糅在一起時,便構(gòu)成谷崎作品中全部的美的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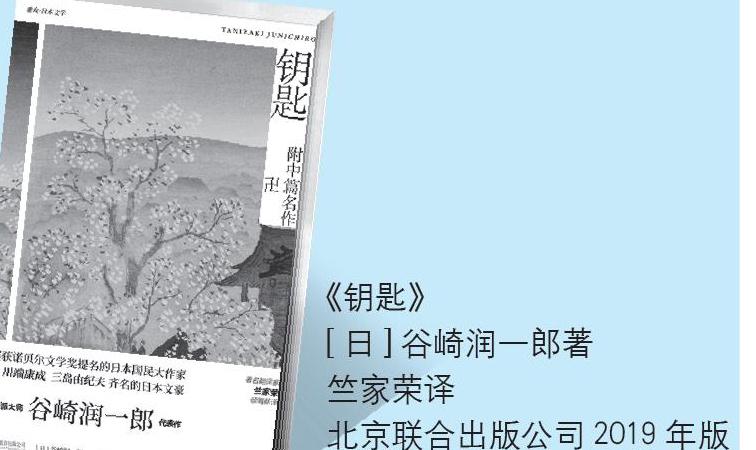
如此,“惡魔主義”和古典唯美之間非但不是彼此矛盾的關(guān)系,反而如同兩條彼此纏繞的藤蔓,本與同根,最終結(jié)出的也是相似的果子。當然,若要追溯這創(chuàng)作觀念與風格的源頭,學界普遍認為一則來自以波德萊爾、王爾德為代表的西方唯美主義文學,二則來自谷崎個人非常欣賞的日本平安朝時期的文學作品。前者為其作品價值的合理性提供了可靠的依據(jù),后者則給予了他源源不斷的素材。谷崎自己在隨筆《戀情與色情》中曾試圖打通這兩個主要來源之間的潛在關(guān)系。他認為平安朝文學中的“拜女情結(jié)”與西方羅曼蒂克小說傳統(tǒng)中的“騎士精神”是可以互通的。從外部視角出發(fā),都是男性擁有女性,但如果換之以內(nèi)部視角,則無一不是男性反過來為他所占有的女性傾倒,乃至自愿跪于其膝下。而文學的核心價值,在他看來本就是悖逆于“從經(jīng)濟組織或社會組織去分析女性地位”的,也就是說,文學所取用的應(yīng)該完全是內(nèi)部的視角,是從個人的感受出發(fā),而不必考慮社會力量對個體可能產(chǎn)生的影響。這既符合波德萊爾們對主體審美價值的最高認同,同時亦是對“私小說”傳統(tǒng)敘述方式的繼承。吉田精一在分析“日本耽美文學”時指出:“谷崎潤一郎的作風是以空想和幻想作為生命,意味著不涉及現(xiàn)實的正道。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羅曼蒂克。這意味著他通過不應(yīng)有的世界、惡魔般的藝術(shù),發(fā)揮了使讀者陶醉的魔力。”如從作品的題材角度看,吉田“不涉及現(xiàn)實正道”的評論是得當?shù)模驗榫汀斗缸镄≌f集》一書中所涉,基本上就都是對所謂的“人間罪惡”不加掩飾的談?wù)摚瑲⑵蕖⒃p騙等惡行比比皆是,特別是其中的代表作《有前科的人》和《被詛咒的劇本》,全然可謂是對道德綱常赤裸裸的挑戰(zhàn)。但從題材到文本,這里頭必然的藝術(shù)轉(zhuǎn)化的過程,以及作者在其中通過具體的敘事行為所投射的復雜意識,是題材分析本身所無法涵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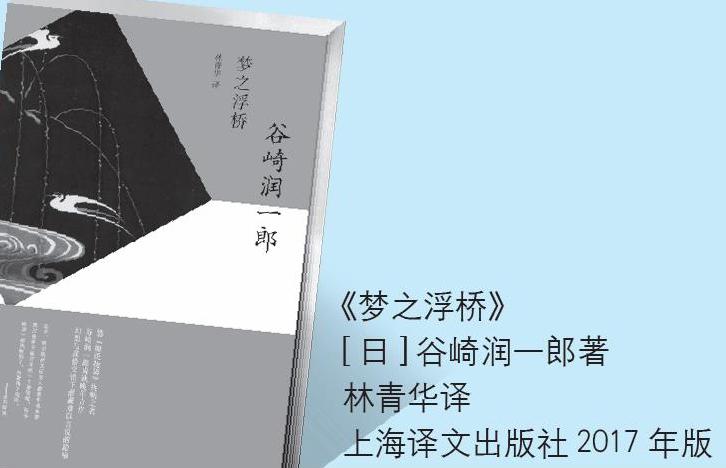
雖然吉田對谷崎作品的分析過多地倚重意識形態(tài),忽略了藝術(shù)創(chuàng)造自身的形式意義及生命力,但他指出的“以空想和幻想作為生命”這一點卻是非常精到的。唯美主義的藝術(shù)價值觀一旦對接日本“私小說”的敘述傳統(tǒng),“空想”與“幻想”幾乎可以說是其必然的結(jié)果。不過在此必須先強調(diào)一點:“私小說”絕不等同于“私生活”,文本中的“私生活”也絕不等同于現(xiàn)實中的“私生活”。雖然《犯罪小說集》中的主人公們大多是藝術(shù)家或知識分子,而在更著名些的作品中,谷崎本人的影子亦似乎是無處不在的:比如《食蓼之蟲》和《卍》都以“小田原讓妻事件”作為素材底本,而《癡人之愛》和《春琴抄》又明顯踐行了作者的“拜女觀念”。在這方面,葉渭渠所著的《谷崎潤一郎傳》可謂開了一個不太好的頭,在書中他以谷崎大量的個人生活為例,或找出他在隨筆漫談中的一些文句,直接對接其作品,并據(jù)此對文本做出價值批判,這多少是模糊了“私小說”與“私生活”、文本與現(xiàn)實直接的界限,也就沒能做到通過文本真正深入到作家的意識中去。事實上正因為谷崎的小說大多采用內(nèi)部視角,即使沒有直接使用第一人稱敘述,視角本身所帶來的封閉性也足以使產(chǎn)生自文本中的藝術(shù)時空體帶有強烈的“幻想”性質(zhì)。當然,在不少讀者看來,谷崎的敘事相當“以假亂真”,但這“逼真”的效果乃是通過扎實精巧的敘事手段達到的,它是一種效果,是以“虛構(gòu)”作為前提的。而內(nèi)部視角恰恰是強化這種效果最好的敘事手段,它使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在最大程度上能夠自給自足,而不需要借助更多的現(xiàn)實條件。這也是唯美主義文學在創(chuàng)作技法方面給予作家的巨大挑戰(zhàn)。所以,“幻想”并不負責揭示現(xiàn)實的“假”,相反,“幻想”的目的在于表達藝術(shù)上的“真”。

谷崎潤一郎正是借此使其創(chuàng)作達到了藝術(shù)上的自足,并且避免了與外部世界進行直接的碰撞。但是,藝術(shù)上的自足是否就能夠幫助作家避免在文本中表達自身的價值理念呢?這幾乎就是等于在問,作者是否可以只完成一個藝術(shù)作品而不自我表達。這也是唯美主義文學經(jīng)常需要面對的一個價值困境,比如吉田精一就斷言谷崎的“空想和幻想比較缺乏變化,專同肉體和感覺緊密結(jié)合,卻不飛翔到觀念上”。這里的“不飛翔到觀念上”,恐怕指的就是谷崎的文本容易給人留下“缺乏價值判斷”的印象。然而確實如此嗎?事實上谷崎經(jīng)常在作品里做著“自剖式”的敘述,借主人公之口訴說自己的罪惡。比如在《被詛咒的劇本》中直言“佐佐木是一個堪比禽獸的藝術(shù)家”,在《有前科的人》中則直接點出“我”是“因可憎的道德敗壞而被送往監(jiān)獄”的。與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力圖完整地展現(xiàn)個體的復雜人性不同,唯美主義文學對“惡”之觀念的揭示恐怕更為執(zhí)著,所以絕不是沒有“觀念”,而是與吉田自己所提倡的“現(xiàn)實的正道”相違背,才被認為只是沉溺于肉體,仿佛惡只能指向肉體,而善便是超越肉體。將肉體與精神、善與惡對立化,這是“醒世喻人”類小說一貫的處理方式,而這類所謂的正向價值引導,恰恰是谷崎有意識悖逆的。所以作者并非沒有意識或刻意隱藏意識,而是通過悖逆和反駁的手段來反向強化其意識。且這意識的核心也并非是美化或消磨罪惡,而是闡明罪惡的無可規(guī)避。
普遍的欲導向普遍的罪,而其最突出的表現(xiàn)則是對痛苦的敏感及作為必然結(jié)果的對痛苦的沉溺。谷崎大部分的小說雖都可從題材上被歸入“倫理小說”,實際上卻很少進入到常態(tài)的“倫常體系”中去。無論從敘事學還是從唯美主義學思想的角度來分析,這類創(chuàng)作都可說是反倫常的。倫理的基底乃是“他者”,基本結(jié)構(gòu)是“自我”與“他者”的彼此關(guān)系。而谷崎的作品卻幾乎不涉及“他者”,他所設(shè)置的視角幾乎全部只關(guān)乎“自我”,所以他的小說結(jié)構(gòu)從根本上講也是封閉的。“我”即是自身存在的前提,也是生產(chǎn)罪孽與痛苦的工廠,更是使痛苦合理化,把罪惡必然化,并最終與之共存的唯一對象。也正是基于此,谷崎對罪惡的指證幾乎不需要通過外部的社會力量,甚至也不需要通過個體與外部進行事實上的接觸來達到,個體只需有意識地認識自己,挖掘自身,沉潛到內(nèi)部的心靈環(huán)境中去,使罪惡顯明即成為必然。
谷崎潤一郎對人性罪惡的認識及處理方式上,他將自己親手創(chuàng)造的“文字”作為“救主”,將被救的希望寄托于文字,托付于自己的寫作行為。他認為,寫作即是懺悔,創(chuàng)作即是自贖,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文學同樣具備自我凈化的功能。于是創(chuàng)作者利用他建筑的這個虛構(gòu)的藝術(shù)時空體親手埋下懺悔的種子,借以反叛僅僅立足于外部批判的文學傳統(tǒng)。當然我們從文學史的發(fā)展脈絡(luò)來看,進入二十世紀以后,現(xiàn)代小說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在自覺地避免過于直接地介入社會事實,于是作者與文本之間的關(guān)系也變得更為曖昧,使讀者捉摸不透。對作家生活逸事或個人言論的挖掘沖動,可能即是來自這種不安全感。谷崎潤一郎的個人生活,一直都是普通讀者津津樂道的話題,但如若真正用心閱讀了他的作品,則仍能從中發(fā)現(xiàn)作家意識在投射于文本之時的那種幽微與玄妙。故此,谷崎潤一郎確可謂一名真正的現(xiàn)代作家,他的作品,也因其作者強烈的現(xiàn)代意識而成為日本現(xiàn)代文學的標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