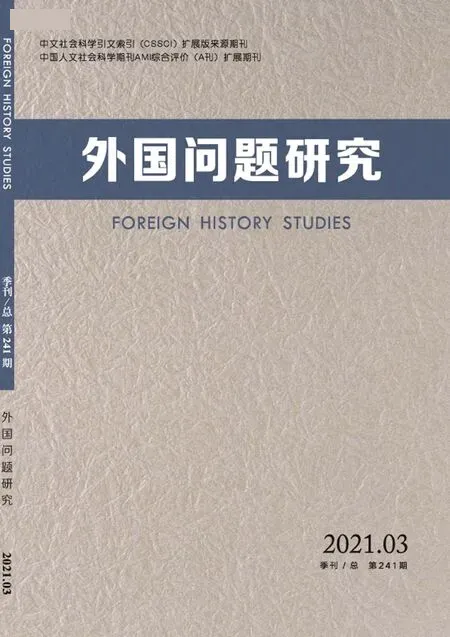后民權時代美國種族主義思潮嬗變:路徑、邏輯與成因
牛忠光
(江漢大學 外國語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56)
20世紀中葉隨著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蓬勃發展,種族主義思潮作為負面社會意識形態,在學理和法理上受到深刻的批判與糾正。(1)皮埃爾-安德烈·塔吉耶夫:《種族主義源流》,高凌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然而,進入后民權時代(2)“后民權”是美國學界針對20世紀60年代末民權運動走向低潮之后的流行話語,更多地用以指轟轟烈烈的民權運動結束至今的較長一段歷史時期的界分。綜合來看,這一術語在國內外學界均強調其時間性和中性色彩。參見Howard Winant, “Race and Racism: Towards a Global Futur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29, No.5, 2006, pp.986-1003;王晴鋒:《后民權時代的美國族群關系:經驗與反思》,《世界民族》2015年第1期。至今,美國社會中基于種族的偏見、歧視、暴力與迫害依然以各種隱性或顯性形式存在,特別是特朗普主政期間乃至其后針對少數族裔的排外思潮、種族仇恨犯罪呈現出不斷潮涌的狀態。(3)王偉:《21世紀美國白人極端主義現象研究》,《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
近年來美國種族主義的潮涌,放在整個后民權時代的歷史時空視野之下,其內涵呈現出從生物性到文化性的變遷,(4)魏南枝:《美國的文化認同沖突和社會不平等性——種族矛盾的文化與社會源流》,《學術月刊》2021年第2期。在社會行為上則體現出公然對抗,隱形對抗、再到顯著對抗的表征,而在社會思潮層面則表現為“白人對抗”(white backlash)、“白人性”(whiteness)、“無視膚色”(colorblindness)和“后種族主義”(post-racism)等種族主義意識形態。這些種族主義思潮看似相異,卻具有內在流變邏輯,而對這一流變內在邏輯及歷史和現實因由進行闡釋,有助于我們更系統性地認清當前美國社會撕裂的種族主義根由。
一、美國種族主義思潮形態與流變路徑
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通常被認為是美國種族政治的分水嶺。(5)Ashley Doane, “What is Racism? Racial Discourse and Racial Politics,” Critical Sociology, Vol.32, No.2-3, 2006, pp.255-274.民權運動之前,美國社會中公然存在種族隔離的吉姆·克勞種族主義或所謂“老式種族主義”,(6)陳跡:《當代美國政治的“種族化”現象探析》,《美國研究》2019年第4期。已經在民權運動之后被大多數民眾所唾棄,而轉變為新的種族主義形式,有學者稱之為“現代種族主義”“象征性種族主義”“結構種族主義”“制度性種族主義”“無視膚色種族主義”“自由放任種族主義”等等。但是,相關研究亦存在爭論,如有學者指出將民權運動之后的美國種族主義稱之為“結構性種族主義”無助于區分新舊種族主義及其所在時代的獨特性,因為無論是17世紀至18世紀的奴隸制,還是19世紀初到20世紀中葉的吉姆·克勞種族主義都是結構性種族主義的一種形式。(7)Lawrence D. Bobo, “Racism in Trump’s America: Reflections on Culture, Sociology, and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68, No.S1, 2017, pp.85-104.暫不論學界對民權運動之后美國種族主義形式變化的爭論,管中窺豹,亦能看出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種族主義所呈現出的圖景,要比過去三個多世紀更為多樣、更為復雜。事實上,這一復雜性使得人們很難像用“吉姆·克勞種族主義”來界定種族隔離時期一樣,確定某個術語來界定后民權時代的美國種族主義。然而,從社會思潮層面縱向剖析,我們仍發現后民權時代的美國種族主義思潮歷經“白人對抗”“白人性”“無視膚色”和“后種族主義”等形態流變。
“白人對抗”及其種族主義行徑一般指白人對黑人鄰里、黑人社會地位上升、種族/族群間更多平等權或相關優惠少數族裔法律和政策的反感情緒與反抗行為。(8)Roger Hewitt, White Backlash and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白人對抗”最早可追溯到美國內戰結束之后的重建時期。美國政府在戰敗南方地區所實施的重建政策,受到南方白人的反對,他們認為這些政策在促進種族平等方面過于激進、過于超前,盡管事實上當時種族平等微乎其微。(9)Nicole Brown Chau, “What Is White Backlash and How Is It Still Affecting America Today?” June 4, 2020, https://www.cbsnews.com/news/white-backlash-civil-rights-movement/, 2021年7月31日。這一時期的“白人對抗”從本質上與極端白人至上主義及其行徑一致,具有顯著暴力特征,具體表現為暴力殘害或謀殺黑人以及白人進步主義者。然而,“白人對抗”作為一股思潮為美國公眾所熟知則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期間,突出的標志性事件便是白人種族主義代表人物喬治·華萊士宣揚“現在隔離,明天隔離,永遠隔離”。馬丁·路德·金也在晚年敏銳地意識到并強烈關注白人對抗,他認為這一股反彈力量,會使得種族融合和平等的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弱化到僅具象征性意義。1964年11月,馬丁·路德·金在《星期六晚報》上寫道:“有一部分白人感受到黑人要求變革的壓力,將其誤解為黑人對特權的要求,而不是對生存的絕望追求。隨之而來的白人對抗讓本已過于膽小的政府官員采取進一步更有力的措施。”(10)Vann R. Newkirki, “Five Decades of White Backlash”, The Atlantic, Jan. 15,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8/01/trump-massive-resistance-history-mlk/550544/,2021年3月20日。此時他筆下的“白人對抗”依然帶有吉姆·克勞時期強烈的白人至上主義恐怖和暴力特性,以致他本人和肯尼迪總統都受此影響而被殺害。民權運動走向式微的20世紀70年代,“白人對抗”盛行于白人工人階層,并表現為對實施民權政策的激烈公開對抗。到了80年代里根總統當政期間,白人群體對民權政策的激烈反抗得以緩和,但是無論在美國法律政策層面還是從白人個體層面,都普遍將給予少數族裔的優惠政策視為“勤勞”白人們的“施舍”。90年代多元文化主義興起,許多白人認為他們是多元文化主義的受害者,并對當時出現的“身份政治”即少數族裔憑借族群身份去追逐政治利益進行猛烈抨擊,白人精英們更擔憂多元文化主義損害美國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的根基。(11)塞繆爾·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進入21世紀,“白人對抗”在奧巴馬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前后出現,其標志是美國茶黨運動以及質疑奧巴馬身份的“出生地主義”(Birtherism),(12)Ben Smith and Byron Tau, “Birtherism: Where It All Began,” Politico, April 24, 2011,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1/04/birtherism-where-it-all-began-053563,2021年3月20日。在這一波思潮中許多白人將種族主義視為輸贏二元對立的零和游戲,即認為對黑人偏見的減少等同于對白人偏見的增加。(13)Matthew W. Hughey, “White Backlash in the ‘Post-Racial’ United Stat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37, No.5, 2014, pp.721-730, DOI: 10.1080/01419870.2014.886710.這種“零和游戲”白人對抗思維一直延續到特朗普競選總統及其當政時期。需特別指出的是,盡管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白人對抗”的暴力色彩相較民權運動之前已減弱,但并未消失,而突出表現在白人警察對于少數族裔特別是黑人的種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和暴力執法。
“白人性”思潮與民權運動之后的“白人對抗”相伴而生,通常指向基于膚色的白人種族身份和認同。美國建國伊始乃至到20世紀前半葉,白人性并不為白人群體所普遍關注。美國主流歐洲移民中的不同祖源群體間的種族偏見,最開始并非基于膚色,而更多是階級對立或源自其祖源國的世代偏見,比如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愛爾蘭移民、意大利移民、猶太裔移民都曾被排斥在白人群體之外,備受種族主義歧視。與此同時,這些歐洲白人新移民以及歐洲以外的淺膚色人涌入美國之后,美國社會對何為白人產生疑問,即究竟是以祖源地為標準,還是以膚色或其他標準進行界分。相關議題曾呈現于《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14)W.L.托馬斯、F.茲納涅茨基:《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張友云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街角社會》(15)威廉.富特.懷特:《街角社會》,黃育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以及《都市村民:意大利裔美國人生活中的群體與階級》(16)Herbert J. Gans,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2(1962).等社會學經典著作中。但是,隨著歐洲移民在美國社會的完全融入,歐洲移民祖源國文化的“異域”色彩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幾乎不可見,換言之,美國人已普遍想當然地認為來自歐洲祖源國的文化已成為美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此時,以文化為核心的白人族群認同好似也不存在,已經完全融入了所謂的“美國白人文化”的日常思維和學術界的概念范疇之中。即使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白人對黑人民權運動的激烈甚至暴力對抗時期,白人也僅僅作為一個與黑人相對的種族類別而非是身份認同突顯出來。在相關研究中,白人僅僅被作為研究非白人的對照組而存在,但卻鮮有人意識到白人的種族身份認同或所謂的白人性問題。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白人性逐漸為美國學界和媒體所關注,學界對于白人族群認同的研究逐漸轉變到白人的種族認同。(17)Monica McDermott and Frank L. Samson, “White Racial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31, No.1, 2005, pp.245-261.美國政治學者阿什莉·賈迪娜的研究表明,美國白人中擁有很強白人性意識的并非局限于中下層工人階級,而是一個很大的群體,并且女性表現得比男性更顯著。(18)Ashley Jardina,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美國白人社會精英中的保守主義者一直不斷地宣揚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白人的種族特性,(19)孔元:《身份政治、文明沖突與美國的分裂》,《中國圖書評論》2017年第12期。比如塞繆爾·亨廷頓堅持認為美國政治文化是在白人文化和種族的支配中發展而來的,將美國國家特性等同于美國白人特性。(20)塞繆爾·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第47頁。事實上,美國白人種族人口比重的變化也助推了“白人性”思潮的興起,美國白人開始像對待黑人一樣,將自身視為一個種族群體而存在,并追尋自身的認同構建和群體情感。“白人性”原本是“無標記的”(unmarked),即默認存在的種族身份,無須受人關注,許多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通常根本無須在意自己的“種族身份”,而不像其他非白人特別是非裔美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常常與其種族身份關聯起來。但是,人口預測普遍指出,2050年非西班牙裔白人的人口比例會從1970年的83.5%下降到52.5%左右,而且在1990年美國10個大城市中已有6個是少數族裔的人口占多數,進入21世紀更多的州出現所謂“少數族裔變成人口多數派”(minority majority)。(21)John Iceland, “Beyond Black and White: Metropolita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Multi-ethnic Americ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33, No.2, 2004, pp.248-271.這一人口族裔結構的變化給美國白人的直觀感受是在日常生活中其他膚色的少數族裔隨處可見,進而引起白人的種族身份“焦慮”。這一“焦慮”的現實考慮是白人特權的喪失,其反映到政治層面便體現在奧巴馬競選總統期間及其任內白人至上主義者和保守派對奧巴馬種族身份的質疑和種族主義攻擊。2016年保守主義者特朗普在白人中下層的支持下當選總統,被普遍認為是美國白人種族身份政治的崛起,(22)Richard D. Kahlenberg, “The Rise of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Washington Monthly, July/August, 2019, https://washingtonmonthly.com/magazine/july-august-2019/the-rise-of-white-identity-politics/. 2021年3月25日。也是美國白人性思潮的凝聚。
“無視膚色”是美國社會中對種族膚色偏見的有意或潛意識否認。(23)該詞最早與種族問題聯結是在1898年美國高等法院對“普萊西訴弗格森案”的判決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哈蘭(John Marshall Harlan)聲稱美國憲法“沒有膚色偏見”。這種對美國社會中明顯存在的“膚色分類”和“膚色偏見”的故意視而不見,構成了美國“無視膚色”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早期雛形。參見Howard Winant, “The Dark Matter: Race and Ra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Critical Sociology, Vol.41, No.2, 2014, pp.313-324. 該案原文參見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Cornell Law School, Plessy v. Ferguson, May 18,1896, 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163/537.該思潮的盛行始于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任內(1981—1989年),其標志是里根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話語層面強調所謂“種族中立”,淡化或回避種族議題。在社會層面,美國白人常認為其個人及群體的成功來自個體能力和成就,而回避不談白人在美國社會中所具有的結構性優勢。美國白人對于美國社會中“白人特權”的否認,構成了“無視膚色”種族主義思潮的根基。這一種族意識形態主張所有種族無論是在權利還是在歷史經歷層面,從根本上都是平等的,美國所出臺的基于種族的政策和項目只能進一步加深種族裂痕。(24)M. L. Andersen, “Reconstructing for Whom? Race, Class, Gender, and the Ideology of Invisibility,” Social Forum, Vol.16, No.2, 2001, pp.181-201.這進而與以往美國白人對美國種族不平等的公然否認截然不同,變得更加隱蔽,而且所波及的人群更廣、影響時間更長。到了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時期(1992—2000年),為應對美國社會中的種族矛盾,克林頓召開全國種族對話,極力宣揚美國多元文化,強化“無視膚色”理想。這一時期的“無視膚色”思潮宣揚不超越種族界線就是在鼓吹種族主義,認為基于種族的政策強化了種族意識,從而導致美國社會倒退,聲稱那些喊種族歧視的少數族裔是在玩“種族牌”,白人是基于自由主義信念和內疚感才支持他們的。(25)伊布拉姆·X.肯迪:《天生的標簽:美國種族主義思想的歷史》,朱葉娜和高鑫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573—574頁。這類意識形態不僅僅是對基于膚色的人類不平等的視而不見,而且再次把白人放到了道德的制高點,而將那些與種族不平等抗爭的人污蔑為玩弄種族伎倆的“宵小之輩”。進入21世紀,此類“無視膚色”論調依然在美國社會彌漫,如知名學者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將非裔美國人蔑稱為“種族結黨營私主義者”,批評非裔美國人及其他有色群體爭取民權的種族運動使得種族概念及其相伴而生的“黑白”二分法持續存在,污蔑非裔美國人是延續種族主義的真正罪魁禍首。(26)Paul Gilroy, Against Race: Imagining Political Culture Beyond The Color Li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2; Sumi Cho, “Post-Racism,” Iowa Law Review, Vol.94, 2009, pp.1589-1645.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后,美國“無視膚色”論者利用民眾的原生情緒,渲染一個團結、愛國的美國,其國防已經超越了種族界限,而反戰的少數族裔及其對戰爭的批評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27)伊布拉姆·X.肯迪:《天生的標簽:美國種族主義思想的歷史》,第585頁。而在2005年8月末卡特里娜颶風災難事件中,由于小布什聯邦政府的無為,自然災難因人為而加深,最終1 000多人喪生和上百萬人受害。然而,美國主流媒體如美聯社卻在散布諸如災區黑人向救援者開槍射擊等等聳人聽聞的種族主義故事,并辯稱黑人對該災難事件中政府實施種族歧視的指控是偽造和夸大的,是在“濫用種族牌”,美國是“無視膚色”的。當時民調顯示,只有12%的美國白人認為“聯邦政府在幫助新奧爾良受害者時的拖延是因為受害者是黑人”,大多數白人不認為種族在這一災害中扮演角色,反而相信一些存在致命種族偏見的媒體報道,即將當地黑人的受災受難歸咎于黑人的病態。(28)有關該事件參見Dara Strolovitch, Dorian Warren and Paul Frymer, “Katrina’s Political Roots and Divisions: Race, Class, and Federal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Iterms, June 11, 2006, https://items.ssrc.org/understanding-katrina/katrinas-political-roots-and-divisions-race-class-and-federalism-in-american-politics/; Michelle Malkin, “Hurricane Katrina and the Race Card: Five Years Later,” August 27, 2010,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10/08/27/_hurricane_katrina_and_the_race_card_five_years_later_106908.html, 2020年12月28日。當時小布什政府和美國媒體的反應是純粹的階級種族歧視,正如哈佛法學院教授拉妮·吉尼爾(Lani Guinier)所言:“貧窮的黑人是被丟棄的人,我們將他們病態化以證明我們對他們的漠視是合理的。”(29)伊布拉姆·X.肯迪:《天生的標簽:美國種族主義思想的歷史》,第595頁。這也是“無視膚色”帶來的最直接社會后果。在種族主義現實面前,無視膚色論黯然失色,顯得極其荒謬。
此后隨著奧巴馬競選總統且成功當選,使得“后種族主義”(30)1971年10月5日左右,《紐約時報》發表了《為“后種族”南方而建立的契約》的文章,其中提到美國正在變成一個種族不再具有價值的國家,“后種族”一詞首次進入了美國的流行話語中。參見Kelli Marie Alsop, “The Post-Racial Question in 2016: A New Point of View,” May 9, 2016, https://www.theodysseyonline.com/post-racial-question-2016,2021年2月20日。話語的流行程度超過“無視膚色”,并演化為美國社會一股種族主義思潮。從流變過程來看,這一思潮由兩條脈絡匯聚而成:第一條是來自奧巴馬及其競選團隊本身,第二條是美國種族主義者對“后種族”或“后種族主義”話語的鼓吹。在第一條脈絡之中,“后種族”話語在奧巴馬決定參與政治競選伊始便已出現,且逐漸成為其競選中明確的“后種族”策略。奧巴馬早在2004年競選美國參議院議員時,便將其自身定義為一個“團結者”,關注所有膚色的美國人,在各種社會議題上追求種族中立。(31)Barack Obama, “Keynote Address at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July 27, 2004,” http://www.barackobama.com/2004/07/27/keynote_address_at_the_2004_de_php.2020年3月20日。他在實際行動上也踐行后種族策略,刻意避免民權議程,比如缺席當時備受矚目的民權活動。(32)Sumi Cho, “Post-Racism,” pp.1589-1645.2008年總統競選期間,奧巴馬發表《更完美的聯邦》的競選講演,依舊延續其后種族策略,拒絕將美國白人對福利制度、平權運動的反對視為種族主義,即認為白人的這些怨恨不是種族歧視,同時他又鼓勵非裔美國人做好自己、成為最好的父母,承擔個人責任。(33)Barack Obama, “Transcript: Barack Obama’s Speech on Race,” NPR, March 18, 2008,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88478467, 2020年3月20日。奧巴馬在其政治崛起過程中將其打造成種族和解與美國例外論的化身。第二條脈絡頗具諷刺意味,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開始并未普遍反對和壓制奧巴馬的崛起,早在2004年便為奧巴馬的學術成就和政治成功而歡呼。(34)伊布拉姆·X.肯迪:《天生的標簽:美國種族主義思想的歷史》,第592頁。當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無法通過野蠻地貶低來抑制黑人以維護其白人種族特權時,奧巴馬的出現使得他們有機會將其作為種族歧視終結的引信,以企終結美國社會中有關種族歧視的話語。當時美國司法領域、學界以及主流媒體,無論是保守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均涌現對“后種族”的鼓吹話語,聲稱奧巴馬當選總統象征著美國成了一個真正的“后種族”社會,一些主流媒體更為“后種族”話語泛濫的推波助瀾,如《經濟學人》稱這是“后種族時代的勝利”,并認為奧巴馬是美國超越種族分歧的希望;(35)Daniel Schorr, “A New, ‘Post-Racial’ Political Era in America,” January 28, 2008,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8489466, 2020年3月20日。《波士頓全球報》宣布“關于種族的舊常識”隨著奧巴馬的當選而消亡;(36)Editorial, “Obama and Affirmative Action,” Boston Globe, Nov. 15, 2008, at A 10.《費城每日新聞報》開設“后種族”專欄,聲稱一個剛剛選出第一位黑人總統的國家再被指責為系統性種族主義是不公平的。(37)Stu Bykofsky, “My First Post-Racial Column: America Is on the Ascent,” Phila. Daily News, Nov. 8, 2008, Local Section, at 7; Joan Vennochi, Op-Ed., “Closing the Door on Victimhood,” Boston Globe, Nov. 6, 2008, at A 23.美國知名右翼民粹主義媒體其時不斷鼓吹美國已處于一個21世紀“后種族”社會。(38)Kelli Marie Alsop, “The Post-Racial Question in 2016: A New Point of View,” Michael C. Dawson and Lawrence D. Bobo, “One Year Later and the Myth of a Post-Racial Society,” Du Bois Review: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Race, Vol.6, No.2, 2009, pp.247-249.然而,美國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因白人警察種族定性的暴力執法所引發的種族暴力事件頻發,特朗普上臺后美國種族仇恨犯罪更加凸顯,并引發聲勢浩大的“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反種族主義運動,從而顯示出“后種族”思潮的荒謬及其種族主義特質。事實上奧巴馬本人在其總統卸任演講中也已坦誠“后種族主義”話語中的種族融合在當前美國只是個還未實現的美好愿望。(39)Obama, “President Obama Farewell Address: Full Text”, CNN, January 11, 2017, https://edition.cnn.com/2017/01/10/politics/president-obama-farewell-speech/index.html, 2021年7月31日。
二、美國種族主義思潮諸形態的內在邏輯
后民權時代上述美國種族主義思潮諸形態雖在不同時期出現,但其歷史分期并非涇渭分明,也并非毫無關聯的獨立存在,而是具有明顯的內在流變邏輯。
首先,吉姆·克勞法被禁止,白人維護種族隔離而實施的恐怖暴力式“白人對抗”失去了其存在的法律保障。后民權時代“白人對抗”思潮開始針對美國少數族裔所獲得的民權政策而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形態。這一時期大批亞非拉新移民涌入美國,改變了美國社會中族裔人口的格局,深膚色族裔人數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挑動了白人群體潛意識中“無標記”的膚色身份意識。一方面,享有種族特權的白人認為“種族身份”成了少數族裔爭取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一些白人認為白人也是一個具有身份認同的種族群體,應圍繞其膚色形成團結的種族團體,從不同社會層面反制諸如“黑人權力”等各種少數族裔權力的出現。換言之,正是在“白人對抗”思潮及其社會行動過程中,“白人性”意識被建構和不斷凝聚,并顯著體現在21世紀美國白人種族身份政治之中。因而,無論是“白人對抗”本身還是“白人性”的涌起,其內在邏輯都是美國一些白人精英和中下層人士白人面對少數族裔對民權的持續訴求以及外來非白人移民的涌入而感覺自身利益受到威脅或損害,認為少數種族和族裔的成功與權利獲取是以蓄意犧牲白人為代價的。(40)Jamie G. Longazel, “Moral Panic as Racial Degradation Ceremony,” Punishment & Socie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nology, Vol.15, No.1, 2013, pp.96-119.
在白人對抗少數族裔應得民權過程中,公然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暴力均已為社會公眾所唾棄,倡導種族不平等的激進分子相應采取更“聰明”的策略,“無視膚色”思潮便應運而生,被白人利用來維護其種族優越性和特權。他們宣揚美國黑人等少數族裔已獲得“真正的”平等權利,美國已“超越”種族問題,白人與黑人之間的二元種族對立已不存在,民權運動之后美國依然存在的種族不平等已與他們無關。一些美國知識分子也否認種族問題在美國社會中的重要性,認為少數族裔生活是由階級而非種族決定的,(41)William J. Wilson,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Blacks and Changing American Institutions, Thir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reface,” p.x.或主張種族膚色特征不應再被作為群體分類或政策制定的參照。(42)Eduardo Bonilla-Silva & Victor Ray, “When Whites Love a Black Leader: Race Matters in Obametica,”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Vol.13, 2009, pp.176-183.“無視膚色”論調的核心是反對針對少數族裔的種族救助措施,特別是教育領域的肯定性行動招生入學政策,其潛在邏輯是以種族中立和平等之名將種族不平等歸咎于少數族裔的“文化缺陷”,維護白人特權,這其實與民權運動之前的種族主義密切相連,最終都是為后民權時代變相的種族隔離主義服務。“無視膚色”思潮影響深遠,居于20世紀最后二十年美國種族意識形態爭鋒的震中。
“后種族主義”思潮與“無視膚色”一脈相承,都主張種族中立或弱化種族在美國社會中的重要性,但是相比后者,前者的新奇和獨特之處則是將美國種族敘事從強調“中立”轉向了強調“進步”。美國保守主義者一直試圖利用“無視膚色”原則來廢止民權運動以及基于種族的彌補措施,但是這一折中框架并未能吸引年輕人以及溫和派白人(43)Sumi Cho, “Post-Racism,” pp.1589-1645.。奧巴馬及其“后種族”競選策略,相比“無視膚色”,贏得了黑人和白人的注意,使得白人歡呼“種族進步”帶給美國的“根本改變”,其背后邏輯便是認為美國取得了如此巨大的種族進步,種族不應再作為美國政府決策和社會行動的核心組織原則。
無論是“白人對抗”,還是“白人性”“無視膚色”“后種族主義”,作為后民權時代的種族意識形態,整體上在物質資源、社會文化和政治形式等層面服務于美國白人社會中彌漫的“規避種族議題”,從而試圖抵制和取消國家層面對種族不公問題的政策干預,特別是民權運動爭取而來的成果,同時試圖割裂后民權時代的白人社會規范與民權運動之前白人種族主義歷史聯系,以達到維護和延續白人種族特權的目的。(44)Sumi Cho, “Post-Racism,” p.1641.從內涵和外延來看,“白人性”“無視膚色”和“后種族主義”也是后民權式“白人對抗”的具體表現。“白人對抗”思潮以不同形式貫穿民權運動之后的時空之中,并且在不同時期隨著政治事件(特別是總統選舉)以及種族暴力事件而走向高潮。
三、美國種族主義思潮延續的歷史與現實因素
不可否認,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促使美國在解決自身種族主義問題上取得一定進步,至少從法律形式上明確了種族隔離、種族歧視、種族暴力不合法,并且采取諸如消除選舉權障礙、實施肯定性行動等有利于美國少數族裔政治和經濟權利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至今近一個甲子的美國種族關系史卻并未讓人看到民權運動成果的完全落地生根,反而是一波又一波或隱或顯的種族主義思潮此消彼長,推動美國社會政治不斷走向極化,使得美國種族和族群關系依然呈現一幅撕裂的圖景。(45)參見唐慧云:《種族主義與美國政治極化研究》,《世界民族》2019年第2期;節大磊:《美國的政治極化與美國民主》,《美國研究》2016年第2期;龐金友:《不平等:當代美國政治極化的經濟與社會根源》,《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9期。究其成因,我們認為主要在于美國歷史上舊有的白人種族主義思想從未被根除、以黨派利益為先的美國政客自始至終并未想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種族主義問題、白人群體中個體種族偏見的代際相傳,以及美國少數族裔群體之間族際利益分化。
首先,追根溯源,美國立國之際適逢歐洲啟蒙運動蓬勃發展,白人至上主義觀念其時已完全滲透到啟蒙思想之中,這從西方先哲康德、孟德斯鳩、伏爾泰以及美國建國精英如托馬斯·杰斐遜等人的著作中便可窺見一斑。另外,當時美國也借助宗教、社會傳統以及所謂的科學性為奴隸制的實施構建起一套種族主義“正當性”理論。(46)梅祖蓉:《美國種族主義“正當性”的來源與建立》,《世界民族》2015年第4期。這些早期為白人至上主義賦予文化合法性的歷史遺存對美國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的影響持續兩三百年之久,直到民權運動之后的20世紀末期才開始受到西方學界的批判,但是知識界的“撥亂反正”并未真正深入西方特別是美國日常社會之中。正如美國學者勞倫斯·鮑勃所言:“種族主義是美國文化根深蒂固的特征,美國最基本制度形成的根源,影響了每個人對許多東西的思維構建,包括真理與謬誤、丑陋與美、純潔與污染和貶低等。”(47)Lawrence D. Bobo, “Racism in Trump’s America: Reflections on Culture, Sociology, and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89.他進而指出,種族主義這一社會現象居于美國社會中心,極其復雜、影響深遠,美國歷史上最具毀滅性、規模最大的南北戰爭,長達十多年的民權運動以及其后沖突不斷的“去種族隔離”和肯定性行動都未能消除種族主義。其根源之根,在于美國白人群體中從上層精英到下層普通民眾的種族思維方式并未徹底改變,舊有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思想依然彌漫于白人社會之中。
其次,美國政治自始至終大都以黨派利益為重,而黨派又往往以白人利益為主導。且不提建國之初制憲會議上白人政治精英們在黑人奴隸制問題上的妥協,就連以解放黑人奴隸而著稱的亞伯拉罕·林肯也承認其終結奴隸制是為了拯救聯邦美國,也就是說只有消除某種形式的種族主義符合他們自身政治利益時,他們才會選擇去做,或換言之,解決某個層面的種族主義只是副產品而已。美國政治的這一“傳統”在不同時期均普遍存在。現有研究表明,除去個別美國總統或其他政治精英的個人理想和信念之外,美國在民權議題上的進步行動更多是受外界客觀因素的推動。黑人民權運動得益于二戰、非洲殖民獨立以及美蘇爭霸期間美國政府對自身形象的維護。(48)袁兆霆、徐榮:《種族歧視對美國國家認同的影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232頁。繼承約翰·肯尼迪民權遺產的林登·約翰遜總統也只是在馬丁·路德·金被暗殺身亡之后,面臨壓力匆忙簽署《公平住房法》,但在白人對民權運動的強烈反抗下,該法案多年來一直被擱置。(49)Vann R. Newkirk II, “Five Decades of White Backlash.”即使成為第一位非裔美國人總統的奧巴馬,如前所述也主要將“后種族主義”作為一個選舉戰略,并未能有顯著改變美國種族主義問題的實質措施。而特朗普在其競選和總統任內,更是利用白人至上主義思潮,為了政治利益而主動挑動種族主義。
再次,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偏見受家庭教育影響存在著顯著的代際相傳,(50)安妮特·拉魯:《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宋爽、張旭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并在外界特別是美國媒體影響下得到強化。從中觀層面來看,家庭是個體與社會聯結的紐帶,家庭原生教育對于個體對社會世界認知的形成至關重要。盡管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能夠彌補家庭教育的不足或匡正家庭教育的缺陷,但是家庭成員的種族偏見和種族主義言行對童年以及青少年個體潛移默化的影響往往會使他們對某個族裔群體形成刻板印象,并且這樣的種族偏見和刻板印象會隨著兒童成長過程中與某個族裔群體負面信息的遭遇而強化。刻板印象一旦形成,便需要更多社會客觀環境資源匡正,但是如果一個社會中種族主義負面思想和行為彌漫,社會教育對個體種族主義刻板印象的匡正便會極其困難。譬如,美國現代電視、電影、廣播等新媒體形式中普遍存在種族主義刻板印象,黑人角色常會被描繪成滑稽、暴力、罪犯等負面形象。(51)相關研究參見Travis L.Dixon & Daniel Linz, “Overrepresentation and Underrepresent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s and Latinos as Lawbreakers on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50, No.2, 2000, pp.131-154; R. M. Coleman, African American Viewers and the Black Situation Comedy: Situating Racial Humor, New York: Garland, 2001;Maya K. Gordon, “Achievement Scripts: Media Influences on Black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Self-Perceptions, and Career Interests,” 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 Vol.42, No.3, 2016, pp.195-220.事實上,相關研究表明,白人至上主義和對少數族裔特別是黑人群體的負面印象,便是從家庭個體間和代際間的傳播開始的,而且家庭相比社會在空間和人際上更具私密性、隱蔽性,往往難以被外界所觸及。(52)褚國飛:《美國種族主義:傳統觀念的消除仍需時間——訪美國三一學院歷史學教授葛榭茹》,《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第296期。白人父母縱容其子女在言語和行為上對其他族裔的種族主義詈語或暴力行為,可以從側面印證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的代際影響和傳播。(53)Joe R Feagin, Hernan Vera and Pinar Batur. White Racism: The Basics, 2nd e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24-30.
最后,美國少數族裔間的族際分化也是美國種族主義難以根除的現實因素。在這方面,種族和階級往往相互糾葛。美國黑人內部已經出現明顯的經濟兩極分化和文化認同分化,中上層黑人在教育、職業結構等方面已與下層黑人截然不同,其在解決種族主義問題上的訴求也不同,從而影響到后民權時代爭取民權時的種族團結力。(54)牛忠光:《當代美國黑人的群體嬗變與文化認同分化》,《世界民族》2017年第6期。另外,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某種程度上是基于工人階級的分裂,在經濟不景氣時尤其凸顯,(55)Melvin M. Lei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cism,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0.這也往往影響非裔、亞裔、拉丁裔等少數族裔之間的經濟競爭態勢,造成其在種族問題上的撕裂。少數族裔族際之間以及黑人內部的階級分化與不同利益訴求,又往往被白人至上主義的政客所利用,例如唐納德·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競選中將其塑造為下層、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的捍衛者,利用美國制度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及其在美國政治中的持久力量,進一步以階級口號掩蓋美國社會中的種族和族群不平等,撕裂少數族裔在民權議題上的種族團結,這不僅成功吸引了白人選民,而且吸引了許多少數族裔的支持。(56)Lawrence D. Bobo, “Racism in Trump’s America: Reflections on Culture, Sociology, and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p.85-104.事實上,自20世紀下半葉至今美國人口的種族多樣化顯著擴大,不同族群的利益訴求變得更加復雜,如果少數族裔無法認清美國白人至上主義政治精英的伎倆,無法尋求族際間共同利益,構建起堅實的利益共同體,美國以強勢白人占主導的種族不平等將會不斷延續和強化。
結 語
民權運動普遍被視為美國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和行為演變的分水嶺。進入后民權時代,受反種族歧視法律的制約,種族主義行為被視為非法,出于“政治正確”,美國社會中公然、公開的種族主義話語與行為一度被弱化或淡化。然而,種族主義已內嵌在美國社會結構和制度之中,美國少數族裔在諸多社會層面依舊遭受不同程度的種族偏見、歧視、不平等和暴力迫害,并且在白人精英政治和主流價值觀偽裝下,比以往更為隱蔽。進入21世紀特別是特朗普時期,美國種族主義的結構性和制度性特征又呈現公開化的趨勢。那么,已內嵌入美國社會結構和制度之中的種族主義為何在當代美國社會難以被解構和根除呢?通過上述對于后民權時代美國種族主義思潮流變的內在邏輯分析,我們看到的是根深蒂固的白人與黑人傳統分野與針對少數族裔的一系列排斥邏輯相結合,這些“排斥邏輯”不僅來自白人這一主流群體,而且涉及不同少數族裔內部或族際間分化或撕裂。(57)達波洛尼亞:《種族主義的邊界:身份認同、族群性與公民權》,鐘震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58頁。在政治層面,美國政治精英們認為他者帶來的文化與身份多樣性威脅到其國族身份的根本即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可能會使美國整體碎片化甚至致使其解體,因此在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名義之下,美國種族主義不斷地被政客們所利用,被制度化、結構化和合法化。總的來看,無論美國種族主義思潮表現為何,無論少數族裔特別是黑人受種族主義迫害的方式為何,無論美國針對外來移民的排斥措施為何,其內在的種族主義傾向均源自美國白人對他者威脅的本質主義想象,以及基于此對自身利益的工具性考量,即維系白人社會規范的主導性及其歷史遺留下的種族優勢和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