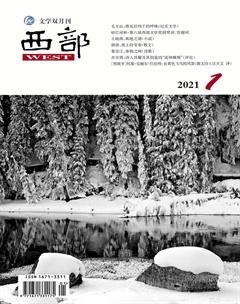有黃色飛鳥(niǎo)的風(fēng)景
何塞·安赫爾·巴倫特 汪天艾

何塞·安赫爾·巴倫特(1929—2000),西班牙戰(zhàn)后涌現(xiàn)出的詩(shī)人群體“世紀(jì)中一代”的代表詩(shī)人,被公認(rèn)為是西班牙二十世紀(jì)下半葉最重要的詩(shī)人之一。巴倫特幾乎包攬了西班牙語(yǔ)詩(shī)歌界的大獎(jiǎng):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jiǎng)(1988年)、伊比利亞美洲詩(shī)歌獎(jiǎng)(1999年)和西班牙國(guó)家詩(shī)歌獎(jiǎng)(2001年)。除了詩(shī)歌創(chuàng)作,巴倫特還翻譯評(píng)論了保羅·策蘭、卡瓦菲斯、霍普金斯等詩(shī)人的作品,并出版數(shù)本文學(xué)、藝術(shù)、哲學(xué)評(píng)論集。
死亡暗沉的呼氣,一如從前你的聲音,自你溺亡的心臟抵臨我。讓我和死亡居住在一起。連死亡都無(wú)法從我這里奪走你。
準(zhǔn)點(diǎn)的時(shí)間。你沒(méi)來(lái)赴約。缺席。你盲目期盼的終結(jié)形式:下午破碎的航程,重重深影終點(diǎn)的爆炸。
我用手指在沙灘上勾勒兩條無(wú)盡的線,作為這個(gè)夢(mèng)永無(wú)終結(jié)的記號(hào)。
緩慢地。從另一邊。而今我?guī)缀趼?tīng)不見(jiàn)你的聲音。
我的眼底驟然聚涌光線。仿佛是你,突然間,回轉(zhuǎn)重生。
一個(gè)陌生男人的身體。你的身體在一個(gè)匿名的黃昏被升起。那里面已經(jīng)沒(méi)有任何你的記號(hào)讓你屬于我們。
無(wú)論詞語(yǔ)還是沉默,什么都不能幫我讓你活著。
我覺(jué)得此刻愛(ài)仿佛靜止懸停。卻并非如此。只是你永遠(yuǎn)不會(huì)回來(lái)了。
沉沒(méi)的風(fēng)景。我走進(jìn)你里面。慢慢走進(jìn)你里面。我赤腳走進(jìn)去卻找不到你。然而,你,一直在。你看不見(jiàn)我。我們已經(jīng)不再有記號(hào)告訴彼此對(duì)方的出現(xiàn)。就這樣交錯(cuò),獨(dú)自,看不見(jiàn)對(duì)方。黃色的飛鳥(niǎo)。最接近時(shí)絕對(duì)的透明。
最后的下午。光線衰退蒼白。我從自己身側(cè)打開(kāi)的傷口中流出,漂到你的血管變硬的河里。
匯合。葉子落在葉子上。大雨是完全展開(kāi)的慟哭。
我曾經(jīng)相信我知道一個(gè)你的名字可以喚你歸來(lái)。現(xiàn)在我卻不知道或者沒(méi)找到。我是那個(gè)死了的人,我對(duì)自己說(shuō),我已經(jīng)忘了你的秘密。
一個(gè)男人胳膊下面夾著小包裹,里面是一個(gè)死人的灰燼。下著雨。路上沒(méi)有人。他走路的方式像是要把這個(gè)包裹帶去某個(gè)特定的終點(diǎn)。他走著。他在無(wú)邊的荒原上走著。到了邊界。
告訴我,黃昏被點(diǎn)燃的邊界上,風(fēng)像席卷長(zhǎng)發(fā)一樣裹挾的那些云是什么?是你走上了這條路嗎?沒(méi)有帶我?什么時(shí)候?
黃昏降臨的時(shí)候,一個(gè)神用看不見(jiàn)的手抹去你,仿佛鳥(niǎo)的翅膀落進(jìn)陰影彼岸更濃稠的陰影。最終,你分解在你自己的目光里。
此刻你疲倦地弄傷自己,好不接受那只已經(jīng)不再伸出的手。強(qiáng)硬的匿名掠奪,你的身體,在這個(gè)不確定的下午。你身邊沒(méi)有任何人。于是,你無(wú)法死去。
鏡子里你的影像被抹去了。我再看的時(shí)候已經(jīng)看不見(jiàn)你。
此刻我知道我們有過(guò)共同的或共享的童年,因?yàn)槲覀円黄鹚廊ァD莻€(gè)欲望觸動(dòng)我,讓我想去你在的地方,把我的灰燼,像遲到的花,存放在你的灰燼旁邊。
靜止的湖泊復(fù)制蔓延的灰色,那下面的空氣有一種金屬質(zhì)地的和平。銀色的,水面的灰燼,翅膀的灰燼,飛行的灰燼,你的灰燼,這場(chǎng)缺席的灰燼。
我知道,只有最后我才能知道你的名字。不是曾經(jīng)屬于你的名字,而是另一個(gè)名字,最秘密的那個(gè),那個(gè)現(xiàn)在還屬于你的名字。
讓我們一起做一個(gè)最微小的藝術(shù),可憐的,不出售的,除了少有的場(chǎng)合從來(lái)不公開(kāi)的,一如此刻,此地,這個(gè)下午,這個(gè)不確定的時(shí)刻絕對(duì)的消失。
什么是孤獨(dú),我問(wèn),終點(diǎn)上你面朝虛無(wú),時(shí)間突然不再是時(shí)間,自己投入井中,暗光刺眼的線條侵襲你的眼睛,你開(kāi)始向它走去,沒(méi)有漁網(wǎng)沒(méi)有證人,陰影沿著你的血液滑進(jìn)你的身體,你在那里不再出生。
你的記號(hào)是月亮。你的光,月光。憂郁的。你的消失如此緩慢。你從沒(méi)如此靠近我。
我是虛弱的。我不知道倚靠何處。空氣里什么都沒(méi)有。你不在。我不在。身體圍繞虛空旋轉(zhuǎn)。
我在黃昏落下的時(shí)候摸索那些影子,在早晨的太陽(yáng)光里,醒著或者最好在做夢(mèng),也許我會(huì)伸出胳膊,觸摸那個(gè)我叫不出名字的看不見(jiàn)的身影。我想我看見(jiàn)了那些我還愛(ài)著的、再也不會(huì)重新看見(jiàn)或者再也不認(rèn)識(shí)我的人,如今誰(shuí)還能認(rèn)出誰(shuí),當(dāng)你已不在,最后的夏天把你的影像席卷去遠(yuǎn)方,很遠(yuǎn)的地方,也帶走了唯一可見(jiàn)的確切的參照。
我想在所有你在過(guò)的地方,所有那些地方也許還有你或你的目光的一塊碎片。是不是疼痛地失去了你才讓一個(gè)空間變成地方?地方,你的缺席?
所有的時(shí)日過(guò)去,我已解碼不出當(dāng)時(shí)召喚的那個(gè)神是誰(shuí)?
月亮慢慢跟隨月亮,如同光線屈從光線,日子讓位日子,黏著的眼皮墜入同一個(gè)夢(mèng)。活著是容易的,艱難的是比已經(jīng)活過(guò)的幸存更久地活。
積雪不祥的潔白。空氣低矮的灰色房頂。云仿佛沮喪的野獸緊挨著屋頂。翅膀或空間的青黑像我們頭上的金屬牌。蒼白暴利的城市。別人也許能用更快樂(lè)的心望向你。這只鳥(niǎo)卻永遠(yuǎn)無(wú)法在你那里找到安歇或住所。
有時(shí)候我覺(jué)得自己離死亡很近。我自問(wèn)這樣的觀察結(jié)論對(duì)誰(shuí)有用。我想,我們寫作終究不是為了有用。那么,為什么不說(shuō)出一個(gè)明顯的瑣碎事實(shí)?死亡的迫近是兩個(gè)赤裸的、平整的表面相遇,互相排斥著融為一體。只是這樣嗎?我不知道。如果沒(méi)有證人確鑿的證言,走到另一邊并不夠,而我還沒(méi)能準(zhǔn)確地記錄它。
活著對(duì)我們而言用處多么小。我們有過(guò)的時(shí)間太短,不夠知道我們?cè)瓉?lái)相同。此時(shí),空氣中微妙的飛鳥(niǎo)正醞釀著你的灰燼,最極限的地方,也許我是不存在的影子的一條細(xì)窄的凸邊。
此刻我獨(dú)坐同一扇窗前,又一次看見(jiàn)天空墜落如劇終的大幕,我還在對(duì)自己說(shuō),阿貢內(nèi),這就是我們簡(jiǎn)單的愛(ài)的終結(jié)嗎?
譯者注:1989年,巴倫特32歲的兒子安東尼奧因吸食過(guò)量藥物死亡。1992年,詩(shī)人寫下此組散文詩(shī)紀(jì)念死去的兒子。他一直說(shuō),安東尼奧是他所有的孩子里最像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