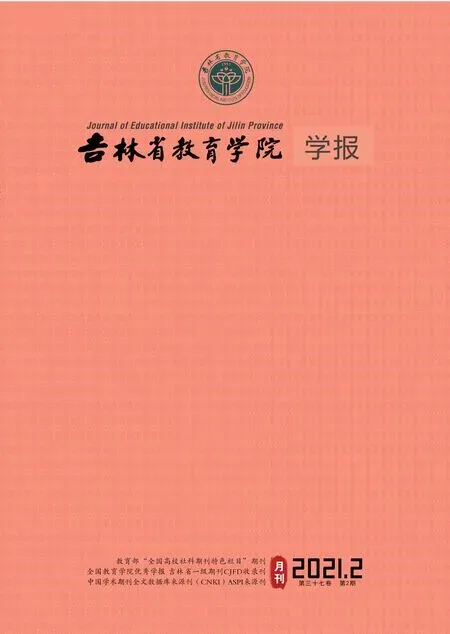教育福利化:斯賓塞的詰問與啟示
鄭霽鵬
(國家開放大學(xué)外語教學(xué)部,北京100039)
教育福利化是公共教育的發(fā)展趨勢(shì),是國家作為教育的責(zé)任主體,把教育產(chǎn)品和服務(wù)免費(fèi)或者低于成本價(jià)值地提供給公民,希望通過國家二次分配更好地提供教育機(jī)會(huì),縮小個(gè)體、群體間因?yàn)橄忍炀秤鲈斐傻牟町悾七M(jìn)教育公平和社會(huì)發(fā)展。其背后的政策預(yù)設(shè)是:公共教育是人人所需的益物,國家有責(zé)任提供,也有能力辦好,教育福利化更有益于個(gè)人和社會(huì)的發(fā)展。這些今天看來不證自明的觀點(diǎn),在斯賓塞那里卻頗受質(zhì)疑,這種質(zhì)疑主要來自對(duì)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公共教育、公共教育權(quán)力和教育福利等問題的不同理解。
一、幸福、福利與國家權(quán)力
與當(dāng)時(shí)占據(jù)主流地位的功利主義者不同,斯賓塞不認(rèn)可“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的說法。他認(rèn)為,一方面,個(gè)體對(duì)幸福的理解不同,即便同一個(gè)體在不同情境下對(duì)幸福的理解也不同,單純地把幸福歸結(jié)為某一個(gè)具體的價(jià)值訴求,就不可能對(duì)幸福有正確認(rèn)知,“要從一般人類所呈現(xiàn)的復(fù)雜現(xiàn)象去推斷出一種真正的社會(huì)生活哲學(xué),并根據(jù)它去創(chuàng)立一部包括獲致‘最大幸福’的各項(xiàng)規(guī)則的法典,是超出任何有限心智能力的一項(xiàng)任務(wù)”[1]。所以,實(shí)現(xiàn)“最大幸福”這一目標(biāo)就成為不可能。
(一)幸福的內(nèi)涵與實(shí)現(xiàn)條件
斯賓塞認(rèn)為,“幸福意味著人體各種機(jī)能都得到滿足的狀態(tài)”[1]。但這種機(jī)能獲得滿足并不依賴于外界的支持和幫助。當(dāng)時(shí)濟(jì)貧法的出發(fā)點(diǎn)是通過公共資源的再次分配使個(gè)體獲得均等的機(jī)會(huì),幫助實(shí)現(xiàn)個(gè)人福祉。但在斯賓塞看來,這并不是幸福的進(jìn)路。每個(gè)個(gè)體都有不完備,這些不完備導(dǎo)致他們對(duì)環(huán)境的不適應(yīng),不適應(yīng)就是禍害。“不論禍害的特殊性質(zhì)如何,它總是可以歸屬于一個(gè)普遍性的原因:各種機(jī)能與他們活動(dòng)范圍之間的不調(diào)和”[1]。消除這些禍害,使個(gè)體各項(xiàng)技能獲得充分發(fā)展,能夠很好地適應(yīng)社會(huì),這就是幸福。這種幸福不是借助外力獲得善物和益處,而是自身不斷提高應(yīng)對(duì)災(zāi)禍的能力,人性就如自然規(guī)律作用下的鮮花和胎兒一樣,會(huì)自然地走向成熟和完美。這是自身機(jī)能不斷獲得提升的過程,也是幸福漸漸獲得的過程。
實(shí)現(xiàn)幸福的條件是什么?斯賓塞認(rèn)為,實(shí)現(xiàn)幸福的最基本條件就是“同等自由”,即每個(gè)人在不傷害他者利益情況下享受同等的自由。既要求社會(huì)給予個(gè)體行為的自由,又要求社會(huì)保障個(gè)體利益。簡單來講,就是每個(gè)人都具有與他人同樣的、不傷害他人的權(quán)力,每個(gè)人都尊重他人合理范圍內(nèi)的權(quán)利,也尊重他人所享有的成果,同時(shí),每個(gè)個(gè)體機(jī)能獲得最大程度的利用。在對(duì)幸福的追求中,斯賓塞認(rèn)為個(gè)人有自我成就的能力,也有自我成就的責(zé)任,對(duì)個(gè)人自由的絕對(duì)追求使公共權(quán)力被弱化。
(二)權(quán)力邊界與公共責(zé)任
與斯賓塞同時(shí)代的洛克等人認(rèn)為人是基于自身權(quán)利獲得保障的需求而讓渡出部分權(quán)利,從而形成公共權(quán)力。在公共權(quán)力的邊界問題上,斯賓塞更加決絕和謹(jǐn)慎。他認(rèn)為“強(qiáng)制性的約束必須是消極性質(zhì)的,而不能是主動(dòng)積極的”[2]。他認(rèn)可的政府角色包括兩個(gè):一是作為保護(hù)者,把人們約束在社會(huì)狀態(tài)之內(nèi),第二是審判者,制止危及該狀態(tài)的行為。公共權(quán)力被囿于如此有限的范圍內(nèi),那么諸多“公共”事務(wù)由誰來承擔(dān)?斯賓塞認(rèn)為,鋪設(shè)道路、提供照明這些事務(wù)都是公共權(quán)力可以退出的領(lǐng)域。這些事情可以由房東這樣的利益相關(guān)者來負(fù)責(zé),因?yàn)橹灰腔诶娴挠?jì)量,他們自然會(huì)提供這樣的設(shè)施來為自己謀取更大的利益,只要存在需要,社會(huì)一定會(huì)有滿足這種需要的沖動(dòng),并且這種沖動(dòng)一定會(huì)付諸行動(dòng)。燈塔、避風(fēng)港這些公共設(shè)施也不是公共權(quán)力需要著力的所在,即便是對(duì)于公共秩序的維持,斯賓塞也是拒絕的。他認(rèn)為,哪怕有人因?yàn)橛贯t(yī)和無照行醫(yī)者而受到傷害,由此帶來的痛苦死亡也不是沒有好處的,因?yàn)樗悄ゾ毴说氖侄巍S纱丝梢姡官e塞認(rèn)為公共權(quán)力可以作為的范圍是極其有限的,更多的行為空間被他讓渡給個(gè)人,他篤信依靠個(gè)體的自發(fā)力量,社會(huì)有機(jī)體會(huì)獲得更持久的發(fā)展動(dòng)力。“每一條有助于改變?nèi)说男袨槟J降姆▌t——強(qiáng)制的,或抑制的,或幫助的,以新的方式——如此影響著人們以至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導(dǎo)致了人性的調(diào)整……在人類尋求滿足的欲望的總結(jié)果中,那些推動(dòng)他們私人活動(dòng)和他們自發(fā)合作的結(jié)果比起政府機(jī)構(gòu)工作對(duì)社會(huì)發(fā)展的作用更大”[2]。
公共權(quán)力是萬能的嗎?通常認(rèn)為,有些事情只能交由公共權(quán)力來做,才可以獲得實(shí)施,或者效率才最高、結(jié)果才最好,這是基于一種這樣的信仰:處理所有的弊端并保障所有的利益是國家的責(zé)任。斯賓塞對(duì)此也持懷疑態(tài)度。首先,“更多的無計(jì)其數(shù)的公共利益,通過更多的難以計(jì)數(shù)的公共機(jī)構(gòu)實(shí)現(xiàn),是以增大的公共負(fù)擔(dān)為代價(jià)的”[2]。為了執(zhí)行公共權(quán)力,就要設(shè)置諸多的公共機(jī)構(gòu)、配備大量的公務(wù)人員,這些成本都來自稅收,公共事務(wù)越多,這種支出越多,也就造成對(duì)國民財(cái)富的更大浪費(fèi)。其次,他懷疑公共權(quán)力處理問題的能力,斯賓塞認(rèn)為趨利避害是每個(gè)個(gè)體的本能,靠個(gè)體各自的抉擇和行動(dòng)而形成的社會(huì)結(jié)果,不會(huì)遜色公共權(quán)力作為帶來的影響,“未經(jīng)足夠的知識(shí)指導(dǎo)下的立法會(huì)帶來大量的災(zāi)難”[2]。再次,他質(zhì)疑擴(kuò)大公共權(quán)力的后果。他認(rèn)為,公共權(quán)力的作用范圍越大,平均主義的取向愈發(fā)明顯,這是功利主義者看重“功利”的表現(xiàn),其后果就是個(gè)人沒有獲得應(yīng)得的待遇,打擊個(gè)人作為的積極性,從而使社會(huì)發(fā)展的動(dòng)力源被大大削弱。
二、教育福利化的合理性
幸福是個(gè)人追求的主要價(jià)值,公共福利是為致達(dá)個(gè)人幸福公共權(quán)力為個(gè)人提供的制度保障和服務(wù)支持,教育服務(wù)以福利的形式向大眾供給,就是公共權(quán)力對(duì)個(gè)人謀取自己幸福的基礎(chǔ)發(fā)展條件的制度性保證。斯賓塞對(duì)幸福共性內(nèi)核的懷疑和對(duì)公共權(quán)力的警惕,也必然使其在教育福利化問題上存在不同主張。
(一)公共福利的必要性
福利向來是政府作用的必然領(lǐng)域之一,一方面,斯賓塞認(rèn)可政府在福利方面的作用:沒有政府的干涉,所有人容易遭受一些摧毀性的傷害,在政府的作用下,“代替它的,是一種政治組織以一種比較溫和的形式犯下的普遍性的侵害。在以前損害是偶爾發(fā)生的,卻是毀滅性的,現(xiàn)在則是不停息地發(fā)生的,但卻是可以忍受的”[1]。另一方面,斯賓塞在否認(rèn)政府行為合法性和效力的基礎(chǔ)上,對(duì)公共福利也采取一種消極作為的態(tài)度。“如果我們不讓人們?nèi)ズ退麄兯幍匚坏恼鎸?shí)環(huán)境相接觸,卻把他們放在人為的環(huán)境中,他們就會(huì)適應(yīng)這些人為的環(huán)境,而最終,他們將不得不遭受對(duì)真實(shí)環(huán)境再適應(yīng)的痛苦”[1]。福利的增加不在于政府行為措施的增加,而在于增加個(gè)人活動(dòng)的自由。因?yàn)楣裉煨陨系娜毕荩粫?huì)因?yàn)橐环N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改變而被克服,“一個(gè)社會(huì)的福利和社會(huì)調(diào)適的公正性從根本上說依賴于社會(huì)成員的天性;通過一類有序的社會(huì)生活所施加的限制下的和平方式的工業(yè)化的實(shí)施,來改善社會(huì)成員的天性,否則社會(huì)福利和社會(huì)調(diào)適兩者中的任何一方面都無法得到改善”[2]。
(二)公共教育的科學(xué)性
在公共權(quán)力對(duì)教育的認(rèn)識(shí)能力方面,如同其他管理能力一樣,斯賓塞也是懷疑的。首先,對(duì)于如何教育兒童,能夠有最正確認(rèn)識(shí)的不是公共權(quán)力,而是和他們關(guān)系最密切的父母。穆勒曾舉例說,消費(fèi)者的興趣和判斷不足以保證商品的優(yōu)質(zhì)。教育也是這樣,這就是國家干預(yù)教育的原因。但斯賓塞認(rèn)為這是通過宣稱人民缺乏能力,來為公共權(quán)力的一切行為做開脫。他認(rèn)為,即便政府擁有權(quán)力,但未必就是教育權(quán)威,對(duì)于教育,公共權(quán)力未必比家庭和社會(huì)懂得更多。其次,在教育問題上,斯賓塞依然相信自然自發(fā)的發(fā)展模式,他批評(píng)國家教育理論者急于用公共教育這種人為的方法去加快或者補(bǔ)救個(gè)人的教育成長,是對(duì)孩子進(jìn)行拔苗助長。他說當(dāng)時(shí)的公共教育是一個(gè)由教師、門房、督察員和理事會(huì)組成的國家機(jī)器,用稅收來使它運(yùn)轉(zhuǎn),以兒童為原料,目的在于加工出一批經(jīng)過良好訓(xùn)練的男人和女人。再次,從公共教育的意義上看,斯賓塞認(rèn)為國家出于好心進(jìn)行公共教育,看似學(xué)生由此獲得了知識(shí),但這是一種以犧牲一種教育而獲得的另一種教育,兒童在獲得知識(shí)的同時(shí)喪失了自我完善、磨練品質(zhì)的機(jī)會(huì),“它阻礙一種極其重要、普遍需要的品質(zhì)的發(fā)展,以便可以給予一點(diǎn)粗淺的知識(shí)”[1]。另外,對(duì)于教育不適合公共權(quán)力來辦,斯賓塞還從教育和公共組織之間的矛盾上進(jìn)行論述,“一切社會(huì)公共機(jī)構(gòu)都具有自我保存的本能,……他們總是植根于過去和現(xiàn)在而絕非將來。改變會(huì)威脅他們,修改他們,最終毀滅他們。因此他們一律反對(duì)改變。而教育卻是與改變緊密聯(lián)系的,總是在使人們適應(yīng)于更高級(jí)的事物,而不是適應(yīng)于事物的現(xiàn)狀”[1]。這樣,追求保持現(xiàn)狀的公共組織和追求改變現(xiàn)狀的教育二者從出發(fā)點(diǎn)上是相悖的。
三、反思與啟示
斯賓塞的上述思想有其產(chǎn)生的時(shí)代背景,去除封建集權(quán)限制是資本主義發(fā)展時(shí)期的時(shí)代主題,追尋自由最大化是現(xiàn)實(shí)條件導(dǎo)致的,也是現(xiàn)實(shí)狀況的要求,由此也就成為當(dāng)時(shí)政治主張的核心。時(shí)代背景是思想的生長土壤,時(shí)過境遷,斯賓塞關(guān)于公共權(quán)力、個(gè)人權(quán)利、社會(huì)福利、國民教育的一系列主張與時(shí)下我們的主流共識(shí)相去甚遠(yuǎn)(表1),我們可以做一比對(duì)。
(一)同一問題的不同歷史鏡像

表1 主流共識(shí)與斯賓塞主張對(duì)比
通過對(duì)比可知,同樣的問題在不同時(shí)代背景下被賦予不同理解,一方面,任何一種認(rèn)知都是行進(jìn)在探究真理的路上,誰也無法到達(dá)真理的終端,都有偏頗和不完善,另一方面,它們都經(jīng)受了時(shí)間和實(shí)踐的檢驗(yàn),都有科學(xué)性存在其中。正確的做法是在時(shí)代背景下做理性分析,在批判中借鑒。
(二)國家權(quán)力的邊界
在斯賓塞那里,政府的職能就是保障個(gè)體自我存在、自我發(fā)展的自由——一種極端的消極自由。他和柏林有相同的理解:過分的積極自由會(huì)導(dǎo)致集權(quán)或者專制的產(chǎn)生,從而以集體的理性來取代個(gè)人理性,用集體邏輯取代個(gè)體選擇,威權(quán)政治下的個(gè)體是被動(dòng)服從的地位,這就破壞了自由的存在基礎(chǔ),斯賓塞也是基于一種這樣的思考,把政府的職能限制在最小范圍,政府應(yīng)該給予的是且只能是一種消極自由,要維護(hù)的“是主體(一個(gè)人或人的群體)被允許或必須被允許不受別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為他愿意成為的人的那個(gè)領(lǐng)域是什么”[3]。把個(gè)人所需要的一切條件都取決于非政府力量的自發(fā)構(gòu)建,由此給個(gè)人追求幸福帶來的障礙,則歸咎為個(gè)體的不適應(yīng)。個(gè)體從不適應(yīng)走向適應(yīng)的過程就是機(jī)能獲得不斷應(yīng)用的過程,也是幸福的獲得過程。既然獲得幸福是個(gè)體有機(jī)體可以自發(fā)實(shí)現(xiàn)的事情,那對(duì)于因?yàn)椴贿m應(yīng)而造成的禍害——這也是福利之所以必要的所在,政府的涉足就幾近多余甚至是有害的,它縱容了個(gè)人的懶惰和依賴,浪費(fèi)了公民的稅收,剝奪了機(jī)能運(yùn)用的機(jī)會(huì)。
如果說強(qiáng)權(quán)政府是在統(tǒng)治國民,那么在當(dāng)下的政府理論和實(shí)踐中,我們所呼喚和經(jīng)營的是一種服務(wù)型的政府,個(gè)體的訴求也從消極的自由轉(zhuǎn)向了積極的權(quán)利,包括了自己可以成為什么,自己可以做什么的自由。“每個(gè)人都可以針對(duì)所有其他的人來主張的一種正當(dāng)要求”[4],是讓他人盡義務(wù)的能力。對(duì)于“他人”的要求不可以單純指向個(gè)體的他人,這在程序上和效力上都是無法保障的,最終的責(zé)任承擔(dān)者還是政府。政府既是他人義務(wù)的代表者,也是個(gè)體權(quán)利的維護(hù)者和建設(shè)者。基于此,政府在社會(huì)福利中的責(zé)任就成為應(yīng)有之意。
(三)教育的社會(huì)屬性
教育福利歷來就是公共福利體系的一個(gè)構(gòu)成部分。它源自國家對(duì)人民的責(zé)任,也源于個(gè)人權(quán)利,同時(shí)也是源于教育對(duì)于個(gè)體生存發(fā)展的必要性。“在每一次大的社會(huì)變遷之時(shí),教育似乎都曾面臨著如何進(jìn)行社會(huì)定位的問題”[5]。為每個(gè)公民提供必要的基礎(chǔ)教育是縮小起點(diǎn)差距、提升機(jī)會(huì)公平的國家責(zé)任,必要的德化教育是保證社會(huì)秩序和國家穩(wěn)定的必要條件。教育與政府、社會(huì)的關(guān)系遠(yuǎn)非斯賓塞所說的,可以付諸個(gè)人放任其發(fā)展,教育尤其是義務(wù)教育的公共物品屬性的分析論述幾乎達(dá)成共識(shí),其意義和正確性也已經(jīng)為實(shí)踐所明證。
斯賓塞對(duì)于公共教育的排斥也源于混淆了公共領(lǐng)域與私人領(lǐng)域。他思考問題,正如他自己所言:“每天都要面對(duì)的一個(gè)問題是,我們已經(jīng)做了這,為什么不應(yīng)該做那呢?”[1]屬于公共事務(wù)的諸多領(lǐng)域,他過分強(qiáng)調(diào)個(gè)體自生自發(fā)的建設(shè),既忽視了個(gè)體構(gòu)建巨大的公共事業(yè)力有不逮,也沒有計(jì)量個(gè)體在建設(shè)公共事務(wù)時(shí)時(shí)間、資源上的浪費(fèi),更為他所忽視或者不屑考慮的是在政府消極作為過程中個(gè)體付出的代價(jià),他把這種代價(jià)看作是由不適應(yīng)走向適應(yīng)的必然條件,其價(jià)值追求的是自由,但事實(shí)上,一旦喪失了行為主體的存在,任何自由都沒有了意義。
(四)啟示
斯賓塞的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和叢林法則只有在缺失了社會(huì)正義、個(gè)體道德的環(huán)境中才能夠?qū)嵤渌^的適者生存“是虛假的,因?yàn)椤m合’不是絕對(duì)的,是有條件的,有一個(gè)對(duì)什么適合的問題,如果只是適合‘生存’下去,那就不是文明”[6],“如果完全按照斯賓塞的理論聽任社會(huì)沿著弱肉強(qiáng)食的道路發(fā)展下去,美國就不會(huì)有今天,或許早已引起革命,或許在某個(gè)時(shí)候經(jīng)濟(jì)崩潰”[7]。但在從小福利走向大福利的時(shí)代主題下,個(gè)人價(jià)值、個(gè)人全面發(fā)展獲得充分尊重,公平、正義作為國家制度的最終追求,教育作為個(gè)人獲得幸福能力的絕對(duì)載體,在這樣的時(shí)代背景下,斯賓塞對(duì)公共教育的一些觀點(diǎn),在今天仍有值得我們思考之處。
從教育權(quán)力問題來看,在兒童教育問題上,公共教育的責(zé)任主體不僅僅局限于政府視域,家庭、社會(huì)都具有責(zé)任和權(quán)力,既有話語權(quán)也有監(jiān)督權(quán),而且對(duì)兒童的培養(yǎng)目標(biāo),是希望他成為一個(gè)有愛的家人、有良知的社會(huì)人和有擔(dān)當(dāng)?shù)膰夜瘢彝ヅ囵B(yǎng)偏重人文性和多元性,社會(huì)培養(yǎng)側(cè)重復(fù)合性和民主性,政府側(cè)重國民性和基礎(chǔ)性,三者合力才可以打造好的教育;從教育學(xué)習(xí)者的教育自由來看,教育過程不應(yīng)是一個(gè)飽和填充的過程,留白給個(gè)體,留下自我發(fā)展的時(shí)間和空間,也更能提供個(gè)性化的發(fā)展機(jī)會(huì),不是生產(chǎn)出了教育產(chǎn)品,而是通過教育培養(yǎng)了人;從教育福利化的發(fā)展上看,福利支持不應(yīng)是一個(gè)直線上升的過程,福利不是多多益善的,不是所有跟義務(wù)教育相關(guān)的事務(wù)都具有福利性,福利性也不完全等同為免費(fèi),只有對(duì)教育福利有理性認(rèn)識(shí),教育產(chǎn)品的福利化才更具社會(huì)效益,獲得可持續(xù)發(fā)展;對(duì)于教育管理的效率而言,教育福利化過程中公共資本使用效率值得注意,公共投入和個(gè)體教育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優(yōu)化其投入效果,在不增加管理成本的同時(shí)滿足個(gè)體的多元化需求,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