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迷術
余幼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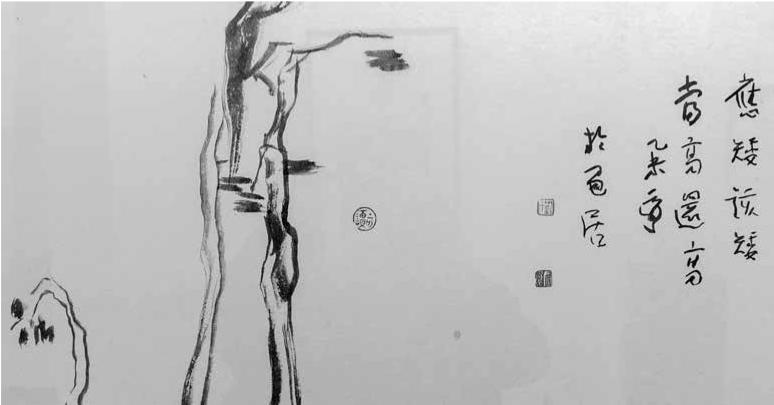
1
卡門在十米開外打量著奎帕,當地向導在旁邊低聲耳語:“瞧,那個老頭兒,他叫奎帕,是個印第安巫士,也是個藥用植物專家。你要的東西或許從他那兒能夠找到。”卡門注視著前方的奎帕,除了相貌著裝與旁人有所區別,行為沒有任何異樣。尤其是在亞利桑那州靠近墨西哥邊境的地方,這里的印第安人并不罕見。卡門對美國西南部這一帶再熟悉不過,此前他已多次深入,收集印第安人使用草藥的資料,作為他人類學研究的田野調查。此時,奎帕站于車站左側,若有所思地低著頭,眼睛固定在大巴車即將停泊的位置,目光銳利如鷹,這個特點讓卡門感到了些許不同。“奎帕不是亞利桑那州本地人,他是來自墨西哥索諾拉省的亞基族印第安人。人們都談論他,但是不敢輕易接近。”卡門側臉面對向導:“我該怎么認識他?”
向導走過去向奎帕打招呼,用西班牙語攀談起來,他介紹了卡門。奎帕彬彬有禮地向卡門致以問候,目光變得柔和。讓卡門欣喜的是,奎帕十分樂意向他提供幫助。八年之后,卡門順利寫完了《印第安草藥之謎》一書,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這本書一經出版便轟動全美,意外地被嬉皮士運動中的青年們奉之以“自由之門”稱號。該書不僅記載了印第安特殊植物的藥用價值,還身臨其境地描繪了植物給人帶來的身體感知的異化,以及精神世界的幻象。用卡門的話說,那些植物絕不只是長在泥巴中的弱小生靈,而在進入人體過后會以千萬倍的能量釋放出來,那些能量在不停地運動,有正有負,經過輪番搏斗最終與宇宙連成一片,在浩瀚的能量場中將人放逐到現實之外的無限場域。盡管書中的描述十分抽象,但有大批追隨者用實際行動驗證了這種抽象文字的成立。在當時,《印第安草藥之謎》不僅僅是一本人類學專著,而被當作通往靈性世界的重要途徑,它在枯萎的心靈中散播一種親密的慰藉與救贖,甚至作為肉體狂歡指南,完全超越了它實際的學術意義。
早在書籍完成之前,卡門就拜在奎帕門下成了他的門徒。卡門曾經有過猶豫,作為一名研究人員必須保持絕對的客觀視角,對現象和發生進行記錄分析。但是奎帕似乎并不在意他的研究項目,總是帶著卡門四處游蕩,在樹林里或沙漠中,就像一個導游帶著一個游客,他從不直面卡門所提出的問題。他只說:“你該去跟它們打招呼,介紹你自己。”它們當然指的是植物,奎帕偶爾會停下來同一棵叫不出名字且看似普通的小草交談,這讓卡門覺得不可思議。他問奎帕:“它能聽懂嗎?你們在聊什么?”奎帕回答:“每一株植物都能聽懂人的話,但你不見得能聽懂它們。這個小家伙在祈求我把它移栽回家,但是我不能,我在向它解釋。”卡門驚訝地問:“為什么不能?”奎帕說:“因為它很危險,不小心碰到就得死!”卡門越發吃驚地張大嘴巴:“可是它看起來這么不起眼,我還以為……”奎帕打斷了卡門:“植物不能光看外表,就像不能以貌取人,這正是它具有迷惑性的地方。越具有能量的東西越不會炫耀,它們通常表現得十分樸實低調……”
與其說是卡門找到了奎帕,不如說是奎帕找到了卡門,在短期的觀察和測試中,奎帕作出判斷,卡門就是他要傳授印第安巫術的不二人選。也許在他們相遇的那天,奎帕就預見他會與此生唯一的門徒碰面,然而他沒有想到,這個人竟然是一個來自理性社會,一切講求科學依據的人類學家,而且還是個白人。好在卡門并不固執傲慢,他聽從奎帕的安排,并無時無刻表達著對印第安人的好感與尊重。這一點是奎帕決心要試一試的原因,更何況在測試中,卡門表現得超乎他的想象。對于奎帕這一提議卡門先是震驚,思索再三后還是接受了。因為他知道,關于印第安這個神秘的種族,只有成為其中的一部分,與其交融共生,才能真正了解它的精神內核,就好比植物,只有親自食用,讓它成為身體的一部分,才能明白它到底在向人類傳遞什么信息。光靠道聽途說,是沒辦法確認那種真實的存在,就連眼睛的關注都是膚淺的。
卡門經過測試的植物,也是他本人最感興趣的植物叫培藥特。起初他并不知道這是測試,而是帶著玩耍心態跟隨奎帕來到樹林里的小木屋,小木屋里已坐了三個人,一個中年女人和兩個青年男子。他們見到奎帕便起身低頭,以示敬意。奎帕是當地最有名的巫魯荷,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為巫魯荷。讓卡門感到意外的是,那兩個男子竟然會說英語,雖然發音不算標準,但起碼能讓人聽懂,他們對卡門說話時用的英語,轉而向奎帕說話時自如地切換成西班牙語,倒是那個女人一直都說西班牙語。當他們知道卡門也會西班牙語后,就不再說英語。奎帕向女人表現出了某種指令,女人連忙轉身從櫥柜取出一個陶罐,那個陶罐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只是一個容器,當她放在桌子中央,奎帕便讓卡門把陶罐打開,將里面的東西取出來。卡門興奮地打開陶罐,掏出里面的東西,臉上卻顯出了失望的神情,這些東西看上去與水果干無異,干癟起皺、歪歪扭扭,它們置于卡門的手心,就像糖果置于孩子的手心,卡門笑著問:“這是餐后甜點嗎?”奎帕并不介意這輕佻的玩笑,他保持鎮定且十分嚴肅地說:“吃吧,咀嚼后吞下去。照我說的做!”同時,其余三雙眼睛同樣嚴肅地盯著卡門,讓他感到強烈的壓力,不得不把僅存在于聽聞中的陌生東西放入自己的口腔,牙齒咬合的過程中,卡門清楚地感覺到這并不是什么水果干,它既不細膩軟糯也不甜蜜,而是無數韌勁十足的纖維在嘴巴里攪動,更像是樹皮,他艱難地吞咽著。奎帕吩咐女人給卡門倒了一杯龍舌蘭烈酒,遞給他:“漱漱口,但是不要吞下去。”此時,所有人都更加專注地盯著卡門。卡門特別明顯地感到胃在燃燒,從舌頭傳遞到大腦的苦澀味道再傳遞到胃,他甚至覺得胃也是苦的,胃壁在被汁液穿透,那些汁液進入毛細血管,通過血液流動運往全身,他的四肢開始發軟,視力逐漸模糊,直到什么也看不見。時間碰巧也與之契合,窗外的天已經黑透,所有人以及木屋和樹林都進入了夜晚的世界。
卡門服用的是曬干后的培藥特,這也是印第安人保存培藥特的慣常方式。他們會專門抽時間去野外的沙漠中采集,有時候一去就是一個星期。他們必須徒步,不能乘坐任何交通工具,以表示虔誠。采集不能在白天,要在天黑以后,因為觸碰神靈般的事物必須小心翼翼,不能被太陽所照見。培藥特實際上是龍舌蘭仙人掌的西班牙俗名。培藥特,這個名字來自印第安部落的納瓦特爾語,有“閃耀”之意。它們一般都直接生長于地表并聚集在一起,呈藍綠、黃綠,有時伴有淡紅色。它們的高度在2到7厘米,直徑在4到12厘米,頂端會有成簇的白色或黃色絨毛。雖然培藥特像一個丑陋的大腫瘤,但是當它開出粉色或白色的花朵時,也有著獨特的美,而且它含有轉變知覺的成分,印第安人把他視作宗教圣物。
2
瓦拉從臥室走出來,端著一盆培藥特,邊走邊向我介紹。他的光頭在自然光的照耀下,顯得格外明亮。剛剛跑上樓的我,呼吸還沒有調整過來,氣喘吁吁地問:“大老遠讓我翹班來這里,就是給我看這個?”瓦拉笑著說:“你不是不想上班嗎?我就給你一個逃班的理由。”我啞然,跟著瓦拉一起訕笑。看著肉乎乎的仙人掌,我問瓦拉這東西哪兒來的?瓦拉把花盆放到日光臺燈下,調整了臺燈的光源和距離,回答了兩個字,秘密。“這東西能活嗎?”我擔憂地問道。“我也不太確定,光照、空氣濕度、土質都有影響,只能碰碰運氣。”說完瓦拉聳了聳肩。我沒有繼續問他培藥特用來干什么,因為我心里明白瓦拉自有他的用處,問了我也不一定懂。瓦拉不是一個普通人,從我第一次見他就知道。
我的注意力很快被房間里的其他事物吸引了,瓦拉向我介紹了他的好朋友大山,還有大山的學徒,他們正在制作“法器”。這時我才注意到,我來到了一個工作室,看上去像一個手工作坊,桌子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工具,很多都叫不出名字,還有不成形的金屬塊和水晶,這個工作室正如瓦拉介紹的是專門制作“法器”的地方。“法器”是什么?我幾乎聞所未聞,好像只有神話故事中才有,瓦拉說:“他們為占卜師制作輔助道具,也會幫人做護身飾物。”我很疑惑:“都什么年代了還有這種東西存在?”瓦拉說:“信則有,不信則無。大山以前跟我一樣都是占卜師,后來他退出了這個行業,才開了工作室。”我問為什么要退出,瓦拉嘴一癟:“我不也退出了嗎?很多時候不需要理由,只需要一個念頭。”
瓦拉泡了一壺茶,領我到陽臺坐下。“最近你的精神狀態看起來好很多了。”瓦拉邊倒茶邊說。“用了你上次教我的‘注意力法,精神沒那么渙散了,可還是難以消除心中的疲憊。”瓦拉酌了一口茶:“你還是太在意自己了,過分關注自己,或覺得自己特別重要都會使人變得沉重、笨拙,甚至虛偽,你得讓自己輕巧流暢起來。”“怎么輕巧流暢?”“放松,這是最好的辦法!”我掩面說道:“太難了,我做不到,每天都充滿了對生活的厭倦。”瓦拉說:“所以你才需要練習,不斷地練習,放松即放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瓦拉隨即從窗臺上拿過一根煙桿,這是我第二次見到這根煙桿,第一次是在小銀家中,瓦拉說這是印第安人用的煙桿。他往煙斗里放了些許干枯草末,如同上一次。他摸出一個打火機,然后說:“下面,我們來放松……”
晚上,我和瓦拉一起到小銀家吃飯。敲了很久門都沒人開,我們不禁對視一眼,心中升起不祥的預感,好在預感還沒消散,門就砰的一聲開了。小銀雙眼無神,臉上掛著兩行淚,屋里撲面而來一股濃濃的大麻味。進到客廳,小銀邊哭邊笑著說:“番茄牛腩已經燉好了,在鍋里,你們自己吃吧!”然后一頭栽到地毯上。瓦拉從臥室拿出被子給小銀蓋好,我發現茶幾上有一盒阿普唑侖,打開里面是空的。我對瓦拉說:“沒藥了!”瓦拉嘆了口氣:“難怪!”我們各自盛了一碗牛腩湯,沒有米飯,坐在地上吃起來。小銀在旁邊已經睡熟,眼角還掛著一滴淚珠。瓦拉說:“小銀對自己的過分關注,比起你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才會變成現在這樣。”我點點頭:“錯不在她吧,她只是太想有人關心她、愛她,畢竟父母都不在了。”瓦拉沉默了片刻說:“你沒有發現她有自毀傾向嗎?”我有點驚異:“這么多年我也很納悶,每次覺得她的生活出現轉機時,她就會陷入新一次的沉淪……反反復復……我也不知道為什么。”瓦拉緊接著說:“她的意志力太薄弱,控制力卻不足,感情過于充沛,還或許是……”瓦拉打住了,我連忙追問:“或許什么?”瓦拉頓了頓說:“或許她壓根就不想好,這樣她才能肆無忌憚,她的所有行為才會得到諒解,引來人們的同情和關注。”我驚愕萬分,誰會用這種方式引人注目?但小銀的一句話突然閃過我的腦門,整個脊椎都在發涼。我們在小銀的客廳坐了整整一個晚上,這是一個不像客廳的客廳,沒有沙發,沒有電視,沒有柜子,甚至沒有窗簾,空空蕩蕩的,只有一個茶幾,茶幾上放著一臺很舊的筆記本電腦,平時人都坐在地上。小銀把墻壁刷成了大紅色,我曾經問她為什么把墻壁搞得這么艷俗,她告訴我,紅色象征生命。
第一次見到瓦拉就是在這個客廳。到小銀家前,我去了趟市二醫院,領導發來信息問我在哪兒,我拍了一張掛號單給她,上面寫著神經內科03號。我以為這次她會放過我,沒想到還是收到了她責難的短信。這并不是老女人第一次刁難我。初入公司頭一年,每天都被各種沉重的任務和KPI壓得喘不過氣,我以為這是每個新人的必經階段,后來才意識到,唯有我才如此。我的工作量幾乎是其他新員工的一到兩倍,自然也比那些已諳熟游戲規則的老油條更甚。項目順利完成是領導的功勞,項目出了岔子就是我的責任。每次報告出了一些不要緊的紕漏,修改過來就行,可老女人偏偏把我推到大領導面前去挨罵,好像罵了我,錯誤就不存在了似的。當然我也不是每次都挨罵,大領導有時候會對我說:“去叫你們的負責人過來。”每當聽到這話,我心里就打哆嗦,一想到老女人回來如鐵板的臉,過后變本加厲施予我的折磨,還不如被罵一通。時間久了我還發現,她對辦公室中某兩個員工從不臉紅,即便他們犯了錯誤,也從不發火,還幫忙在大領導面前開脫。聽別人私底議論,她的升職、兒子讀書都要靠那兩位同事的家長。今年是我到公司的第二年,長期加班已經掏空了我全部的精力,睡眠不佳造成了習慣性失眠。在公司要好的同事幫我想了一個辦法,讓我到網上去制作一個指紋模型,她每天替我打卡,我則可以遲一點到單位。不想老女人對我的挑剔源于她對我的注意,沒過多久就被她發覺了破綻,因為我時有不在,出勤率卻是滿分。她開始追查此事,追到那位同事身上,迫于老女人出了名的惡人聲譽,她害怕得把我供了出來。當月我與她都遭到了全公司通報批評,扣了半個月工資。作為警示,我倆的名字在公司樓道張貼了整整一個月。事后我問自己,既然做什么都不對,那為何還要努力去做?我不再像從前那么任勞任怨,像一坨摔爛的泥巴,一點上墻的意愿也沒有。
下午的醫院人不是很多,診室外只坐了一個人,我們互相掃了一眼對方,好像都沒發現彼此有什么毛病。里面的人出來,他隨之進去,但很快就出來了。手機鈴聲突然響起,屏幕上顯示出老女人冷冰冰的回復:這個月你已經曠工2天,早退3次,獎金全扣。我按了鎖屏鍵,走進診室。坐在面前的是一位戴眼鏡的女醫生,漫不經心地在電腦上查看病人名字,她喊我坐下,沒有看我,“你的癥狀是什么?”她問。我答曰:“失眠。”她把頭轉過來對著我:“多久了?”“差三天一個月。”她愣了一下,沒等她說話我就開口:“幫我開點能睡覺的藥就行。”她的臉立刻嚴肅起來:“藥,我們不能亂開。我問你,你是不是覺得生活沒有意義?”我在心里冷笑了一聲:“一直都覺得。”她的臉更緊了些,說:“我建議你去省醫院的精神心理科看看。”我在心里又罵了一句,還是心平氣和地說:“我就是睡不著,別的沒什么,想吃點藥。”她擺出了一副專業的模樣,扶了扶眼鏡:“失眠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很多時候只是病癥的表現,你還是去大醫院看看。”我按住怒火說了一個字,好。
出了醫院大門,收到辦公室會議的通知。我打了一輛出租車,準備回家。在路上我想起小銀,她在醫生提到的那家大醫院的九樓,差點跳下去。我給小銀發了一條消息,她很快回復。我對司機說:“師傅,換個地方,去云石街6號。”
到了小銀家,只見她和瓦拉癱在地上,正在交替吸一根奇怪的煙桿,煙柄筆直,10厘米左右,像某種植物的根做成的,煙斗是打磨光滑的木頭,材料與煙柄明顯不同。煙柄末尾吊著一根尼龍繩,拴了幾片彩色羽毛,茶幾上放著一個煙袋,里面裝了半袋草末。我既生氣又疑惑,小銀旁邊的男人到底是誰?他穿著紅袈裟,光著腳,活像一個僧人。他們盡情地吞吐,煙霧彌漫房間,紅色的墻壁顯得沒那么刺眼了。小銀呼我,來一口。那副模樣特別像民國時期抽鴉片的女人,讓人有點反感,我拒絕了。她又喊,不是大麻,不會飛。我盤腿坐下,從包里拿出香煙,點了一支。三個人開始互相朝對方吐煙,故意吐到臉上,嗆得咳嗽流淚,然后不約而同哈哈大笑。小銀向我介紹瓦拉,他在緬甸出家兩年,剛回國不久。瓦拉拿出一副塔羅牌,洗牌、切牌后讓我任意抽三張,他看了一會兒說:“火不足,土太多,難以動彈。”我問他什么意思?瓦拉解釋說,火元素是光明與熱烈的力量,領域上常與目標、認同感、技能、理想、信仰相關;火元素關系著一個人的直覺感受,性格上會表現得大膽、脾氣壞、跋扈、自發、鼓舞、活力、應變。火元素的人,有快速思考過程并且依照直覺做事。直覺性強的頭腦能夠憑空產生靈感,不論是跳躍式的理解或者是快速下結論,火象的人從出生就學會依靠自己的直覺行事。土元素是堅實與穩定的力量,領域上常與物質、現實、物資、金錢、財富、身體健康、體質、日常性的事物等相關;土元素代表一個人的感官體驗,性格上會表現得緩慢而審慎、言語中帶著尊嚴和保守、明確、踏實、冷靜、限制,土元素的個性強調重視實際與基本需求,像是生存、安全感、食物和溫暖,使用五官來了解這個世界并與之互動。可被依賴,肩負重任。
我似懂非懂,歪著腦袋問:“那跟我有什么關系?”瓦拉繼續解釋道,元素之間是講求平衡互補的,塔羅的系統是把世界劃分為四大元素:水、火、土、風,就像中國文化中的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元素過多和過少都會帶來問題。比如你,缺少火元素就意味著你缺乏動力、勇氣或毅力,自信不足,會讓人體比較沒有抵抗力;而土元素太多,事態上會呈現出受到阻滯、無法突破困境、缺乏彈性和變通,性格會變成缺乏彈性和呆滯,思考遲鈍和理解緩慢……瓦拉緊接著說:“而且你現在一定陷在某種抉擇當中,你很踟躕,難以斷絕。”我能感覺我的下巴在往下掉,小銀搶過話說:“說得太準了,她就是在猶豫要不要辭職!”我突然漲紅了臉朝小銀扔了一句:“辭了你養我啊?”小銀無奈地望著我:“少來,我都快沒錢吃藥了!”瓦拉指著中間一張牌說:“你抽到寶劍九,證明你還有嚴重的睡眠問題。”我嚇得不敢說話,小銀在旁邊笑了起來,瓦拉轉而對小銀說:“你別笑,你的問題比她還嚴重。”小銀突然住了嘴。瓦拉又說,戴好大山給你做的“銀戒”,盡量保持平靜。小銀哦了一聲。
凌晨三點,瓦拉把小銀抱上床,我把沒喝完的牛腩湯重新倒回鍋中。臨走關燈,我看到黑洞一般的客廳有一個金屬物在角落里閃閃發亮。回家躺在床上,耳邊回響起白天瓦拉對我說的話,要放松!我像催眠大師一樣不停地告訴自己,放松,放松,放松就會睡著……
3
奎帕對卡門大喊:“放松,把你的身體全部放松,像不存在一樣!”卡門的眼前一片漆黑,仿佛掉入無盡的深淵,他奮力掙扎,但是越掙扎越往下掉,速度極快,他的心臟提到了嗓子眼,像是有巨大的吸引力把他往下拽。卡門口吐白沫,如同癲癇病人躺在地上抽搐,發出烏鴉的嘶叫,這個聲音充滿回響,仿佛卡門的喉嚨里有一個洞穴,洞穴里有一只真正的烏鴉。兩個男子臉色鐵青,他們想去幫忙,被奎帕攔住了。卡門繼續往下掉,過了一會兒突然停住,他像氣球一樣開始往上升,身子變得輕盈。他的小腹愈發溫暖,胃中的火像熄滅了似的保存著余溫,他無比舒服,升騰的感覺如若母親的手把嬰兒般的他托舉起來。他的視線中出現無數移動的閃點,一會兒清晰一會兒模糊,他追隨那些閃點不停地擺動跳躍,直至閃點在他身上匯聚,一股巨大的能量將他擊穿,卡門覺得雙臂越來越搖曳,仿佛長出了翅膀。他飛了起來,在樹林里自由地穿梭,從這片樹林穿到那片樹林,他遇到了同類,他們一起飛,比賽誰飛得快,誰的叫聲更長,傳得更遠……卡門記不得自己飛了多久,他累了,停在一塊石頭上,合攏翅膀,睡了過去。
當他醒來,一陣強烈的光刺激得他睜不開眼睛。他慢慢適應著外界的光線,聽到旁邊有人說話的聲音,那聲音來自熟悉的奎帕,聽上去他的心情十分愉悅。卡門完全睜開眼睛,奎帕的臉浮現在他的上方,嚇了他一跳,那深密的皺紋像刻上去似的,略有些驚恐,卡門從未這么近距離看過奎帕。奎帕笑呵呵地說:“你醒了?我以為你熬不過去了呢。”卡門撓撓頭:“我睡了很久嗎?”奎帕說:“昨晚你吃下麥斯卡力陀是晚上九點,現在是早上七點。恭喜你!”卡門不解地問:“為什么要恭喜我?”奎帕變得正經起來:“因為你活了下來!”卡門感到一陣后怕,不過很快就被興奮掩蓋了,他第一次體驗到培藥特的魔力,令人難以置信。這是最好的一手資料,他不禁沾沾自喜。
奎帕幾乎不稱培藥特為培藥特,而是叫它麥斯卡力陀。他對卡門說,這種非尋常現實狀態的產生,是植物在把自己的力量贈予人類。雖然麥斯卡力陀有著神奇的力量,但他絕不是修行的起點,它只是給人提供另一種觀察世界的角度。人要懷著敬畏之心,不可濫用這種力量,因為萬事萬物都是我們的親人,不可對親密的人進行掠奪,不能像你們那個世界的人類一樣貪婪。這只是“入迷術”的起點,而真正的巫魯荷是不會借助任何知覺轉變物質,就能達到與天地通靈。卡門慢慢領悟著奎帕的這番教誨,但仍舊沒法從魔幻般的經歷中脫生,因為這一切都有悖于他的認知系統。但他記住了奎帕的話,世界本是奧妙無窮的,人的知覺卻受限于人類的作為與描述,因而對世界的奧妙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巫術是使人知覺自由與完整的追求,絕不是怪力亂神的迷信,也不是逃避現實和自然規律的方式。人終將一死,奎帕說這句話的時候指了指自己:“包括我!”
4
三個月后,小銀如愿以償地死去。自她從住院部九樓試圖跳下來那次,我就知道,這一天不會太久。盡管她那次活了下來,但死亡不會就此放過她,準確說是她不會輕易放過死亡。那次,我親眼目睹她凌亂的頭發飄在空中,額頭碰了一條很長的傷口,鮮血直流,和眼淚交匯形成血淚,她哭嚎著:“人終將一死,不如就趁現在!”醫護人員從窗臺上把她拉下來時,她依舊喊著這句話。我在病床邊陪了她兩天,臨走前她拉住我的手說:“我沒病!”
我想了很久小銀這個舉動,心中不寒而栗。最讓我害怕的不是小銀,而是我會不會也變成小銀那樣。望著小銀,我更多的憐憫和擔憂是對自己的。這座城市好像在有意排擠我和小銀這樣的人,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有現在這么弱小,從來沒覺得通過努力不能獲得想要的生活。不知道小銀怎么看待這個世界,她看上去對什么都漠不關心,她說活著已經很不容易了,讓我不要太貪心。然而,我并不同意她的說法,我還是相信著什么,盡管這個東西那么模糊,那么遙不可及,我試圖揣測這個東西是什么,也許是個人,也許這個人是瓦拉。瓦拉或多或少給過我某種希望,如果不是假象的話。他總是用一種出離現實的方式同我接觸,并且教我一些超越現實的方法,比如他讓我用“注意力法”訓練自己的思維,這是一種宇宙思維,他讓我把自己和所處的世界縮小到一點,就像站在宇宙深處觀看,他說意識到自己的渺小,痛苦也就沒那么大了。“生命起源于無限,也終結于無限,我們應該置于宇宙之中而不是某個具體的地點、建筑中,淡忘你自己,用你的能量來活著,而不是‘你來活著。”瓦拉經常對我講些聽不懂的話,雖然聽不懂,但也慢慢影響著我。我越來越感到物質世界的了無生趣,人們每天疲于奔命的事物是如此枯燥。在我的內心,開始出現某種神奇的力量,變得越來堅固,盡管若隱若現。瓦拉在我身邊似乎扮演著一個精神導師的角色,雖然我們從來沒有明確過這種角色的分配,但我自愿降低身份,聆聽他的說教。我經常去找瓦拉,或者瓦拉來找我,他每一次的滔滔不絕,都足夠我消化很久。
有一次瓦拉提到,小銀沉浸在大麻的迷幻之中,壓根就是不必要的,長期使用大麻對神經系統的損傷是不可逆轉的,如果小銀只想通過大麻去獲得某種現實中沒有的歡愉,只能說她走上了歧路。要達到真正的靈性世界,根本不需要用那玩意兒,印第安人用鼓點就能進入靈性世界,何況好的巫魯荷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我問他,什么是巫魯荷?他告訴我,巫魯荷是西班牙語,意思是懂醫術的人、巫士或法師,是一個擁有力量的人。他還說,每個巫魯荷都有一支煙桿,煙桿象征著巫魯荷的生命。我問:“他們也抽白鼠尾草嗎?”瓦拉搖了搖頭:“白鼠尾草是我自己用來凈化身體的。每個巫魯荷都會自己配置煙料,他們會根據需求加入不同的材料。但是在儀式進行的時候,他們絕不會使用,而只吸入新鮮空氣。”那天瓦拉又一次為我點燃了白鼠尾草,那略帶枯樹枝的氣味竄進肺部,在里面氤氳游蕩,我像一個空瓶被填滿。瓦拉說:“別急著吐煙,盡量保持久一點,然后放松……”瓦拉拿出了薩滿鼓,他放了一段印第安音樂,開始敲起鼓來。他讓我選擇一個舒服的位置和姿勢,保持不動,閉上眼,盡量把自己和這個世界縮小。他問我看到了什么,等待了很久,我說,什么也沒看到。
5
當我把小銀那次在醫院自殺的事告訴瓦拉的時候,我們正在三環上徒步。瓦拉經常和大山一起徒步,從凌晨走到天亮,就可以繞三環一圈。瓦拉把這種徒步稱之為對自己的觀察,他說一定要認真感知腳底的變化,注意呼吸,要讓能量在全身循環,頂部為頭,底部為腳。徒步最佳狀態是忘記自己在走路。我一直想和瓦拉進行一次徒步,但總是畏懼距離的遙遠。十二月,瓦拉仍舊穿著袈裟,腳上只多了一雙襪子,看到他出現在眼前時,我打了一個寒戰。
當晚,還沒等到城市的霓虹通明,在小銀的紅房子里,大山就迫不及待把手放在了小銀的乳房上,嘴唇在脖頸上婆娑。小銀不知道這是她勾引的第幾個男人,她也從來沒數過。生殖器要進入的那一刻,小銀要求背過身去,大山從后面進入。小銀不想看到他的臉,也不愿意大山看到自己。
夜里的三環路一點也不可怕,反倒有種人工修飾的溫暖,我們走在新建的綠道上,路燈打出昏黃的光圈,地面鋪了一層有彈力的塑膠。瓦拉對我講的小銀的經歷沒有表現出多大興趣,反倒顯出了難得的乏味。從頭到尾,他不停地給我講印第安人,講印第安的薩滿文化。他說沒有哪個民族能像印第安人一樣崇敬自然,大自然是無限的,人是有限的,人只有去接近自然的無限才會發掘自己的潛能,才有足夠的力量去抵御痛苦與折磨。很多人對印第安薩滿文化的誤解就在于,他們迷醉于超自然現象與物質的存在,試圖拋開現實世界,其實印第安薩滿文化并不是幻覺和想象組成的,而是深刻具體的世界,他們無非是更在意精神層面的力量塑造,他們把世界的推進都歸結為力量的使然。瓦拉對印第安薩滿文化的研究還是令我吃驚,雖然并非剛剛才知道,但那天在路上我聽得如癡如醉,確實忘記了自己在走路。
直到太陽掛在城市上方,明亮的天空懸了一層薄薄的霧氣,我和瓦拉又回到了徒步的起點,路人紛紛向瓦拉投來異樣的目光。瓦拉停下來說:“我的煙桿斷了,就在昨天晚上。”
那次徒步后,瓦拉和小銀再也沒有同時出現。最后一次我們三個人一起是在大山的工作室。瓦拉先是教我和小銀腹式呼吸法,然后教我們如何打坐,消除疲勞,與紛亂的俗世隔離。小銀靜不下心來,便跑去跟大山聊天,兩個人嘻嘻哈哈。我發現打坐的時候,耳朵格外靈敏,很多平時聽不見的聲音會鉆進耳朵,瓦拉說這就是要去克服的地方,完全靜下來并不容易。那天瓦拉給我們講了一個可怕的事,他說大山的工作室鬧鬼,并且不是一天兩天了。我向大山求證,大山說是的,以前有朋友來這里住后,都會生一場大病。幸虧這次是瓦拉,他可以降住那些東西。小銀不以為然地朝大山拋去一個眼神:“莫不是什么女鬼吧?”瓦拉站在陽臺,向我們招手,快來看。我先過去,瓦拉指著前方的一棟高樓。我問,怎么了?瓦拉說:“我以前學過一點風水,前面那棟房子就是一塊墓碑。”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過去,小銀和大山也擠了過了,大山的臉耷拉下來,咕噥道:“瓦拉是對的,看來我得搬走了。”當天我們就開始為大山找房子,翻遍了各種租房軟件。晚飯也是大山叫的外賣。整個屋子里最興奮的就是小銀,我們所有人都在看各種租房信息,只有小銀在暢想成為鬼之后的情景。我不耐煩地說了一句:“別鬧了,做鬼也輪不到你!”小銀一臉不悅,使勁把一個金屬物捅進我的手心。我看是一把鑰匙。小銀說:“就你不想我變成鬼,那你就來救我啊。”我把鑰匙揣進荷包說:“誰也救不了你!”小銀高興得跳起來:“那我就可以變成鬼啦……”沒有人再理會她。
6
據說小銀是中毒身亡的,我沒有見到她最后一面。就在那時,瓦拉也消失了。我去工作室找大山,他正在搬家,顧不上搭理我。我說小銀死了,大山縮到了地上。我到瓦拉住過的臥室,里面什么變化也沒有,跟我上次看到的一模一樣。無意中掃過桌面,看到那盆培藥特,泥土中間空出了一個窟窿。幾天后,我與大山一起去小銀家收拾遺物,用了小銀給我的那把鑰匙,開門的瞬間,再也沒有那股熟悉的味道。小銀沒有留下任何遺書之類的東西,我們除了撿到丟在角落里的“銀戒”,還發現一本《印第安草藥之謎》的書,翻開封面,扉頁上寫著“瓦拉購于2015年3月”的字樣。我隨手翻開一頁,讀著卡門的記錄:
我抽了一口奎帕的煙,立馬昏了過去。當醒來已經是兩天以后了,奎帕在我面前走來走去,一言不發。直到中午,太陽無比強烈,奎帕背上布包就準備出門,我用僅剩的力氣跟上,問他要去哪里。奎帕說去一個很遠的地方。我問有多遠,奎帕說太陽照不見的地方。我想都沒想,帶上外套跟上了奎帕的腳步。路上我忍不住問:“我到底發生了什么?”奎帕急促地喘息著說:“你太著急了,我的煙并不喜歡你,你應該尋找自己的煙料。”我解釋道:“我并不知道威力有這么大。”奎帕突然停下來,眼睛直直地盯著我,我從來沒見過如此兇狠的眼神,我害怕極了,但卻逃不出奎帕的目光。奎帕憤怒地吼道:“你差一點就毀了它。”我的身體發著抖,雙手合十向奎帕致歉,請求原諒。奎帕說:“你知不知道煙桿對巫魯荷來說意味著什么?煙桿要是壞了,我也會死!”
一路上奎帕沒有再理我,我只是跟著他走了很遠很遠的路,勞累使我忘記了路途的遙遠。走到一個山谷中,奎帕突然唱起了曾經教過我的《麥斯卡力陀之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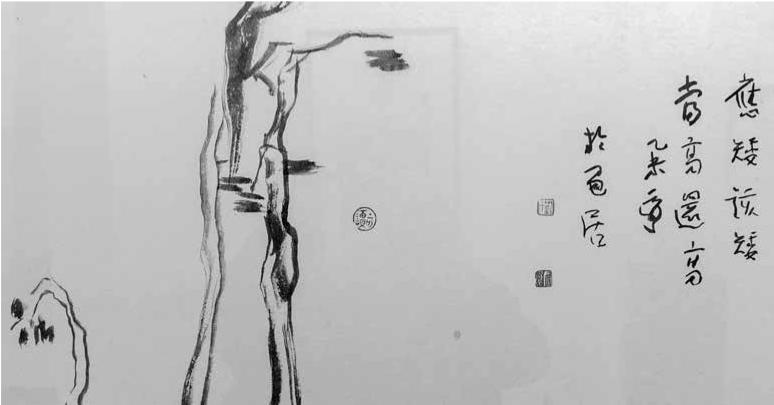
大地是我的父親
天空是我的母親
森林是我的祖父
河流是我的祖母
我是精靈的孩子
……
我從疲憊中打起精神,因為那歌聲太有穿透力,使我忍不住想要用耳朵去捕捉,那聲音像是要穿破巖壁,達到山的另一邊。聲音在山谷中回蕩,形成無數疊加的聲音,甚至招來了猛禽的回應。我能準確無誤地判斷最初聲音抵達的位置,因為那實在是太清晰不過了。那絕不是一個正常人能發出的聲音,更像一只老烏鴉。我清楚地記得上次奎帕對我說的話:“你可以通過斯卡力陀變成任何你想成為的東西,并且第一次你就做到了。你成了一只烏鴉,我也很震驚。同時,你也體驗到了死亡的感覺,你面對了死亡,也面對了這種停頓,但是你克服了它,打敗了它,所以你活著回來了。”
責任編輯 冉云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