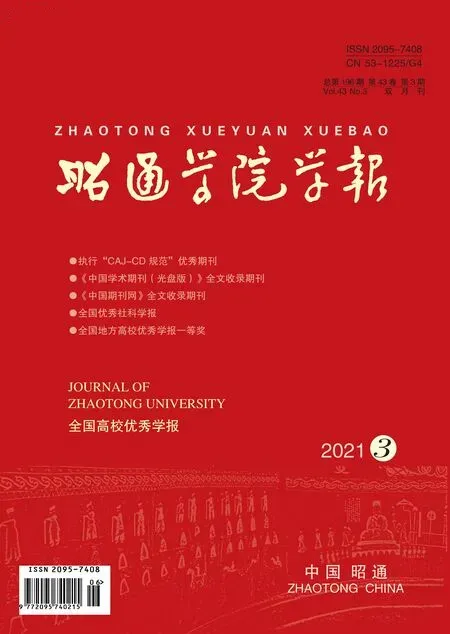哈貝馬斯論主體間性的生成
——從先驗到實踐維度的轉向
劉云霏
(河北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401)
主體性問題是傳統意識哲學中的主要研究內容。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理性統治和工具理性的弊端日益呈現,主體性內在包含的先驗性、獨白性的特征便暴露出來,使其發展陷入困境。20世紀初哲學研究發生語言學轉向,哈貝馬斯順應這一轉向,批判傳統哲學中主體性所具有的先驗性和獨白性,主張將主體性問題從先驗層面回歸到實踐層面,同時依據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哈貝馬斯指出社會實踐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在語言哲學基礎上突出強調了主體間性。
一、近代意識哲學主體性發展的困境
對主體間性的討論應以對主體性哲學的思考作為前提,因此對主體性問題的發展進行梳理有利于深刻理解主體間性思想產生的背景。主體性哲學得以確立和發展是由笛卡爾“我思故我在”這一命題開始的。主體性哲學發展以來人逐漸取代神成為了世界的主宰,同時作為主體被區分出來,與客體相對立。笛卡爾對所有知識采取懷疑的態度,然而唯獨“我思”這一點是不可懷疑的。笛卡爾這一命題將“我”與思維內在地聯系起來,“我”的本質在于“思”。主體性哲學的轉向是由笛卡爾開啟的,康德則在一定程度上系統地完成了這一轉向。康德在探究“知識是如何可能的”這一問題時率先提出先驗自我和經驗自我兩個概念。他將感性、知性和理性作為人的意識能力,對人作為主體所具有的認識能動性進行了系統性論證。康德指出,人作為主體經由感性這一環節將無秩序的外在世界進行整理從而形成經驗現象,然后再通過理性認識將經驗現象整理成知識。人的直覺感受自然界現象的總和,而人的理性產生萬事萬物的普遍法則,即“人為自然立法”。黑格爾雖然被認為是客觀唯心主義的集大成者,但是他在某種程度上也對主體性哲學的衍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提出的“絕對精神是實體與主體的統一”的觀點在某些側面將主體性發展推向了極端。與康德的自我意識不同,他認為主體—客體統一的基礎是“絕對精神”,賦予了主體性絕對的本體屬性和現實力量。
近代以來西方哲學家對主體性的思考既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也有思想上存在的誤區。從積極的方面來看,主體的發現和確立推翻了宗教神學對人的統治,高揚了人的尊嚴和價值。但是其內在包含著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將主體放在中心位置,只是自我意識的獨白,使得主體性的發展陷入困境。
在認識論上表現出的“唯我論”困境。近代主體性哲學發展的顯著特點是從單一主體自身出發,將自我與客觀世界對立導致主客體二元分裂。首先,傳統意識哲學中的主體性具有一定的先驗性。在近代主體性哲學中,客觀對象是作為主體的思維形式而內在,建立在人的先天認識形式的基礎上,并非是一般意義上具有獨立性的客觀存在。然而真正的客體即物質存在是獨立存在于主體之外的,這種先驗性必然會造成主體無法達到客觀外在事物的問題。其次,這種單一性使得主體限制于自我中便造成“自我”無法實現對“他我”的確認。不管是笛卡兒還是黑格爾,他們所規定的主體概念實質上都是將主體局限在單一個體中,忽略了主體與其他社會主體之間的差別以及主體的社會化過程,排斥了主體內在應當具有的多樣性。對于“自我”來說,個體與個體之間以及共同體之間不存在差異,個體與其他社會主體之間的差別被取消,于是“他我”的確認成為難題。因此這一難題只能夠通過先驗地假定“自我”代表人類整體這一抽象的方式解決,以“自我”為基點則會直接引向“唯我論”的困境中。最后,這種唯我論的困境實質上體現為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困境:無論是主體對物質存在的認識,還是單一主體實現對其他社會主體的確認,主體都必須借助認識這一形式去認識客體,其結果無法避免具有主觀性。主客體之間的認識關系事前就先在地肯定了主體的地位,表現在認識論中就是“唯我論”。
在現實中體現出“人類中心主義”的困境。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主體與客體關系的異化、主體與主體關系的異化以及主體自身的異化,首先,主體與客體之間關系異化直接造成人與自然的關系失衡,其中主體指人類,客體指自然界。通過高揚主體性原則,人類的自我意識極大增強,在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上則表現為一種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于是在現實中便造成對自然界的無限開發和貪婪占有。由此主體與客體之間發生異化,造成對大自然的極大破壞,引發諸如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等一系列危機;反之,自然也以自身的方式對人類進行報復。其次,主體與主體關系的異化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失衡。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域限制被打破,人與人之間更多是以自身利益為目的的交往,人際關系變得日益冷漠。單一主體從自我出發將他人看作客體實現自己的目的,他人也以同樣的方式將前者視為客體,人際關系退化為工具性存在。不同于物的客體,將他人視為客體會引起他人作為主體的“反抗”,這便會使自己與他人的關系陷入困境。最后,主體自身的異化導致人過分追求物質滿足導致內在精神缺失以及個性與社會化的矛盾。商品經濟發展則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金錢至上的不良風氣,人們在這種背景下表現為過分依賴物質帶來的滿足感,從而忽視了對內在精神的重視。同時,現代生產要求人與人之間達成合作、實現團結,以追求高利潤,提高生產效率。在這個過程中人的社會性得到極大發展,但是作為有生命的個體的人的個性化發展也需要得到重視,因此主體在受到社會化的同時也受限于社會化,人的個性得不到發展,處于一種兩極對立的矛盾中,進而束縛主體的發展并阻礙主體性的發展。
二、對意識哲學中主體性的重建——從先驗到實踐維度的轉向
近代以來,西方哲學家為解決主體性困境做出了許多努力,諸如胡塞爾在其現象學中建構的先驗的主體間性,海德格爾由“此在”出發討論主體間性,以及馬丁·布伯提出的“我與你”區別于“我與它”的哲學模式。而哈貝馬斯順應語言學轉向,試圖通過恢復語言內在具有的交往功能建構交往理性以實現對傳統主體性的改造與重建。
(一)先驗主體性概念的抽象困局
哈貝馬斯將傳統認識論階段的哲學稱之為意識哲學并對意識哲學主體性這一概念進行了深刻批判。首先,他依據福柯對現代性的批判指出傳統意識哲學所規定的“主體”是矛盾的概念。這體現在主體“既是世界上的一個經驗主體,表現為眾多客體中的一個;又是一個面對世界的先驗主體,并把世界作為一切經驗對象的總和加以建構。”[1]309由于主體所具有的雙重性質導致認知主體在先驗層面上是自由的,在經驗層面上又受到自然界的限制,處于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狀態中。哈貝馬斯指出“從黑格爾到梅洛·龐蒂,人們都一直在努力用一種綜合兩個方面的原則來克服上述兩難處境,把先驗形式的具體歷史理解為精神或人類的自我創造過程。但一次次地落入了實證主義。”[1]309-310其次,哈貝馬斯還指出意識哲學中所談論的主體意識是一個抽象概念,是主體內心的獨白,在實踐中無法得到證明。意識哲學凸顯出的主客二分的根本局限性形成了唯物論和唯心論兩種觀點對立的基本表現形式。哈貝馬斯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一個相同的前提條件,即將意識作為認識世界和知識得以產生的可靠性保證。哈貝馬斯認為,唯物論和唯心論關于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的思考是建立在“模仿論”上的。這種模仿論體現為:在唯物論中,意識是外部世界的反映,思維“模仿”外部世界;在唯心論中,外部世界是思維的外化,外部世界是對思維的“模仿”。這種模仿論是以原型的存在為基礎的,而原型的再現和重復是通過語言作為中介被表達和存在的。如此看來,意識與存在的同一是通過語言言說這一中介過程實現對主體自我意識的表達,難免具有先驗性和獨白性,在人的社會實踐中不能得到證明。
(二)從先驗到實踐維度的轉向
哈貝馬斯認為對主體性的解釋不應該局限于先驗主體,而應當下降到實踐層面,在主體的社會化過程中解釋主體的生成及其本質。他將社會化進程稱之為“教化過程”,主體在這一過程中實現社會化與個性化的雙向發展。教化過程表現出主體在融入相應的社會系統中獲得更大獨立性的特征,這種獨立性既表現在以物質生產為目的同外在自然進行的對象性活動中,也表現在以達成共識為目的同社會其他主體進行的交往活動中。哈貝馬斯強調:“‘自我’是在與‘他人’的相互關系中凸現出來的,這個詞的核心意義是其主體間性,即與他人的社會關聯。”[2]我們可以發現哈貝馬斯對主體和主體性本質的理解與弗洛伊德和拉康所強調的“無意識是主體性的體現”不同,他認為社會性是主體的本質所在,主體性只有在主體與主體之間建構的交往關系中才能得以體現。
哈貝馬斯不是摒棄主體性,而是主張在實踐層面重建主體性,即在交往行為的社會實踐中討論主體性,其核心是強調“主體間性”。在交往范式中,主體作為參與者同他人就某一事物進行溝通,主體與主體之間相互尊重并處于平等地位,進而達成共識。一方面,人們通過進入一種相互協商、相互理解的人際關系,避免了主體性自身所具有的片面主觀性。另一方面,社會實踐中的交往行為是人與人之間互為主體,通過語言中介相互理解以達成共識。這不像以工具理性為核心的工具性行為那樣將其他社會主體當作是客體。在交往過程當中“自我”既不是“先驗自我”也不是“經驗自我”,便克服了意識哲學主體概念先驗和經驗間的矛盾。哈貝馬斯順應語言學轉向,在語言哲學基礎上論證了主體間性的生成:通過語言這一中介實現交往行為,各主體之間彼此理解而達成共識,從而構成一個由多重視角組成的交往網絡,在這一過程中體現主體間性。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哈貝馬斯所談及的交往行為中的主體間性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主體—主體”之間所呈現出的結構,而是在交往過程中,通過語言并遵循有效性規范而形成的平等的、合理的主體間的關系。
(三)主體性的實踐維度——以普遍語用學建構主體間性為核心的交往
在哈貝馬斯看來,交往和語言使用一方面形成一種促使主體個性化的動力,一方面又通過語言中介體現出社會化的主體間性。如此,單一主體便通過語言使用在社會交往行為中實現了個性化和社會化的同步發展。
在交往范式下,語言作為交往工具無疑成為最關鍵的一環,因此必須在語言基礎上進行對主體間性的建構。哈貝馬斯分析當代語言哲學,指出語言哲學理論中仍然無法避免存在主體意識哲學的灰燼。第一,意向論語義學堅持傳統的主體—客體模式。格賴斯(H.P.Grice)作為該理論的主要代表,“他認為一個符號所表達的意義在于說話者借助這個表達所想表明的意圖。”[3]哈貝馬斯指出,這要求聽者理解兩方面內容,一是理解言語者所使用的符號的意義,二是言語者自身使用符號所要達到的目的,只有聽者將這兩方面完全領會,言語者才能夠真正將意圖展示出來。這種根據說話者意圖進行分析的意義理論無疑又退回了傳統意識哲學之中。第二,真值條件語義學的意義理論提出“一個命題的意義是由其真實性條件決定的。”[4]264該理論研究對象是語言表達式,對語言表達式的用法和理解建立在表達式自身的屬性和它們之間構成的規則。哈貝馬斯肯定這一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傳統意識哲學的先驗性,但是仍具有一定的局限:由真實條件所決定的命題實屬斷言命題,這種單一模式并不能對所有命題進行分析。第三,后期維特根斯坦逐漸朝著從獨白式轉向對話式的方向發展。沿著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路徑,又經過奧斯汀和塞爾的發展,命題的形式語義學逐漸擴展到言語行為中,表現出語言所具有的以言行事的功能。但是他們并沒有擺脫真值條件語義學的影響,繼續采用經驗觀察的方法,僅僅將其視為是不同形式與類型的語言的概括,而沒有意識到語言的交往功能存在于語言本身中。因此,哈貝馬斯通過借鑒美國實用主義言語行為理論的內容,揚棄言語行為理論形式化的內涵并建立普遍語用學來恢復語言本質上具有的交往功能。
哈貝馬斯指出:“普遍語用學的任務是確定并重建關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條件。”[5]那么主體間如何才能夠達成理解呢?要想達成理解,就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即使用讓人能夠聽懂的語言;達到某些語用學條件;履行達成共識后所內含的義務。在交往行為中,參與者遵循言語行為的有效性要求,在主體間構建一種相互平等、互相尊重的交往關系,從而通過語言這一中介達成共識。在此過程中體現“主體間性”,以區別意識哲學中將他人視為客體呈現出的被動交往關系。
哈貝馬斯基于普遍語用學建構了以主體間性為核心的系統的交往行為理論,該理論的主要目的是挽救現代性危機,恢復交往理性的地位。所以他試圖通過普遍語用學強調語言所具有的交往功能,在交往行為中達成共識,之后再通過程序化論證對之前所達成的共識進行檢驗,以此來恢復交往理性的地位。哈貝馬斯明確交往理性是“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確立了客觀世界的同一性和生活世界的主體間性。”[4]10他通過分析三種不同行為模式即目的行為、戲劇性為和規范行為,表明唯有交往行為可以全面體現語言的溝通功能與理性的統一性。于是,我們可以將交往行為設定在以下情境中:交往主體處于理想的言談環境中共同承認論證程序的規范性并遵守這一程序,同時他們不受到外界力量強制,基于平等自由實現對話,從而對客觀世界的某一事或物的認識達成一致。哈貝馬斯為恢復交往理性創建了交往行為理論,在理論上完成了主體性研究到主體間性轉向,同時也在語言哲學基礎上開啟了主體間性哲學研究的新視域。
三、哈貝馬斯主體間性思考的價值和局限性
哈貝馬斯討論主體間性的生成以及對主體間性思想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價值,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理論上,他開辟了在語言哲學基礎上主體間性哲學研究的新路徑,同時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人的本質是其社會性”的觀點。實踐上,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但也忽略了人自身的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相互制約的關系,現代性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這些問題的解決可借鑒其交往行為理論。
然而,他對主體間性思想的發展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試圖通過主體間性解決先驗與經驗之間的問題,卻將精神交往看成是其發展基礎,而忽略了發揮基礎作用的物質生產實踐。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基礎是物質生產實踐,取代物質交往的基礎地位使得主體間性理論有可能陷入某種唯心主義的虛幻中。其次,他倡導的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對話模式過于理想化。這種對話模式忽略了現實中人們往往存在較大的社會差異性,交往主體不同的生活背景、知識結構等都會成為影響交往行為的重要因素。平等對話在邏輯上成立,但在現實中可能無法實現。最后,交往過程中程序上的合法性不一定能夠完全保證實質上的正當性。哈貝馬斯強調的以相互尊重、自由認同為價值訴求,通過合理民主的程序進行對話的主體間交往模式在現實中具有自身局限性。
四、結論
哈貝馬斯批判傳統意識哲學描繪的主體性概念內在地包含著某種先驗性并表明主體的本質在于其社會性,自我在與他人形成的交往關系中才能顯現出來。同時他以主體間性為核心建構了其交往行為理論,這為恢復交往理性的地位,拯救危機做出了重要貢獻。哈貝馬斯對主體間性的思考無疑具有一定的價值,但是其中存在的烏托邦性質以及將交往放在基礎性位置而忽視物質生產實踐卻將自己陷入理想化的困境中。因此,對待主體間性問題的思考應該綜合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研究主體間性問題要立足于現實社會生活,將抽象的人還原為現實的人,并且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觀,消除意識哲學中主客體之間存在的鴻溝,將主客體統一于人的社會實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