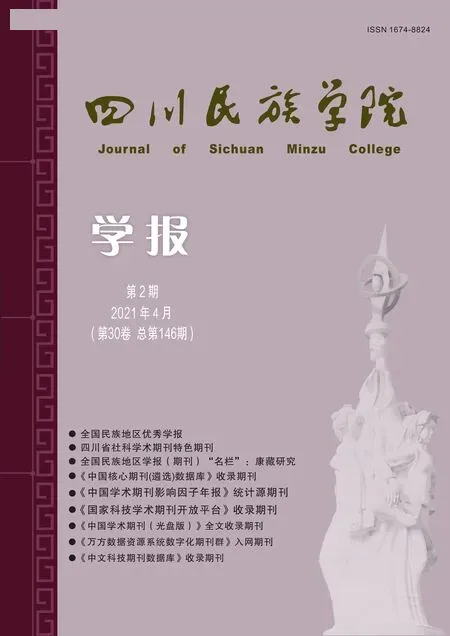國(guó)內(nèi)《格薩爾》史詩(shī)傳播研究綜述
鄭敏芳 崔紅葉
(西藏民族大學(xué),陜西 咸陽(yáng) 712082)
被譽(yù)為東方“伊利亞特”的格薩(斯)爾史詩(shī),既是族群文化多樣性的熔爐,又是多民族民間文化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見證。格薩(斯)爾在多民族中傳播,不僅是傳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紐帶,同時(shí)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生動(dòng)見證[1]。近年來(lái),習(xí)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要重視《格薩(斯)爾》史詩(shī)(1)1. 2011年,習(xí)近平參觀西藏文化事業(yè)繁榮發(fā)展的圖片和實(shí)物時(shí),看到藏戲、史詩(shī)《格薩爾王》被列入聯(lián)合國(guó)人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作名錄,他就充分肯定了對(duì)藏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保護(hù)和發(fā)展的工作。(習(xí)近平率中央代表團(tuán)參觀西藏和平解放60年成就展[EB/OL].[2011-07-18].https://www.chinanews.com/gn/3191069.shtml)2.2014年10月14日,習(xí)近平在《在全國(guó)文藝工作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中談到:“……從《格薩爾王傳》《瑪納斯》到《江格爾》史詩(shī),從五四時(shí)期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新中國(guó)成立到改革開放的今天,產(chǎn)生了燦若星辰的文藝大師,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藝精品,不僅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豐厚滋養(yǎng),而且為世界文明貢獻(xiàn)了華彩篇章。(習(xí)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huì)上講話(全文)[EB/OL].[2014-10-15].http://culture.people.com.cn/c22219-25842812.html)3. 2018年3月20日,在第十三屆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第一次會(huì)議上講話中,習(xí)近平再次談到“中國(guó)傳承了格薩爾王、瑪納斯、江格爾等震撼人心的偉大史詩(shī)”。( 習(xí)近平:在第十三屆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第一次會(huì)議上的講話[EB/OL]. [2018-03-2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c_1122566452.htm)4.2019年7月15日,習(xí)近平在赤峰考察調(diào)研時(shí),同古典民族史詩(shī)《格薩(斯)爾》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親切交談。(這件事,在習(xí)近平心中有多重[EB/OL].[2019-08-19].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c_1124894941.htm)的保護(hù)與傳承。傳播能夠架起文化遺產(chǎn)與公眾世代對(duì)話、交流的橋梁,所有與遺產(chǎn)價(jià)值有關(guān)的變化也都需要借助于某種傳播手段來(lái)傳遞[2]2,因此,傳播研究也是“格薩爾學(xué)”研究的重要課題。當(dāng)前,以“格薩爾傳播”為主題的研究已有諸多成果出現(xiàn),但依然存在一些研究的盲點(diǎn)和短板,本文在盤點(diǎn)已有成果的基礎(chǔ)上,擬就國(guó)內(nèi)《格薩爾》史詩(shī)傳播研究的現(xiàn)狀及存在的問題進(jìn)行分析。
一、研究熱點(diǎn)
美國(guó)傳播學(xué)奠基人之一的哈羅德·拉斯韋爾于1948年在《社會(huì)傳播的結(jié)構(gòu)與功能》一文中,明確提出了傳播過(guò)程及其五個(gè)基本構(gòu)成要素,即:誰(shuí)(who)、說(shuō)什么(what)、通過(guò)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對(duì)誰(shuí)(to whom)說(shuō)、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即“5W模式”[3]。十年后,布雷多克在《“拉斯韋爾公式”的擴(kuò)展》一文中又增加了兩個(gè)W,即:“在什么情況下(in which circumstance)、為了什么目的(in which aim)”,構(gòu)成“7W模式”[4]。作為人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格薩爾》,其傳播除了具備“7W模式”中的各要素外,還有其獨(dú)特的要素,即:“在什么地方(where)”“以何種面貌(in which form)” 、表現(xiàn)出“什么特征(what characteristics)”。但國(guó)內(nèi)的《格薩爾》傳播研究并不是對(duì)上述傳播要素均做了探討,而是只關(guān)注其中的某幾個(gè)要素,研究熱點(diǎn)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
(一)傳播者研究
“7W模式”中的“who”指的是傳播者。《格薩爾》說(shuō)唱藝人既是史詩(shī)的創(chuàng)造者也是史詩(shī)的傳播者,說(shuō)唱藝人研究是史詩(shī)傳播研究中關(guān)注最多的課題。國(guó)內(nèi)史詩(shī)的傳播者研究以陶陽(yáng)的《琶杰的詩(shī)歌藝術(shù)》拉開序幕,此后格勒、楊恩洪、降邊嘉措、旺秋、斯欽孟和等二十多位學(xué)者都對(duì)這一課題做了研究并發(fā)表成果。其中,楊恩洪的《民間詩(shī)神——格薩爾藝人研究》既有對(duì)藝人群體的宏觀研究,也有對(duì)具有代表性的藏族、蒙古族、土族民間藝人的個(gè)案研究,她首次將藝人分為神授藝人、吟誦藝人、掘藏藝人、學(xué)識(shí)藝人( 聽別人說(shuō)學(xué)而識(shí)得的)、圓光藝人五個(gè)類別[5]。于靜和王景遷在專著《〈格薩爾〉史詩(shī)當(dāng)代傳播研究》中沿襲了她的這一分類。此外,楊恩洪還試圖探討藝人的“神授”之謎。對(duì)這“神授”之謎做了探討的學(xué)者還有何天慧、角巴東主、徐國(guó)瓊、閻振中、頓珠和高寧等。降邊嘉措、角巴東主等主要對(duì)說(shuō)唱藝人這一群體進(jìn)行了宏觀研究。談士杰關(guān)注的是青海省的藝人的說(shuō)唱情況,向波探訪了土族的說(shuō)唱藝人,格日勒扎布概覽了蒙古族的說(shuō)唱藝人。甲央齊珍、陶陽(yáng)、格來(lái)、旺秋、熱噶和王國(guó)明等學(xué)者分別對(duì)藝人迪瓊·巴吉、才智、琶杰、扎巴、桑珠、玉珠和王永福等做了個(gè)案研究。努木探討了加強(qiáng)《格薩爾》說(shuō)唱藝人工作的舉措。張蕊以紀(jì)錄片的形式記錄了部分格薩爾說(shuō)唱藝人的說(shuō)唱情況。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丹曲發(fā)現(xiàn)了史詩(shī)的特殊傳播者——寺廟。他通過(guò)對(duì)達(dá)那寺的實(shí)地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在史詩(shī)《格薩爾》的流傳過(guò)程中,藏傳佛教寺院及高僧大德發(fā)揮了傳唱、收藏、撰寫、研究、收集格薩爾文物等重要的作用[6]。
(二)傳播內(nèi)容研究
“7W模式”中的“what”指的是傳播內(nèi)容。《格薩爾》史詩(shī)傳播內(nèi)容指的是史詩(shī)在流傳的過(guò)程中在不同的族群、不同地區(qū)出現(xiàn)的不同版本。目前國(guó)內(nèi)這一方面的研究多聚焦在四個(gè)方面:藏、蒙、土、普米、裕固等民族間流傳的《格薩爾》史詩(shī)特征;某兩個(gè)或多個(gè)民族或地區(qū)流傳的史詩(shī)異同比較和關(guān)系分析;北京木刻版和某些地區(qū)或某位藝人演唱版本的異同分析;史詩(shī)傳播內(nèi)容的變化。齊木道吉分析了蒙文《格薩爾》的特征。楊恩洪、王興先探討了土族地區(qū)流傳的《格薩爾王傳》的內(nèi)容。王軍濤分析了裕固族《格薩爾》的故事類型。袁曉文和李錦詳述了藏彝走廊上各民族間流傳的《格薩爾》版本。烏力吉簡(jiǎn)要介紹了蒙藏《格薩爾》的異同。班馬扎西將土族和藏族的《格薩爾》做了對(duì)比。李垣比較了普米族和藏族《格薩爾》的差異。王興先分析了藏、土、裕固族中流傳的《格薩爾》的不同。徐國(guó)瓊的探討了普米族《支薩·加布》與藏族《格薩爾》《昌·格薩爾》與《嶺·格薩爾》及西藏的《格薩爾》與巴爾底斯坦《蓋瑟爾》之間的關(guān)系。齊木道吉論述了青海《厄魯特格斯?fàn)枴放c《北京木刻本》的關(guān)系。斯欽巴圖分析了青海蒙古口傳《格斯?fàn)枴放c北京木刻本《格斯?fàn)枴返漠愅=颠吋未氡容^了扎巴老人說(shuō)唱本與木刻本《天界篇》之間的差異。次仁平措在訪談中談到了史詩(shī)傳播內(nèi)容的變化:當(dāng)代新的藝人所表演的多是一些短的說(shuō)唱,而傳統(tǒng)的說(shuō)唱藝人說(shuō)唱的故事很長(zhǎng),內(nèi)容十分龐雜多樣,而且時(shí)間跨度大,說(shuō)的內(nèi)容也可能會(huì)出現(xiàn)前后人物不一致、故事情節(jié)銜接不連貫等問題[7]。
(三)傳播方式研究
“7W模式”中的“In which channel”指的是傳播方式。《格薩爾》史詩(shī)的傳播方式主要體現(xiàn)在其傳播渠道、傳播工具上。《格薩爾》史詩(shī)流傳千年,傳播方式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許多學(xué)者在研究《格薩爾》史詩(shī)的傳播時(shí),都關(guān)注到其傳播方式的變遷。袁愛中認(rèn)為《格薩爾》史詩(shī)的傳播貫穿口頭傳播時(shí)代、手抄本傳播時(shí)代、印刷傳播時(shí)代、電子傳播時(shí)代直至網(wǎng)絡(luò)傳播時(shí)代:藏文字產(chǎn)生以前,史詩(shī)以口耳相傳的形式流傳民間;印刷術(shù)傳入后,史詩(shī)開始借助印刷媒介傳播,以“說(shuō)唱”和“文本”的形式并存流傳;進(jìn)入電子傳播、網(wǎng)絡(luò)傳播后史詩(shī)以“音視頻”、藝人說(shuō)唱、文本形式并存流傳[8]。王治國(guó)指出,史詩(shī)的傳播分為口頭傳承、書面文本傳播和現(xiàn)代多元媒介傳播三個(gè)階段,其傳播方式歷經(jīng)了從聽覺主導(dǎo)的口頭媒介經(jīng)由視覺中心的印刷媒介再到綜合延伸的電子媒介的變化過(guò)程[9]。此外,他還對(duì)史詩(shī)藝術(shù)改編與跨媒介傳播進(jìn)行二度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可行性與運(yùn)作機(jī)制進(jìn)行了探討[10];并提出傳媒時(shí)代要發(fā)揮現(xiàn)代科技與視覺文化的優(yōu)勢(shì),要想讓《格薩爾》文化代代不息地傳承與傳播下去,就必須在史詩(shī)的傳播渠道和方式上創(chuàng)新模式與方法,運(yùn)用影視數(shù)碼技術(shù)來(lái)進(jìn)行《格薩爾》文化的保護(hù)與搶救[11]。張美認(rèn)為雖然說(shuō)唱藝人是傳播主體,但因傳播范圍窄、傳播方式形態(tài)單一、受眾心理差異、“人亡歌息”等問題的出現(xiàn),史詩(shī)的傳播需要探尋多種途徑。因此,她認(rèn)為探索利用新媒體傳播《格薩爾》史詩(shī)顯然具有重要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和現(xiàn)實(shí)意義[12]。索南措的《〈格薩爾王傳〉傳播方式對(duì)藏民族崇拜心理的影響》則探討了《格薩爾王傳》的傳播方式對(duì)藏民族崇拜心理的影響。
(四)翻譯研究
翻譯研究既包括對(duì)譯本的研究也包括對(duì)翻譯理念、翻譯策略、翻譯活動(dòng)等的研究,可以將它看作“7W模式”中的“what+ in which channel” 。翻譯決定了《格薩爾》史詩(shī)以何種面貌出現(xiàn)在異質(zhì)文化中,翻譯史、翻譯理念、翻譯原則、已有版本的成因等都是它關(guān)注的話題。《格薩爾》的翻譯研究遠(yuǎn)遠(yuǎn)晚于其翻譯活動(dòng),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格薩爾》在國(guó)外的翻譯活動(dòng)始于1771-1776年俄國(guó)旅行家帕拉萊斯將其蒙文本譯為俄文本,國(guó)內(nèi)的翻譯活動(dòng)始于什么時(shí)候,目前尚無(wú)定論[13],但普遍認(rèn)為藏漢翻譯的時(shí)間,始于1930年任乃強(qiáng)將《降伏妖魔》一章譯為漢語(yǔ)。而對(duì)譯介的研究則始于1981年,王沂暖梳理國(guó)內(nèi)外《格薩爾》翻譯簡(jiǎn)史[14]。此后,在宏觀翻譯及漢譯研究方面:張積成論述了藝術(shù)性翻譯原則,馬進(jìn)武論述了翻譯中存在的問題, 崗·堅(jiān)贊才讓提出了翻譯的原則及《格薩爾》翻譯中不可丟失的文化層面。扎西東珠論述了《格薩爾》的文學(xué)翻譯研究問題及翻譯原則等。降邊嘉措論述了《格薩爾》翻譯面臨的困難及存在的問題,并提出要將《格薩爾》的翻譯提高到文學(xué)翻譯的高度[15]。平措提出《格薩爾》漢譯,應(yīng)以達(dá)意、傳神、措辭通順自然、讀者反映相似等為譯文標(biāo)準(zhǔn)[16]。外譯研究方面的成果有:王治國(guó)探討了《格薩爾》翻譯的學(xué)科定位、英語(yǔ)世界《格薩爾》史詩(shī)的接受語(yǔ)境、翻譯現(xiàn)象、翻譯策略等,重點(diǎn)關(guān)注了道格拉斯·潘尼克譯本、葛浩文譯本和達(dá)維·尼爾譯本。弋睿仙等分析了艾達(dá)·澤特林譯本,對(duì)其中的 “去史詩(shī)化”現(xiàn)象進(jìn)行了闡發(fā)。邵璐以阿來(lái)小說(shuō)《格薩爾王》中佛教用語(yǔ)英譯為例,運(yùn)用文體分析法對(duì)譯者認(rèn)知進(jìn)行探索。王景遷、拉姆卓嘎、臧學(xué)運(yùn)、張寧等則從文化傳播角度闡述了文化負(fù)載詞的翻譯原則和策略。楊艷華分析了譯本的質(zhì)量,殷培賢探討了英譯的理路、臧學(xué)運(yùn)還提及了史詩(shī)的英譯史。陳琪和趙蕤梳理了《格薩爾》在日本的譯介研究情況。張曉闡述了《格薩爾》譯介模式構(gòu)建中應(yīng)該注意的因素。
(五)傳播形態(tài)研究
“7W模式”中并未包括“in which form”,即傳播形態(tài),但《格薩爾》史詩(shī)的傳播中體現(xiàn)出這一獨(dú)特的傳播要素。《格薩爾》史詩(shī)在流傳過(guò)程中,除了口傳史詩(shī)形態(tài)外,不斷有新的形態(tài)出現(xiàn),史詩(shī)的傳播形態(tài)自然引起學(xué)者們的關(guān)注。20世紀(jì)90年代,徐國(guó)瓊在《〈格薩爾〉考察紀(jì)實(shí)》中的《格薩爾唐喀與畫像》中,介紹了他所見到的六種不同類型的格薩爾圖像;在《別墅里的格薩爾壁畫》中,介紹了在西藏昌都寺活佛希哇拉的別墅中所見到的一幅巨幅格薩爾壁畫;并在《記鄧柯·吉蘇雅的“格薩爾神廟”》中,對(duì)格薩爾王誕生地林蔥土司執(zhí)政時(shí)期,修建于 1790 年的“格薩爾神廟”內(nèi)的壁畫作了詳細(xì)的介紹。楊嘉銘自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致力于《格 薩(斯)爾》圖像文化研究,成果頗豐(2)論文有《松格嘛呢——格薩爾的寄魂城》 《石渠格薩爾文化探索之旅》 《格薩爾造型文化論綱》《格薩爾圖像藝術(shù)的新開拓》《格薩爾圖像的基本類型》《〈 格薩爾千幅唐卡〉繪制紀(jì)實(shí)》 《關(guān)于英雄史詩(shī)主人公嶺 · 格薩爾 是否有原 的討論》《一部展 示偉大史詩(shī) 〈 格薩爾 〉的精美畫卷——藏族英雄史詩(shī)〈格薩爾〉唐卡述評(píng)》。出版的專著為《琉璃刻卷 ——丹巴莫斯卡 〈格薩爾〉嶺國(guó)人物石刻譜系》《雪域驕子嶺·格薩(斯 )爾的故鄉(xiāng)》《西藏格薩爾圖像藝術(shù)欣賞》(上、下)。。降邊嘉措等在2003年出版了《藏族英雄史詩(shī)〈格薩爾〉唐卡》,此后索朗格列、青措、文德等及四川博物院和四川大學(xué)博物館也加入《格薩爾》唐卡研究中來(lái)。楊勇研究了唐卡形態(tài)的格薩爾文化品牌傳播及其衍生品開發(fā)。吳結(jié)評(píng)和陳歷衛(wèi)分析了英語(yǔ)世界的《格薩爾》唐卡傳播與傳承過(guò)程中面臨的問題。索南卓瑪、曹婭麗致力于藏戲形態(tài)的《格薩爾》史詩(shī)研究。譚春艷論述了色達(dá)格薩爾藏戲在傳承少數(shù)民族民間音樂文化過(guò)程中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并探討了其對(duì)當(dāng)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hù)的重要意義。于靜和王景遷探討了新時(shí)代《格薩爾》的新傳播形態(tài)。金石和彭敏指出《格薩爾》史詩(shī)有多種傳播形態(tài),包括文本類、影視類、曲藝類、其他衍生品類以及傳統(tǒng)說(shuō)唱類。丹珍草認(rèn)為,傳唱千年的《格薩爾》史詩(shī),除了民間藝人的口頭說(shuō)唱和各種版本的書面文本并存外,還有格薩爾藏戲、格薩爾唐卡、格薩爾音樂、格薩爾石刻、格薩爾“朵日瑪”、格薩爾漫畫、格薩爾彩塑酥油花等等[17],并研究了當(dāng)代格薩爾壁畫“圖式”表述。楊恩洪談到了相聲形態(tài)的《格薩爾》。卡先也對(duì)制作《格薩爾》動(dòng)畫片可行性及其意義進(jìn)行了探究。甄卓英指出史詩(shī)網(wǎng)絡(luò)傳播中的問題并提出解決問題的對(duì)策。
(六)傳播區(qū)域研究
“7W模式”中也不包括“where”(傳播區(qū)域)。但《格薩爾》的傳播區(qū)域是《格薩爾》傳播研究中的重要因素,因?yàn)閭鞑^(qū)域研究不僅可以勾勒出《格薩爾》的傳播軌跡,還可反映出《格薩爾》流傳地區(qū)各民族交往交融的情況。《格薩爾》史詩(shī)由產(chǎn)生地向四周輻射,學(xué)界用“三個(gè)九”(3)《格薩爾》學(xué)界用“三個(gè)九”來(lái)概括其流傳的廣泛性。“《格薩爾》流布于中國(guó)、蒙古國(guó)、俄羅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爾、印度、不丹、錫金環(huán)‘世界屋脊’九個(gè)國(guó)家的藏族后裔、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當(dāng)中,以及國(guó)內(nèi)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甘肅、寧夏、內(nèi)蒙古、遼寧、新疆九個(gè)省區(qū)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普米族、納西族、白族、傈僳族九個(gè)民族和摩梭人當(dāng)中”(參見:格薩爾學(xué)刊[M].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11:161)。來(lái)概括其流傳地域的廣泛性。因?yàn)楦鞯氐膫鞑デ闆r不盡相同,因此史詩(shī)的傳播地域也是學(xué)者們關(guān)注較多的課題之一。域內(nèi)傳播方面,楊恩洪認(rèn)為,史詩(shī)的流傳是以德格、鄧柯為中心的青海、西藏、四川三省交界處的康區(qū)為發(fā)源地,向四周呈放射狀傳播,距離這一發(fā)源地越近,史詩(shī)流傳則廣泛,距離越遠(yuǎn)則反之[18]。此外,她也注意到新時(shí)期史詩(shī)傳播環(huán)境的變化:從過(guò)去比較偏遠(yuǎn)的傳統(tǒng)藝人說(shuō)唱的環(huán)境逐漸開始城鎮(zhèn)化,到人集中的地方[19]。謝繼勝認(rèn)為史詩(shī)所涉及的地區(qū)幾乎全部是游牧草原地區(qū)。史詩(shī)流傳在今天西藏自治區(qū)西北部和北部、四川省西南部、西部,青海全境,新疆東南邊緣地帶,甘肅西南部,河西走廊地區(qū)也被史詩(shī)滲透放射到蒙古地區(qū);出境則流傳到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帶[20]。韓喜玉認(rèn)為從分布的格局上看,《格薩爾》的流傳有若干個(gè)點(diǎn), 四條線和兩個(gè)面[21]。索南措認(rèn)為今天的格薩爾文化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流傳區(qū)域。一是以三江源地區(qū)為主的 “核心流傳區(qū)域”,另一個(gè)是后來(lái)隨著文化和商業(yè)的來(lái)往,格薩爾文化逐漸輻射和流傳到非牧業(yè)地區(qū)[22]。安惠娟的《近30多年來(lái)國(guó)內(nèi)裕固族〈格薩爾〉研究綜述》梳理了近30多年來(lái)國(guó)內(nèi)裕固族《格薩爾》研究狀況。王艷的《跨族群文化共存——《格薩爾》史詩(shī)的多民族傳播和比較》研究了《格薩爾》史詩(shī)跨民族傳播的情況,并探討了《格薩爾》史詩(shī)多民族傳播中的文化共存;姚慧的《〈格薩(斯)爾〉史詩(shī)跨民族傳播的音樂建構(gòu)——以扎巴老人,琶杰,王永福說(shuō)唱的“霍爾之篇”為例》研究的是跨民族傳播中的音樂建構(gòu)。域外傳播研究方面,王宏印和王治國(guó)勾勒出了《格薩爾》從藏族向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國(guó)內(nèi)的其他民族(主要是漢族和蒙古族)再走向世界的翻譯傳播認(rèn)知地圖。
(七)傳播特征研究
時(shí)代、地域、媒介等不同,《格薩爾》史詩(shī)的傳播呈現(xiàn)出不同的傳播特征,即“what characteristics”,學(xué)者們對(duì)這一領(lǐng)域也做了探討。袁愛中和楊靜分析了不同媒介形態(tài)下《格薩爾王傳》史詩(shī)傳播的特點(diǎn)。李連榮探討了史詩(shī)在西藏南北的傳播存在的差異,認(rèn)為隨著西藏南北生產(chǎn)生活模式的明顯差異,演唱形式的《格薩爾》史詩(shī)只流傳和分布在北部牧區(qū)地帶,而南部農(nóng)區(qū)的雅魯藏布江流域則很少有史詩(shī)的演唱形式[23]。丹曲從國(guó)內(nèi)外研究現(xiàn)狀、地理位置和地域文化等方面探討了《格薩爾》在德格地區(qū)的傳播特征。韓喜玉認(rèn)為《格薩爾》傳播過(guò)程中,具有與宗教信仰交織纏繞、眾多遺物遺跡印證、作為一個(gè)學(xué)術(shù)概念和學(xué)科體系以及有效利用大眾媒介的傳播特征[24]。張諾增尕瑪通過(guò)田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史詩(shī)《格薩爾》在海西地區(qū)的傳播特征為:①地域性。其大多數(shù)風(fēng)物遺跡和民間傳說(shuō)均與《霍嶺大戰(zhàn)》相關(guān);②本土化。蒙藏雜居地區(qū)《格薩爾》的傳播與變異,《格薩爾》傳入蒙古族之后,在藝人的創(chuàng)作、改編下,并吸收和融入了本民族及其周邊民族的民間故事,使史詩(shī)印上了本民族文化的印記;③滯后性。缺乏利用大眾媒體帶動(dòng)格薩爾文化發(fā)展[25]。楊恩洪和次仁平措均在訪談中談到,傳統(tǒng)的說(shuō)唱藝人一般都是到老百姓的帳篷里去說(shuō)唱,現(xiàn)代的說(shuō)唱藝人很多都是在說(shuō)唱廳里給大家說(shuō)唱,或者表演給觀眾欣賞。
(八)其他
韓喜玉闡釋了藏族《格薩爾》外向傳播原因,對(duì)“在什么情況下(in which circumstance)”作了初步闡釋;劉新利則關(guān)注《格薩爾》史詩(shī)的傳播與保護(hù)。張美分析了新媒體語(yǔ)境下史詩(shī)的傳播效果,是唯一關(guān)注“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的研究成果。臧學(xué)運(yùn)也在書評(píng)中談到史詩(shī)的對(duì)外翻譯傳播及其拓展,王倩從翻譯出版角度論及格薩爾的傳播。
二、存在問題
雖然上述成果均從不同方面對(duì)《格薩爾》史詩(shī)的傳播進(jìn)行闡釋,不同程度上推動(dòng)了史詩(shī)研究的發(fā)展,但還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傳播目的、傳播對(duì)象、傳播者及傳播內(nèi)容研究均存在盲點(diǎn)。迄今,傳播目的(in which aim)研究尚無(wú)成果出現(xiàn)。傳播對(duì)象(to whom)研究方面僅有于靜和王景遷提到了新時(shí)代《格薩爾》史詩(shī)受眾的變化。傳播者的研究局限在說(shuō)唱藝人上,僅有一篇文章關(guān)注到藝人以外的傳播者,而且藝人研究中缺乏對(duì)新生代藝人的研究。傳播內(nèi)容主要集中在關(guān)注藏、蒙、土、裕固等民族間的傳播內(nèi)容上,其他民族的《格薩爾》傳播內(nèi)容關(guān)注幾近空白;現(xiàn)有的傳播內(nèi)容研究多為個(gè)案研究,缺乏對(duì)史詩(shī)現(xiàn)有全部版本的宏觀研究。對(duì)傳播效果的研究也較為匱乏,當(dāng)然,傳播效果本身的受制因素較多可能也是學(xué)者們很少研究這一課題的原因之一。
其次,缺乏文化環(huán)境變遷對(duì)傳播內(nèi)容、傳播方式等因素的影響的研究。史詩(shī)流傳千年,文化環(huán)境不斷發(fā)生變化,尤其是在日新月異的今天,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及當(dāng)前的文化語(yǔ)境對(duì)史詩(shī)的傳播內(nèi)容及傳播方式等會(huì)產(chǎn)生什么影響?面對(duì)這些影響,史詩(shī)何去何從?均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第三,對(duì)史詩(shī)傳播地域關(guān)注不均衡。關(guān)注域內(nèi)傳播研究的成果較多,而關(guān)注域外傳播研究的較少。域內(nèi)研究方面,大部分學(xué)者的關(guān)注點(diǎn)多集中在青海、西藏、內(nèi)蒙古和藏彝走廊上,對(duì)其他地區(qū)的傳播情況關(guān)注較少。《格薩爾》研究發(fā)展半個(gè)多世紀(jì),尤其是《格薩爾王故事》被選入大中小學(xué)課本后(4)《格薩爾王的故事》被選入S版教材小學(xué)五年級(jí)語(yǔ)文課本下冊(cè)第二課。《格薩爾王全傳》(節(jié)選)被選入國(guó)防科技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大學(xué)語(yǔ)文》第四單元。,其傳播地域遠(yuǎn)遠(yuǎn)超出原來(lái)的“三個(gè)九”地區(qū),但目前的研究還局限在其產(chǎn)生地及周邊,甚至對(duì)“三個(gè)九”里的一些地方的研究也不充分。而域外的傳播研究,大多集中在英語(yǔ)國(guó)家,其他國(guó)家的傳播情況只是學(xué)者們?cè)陉愂觥陡袼_爾》的流傳地域時(shí)提到一些國(guó)家和地區(qū)名,但這些國(guó)家及地區(qū)的《格薩爾》呈現(xiàn)什么面貌,傳播方式有什么特點(diǎn)等,目前尚無(wú)研究。
第四,對(duì)非英語(yǔ)國(guó)家的史詩(shī)翻譯關(guān)注不足。目前的翻譯研究大多集中在《格薩爾》的漢譯、英譯及英語(yǔ)國(guó)家的接受語(yǔ)境等研究方面,但對(duì)于藏學(xué)研究處于世界前列的俄羅斯、日本、法國(guó)、德國(guó)等國(guó)家的《格薩爾》史詩(shī)的譯介,除了提及早期的譯介情況、幾個(gè)典型的史詩(shī)研究者及其成果外,其他方面鮮少論及。
第五,傳播方式、傳播形態(tài)和傳播特征研究視角單一。傳播方式、傳播形態(tài)和傳播特征的研究較為成熟,但多名學(xué)者的視角基本一致,缺乏新的研究角度。
三、未來(lái)研究趨勢(shì)
《格薩爾》史詩(shī)是人類口頭藝術(shù)的杰出代表。雖然其傳播研究還存在上述不足,但這些不足將會(huì)成為《格薩爾》未來(lái)研究的增長(zhǎng)點(diǎn)。未來(lái)的《格薩爾》史詩(shī)研究將呈現(xiàn)以下特征:
首先,史詩(shī)傳播目的研究會(huì)從無(wú)到有;傳播者、傳播內(nèi)容研究會(huì)產(chǎn)生新變化;宏觀研究也將問世。由于當(dāng)前有關(guān)傳播目的研究成果較為匱乏,未來(lái)將會(huì)有探討史詩(shī)傳播目的的成果問世。而新時(shí)代史詩(shī)傳播受眾的變化依然會(huì)是史詩(shī)傳播研究關(guān)注的課題之一。隨著史詩(shī)傳播者身份的多樣化,未來(lái)的史詩(shī)傳播者研究可能會(huì)出現(xiàn)以史詩(shī)研究者為研究對(duì)象的成果。傳播內(nèi)容方面,藏、蒙、土、裕固等民族外的其他民族間的史詩(shī)傳播也將會(huì)進(jìn)入學(xué)者們的視野。史詩(shī)傳播研究的不斷深入,也必將促使以史詩(shī)現(xiàn)有全部版本為研究對(duì)象的宏觀研究出現(xiàn)。
其次,文化環(huán)境的變遷對(duì)史詩(shī)傳播的影響將會(huì)成為未來(lái)研究迫切需要關(guān)注的課題。文化環(huán)境的變遷是史詩(shī)傳播研究中恒久彌新的課題,文化環(huán)境的變遷對(duì)史詩(shī)的傳播內(nèi)容、傳播方式等都會(huì)產(chǎn)生深遠(yuǎn)的影響,因此,文化環(huán)境的變遷對(duì)史詩(shī)傳播的影響也會(huì)成為未來(lái)史詩(shī)傳播研究需要關(guān)注的課題。
第三,史詩(shī)傳播地域研究在原有研究對(duì)象的基礎(chǔ)上向周邊擴(kuò)展。“三個(gè)九”里的地區(qū)和國(guó)家是史詩(shī)流傳較為廣泛的區(qū)域,但隨著史詩(shī)傳播方式的多樣化,史詩(shī)將會(huì)傳播到更遠(yuǎn)更廣闊的天地,同時(shí)“三個(gè)九”里的史詩(shī)傳播也會(huì)呈現(xiàn)出新的特征。因此未來(lái)史詩(shī)傳播地域研究方面,“三個(gè)九”依然會(huì)是研究的重點(diǎn),但也會(huì)出現(xiàn)以“三個(gè)九”以外地域的《格薩爾》傳播情況為研究對(duì)象的成果。
第四,譯介研究會(huì)進(jìn)一步深化。《格薩爾》史詩(shī)各語(yǔ)種的翻譯極大程度上促進(jìn)了史詩(shī)的傳播,但以往的研究中,對(duì)史詩(shī)的翻譯研究關(guān)注不足。未來(lái),西藏周邊及藏學(xué)研究較為先進(jìn)的國(guó)家和地區(qū)的《格薩爾》翻譯史、翻譯理念、流傳版本等研究也將是《格薩爾》傳播研究的新增長(zhǎng)點(diǎn)。
最后,傳播方式、傳播形態(tài)和傳播特征也會(huì)出現(xiàn)新的研究視角。隨著史詩(shī)傳播研究的深入,從新的視角探討《格薩爾》的傳播方式、傳播形態(tài)和傳播特征將是未來(lái)這些研究的必由之路。
四、 結(jié)語(yǔ)
《格薩爾》史詩(shī)不僅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cái)富。史詩(shī)懲惡揚(yáng)善、弘揚(yáng)真善美的主題,無(wú)論是現(xiàn)在還是未來(lái)都對(duì)人們的生活有著積極地意義。史詩(shī)的傳播研究不僅能促進(jìn)格薩爾學(xué)的學(xué)科發(fā)展,而且能推動(dòng)藏族文化在世界的傳播、提升中國(guó)文化在世界的感召力和影響力。雖然目前《格薩爾》史詩(shī)在國(guó)內(nèi)的傳播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但黨的十八大以來(lái),以習(xí)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弘揚(yáng)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全國(guó)多家科研院所及高校學(xué)者也都勠力同心、砥礪奮進(jìn),奮戰(zhàn)在《格薩爾》史詩(shī)研究的最前沿,相信在不久的將來(lái),《格薩爾》的傳播研究必將取得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又會(huì)進(jìn)一步促進(jìn)了史詩(shī)的流傳,未來(lái)《格薩爾》史詩(shī)必將“支芭盛茂滿天空,根兒蔓延遍大地”,必將造福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