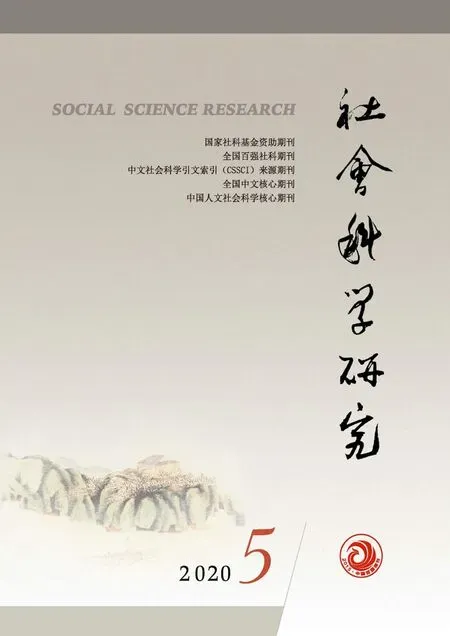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何以發生
——一種新結構政治學的分析
高奇琦
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表現。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取得了重要進展,然而,中國在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上取得的進展還非常有限。與自然科學相比,哲學社會科學對國家綜合國力支撐的效應會更加明顯。伴隨著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越來越走到世界的前列,這種對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創新的原動力會變得更加強烈。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在近幾十年來取得了重要進展,西方主流的政治學理論卻無法對中國的這些進展進行充分解釋。因此,中國學者需要在中國經驗基礎上進行更為抽象和深入的理論總結。筆者在之前的研究中提出了新結構政治學的分析框架。①在本文,筆者將運用這一框架對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生邏輯進行討論。筆者首先討論了中國治理現代化的中國經驗與西方理論解釋之間的緊張關系,然后在新結構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上試圖對國家治理的相關理論做進一步的概括。本文初步嘗試構建這樣一個中國特色概念體系和解釋框架。筆者希望在新結構政治學的框架下對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取得的成績加以總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國家治理的需求層次理論。
一、中國治理現代化的難度與成就
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本身面臨巨大難度,這主要體現在如下五個方面:第一,人口規模巨大。中國擁有著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數量。巨大的人口規模使得中國的國家治理與城市治理面臨非常大的壓力;第二,中國國土面積相對較大。并且,在中國的邊疆地區存在著許多生存條件較為惡劣的地方,這對中國的國家治理造成了嚴峻的挑戰;第三,中國有56個民族和5個民族自治區,并且大部分少數民族分布在邊疆。因此,民族的和諧與繁榮一直都是中國國家治理所要面對的重大問題;第四,中國是世界上擁有鄰國最多的國家,且周邊環境較為復雜。中國共擁有鄰國20個,其中14個為陸上鄰國,6個為海上鄰國。盡管中國已經解決了多數的邊界爭端,但依然存在邊界上的領土爭端,這也在客觀上增加了治理的壓力;第五,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三期疊加使得國家治理不能按照自然的節奏緩慢展開。由于中國的地區間差別比較大,所以不同地區所面臨的問題可能完全不同。譬如,發達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等所面臨的許多問題是后現代的問題,一些中部城市所面臨的問題是現代化的問題,而那些西部貧困地區面臨的則是前現代的問題。從整個國家層面看,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問題同時出現,使得國家治理需要從整體考慮。譬如,國家戰略一方面要考慮精準脫貧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要考慮科技創新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問題。②上述這些特點,使得中國的國家治理變得極為復雜。
盡管中國國家治理的難度非常高,但是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來也確實取得了許多重要成就:第一,中國用40年完成了西方近100年的發展。這一點從中美之間的簡要比較中可以看出。中國的GDP總量目前已經處于世界前列,2018年GDP總量約為900309億元,排在世界第二位。中國GDP在40年期間年均增長9.5%,這在世界各國的發展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而人均GDP則從1979年的2616元增加到2018年的59660元;第二,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取得了許多重要進步。在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和地鐵建設等方面,中國在世界上都具有相對領先的地位。③就建設的實際績效看,中國的實際水平與美國的實際水平在不斷接近。在通信設施建設上,中國在某些方面還優于美國。例如,截至2015年年末,中國手機用戶每百人擁有手機量為95.5部④,而美國則為89.86部;第三,在健康與教育等基礎公共服務建設上,中國也取得了重大進步。從一些重要的指標看,中美兩國在基礎公共服務建設上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人均預期壽命方面,美國從1960年的人均預期壽命69.7歲增加到2018年的78.54歲⑤,中國則從1960年的43.3歲增長到2014年的76.71歲。⑥在25歲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這一指標中,美國由1980年的11.9年增長到2018年的13.4年,而中國則從1982年的4.3年增長到2018年的13.9年⑦;第四,在科技進步等創新領域,中國目前也越來越接近世界發展的前沿水平。當前,中國科技發展水平正從全面跟蹤轉變為“三跑并存”。⑧在5G和量子衛星等先進技術上,中國的優勢也逐漸顯現出來。⑨整體來看,在極為復雜與困難的環境下,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取得如此的成績實屬不易。
二、西方政治學框架對中國治理成就的解釋困難
然而,中國在國家治理上取得的進展,并不能在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中得到充分解釋。在西方政治學知識中,“自由民主”的“歷史終結論”仍然是主導模式,并且越來越神圣化。即便是定量研究,其預設的前提也建立在這一假設的基礎之上。西方政治學的教科書和“經典作品”都體現出很強的一元知識的特征,即把代議制選舉、政黨輪替等看成是現代政治的唯一特征,并把美國的所謂“自由民主體制”看成是世界各國都應該追求和學習的最佳實踐。雖然很多學者和政治家對這一傾向都進行了批評,但是這種邏輯的影響仍然根深蒂固。在這種自由民主的定義下,中國仍然是未發生民主轉型的非民主國家。因此,按照西方主流理論的邏輯,中國不應該也不可能取得目前這樣的治理成績。從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論出發,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中國必然走向危機或崩潰。⑩中國的治理成績與西方主流理論之間產生了巨大張力,西方學者總是認為中國的發展不符合其常理,但實際上這是西方主流理論產生的問題。具體而言,西方主流政治學研究目前主要存在兩大問題:
第一,為了簡化和操作化知識最終導致知識出現偏見與極化。西方政治知識的重要特征是簡單易行,便于操作。譬如,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把民主的要義界定為選舉。之后,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等學者把民主進一步界定為政黨的兩次輪替。這樣的定義利于操作和測量,但是其對民主內涵的指向卻越來越狹窄。因此,當非西方國家用這一標準為其國家治理提供方案時,就會出現諸多正如喬萬尼·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言的“概念延展”(concept stretching)的問題。簡言之,西方的簡單性標準無法應對各國國家治理的復雜性。這種偏見與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礎上有著密切關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許多進展都建立在基督教知識的基礎上,或者是在與基督教神學的對話中產生的。簡言之,按照西方基督教神學的一神教傳統,信眾不能選擇第二種信仰。選擇其他信仰被認為是一種背叛。這種排他性的信仰特征和信仰知識絕對正確的認知使得這種一元邏輯深深地鐫刻在西方文化之中。
由于西方主流的政治學理論把現代化簡化為民主化,又將民主化簡化為政黨輪替。這種簡化知識的所謂“民主化”實踐并沒有促使發展中國家得到全面發展,而“民主化”所推動的過度社會動員最終導致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動蕩與社會問題。許多“第三波民主化國家”都遭遇了民主的困境或出現了民主的倒退。美國在冷戰后推動的“阿拉伯之春”等運動并沒有導致這些發展中國家治理狀況的改善,反而增加了政治動蕩,并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恐怖主義的蔓延。例如,敘利亞在2011年爆發內戰,至2015年大約有20萬人死于內戰,一半人口淪為難民。而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之后政治極不穩定,恐怖主義滋生,并在2015年6月26日發生了歷史上最為嚴重的針對游客的恐怖襲擊。
第二,過于強調知識導向而忽略實踐導向。以國家研究為例,西方的國家研究更多是知識論導向的,這就是西方有很多關于國家的研究、但關于國家治理的研究成果卻相對不足的重要原因。西方的國家研究一直在試圖解釋一些由其代表性學者提出的所謂經典問題。例如,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試圖回答,為什么歐洲會出現國家?戰爭和資本在歐洲國家構建中發揮了什么作用?這樣的研究同樣主要是知識導向的,而不是實踐導向的。蒂利的重要結論是,在歐洲國家形成和轉變的過程中,戰爭起了重要作用。蒂利的觀點被西方學術界看作是經典觀點,但是其作為實踐論的運用卻會出現許多困難。譬如,卡梅倫·蒂斯(Cameron Thies)對83個后殖民的發展中國家(1975-2000年)進行研究后得出結論,認為國家間競爭有利于國家形成汲取能力。同時,蒂斯認為,非洲等地的發展中國家中正在發生類似于歐洲式的戰爭促進國家形成的過程。實際上,仔細思考后會發現,蒂斯的結論是危險的。因為如果沿著這一結論的邏輯走下去,似乎國家構建必須以戰爭為前提。迷戀知識導向的另一種形式是過度理性化。過度理性化導致許多學者迷戀定量技術。西方的政治學研究出現了過度理性化的趨勢,即定量技術的絕對主導導致研究內容的空心化,專業性的學術研究越來越演變成一種數學游戲。數學程度的提高增加了解決方案的復雜性,提高了學術研究的門檻,但是對問題解決的助益似乎卻很難有明顯的增加。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政治學家喬萬尼·薩托利用過度自覺(overconscious)這一概念來批判那些過度使用定量方法的研究者。
因此,西方知識在生產的過程中,知識論與實踐論變得越來越對立。“理性人”假設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無知之幕”則是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正義論的核心假設。然而,“理性人”和“無知之幕”都是一種假設。換言之,西方的權威性研究建立在一些重要的假設之上,然而這些假設似乎與常識不相符合。盡管這些假設在研究中都已經成為毋庸置疑的慣例,但是從反思與批評研究的角度出發,我們似乎需要重新考察這些假設的合理性。中國學者的通常反問是,若假設都不正確,結論如何正確?這些假設希望構筑一個簡明的分析起點,然而正如查爾斯·泰勒所指出的,人是生活在復雜的情境之中的。另外,西方知識相對忽視實踐性理論。多數西方的經典研究更多注重解釋,而忽視操作性的建議。西方知識的優勢在于其往往可以窮盡所有的解釋范式,但是許多范式在實踐論上是相對虛弱的。例如,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通過對巴厘劇場國家圖景的描述,展示了國家通過儀式在想象與真實之間進行展示和表演的過程。格爾茨的這一作品被看作是文化主義流派的代表性作品。然而,這一理論對實踐很難有建設性意義。難道我們要鼓勵國家通過儀式和戲劇扮演來完成國家構建嗎?在知識論背景下,西方的解釋性知識越來越走向形式意義,而忽視了實質性內容的構建。
簡言之,西方的主流政治學研究存在兩大問題:一是在簡化知識的過程中生產出帶有偏見性的知識,二是過于強調知識導向而忽視了實踐導向。這兩點意味著西方的主流政治學理論不僅可能是有偏誤的,而且也是不實用的。這也是其不能解釋中國案例的重要原因。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討論了新結構政治學的分析框架。本文在這里就運用新結構政治學框架來對中國治理現代化的發生加以討論。
三、從新結構政治學看中國治理現代化的發生
新結構政治學的結構主要包括四大維度:系統、動力、行動者與過程。系統被分為時間條件和空間條件,二者共同構成結構的外部條件。動力是結構運行所遵循的規律,而行動者則作為整個結構的核心行為體。行動者在結構中具有一定的主動性,可以對結構的外部條件進行一定程度的建構,但同時這種建構仍然無法完全超越結構的外圍約束。這里的過程是行動者運用規律對系統進行建構和互動的過程。與結構功能主義相比,新結構政治學中的四大維度設計更加強調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平衡。與傳統的結構主義相比,新結構政治學更加強調行動者的主動性。行動者在中觀層面的表現可以影響到微觀條件下的個體行為以及宏觀條件的外部環境。從新結構政治學的框架來看,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如下特征:
從系統機制來看,核心行動者對外部條件的把握對中國國家治理具有重要意義。在時間特征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核心行動者對時代特征與自身發展階段的把握還是比較準確的,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出現了短暫的誤判,例如將中國發展的目標定位為“超英趕美”,這導致了50年代中后期的“大躍進”。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做出兩個重要判斷:一是對時代特性的判斷,二是對中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這兩個判斷使中國在之后的40年中始終圍繞經濟建設為中心展開工作。在空間特征上,核心行動者對中國的自然稟賦、國家規模以及外部環境在改革開放之后都有相對準確的認識。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充分利用了勞動力密集的特征,發展了以其為中心的制造業,這是中國現代化治理的重要支撐內容。另外,盡管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一段時期內采取出口導向的戰略,但是由于中國國家規模巨大,所以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采取拉動內需與出口導向并重的戰略,由此推動并產生了繁榮的內部市場。
從動力機制來看,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在效率與公平、集權與分權的動力機制的不斷平衡中發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公平性更加容易實現,但是因此卻導致效率低下的問題。因此,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就是通過市場化的力量激發中國社會的效率與活力。例如,國企職工的下崗被看作是“打破鐵飯碗”,這是促進國家治理由公平轉向效率的典型例證。對效率的強調使中國經濟增長得以在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以每年約9.5%的速度增長。然而,在效率被充分激發后,公平的問題便逐漸顯現,例如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關于維權的社會事件逐漸增多。中國在20世紀末就開始注重對公平的建設,在1998年之后逐步建立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同時稅費改革也使得農民的負擔日益減輕。另外,近年來中國政府也在積極推動精準扶貧與反腐敗,這些都是推動中國從高效率向公平轉變的重要舉措。中國國家治理在集權與分權之間的平衡也是中國國家治理中的重要經驗。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權力相對集中。因此,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就是從相對集權向分權的方向發展,例如給予地方政府較大的積極性,以及給予民間社會更多的活力。然而,過度分散化會導致新的問題。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央政府啟動了一些權力集中的舉動,例如加大中央財權的分稅制改革,這種調整使得中國可以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全球化流動的背景下,民眾的利益日益碎片化。如果不能有效地整合這些碎片化的利益,那么國家治理就可能面臨斷裂或崩塌的危險。并且,在新媒體迅速發展的今天,每個人都能夠成為新聞發布的中心,這種自媒體日益顯著的特征對傳統的國家治理也構成了非常嚴峻的挑戰。因此,中央政府一直試圖在權力的集中與分散之間尋求平衡。例如,近年來,一方面中央政府采取了鼓勵創新、負面清單以及簡化公司準入門檻的措施,但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對恐怖活動和意識形態安全等行為的管控。這就是國家權力集中與分散之間的平衡,同時這也是中國一直所強調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內容。
從行動者來看,中國的國家治理則在行動者之間形成了多元互動的機制。從組織視角看,政黨是中國國家治理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方向進行了把握并在關鍵時刻進行重大決策。同時,國家機關越來越職業化與現代化,并成為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關鍵保障力量。社會組織則是中國國家治理活力的重要來源。這三大類組織各司其職,在一個積極互動的背景下對中國的國家治理形成合力。從個人視角來看,一些先進的行動者,如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等對時代的把握以及在重要關頭的決策至關重要。但同時,普通民眾在這互動框架中保持積極合作而不是消極拒斥的態度,這也是中國國家治理順利開展的群眾基礎。先進行動者通過政黨、國家機關與社會組織對普通民眾發揮了重要的方向引導功能。而普通民眾則通過充分發揮自身潛能,并積極主動地參與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建設。
從過程來看,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在重要的歷史趨勢面前都有較好的把握。中美建交與改革開放是在雙向互動的過程中發生的。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推動了中國與美國的建交,同時改革開放也是在中美關系逐步走向正常化的背景下發生的。因此,1979年中美建交是中國治理現代化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歷史關節點。改革開放也促使中國向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管理和發展經驗,這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得以發生的重要條件。另一個重要的歷史關節點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在2001年之前,中國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國際經濟治理的分工合作。然而,中國參與的程度比較有限,西方國家也將中國標簽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從而對中國的產品采取貿易歧視等政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使得中國可以進一步學習國際上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并更多地引入國際資本,同時也使得中國產品可以在世界范圍內與他國商品展開更加充分的競爭。
整體來看,從新結構政治學的分析框架出發可以更加完整地把握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經驗。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生是在系統、動力、行動者與過程這四方面要素綜合互動的基礎上實現的。首先,核心行動者清楚地認識到時代發展的主題,秉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并且,在對自身要素特征充分認識的基礎上提出發展戰略。其次,中國一直試圖在集權與分權、效率與公平之間實現動態平衡。這使得中國在保持活力的基礎上又不至于陷入危機。再次,中國共產黨的方向引導、國家機關的現代化與活躍的社會組織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這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行動者基礎。最后,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中把握住了兩個最重要的全球性趨勢。一是中國通過中美關系正常化在美蘇爭霸的末端加入了全球化進程之中。二是通過加入世貿組織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治理。
四、新結構政治學視野中的中國經驗
上一部分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生史進行了粗線條的描述,這里需要對其中的中國治理經驗做進一步的總結。在新結構政治學的框架之下,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經驗可以做如下總結:
第一,從系統來看,對時代特征、發展階段以及自身稟賦的客觀判斷使中國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特別強調基礎性條件的重要作用。盡管,中國在幾十年的發展中也面臨過許多困難,例如蘇東劇變對中國的沖擊,但是中國一直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所處的發展階段,并在自身空間稟賦的基礎上加強進一步發展的基礎性條件。中國對基礎性條件的強調,非常明顯地表現在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程中。中國有著很強的唯物主義和實用主義傳統,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就特別強調基礎設施的重要性。
第二,從動力來看,在效率與公平、集權與分權之間的平衡使得中國極為強調秩序穩定的重要性。將各國的情況簡單比較就會發現,中國擁有多項超大型的記錄。譬如,2018年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比例為18.3%。2018年世界上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型城市有46個,而中國有15個。再如,2018年中國有1660萬的貧困人口。另外,雖然印度、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等國的人口數量也較多,但是這些國家現代化的程度還相對不高,即現代化對這些國家普通民眾的動員還未完全完成。按照亨廷頓的理論,普通民眾的需求被現代化動員起來之后,便會對政治體制形成巨大的壓力。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卻處于急速的現代化之中,民眾的需求被動員起來,同時這種需求是超大規模的,這都給國家治理帶來了巨大壓力。超大規模的復雜性治理使得中國特別強調秩序和穩定的意義。例如,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在進入21世紀之后,維穩便逐漸成為一項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
第三,從行動者來看,中國在強調執政黨引領功能的同時,也強調國家的制度保障以及社會的活力功能。中國共產黨的強大動員能力使得中國的超大有序治理成為可能。譬如,當社會出現嚴重的奢靡之風后,中國共產黨率先在黨內采取了“八項規定”。“八項規定”的實施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進步運動。在“八項規定”之后,奢靡和浪費等情況大大減少。在執政黨的引領功能之外,國家機關的現代化與專業化則是中國國家治理行政效率得以提升的重要內容。同時,活躍的社會組織則是激發國家治理活力與創新的重要支撐。
第四,從過程來看,層次推進與漸進改革使得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得以穩步發生。不同于休克療法,中國改革是漸進改革。具體而言,漸進改革有如下幾點特征:一、點式試驗,即選擇某一個或幾個城市或地區進行試點,這樣降低了試錯的成本,同時有效且快速地推動了改革,經濟特區、自由貿易區等試點都采取了這一模式;二、線面鋪開,即把試點成功地區的經驗先按照線和面的方式逐層鋪開,把試點的成功經驗進行推廣和復制;三、雙軌運行,即把正在進行的改革與傳統的體制機制放在同一個秩序下運行,這樣既保證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和民生的基本保障,也在同時漸進地推進改革,尋求改革與傳統的磨合和最大公約數;四、地方競賽,即通過地方競爭保證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活力,并形成了在國家統一的穩定框架下、地方政府競相采取改革措施的新局面。
五、治理階梯:國家治理的需求層次理論
近年來國內關于國家治理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現。這類成果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方面希望在國家治理的概念和內涵上尋求突破,另一方面則力圖總結中國國家治理的經驗。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對國家治理的理論關注不僅僅局限在政治學的范圍之內,許多其他學科的重要學者也積極參與國家治理的研究和討論。總體來看,對中國國家治理的未來方向的討論較少。筆者認為,國家治理相關基礎理論的進一步提煉和完善需要建立在新的理論范式的基礎上。從新結構政治學的視角看,因為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不同,所以要根據其發展階段來設計和規劃國家治理的重點。國家治理的第一階段可看作是國家建構的馬基雅維利時刻,側重于搭建國家的整體治理結構。第二個階段則是在國家建構的基礎上,各方面都有較大程度的發展,重點體現在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的建設上。鑒于此,筆者在新結構政治學的基礎上提出國家治理的需求層次理論。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人的需求層次理論。實際上,國家治理的需求也存在層次。筆者認為,國家治理的需求存在基礎、價值和可持續三個層次。由于發展階段不同,不同國家所面對的主要治理問題也明顯不同。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地考慮基礎性需求,而發達國家則需要更多地考慮價值性和可持續性的需求。鑒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存在階段性特點,需求層次理論將國家治理的目標進行階梯化劃分,這樣可以促進各級目標逐級穩步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實現所需要的是逐步推進,而不能是直接跨越基礎階段的跨階段發展。
基礎性指標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剛剛完成民族獨立或處于現代化初期的國家首先需要完成基礎性指標的建設。那些被西方指稱為失敗國家的國家實際上并未有效完成基礎性指標。筆者認為,基礎性指標主要由設施、秩序和服務三大類指標構成。設施(即基礎設施)是任何活動所必須依靠的物質性條件。秩序是使得基礎設施和社會活動正常開展的保障環境。服務(即基本公共服務)則是國家正常運行所依賴的最低保障條件。例如,福山以艾滋病在非洲的蔓延為例,討論了貧困國家缺乏國家能力的問題。這一問題的實質是這些國家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基礎設施、秩序和公共服務。換言之,這些國家的基礎性條件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建設。中國國家治理中的一個重要經驗是,中國在基礎性條件上進行了非常扎實的建設。在這些基礎性指標建設的過程中,有效政府是前提條件。
價值性指標需要在基礎性指標基本完成之后再有效推進。例如,亨廷頓也強調政治參與是發展的副產品。筆者認為,價值性指標主要由公開、公平和公正三大項內容構成。公開就是透明。公平是最小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公正是針對婦女、兒童、殘疾人等少數群體的正義。當然,這三個價值的實現也存在階梯。首先要通過信息公開讓公民對政治過程有知情權,然后就需要在平等的意義上推進那層最薄的公共福利的均等化,最后再通過差別原則對少數群體的弱勢地位進行補償。在現代化初期,公開透明、權利平等和機會平等是最先追求的目標。伴隨著現代化程度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保障弱勢群體的差別原則逐漸成為人類價值追求的目標。
價值性指標的實現很容易導致持續性的不足,因此需要持續性指標來對價值性指標進行平衡和調整。持續性指標包括效率、環保和創新。價值性指標往往容易導致效率下降,因此重新強調效率便非常有意義。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是國家治理持續推進的重要條件,而創新是推動社會不斷進步的核心內容。這三項內容也需要層級推進。效率目標首先是最重要的,一個低效的國家治理系統肯定是無法持續的。在效率的基礎上,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就會自然成為接下來追求的持續性目標。之后,效率和環保的實現都高度依賴技術、制度和治理方式的不斷創新。
西方的民主化理論是超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應該首先建設好基礎性指標,然后再考慮價值性指標。經過工業化的發展,發達國家的基礎性條件已經非常完善,所以其在考慮國家治理問題時,往往會忽視這些在實際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基礎性條件。例如,基礎設施對于國家治理至關重要。沒有必要的基礎設施,國家力量的投射都會成為嚴重的問題。因此,這些基礎性條件對發展中國家至關重要。整體來看,國家治理的實踐論應該是一種層次理論,即先從基礎設施、秩序和基本公共服務入手,在這些條件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引入公開、公平和公正等價值性指標。同時,在引入價值性指標后可能會帶來持續性的問題,所以在價值強調之后,可持續性發展便需要被提上議程。從更為形象的角度來表述,國家治理的需求層次理論可以被總結為“治理階梯理論”,即國家治理的實現類似于爬梯子,需要一層一層地往上面走。

圖1 治理階梯理論
治理階梯理論與新結構政治學的框架是相互融通的。治理階梯理論反映了新結構政治學四大要素的核心內容:第一,該理論強調國家的核心行動者應該首先考慮自身所處的時間與空間背景。在時間背景中,核心行動者首先要考察自身所處的發展階段。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所面對的問題是不同的。發展中國家所面對的更多是基礎性問題,而發達國家面對的更多是價值性問題與持續性問題。任何一個國家在制定國家治理發展大戰略的時候,都要對自身所處的時間和空間特征做比較準確的判斷。第二,穩定的秩序對于國家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而在重要的要素如效率與公平、集權與分權之間的平衡則有助于秩序的穩定。任何一個要素的極化都非常有可能導致不穩定情況的出現,并最終會阻礙國家的健康發展。第三,多元行動者的良性互動對治理目標的階梯實現具有重要意義。盡管各國的政黨制度不同,但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治理都需要在政黨、國家與社會三者良性互動的基礎上實現。只有這三者良性互動,才能保證公開、公平和公正三大價值的有效實現;第四,國家治理目標的實現需要逐級地漸進推動,而不能直接跨越基礎階段而達到更高的階段。
六、結語
新結構政治學還試圖將中國國家治理經驗與中國文化的要義結合起來。在筆者看來,中國國家治理經驗的要義是平衡和調和。平衡是一種內在觀念,調和是一種解決方案。譬如,在經濟實務領域經常使用的“宏觀調控”就是平衡與調和的完美結合。宏觀調控是指從結構的整體性上對細節進行微調,這與西方的休克式療法是不同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新結構政治學是對中國國家治理經驗的總結和再闡發。更進一步講,新結構政治學不僅是一種分析框架,同時也是一種實踐框架。在新結構政治學與中國國家治理經驗的基礎上,筆者提出了國家治理的需求層次理論,即國家治理的目標本身存在層次,并且目標的實現需要逐級推進。整體來看,需求層次理論強調,行動者要對自身的發展階段與自身稟賦有清楚的理解,強調穩定的秩序在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治理目標的逐級推進。可以說,需求層次理論是新結構政治學在國家治理領域的一個相對抽象的理論化表達。當然,行動者在具體的國家治理實踐中仍然需要回到新結構政治學的應用性框架,因時制宜和因地制宜地考慮自身的治理問題。在時間、空間等約束性條件下,行動者要找到自己在歷史趨勢中的位置,在自己經驗拓展的基礎上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案,并通過調和來實現自身在歷史趨勢中的價值,這便是新結構政治學的要義。通過這種知識構建和傳播,新結構政治學或許可以為發展中國家的國家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新結構政治學是中國學者參與思考和構建中國本土解釋框架的一個初步的粗淺嘗試。筆者希望用新的分析框架對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成就加以解釋,并將其提煉為更具普遍性的理論知識。目前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中國正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其中承擔的責任會更加重大。面對國際上各種社會思潮紛繁復雜的新形勢,中國學者有責任在中國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提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向系統的話語體系和學術體系靠近。通過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的概念和知識體系的原創性發展,中國學者可以逐步與世界上各類交鋒的代表性觀點進行對話,并為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進一步的理論支撐。
① 高奇琦:《新結構政治學的傳統文化之源——一種〈周易〉的分析框架》,《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高奇琦、張鵬:《英國“脫歐”與歐洲一體化前景:一種新結構政治學的分析》,《探索》2019年第1期。
② 例如,中央對上海最新發展的定位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參見《上海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方案》,《人民日報》2016年4月16日,第1版。
③ 《創造高鐵的“中國標準”——寫在京津高鐵開通運營650天之際》,《人民日報》2010年5月13日,第5版。
④ 《2015年通信運營業統計公報》,2016年1月21日,http://www.miit.gov.cn/n1146312/n1146904/n1648372/c4620679/content.html,2020年3月14日。
⑤ ⑥ The World Bank,Life Expectancy at Birth,Total(years),July 1,2020,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DYN.LE00.IN?,July 23,2020.
⑦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December 9,2019,http://hdr.undp.org/en/content/human-development-report-2019,June 9,2020.
⑧ 《我國第五次技術預測顯示:“領跑加并跑技術”接近一半》,《中國科技財富》2016年第8期。
⑨ 《揭秘全球首顆量子衛星》,《人民日報》2016年8月16日,第12版。
⑩ Gordon Chang,“Halfway to China’s Collapse,”FarEasternEconomicReview,vol.169,no.5,2006,p.5;Minxin Pei,“China’s Governance Crisis,”ForeignAffairs,vol.8,no.5,2002,p.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