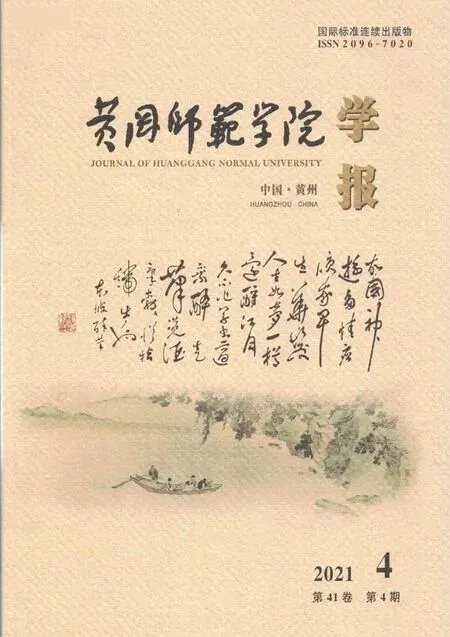鄂東本土影視作品中的人物塑造策略
張才剛
(湖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0)
鄂東獨特的地理與歷史環境,造就了兼具保守與開放、獨立與包容特性的地域文化,也賦予了本土人物鮮明的性格特質。從蘇東坡到當代鄂東作家群,從李時珍、畢昇到李四光,從邢繡娘到歷代黃梅戲表演者,從禪宗開創者到功勛卓著的鄂東革命者,在歷史時空中交相輝映的“鄂東人物”不僅清晰地勾勒出鄂東文化的演進脈絡,還為地域生活方式與人文精神做了最好的注解。已經被經典化、符號化的鄂東人物,已然成為本土物質生活與價值觀念的綜合載體,同時也為文學、戲曲以及現代影視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可以說,“自古光黃多異人”中的“異”,指的就是一種深植于鄂東鄉土之中的性格養成。鄂東本土影視作品的審美意蘊與傳播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創作者對這種“異”的藝術化發掘與影像化闡釋。《鐵血紅安》《黃梅戲宗師傳奇》《全城高考》等本土影視作品,表現的雖然是不同歷史語境中的鄂東人物,但觀影者依然能夠從他們身上感受到源于“大別山水”的個性氣質,折射出創作主體相對一致的審美尺度和藝術手法。以“人物”為線索,能夠窺見鄂東本土影視的敘事策略與價值追求。
一、在鄉土情懷與革命理想的交融中再現“紅色人物”
鄂東地域與歷史語境中,“紅色人物”具有尤為特殊的意義。他們既是特定歷史時期民族大義與革命理想的踐行者,也是地域生活方式及其生存理念的傳承者——“鄉土氣息”與“革命情懷”的交互滲透,塑造出“鄂東革命者”這個特定的人物群體,也建構起“將軍縣”這一宏大意象。對于文學與影視藝術而言,“放牛娃團長”韓東山、“私塾先生黨代表”王樹聲、“王瘋子”王近山等鄂東革命者無疑是十分難得的表現對象:這些極富個性色彩的紅色人物,不僅能夠有效激發創作者的藝術靈感,還為其提供了足夠豐富的故事與符號資源。在鄂東文學與影視藝術實踐中,本土作家與影視創作者對紅色人物塑造有著高度共識:他們往往不會高調宣揚革命人物的成就與功績,而是將其置于鄂東自然地理與鄉土生活場景之內,為個體行為方式、思想觀念甚至命運走向的合理性提供成分的“證據”。這一人物塑造策略,摒棄了“高大全”的傳統模式,由此催生出專屬于鄂東地域的影視形象。對于觀賞者來說,能夠在自己熟悉場景中“遇見”的革命英雄,其性格、思想與行為更容易理解,整體形象也顯得更加可親、可信。這就印證了黑格爾的觀點,“藝術作品之所以創作出來,不是為著一些淵博的學者,而是為一般的聽眾,他們須不用走尋求廣博知識的彎路,就可以直接了解它、欣賞它。”[1]鄉土鄂東代表的是一種世俗化力量,它既是藝術形象生成的本源,也為影視創作者與鑒賞者之間的相互理解創造了空間。
鄂東本土革命題材電視劇《鐵血紅安》中“劉銅鑼”的形象塑造,明顯受到了《亮劍》中“李云龍”的啟發。“李云龍”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將世俗生活的質感融入到了人物身上,使得鄉野之中生長出來的“痞氣”與投身民族救亡時的“大義”結合起來,塑造出一個符合普通中國人審美認知的革命者,引起觀影者強烈的情感共鳴。“劉銅鑼”之所以被譽為“又一個李云龍”,正是因為其實現了鄂東鄉土氣質與宏大革命場景的有機統一,并在人物的語言行為與性格命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使其成為了鄂東革命者群體的典型代表,迎合了現代觀眾多樣化、個性化的審美趨向。正如有研究者所說,“劉銅鑼是紅安地區的革命符號,被劇作家準確抓住了。”[2]面對這位“敲著銅鑼打沖鋒、光著膀子拼刺刀”,從占山為王到下山革命,最后成長為開國將軍的人物,觀影者(尤其本土民眾)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因為他們與革命者有著同樣的鄉土生活經驗。相較而言,在《夜襲》《旋風司令》《驚沙》《王樹聲征戰豫西》《胡奇才痛殲千里駒》等以鄂東革命者為對象的影視作品中,表現的大多是主人公離開鄂東后的斗爭經歷,其地域性格并沒有得到太多的展現,觀眾甚至難以從作品中識別其真實的地域身份。
我們將《鐵血紅安》視為“黃岡出品”中本土革命題材的代表性作品,正是源于其在人物塑造中表現出來的獨特個性,它使得“鄉土鄂東”與“民族情懷”有了交互融合的鮮活載體——即主人公“劉銅鑼”。《鐵血紅安》中,另一位人物“李坪山”既是老師又是紅軍師長,盡管他集滿口“子曰”、喜歡引經據典的“夫子”與戰場上的指揮者兩種相互矛盾的形象于一身,在鄂東文化語境中卻并不顯得突兀。在這一人物身上,人們依稀看到了“木匠司令”“放牛娃團長”“私塾先生黨代表”的影子。同樣以黃麻起義為背景的電視劇《紅槐花》,由本土作家何存中的文學作品《門前一棵槐》改編,故事地點設定在“麻安縣”,男主人公“程牛兒”原本就是大別山中一個獵戶,以“牛兒”為名的原因是山里人覺得“賤名好養活”。他愛恨分明,敢于掙脫民間習俗與宗族勢力的束縛,唱著“高高山上一棵槐”的鄂東民歌搶親,后參加革命并成長為一名有勇有謀的紅軍指揮員,及至成為開國將領。在何存中另一部長篇小說《太陽最紅》中,主人公“王幼勇”的“敵人”就是自己的親舅舅,使他不得不深陷于家族情感與革命理想的糾結,最終在取義成仁中獲得升華。由此可見,鄂東地域影視與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有其內在“慣性”,創作者始終力圖在“鄉土”與“革命”的沖突之中尋求調和之策,為觀眾(讀者)展示一個獨一無二的鄂東革命者形象,如“李云龍”一般鮮活。正如本土作家何存中所言,他筆下的人物“沒有絕對的好與壞,每個人都向往光明,只是信念不同”[3]。
在以往的革命題材作品中,創作者往往更加傾向于塑造宏大的歷史場景與“高大全”式的人物,以滿足觀眾尋找英雄、戰勝敵人的心理期待。這一傾向,在文學創作中早就有所顯現,“中國文學久來熱衷于向歷史邀寵,寄希望于歷史的參與而使作品偉岸光亮流芳百世,特別是大歷史,越大越好。這幾乎已成一種病,一種追求向往的不病之病;也可說,這是一種自宮,是中國文學把‘歷史’當切刀對自己的文學細胞、文學生長力進行的‘閹割’”[4]。正因為如此,磨滅了許多革命文藝作品應有的“人性”光芒,其人物難免千人一面。鄂東革命者之所以具有很強的可塑性,正是因為他們身上天然交融的“鄉土氣質”與“革命情懷”,這兩大性質完全不同元素一旦碰撞到了一起,就會催化出出人意料卻在情理之中的藝術形象。如同《鐵血紅安》與《紅安兵謠》的編劇夏啟發所說,劉銅鑼除了是將軍們的縮影,更是紅安當地民風的縮影,“他代表了紅安人的共同屬性:執著、拼搏”[5]。在他們身上,鄂東生活的經驗已然融入了其革命行為與精神之中,銅鑼、布鞋乃至于紅苕都不再只是“身外之物”,而變成了人物生存環境、成長歷程以及革命意志的象征物,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顯示出特有的符號價值。對于現代觀眾而言,這種立體化的人物塑造方法更接近于歷史真實與生活真實,也更能體現地域性格對個體所產生的“規約”——使得觀眾在影像空間中能夠清晰地分辨出“鄂東人物”。
二、在文獻史料與民間傳奇的平衡中塑造“歷史人物”
鄂東既是“紅色圣地”,亦是“名人之都”。相對于鄂東革命者有史可循、較為清晰的形象,包括蘇東坡、李時珍、畢昇、邢繡娘以及禪宗祖師在內的歷史名人,大多并無確切的文獻記載可供查詢,其形象顯得模糊而又飄忽。正是因為這一特質,使得鄂東歷史人物在文學、戲曲乃至于民間傳說中具有獨特的價值,不同時代的“創作者”都可以將自己的情感植入其中,豐富甚至重構符號與故事系統,使經過“加工”與“再造”的人物更加符合特定的價值取向與審美標準。這里所謂的“創作者”,既包括專業的文學作家與戲曲表演家,更包含無數生活在各個時代的本土民眾,他們的創造活動賦予了鄂東歷史人物以新的生命。沿著這一路徑觀察現代鄂東影視生產,其中大量歷史人物題材作品的出現并非偶然,而是本土生活與藝術實踐在新的媒體語境中的延續,其生成的內容產品更加適應“讀圖時代”文化消費的需求。審視鄂東歷史人物題材影視作品,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多元化主體介入帶來的影響:影像化呈現出來的“鄂東人物”,在其活動軌跡、主要貢獻以及命運歸宿等大體上遵循有限的文獻記載,而在生活場景、社會關系、經典故事等層面,則更多地取材于民間傳說。這一人物塑造策略,既展示出對歷史事實尤其是人物歷史定位的尊重,也獲得了生動、鮮活的故事素材,符合大眾的審美期待。
對于鄂東人物的文獻記錄,主要包括正史、地方志以及家族族譜等。囿于文獻史料的體裁形式及表達方式,其內容大多是梗概式的,一般以紀年的形式呈現人物的生辰、經歷與歸宿,缺少故事與場景等細節。其中,與李時珍有關的記載,主要見于《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列傳第一百八十七》與《進〈本草綱目〉疏》之中,前者內容為概述其出生、治學、成書、去世,后者主要講其子進獻《本草綱目》的原因并頌揚父親著述的艱辛過程,均十分簡略。對于活字印刷術發明者畢昇的記載更為簡略,僅見于沈括的《夢溪筆談》,書中稱畢昇為“布衣”,且只用了274字描述了活版印刷的流程,而對其籍貫、生平等并沒有介紹;1990年英山縣五桂村畢家坳發現一塊刻有“畢昇神主”的宋代墓碑,經專家鑒定認定為畢昇墓,可為其籍貫、生平的佐證。至于黃梅戲“一代宗師”邢繡娘,目前所見除了地方志、家族族譜對其個人經歷有一些記載之外,其他主要是流傳下來的戲曲文本。禪宗開創者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其個人經歷與思想主張則主要見于佛教典籍;基于宗教傳播的需要,這些記載本身就帶有一定的傳奇色彩,并不都是史實。
相較于史料記載的單調與簡略,民間傳說的內容顯得更為豐富:不同時代的民間講述者將其情感、理想與期待投射到了特定鄂東人物身上,衍生出了結構完整且具有傳奇色彩的故事系統,為職業作家與現代影視生產者提供了極佳的再創作資源。鑒于人物形象與故事線索的復雜性,鄂東歷史人物題材多以長篇電視劇的形式價值呈現,其中包括已經播出的《黃梅戲宗師傳奇》《大明醫圣李時珍》和完成劇本創作的《禪宗》《畢昇傳奇》,篇幅均較為宏大。《黃梅戲宗師傳奇》中,邢繡娘經歷愛情、逃荒、斗惡霸、告御狀、收徒傳戲直至被御賜“黃梅名伶”,成就一代宗師;《畢昇傳奇》中,畢昇受到同門的刁難與陷害,被官府威脅、逼迫,卻始終不忘初心與使命,最終被封為“大宋活字神”;《大明醫圣李時珍》中,亦加入了情感糾葛、正邪斗爭以及宮廷較量等內容,以塑造一個義勇雙全的“大明醫圣”形象;《禪宗》劇本以人物為主線分為《禪宗四祖》《禪宗五祖》《禪宗六祖》三部,分別講述道信、弘忍、惠能三人的故事,其主要內容來自文史資料、佛教典籍以及民間傳說。這些本土影視作品在故事建構以及人物形象塑造上表現出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創作者在不違背宏觀歷史真實的基礎上,明顯引用與吸收了大量民間敘事的成果,塑造了一個可感知的影像化“鄂東人物”,更新了人們即有的認知。
對于文學、戲曲與現代影視創作來說,片段式或者紀年式的文獻記載雖然不足以直接轉化成為藝術產品,但其對鄂東人物本土身份及歷史地位卻產生了一種不容置疑的確定感,使得李時珍、畢昇、邢繡娘與禪宗祖師成了最為顯著的地域符號,能夠跨越時空的局限反復出現在不同時代的文藝產品之中,獲得不斷拓展、衍生與更新的機會。不論故事系統如何演繹,歷史文獻中呈現的內容依然是其源頭與根本,在敘事系統中發揮著“穩定劑”的作用,民間傳說的演繹同樣必須遵循其所設定的歷史語境,不至于產生大的偏離。與文獻記載的客觀性與粗線條相比,民間話語系統中的鄂東人物則顯得豐滿、生動得多,更加適合進行藝術化再創造。與文獻記載賦予的確定性與權威性相比,民間傳說中的鄂東人物則能夠為大眾帶來一種獨特的神秘感與親近感,更加符合其心目之中的“理想狀態”。在影視傳播過程中,這種基于文獻記載與民間演繹基礎上的藝術形象再創造,既可以使觀眾在歷史語境之中產生一種明確的真實感,又能夠讓其在民間視角與生活場景之中形成強烈的代入感;“真實感”與“代入感”的融合,無疑有利于鄂東人物的接受與認同。當然,藝術創作雖然強調“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對于地域身份與歷史定位已經十分明確的人物而言,關鍵還在于掌握演繹的限度與邊界;一旦為了追求娛樂化效果而出現“過度創作”的現象,將會損害歷史人物的整體觀感與社會認同。
三、在現實時空與人文傳統的交匯中建構“現代人物”
鄂東本土影視作品中的現代人物形象大體上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全城高考》《夢行者》《守護童年》《不愿沉默的知了》《馬蘭花開》等作品中虛構的人物,另一類是《西河十八灣》《英雄無悔》中以當地先進個體為原型的寫實性人物。前者雖然大多在鄂東地區各縣市拍攝制作,但人物身上的時代標簽十分明顯:《全城高考》中面臨人生抉擇的青少年學生、《守護童年》中替罪犯子女尋親的女志愿者、《夢行者》中三個回鄉創業的本地青年、《不愿沉默的知了》中通過個人奮斗走出大山的男主人公、《馬蘭花開》中的共產黨員選調生馬蘭等,無一不是當前時代中某個特定群體的縮影,其形象意涵顯然已經超越了地域與個體的層面。在《全城高考》這部典型的“黃岡出品”中,創作者將“高考故事”設置在了有著“教育名城”之譽的黃岡,并將一系列鄂東經典景觀符號呈現在影像空間中,試圖借此強化觀影者對“高考神話”發生地的感知印象。應該來說,將師生群體置于“黃岡”這個獨特人文環境中,的確使其獲得了較為鮮明的地域身份,同時也使“高考”主題具有了特定的意義指向,更易于被觀眾所理解與接受。在這一具體語境中,黃州古城、黃岡中學、東坡赤壁等本土經典景觀所承載的鄂東傳統文化,與現代教育制度之間產生交匯碰撞,為解讀師生群體提供了一個多維、立體的視角。由此建構的影視人物,其語言、行為、心理等已然超越了純粹地域的局限,成為時代背景中某個群體的縮影。
基于主流價值傳播的需要,《西河十八灣》《英雄無悔》等本土電影中的主人公均以現實人物為原型,具有一定的紀實色彩。《西河十八灣》以2018年全國脫貧攻堅獎獲得者為原型,《英雄無悔》則以浠水民警“撲爆哥”吳俊為原型,主要講述他們的典型事跡。這種以先進典型為原型的人物塑造模式,符合主旋律影視作品的基本創作導向。由于這些人物先期已經通過媒體報道獲得了廣泛的知名度,其形象與故事相對確定,藝術化再創造的空間比較有限。在具體藝術實踐中,創作者往往通過本土化的場景設置,尤其是經典景觀、建筑以及器物的影像化再現來標識人物地域身份;與此同時,在不損害人物形象以及典型意義的基礎上,圍繞典型人物的行動軌跡創設必要的矛盾沖突,為其形象與精神的雙重建構提供支撐,借此增強人物的可信度與感染力,使他們作為主流價值觀踐行者與弘揚者的功能得到強化。從宏觀的社會背景來看,這些典型人物更多地被視為時代發展的產物,創作者更期待觀眾能夠從他們身上看到特定社會群體的共同屬性,以此實現價值引領目的。或者說,時代背景的強化使得這些鄂東典型人物具有了更為普遍的示范作用,其地域身份則附著于其上、融合于其間,為其真實性提供支撐。與《全城高考》中虛構的人物一樣,經過藝術創造的典型人物同樣獲得了超越個體與地域界限的能力,成為特定時代的一面鏡子。
影視作品對現代鄂東人物典型意義的強調,與地域生活的變遷不無關系。在媒體技術變革的推動下,人們的交往范圍、交往對象以及交往方式發生顯著變革,傳統意義上以民族和地域為邊界的文化認知亦隨之遷移,全球化、大眾化使不同民族與地域擁有了相對接近的審美標準,重塑了文化生產與消費格局。在這一宏觀背景下,“鄂東”這個原本十分確定的生活空間概念逐漸被消解,其所指向的地域文化邊界也日漸模糊,場域中心地位被具有極強擴散能力的大眾文化所占據。地域文化的邊緣化,使其在本土社會生活中的規約功能與導向價值大大降低,直接表現就是社會成員身份標簽的淡化。正因為如此,較之于紅色革命者與歷史名人鮮明的地域身份,現實題材影視作品中鄂東人物表現出來的“共性”明顯強于“本土性”;即便許多作品在場景的設計上盡力突顯“鄂東色調”,但其人物的“鄂東身份”仍然無法像“劉銅鑼”“邢繡娘”那樣鮮明。再者,基于主流價值導向的既定要求,創作者更多地關注主要人物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典型價值和普遍性意義,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其身上的本土化特質。理性而言,“鄂東人物”一旦無法承載地域性格,其身份辨識度將大為降低,文化傳播價值必然受到限制。將鄂東文化的基因有效融入影視人物之上,是當前現實主義題材“黃岡出品”面臨的核心挑戰。
地域語境中的影視藝術生產,必須依托本土優勢文化資源。鄂東文化系統中,最為顯著與豐富的資源就是“人”——生活于各個時代的“鄂東人物”,構成本土影視創作的“原材料”與“原動力”。在鄂東歷史時空中,雖然早期革命者、文化名人以及現代鄂東人物出場的背景各有不同,但創作者對他們本土身份突出與強調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這也使得人物身上具有了某些共通的元素,易于識別。與其說這是影視創作者的“審美慣性”所致,不如說是鄂東文化符號形式與精神內容內在建構的結果。對于觀賞者而言,唯有回到鄂東生活場景之中才能真正與創作者進行“對話”,也才能確切地解讀本土影視人物的性格、行為特征及其命運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