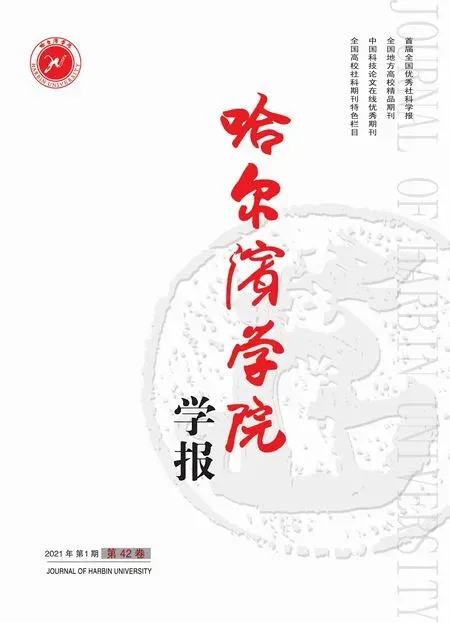鮑勃·迪倫作品的風格美學解讀
鄭燕紅
(閩南理工學院 外國語學院,福建 石獅 362700)
2016年,鮑勃·迪倫(Bob Dylan)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作曲家。諾貝爾委員會成員霍勒斯·恩達爾(Horace Engdahl)評價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迪倫是一位值得占據很多位置的歌手,他值得在希臘吟游詩人旁邊,值得在奧維德旁邊,值得在浪漫主義者的旁邊,值得在藍調國王和王后旁邊,值得在被遺忘但具有突出成就的大師旁邊。”[1]迪倫是一位具有感知銳度的藝術家,從政治、文化、性別問題到生活、愛情、音樂本身,都可以成為他創作的素材,他源源不斷的靈感正是來源于他強烈的感受力和永不停止的思考活動。
從1961年發布首張專輯至今,迪倫在流行音樂界和文化界產生的影響已超過60年。他的多數著作都來自于1960年代的反抗民謠,也被廣泛認為是當時美國新興的反叛文化的代言人,盡管他否認了這一點。他的早期代表作品《答案在風中飄》成為了當時“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的圣歌,另一首作品《時代在變》成為反戰運動的頌歌。本文以傳紀電影《我不在那兒》①為線索解讀迪倫的藝術創作,以及他作品中呈現出來的獨特個人風格和審美意識。
一、鮑勃·迪倫的風格美學
康德哲學思想中有一個重要的環節即是對想象力的論述,他把此概念的基本涵義規定為人的心靈上的一種直觀能力,想象力能夠表象即使不在場的對象。在迪倫的音樂藝術中,我們透過歌曲《答案在風中飄》的歌詞可以解析這一過程。
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才能稱為真正的男子漢?一只白鴿要飛越過多少片大海,才能在沙灘上得到安眠?炮彈要多少次掠過天空,才能被永遠禁止?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風中飄揚……一座山要佇立多少年,才能叫做滄海桑田?人們究竟要活到多久,才能被允許擁有自由?一個人要多少次回首,才能做到真正的視而不見?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風中飄揚。答案它在這風中飄揚。一個人要抬頭多少次,才能望見天空?一個人有多少只耳朵,才能聽見哭聲?究竟要失去多少條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經死去?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風中飄揚。
迪倫將對和平的向往表達在一句句的發問中,引發人們的聯想與想象,透過“白鴿”“生命”“自由”“風”等詩歌中常用的意象,體現出不在場的對象。評論家邁克爾·格雷(Michael Gray)認為,這首歌是迪倫將圣經修辭融入自己風格的一個例子。這種特殊的反問修辭方式常常在《新約》中被使用,歌詞基于《舊約》的《以西結書》:“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們有眼睛看不見,有耳朵聽不見。’”迪倫把這句話改編成“一個人要多少次回首,才能做到真正的視而不見?”和“一個人有多少只耳朵,才能聽見哭聲?”[2](P63-64)
康德把想象力進行了區別和分類,依其是否具有創造性而劃分為兩種:一是生產性的想象力;二是再生性的想象力。康德特別重視這里所說的生產性的想象力,例如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他將想象力的基本含義規定為人的心靈的直觀能力。他說:“想象力是把一個對象甚至當它不在場時也在直觀中表象出來的能力。就想象力就是自發性這一點而言,我有時也把它稱之為生產性的想象力,并由此將它區別于再生的想象力。”[3](P101)生產性的想象力在藝術創作活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迪倫的創作很大程度上發揮了這種生產性的想象力,如這一首《時代在變》的歌詞:
無論何處漫游,請快聚首。承認吧周遭洪水已開始漲起,接受這現實很快你會感到透骨涼意。若你的時代仍有價值,值得拯救,那就趕快游起,否則沉淪如石頭。因時代變革在不久,來吧,預言以筆的作家,批評家們,請睜大你們的雙眼,良機難再至。不必太快做出結論,因車輪在飛馳。誰被提名無從知,輸家翻盤早晚的事,因時代變革在不久。來吧,議員們,請留心這呼聲。別把著門,不要阻住走廊,因為容易受傷的,正是那些墨守成規的人。外面風起云涌,戰斗正酣,就快把你們的門窗震動,你們的墻壁將震顫,因時代變革在不久。來吧,這大地上的父親、母親,不要隨意批評那些,你無法理解的事情。你們的兒子女兒不再受你們安排,你們走過的道路正迅速陳舊。
文藝評論家克里斯托弗·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認為,這首歌超越了它被寫作時的政治成見,即使在今天演唱也意味深長。[4](P260-271)
歌曲《答案在風中飄》創作于1963年,而《時代在變》創作于1964年,此時的迪倫還沒有成為一名基督徒,而根據評論家的說法,這兩首作品都已經具有了宗教色彩。到了1979年,迪倫成為一名重生基督徒,影響到他從1979年到1982年的創作,如《火車慢慢來》《留存》《愛的射擊》三張專輯都帶有濃重的基督宗教氣息。迪倫的歌曲創作很多來源于宗教典籍,這與西方的宗教文化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的歌曲更能直擊心靈。康德說:“想象力作為一種即使對象不在場也能具有的直觀能力,要么是創制的,這就是本原地表現對象的能力,因而這種表現是先于經驗而發生的;要么就是復制的,即派生地表現對象的能力,這種表現把一個先前已有的感性直觀帶回到心靈中來。”[5](P49)依照康德的觀點:藝術是一個天才喚起另外一個天才。藝術作品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梁,此溝通的基礎是我們共同的情感。迪倫的歌詞語言平實,看似只是在敘述平常的瑣事,但其中卻充滿了想象力和象征意味,這使得迪倫的音樂被公認為是具有內涵的音樂。
二、鮑勃·迪倫作品的美學影響及價值
迪倫的努力和新的嘗試從未間斷。1960年代中期,迪倫開始從民謠風格向民謠搖滾風格轉型,并在1965年發行長達六分鐘的單曲《像一塊滾石》,也從此改變了流行音樂的傳統分類。自1994年以來,迪倫出版了八本繪畫書籍,他的作品已在各大美術館展出;他已售出超過1億張唱片,使他成為有史以來最暢銷的音樂藝術家之一;他還獲得了無數獎項,包括總統自由勛章、格萊美獎、金球獎和奧斯卡獎。
2016年10月13日,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授予迪倫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他在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中,創造了新的詩意表達。”[6]但很多人質疑:迪倫寫的東西算文學嗎?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上,迪倫雖然缺席,但他親筆寫了一篇演講稿,由美國駐瑞典大使代為朗讀。透過迪倫的諾貝爾獎獲獎感言,我們可以見出他對于文學、對于音樂的思考。他誠懇地袒露了自己也在想他的歌曲和文學有什么關系,并回顧了自己創作過程中如何受到文學的影響,也就解釋了這些作品深層的內涵和人文關懷:
當我開始自己寫歌的時候,我唯一知道的辭藻就是民謠的語言,我也就使用這樣的語言。但我也有些其他的東西。我有我的主題,我的情感,和對世界的認知。我一度有過這些東西,全都是在文法學校學到的:《唐吉坷德》《艾凡赫》《魯賓遜漂流記》《格列佛游記》《雙城記》等,這是文法學校的典型閱讀清單,教給你一種看待生活的方式,一種對人類本性的理解,和度量世間萬物的尺度。當我開始寫歌的時候,這些東西都陪伴著我,它們的思想以各種有意無意的方式走進我的歌里。我想要寫的歌同以往任何歌曲都不一樣,而這些書的主題是至關重要的。
迪倫在他的講稿中闡述了閱讀給他帶來的影響,并細致地列舉了具體的書籍:“我在文法學校讀過的書里面,有些書對我影響至深——我想專門提出其中的三本:《白鯨記》《西線無戰事》和《奧德賽》。”他把每一本書中令他印象深刻的部分都寫了下來,既有書中的情節,也有他閱讀時候的感受。
歌曲也是同理,我們的歌活在生命的大地上。可是歌和文學不同。它們應該被歌唱,而不是被閱讀。莎士比亞的戲劇應該演出來,就好像歌曲中的歌詞也是應該被唱出來,而不是印在紙上讀。我希望你們當中一些人,可以在歌中聽出創作者寫下這些歌詞的本意:無論是在音樂會上,還是在唱片里,還是現在任何一種聽歌方式。我得再一次引用荷馬:“在我的體內歌唱吧,繆斯!讓故事從這里生發。”
正如迪倫在感言中寫道:“所以這一切意味著什么呢?我和其他許多作曲者都曾被這相同的主題影響過。它們可能意味著許多不同的事。如果一首歌打動了你,那就夠了。”我們與其用“文學性”去衡量音樂,不如將文學性替換成“藝術性”的概念。這一點著名的日本編劇野田高梧在電影領域中也作出過思考和解釋:“想來,人們常常把電影與文學聯系在一起,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它們碰巧站在同樣的立足點上,用同樣的視角觀察,用同樣的耳朵聆聽。但實際上,文學也好,電影也好(或者說美術也好,音樂也好),它們源自同一個祖先,之后發展成不同的派系,血統相同,但系統不同。”[7](P54)迪倫也舉出了莎士比亞的例子,莎士比亞寫的是劇本,但是沒有人會質疑莎士比亞的作品不是文學,莎翁在創作的過程中想必也不會去思考自己寫的東西是不是文學。
對于迪倫的作品,也許我們可以拋開“文學”的范疇,在其表達的終極人文關懷之中,進行一種“無功利的審美判斷”。他帶來的藝術不僅是一種獨特的個人風格,更有其深刻的美學價值。如果我們將藝術看作是自身的生存條件之一,我們就可以跳脫出迪倫與諾貝爾文學獎究竟如何關聯的問題,而將迪倫的藝術看作是我們共同的經歷。而這共同的經歷,以他的歌謠作為媒介,交流了我們彼此之間的感情,也因此升華了這一藝術精神遺產。
注釋:
①電影《我不在那兒》是一部講述鮑勃·迪倫生活經歷和音樂故事的傳記影片,其講述了迪倫早期作為民謠歌手艱苦奮斗的生活和內心的掙扎。影片以迪倫接受記者采訪的對話形式展現,分別由六位演員扮演迪倫的不同時期,演繹迪倫在不同時代的音樂生涯和創作背景。每一次迪倫思想上的轉折會出現某些人物進行發問,然后以演繹他的音樂作品作為回答。《我不在那兒》這部電影涵蓋了迪倫對于音樂、對于藝術問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