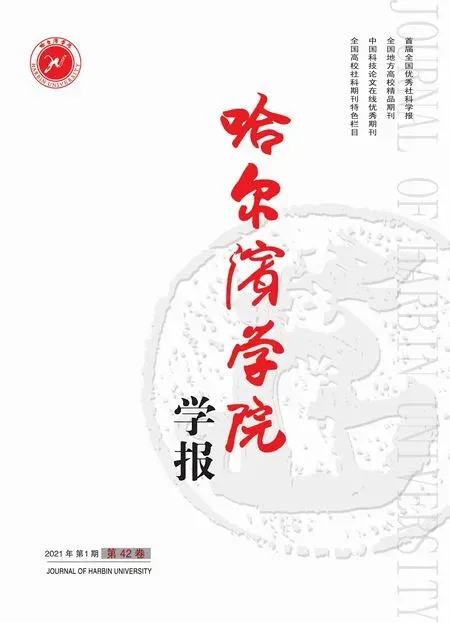“索菲亞論”及其對弗洛羅夫斯基哲學思想的影響
勞靈珊
(浙江外國語學院 西方語言文化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格奧爾基·瓦西里耶維奇·弗洛羅夫斯基是俄國著名的宗教思想家、神學家和歷史學家,他為后人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縱觀弗洛羅夫斯基的一生,他在歐洲的最初幾十年僑居生活可謂豐富多彩。在這個階段,他結識了大批當時同在保加利亞和捷克避難的俄國優秀知識分子代表,與他們的交往開拓了弗洛羅夫斯基的思維,使他的思想觀念愈發成熟,這為之后他在巴黎神學院執教期間完成一系列承載其主要神學和哲學思想的鴻篇巨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更為可貴的是,這位杰出的思想家并沒有被淹沒在周圍眾多思想家的光環中,與“索菲亞論”代表學者之間的思想交鋒使弗洛羅夫斯基學會了獨立思考,并最終形成了獨具自身特色的一套思想體系。
一、俄羅斯“索菲亞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觀點
“索菲亞論”這一術語源于俄語Софиология,因София在俄語中有“智慧”之意,也被翻譯成神智學或智慧學,是討論神的圣智慧問題的一種學說。
在俄羅斯,最先提出這一理論的是索洛維約夫。當然,他并不是“索菲亞論”的第一個發明者,他也是從世界思想傳統中借鑒而來的,但不是來源于哲學領域,而是直接源于《圣經》。索菲亞,神的圣智慧,這是《圣經·舊約》一些經卷里的神話形象。就非哲學根源而言,索菲亞不是一個概念,而是具體的形象、人物。在《圣經·舊約》里,索菲亞在世界大廈里有一定的行為,扮演一定的角色。《舊約》主要文本稱其為“神身邊的女藝術家”,是對世界大廈進行藝術塑造的某種原則。這不僅是個原則,更是獲得實現的原則,化身為具體人物的原則。[1]索洛維約夫從青年時代就開始迷戀“索菲亞論”,存在于其意識中的這個索菲亞與其說是個觀念或原則,不如說是個人物。因此,索菲亞成了索洛維約夫特殊體驗的對象,但這不是哲學體驗,而是一種神秘的個人體驗。索洛維約夫認為,他與索菲亞有過私人相遇,并進行過對話,這體現在他著名的長詩《三次約會》中。哲學家在詩中描述了他與索菲亞的三次相遇:第一次與索菲亞的相遇發生在1862年,當時索洛維約夫只有九歲,在他進行宗教祈禱的時候看見了一個神秘的女性形象;第二次看到類似的形象是在1875年,當時他為了收集盡可能多關于索菲亞主題的資料來到倫敦,在大英博物館經歷了神秘的幻象,并聽到索菲亞的吩咐,讓他去埃及;第三次,聽從吩咐的索洛維約夫于1876年前往埃及,并在開羅周邊的荒漠地帶與索菲亞再次相遇。[2]盡管當時這部長詩里記載的并不屬于哲學體驗,但是,索洛維約夫憑借自己卓越的哲學才能把看到的幻象與《圣經》中神的圣智慧索菲亞聯系在一起,發展出了一套索菲亞哲學。與此同時,經歷了第三次幻象后的索洛維約夫開始著手撰寫自己的第一部“索菲亞論”著作——《索菲亞:普世學說的基礎》。索洛維約夫在該書中提出了希望確立“普遍發展的基礎”的想法,不但要建立“所有宗教的綜合,而且還有宗教、哲學和科學的綜合”。[2]雖然索洛維約夫本人在不久之后也發現并承認了該書文字的幼稚和論述形式的不平衡性,但這部探索性的作品對其成熟的“索菲亞論”的最終形成無疑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而作為一個哲學家,索洛維約夫最偉大的創舉莫過于將“索菲亞論”和萬物統一學說結合在了一起,構成了一種完整知識的綜合哲學,也是所謂真正的哲學——自由神智學。在索洛維約夫看來,自由神智學是神學、哲學和科學的有機綜合,只有這種綜合才能包容知識的完整真理;沒有這種綜合,無論科學、哲學還是神學,都僅僅是知識的一個局部或方面,是一個脫離完整機體的器官,因而不會與完整真理有任何程度的相符之處。這種自由神智學,既不是以哲學來為論證神學服務,也不是客觀唯心主義哲學為證明自身而訴諸宗教信仰,其基本宗旨是建立一種既包括世界的理想模式又包括人的行為原則的完整的世界觀。[3](P115-116)
俄羅斯“索菲亞論”的另一位杰出代表是布爾加科夫,他的索菲亞學說是影響最廣的,同時也是最受爭議的。與索洛維約夫的哲學一樣,在這位“白銀時代”著名哲學家和神學家的思想體系中,索菲亞概念或神話形象也處于中心地位。在《經濟哲學》一書中,布爾加科夫首次較為詳細地論述了自己的“索菲亞論”。在布爾加科夫看來,“索菲亞論”就是認為索菲亞是全部世間存在的理想原型,同時也是歷史經濟活動的主體的一種學說。與萬物統一學說一樣,“索菲亞論”也是基督教思想大背景下的哲學宇宙論,其基本觀點是確認世界有一種普遍的本質或理想觀念,即整體統一性;而與此相比,單個的人和經驗個體則是屬于第二性的。不同于索洛維約夫從宗教神秘體驗出發來論述這一學說,布爾加科夫是借助經濟理論來進行論證的,他認為經濟活動是全人類的活動,而不是個人活動。[2]如果說,《經濟哲學》中論述的主要是關于索菲亞與經驗世界和人的關系,那么在布爾加科夫的《不夜之光》這部著作中,作者系統、詳盡地闡述了索菲亞與神的關系,以及經驗世界與神的關系。他在書中這樣寫道:“上帝在創造了處于自己之外的世界的同時,也在自己和世界之間設置了某種界限,這個就其概念來說處于神與世界之間、創造者和受造物之間的界限,其本身既不是神,也不是世界,而是某種完全特別的東西,它既把上帝和世界聯結起來,又把它們分隔開來……這個受造物的天使,神的道路的開端,就是神圣智慧。神圣智慧是對大愛的愛。”[3](P149)由此可以看出,在布爾加科夫眼中,索菲亞是神與世界之間的中介。但是這個論斷必然會涉及神學中的“三位一體”問題,因為在傳統神學中,神與受造世界的關系就是通過神的“三位一體”來進行說明的。那么如果索菲亞是中介,那它與同樣作為中介的“三位一體”有何區別?面對這個問題,布爾加科夫是這樣解釋的:“智慧作為大愛的愛和對大愛的愛,擁有自己的個性和面孔,是主體、人格,或者用神學術語來說,是位格;當然,它不同于圣三位一體的諸位格,是特殊的、另類的、第四位格。它不參與神的內在生活,不是神,因此不會把三位格性變成四位格性,把三位一體變成四位一體。”[3](P149)而正是這個“第四位格”說法的提出,使布爾加科夫遭到了東正教會和一些東正教神學家的嚴厲批判。1918年,布爾加科夫接受了神職,完成了從馬克思主義和唯物主義到唯心主義,進而向東正教神學的轉變。在1933年出版的《神的羔羊》一書中,布爾加科夫試圖對索菲亞與神的位格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重新解釋。在這里,布爾加科夫不再將索菲亞置于神與世界的中間地位,而認為索菲亞本身就是神性的,存在于神之中,它不再與位格范疇近似,而與本質范疇近似。[3](P152)盡管布爾加科夫對自己的“索菲亞論”進行了重新論證,否定了先前提出的“第四位格”說法,但把索菲亞與神的本質等同起來這種做法仍然無法被東正教會所接受。1935年9月,莫斯科東正教會把布爾加科夫的學說判為異端。此后,布爾加科夫繼續在巴黎神學院任教,并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盡管俄羅斯東正教會最后于1937年廢除了關于布爾加科夫“索菲亞論”是異端的指責,但圍繞這一學說的爭論在東正教神學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一部分人還是對“索菲亞論”持保留甚至堅決否定的態度,其中就包括與“白銀時代”宗教哲學家所不同的新一代東正教神學家的杰出代表弗洛羅夫斯基。
二、“索菲亞論”對弗洛羅夫斯基哲學思想的影響
被稱為“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的布拉格是捷克人理想的生活家園,與此同時,這座偉大包容的城市也使無數外國知識分子為自己的靈魂找到了精神避難所。與許多俄國僑民知識分子一樣,被迫離開祖國的弗洛羅夫斯基也曾在這里尋找生命的歸屬。在布拉格,弗洛羅夫斯基加入了由眾多俄羅斯優秀僑民宗教哲學家和作家組成的“圣索菲亞兄弟會”。該組織每月舉辦一次會議,成員聽取有關教會和歷史主題的報告并進行討論,同時也關注當下重大的教會和社會事件。但是在1925年,弗洛羅夫斯基因無法接受該組織精神領袖大司祭布爾加科夫提出的“索菲亞論”打算離開兄弟會,但他還是繼續參加該組織的會議。隨后,由于巴黎神學院的建立,兄弟會的很多成員都受聘前往巴黎任教,其中也包括弗洛羅夫斯基。早在與歐亞主義者發生思想分歧之初,弗洛羅夫斯基就逐漸開始把俄國未來的希望寄托在從拜占庭繼承而來的東正教傳統中。于是,這位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神學教育的思想家借著在神學院工作的便利開始著手研究東方教父的學說。在巴黎神學院工作期間,弗洛羅夫斯基就已經成為了一位小有名氣的教父學家。在那里,他和同事們一起致力于恢復東正教神學,積極參與普世教會運動,但卻總是與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宗教哲學思想——“索菲亞論”格格不入。
對于弗洛羅夫斯基來說,他把自己在巴黎神學院執教期間寫作的精神動力歸結于對以一切形式存在的“索菲亞論”的反駁。在他看來,俄國的“索菲亞論”就是德國唯心主義的變種,是一種特殊的諾斯替教派,①是對用來闡述基督教教義的哲學的一種非法利用。弗洛羅夫斯基之所以開始研究教會圣父的學說,除了離開歐亞主義后向東正教傳統的靠攏,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索菲亞論”者試圖把自己的思想說成是傳統思想,而且把自己對哲學的運用說成是有圣父先例可循的。弗洛羅夫斯基研究教父學的主要目的是找到正確理解世俗哲學和神學之間聯系的那把鑰匙。在他看來,“索菲亞論”者沒能找到這把鑰匙,但是可以在希臘教父的身上,即拒絕了非基督教因素的基督教希臘化時代中找到。弗洛羅夫斯基寫道:“教父作品不僅是不可侵犯的瑰寶,它對于我們來說更是創作靈感的源頭,是基督教的勇氣和智慧的榜樣,是走向當今時代苦苦追尋的新基督教綜合的道路。恢復教會思想的時刻已經到來了。”[4](P5)
可見,弗洛羅夫斯基不僅對“白銀時代”宗教哲學的代表性學說“索菲亞論”提出了批判,而且還在此基礎上加入了自己獨特的思考,表述了另一種全新的原則,即完整準確地表達東方基督教話語,并提出要按照這一原則為俄國宗教思想制定新的戰略和新的發展道路。嚴格來說,在對待東方基督教話語,即古代教會精神遺產的態度方面,“白銀時代”哲學家和新一代東正教神學家存在一定的共同點:即二者都要求創造性地對待精神遺產,對遺產進行現代化理解,而不能盲目和保守地一味保衛它。但是,除此之外,新一代東正教神學家還特別強調對精神遺產的哲學表達必須是準確的,必須保留該遺產的全部內容,這一點在“白銀時代”的哲學里是沒有體現的。“白銀時代”哲學家只把精神遺產當作最初的基礎,當作其哲學創造的跳板,而弗洛羅夫斯基卻提出必須完整而準確地保留這個遺產。因為在他看來,在利用東方基督教話語作為哲學創造的基礎之前,首先要完整而準確地恢復和表達它。而東方基督教話語顯然不是一開始就是用哲學方法來表達的,而是用純粹的宗教語言表達的,這是神學的和禁欲主義的語言。所以,俄國宗教思想繼“白銀時代”之后的下一個發展階段就是從哲學返回到神學。為順利實現這一轉變,首先要完成一個方法論任務,就是確定對待東方基督教話語的新態度。這種新態度應該要避免兩個極端立場,即既要擺脫純粹的保守主義,不能一成不變地保留遺產,盲目服從舊規范,同時也要擺脫純粹的現代派立場,杜絕根據自己的意愿隨意使用并歪曲古代遺產。
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俄國宗教思想的新階段逐漸開始。與此同時,弗洛羅夫斯基的東正教神學價值觀也最終形成,由他創立的新教父綜合理論完成了俄國宗教思想從哲學轉向神學的方法論任務,即回答了如何對待東方基督教話語,才能同時擺脫保守主義和避免現代派的問題。弗洛羅夫斯基的理論包含兩個層面,其中第一個層面就是“教父綜合”論題。他認為,要想正確對待東方基督教話語,首先應該精確而完整地保留古代教會的精神遺產。在他看來,這個精神遺產的主要內容就是希臘教會的教父遺產,而且在任何時代,它都應該成為宗教思想的基礎、支柱和方針。這個原則看似有些保守主義的意味,的確,弗洛羅夫斯基對神學也持有一定的保守態度,但保守絕不代表蒙昧,他堅決反對對過去的盲目崇拜,認為最重要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由此,便引出了第二個層面,即“新”。弗洛羅夫斯基認為,向傳統的返回,向古代教會教父的返回,不是針對其詞句,而是針對其精神。也就是說,保留精神遺產不是要求逐字逐句地重復教父的某些具體觀點和理論,而是要學習教父們對待問題的態度和方法。在他看來,教父學說是一種無所不包的基督教思想標準,但絕不是對所有問題的現成回答,而是不斷更新的精神財富。對教父學說的忠誠不僅要求對其遺產有形式上的了解,更要掌握其內在的神學風格和思維方法。也就是說,必須創造性地遵循傳統,而且這種創造必須面向自己所處的時代,回應現代性所提出的挑戰,這就是新“教父綜合理論”最為重要的實質所在。正如弗洛羅夫斯基自己所強調的那樣:“這不應該是簡單地把教父的意見和主張匯集起來。這應該是一種綜合,是對古代圣人洞察力的一種創造性重新評價。這種綜合應該具有愛國主義性質,并忠于圣父的精神和觀點。同時,它也應該是一種新的教父綜合,因為它是面向新世紀的,有屬于它自己的問題。”[5]
弗洛羅夫斯基沒有過喪失信仰、迷戀無神論的經歷,更沒有離開過教會,可以說,在所有俄國神學家中,他對東正教學說是最忠誠的。弗洛羅夫斯基畢生遵循圣經和教父哲學的傳統,在教父神學研究方面成績卓著,對教父思想有著深刻的體悟。然而,這位出生于東正教神職人員家庭的思想家的神學世界觀并不是家族遺傳式的,而是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其中僑居歐洲的生活經歷對他的影響最為深遠。通過對俄羅斯“索菲亞論”的思考和反駁,弗洛羅夫斯基更加堅定了要發展一套屬于自己的神學理論的決心。最終,思想家在希臘教父的精神遺產中找到了答案,新“教父綜合理論”應運而生。至此,弗洛羅夫斯基獨具東正教特色的思想體系也最終形成。
注釋:
①諾斯替教派,是早期基督教的一種宗教哲學思潮,力圖從宗教信條和東方神話的觀點出發來建立關于上帝和世界起源及其發展的一種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