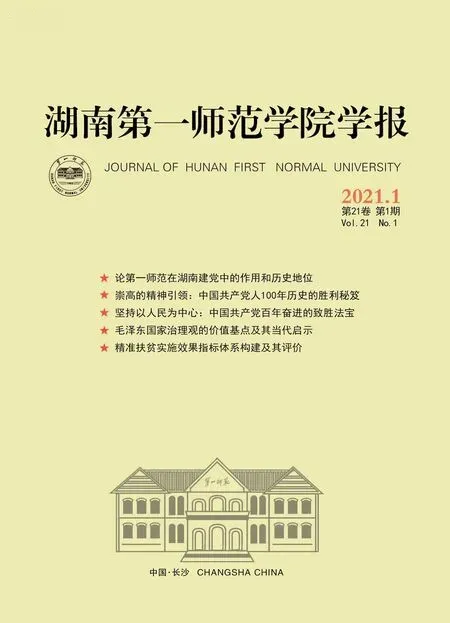從文化適應到文化自覺
——論晚明來華耶酥會士的身份演變
王佳娣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湖南長沙 410205)
引言
在早期來華耶穌會士的傳教史研究中,兩次易服及其帶來的身份演變是研究的熱點。關于傳教士易服的研究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考證易儒服的時間、地點、動因等史實[1];二是關注傳教士的兩次易服,肯定第一次易服(從中式普服到僧服)的重要性,認為兩次易服本質上都是文化適應策略的反映[2];三是將傳教士的易服事件置于明末中國社會和東南亞傳教區的復雜歷史語境中加以分析,全面探究易服的歷史動因及由此帶來的影響[2]。現有研究已明確明末來華耶酥會士從“西僧”到“西儒”的轉變不僅是服飾的更易,更是在華身份、傳教策略、文化認知的變化。那么在易服的標志性事件背后,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力量在無形中推動事件的發展?易服是“迫于生存壓力的無奈之舉,是向社會上層和主流意識的屈從”[3]抑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適應和自覺重建?本文將重新審視晚明來華耶穌會士的兩次易服及身份演變,試圖呈現早期來華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認知、認同、思考、比較和重建的過程。
一、由外而內的文化適應:從“耶穌會士”到“西僧”
文化適應的傳教策略由時任耶穌會亞洲區巡視員的范禮安神父提出,在當時的耶穌會是創新之舉,他認為傳教士應該學習所在國家的語言及生活方式,適應當地習俗,尊重當地傳統。漢學家德禮賢(Pasquale D’Elia)將其文化適應策略描述為:“很明顯他的目的不是把遠東人民‘歐洲化’,而是在遵守耶穌會教義和規范的前提下,讓傳教士們在印度成為印度人,在中國成為中國人,在日本成為日本人,即適應本地的衣食習慣和社會習俗。簡而言之,只要不違反教規,一切皆可適應。”[4]
關于初入華耶穌會士著僧服有來自中國和西方的史料描述[5]124[6]。從現有的文獻和研究看,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和利瑪竇(Ricci Matteo)著僧服入華有其傳統淵源和現實策略需要。大部分耶穌會士均出身貴族,走“上層路線”是他們的主要傳教策略。在當時的亞洲傳教區,僧侶在印度和日本均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特別是在日本,僧侶常是社會精英階層的代表,因此在日本的耶穌會士通過著僧服迅速地融入了當地的主流階層。范禮安指示即將入華的中國傳教團著僧服、刮去發須,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現耶穌會的宗教性質。他的策劃與中國官員的要求不謀而合。羅明堅在寫給澳門傳教團的信中提到中國官員希望他和利瑪竇能夠穿僧侶的衣服,當時他們以為中國的僧侶和日本的僧侶一樣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便沒有提出異議[7]。由此,在內外兩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西方的耶穌會士換上僧袍,以“西僧”的身份走進中國,在廣東肇慶定居下來,開始了未知的傳教之旅。
(一)身份困惑
從1583年到1595年的12年間,以羅明堅和利瑪竇為代表的早期來華耶穌會士一直以“西僧”的身份在華生活,雖然利瑪竇在晚年的回憶錄(《利瑪竇中國傳教史》)中對此幾乎略而不提,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是初入華的耶穌會士們探索天主教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一個重要階段。但“西僧”身份的確立顯然是從外表服飾的改變開始的,耶佛兩種文化在由外而內的接觸中所產生的沖突與碰撞,也許是早期來華耶穌會士所未料及的。
定居在肇慶的羅明堅和利瑪竇很快取得知府王泮的信任,新建的別院獲得王泮題的兩塊匾,一是“仙花寺”,二是“西來凈土”。初入華的傳教士受到官員的如此禮遇,沉浸于初戰告捷的喜悅之中,便默認了“寺”和“凈土”的稱謂。而后的中文教理著作更加強化了他們“西僧”的身份。《天主圣教實錄》是在利瑪竇的協助下,由羅明堅寫成的第一部中文護教著作,初版刻于1584年。其中,羅明堅自稱“西僧”來自“天竺”,并大量借用佛教術語解釋天主教教義,如用“出家者”“入道之僧”等指耶穌會士,用“得道之人”指圣人,另有“輪回”“投胎”等佛教術語。方豪認為傳教士使用“僧”字并不代表依附佛教之義,但也不排斥佛教[8][9]89。顯然“不排斥佛教”的說法有待商榷,羅明堅的《天主圣教實錄》的最初版本中就已對佛教的天堂地獄說和輪回說加以批判。《利瑪竇中國傳教史》提到該書“駁斥了偶像崇拜者的錯誤”[10]。這里提到的就是《天主圣教實錄》的初版,“偶像崇拜者”指的就是佛教徒。早期來華耶穌會士對佛教的批判是基于對佛教教義的理解之上的。據張西平的考證,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天主教教義》一文實為早期來華傳教士在華期間抄寫的一篇佛教經文,屬于《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但內容更簡單,抄寫者并非羅明堅和利瑪竇,疑為麥安東或孟三德神父。該文獻是耶穌會士入華不久,仍以“西僧”名義展開活動時期的文獻,是他們學習中文的一個讀本,同時也是他們學習佛教教義的見證[11]。由此可見,耶穌會傳教士并非一入華便與佛教劃清了界限,而是在不斷適錯的過程中發現僧侶在中國的地位和名聲,并逐漸形成“補儒易佛”策略的[9]91。
一方面,他們對外自稱“西僧”,來自“天竺”,并以僧人的面目示人,其所恪守的清規也與僧人并無二致,且借用佛教術語論證天主教義;另一方面,他們又對佛教的教義加以批判,宣稱“我們的教義與規律與他們完全不同”[5]153,試圖與佛教劃清界限,這種內外的不一致構成了早期來華耶穌會士的身份困惑。身份不明直接導致傳教效果不佳,在最初的幾年里,肇慶的官員和百姓均把他們視為“洋和尚”,受到了各種挑釁和誣陷,生存尚且艱難,何談傳教。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洋和尚”的身份對早期入華耶穌會士們又何嘗不是一種保護,以“僧”的身份掩蓋了“洋”和“耶穌會士”的真實身份,才在晚明的廣東得以居留下來,為后來傳教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自我反思
自我反思主要表現在利瑪竇對佛教教義的批判上。1584年,由羅明堅為主編寫的《天主圣教實錄》正式出版印刷,他在向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報告時,強調該書得到了中國官員的褒獎[5]459。利瑪竇也在多封信中提到該中文著作在中國很受歡迎,認為其條理分明,文詞相當優美[5]64,但同時也介紹該書駁斥了中國主要的宗教思想(佛教),也對中國所有的種種惡行與罪愆(迷信)加以斥責[5]72。
1589年,傳教士被迫由肇慶遷往韶州,利瑪竇在寫給范禮安的信中詳細描述了他們被安頓在南華寺,但拒絕向偶像行禮,也與和尚保持距離的細節,由此表明他們與中國和尚的信仰格格不入[5]95。雖然利瑪竇正式著儒服是在1595年,但在1592年的一封信中已流露出對“西僧”身份的不滿:“洋人、和尚和道士在中國并不受尊重,因此我們不能以和尚、道士之流出現。”[5]124
張曉林對利瑪竇反對佛教的理由進行了歸納,認為佛教一直構成中國文化階層精神生活的另一向度,是天主教進入中國的一個直接的競爭對手,利氏希望通過排佛,最終以天主教取代佛、道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12]。無論動因如何,利瑪竇對佛教越來越嚴厲的批判是不爭的事實。從最初《天主圣教實錄》剛出版時的贊美之詞與成功的自信,到后來考慮撰寫傳教著作的替代品《天主實義》,再到全面銷毀《天主圣教實錄》的刻版,利瑪竇在不斷加快與佛教劃清界限的步伐。這種自我反思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對傳教效果的不滿,用利瑪竇的話來說,傳教事業還在“清除毒草”的開荒階段[5]256,于是傳播路徑亟待調整。
二、由內而外的文化自覺:從“西僧”到“西儒”
如果說從“耶穌會士”到“西僧”的轉化是由外而內的文化適應,那么由“西僧”向“西儒”的轉化則是由內而外的文化自覺。根據費孝通的觀點: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人要對自身所處的特殊文化語境有一定的認知能力,理解其歷史、現狀及未來,用客觀的眼光來看待該文化的一切[13]。張冉進一步將文化自覺解釋為民族集體對文化認同、比較、反思、批評和創新的實踐活動[14]。從文化自覺的視角來看待早期來華耶酥會士的活動,不難發現,晚明社會儒學仍是主流文化,正確認識儒學的地位及要義對于耶穌會士來說是理解中國文化的關鍵。在華傳教,直接傳播天主教教義或者比附佛教術語都不是好的選擇,找到與儒學的融合之道才能為傳教事業打開新的局面。因此,耶穌會士的文化自覺是建立在對儒學的認知、認同、思考、比較和重建的基礎之上,二次易服便成為必然的結果。
(一)內在覺醒
自我覺醒源于對儒學經典的深入理解。從認識到儒學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到閱讀和翻譯“四書”,再到撰寫《天主實義》中引用儒家經典論證天主教教義,是來華耶穌會士對儒家教義的認知不斷深化的過程。
利瑪竇在入華不久后便對儒學在中國社會的地位有了認識。1584年9月13日他在廣東肇慶寫給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先生的信中談到中國的宗教與教派時,已認識到儒教在中國最為出名,但他們不信靈魂不死之說,與釋、道的觀點也不同[5]62。雖入華僅一年,利瑪竇已經清楚了儒學與佛教和道教之間的差異,同時也深知儒學的“不信靈魂不死”的觀點成為其與天主教融合的鴻溝。
利瑪竇等人在逐漸意識到“西僧”身份的局限的同時,對儒學的認知也在不斷加深。應視察員范禮安神父的要求,利瑪竇著手將“四書”譯成拉丁文,在談到翻譯的進程和感受時,利瑪竇認為該翻譯對中國和日本的傳教士非常有用[5]135。顯然,利瑪竇所謂的“有用”定是發現了儒學與天主教教義相契合之處。對“四書”的閱讀和翻譯為利瑪竇后來撰寫《天主實義》打下了理論的基礎。隨即,他便開始用中文編寫《天主實義》,試圖用“自然推理證明教義為真”[5]139。
利瑪竇在晚年回憶錄中也意識到,其實儒教只一種學派,其主要目的是齊家、治國,在倫理方面與天主教有著許多共通之處[10]86-87。事實上,利瑪竇清楚地意識到耶儒之別,但他仍然從儒學的倫理道德中找到了與天主教教義的共鳴之處,從而走上“合儒”“補儒”的道路。盡管這種耶儒融合可能是特定時空中的“自說自話”,“從未實現真正的交流”[15],但“補儒易佛”仍然是利瑪竇等人在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結構后做出的主動選擇。與進入“西僧”身份時的倉促、妥協與被動相比,“西儒”身份的確立經歷了由內而外的主觀自覺的過程。
(二)身份重構
當認識到“我們從事文人的工作,我們學有專長”之后[5]153,利瑪竇等人遵從內在的變化,通過第二次易服實現了由“西僧”到“西儒”身份的轉變。
利瑪竇正式著儒服的記載見于1595年8月29日寫給澳門孟三德神父的信中:“我們已決定放棄僧侶的名稱,而取文人的姿態,因為‘僧人’在中國人眼中身份很低而卑賤。”[5]153這是利瑪竇對蓄須留發、著儒服的明確記錄,他在信中還詳細地描述了晚明儒服的式樣以及第一次著儒服拜訪在江西的廣東官員的情景。利瑪竇利用宴會的時機,向官員說明自己學有專長,表明真正身份,解釋天主教與佛教教義的差異。
利瑪竇“西儒”的身份重構對于以“規矩嚴明、絕對服從”為宗旨的耶穌會的影響是較為深遠的。儒者的身份提高了耶穌會士們的社會地位,交游更加廣泛,為后來以德傳教、以禮傳教、以器傳教、以文傳教等策略的實施奠定了基礎。以“西儒”的身份進入中國傳教也成為耶穌會的傳統,與中國士人合作著書立說,從事翻譯,促進雙方的科技和文化交流,成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結語
以羅明堅、利瑪竇為代表的晚明入華耶穌會士經歷了從“耶穌會士”到“西僧”再到“西儒”的身份轉變,其背后的文化意義值得深入思考。在羅明堅時代,“西僧”的身份既是一種保護,又因其內外的不一致造成身份不明,導致猜疑與誤解。利瑪竇一方面嚴格劃清與佛教的界限,另一方面加深對儒學的認知,尋找耶儒融合的路徑。從最初面對陌生文化的妥協適應,到深入理解中國社會后的文化自覺,耶穌會士們經歷了身份困惑、自我反思、自我覺醒與身份重構四個階段后,迎來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個高潮時期。在當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國文化的傳播者已經走過了身份困惑的階段,在積極地反思文化傳播的效果與路徑之間的關系。早期來華耶穌會士的文化自覺過程為中國文化傳播者的自我覺醒與身份重構帶來了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