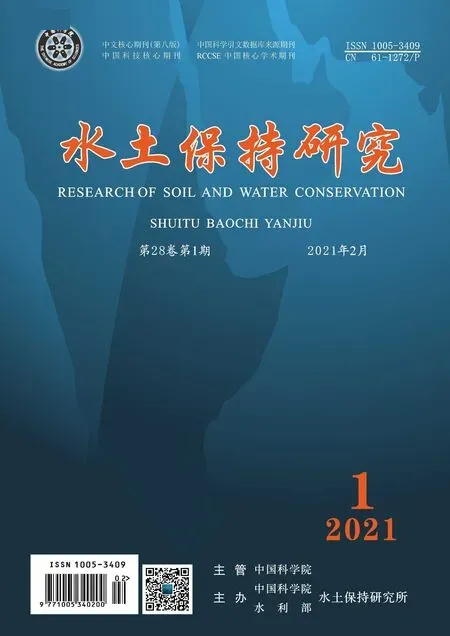伊犁河谷草地生態系統水分利用效率時空變化及影響因素
付秀東, 閆俊杰, 沙吾麗·達吾提, 劉海軍, 崔 東, 陳 晨
(伊犁師范大學 資源與生態研究所, 新疆 伊寧 835000)
草地是陸地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表明全球一半以上草地發生退化[1],草地退化的環境效應被廣泛關注[2-3]。水分利用效率(Water Use Efficiency,WUE)代表了植物固定單位質量碳消耗的水分[4],由生態系統生產力和蒸散發(Evapotranspiration,ET)共同作用[5-6],是表征生態系統碳水耦合的重要指標[7],也是預測生態系統對環境變化響應的重要參數[8]。分析草地退化對生態系統WUE的影響,對從生態調節的角度來揭示草地退化的環境效應具有重要意義。
前人對植物個體或農田植被WUE特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廣泛研究[9-10]。遙感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生態系統水平WUE研究的廣泛開展[11-12]。基于遙感技術,Xia等[13]對全球陸地2000—2013年WUE分析表明非洲和大洋洲由北向南以及歐洲和南美洲由東向西,WUE有所增加,而Chen等[10]發現1999—2008年溫帶歐亞草原WUE整體呈增加趨勢,但存在明顯的空間分異;鄒杰等[14]對2000—2014年包括新疆在內的中亞地區WUE分析表明,該區域內主要生態系統的WUE均有所增加。對于WUE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干旱是促使生態系統WUE變化的重要原因[15-16],適度干旱將激發植物通過自身調節提高對水分的利用效率[17];穆少杰等[18]發現,相對于溫度,降水量的變化對WUE的影響更大。除氣候影響因素外,Jin等[19]研究表明植被物候的改變也是生態系統WUE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Zheng等[20]發現植被重建促進了黃土高原生態系統WUE的提高;同時,Huang等[21]的研究發現高強度的放牧活動致使新疆覆蓋水平較高的草地WUE發生明顯降低(牧民更偏向于在覆蓋度高的草地放牧)。可見除氣候因素影響外,植被覆蓋水平及物候等自身特性的改變也是影響生態系統WUE變化的重要原因。
位于我國天山西段的伊犁河谷,草地發育良好,是我國重要的優質牧場[22],但近15 a在氣候變化和過渡放牧等干擾影響下,草地退化日趨嚴重[23]。基于此,本文利用遙感數據及氣象數據,借助于GIS空間分析技術,對伊犁河谷草地WUE時空變化進行分析,探討氣候變化及草地退化對WUE影響,以期為草地退化環境效應的研究提供支持和參考。
1 研究區概況
伊犁河谷介于80°09′42″—84°56′50″E,42°14′16″—44°53′30″N,地處天山山脈西端(圖1),北、南、東三面高山環繞,地形呈向西敞開的“V”字;特殊的地形為西風帶濕潤水汽抬升凝結成雨提供了有利條件,河谷內降水充沛,造就了其“塞外江南”的美譽[24-25]。境內有鞏乃斯河、喀什河、特克斯河以及伊犁河等主要河流。山脈和河流將整個河谷分割為伊犁河谷、特克斯谷地、鞏乃斯谷地、喀什河谷丘陵和昭蘇盆地5個地域單元,形成了獨特的“山地—盆地—河谷平原”地形地貌[26]。河谷內年平均降水量200~800 mm,受到地形影響,山區降水是平原的3~5倍;年平均日照時數達到2 700~3 000 h,年均氣溫2.9~9.1℃。河谷內草地植被發育良好,類型豐富,且垂直分異明顯[27]。

圖1 研究區概況
2 材料與方法
2.1 數據來源與預處理
本研究所用到的遙感數據包括MODIS的NDVI,ET以及總初等生產力(Gross Primary Productivity,GPP)成品數據,時間序列為2000—2014年。NDVI數據為MODIS MOD13Q1產品數據,該數據為16 d合成數據,其空間分辨率為250 m;GPP和ET數據分別為MODIS MOD17A3和MOD16A3產品數據,時間和空間分辨率分別為1 a和1 km。GPP和ET數據由蒙大拿大學密蘇拉分校地球動態數值模擬研究組制作,數據經過全球多個區域地面通量數據的驗證,被廣泛應用于區域及全球尺度的相關研究[28-29]。草地空間分布數據是基于Landsat 8OIL近外、紅和綠波段假彩色合成影像,利用目視解譯方式獲得其矢量數據,為便于數據處理,將矢量數據轉換為柵格數據。
氣象數據來自中國氣象局氣象數據中心,包括2000—2014年伊寧市、伊寧縣、霍城、察布查爾、霍爾果斯、尼勒克、鞏留、新源、昭蘇、特克斯及巴音布魯克11個氣象站月平均氣溫和月累積降水量數據。利用Anusplina 4.2軟件進行空間插值生成月氣溫和月降水量柵格數據。之后利用月氣溫和月降水量柵格數據,按照標準化降水蒸散發指數的計算步驟[30],逐像元計算,獲得年SPEI空間分布數據,用SPEI指數來表征研究區干旱狀況。
為保證多種數據的空間匹配,在數據計算和預處理過程中,將柵格化的草地空間分布數據、氣溫、降水和SPEI空間分布柵格數據以及NDVI,GPP和ET的像元大小統一設置或重采樣為250 m。
2.2 研究方法
2.2.1 單調趨勢的Mann-Kendall非參數檢驗法 Mann-Kendall非參數檢驗方法特別適用于類型變量和順序變量的趨勢檢驗[31],廣泛應用于水文、氣象、植被及其他長時間序列數據趨勢檢驗,其計算過程如下:
(1)
(2)
(3)
(4)
式中:xk,xi表示第k和第i個時間的ET,GPP或WUE值;sign為符號函數;n為時間序列長度。Zc為時間序列數據變化趨勢檢驗統計量。若Zc>0,則時間序列變化趨勢為上升,若Zc<0,則變化趨勢為下降;α=0.05水平上;|Zc|=1.96,若|Zc|>1.96,則時間序列變化趨勢在0.05水平上顯著。
2.2.2 WUE計算方法 WUE通常利用固碳量與耗水量的比值來計算,但對固碳量和耗水量兩個分量表達時所選指標常有不同[15]。凈初級生產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4,10,13]和GPP[5,7,14,32]常用來表達固碳量,但也有用地表NPP和凈生態系統生產力(Net Ecosystem Productivity,NEP)來表達[33];對耗水量的表達,ET是通用指標,但也有用降水量來表達[15]。為便于與國內相關研究[5,7,14,32]的對比,本文采用GPP與ET比值計算,詳細公式為:
WUE=GPP/ET
(5)
式中:WUE,GPP和ET分別為生態系統水分利用效率(g C/kg H2O),總初級生產力(g C/m2)和蒸散發(mm)。
3 結果與分析
3.1 草地WUE,ET和GPP的空間分布特征
基于2000—2014年伊犁河谷草地ET,GPP和WUE的年空間分布數據,計算其多年平均值,用其代表伊犁河谷草地ET,GPP和WUE空間分布,制作空間等級分布圖(圖2),依次分析其空間特征。

圖2 伊犁河谷和等級空間分布
由圖2A可知,伊犁河谷草地WUE海拔分異明顯,WUE較高(>1.25 g C/kg H2O)的區域主要分布在烏孫山—昭蘇盆地—那拉提山以及科古琴山—阿吾勒拉山的中山區,而WUE較低(<1.25 g C/kg H2O)的區域則主要分布河谷平原、低山丘陵以及河谷周圍的高山區。具體來看,1.25 g C/kg H2O
ET的空間分布也呈現明顯的海拔分異,但與WUE的海拔分異存在一定差異(圖2A,圖2B)。不同于WUE,ET低值(<300 mm)區域集中分布在鞏乃斯河下游—伊犁河兩岸、以及喀什河下游和特克斯河下游兩岸平原區和低山區,該區域也是伊犁河谷最為干旱的荒漠區,而河谷周圍的高山區ET相對較高(>400 mm);此外,昭蘇盆地—特克斯周圍區域為WUE高值區域(>1.50 g C/kg H2O)而ET則相對較低(300 mm
對于GPP,對比圖2C與圖2B和圖1A可以看出,在河谷平原、低山以及中山區域,GPP的空間分異與ET較為一致,但在河谷周邊的高山區域GPP的空間分異則與WUE較為一致。具體來看,伊犁河谷59.12%的區域GPP>500 g C/m2,空間上主要位于河谷的中山區域,該區域中,500 g C/m2 綜合圖2A、圖2B與圖2C可以看出,昭蘇盆地—特克斯的區域以及科古琴山的南部低山區,由于GPP高(>650 g C/m2)而ET相對較低(300 mm 由圖3A可知,在空間上,伊犁河谷絕大部分區域草地WUE有所增加,根據統計結果,其比例為79.20%,但增大達到顯著水平的面積有限,比例為16.61%,空間上主要分布在河谷北部、烏孫山及那拉提山的中山區域;WUE呈減少趨勢的草地面積比例為20.79%,其中20.04%的區域呈非顯著減少,空間上主要分布在河谷南部高山區域、烏孫山南麓喀什河下游兩側的低山和洪積沖積扇區。 從圖3B可以看出,2000—2014年伊犁河谷草地ET減少區域占了絕大比例。根據統計結果,ET減少區域面積比例高達92.31%,而ET增加區域僅有零星分布。具體來看,ET呈顯著減少的比例達到了48.21%,分布于鞏乃斯河兩岸、尼勒克和特克斯及科古琴山中山區;ET呈非顯著減少的比例為44.10%,主要分布于沖積扇平原區以及那拉提—婆羅科努山—天山山脈高山區;ET呈顯著增加的比例僅為0.35%;ET呈非顯著增加的比例僅為7.34%,分布于河谷周邊區域。 GPP總體變化趨勢雖然與ET相同,但在空間上,GPP有所減少的區域明顯少于ET(圖3B和圖3C)。根據統計,GPP呈減少趨勢的比例為78.11%,其中,58.66%呈非顯著減少,減少達到顯著水平的比例僅為19.45%,空間上主要分布于特克斯河和鞏乃斯河周邊的低山和沖積平原區,以及烏孫山北麓的部分區域;GPP呈非顯著增加的比例為20.34%,主要分布于研究區海拔較高的東部、南部和北部邊緣區域,以及伊犁河出國境口的河谷平原區;GPP呈顯著增加的比例僅為1.55%。 圖3 伊犁河谷WUE、ET和GPP變化趨勢空間分布 近15 a伊犁河谷草地ET總體呈現極顯著下降的趨勢(Zc=-2.67,p<0.01)。在2000—2002年,ET逐漸增加,并在2002年達到最大值(453.66 mm),之后呈現波動式下降,在2014年達到最小值(335.97 mm)。GPP在研究時間范圍內同樣呈現降低的趨勢,但其變化不顯著(Zc=-1.5,p>0.05)。在年際波動上,GPP與ET的波動較為一致,最大值和最低值分別出現在2007年和2014年,分別為564.84 g C/m2,409.63 g C/m2。研究時段的15 a間,伊犁河谷草地WUE總體呈增加趨勢,但變化趨勢不顯著(Zc=1.78,p>0.05)。2000—2007年時,WUE整體呈現上升的趨勢,之后逐漸下降,在2010年達到最低值(1.19 g C/kg H2O)。在2011年、2012年,WUE逐漸上升,在2012年達到最大值(1.35 g C/kg H2O),之后再次下降。 對研究時段的前3 a(2000—2002年)及后3 a(2012—2014年)ET,GPP及WUE求平均值,并進行差值計算,得到其變化量。ET,GPP及WUE的在2000—2002年及2012—2014年的平均值分別為427.33 mm,524.86 g C/m2,1.21 g C/kg H2O及367.59 mm,480.48 g C/m2,1.29 g C/kg H2O,ET和GPP分別減小59.74 mm和44.38 g C/m2,減小13.98%和8.46%,WUE增加0.08 g C/kg H2O,增加6.61%。 圖4為利用ET,GPP及WUE變化趨勢Zc值空間分布數據進行疊加分析而得到的三者變化趨勢交互關系圖。由圖4可見,伊犁河谷草地的絕大部分區域表現為GPP降低、ET降低而WUE增加,表明相對于GPP,ET減少速率更大,因此WUE才有所增加。研究表明干旱生態系統中,GPP高的季節或年份,其WUE也高[34],但伊犁河谷草地WUE的年際波動與GPP存在較大差異,兩者相關系數為0.31(p=0.27)。同時WUE與ET的年際波動也存在較大差異,兩者相關系數為-0.18(p=0.53)。相反,ET與GPP的年際波動一致性很高,兩者相關系數高達0.88(p<0.001)(表1)。 圖4 WUE與ET及GPP變化趨勢交互關系空間分布 WUE為GPP與ET比值,其變化由GPP和ET共同決定。但顧春杰研究表明,相對于ET,GPP是影響不同生態系統WUE的決定因素[35],而宮菲等人對寧夏陸地生態系統WUE與GPP和ET關系分析表明,該區WUE與ET呈極顯著負相關(p<0.01),并指出生態恢復工程雖增加了生態系統的生產力,但也增加了水分消耗,致使生態系統WUE降低[36]。而本文中伊犁河谷草地WUE的增大雖然是因為GPP減少速率小于ET減小速率,但WUE與GPP及ET的相關性均不高,而GPP變化與ET卻具有很高的相關性,這表明,不同于顧春杰及宮菲等人[35-36]的研究結果,單一的GPP或ET均不能構成伊犁河谷草地WUE變化的主導原因;而同時,WUE的變化也不僅僅是GPP變化與ET變化的簡單的累加,而是GPP和ET綜合作用的結果。 用NDVI作為表征草地植被覆蓋水平的指標,討論植被變化對WUE的影響。 就NDVI與WUE的直接關系來看,由圖5可知,2000—2014年伊犁河谷平均NDVI與平均WUE變化趨勢相反,NDVI減小而WUE增加,根據表1,兩者相關系數僅為-0.11(p=0.71),表明NDVI變化不是影響WUE的直接原因;而空間上,絕大部分區域在NDVI減小的背景下WUE有所增大。 圖5 WUE與NDVI變化交互關系空間分布及兩者的年際變化 根據上文分析,伊犁河谷草地WUE增加主要是由于ET減小的程度高于GPP的減小程度。對于草地生態系統,植被覆蓋的降低通常伴隨著GPP的降低,根據表1,2000—2014年伊犁河谷NDVI與GPP的相關系數達到了0.86(p<0.001);但更為重要的是,植被覆蓋對ET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植被覆蓋降低不僅致使草地植被蒸騰量減少[37],還致使植被水源涵養的功能降低[38],使降水及冰雪融水等水分更容易形成地表徑流而流失,減少可供蒸騰和蒸發的水量,從而使ET總量減少。同時圖6中,伊犁河谷草地NDVI與ET年際波動高度一致性,兩者相關系數也高達0.95(p<0.001),這進一步表明伊犁河谷草地植被覆蓋降低促使ET逐漸減少。 表1 WUE以及其他要素相互之間相關系數和p值 圖6 2000-2014年伊犁河谷草地NDVI與ET年際變化 Zhu等[39]基于通量監測的數據發現,在我國的溫性草地、高寒草甸及溫帶落葉闊葉林,葉面積指數能通過調控ET中的蒸發和蒸騰兩個分量的比例來影響生態系統的WUE。本文雖采用NDVI來反應植被覆蓋,但由NDVI與ET卻具有很高的相關性,同時,NDVI與WUE的相關性并不高,由此可見,伊犁河草地NDVI可以通過對ET的調節來影響WUE。 除植被覆蓋外,氣候因子對WUE的變化也具有重要影響[40-41]。伊犁河谷草地降水及SPEI總體均呈現降低的變化趨勢,空間上,絕大部分區域在降水減少及氣候變干旱(SPEI減小)的條件下WUE增大;氣溫也呈降低趨勢,但卻存在明顯的空間差異,有大面積區域在氣溫升高的條件下WUE增大,也有大面積區域在氣溫降低的條件下WUE增大。根據表1,WUE與降水和SPEI的相關系數分別達到了-0.49(p=0.06)和-0.58(p=0.03),而WUE與氣溫的相關系數為0.34(p=0.21)。可見相對于氣溫變化,WUE與降水和SPEI相關性更高。 降水是生態系統水分的最終來源,根據表1,ET與降水的相關系數達到了0.55(p=0.03),而ET與氣溫的相關系數僅為0.04(p=0.89)。由此可見,相對于氣溫,降水的減少是導致伊犁河谷ET減少的主要驅動因素,因而也是促使草地WUE的增大的重要驅動因素。關于降水與WUE關系的研究較少,但這些研究表明降水是控制WUE時空變化的主要因子[42],本文的研究結果支持該結論。同時,Hu等[43]的研究指明草地WUE之所受到降水的控制,原因可能是WUE和降水的關系主要由碳過程控制,而不是水過程,而本文中降水與NDVI的GPP的顯著相關性也對該結論給予了支持,且NDVI降低所致使草地生態水源涵養功能的降低對ET減少的影響和伊犁河谷草WUE增加起到重要作用。 干旱是植被生長的重要抑制因子,但在一定范圍內,隨干旱程度增加,植物通過自身調節,使GPP減少低于ET減少[44],提高WUE。伊犁河谷草地WUE雖然與SPEI具有較高相關性,且全區絕大部分區域也是在干旱化的條件WUE有所增加,但這并不能證明干旱程度的加深就是致使伊犁河谷草地GPP減少程度低于ET減少程度的驅動因素,干旱對WUE的影響仍需深化研究。 (1) 伊犁河谷草地WUE,ET和GPP均存在明顯海拔分異;海拔較低的河谷平原區為三者的共同低值區,而中山區域雖為三者的共同高值區域,但該區內WUE與GPP和ET卻存在明顯空間差異;高山區域內GPP和WUE均較低,而ET則較高。 (2) 2000—2014年伊犁河谷草地平均ET和GPP呈降低趨勢,而平均WUE則呈增加趨勢,但僅ET變化達到顯著水平;15 a內,全區平均ET和GPP減小13.98%和8.46%,WUE增加6.61%。空間上,全區有92.31%和78.10%的區域ET和GPP有所降低,其中48.21%的區域ET降低達到顯著水平,而GPP的該比例明顯小于ET,為19.45%;全區79.20%的區域WUE有所增加,但達到顯著水平的比例僅為16.60%。 (3) 伊犁河谷草地WUE增加主要是由于GPP降低速率低于ET,但ET變化與GPP關系緊密,WUE的變化并不由單一的GPP或ET變化所主導,而是GPP和ET變化綜合作用的結果。 (4) 相對于氣溫,降水是影響伊犁河谷草地植被覆蓋和ET的主要氣候因子。在2000—2014年,伊犁河谷降水的降低是導致草地WUE升高的主要因素。3.2 2000-2014年草地WUE,ET和GPP的空間動態

3.3 2000-2014年草地WUE,ET和GPP的時間動態
4 討 論
4.1 ET和GPP變化對WUE的影響

4.2 植被覆蓋變化對WUE的影響



4.3 WUE與氣溫、降水及SPEI指數關系
5 結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