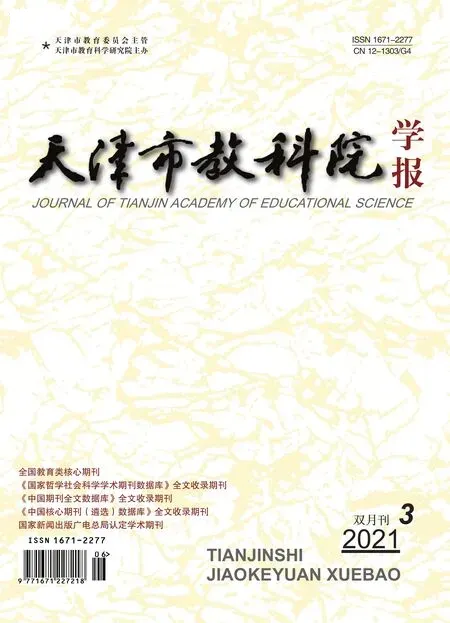頭胎兒童生活困境與家庭教育建議:基于個體心理學理論
王睿慜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如何對二孩家庭中頭胎兒童進行教育成為新聞報道、育兒節目及學術研究的熱點。既有研究表明,影響頭胎兒童心理變化的因素既包括年齡、性別等人口變量,氣質、共情能力等個性特征,也涉及親子關系、教養方式等家庭因素。這些因素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頭胎兒童行為的部分原因,但側重變量和獨立模型的分析,并不能全面完整地揭示頭胎兒童生活困境的內在邏輯及其緣由。因此,本文借鑒阿德勒(Alfred Adler)的個體心理學理論,從兒童自身立場出發,基于整體行為表現和心理活動邏輯來理解新家庭環境給頭胎兒童特別是幼齡大孩所帶來的“挑戰”,從而嘗試幫助父母更好地應對紛繁雜亂的家庭教育現場。
一、二孩家庭頭胎兒童的生活困境分析
當前,隨著對二孩家庭調查研究的增加,頭胎兒童家庭教育問題受到較大程度的關注。有研究發現,在家庭環境變化的壓力下,頭胎兒童在行為上往往出現退行性行為、情緒易怒、社會適應不良等問題,且面臨著巨大的心理壓力。[1,2]這些心理壓力具體指什么?又會引發什么不良行為?為何它們引發了不同類型的不良行為?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從個體思想和行動的關系中找尋答案。個體心理學認為,人類豐富的活動(精神或身體的活動)由適應所處生活環境引領,只有達成適應的目標我們才能感到安全。同時,人在確保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活動中有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即我們采取的一切活動必須符合人類共同生活的準則。換言之,我們在社會共同生活準則的約束下獲得安全,滿足各項生存欲望并確保自身幸福。當然,我們還要根據環境的變化調整自己的行為達成生活目標,以便獲取安全幸福的人生。因此,從個體心理學角度看,頭胎兒童心理和行為上遇到的困境主要源于他們生活目標無法達成,目標達成失敗的不安感將他們推向了借助不適宜行為尋求權力地位和幸福生活的環線。如果缺乏適宜的支持,他們可能直到長大成人也難以走出童年經驗的“循環詛咒”。
(一)心理層面:權力、地位的再尋求
二孩出生前,頭胎兒童在觀察和比較中逐步對自身所處的家庭環境形成認同,并通過與家庭成員的互動確認自我的家庭地位和自我價值。對生活環境的清晰把握在給頭胎兒童生存適應帶來安定感的同時,也幫助他養成了相對固定的人際互動模式,并確定他賴以生存的生活風格。換言之,只要按照既有生活風格參與家庭互動,他的需要和愿望即可得到滿足,這種認識將幫助兒童獲得深層安全感并適應社會。
而隨著二孩降臨,家庭環境發生變化,有著一整套生活方式和“慣習”的大孩本能地需要確認家庭成員對他的態度以確保自身地位安全。一時間,頭胎兒童面臨三個方面的挑戰:弟弟/妹妹是否會奪走我的家庭地位,他/她是否接納自己,同胞比較中能否取勝。這些挑戰將帶來一系列無法言說的心理壓力,他們必須在新處境中重新評估自我價值:通過對生活的細致觀察、比較,特別是對家庭生活中新的人際互動狀況來評價自我——“我屬于這個家庭”“我仍然很重要”;當觀察、識別到與自身預期或過往熟悉的狀況不一致時,這種差距將威脅到他自身的家庭歸屬感、自我價值感和安全感。因此,新的評價或判斷將引發一系列追求既有地位的行為。
具體來說,頭胎兒童如果身處“父母花更多時間照顧弟弟或妹妹卻沒時間傾聽自己”,或者“父母對我的要求比過去多得多”的新環境,將促使其思考自身地位問題,即“我是家庭中的失敗者還是參與者,這個位置對我意味著什么”。據此,他們可能錯誤地將自己置于低自我價值的處境,并形成關于家庭和自我的錯誤觀念。其中,淺層的錯誤觀念可能是“我在家里的地位受到了威脅”,或者“媽媽是我的,別人不可以擁有她”,或者“媽媽贊成誰,誰就在家中更受歡迎”,再或是“我是一個壞孩子,要不斷制造麻煩來確定我的位置”(成為焦點才意味著地位安全)等,而背后深層的錯誤觀念在于“只有得到媽媽的關注,才能確保我在家中的地位”(安全地位受制于外在環境)。
在這種心理壓力下,頭胎兒童利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已有的生活風格)來重新確立地位,保證自身歸屬和安全,以克服二孩到來后自我處境不利所帶來的“自卑”感。頭胎兒童基于觀察和對環境的判斷進行自我評價,完成了對生活目標達成與否的評估,而新環境很難確保他們持續擁有以往的地位,于是他們將依據既有生活風格來重新達成目標,由此開始借助這樣或那樣不適宜的行為試探和控制環境以尋求自身權力、地位的安全。在此,頭胎兒童的錯誤源自兩個方面:一是新家庭教養環境的錯誤阻礙了他對自身地位、價值的判斷;二是他以往確定的生活目標本身不健全,迫使他追求過度的優越感和地位,進而加倍采取行動達成錯誤目標。
(二)行為層面:錯誤行為補償
二孩的出生讓頭胎兒童面臨前所未有的環境,感受到從未有過的心理壓力,為了控制環境、緩解壓力,重新獲得家庭地位和尋求優越感——確保安全和適應,頭胎兒童需借助各種行為活動。這些行為可能表面上看大相徑庭,但是它們卻可能指向同一目標。其一,通過對家庭的“貢獻”確認地位,如努力按照父母要求去關愛、謙讓弟弟或妹妹;其二,借助迂回的方式達成目標,例如憑借各種借口、適應性不良的行為;其三,借助比較激進、明顯的錯誤行為,例如嫉妒、攻擊或貶損他人來補償自我地位受到威脅所引發的自卑焦慮。自卑感通常表現為兩種極端的行為方式,要么咄咄逼人,要么膽怯退縮。[3]常見的錯誤行為方式包括退行性行為、乖巧順從、逃避退縮和破壞性行為。
退行性行為主要包括“要媽媽喂飯”“輕微的磕碰就哭鬧不止”“晚上睡覺必須挨著媽媽”等,它是較年長的兒童表現出類似嬰兒或者較低年齡段兒童的不成熟行為。[4]乖巧順從則意味著使用“正面手段”(如粘著媽媽)來尋求家庭地位,但這類行為通常以犧牲自我的真實需要為代價。現實中,當頭胎兒童利用退行性行為或順從而成功博得父母的關注時(不論這種關注是責備、訓斥還是疼愛、照顧),他們都將確認這種行為有效,于是這類行為將在日常生活中不斷上演。而破壞性行為主要是指兒童用對抗性、攻擊性或“負向”行為等反社會行為來確認自我地位。在家庭生活中,頭胎兒童與其他家庭成員發生言語或行為的對抗,有的源自對父母權威的反抗,表現為話語權爭奪,有的則出于與同胞爭奪權力,常常表現為物權的爭奪(即得到物品的一方并沒有終止爭奪戰)。頭胎兒童通過展現自身的權力,實現自我價值和尋求優越感確認的目標。
如果前兩種行為無法獲得地位和優越感,那么頭胎兒童可能進一步用逃避或退縮的方式來“補償”自己,以期迂回地達成其追求優越的目標。他們會借助懶惰、幻想、拒絕或者強烈的哭鬧來逃避失敗,避免承認自身弱勢,最終可能用“懶得做”“不屑做”來凸顯自身地位。除此之外,他們還會表現出自暴自棄、悶悶不樂——“我不需要成為你們期待的那樣”,迫使“束手無策”的父母選擇放棄管教,進而再次確認自我地位(沒人管得了我)。不過,這些行為雖然能幫助頭胎兒童達成自己尋求地位的目標,但卻限制了他們的眼光——使他/她看不到自己作為一個大孩子有超越嬰兒的能力。[5]
二、頭胎兒童生活困境的原因剖析
阿德勒認為追求優越感是每個孩子的本能,[6]每一種自主的行為都源于一種缺陷感,而要消除之就要朝著滿意的狀態行進,這無可厚非。而頭胎兒童的錯誤行為正是其實現自我價值、追求優越的一次“無奈”嘗試,并試圖以此來抵抗在追求優越中形成的自卑感。[7]在此過程中,低自我評價和氣餒的兒童體驗到了失敗,因為既往樹立的過高的追求優越的生活目標,以及以往慣用的生活風格都指引著他用錯誤的行為來實現目標。根據個體心理學理論,這種心理和行為偏差的直接原因在于兒童精神生活的氣餒,而兒童之所以感到氣餒與其過高的優越感尋求和社會興趣不足有關,這些過高關注自我而忽視他人利益的性格追根溯源在于家庭教育的失范。
(一)直接原因:兒童精神生活的氣餒與自我封閉
二孩出生并不必然導致頭胎兒童的困境,他們之所以產生自我地位尋求的焦慮,并通過錯誤行為補償自我地位,主要源自頭胎兒童既有的關于自我與家庭環境關系的錯誤觀念,而這背后反映出了兒童無意識追求優越[8]所引發的自我迷失與封閉。
首先,頭胎兒童關于自我和家庭環境關系的認識在二孩出生前就已確立,而且可能已經形成了“我是家庭唯一中心”的個人邏輯,他們對社會生活沒有興趣且缺乏安全感,人生的意義僅限于以自我為中心。[9]阿德勒認為,人性十分關鍵的心理事實是對優越感和成功的追求,這種追求與人的自卑感之間有著某種直接的關聯。[10]只有達成了優越感和成功這一目標,個體的安全幸福才有保證。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帶著錯誤觀念的頭胎兒童更看重自身優勢地位的保持,于是在對比二孩降臨前后自身家庭地位出現的偏差后,他們感到氣餒和不滿足。頭胎兒童對“我”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對新環境的解釋指引著他,如果以往的生活習慣已經教會他追求“過度”的家庭地位目標,那么他將采取各種錯誤行為,如退行性行為或破壞性行為來彌補這種氣餒和不滿足感。他們之所以形成這樣的目標“是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或是可能帶來一種優越感,或是可能大幅提升人格,使得人生看起來值得去度過”[11]。因此,頭胎兒童對家庭與自身處境的判斷(過高的家庭地位期望)與客觀事實(實際的家庭地位)差距越大,知覺到的心理位置與客觀位置差距就越遠,其所確立的生活目標偏差也就越大,心理上也就越難以承受。
因此,頭胎兒童對新環境的適應不良首先表現在其內部發展的缺憾。內部過于關注自我優越感的實現恰恰反映出兒童對自我的迷失與自信的不足(我是否獲得了優越地位)。正如德雷克斯(Rudolf Dreikurs)所言,一個欺負弱者的孩子,通常是個氣餒的孩子,而不良行為是其內心氣餒的錯誤表現。[12]經驗事實也表明,一個內心富足的孩子,通常可以勇敢面對針對自我地位挑戰的新情境,并將之轉化成積極有用的行動來找到歸屬;而一個自卑沮喪的孩子,往往認定自己無法用良好表現來獲得認同,便自暴自棄。對于后者,無論是通過控制他人行為來獲取優越感,還是逃避退縮或乖巧聽話,或是采取退行和破壞性行為,都體現了一種內在的虛弱感,而這些行為正是其獲取尊重的一種偽裝。
其次,頭胎兒童借用錯誤行為適應新環境也是其個性發展不足的外化反映。具體而言,外部發展不足表現在嫉妒、惡意中傷、攻擊性行為等,這些行為反映出其對他人利益的漠不關心,這背后折射出兒童個性發展中的社會興趣匱乏(我的利益應當先被滿足)。頭胎兒童對自身地位的過度關注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在已有生活風格(1)生活風格:德雷克斯將生活比喻為一首曲子,而生活風格即是生活不斷重復的主旋律。生活風格在四五歲時開始確立,其形成依賴于兒童早期的記憶、圖像等“生活素材”原型,并在一定的生活環境中通過對知覺到的事物帶有個人興趣偏向的統覺及自我強化而隨之穩定。生活風格是個人思考、感覺和行為的模式,它決定了個體對生活的基本傾向、個人理想和對世界的反應。生活風格可以幫助研究者界定兒童會做什么或不會做什么。中缺乏必要的社會興趣(2)社會興趣:他以是否符合社會利益作為依據將追求優越區分為有益和無益的優越感。社會興趣包括對他人的積極態度,共情、認同等過程性因素以及不再指向內部的自我中心。。尤其是兒童的任何需要都由父母滿足,而不是由自身努力去實現的生活風格,不僅使兒童喪失了與外界的必要接觸,也使其無法以社會人的姿態去理解和培養社會情感。[13]他們考慮更多的是“我能獲得什么”而不是“我能給予什么”。正因為如此,他們表現出更多的雄心、更重視自己目標的達成、渴望獲取更多優越感,完全封閉在自身利益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社會適應不良的錯誤行為。
(二)根本原因:家庭教育方式和要求不當
二孩到來后頭胎兒童出現的“前所未有”的問題常常讓人誤以為是孩子突然變了,實際上新舊家庭環境的變化更像是兒童家庭教育的試金石,它在幫助成人更全面地認識家庭生活中自己塑造了一個怎樣的孩子。阿德勒人格的統一性理論認為,兒童所經歷和參與的每一項活動都是他整體生活和完整人格的表達。[14]對于一個處在順境中的人,我們無法清晰地看出他的生活風格,但如果他處在一個陌生的、困難不斷的生活環境里,他的生活風格就會非常明顯地暴露出來。其實,生活風格在兒童早期生活及其追求目標的過程中就已經形成了。[15]因此,要分析兒童錯誤的行為和觀念還要回到兒童的整體生活和整個社會關系背景中,在此最主要的就是要反思頭胎兒童以往的家庭生活。
頭胎兒童在舊家庭環境中形成的關于自我的錯誤判斷和社會興趣的匱乏是導致其生活困境最直接的原因,而家庭教育的不當在頭胎兒童經歷一個新環境時會將其“隱藏人格”展露無遺,這也是為什么有家長感覺二孩出生后大孩突然像變了一個人,“性格局限也能清晰地浮現,就像老照片的底片被放進沖洗液之后,畫面就會清晰顯現出一般”[16]。新舊家庭教養環境中存在的兩股力量撕扯著頭胎兒童:一邊是父母對大孩關心他人利益的新要求,一邊是大孩對自我力量的低估計。
從時間進程上看,二孩出生前,父母包辦代替、溺愛或嚴厲的舊家庭環境,削弱了頭胎兒童關于自我能力、自我價值的判斷,要么等著父母來做,要么父母看不上自己做的,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卻同時以削弱兒童作為創造性個體的勇氣、力量和自信心為代價。另一方面,父母費盡心力滿足孩子需要的錯誤教養方式,衍生出頭胎兒童缺乏社會興趣的生活風格——與他人相比,自身利益更為重要。包辦代替和溺愛的父母讓孩子形成了周圍人有義務滿足自己利益的錯覺而忽視了作為平等主體——父母的利益訴求,使兒童過度追求個人利益,變成缺乏社會感的“小霸王”;而嚴厲的父母讓孩子體驗到的只是挫敗,其社會交往只能選擇逃避和退縮到自我關注上來,只能在有限的人際中進行。如果說在舊家庭環境中二者還能保持平衡,那么到了新的環境中,兒童隱藏的不平衡即將被打破。
二孩出生后,父母對待頭胎兒童的教養方式出現轉折,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滿足其各種要求,有的甚至有失公允地偏袒弟弟妹妹,抑或是鼓勵同胞間的競爭;同時,父母對頭胎兒童提出了他們力不能及的要求,如“把好吃好玩的先讓給弟弟妹妹”,更多地要求大孩“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這些高要求有的來得毫無準備,有的一來就是“天花板”要求,這些不當的教養方式和要求向頭胎兒童不時地傳遞出不信任和不滿意“信號”,其自我價值和家庭地位受到了嚴重威脅卻不能被父母察覺、融通。于是在頭胎兒童對新環境作出判斷后引發了以上描述的心理和行為困境。總之,在新舊家庭教養環境中父母錯誤的教養方式和對頭胎兒童不當的要求,非但不能中止頭胎兒童對既有地位的尋求,培養不出頭胎兒童對二孩的社會性情感,反而強化了其追求錯誤目標的心理和行為,這也就是所謂的“兒童替父母生病”(3)“兒童替父母生病”:復雜的人際關系、緊張的家庭生活會讓注意觀察和敏感的兒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其情感活力及健康狀況。人們把一些反應稱為疾病,其實它們只是情感性的。法國小說家瑪麗·卡爾迪納提到過,當兒童與父母交流順暢、有話可說的時候,作為與父母緊密相連的人以及父母的探測器,他不需要用“疾病”變相地表示他正在遭受、忍受父母為之痛苦并也讓他痛苦之物造成的后果。當父母能說出他們的焦慮困惑時,他們的孩子受到的負面精神影響也就會減少。否則兒童將會以“疾病”的形式表現出來。參見弗朗索瓦茲·多爾多的《兒童的利益——學會尊重孩子》。。
三、改善頭胎兒童生活困境的家庭教育建議
頭胎兒童生活中出現的問題追根溯源在于父母的錯誤養育方式,因此改變應從家長著手。個體心理學認為,通過懲罰、簡單說教難以有效幫助頭胎兒童應對生活困境,需要圍繞精神生活對其進行指導。因此,父母應養成耐心觀察兒童行為的習慣,而非急于糾正其錯誤;了解其真實想法,調整家庭教養方式,給予他們充分的尊重和信任,幫助其樹立獨立、勇敢、自信的品格;鼓勵家庭成員間的合作,培養他們的社會興趣和與人協作的能力,最終幫助頭胎兒童從心理和行為上走出困境。
(一)從尊重和信任開始,激發創造性自我
二孩的到來不僅給成人的生活狀態帶來沖擊,更會使頭胎兒童的心理和行為出現波動。因此,父母這段時間正視頭胎兒童出現的變化并幫助他們增強自身能力顯得尤為必要。首先,對頭胎兒童心理和行為變化予以充分重視和必要寬容是問題解決的前提。通過理解頭胎兒童的精神生活,傾聽他們內心真實的聲音,認可和接納他們對家庭歸屬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理解他們通過錯誤行為確認自我價值和地位的個人邏輯與情感需要。承認他們作為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想法,體諒他們在新異環境中經驗不足的虛弱,適時地滿足他們對歸屬和認可的尋求,幫助其建立新家庭環境下的安全感。
其次,由于舊家庭環境削弱了頭胎兒童的自我力量,家長應有意識地提高兒童的自信心和自我能力,要做到尊重和信任兒童。父母應該看到孩子同自己一樣是擁有同等決定權、有能力的主體,只有父母先尊重和信任兒童,兒童才能感受到自己及其權利受到家長的尊重和認可,他們才能學會尊重和信任自己。家庭中還要營造尊重兒童的氛圍,不過度保護和包辦、不過度關注、不憐憫、不取悅,不強迫,不指責,不大驚小怪地擔心,也不夸張地贊賞兒童,相信他們是有自己的需要、意愿并能自己處置個人事宜的人。區分孩子的事和家長的事,屬于兒童的事盡量交由他們來做,父母應學會克制和隱忍,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兒童需要時“現身”。只有當家長信任孩子、信任他們的能力時,才是對他們真正的尊重。
最后,兒童的成長不能局限于從父母的關注和照顧中滿足自身需要、獲得安全感,更需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學會自給自足,對其提出力所能及的要求,不過高也不過低。真正快樂的人不需要建立在他人的關注上,而是發自內心地感受到內在的滿足。[17]家長要相信孩子能找到讓自己滿足的活動,而不再是如同小嬰兒一樣需要借助父母的關注、照顧來滿足自己的需要,由此真正實現對自我的尊重。因此,可以為頭胎兒童提供難度適宜的活動訓練以提高兒童的獨立性、自信心。家長要尊重和鼓勵兒童,利用生活中他們力所能及的事,訓練他們學習新技能,增強自我力量,樹立“我能夠依靠自己”的信念,激發兒童的創造性自我,使其能獨立和自信地應對環境的變化。
(二)從尊重他人到與人協作,培養社會興趣
人作為社會性存在,其行為必須符合社會現實的需要和利益。以自我為中心的兒童在追求優越感的同時,也使自身囿于對自我利益和自我不足的關注中,而忽視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阻礙了人格的完整發展。教育者要確保孩子對優越感的追求符合社會利益,讓他們獲得健康而有益的生活,[18]就要注重培養兒童有益的社會情感,形成和社會一致的價值取向,以利于兒童形成對自我和環境的正確判斷,適應生活。
相互尊重的家庭氛圍是兒童發展社會情感的出發點,父母對兒童的尊重影響著兒童尊重家庭其他成員。要培養兒童對父母的尊重,父母同兒童一樣也有自己的需要和權益,他們有自由決定個人時間、物品、意愿的平等權利。引導兒童逐步認識父母的這些權利,適當拒絕或延遲滿足能幫助兒童發現父母沒有義務完全滿足自己,這既尊重了兒童的自身能力,也教會了孩子尊重他人。在二孩出生前,有意識地幫助頭胎兒童樹立尊重父母的意識,認識到家中并不是所有的人、事、物都在圍著自己轉,他們才能更快地適應與家庭新成員相處,更好地理解自身所處的環境。
頭胎兒童的自我不足感(自卑感)是其社會適應不良的結果,在發展兒童自身能力之外,戰勝自卑最好的方法就是社會學習。家長應為兒童提供發展社會興趣和社會責任的機會。一是為頭胎兒童提供難度適宜的合作任務。面對新家庭環境,他們需要確認自身地位,邀請他們適當幫助父母,有助于他們重新評估和認識自身處境。如果只是一味地讓頭胎兒童逃避做哥哥/姐姐的責任,不僅會削弱他們對自身價值和地位的認識,而且不利于他們家庭歸屬感的滿足和家庭責任感的培養,不利于培養其完整人格。因此,在兒童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要求他們完成必要的家務勞動,適時地布置需要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務(例如一起幫助弟弟/妹妹進餐),讓他們在合作中看到自己對家庭的貢獻,體驗自身的價值和力量,增進其家庭歸屬感。
二是當家庭成員發生爭執時,特別是兩個孩子發生沖突時要營造相互尊重的家庭生活氛圍,使用討論、協商等多種形式,而非命令的方式來解決沖突。保持平等的關系,以客觀實際需要為出發點,通過協商選擇最符合實際情況的處理方法,征求他們的意愿,給他們完成家務勞動、自主活動和照顧弟弟妹妹的時間或類型的自由選擇。一視同仁地對待孩子,謀求兒童間的合作而非同胞競爭,讓他們共同承擔發生沖突的責任,進而用實際行動讓頭胎兒童有機會學習如何合作,并引導其發展共同生活的觀念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