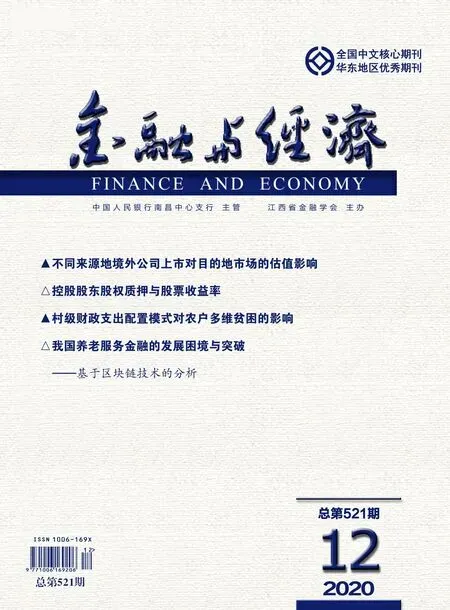不同來源地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的估值影響
■馬蒙蒙,易榮華,俞 瑩,姚曉陽
一、引言
隨著證券市場全球化,各交易所紛紛開放市場,參與到吸引境外公司的上市競爭中,引進境外公司上市將給目的地市場帶來何種估值影響至關重要。一般而言,境外公司上市至少在短期內可以獲得估值溢價,而在長期影響方面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境外公司上市會產生一個正的市場外部性,增強市場規模和流動性,從而顯著提升市場競爭力。另一種觀點認為,公司通常在高估值期間選擇交叉上市,隨著上市存續時間增加,公司估值呈現下降趨勢甚至負增長。
境外公司的質量也將影響市場效率和估值水平,在不同層次的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的估值影響上也存在爭議。一方面,優質公司上市后憑借其較高的市場聲譽獲得投資者關注,擴大市場規模,從而獲得估值溢價;另一方面,如果境外公司股票的特質信息較少或質量不佳,可能會對目的地市場產生質量傳染,對市場效率產生負面溢出效應。因此,對目的地市場而言,分析境外公司上市存續時間以及不同來源地的差異性影響,有助于選擇合適的上市監管制度和標的公司。此外,對致力于設立“國際板”的上海證交所及其他尚未引進境外公司上市的新興市場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筆者從目的地市場視角,以聲譽綁定、“質量傳染”效應等理論為基礎,選擇境外公司來源廣泛的美國市場和來源相對單一(主要為中國大陸)的中國香港市場作為研究對象,實證分析不同來源地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估值的影響。這一研究從目的地市場出發,驗證了境外公司上市的市場時機假設,研究了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的短期和長期的估值效應。同時,從境外上市公司來源地出發,驗證了“質量傳染”假說,將不同來源地分為成熟市場和新興市場,實證分析不同來源地對目的地市場的估值差異性。
二、文獻評述與研究假設
(一)境外公司上市的估值溢價及對目的地市場估值影響
聲譽綁定理論認為公司在聲譽更好的高質量市場上市將獲得估值溢價,Doidge et al.(2004)研究發現與沒有境外上市相比,公司在美國等成熟交易所交叉上市產生了明顯的估值溢價。近年來,公司境外上市的好處已獲得充分驗證。例如,Moeti(2019)研究發現交叉上市導致公司流動性增加,帶來總體收益增長。Abed et al.(2019)通過對在美國受監管和不受監管的股票市場上交叉上市的英國公司分析后發現,公司在交叉上市后提高了投資效率。Ghadhabh&Hellara(2016)考察了雙重上市和其后的三重上市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后發現,雖然其后的三重上市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越來越小,但仍然會產生積極的價格反應。另外,在公司治理水平方面,陳克兢(2017)認為市場法治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提升公司估值。總的來說,公司在成熟市場上市可以獲得更加嚴格的投資者保護和法律制度約束,能夠規范公司治理進而提升公司質量,產生估值溢價。
市場時機假設表明,較多公司在高估值期間選擇交叉上市,公司估值的增長并非永久性。或者公司為了上市而過度包裝,進行盈余管理,因此公司經營績效在境外上市前顯著上升,產生短期正面溢出效應。而境外上市后由于嚴厲的監管環境和投資者保護導致其不敢進行盈余管理,使得公司上市后的績效出現下降趨勢,產生負面溢出效應。“質量傳染”假說認為,低質量公司在目的地市場上市,可能通過增加信息不對稱、加劇市場波動性、對目的地同行業競爭對手的負面沖擊等“污染”目的地市場質量,進而對目的地市場估值產生負面溢出效應。胡聰慧等(2019)通過對中國上市公司送轉動機研究發現,操縱迎合類送轉的短期公告效應雖為正,但一年內便會反轉。Nicola&Stavros(2015)發現,當公司在一個更高聲譽的市場交叉上市后,5年內可以獲得顯著的估值溢價,而在聲譽較差的市場交叉上市后,5年內的估值顯著下降,產生“短期溢價、長期折價”現象。隨著“質量傳染”的發生,負面溢出效應可能進一步加強。董秀良等(2016)通過研究中國先H股后A股上市的公司,發現交叉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優于非交叉上市的純A股公司,交叉上市后其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并未提高,反而出現了下降。易榮華等(2017)通過分析華晨汽車上市模式的短期和長期效應發現,華晨汽車從NYSE退市對其在HKEX的累計超額收益率和換手率產生了短期積極影響,但對公司估值的短期影響是負面的。
綜上所述,不論是成熟市場還是新興市場,吸引境外公司上市至少在短期內是有利的,而關于長期影響的觀點不一。從公司層面而言,境外公司上市可能獲得短期估值溢價和長期折價。這對于目的地市場的估值影響而言,意味著短期提升了目的地市場整體估值水平,長期則可能降低目的地市場的整體估值水平,借鑒寇明婷等(2018)對股票市場短期和長期兩個時間階段分析的思想,提出假設1。
H1a: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整體估值水平具有短期正面溢出效應。
H1b: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整體估值水平具有長期負面溢出效應。
(二)不同來源地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的估值影響
不同開放程度的證券市場對上市公司發展的影響存在差異,屈超和高鵬(2020)認為證券市場的開放水平對證券公司效率呈現U型影響。當市場多元化程度較低時,會對證券公司效率產生抑制作用,當多元化程度超過門檻值時,證券市場開放對證券公司效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經典理論認為公司在成熟市場交叉上市將獲得估值溢價,如果公司通過交叉上市真正改善了公司治理、投資者保護和公司業績,這一估值溢價具有持續性,對目的地市場估值水平具有正面溢出效應,反之則具有負面溢出效應。Yi et al.(2019)認為母國和目的地股票市場之間存在聯系,他們的估值效率受到相同環境因素的影響,進而導致兩個市場之間的強烈聯動。Shi&Kim(2012)表明,當境外公司在美國市場上交叉上市時,上市公司的報告質量會受到母國法律環境的影響,Cumming et al.(2011)進一步分析發現來自更強大的母國治理環境的公司對目的地市場具有更高的回報和市場價值。近年來,逆向交叉上市的估值問題在新興市場引發討論,俞瑩和易榮華(2020)通過分析H股對中國香港市場的影響發現,來源于新興市場的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的影響是積極的,溢出效應大于“質量傳染”效應和分流效應,促進了目的地市場質量提升和市場發展。積極觀點認為,不斷增長的逆向交叉上市對發行者和新興市場都是有益的。一方面,發行者在已經“法律綁定”成熟市場而不影響其估值支撐的前提下,改善其在新興市場的消費者商業市場綁定;另一方面,優質境外公司上市有助于改善新興市場的結構和效率,提升市場聲譽(Howson et al.,2014)。
然而,聲譽尋租理論認為來自新興市場公司試圖通過到成熟市場上市,在沒有從事生產情況下壟斷目的地社會資源,從而得到壟斷利潤,這一現象嚴重影響目的地市場質量,降低市場估值。Melvin&Valero(2009)研究了在美國交叉上市ADRs股票價格對本地市場競爭對手公司的影響,發現對競爭對手公司存在正面和負面溢出效應,但主要效應是負面投資者認知。Singgih&Sidney(2018)證明了市場對盈利公告的反應會因公司母國在美國股票市場中的文化價值觀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即市場對交叉上市公司盈利公告的反應與公司母國聲譽呈顯著負相關。Sun et al.(2013)研究發現中國大陸股票所包含的公司特質信息少,當他們在中國香港上市時,對中國香港市場的股票產生了負面溢出效應。Karolyi(2004)認為,通過面向全球投資者發行ADR增強了母國市場流動性、可見性和信譽,但分流效應會導致母國市場質量惡化,對目的地市場質量的影響不顯著。
綜上所述,不同來源地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估值的影響不同,來自成熟市場的公司對目的地市場估值產生正面溢出效應,來自新興市場①新興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商務部在1994年提出的。關于來自新興市場境外公司的概念,大多數學者將其定義為來自發達國家之外的所有發展中經濟體的境外公司。的公司對目的地市場估值可能產生負面溢出效應。由此提出假設2。
H2:不同來源地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整體估值水平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且:
H2a:來自成熟市場的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整體估值水平具有正面溢出效應。
H2b:來自新興市場的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整體估值水平具有負面溢出效應。
綜上,關于交叉上市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鮮有文獻從目的地市場的視角研究境外公司上市的估值效應,僅有少數文獻沒有區分境外公司不同來源地可能帶來的異質性影響,如Liu(2019)認為東道國股票市場的估值是決定外國投資方式的重要因素,但并未明確區分不同來源地這一因素,故而引發筆者基于目的地市場對境外公司上市影響的存續時間及不同來源地的估值差異性進行分析。
三、模型設計與數據說明
(一)基于事件研究的估值檢驗模型
為檢驗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估值的短期影響,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事件日(允許境外公司上市)前后目的地市場指數成分股的估值表現。由于證券市場開放是一個漸進過程,所以圍繞事件日測度的變化很可能低估市場開放帶來的真正效果。鑒于此,參照Green et al.(2008)的思路,使用事件虛擬方法計算估計窗口(180天)的超額收益(ARs),該方法不僅提供了更嚴格的檢驗,還能夠對估計的虛擬變量進行F檢驗。因此,以標準方式(市場模型)估計ARs,但使用事件虛擬方法模型(4)來計算F統計量。即:

其中,Ri,t與Rm,t分別表示股票i和市場m在t時的收益率,εi,t為擾動項,其均值為0,方差為。αi、βi,與為市場模型的參數。

其中,t=t-u…,T,…t+v為事件窗口,t=T為事件日,Dh,t是事件窗口中的日虛擬變量,當 h=t,Dh,t=1;否則,Dh,t=0。
(二)基于Tobin’q的公司估值檢驗模型
為從公司層面檢驗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長期估值的影響(H1b)以及不同來源地公司對目的地市場的估值影響(H2a/b),從公司Tobin’q的視角,參照Nicola&Stavros(2015)的思想構造Tobin’q模型分析境外公司上市后股票的市場表現,自變量為境外公司股票上市變量(FCP),即境外公司與目的地市場相對總市值(McapF)以及境外公司與目的地市場相對總成交量(VolF),考慮到境外公司上市后長期收益變化與公司特質密切相關,又因為公司特質受國家特征和企業特征共同影響,因此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Tobin′qi,t表示公司 i在 t季度的市場估值表現,Ic為國家特征控制變量,Ie為公司特征控制變量,CVi,t為其他控制變量,式(5)中解釋變量均采用季度數據。FCPt為境外公司股票上市相對市值和成交量:McapF,VolF。為區分不同來源地,對McapF,VolF進行細分,即FCP1t為來自成熟市場境外公司的相對市值和成交量(McapF1和VolF1);FCP2t為來自新興市場境外公司的相對市值和成交量(McapF2和VolF2)。不同來源地境外公司上市回歸模型分別為:


表1 變量定義
參考Nicola&Stavros(2015)的變量選擇,國家控制變量考慮以下三個變量: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R_GDP);自由化指數(Freedom):采用美國遺產基金會公布的經濟自由化指數;貿易開放度(Openness):進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參考Sun et al.(2013)的做法,公司特征變量由對數總資產(Size)、公司上市年齡(Age)、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Growth)、凈資產收益率(Roe)以及杠桿比率(Lev)五個變量組成。此外,考慮到目的地與公司母國之間的匯率與利率變化會影響資本流動和公司估值,將匯率(Rate_F)和利率(Rate_H)作為其他控制變量,同時預期與Rate_F正相關,與Rate_H負相關。
(三)數據來源及說明
選取1991—2018年間美國和中國香港市場的所有境外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并將其分為來自成熟市場和來自新興市場兩類。剔除金融行業、注冊地與經營所在地不一致以及數據嚴重缺失的公司后,對于個別缺失值,采用多重插補(mice命令)填補缺失數據。截至2018年底,美國市場共413家公司(來自成熟市場324家、來自新興市場89家);中國香港市場共271家公司(來自成熟市場68家、來自新興市場203家)。數據來自Wind客戶端、Choice金融終端等,數據處理通過Excel,R studio及Matlab實現。
由表2可知,從市場來源地看,美國市場McapF,VolF小于中國香港市場,這與美國具有最大證券市場規模有關,美國市場McapF1>McapF2、VolF1>VolF2,說明美國市場境外公司中來自成熟市場的股票總市值和成交量多于新興市場,而中國香港市場相反,這與中國大陸公司占中國香港境外公司總量70%這一特殊性有關。美國市場中,境外公司占美國市場平均總市值達37.8%,成交量達44.6%,說明境外公司對美國市場的貢獻度很大,而在中國香港市場中,總市值和成交量占比分別達到55.2%、56.3%,這也說明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同時,ADF檢驗均顯著,說明時間序列數據平穩。
四、實證分析
(一)基于Tobin’q的境外公司估值描述性統計
表3顯示,兩個市場的境外公司Tobin’q大多小于1,且隨存續時間有逐步降低的趨勢,說明目的地市場給予境外公司的估值溢價并不顯著,且具有長期折價的趨勢,因而對目的地市場整體估值存在負面溢出效應。從境外公司來源地看,美國市場對來自成熟市場公司的估值明顯高于來自新興市場公司的估值,估值溢價與來源地成熟度正相關,中國香港市場則表現出相反的情形,這可能與該市場相對不成熟或其境外公司來源以估值過高的A股居多的特殊性有關。

表2 McapF,VolF的數據描述性統計(1991—2018)

表3 基于Tobin’q的美國和中國香港市場境外公司估值表現(按上市存續時間和來源地統計)
(二)基于事件研究的短期估值影響的檢驗
分別以市場第一只境外股票上市日(以有連續的境外股票上市算起)作為事件日,其中,美國市場為1991年8月28日(以色列Msgic Software Enterprises上市日),中國香港市場為1993年7月15日(中國青島啤酒上市日)。基于事件日,選擇(-360,-90)作為估計窗,(-90,+90)作為事件窗,(+90,+360)作為事后窗,共720個交易日作為研究區間。樣本為標普500指數及恒生指數成分股,剔除指數調整及退市成分股,最終選擇301家指數成分股公司作為有效樣本,其中美國市場267家,中國香港市場34家。
圖1、圖2分別為美國和中國香港市場的平均超額收益率(AAR)和平均累計超額收益率(ACAR)在事件窗口的變化趨勢,由模型(4)計算的F統計量見表4。

圖1 美國市場事件窗口AAR,ACAR變化趨勢

圖2 中國香港市場事件窗口AAR,ACAR變化趨勢

表4 平均累計超額收益率ACAR的描述性統計

表5 事件窗口平均超額收益率(AAR)的F檢驗
由圖1、圖2可知,兩個市場AAR在事件窗口期間圍繞0上下波動,中國香港市場波動幅度超過美國市場,但均沒有明顯波動變化。ACAR在事件后發生顯著變化,對美國市場來說,ACAR始終呈現顯著上升趨勢。對中國香港市場來說,事件前90—30天,ACAR緩慢增長,但是在事件前30天出現下降趨勢,并且持續至事件日后10天左右,之后呈現逐漸上升趨勢,且增幅變大。由表4可知,美國和中國香港市場ACAR在事件日前后均發生顯著變化,均值上升,P值顯著。表5中事件窗口的F檢驗統計量表明美國和中國香港市場在事件窗口表現出顯著的AAR,這一結果支持H1a,即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整體估值具有短期正面溢出效應,這與Nicola&Stavros(2015)研究結論相同。
(三)基于Tobin’q模型的公司估值檢驗
采用EG檢驗法檢驗Tobin’q和被解釋變量及控制變量間的協整關系。用變量Tobin’q對其他變量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得到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并生成一個新的估計殘差序列e,最后對殘差序列e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模型具有長期穩定關系,滿足Tobin’q多元回歸模型需求。
1.基于公司Tobin’q模型對長期估值影響的檢驗
由模型(5)所得的公司長期估值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表6顯示,兩市場McapF,VolF對Tobin’q有負面影響,但是不顯著,說明境外公司上市對美國及中國香港市場長期估值不存在負面溢出效應。從不同市場看,McapF對Tobin’q回歸結果表明,中國香港市場比美國市場更顯著,說明境外公司上市對美國市場的影響比對中國香港市場小,這與美國證券市場的高穩定性有關,驗證了市場時機假設,因此拒絕假設H1b,即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長期估值不存在負面溢出效應,這一結果與Nicola&Stavros(2015)的長期負面估值溢價的觀點不同。

表6 公司估值指標Tobin’q的回歸結果(長期估值)
2.基于公司Tobin’q模型對不同來源地估值影響的檢驗
由模型(6)、(7)所得的不同來源地估值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表7可知,從不同來源地看,兩個市場McapF1,VolF1對Tobin’q均有顯著為正的β1,說明來自成熟市場的境外公司上市提升目的地市場估值。從不同市場來看,McapF2,VolF2對Tobin’q的顯著性結果在兩個市場存在一定差異,在美國市場有顯著為負的β1,在中國香港市場不顯著。說明來自新興市場的境外公司上市對美國市場存在顯著負面溢出效應,但對中國香港市場不存在顯著負面溢出效應,這一結論與俞瑩和易榮華(2019)的積極影響結論不同,可能與中國香港市場上市的大量H股有關。總體來說,溢出效應與公司不同來源地密切相關,來自成熟市場的境外公司上市不僅增加了市場整體估值,也擴大了公司聲譽,提升上市公司估值。但隨著來自新興市場境外公司上市數量增加,來自新興市場境外公司的“質量傳染”效應對目的地市場估值產生了負面影響,同時這一結果可以解釋不區分來源地時出現的長期不顯著結果,且目的地市場與母國市場成熟度差異越大時負面溢出效應越大。因此,驗證假設H2a和H2b成立。

表7 公司估值指標Tobin’q的回歸結果(不同來源地)
(四)穩健性檢驗①
①限于篇幅,結果留存備索。
為驗證基于公司Tobin’q模型的可靠性與適配性,在回歸模型(5)、(6)、(7)中,選用公司財務的總銷售收入代替總資產作為公司規模Size的代理變量,同樣對總銷售收入取對數處理,其他國家特征及公司特征的變量不變,即將境外公司的Tobin’q與目的地市場相對總市值(McapF)和相對總成交量(VolF)分別進行回歸,其中長期穩健性檢驗模型如式(8)所示:

其中,Tobin′qi,t表示公司i在 t季度的市場估值表現,Ic為國家特征控制變量,Ie′為穩健性檢驗的公司特征控制變量,CVi,t為其他控制變量,式中解釋變量均采用季度數據。不同來源地實證檢驗模型如模型(9)和(10)。其中,FCP1t為來自成熟市場境外公司的相對市值和成交量(McapF1和VolF1);FCP2t為來自新興市場境外公司的相對市值和成交量(McapF2和VolF2)。

回歸結果顯示,兩個市場的McapF,VolF對Tobin’q影響不顯著,McapF1,VolF1對Tobin’q有顯著為正的影響,美國市場McapF2,VolF2對Tobin’q有顯著為負的影響,中國香港市場回歸結果不顯著,這與前文以總資產為公司規模代理變量的實證結果一致,且控制變量與預期回歸結果一致,驗證了模型的適應性與準確性。
五、研究結論
從境外公司上市的市場表現和公司估值兩個層面,采用1991—2018年間美國及中國香港市場的境外公司數據,運用事件研究法及Tobin’q模型研究了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估值影響的時變性和不同來源地的異質性特征。研究發現:
從時間層面看,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整體估值水平的影響隨存續時間發生變化,具有顯著的短期正面溢出效應和不顯著的長期負面溢出效應,且目的地市場成熟度與短期正面溢出效應正相關,盡管存在長期負面溢出效應但不顯著,這主要受到不同來源地影響。
從不同來源地看,不同來源地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整體估值水平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來自成熟市場的境外公司對目的地市場整體估值水平的正面溢出效應更顯著,而來自新興市場的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整體估值水平具有負面溢出效應。這說明溢出效應與公司的不同來源地密切相關,來自新興市場的公司確實存在聲譽尋租及“質量傳染”效應等負面影響,且當目的地市場與母國市場成熟度差異越大時負面溢出效應越大。
基于以上結論,提出如下建議:第一,目的地市場應增強與成熟市場之間的聯動性,大力引進成熟市場的境外公司上市,提高市場估值,增強市場競爭力。上市公司來源地也可挑選與目的地市場發展程度相近的新興市場,且發展程度越一致、聯動性越強的兩市場,其境外公司上市對目的地市場的沖擊越小,正向溢出效應越大。此外,目的地市場應建立規范的市場及公司管理條例,尤其對上市時間較長的境外公司實施重點監控,以減少境外上市公司對目的地市場的負面溢出效應。第二,鑒于中國證券市場的新興市場特性,面向成熟市場境外公司上市無疑是有正面溢出效應,如果面向“一帶一路”新興市場國家開放境外公司上市,由于其母國與中國市場成熟度差異不大,所以其負面溢出效應也不大,開設上交所“國際板”是可行的,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升上交所的國際競爭力,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