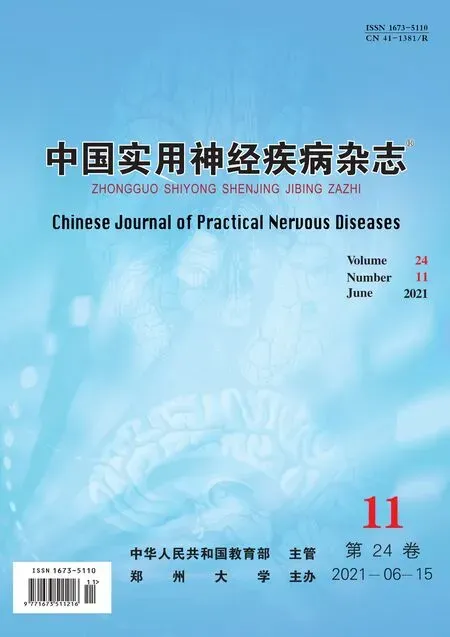阿爾茨海默病的生物標記物研究進展
劉亞君 王運良
解放軍第960醫院,山東 淄博 255300
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一種神經退行性疾病,也是癡呆最常見的病因。該病由德國精神和神經病理學家ALZHEIMER于1907年首次報道,盡管過去了幾十年,但許多機制仍然未完全了解[1]。AD是現代神經科學和醫學診斷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影響著全球約3 500萬人,預計2050年其發病率將增加3 倍。AD 是一種主要見于老年人的疾病,很多患者在65歲以后出現癥狀,由于目前還不具備從發病初就能進行早期診斷的知識或手段,因此很難證明病理侵犯從何時開始。其中散發性AD(SAD)占90%,5%~15%患者為家族性AD(FAD)。早發性AD(EOAD)發病年齡40~65 歲,65 歲以后的晚發性AD也被稱為遲發性AD(LOAD)[2]。通常情況下,AD的癥狀開始于輕微的記憶障礙,并逐漸發展為認知障礙、大腦功能失調及日常活動受損。雖然遺忘是AD早期發病最常見的癥狀,但研究者特別關注內側顳葉記憶功能[3]。被確診時患者許多腦區均出現了神經元丟失和神經病變。記憶障礙似乎與內側顳葉萎縮和低激活顯著相關,線粒體和皮膚電生理活動可能對檢測腦功能的改變有某些作用,但在臨床應用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根據最新的國家老年研究和AD協會工作組的標準,準確診斷可以基于一般的臨床和病理生理條件,以及幾種體內生物標志物和記憶測試的評估,將AD分為8種類型:前驅AD、AD癡呆、典型AD、非典型AD、混合AD、AD臨床前狀態、AD和MCI,但各型之間存在某些交叉且缺乏嚴格的界限[4]。由于目前對AD病因、病理學和明確的診斷標準尚缺乏全面了解,許多學者正在致力于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有關該病新的標志物,如神經顆粒蛋白、NFL、CCL2、CXCL8、CXCL10、CXCL12、CCL5、CX3CL1、CXCL9不斷涌現,通過綜述和薈萃分析,對有前景的生物標志物有了更清晰的認識[5-6]。本文對導致AD發生、發展的重要病理機制進行綜述。
1 AD發病機制和病理生理學
過去30 a來對AD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證據,證明異常折疊蛋白的積累導致神經元死亡,隨后引起神經退行性變過程[7]。AD最早發現的病理特征是淀粉樣蛋白斑塊和神經原纖維纏結(NFTs),因此,作為病理機制研究最多的是淀粉樣級聯和NFTs級聯[8]。盡管多年來一直在尋找該病的發病機制或治療方法,但基于這兩種最具特征性的癥狀,仍然缺乏治愈的方法。除這兩種假說外,也有多種假說試圖解釋疾病的觸發,如多巴胺能和淋巴系統假說。
1.1 淀粉樣蛋白假說老年斑的主要成分是β淀粉樣蛋白(A β),它是由前體蛋白(淀粉樣前體蛋白-APP)不適當水解產生,Aβ蛋白有兩種不同形式:Aβ40是一種不引起病理性積聚的蛋白質;Aβ42是一種淀粉樣蛋白,是淀粉樣斑塊的主要成分[9]。APP基因位于染色體21q21,編碼由3 個結構域組成的1 型跨膜蛋白:胞質中N 端的長胞外區段、短內皮段和短C端段。APP 蛋白由α、β、γ 3 種分泌酶的酶復合物加工而成。α-分泌酶將APP(CT83)的C端片段轉化為83 個氨基酸的可溶性肽,具有調節功能。β-分泌酶切割長度為99個氨基酸(CT99)的N-末端片段,該片段與細胞膜結合。γ-分泌酶通過非均相蛋白水解將CT83和CT99代謝為Aβ40和Aβ42形式的Aβ肽。Aβ42是一種危險的神經毒性形式,具有疏水性,并與老年斑的形成有關,大多數小膠質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負責產生這種形式的Aβ[10]。細胞外Aβ蛋白沉積,在控制記憶和認知功能方面起關鍵作用。研究發現APP基因的多個突變可導致EOAD,大多數突變集中在APP 基因Aβ編碼區。早老素1(PSEN1)和早老素2(PSEN2)位于內質網,是γ-分泌酶-蛋白復合物的輔助因子,盡管其機制和作用不同,但也參與了Aβ神經毒性形式的形成和FAD患者的發病[11]。早老素是具有8~9 個跨膜束的高度同源蛋白,在神經細胞中扮演膜受體和鈣通道的角色,提供穩態作用。在PSEN1基因已鑒定出185 個顯性突變,導致約80%的EAOD-AD。PSEN2 突變數量少,引起約5% EAOD。除基因突變導致AD外,遺傳因素也與AD發病有關,其中研究最多的是APOE,尤其是APOE4 亞型。APOE 具有某些不同功能,包括膽固醇轉運,它能與引起Aβ沉積形成的病理形態結合,作為膜受體影響新陳代謝。E2、E3和E4的半胱氨酸和精氨酸殘基在112 和158 位點不同,一個APOE4 等位基因使AD 發病風險增加3倍,兩個等位基因使AD發病風險增加12倍,與此相反,APOE2異構體與AD的風險較低[12]。
1.2 神經原纖維纏結假說AD 第2 個最常見的聚集物是存在于大腦不同區域的NFTs,主要由成對的高磷酸化tau蛋白螺旋絲(PHF)組成。細胞內高磷酸化tau蛋白聚集引起微管功能受損、軸突運輸或神經細胞骨架的破壞,從而導致神經元變性[13]。激酶和磷酸酶分別導致tau蛋白的磷酸化和去磷酸化,影響游離tau 蛋白和微管相關蛋白之間的平衡調節。蛋白質磷酸化和去磷酸化之間的失衡導致這種蛋白質與微管的結合受損,并形成PHF 和NFT[14]。磷酸化tau 蛋白結構可能受到Aβ、氧化應激、神經炎癥以及影響激酶和磷酸酶的影響,糖原合成酶激酶3(GSK3)、周期蛋白依賴性激酶5(CDK5)和微管親和力調節激酶(MARK)是3 種最重要的影響酶[15]。研究表明,CDK5參與tau-磷酸化和NFT進展,CDK5作為GSK3激酶的調節因子參與AD的發病。
1.3 淋巴系統假說人腦有4 種主要液體:腦脊液(CSF)、間質液、細胞內液和血液,最近研究發現,阻止β淀粉樣蛋白聚集和清除沉積代謝物的機制之一是淋巴系統(GS)[16]。GS 在清除腦實質分子中起重要作用,該研究在慢波睡眠期間進行并首次提供的直接證據,證實在靜息狀態下,組織間隙“廢物”的清除率增加。GS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CSF的壓力和流量,CSF循環的標記物表明,進入GS的通路是從動脈周圍開始,該通路圍繞著血管平滑肌細胞,與血管周圍的星形細胞尾足相連。腦脊液流量與足端星形細胞水通道和水通道蛋白4(AQP4)有關,GS對AD 和其他依賴于代謝異常的神經退行性疾病至關重要[17]。最近一項研究[18]認為,AQP4的不穩定表達與衰老有關,可能更容易受到腦內Aβ聚集的影響。GS 在睡眠時發揮最有效的功能,晝夜節律和睡眠紊亂可能是導致GS功能異常的另一因素。
1.4 多巴胺能假說多巴胺系統(DS)與帕金森病有關,但其在AD 中的作用正在研究中。AD 患者表現的錐體外系癥狀和淡漠,可以用多巴胺能失調來解釋。一項研究顯示,與對照組相比,AD 患者的多巴胺受體1、2(D1、D2)濃度降低,應用羅替戈汀等藥物治療AD 患者具有明顯效果[19]。AD 動物模型研究[20]也探討了神經元多巴胺喪失對記憶和獎賞功能的影響,該研究使用過表達人類突變APP的Tg2576小鼠AD模型,顯示在小鼠大腦斑塊形成之前腹側被蓋區的多巴胺能神經元喪失。這種喪失僅見于腹側被蓋區,而在黑質中沒有發現,因此導致大腦記憶和獎懲區域的海馬和伏隔核中多巴胺流動減少。
2 AD的診斷
AD診斷是現代醫學的重大挑戰之一,不僅在癥狀不明顯的早期階段,且在癡呆的最晚期階段也是如此。由于神經退行性變開始于癥狀出現之前的相當長時間內,即使癡呆的癥狀非常明顯,診斷的確定性也只能通過尸檢實現[21]。近年來,根據生物標志物和影像學數據更新了診斷標準,因此有必要采用多學科方法,包括影像學和臨床生物化學方法,并輔以神經心理學分析評估患者的狀態[22]。AD 的生化和影像學診斷標準基于AD 的主要特征:Aβ斑塊和tau-NFTs。放射性標記分子能夠通過血腦屏障并與Aβ斑塊或tau-NFTs結合,因此可以評估人腦中的聚集。首次開發的分子是匹茲堡化合物B,其能與Aβ結合,開啟了AD 成像時代[23]。在這些分子合成之前,只有通過MRI評估大腦萎縮。除匹茲堡化合物B外,目前已開發出能結合tau聚集體的放射性標記分子用于臨床檢查。
2.1 AD的生化評估除影像技術外,生物液體的生化評估也用于AD診斷。生化試驗評估了兩種Aβ亞型(Aβ40、Aβ42)和兩種tau 蛋白亞型(磷酸化tau 亞型和總tau 蛋白濃度)。認為CSF 中Aβ42是AD 的生物標志物,CSF中Aβ42濃度較低和腦組織中Aβ42濃度較高與Aβ斑塊存在相關,但這種現象不能解釋克-雅病和細菌性腦膜炎病例也存在CSF中Aβ42濃度降低和腦組織Aβ42濃度增高的現象[24]。為提高Aβ42作為生物標志物的特異性,研究發現Aβ42/Aβ40的比值明顯優于Aβ42濃度在疾病早期檢測腦內淀粉樣蛋白沉積。CSF總tau蛋白,包括磷酸化和非磷酸化tau是神經退行性變的常見生物標志物,但對AD 無特異性。相反,CSF 磷酸化tau 似乎反映了腦內神經原纖維纏結的形成[25]。為了更好地解釋這些結果并減少不同實驗室之間的差異,已開發出Erlangen 評分評估AD患者CSF生物標志物。該算法按照神經生物標志物正常(=0)到可能AD(=4)的順序排列,預測AD 患者輕度認知障礙患者(MCI)到癡呆的演變[26]。
2.2 有前景的生物標志物由于AD 導致神經退行性變,而這些神經變性發生于癥狀明顯之前數年,因此人們開始探索能夠在AD 早期診斷中發現腦損傷的生物標志物。神經絲輕多肽(neurofilament light polypeptide,NFL)是人輕肽神經絲蛋白(NEFL)基因編碼的一種內源性細胞骨架蛋白,可作為軸突損傷后CSF 和血漿的生物標志物。神經細胞死亡后,在腦間質和CSF中釋放NFL,并通過蛛網膜絨毛和血管周圍引流系統到達血液[27]。最近研究發現,攜帶該基因突變患者的血清中NFL濃度在最初癥狀發生前6.8 a 升高。此外,在癥狀出現前16 a 評估NFL 的年變化率能夠區分突變攜帶者和非攜帶者[28]。然而,NFL不能作為AD的特定生物標志物,在其他神經退行性疾病,如克-雅病、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癥、額顳葉癡呆、HIV相關癡呆等觀察到NFL濃度升高[29]。
另一種在AD 早期診斷中非常有用的蛋白質是神經顆粒蛋白,這種鈣調素結合蛋白主要在受AD影響最大的腦區表達,如皮層和海馬。該蛋白由興奮性神經元產生,與蛋白激酶C 有關[30]。一項研究比較了AD、額顳部癡呆、Lewy體癡呆、帕金森病和多系統萎縮患者CSF 神經顆粒蛋白的水平,發現AD 組CSF神經顆粒蛋白濃度高于對照組,表明CSF較高的神經顆蛋白濃度對AD具有特異性[31]。
動物模型和臨床研究已證明炎癥在AD 中起核心作用,AD 炎癥可加重神經功能缺損,炎癥分子可促進血腦屏障通透性。近年來大量研究探討了AD外周炎癥分子濃度的變化,ITALIANI 等[32]檢測IL-1家族細胞因子及其受體的循環水平,結果發現AD患者炎性IL-1 家族細胞因子較對照組明顯增加,尤其是促炎性細胞因子IL-1α、ILl-1β明顯增加。假設可能存在某種生理機制對AD 發病時的炎癥環境作出反應,可溶性受體sIL-1R1 和sIL-1R3 濃度增加,但sIL-1R2的濃度不增加。大量研究探討了AD患者血液或CSF 趨化因子濃度的變化,AD 患者血液CCL2蛋白[也稱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CP1)]濃度增加,CSF 中CXCL8(以前稱IL-8)濃度升高。有趣的是CXCL10[干擾素-γ誘導蛋白10(IP-10)僅在AD患者CSF升高,而AD患者全血CXCL9(γ-干擾素(MIG)誘導的單因子]濃度更高[33]。CXCL12的濃度變化不一致,血 清 和CSF 中CXCL12 濃 度 降 低,而CCL5 和CX3CL1 濃度降低只見于血清。這些蛋白濃度的波動以及不同趨化因子之間的差異可能與其所起的不同作用有關,目前尚無法確定上述趨化因子在外周血中的改變與CNS 退行性變有關,也可能由全身疾病或衰老引起[34]。
3 結論與展望
AD導致的癡呆是老年人的第五大死因,盡管早在一個多世紀之前就發現了該病,但目前尚不清楚AD的確切病理機制,因此是生物醫學和臨床研究的一個重大挑戰。盡管病因不清,但最重要的分子標志是淀粉樣斑塊和神經原纖維纏結,這些蛋白質的積累會觸發細胞死亡,導致持續的、不可逆的神經退行性變。基于目前證據已提出多種假說來解釋疾病的發生,包括淀粉樣蛋白、神經原纖維纏結、多巴胺能和淋巴系統假說等,但不應低估促炎分子在大腦炎癥環境中所起的作用,這種促炎環境可能是疾病的直接結果,也可能導致疾病的發生。研究目的不僅在于了解AD 的病因,更在于提高診斷性檢查,以便早期識別AD。AD 診斷應采用多學科方法,評估內容包括:受試者神經心理狀況、影像學檢查腦組織病理變化,以及特定病理蛋白的生化檢測。測定Aβ 40和Aβ42、磷酸化tau 和總tau 水平對AD 診斷具有重要意義,但更重要的是實施Erlangen評分和Aβ40/Aβ42比值以評價疾病的分期。由于經典生物標志物的特異性不足,需要尋找某些有助于早期診斷的新的生物標志物,如某些炎癥分子和突觸蛋白。盡管對AD生物標志物的研究取得很大進展,但對本病的診斷,尤其是病因診斷仍然沒有定論。鑒于AD 是一種異質性、多因素的疾病,診斷應以反映不同病理機制的多種蛋白質分析為基礎,結合影像學和神經心理學檢查。因此,有必要創建一組特定的蛋白質,其濃度將隨疾病的階段而變化。研究需要團隊合作構建精確的疾病模型,通過生物標志物濃度變化,利用人工智能(AI)建立疾病模型提供必要的數據,從而為疾病的發展提供更準確的診斷和信息。未來基于生化、神經影像和生命追蹤數據模型有助于識別AD最特異和最敏感的生物標志物,為AD早期診斷和預后提供重要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