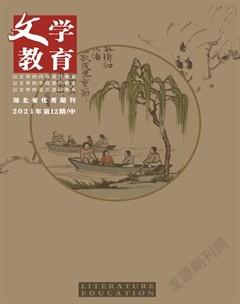從畢飛宇《玉米》看鄉村女性的悲吟
常劉宇

內容摘要:在畢飛宇的小說《玉米》中,一個個以玉米為首的、與權力密切相關的鄉村女子,她們在權力至上的男權社會中艱難地抗爭,卻最終走向了悲劇的深淵。本文將從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入手,分析鄉村女性在權力壓迫下的轉變,并與文學史中的類似女性相比較。
關鍵詞:《玉米》 鄉村女性悲劇 女性形象 權力
畢飛宇的《玉米》是他對鄉村題材的回歸。《玉米》講述了鄉村女性的悲劇,通過女性的生活和命運來揭示男權社會中女性的不可反抗。堅韌的玉米在不如意的生存困境中頑強抗爭,最終卻仍然走向了痛苦頹落的命運。李敬澤在序言中寫到:“玉米”與莫言《紅高粱》中的“高粱”一樣,都是貧賤的作物。在很多地方,玉米是鄉土中國中最普通而常見的作物。但畢飛宇把這個詞給了一個女人,他讓“玉米”有了身體,美好的、但傷痕累累的身體。在大眾認知中,莫言的《紅高粱》讓“高粱”在被人提起時顯現的是耀眼的紅、妖冶的綠,是豐饒而殘忍的大地;但因了畢飛宇,提起“玉米”這個詞,我們卻可以看到鄉村女性柔軟的眼淚,堅硬的身軀和對命運的頑強抗爭。
一.女性形象及命運探究
小說中塑造了許許多多的女性形象,畢飛宇也在女性人物上運用了大量筆墨。
1.女性形象探究
在本篇小說中,畢飛宇花費最多心思去揣摩的人物,也是最突出的女性,就是小說的主人公——玉米。
玉米是村支書王連方的長女,她漂亮而能干、懂事又顧家。小說中穿插提到:“玉米是母親的長女,而從實際情況來看,玉米自愿替母親照顧小八字,因為母親的懦弱和懶散,玉米將一家子的重擔挑在自己肩頭。不知不覺已經是母親的半個姐妹了。事實上,母親生六丫頭玉苗的時候,玉米就給接生婆做下手了。”由此可見,玉米在極小的時候,已經成為了家中的幫手。從表面,我們能夠看到的是玉米的勤勞和懂事,這是一個鄉村姑娘的極其動人的品質。但當我們深入挖掘玉米的家庭環境就能夠發現,玉米的懂事是一方面,但正因為是“長女”,玉米不能不懂事。在70年代的中國,農村仍然存在以家族為中心的宗法社會的鮮明特點,小說中隱晦地提到張、王兩大家族的明爭暗斗,家族間的爭斗跟人丁興旺與否關系密切,因此男嗣顯得尤為重要。玉米的父親王連方荒淫無度,而母親施桂芳懶惰軟弱,二妹三妹都還不能挑起擔子,其他妹妹年紀也都小,種種情況“逼迫”著玉米挑起家庭的重擔。
玉米任勞,卻不任怨,她絕對不能答應誰家比自家過得強。在知道父親尋花問柳之后,她再也不同作為家中最高掌權者的父親說話。這是一個倔強而又自尊的姑娘。在見到彭國梁后,小說這樣描寫:“女孩子的心里一旦有了心上人,眼睛就成了卷尺,目光一拉出去就能量,量完了呼啦一下又能自動收進來。”這些細致入微的描寫給玉米的形象又增添了幾分“小女孩”的色彩。
在小說中,雖然玉米有很多動人的典型的鄉村女性高的品質,但也有鄉村婦女的愚昧。在男權社會中,玉米在內心也是認為男孩比女孩更好。在家庭的變故和世道環境下,玉米在對權力的追逐中也最終喪失了人性光輝,她追逐權力、享受權力,最終在權力的深淵迷失自我。
除了玉米,小說中還出現了一位特殊的女性——有慶家的。剛出場時,畢飛宇將其描寫得極其放蕩,她帶著身子嫁到王家莊來,在王連方的性暗示下半推半就。但在小說后面,有慶家的在玉米猶豫見彭國梁穿什么時,給玉米送來了衣服,她對玉米說:“做女人的可以心高,卻不能氣傲,天大的本事也只有嫁人這么一個機會,你要把握好。可別像我。”在得知玉米被彭國梁退婚后,她還想著要去安慰玉米。她絲毫不在意玉米之前對她的嘲諷和輕蔑,甚至對玉米產生了同情。她說:“別像我一樣。”這是一個不幸的女人對另一個不幸的女人的同情和關懷。看到這里時,筆者已經完全顛覆之前對有慶家的這一形象的印象。她的放蕩可以說是這個女人對悲劇命運的極端性的反抗,在現實的壓迫下,她無能為力,只能通過摧殘自己的方式在麻木的生活中找到一點自己還活著的疼痛。
玉米和有慶家的同為鄉村女性,盡管性格不同、出身不同,但最終“殊途同歸”,都在一步一步走向悲劇的深淵。畢飛宇既有對這些女性的同情和悲哀,也有對這個特殊時代的鄉村文化的揭露和深深的批判。
2.女性命運悲劇的探析
玉米的母親施桂芳生子后越發懶散,玉米逐漸做起了家中的掌權人,她聰明伶俐,清楚地知道家中每個人的脾氣秉性,并通過抓住他們的弱點,來逐步掌握權力。這是玉米對權力追逐的開始。在此之后,玉米已經承擔起家中的大部分責任,成為家中真正的“掌權人”。在愚昧野蠻的氛圍中,儒弱而滿懷怨恨的人們變態地“在受難者身上獲得自己心理滿足的快感,而他人‘落難’便成為人們的普遺的潛意識企盼”,玉米在這樣極度困窘的情況下,還要替玉葉處理學校惹下的麻煩等等。身為家中的長女,玉米只能壓抑住心中的痛苦,盡管處理事情成熟穩重,但是玉米的尷尬處境也使自己受到了很多的委屈。
在有了這樣的經歷后,玉米愈發認識到權力的重要性。玉米讓父親給她說親:“不管什么樣的,只有一條,手里要有權。”盡管玉米知道郭家興道貌岸然,但她還是放下尊嚴出賣身體,這與之前玉米拒絕彭國梁肌膚之親時的堅決形成鮮明的對比,也是玉米開始轉變的顯著表示。那時的玉米還能夠因為羞澀和倫常守住貞操,但在命運的催使下,在權力面前,玉米將身體作為交換的商品。到這里,玉米已經完全轉變,對權力進行了更深的追求,為此不惜付出一切。
在權力場上,玉米逐漸被異化。為了鞏固自己在郭家的地位,玉米甚至將玉秀被強暴的事情告訴丈夫的兒子郭左,直接導致了玉秀懷孕又棄子的悲劇。在玉米回鄉后,她盡情享受權力帶給她的快樂。在對權力的追逐中,玉米也從純真的鄉村少女變成被權力異化的俗不可耐的婦人。最終成為一個徹底的唯權主義者。玉米命運的悲劇性就此完全形成。
二.男權社會下的女性
畢飛宇在小說的序言中提到:“中國人的身上一直有一個鬼,這個鬼就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們最基本、最日常的夢。這個鬼不僅僅依附于權勢,同樣依附在平民、下層、大多數、民間、弱勢群體,乃至于‘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身上。”
這段話使我們不能將《玉米》簡單看成是一個鄉村故事的縮影,更應該將它放到時代的大背景下,去探析男權社會中的女性悲劇。
1.“重男輕女”的現象探析
小說中提到:玉米的母親施桂芳連生了七個女兒,在終于生了兒子之后的揚眉吐氣和懶散。在村莊中,女人儼然成為了一個生育機器,她們除了生兒子,沒有其他用處。學習過所謂“辯證法”的王連方認為:“好種子才是男孩,種子差了則是丫頭。”雖說是村中的“文化人”,但運用辯證法得出的竟然是這樣一種結論。學過的辯證法,了解的內因、外因,竟然被這樣解釋,這雖然在我們現在看來荒謬而無理、諷刺而無知,但在那時男權至上的鄉村,卻是公認的事實。
甚至是玉米,這個不甘屈服命運,在后來掌握家中大權的女孩,也幼稚地認為:“王連方要不是在她們身上傷了元氣,媽媽不可能生那么多的丫頭。”玉米在男權的大環境中耳濡目染,“重男輕女”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
鄉村人的愚昧在這里體現得淋漓盡致,人們對某些觀念持有不公正的態度,這種態度毫無理由不講道理,卻無比根深蒂固。
2.男權駭人、女性依附的現象探析
王連方作為村支書,憑借權力在村中到處鬼混,有的女人迫于他的權勢,有的女人依附他的權力,最終都順從了他。王連方要人的事已經是眾人皆知,但礙于王連方“村支書”的官職,他們膽怯而沉默。沉默,即默許。作者在此諷刺:有了權力,就可以為所欲為。
在玉米認識到權力的重要性之后,她讓父親給她說親,條件只有一條,就是手里要有權。玉米用身體作為交換,在作為干部家屬回鄉時享受到了人們的巴結和奉承,也由此沉淪。
與王連方鬼混的女人和玉米最終以身換權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她們都是男權的依附者,或者說是附屬品。在權力的壓迫下,在男尊女卑的社會大背景下,她們只能通過出賣身體來換得權力。在畢飛宇的筆下,女性的命運悲劇來自對權力的追逐,但正是悲劇的命運促使她們去追求權力,這樣形成一個惡性的循環圈,將女性圈在其中,難以掙脫。
正如小說中所寫的那樣,玉米接到彭國梁退婚的信,才決定拿自己的婚姻做賭注,嫁一個有權力的男人重新安排自己和家人的命運。純真的鄉村姑娘成了權力的獻祭品,由此引發了悲劇的產生。
畢飛宇說:我只是描寫了一些我們必須經歷的場景,那些最普通的生活,那些像吃飯和呼吸一樣無法回避的必由之路。在我看來,人生的悲劇不是道路上鋪滿了地雷,而是有人在你的必經之路上埋下了地雷。
窺視整個文學史,我們可以找到與《玉米》中的人物類似的形象。
玉米不但沒有因為持家辛苦而抱怨,反而為能夠掌權而高興。這與《紅樓夢》中鳳姐這一形象有所類似,她們都是爭強好勝且很有能力的女性,但最終都逃不過命運的悲劇。除此之外,《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在一片徹底的冷漠仇恨中孤寂死去。玉米和曹七巧,一個是對權力的追逐,一個是對金錢的追逐,最終都造就了她們的悲劇命運。
由此可見,玉米的悲劇、鄉村女性的悲劇不只是她們對自己人生選擇所造成的悲劇,更是時代社會造成的悲劇。
參考文獻
[1]蔡建萍.無望的抗爭 女性的悲歌——分析畢飛宇《玉米》系列小說[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6,3(3):23-24.
[2]汪延芳.畢飛宇《玉米》中的長女形象探析[J].滄州師范學院學報,2016,32(6):18-20.
[3]昌切.性別與權利——評畢飛宇《玉米》和《玉秀》[J].文藝研究,2014,6(7):37-42.
[4]翁菊芳.“鬼文化”帶來的傷痛——讀畢飛宇的《玉米》[J].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5(5):33-36.
[5]吳雪麗.論畢飛宇小說的敘事倫理及其文學史意——以畢飛宇的“王家莊”系列小說為考察對象[J].南方文壇,2012,3(5):131-135.
(作者單位:南通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