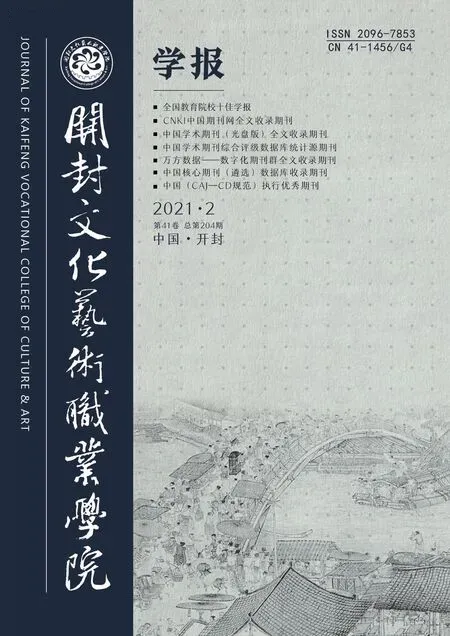中國書法審美“古”范疇探微
陳 悅
(華南師范大學 城市文化學院,廣東 佛山 528225)
中國書法最初以篆書和隸書為載體而呈現,之后又衍化出了楷書、行書和草書。中國書法審美范疇一直以來都有著厚古薄今的審美傾向,楷書的層次以帶有篆隸的色彩而稱之為高古,篆隸之意即為古意。東漢時期的書法家蔡邕認為:“此名九勢,得之雖無師授,亦能妙合古人,須翰墨功多,即造妙境耳。”[1]7這說明,在當時書法創作可以達到“妙合古人”的境界已經是對其作品的最高評價。
一、“古”范疇的藝術來源
但凡藝術,都有從粗糙到精致的發展階段,藝術在發展的總體過程中是逐步趨向于精致妍美的。然而,這種規律并不完全適用于書法藝術。中國書法的審美趨向不以精致和現代為美,而是以“古”為美,即推崇一種具有時間意蘊的美,強調渾厚的滄桑感和歷史感。
魏晉時期,書法藝術進入了空前的鼎盛時期,后世將這一時期的書法作品視為典范而爭相效仿。但在當時,人們卻不認為書法藝術正處于鼎盛時期。衛夫人在《筆陣圖》當中說道:“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才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1]21其批判了當時的書法創作“不師古”的現象,說明魏晉時期的書法一樣有厚古薄今的趨勢。到了宋代,米芾在其草書作品《論草書帖》中寫道:“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2]由此可以看出,米芾也是“崇古”的,米芾認為張旭沒有“崇古”,雖然懷素較好一些,但是也未達到“崇古”的境界。宋代朱熹認為古人作書在很多方面都要優于今人:“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3]書法家的“崇古”精神賦予了書法作品書卷氣,姜夔《續書譜》云:“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筆紙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1]392
人們對于“古”的追求來源于中國哲學當中的“道”,“道”是中國傳統美學的源頭,“道法自然”是中國傳統美學亙古不變的追求。古人作書講究實用,不同于今人的刻意而為之。古人作書講究實用,書法創作之時不加修飾,故有今人無法企及的古樸率真之感。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藝術技藝的多元化,人們漸漸舍棄了原本的古樸自然。當人們覺察到這一點時,便在藝術創作之中尋求這種漸漸被遺忘了的古樸自然之感。儒家也有著明顯的“崇古”傾向,《論語·述而》中就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4]的說法。中國人的潛意識里都有著強烈的“崇古”意識,這種遠古崇拜意識在書法創作當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復古”成為中國書法的審美趨勢。
中國書法的審美范疇一直具有“古質今妍”的傾向,有關“古”的釋義,唐代的竇蒙在其《述書賦》語例字格中云“除去常情曰古”[1]266。從商代甲骨文至今,中國書法藝術的存在經歷了三千多年的積淀,這些經歷了時間的考量而流傳下來的書法大家以及著名碑帖確實是書法藝術長河之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因而,書法追求“古”意,將古代的書法作品作為臨摹的不二之選,從古至今幾乎是不變的。臨習古代的名碑名帖、名家名作,可以確立規范的審美標準,很好地避免了書法作品浮躁淺顯、流于俗套。
二、書法線條之“古”
早在原始時期,線條就已經被人們用計數的形式而表現出來,那時候藝術還遠遠沒有出現,但是人類早已對線條具有了先天的感知能力。漢字的演變過程從早期的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到后來的隸書、楷書、行書、草書,都離不開線條。當代人們對于線條的認識已經發展到了美學領域,而書法在線條的運用上始終處于領先地位。在書法創作當中,線條一直是抒發情感意趣的造型元素,它將作者的內心所想和藝術感受逐一表現出來。因此,線條在中國書法創作中一直都發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藝術家在進行書法創作時賦予了線條豐富的表現力。他們的書法線條或拙澀,或質樸,或凝重。歷代書法理論家經常運用自然界中的事物來描繪書法線條,如衛夫人《筆陣圖》云“橫如千里陣云,隱隱然其實有形。點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撇陸斷犀象。折百鈞弩發。豎萬歲枯藤。捺崩浪雷奔。橫折鉤勁弩筋節”[1]22。宋趙佶在《宣和畫譜·顏真卿》中提出:“后之俗學,乃求其形似之末,以謂蠶頭燕尾,僅乃得之。”[5]理論家們都將線條的內在美外化,把抽象的書法線條比擬為自然之中的萬事萬物,賦予其栩栩如生的形象。如此抽象的比擬恰巧說明了書法家進行書法創作時是信筆書寫而不是刻意為之,在這種看似“隨意”的揮灑當中,往往蘊含著書法家精湛的筆墨功夫。東晉王羲之的《蘭亭序》、唐代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和北宋蘇軾的《黃州寒食帖》被譽為“天下三大行書”,這三件書法作品的共同特點都是“草稿”,正是這種信筆書寫而非刻意為之的狀態下“隨意”揮灑出來的效果,往往令人為之感動和贊嘆,從而成為后世書法家不斷師法的對象。
《黃州寒食帖》是蘇軾被流放到黃州時所作,在這一時期蘇軾的情感爆發,使得蘇軾的書法創作進入了一個大變革時期,這種變化在他的書法作品之中也體現了出來,《黃州寒食帖》便是這一時期的巔峰之作。此帖創作于蘇軾被流放到黃州的第三年,正值寒食節,蘇軾百感交集,于是,他把滿腔的屈辱與絕望都傾注于此詩之中,用筆墨詮釋他激憤的情緒。這幅行書作品的第一行介紹了創作的時間背景,前十個字的筆畫沉著有力,行距字距寬闊,整體行氣舒朗。在看似平靜沉穩的表象之下,字態卻是搖擺不定的,“來”“黃”“過”等字有力的折筆都體現出了他憤懣不平的內心。第二行“年”字突然增大,最后一筆豎畫直貫而下,之后,筆畫的提按頓挫削弱,牽絲映帶加強,行筆速度明顯變快,不同于之前拘束嚴謹的字勢,線條的擺動也顯得更加“隨意”,內心的復雜情感也借助毛筆躍然紙上。
書法線條之中的“古”體現了書法創作時書法家對于線條力道的把握,線條力道的不同決定了線條的質感。線條是抽象的,要想在書寫的過程當中把握線條的質感、美感和力量感,對于毛筆的運用要經歷一個熟能生巧的過程。運用毛筆之時須加以練習和推敲,以便更好地追求書法線條之“古”。
三、風格韻味之“古”
每一位書法家的書法風格的形成都經歷了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伴隨著人生階段的轉換、個人思想意識的轉變,在個人風格的呈現上也表現出了不同程度的差異,但追求“古質”的審美觀念一直是歷代書法家所重視的。唐代書家張懷瓘《六體書論》中說:“故學真者不可不兼鐘,學草者不可不兼張,此皆書之骨也。如不參二家之法,欲求于妙,不亦難乎!”[1]214張懷瓘認為,書法創作應該返璞歸真、追本溯源,要以鐘繇、張芝為師法對象,學習他們的書法精神。張懷瓘所提出的“復古”主張,有助于追根溯源,引導書法風格走向正統,推進書法風格在繼承中得到發展。
在書法風格上主張“習古”的書法家不計其數,徐渭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臨摹書法作品時主張學古,他認為充分理解書法作品之后才能為己所用,從而得以創新。學習書法有其必然的規律,開始學習書法時先要臨摹名家法帖,通過刻苦練習,打下扎實的基本功,在這個基礎之上博采眾長、大膽創新。徐渭《筆玄要旨》云:“一日不思便覺思澀,古人未嘗費書,須將名書日課臨數紙,方入書道。”[6]徐渭所說“方入書道”的前提是從古人的書法作品當中汲取營養。正如黃庭堅在《論書》中所說:“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1]354兩人所提出的觀點可謂是遙相呼應。徐渭認為,在“習古”的過程之中要注重方法。他在《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中寫道:“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7]
同一時期的書法家文徵明在書法風格上也主張“習古”。有關文徵明的取法,明文嘉《先君行略》述:“公少拙于書,遂刻意臨學。始亦規模宋、元之撰,既悟筆意,遂悉棄去,專法晉、唐。其小楷雖自《黃庭》、《樂毅》中來,而溫純精絕,虞、褚而下弗論也。隸書法鐘繇,獨步一世。”[8]文徵明深知成為一名書法大家需要對古人進行不斷地學習和繼承,他對于鐘繇、王羲之以及“宋四家”(北宋時期四位書法家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的合稱)皆有所取法。文徵明早期效仿宋人,他的行草書《西苑詩十首》從筆意而觀之,明顯是師法于“宋四家”的作品。而文徵明晚年的楷書作品風格則上溯魏晉,章法結字皆具鐘王之態。從文徵明臨作《黃庭經》可以看出,他在用筆、結字、線條、章法等方面與王羲之原作都十分相似,足以見得其對“二王”(指王羲之和王獻)取法之深。文徵明在向古人取法的過程之中,漸漸形成了自己清秀俊美、溫潤細膩的書法風格。由此可見,個人書風的形成需要經歷一段從量到質的長久過程,在此過程當中,“習古”便是每個書法家的必修課。
四、章法結構之“古”
書法章法是書法創作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書法章法是指字形以及結構安排的方式,包含點畫的空間分布、墨色的濃淡變化、篇章結構的合理安排等幾個主要方面。章法是書法家在構思書法作品時,謀篇布局必不可少的一個考量方面,也是書法創作中必不可少的一個考量因素,歷來備受重視。韓方明在《授筆要說》中說道:“夫欲書先當想,看所書一紙之中是何詞句,言語多少,及紙色目,相稱以何等書令與書體相合,或真或行或草,與紙相當。然意在筆前,筆居心后,皆須存用筆法,想有難書之字,預于心中布置,然后下筆,自然容與徘徊,意態雄逸,不得臨時無法,任筆所成,則非謂能解也。”[1]287論述了章法對于書法作品的重要性。
書法創作的章法布局方式有很多種,其中行書、草書以有行無列的布局為主,這種布局方式使得書法家在創作的時候自由發揮的空間比較大,能夠淋漓盡致地展現對比關系又不失法度。王羲之的《蘭亭序》、楊凝式的《韭花帖》、陸機的《平復帖》等都屬于此種布局形式,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無疑是有著“天下第一行書”美譽的《蘭亭序》。《蘭亭序》在線條、用筆、風格、結字、章法上皆受推崇,線條起收得當、富有彈性,用筆中鋒、側鋒結合,風格變化多端,結體虛實輕重對比明顯、骨力內含,章法天然、氣韻流動,帖中數次出現的字,用筆與結體均無一雷同、字字意別。在章法上,字距窄于行距,字與字之間筆斷意連、相映成趣,整體章法布局參差錯落又具平正之態,章法變化富有層次。正是“無意于佳乃佳”的書寫狀態使得《蘭亭序》渾然天成、章法經典,而被后世譽為“天下第一行書”。
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在中國書法史上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被譽為“天下第二行書”。《祭侄文稿》線條厚重而不遲澀,用筆以裹鋒頂紙為主,以加強線條的力量感。結體外拓,章法開闊,通篇以“勢”貫穿,正所謂“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1]6。顏真卿在章法布局上并非刻意為之,同樣處于“無意于佳”的書寫狀態之中,正是因為書寫時的不計工拙,所以作品中圈點涂抹的痕跡多次出現。但由于顏真卿技法嫻熟精湛、又具備超然物外的藝術境界,通篇揮灑之間線條、章法皆以勢出,呈現出一幅渾然天成的藝術作品。
結語
綜上所述,“古”范疇以其樸素的自然主義思維的特征,即拙澀、質樸、凝重的美學特色,與農耕文明和內陸文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密切相關。中國書法藝術獨特的審美形式只有扎根于傳統的民族文化特色,才能在吸收與融合中不斷前進。人們對于“古”范疇的探究,不僅是傳承優秀民族文化的首要切入點,而且體現出人們對于民族文化傳統的自信與底氣。在書法創作過程當中,毛筆的軟硬、運筆的力度、墨色濃淡的不同,都將決定書法作品的最終呈現。中國書法藝術之所以被稱為古老的東方藝術,是因為它融合了文學、繪畫、武術、音樂、舞蹈之中的意境、色彩、力量、節奏、動態之美,書法藝術與傳統民族文化密不可分,這也是中國書法審美范疇多元化的內涵所在。整體而言,中國書法審美范疇自始至終都沒有離開過一個“古”字,在學習書法之時,應當對于書法“古”范疇有一個全面的認識,這也有助于構建正確的書法審美思維,更好地學習中華民族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