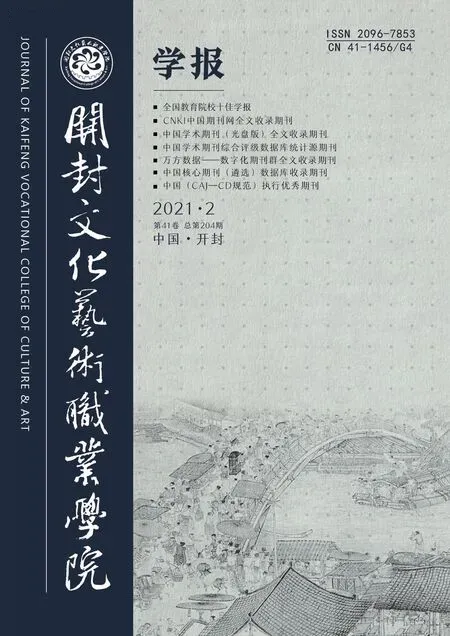隱在的“瘋狂”
——從福柯《瘋狂史》窺探莫言短篇小說《枯河》
馬加駿 呂 穎
(北方民族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
《枯河》是莫言早期創作的短篇小說之一,作者以一位身心不健全的男孩小虎的兒童視角俯瞰世界。主人公小虎,是一個“從來不知道什么叫生病的男孩子”,文中描寫的諸多細節都可以印證他是一個從小頭腦、身心都不健全的孩子。小說主要圍繞小虎爬樹意外摔落砸傷村支書的女兒小珍這一事件展開,人物、視角、矛盾主要集中于小虎身上,其在文本中具有“敘事人”與“敘事對象”雙重身份。小說以小虎的“癡兒視角”透視全文,作品中的環境、故事、人物、對話都經由小虎的“大腦”得以呈現,彰顯莫言的敘事藝術,呈現出復雜的敘事時空。作品延續了莫言之前先鋒的敘事風格,即打破傳統的線性敘事,敘事時空根據人物的意識流動或情節的發展使得現實與記憶交錯。并且,《枯河》屬于象征隱喻意味較為濃厚的作品,莫言從福柯對于“瘋狂”的界定入手,對文中“癡兒”小虎予以觀照,尋得闡釋“瘋狂”的路徑。因此,從福柯的《瘋狂史》進入莫言的書寫世界,探討他在《枯河》中的敘事生成機制,對把握作品中的隱喻所指、明晰隱在的“文本真實”具有積極意義。
一、癡兒視角與“沉默的考古學”
莫言早期的一批作品,如《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等中短篇小說,都屬于以“癡兒”作為敘事人的“白癡敘事”類型的文學文本,并有其內在的生成機制,特別是潛藏于“白癡”之后的隱秘話語,與福柯在《瘋狂史》中那套關于“沉默的考古學”的哲學話術異曲同工。福柯“已經意識到歷史記載中史實的被建構性,所以他要求呈現人們借以塑形和構序歷史研究本身的隱性理性結構,或者說是明確主張界劃和排除存在于歷史柵格構序之外的另類沉默存在,即隱在人們所指認的瘋狂和瘋子背后的真實歷史”[1]34。福柯在面對歷史存在之時,悉知歷史之外的諸多不可抗拒因素,導致“歷史”具備人為的建構性特征,并相信在此段被建構的歷史背后必然存在“隱性理性結構”以掩蓋“真實的歷史”。“瘋子”以“隱在真實”的功效存在于歷史之中,以遮蔽甚至可以毫不諱言地說,以建構歷史。所以福柯才會認為“‘瘋子’并不是天生的自然有序存在,而恰是‘一種文明的產物’,即某種在所謂的文明社會中才被入序和建構起來的東西”[1]34。也就是說,“瘋子”在福柯眼中是主觀存在于文明社會中,并基于文明的需要被建構起來的類群,它隱在的是平常理性結構和常識可見性中不可見的沉默存在。“瘋子”將不可言說或難以言說的“真實歷史”隱在于其在場之中。因此,福柯極力主張對“沉默的考古學”加以開掘。
在敘事策略上,作者除了以第三人稱“他”的視角敘述故事之外,還根據情節的推進和人物刻畫的需要,短暫切換視角,使得敘述過程頗具活力而不單調,積極調動讀者對情節發展與人物命運的思考。例如,《枯河》開篇描寫:“一輪巨大的水淋淋的鮮紅月亮從村莊東邊暮色蒼茫的原野上升起來時,村子里彌漫的煙霧愈加厚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的那種凄艷的紅色……一個孩子從一扇半掩的柴門中鉆出來,一鉆出柴門,他立刻化成一個幽靈般的灰影子,輕輕地漂浮起來。”[2]顯而易見,作品開篇采用的是全知視角,對事件發生當晚的環境近似“詭異”的描寫,交代了主人公小虎離家出走時的場景。這時的敘述者處于上帝視域,全知全能,既能看到月亮與原野,又能捕捉到一個離家出走的小孩。但仔細考察其敘事語言則不難發現,其有別于常規的全知視角,主要表現在對于月亮的“詭異”描寫——“一輪巨大的水淋淋的鮮紅月亮”。眾所周知,正常的月色或是皎潔明亮,或是暗淡朦朧,但都不會呈現出鮮紅之狀,這顯然有別于常人的敘述。而后對小孩離家出走的描寫也表現出“詭異”之狀——“他立刻化成一個幽靈般的灰影子,輕輕地漂浮起來”。孩子何以能成為一個幽靈般的灰影,漂浮著行走呢?全文中類似的“詭異狀”不勝枚舉,如“父親綠色的眼淚”“書記眼里噴著一圈圈藍煙”等,不禁加劇了我們對敘述主體身份的疑惑。但是,仔細推敲可以得知,這些“詭異”的描寫,都是基于文中小虎“白癡”的眼光。正是由于小虎的“白癡敘事”,文中的敘事話語呈現出“非理性”的特點。
而在以莫言創作為代表的新時期“白癡敘事”系列文學文本中,恰恰以所謂“白癡”的文學形象,隱藏了作者真實的敘事意圖。相較于作者所塑造的“文明”的文本世界,他們瘋癲、癡狂的行動,“非常識性”“非理性”的話語,顯得格格不入。他們的存在具有特別的文學意義,作者許多難以言說的“真實”,都假借瘋癲之由得以傾訴。如同福柯眼中“隱在的真實歷史的瘋子”一般,“白癡”形象也是作家主觀建構起來的用于言說“真實”的“工具”,他們的“非常人”形象,成為“隱藏”作者真實言說的軀殼。與此同時,正是由于這一軀殼,延伸了形象與意義的感知空間,成就了其藝術價值。“白癡形象”的符號學意義,即隱喻的深層結構,要遠超于他們自身的形象意義。
二、隱在的文本真實
以《枯河》為例,主人公小虎諸多“非正常”的行動與話語,都隱藏了作者欲闡述的“文本真實”,他的背景、遭遇、話語、行動都蓋上了一層濃厚的隱喻意義之紗。這一在常人眼中不起眼的“癡兒”雖然被視為與常人相異,但卻擁有那些所謂常人沒有的品質——反抗。他從出生到死去,都“努力的哭著,為人世的寒冷”。面對世人的譏諷與父親的暴治時,他毫不膽怯地以一聲聲“臭狗屎”回擊。在經受不公允的虐打之后,他遍體鱗傷,卻仍然尋求“反抗”,竭盡全力蜷伏在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枯河之上,并露出他那隱秘又充滿“暴行”的屁股,隱忍至翌日朝陽升起之時,伴隨著母親的慘叫與眾人的嗟吁,“他心里充滿了報仇雪恨后的歡娛,竭盡全力喊了一聲”,點燃了最后一絲反抗的火焰,但終究逃不出“熄滅”的命運。小虎生活在一個被他人定義為反常的環境,卻表現出最真實的行動與話語,讓人不禁反思:瘋癲的究竟是小虎還是外部環境?
“白癡敘事”是作家隱在深層含義時“沉默的考古學”,它同福柯所定義的“瘋狂”一樣,具有內在的發展過程與生成意義。如福柯所言,在文藝復興時期,“瘋狂在社會的視野中是作為一種美學的或日常的事實而存在的……在十七世紀,它失去了它在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時代原本具有的展現、啟示的功能(比如說,麥克白女士在瘋狂之后開始說出真相),它變成了嘲笑的對象,變得具有欺騙性。最后,20 世紀掌握了瘋狂,把它還原為一種與世界之真理相關的自然的現象”[1]34-35。“白癡敘事”正是作者在現代文明的視域內主動生成的敘事機制,是作家有意隱在“文本真實”的敘事策略。同時,它與新時期文學之初的時代語境密切相關。改革開放初期,作家對未來形勢和話語空間的判斷尚不明晰,“白癡敘事”的興起便顯得適逢其會,它為作家的話語生成提供了隱在場域。而文學批評者要做的,正是要將已經“還原為世界之真理”的自然現象還原——將人為隱在的“文本真實”還原。
三、潛隱于“瘋狂”中的保護機制
質言之,《枯河》最大的藝術成就,便是讓“白癡”作為敘事中心參與文本的生成,并隱藏了一系列作者的隱喻符號用于深化文本的外延意蘊。這一藝術構思,一方面是受到相關西方現代主義作家的影響,并在《透明的紅蘿卜》的“黑孩”形象中初步實踐取得不錯成效后,進而在《枯河》中錘煉這一技法;另一方面,其更重要的是想要隱藏,甚至是遮蔽自己的敘事意圖。
莫言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為其舉辦的新書發布會中談到他對于自己作品中“傻瓜”的認識:“聰明的人說自己是傻子,說別人是傻子的人才是傻子。”這句話對于《枯河》敘事意圖的揭示具有啟示意義。小虎是《枯河》中唯一一個“傻子”,他被人當眾嘲笑、爬樹、反抗等一系列“白癡行徑”所表現出來的真實反映,與文本中那群正常人形成鮮明對比,讓人不禁反問: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白癡”?莫言解釋道,同樣一句話或一件事,“傻的人”不容易引起別人的嘲諷,但換作是別人則完全相反。莫言既想借由“小虎之口”揭露一些現實性的敏感問題,也通過增加一些藝術性表達掩藏自己的創作意圖。
作者將文本中潛藏的能指符碼透過“白癡”的視角進行呈現,讓所謂的“不合理”現象合理化。“白癡視角”是文本中能指符碼得以呈現的形式要素,其更多通過“白癡”與“常人”間行為之落差起到反諷的藝術效果。正如福柯所言:“荒蠻狀態下是不可能出現什么瘋狂和瘋子的,因為沒有建構出一個關于‘正常人’的標準,自然就沒有不正常的瘋狂;而這種在現時代被釘上確鑿科學標簽的不正常的瘋狂,在以前的神性存在中,僅只是一種魔鬼附體的一段而已,只是到了20 世紀,才由現代醫學給瘋狂套上頸圈,把它塑性為自然現象,入序于這個世界的科學真理鏈。”[1]35而白癡敘事中諸多的“非理性”現象后隱藏的“文本真實”,才是莫言的匠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