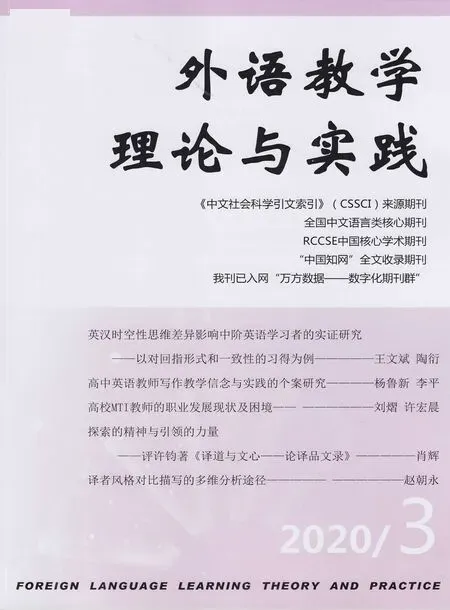社會(huì)翻譯學(xué)視域下“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因素之間的困惑*
——譯者行為研究關(guān)鍵概念芻議
哈爾濱工業(yè)大學(xué) 王軍平
提 要: 譯者行為研究中的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因素一直模糊不清,從理論上探討二者之間的區(qū)分與聯(lián)系,既是描寫性翻譯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訴求,也是翻譯文化研究與社會(huì)翻譯學(xué)研究理清各自視野與焦點(diǎn)的重要問題。通過概念界定和辨析,可以認(rèn)為,社會(huì)翻譯學(xué)視域下的譯者行為研究關(guān)注翻譯的社會(huì)性,聚焦譯作生成過程中譯者的社會(huì)化行為及其動(dòng)因,文化性因素則融入了譯者的認(rèn)知語境,是譯者行為背后可能的動(dòng)因之一。
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是一次具有深遠(yuǎn)意義的研究范式轉(zhuǎn)變,因此“毫無疑問,(它)是翻譯研究自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肇始以來最具有決定意義的轉(zhuǎn)折點(diǎn)”(Wolf, 2011: 2)。此后,翻譯研究一改語言學(xué)階段僅僅關(guān)注語言結(jié)構(gòu)層面的研究分析,將視角延伸到了文本以外的社會(huì)文化語境,探究翻譯在目的語文化中的功能以及翻譯過程中超文本的制約因素。翻譯不再尋求傳統(tǒng)的語言意義對(duì)等,而是作為文化歷史事實(shí),追蹤其文化交流功能及潛藏在翻譯背后的各種力量角逐,凸顯了“所有的譯文都反映了其生成的歷史文化條件”(Wolf, 2011: 2)這一特性。據(jù)此,翻譯研究對(duì)象被重新界定為“嵌入原語和目的語文化符號(hào)網(wǎng)絡(luò)中的文本”(Bassnet&Lefevere, 1990: 12),這一界定提供了一個(gè)全新的研究視角,譯文生成的外在社會(huì)文化因素便開始介入翻譯過程,研究的視域被大大擴(kuò)展,翻譯研究開始了從語言學(xué)規(guī)定性、原語朝向的語言分析走向了描寫性的、目的語朝向的功能描寫研究,實(shí)現(xiàn)了方法論上的突破,促成了描寫翻譯學(xué)的蓬勃發(fā)展。
從宏觀角度來看,“原語朝向”的語言學(xué)研究關(guān)注語言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強(qiáng)調(diào)語言層面的意義“對(duì)等”;而“目的語朝向”的文化研究則關(guān)注翻譯的外部語境,側(cè)重對(duì)翻譯過程中所有外在制約因素的描寫和分析。雖然后者所涉因素五花八門,但基本都被統(tǒng)轄在“社會(huì)文化”范圍之內(nèi),因此到處可以看到被“sociocultural-”這一復(fù)合前綴修飾的有關(guān)翻譯現(xiàn)象和翻譯過程所進(jìn)行的研究,“社會(huì)文化”因素成為了翻譯研究“文化轉(zhuǎn)向”之后的一個(gè)特定標(biāo)簽。但值得注意的是,從二十世紀(jì)大約七十年代“文化轉(zhuǎn)向”興起,一直到新世紀(jì)之初的近三十多年期間,學(xué)界對(duì)“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二者之間的區(qū)分都沒有給予重視,徹斯特曼(Chesterman)就曾指出:“翻譯研究已經(jīng)極大地拓展了它的關(guān)注點(diǎn),從偏狹的語言學(xué)視野拓展到了各種語境之下,但對(duì)于如何精確地厘定這些語境,我們還缺乏統(tǒng)一的理解”(2006: 9)。實(shí)際上,過去二十多年,翻譯口筆譯研究經(jīng)歷了一個(gè)“社會(huì)(學(xué))轉(zhuǎn)向”(Wolf, 2012; Angelelli, 2014),也就是在社會(huì)翻譯學(xué)研究,特別是譯者行為研究逐漸興起之際,有個(gè)別學(xué)者開始了對(duì)此問題的考量。
徹斯特曼認(rèn)為,翻譯的“文化轉(zhuǎn)向”更像是“社會(huì)文化轉(zhuǎn)向”,因?yàn)椤皩?shí)際上,文化轉(zhuǎn)向旗幟下的大部分(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相比,更加接近于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06: 10)。就目前學(xué)者們?cè)诖祟I(lǐng)域的研究課題來看,“至少可以說,這些題目既是社會(huì)學(xué)的,又是文化研究的”(Chesterman, 2006: 10)。沃夫(Wolf)則特別關(guān)注翻譯“社會(huì)轉(zhuǎn)向”中的譯者行為研究,甚至直接將此轉(zhuǎn)向稱為“行動(dòng)者轉(zhuǎn)向”(2012)。他在對(duì)翻譯研究發(fā)展過程進(jìn)行回顧,特別是對(duì)文化轉(zhuǎn)向進(jìn)行分析以后認(rèn)為,“翻譯過程的一個(gè)重要特性雖然沒有被完全棄之不理,但也是被廣泛地忽視掉了: 翻譯是一種社會(huì)實(shí)踐,因此需要考察譯者的角色以及作為社會(huì)代理人的其他參與者的角色”(Wolf, 2011: 3)。這一提議將翻譯研究的社會(huì)性凸顯了出來。可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對(duì)翻譯的“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因素,學(xué)界并沒有進(jìn)行相應(yīng)的區(qū)分研究,特別是近二十年,社會(huì)翻譯學(xué)發(fā)展過程中所催生的譯者行為研究,正在因面臨著“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因素的模糊不清而引起困惑。因此,我們需要關(guān)注的問題是: 首先,在翻譯研究中, “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兩類要素之間區(qū)分的訴求和必要性在哪里?其次,兩種因素之間到底有什么樣的區(qū)分和聯(lián)系?最后,基于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因素的區(qū)分,在社會(huì)翻譯學(xué)研究視野之下的譯者行為研究中,這兩種因素呈現(xiàn)怎樣的相互關(guān)系?
一、描寫性翻譯研究的理念與方法訴求
描寫性方法是譯者行為研究的主要方法,對(duì)譯者行為的解釋,需要我們對(duì)其背后的動(dòng)因進(jìn)行充分的描寫與挖掘。譯者作為社會(huì)個(gè)體所考量的因素,是譯者行為研究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所在。亨佩爾(Hempal)曾認(rèn)為就一門經(jīng)驗(yàn)性學(xué)科而言,主要有兩個(gè)目標(biāo):“一是對(duì)我們經(jīng)驗(yàn)世界中的各種現(xiàn)象進(jìn)行描寫,二是制定通用的原則,對(duì)這些現(xiàn)象進(jìn)行解釋和預(yù)測(cè)。”(1952: 1)據(jù)此,霍姆斯當(dāng)年就明確認(rèn)為翻譯無可否認(rèn)地是一門經(jīng)驗(yàn)學(xué)科,因此其研究目標(biāo)也就相應(yīng)地有兩個(gè):“一、對(duì)我們經(jīng)驗(yàn)世界中出現(xiàn)的翻譯過程和翻譯現(xiàn)象進(jìn)行描寫;二、建立能夠?qū)@些現(xiàn)象進(jìn)行解釋和預(yù)測(cè)的通用原則”(Holmes, 2000: 176)。因此,翻譯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先對(duì)翻譯現(xiàn)象進(jìn)行觀察,然后嘗試對(duì)其做出解釋,通過解釋分析,逐步建立通用的規(guī)則,來對(duì)翻譯現(xiàn)象進(jìn)行預(yù)測(cè)。基于此研究目標(biāo),翻譯研究的描寫過程就首先需要對(duì)翻譯過程中所涉及的各種因素進(jìn)行詳盡的分析,而對(duì)于某些翻譯現(xiàn)象的解釋都必須回到原來的社會(huì)文化歷史語境中去,尋找其背后的原因,找到彼此之間可能的因果關(guān)系。當(dāng)然,這樣的描寫會(huì)面臨很多的困難,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遵循上述思路的同時(shí),要注意不能產(chǎn)生簡單“機(jī)械決定論”的思想,也就是說,基于翻譯研究本身的復(fù)雜性以及社會(huì)文化因素的多樣性,我們不能簡單地對(duì)某個(gè)因素與翻譯現(xiàn)象之間的聯(lián)系進(jìn)行簡單的因果聯(lián)系和推理,也不宜對(duì)某一因素所產(chǎn)生的影響過度放大或者太過忽視。
描寫翻譯學(xué)的代表人物圖里(Toury)就始終避免尋求可能給予漂亮解釋的單個(gè)誘因變量,在他看來:“每一個(gè)單個(gè)的因素,都可能被夸大、削弱,甚至可能被其他的因素抵消”(Toury, 2004: 15)。這也就意味著決定論的推理不能對(duì)翻譯做出解釋。可是,如果拋棄了因果推理,那就意味著另外一種情況:“對(duì)翻譯現(xiàn)象的解釋就會(huì)變成一張張各種不同條件因素的清單,每種都有可能,卻沒有起作用的主導(dǎo)因素”(Pym, 2006: 5),翻譯解釋就呈現(xiàn)出了多元化格局(目前的研究狀況就是如此),除了讓解釋變得更加復(fù)雜之外,不會(huì)得出真正令人滿意的結(jié)果。雖然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承認(rèn)每個(gè)因素都可能發(fā)揮了作用,但沒有理由認(rèn)為,所有能想到的因素都能潛在地、平等地對(duì)翻譯進(jìn)行足夠好的解釋。面對(duì)此種窘境,圖里提出了“蓋然率”(Probability)的概念,嘗試擺脫此種尷尬的處境。
蓋然率意味著我們?cè)谔岢龇g解釋的假設(shè)時(shí),主要關(guān)注的是“趨勢(shì)”(Tendency),而不是機(jī)械的因果關(guān)系。“蓋然率采用‘越X,越Y(jié)’的形式,意味著我們的研究期望在一定程度上能預(yù)測(cè)一些解釋因素出現(xiàn)變化時(shí),可能會(huì)發(fā)生的事情”(Pym, 2006: 5)。比如,當(dāng)我們做出原語文化聲譽(yù)越高,翻譯就越可能采用異化策略的判斷時(shí),就意味著我們基于此前的研究,認(rèn)為文化聲譽(yù)可能與翻譯中的策略選擇存在因果關(guān)系,也就是說,“與其他潛在因素相比,該因素更有可能是其起因”(Pym, 2006: 5)。這種蓋然率的思考模式是描寫性翻譯研究的基本方法,但就具體的翻譯研究,特別是譯者行為研究而言,對(duì)翻譯解釋因素的蓋然率評(píng)價(jià),我們所要面臨的首要任務(wù),就是為各種已知的因素建立一個(gè)數(shù)據(jù)庫,以便在具體語境下尋找翻譯背后的最可能合理的解釋和最具有因果關(guān)系趨向的分析,而建立數(shù)據(jù)庫的前提就首先需要我們對(duì)翻譯過程中的各種可能因素進(jìn)行辨別與分析。因此可以說,在譯者行為研究之中,我們進(jìn)行“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 因素的區(qū)分,既是描寫性翻譯研究方法的根本訴求之一,也是我們對(duì)譯者行為進(jìn)行描寫和解釋的前提條件。
二、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因素區(qū)分的可能性
從歷時(shí)角度來看,“文化轉(zhuǎn)向”之后翻譯研究學(xué)派的研究中,都無法避免地涉及到翻譯過程中的社會(huì)因素。以勒弗菲爾(2004)為代表的“操縱改寫”理論,將翻譯置于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看成是一個(gè)受制于各種文化要素而進(jìn)行的“改寫和操縱”的過程。其研究的重點(diǎn)是翻譯過程中各種文化因素,比如意識(shí)形態(tài)、詩學(xué)等對(duì)于譯文生成的制約關(guān)系。但如果將所謂的“譯文生成”重置于具體的社會(huì)生產(chǎn)語境,就可以看到,在實(shí)際的翻譯過程中,這些因素施加影響的過程和渠道則主要是社會(huì)中的各種參與者,比如贊助人、專業(yè)人士、評(píng)論家等。通過他們,這些文化因素才能對(duì)譯者的行為產(chǎn)生制約,并最終“操縱”整個(gè)翻譯過程,而對(duì)于這些社會(huì)參與者之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以及各種參與者行為的研究,則主要屬于社會(huì)性的研究。因此可以說,在勒弗菲爾所勾勒的這樣一個(gè)文化因素制約的翻譯操縱改寫過程模式中,也到處都鑲嵌著各種社會(huì)性的因子。沃夫(Wolf)就認(rèn)為:
將翻譯視為社會(huì)實(shí)踐也是勒弗菲爾研究的核心。特別是改寫的概念,不但意味著在文本層面的操縱干涉,也意味著在社會(huì)力量互動(dòng)中引導(dǎo)和控制生成過程的文化機(jī)制,而在這一互動(dòng)過程中發(fā)揮作用的贊助人系統(tǒng)包括了個(gè)人、集體以及各種機(jī)構(gòu)。……勒弗菲爾不但將社會(huì)視角融于了這一概念,而且還通過布迪厄的文化資本概念對(duì)其進(jìn)行了拓展。而文化資本,在他看來,是一個(gè)特定文化中翻譯流通的驅(qū)動(dòng)力(Wolf, 2007: 10)。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翻譯過程中社會(huì)性因素發(fā)揮重要作用的主要機(jī)制。
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翻譯首先是一種具體的社會(huì)實(shí)踐,這就肯定牽涉到了各種社會(huì)因素,而每個(gè)具體的社會(huì)因素都具有其深層的文化背景,所以社會(huì)因素和文化背景一起,就構(gòu)成了翻譯的“社會(huì)文化”語境。但對(duì)于翻譯現(xiàn)象的觀察和解釋而言,直接從這么寬泛的視角進(jìn)行研究,恐怕難以獲得更有成效的成果。所以說,我們有必要對(duì)翻譯研究分成“社會(huì)的”和“文化的”兩類因素,進(jìn)行逐一分析,然后形成對(duì)翻譯過程和翻譯現(xiàn)象的綜合解釋和預(yù)測(cè)。因此,對(duì)于文化因素與社會(huì)因素的辨析和厘定,也就構(gòu)成了社會(huì)翻譯學(xué)的基本出發(fā)點(diǎn)。那么,鑒于“文化社會(huì)性”的緊密關(guān)系,對(duì)于二者的區(qū)分,是否可行并真的有必要嗎?
正如我們此前所言,描寫性是社會(huì)翻譯學(xué)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對(duì)翻譯現(xiàn)象與行為進(jìn)行描寫解釋,就如圖里所言,要考慮“蓋然率”的問題(Toury, 2004)。而對(duì)各種可能因素之間進(jìn)行一個(gè)相對(duì)比較清晰的區(qū)分,則意在建立起蓋然率選擇的數(shù)據(jù)庫。因此,對(duì)于“社會(huì)性”與“文化性”要素有必要進(jìn)行一些比較深入的界定和厘清。雖然社會(huì)與文化的關(guān)系可謂錯(cuò)綜復(fù)雜,誰也無法真正在二者之間劃分出一個(gè)明確的界限,但基于不同的研究要求、視角、方法的差異,進(jìn)行這樣一個(gè)基本的區(qū)分和辨別不但是必須的,而且從某些程度而言,也是可能的。徹斯特曼就認(rèn)為,“對(duì)‘社會(huì)文化’這一概念從中間進(jìn)行粗略的區(qū)分應(yīng)該是可能的,其中一個(gè)層面主要是社會(huì)問題,另一個(gè)層面主要是文化問題”(2006: 10)。這樣的劃分,能讓我們更加有效地把握翻譯問題的不同層面,因而更加有助于深入研究的開展。總而言之,在我們看來,其意義首先可以讓我們對(duì)翻譯的文化性和社會(huì)性有一個(gè)宏觀的認(rèn)識(shí)和把握,能夠增進(jìn)我們對(duì)翻譯復(fù)雜性的了解;其次,這樣的劃分有助于我們對(duì)翻譯過程、特別是譯者行為研究,構(gòu)筑起一個(gè)比較明晰的研究視角,通過對(duì)各種因素的辨別分析,明確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的異同,更利于探索譯者行為背后的各種制約要素和互動(dòng)機(jī)制;最后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劃分還具有方法論上的重要意義,因?yàn)樯鐣?huì)翻譯學(xué)研究整體框架的建立,最終需要在充分借鑒社會(huì)學(xué)研究方法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充分的描寫和分析,因此,對(duì)翻譯社會(huì)性與文化性因素之間關(guān)系的把握,有助于為研究方法上的開拓掃清障礙。
三、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因素辨析
文化是一個(gè)涵蓋面非常廣的概念,學(xué)界歷來對(duì)其界定林林總總,光定義就不下四百多種,而且還處在不斷的增加之中(吳克禮,2002)。很長時(shí)間以來,對(duì)如何比較精確地界定“文化”,總是存在不同的意見。當(dāng)然,作為一個(gè)術(shù)語,“文化”一詞在漫長的語義發(fā)展變遷中其內(nèi)涵與外延都處在不斷變化當(dāng)中。最近幾十年,學(xué)界好像慢慢取得了一些一致認(rèn)識(shí)(Katan, 1999)。其中克勞伯(Kroeber)和克魯克霍姆(Kluckholm)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他們?cè)趯?duì)以前160多種典型的“文化”定義進(jìn)行分析和比較的前提下,給出了一個(gè)總結(jié)性的建議。在他們看來:“文化包括通過符號(hào)傳遞的、已獲得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行為方式,構(gòu)成了人類群體的區(qū)分因素,包含了他們?cè)谄魑锷铣尸F(xiàn)的方式;文化的根本內(nèi)核是(比如,從歷史上衍生的、經(jīng)過歷史選擇的)傳統(tǒng)的思想,特別是他們所秉持的各種價(jià)值。文化系統(tǒng)可以一方面視為行為的產(chǎn)物,另一方面也可以視為未來行為的制約因素。”(Katan, 1999: 16) 這一界定將文化分成了兩個(gè)部分,一部分是體現(xiàn)在外在的行為方式,而另一部分則是其核心部分,包括了傳統(tǒng)的思想和價(jià)值。文化的核心部分,即價(jià)值思想層面是決定一種文化區(qū)別于其他文化的根本所在,是所有被一個(gè)文化所認(rèn)可的行為的最終根源,因此,行為與價(jià)值之間構(gòu)成了一種“向心性”(centrality)的關(guān)系。霍夫斯泰德(Hofstede)所提出的具有多層面的“洋蔥模型”(Onion Model)比較清晰地展示了文化的構(gòu)成:
文化的中心是價(jià)值,環(huán)繞價(jià)值的是實(shí)踐(行為),實(shí)踐包含了慣例、英雄人物以及符號(hào)。因此,我們?cè)竭h(yuǎn)離文化核心,我們就越深入到社會(huì)學(xué)領(lǐng)域,深入到了社會(huì)行為和包含各種機(jī)構(gòu)、物品生產(chǎn)和流通的社會(huì)關(guān)系領(lǐng)域(轉(zhuǎn)自Chesterman, 2006: 11)。
而文化系統(tǒng)的外在層面,則指明了文化系統(tǒng)同時(shí)可以是行為的結(jié)果,那就說明行為可以對(duì)文化產(chǎn)生影響,是外在的影響因素。而作為未來行為的制約因素,文化卻又對(duì)行為產(chǎn)生制約作用,這里的文化,呈現(xiàn)出了一種“結(jié)構(gòu)化”和“被結(jié)構(gòu)化”的雙重屬性。簡而言之,在文化核心思想與行為之間,存在一種持續(xù)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這是一種雙向的“因果”關(guān)系。對(duì)社會(huì)學(xué)和文化研究而言,“社會(huì)學(xué)家關(guān)注的主要是行為,而文化研究學(xué)者則更關(guān)注思想”(Chesterman, 2006: 11)。基于思想與行為之間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分,徹斯特曼將翻譯過程的主要語境劃分成下面三類:
一是文化語境: 關(guān)注價(jià)值、思想、意識(shí)形態(tài)以及傳統(tǒng)等;二是社會(huì)語境: 關(guān)注人(特別是譯者),他們可見的群體行為,他們的制度等;三是認(rèn)知語境,關(guān)注心理過程和決策過程等(2006: 11)。
實(shí)際上,在我們看來,就具體實(shí)際的翻譯過程而言,這三個(gè)層面的因素又可以大致歸結(jié)為兩類,因?yàn)殛P(guān)注人及其行為,實(shí)際上就包含了認(rèn)知語境,因?yàn)檫@里的“人”主要是指以譯者為代表的所有翻譯活動(dòng)的參與者,正是因?yàn)椤叭恕被蛘哒f“行為者”的存在,社會(huì)語境與文化語境才在認(rèn)知語境中獲得了聯(lián)結(jié)。換言之,認(rèn)知語境,涉及到的就是“行為者”行為背后的心理認(rèn)知與決策過程,正是認(rèn)知語境實(shí)現(xiàn)了文化語境與社會(huì)語境在行為者身上的統(tǒng)一。相對(duì)而言,沃夫?qū)Ψg過程的分析更加簡潔而具有概括力,他認(rèn)為:
翻譯過程,從不同程度來看,受到了文化和社會(huì)兩個(gè)層面的制約。第一個(gè)層面是結(jié)構(gòu)性的,包括了權(quán)力、統(tǒng)治、國家利益、宗教或者經(jīng)濟(jì)等影響因素。第二個(gè)層面關(guān)注翻譯過程中的行為者,他們不斷內(nèi)化上面提及的結(jié)構(gòu),并遵從他們的文化價(jià)值系統(tǒng)和意識(shí)形態(tài)來采取行動(dòng) (Wolf, 2007: 4)。
但同時(shí),沃夫也反對(duì)將文化與社會(huì)兩個(gè)層面進(jìn)行對(duì)立,因?yàn)椤皼]有文化,社會(huì)就無法得到充分的描述,同樣,沒有社會(huì),文化也得不到充分描述”(Wolf, 2007: 4)。由此可見,翻譯過程從頭至尾都涉及到了文化與社會(huì)因素,又加上二者的緊密關(guān)系,要想對(duì)翻譯進(jìn)行深入的研究和把握,就不能也無法將文化和社會(huì)進(jìn)行完全剝離。從我們前面的分析來看,翻譯研究學(xué)派,特別是“操縱改寫”論者主要關(guān)注于翻譯過程的文化層面,而對(duì)實(shí)際翻譯過程中社會(huì)層面的要素則很少或者可以說沒有給予應(yīng)有的重視,正如有學(xué)者所言:“誠然,文化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密不可分,然而,一直以來,在社會(huì)環(huán)境中探討譯作的生產(chǎn)與接受卻受到了極大程度的忽視”(胡牧,2011: 7)。因此,從社會(huì)生產(chǎn)視角來對(duì)翻譯過程進(jìn)行考察也就成為翻譯研究中“社會(huì)學(xué)轉(zhuǎn)向”的動(dòng)因。
在實(shí)際的翻譯過程描寫中讓人感到迷惑的是,有時(shí)我們很難明確對(duì)某個(gè)具體的因素進(jìn)行簡單的“文化性”或者“社會(huì)性”的辨別,因?yàn)檎缟厦嬗懻摰哪菢樱幕c行為(社會(huì))的關(guān)系就如一個(gè)連續(xù)統(tǒng)的兩端,從文化到行為并沒有一個(gè)特別清楚的分界線,兩者彼此影響與制約的關(guān)系更加讓我們無法具體地、清楚地分辨實(shí)踐中的你我。但在我們看來,文化與社會(huì)的基本分野卻并不模糊,社會(huì)翻譯學(xué)視域下的譯者研究關(guān)注的就是譯者的行為,涉及到了由社會(huì)生產(chǎn)關(guān)系所制約的所有“行動(dòng)者”的行為,這是翻譯的社會(huì)實(shí)踐層面的問題。因此,在社會(huì)翻譯學(xué)研究的視域中,所有行為者的行為都受到了各種社會(huì)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制約,也就是說,影響他們行為的首先是社會(huì)因素,比如個(gè)體的行為或者群體的行為,還有“譯者培訓(xùn)機(jī)構(gòu)、職業(yè)組織以及他們對(duì)翻譯實(shí)踐的影響,同時(shí)還涉及工作環(huán)境、翻譯中的倫理問題、翻譯政策等許多因素”(Wolf, 2012: 133)。相對(duì)而言,所有社會(huì)影響因素對(duì)行為者而言是一種“在場(chǎng)”因素,而文化因素的影響,只是參與者作為社會(huì)人,其行為背后的動(dòng)因之一,是社會(huì)人屬性的一個(gè)方面而已。簡而言之,以前的文化研究將翻譯過程納入文化力量角逐之下,將翻譯看成是文化“操縱”的過程;而社會(huì)學(xué)視角之下,翻譯是各種社會(huì)影響因素之下譯者行為的結(jié)果,文化只是影響行為者行為的因素之一。正是基于這樣的視角差異,我們可以看到各種概念里面社會(huì)性與文化性因素之間難以割舍的關(guān)系。值得說明的是,不同路徑的翻譯研究所建立起來的概念,雖然本身基于不同的研究視角,卻往往都融入了彼此的“模因”,社會(huì)翻譯學(xué)研究也不例外,這方面的突出代表就是圖里所倡導(dǎo)的“翻譯規(guī)范”研究。
可以說,圖里(2001)的“規(guī)范論”是社會(huì)翻譯學(xué)研究的里程碑之一。在他看來,翻譯是規(guī)范制約下的社會(huì)活動(dòng),這里的規(guī)范是對(duì)于外在社會(huì)和文化因素的一個(gè)總括,其雖然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潛在的行為準(zhǔn)則和關(guān)系契約,但同時(shí)也融入了對(duì)翻譯的價(jià)值認(rèn)知,包含了某個(gè)特定社會(huì)文化語境下人們對(duì)“何為翻譯”等問題的基本判斷。正是現(xiàn)實(shí)中翻譯過程的參與者,將本來我們所要區(qū)分的“文化”和“社會(huì)”因素融合了起來。而社會(huì)學(xué)視域下的行為者研究,是對(duì)包括以譯者為代表的所有翻譯參與者行為的研究,其重視個(gè)體與群體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與行為。在譯者行為研究中,翻譯過程就成了譯者通過對(duì)外在翻譯規(guī)范的習(xí)得,通過參考具體的、現(xiàn)實(shí)中的社會(huì)因素,在選擇遵從或者違背翻譯規(guī)范的互動(dòng)過程中做出翻譯決策的社會(huì)生產(chǎn)過程。也就是說,譯者行為的背后,是譯者針對(duì)面臨的實(shí)際條件進(jìn)行權(quán)衡抉擇的結(jié)果。在現(xiàn)實(shí)中,鑒于譯者的“社會(huì)性”和能動(dòng)性,順從規(guī)范并不是譯者的唯一選項(xiàng),有時(shí)對(duì)規(guī)范的“違抗”可能更能體現(xiàn)特定語境下譯者的社會(huì)性(王軍平,2017)。簡而言之,社會(huì)翻譯學(xué)視域下的譯者行為過程,就是譯者面對(duì)各種翻譯規(guī)范進(jìn)行抉擇的過程。譯者選擇遵從或者違背翻譯規(guī)范,是譯者對(duì)現(xiàn)實(shí)中的社會(huì)因素(當(dāng)然包括社會(huì)關(guān)系中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影響)進(jìn)行深入考慮,并與各種社會(huì)關(guān)系互動(dòng)之后所做的決策在行為層面上的反映。
四、譯者行為研究中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因素之間的關(guān)系
以勒弗菲爾為代表的翻譯研究學(xué)派注重翻譯中的文化因素,將譯作看作是文化因素影響甚至是“操縱”下的產(chǎn)物,其研究過程注重翻譯背后因文化地位差異而形成的文化權(quán)力、文化干涉對(duì)譯作生成的影響,似乎文化成為了譯作生成的真空,任何具體的、社會(huì)的因素都對(duì)其無從干涉,真正付諸翻譯行為的行為者都成為了文化的玩偶,整個(gè)翻譯過程中都沒有“人”或者“行為者”的主動(dòng)參與。而社會(huì)翻譯學(xué)研究就是要讓翻譯回歸現(xiàn)實(shí)世界,讓具有社會(huì)屬性的社會(huì)參與者都在譯作生成的過程中“現(xiàn)身”,將翻譯的社會(huì)性從文化研究學(xué)派籠統(tǒng)的“社會(huì)文化”語境中凸顯出來,關(guān)注譯作生成過程的社會(huì)性。基于這樣的理念,“文化性”因素與“社會(huì)性”因素在社會(huì)翻譯學(xué)研究中便具有了與以往不同的關(guān)系,主要體現(xiàn)在研究視角上的變化和調(diào)整。
有學(xué)者曾將社會(huì)翻譯學(xué)視域下的“行動(dòng)者”研究劃歸為“翻譯生產(chǎn)與傳播過程”的研究(汪寶榮,2019),選擇將包括譯者在內(nèi)的社會(huì)行為者及其社會(huì)行為視為主要的研究對(duì)象,將譯者的行為納入社會(huì)生產(chǎn)的背景下進(jìn)行研究,但這并不意味著徹底摒棄了對(duì)文化因素的考察。區(qū)別只在于社會(huì)翻譯學(xué)的研究是從社會(huì)因素入手,關(guān)注翻譯過程中行動(dòng)者,特別是譯者的各種社會(huì)化、角色化的行為(周領(lǐng)順,2013),以及各種社會(huì)行為與社會(huì)關(guān)系,從而對(duì)翻譯作為一種社會(huì)實(shí)踐中的各種翻譯現(xiàn)象進(jìn)行描寫解釋。文化因素則被視為譯者社會(huì)屬性中一個(gè)組成部分,成為了翻譯生產(chǎn)的背后場(chǎng)景,成為翻譯過程中譯者考量的一個(gè)視點(diǎn)而已。沃夫在談到權(quán)力關(guān)系時(shí)就提及:“文化路徑的研究已經(jīng)將翻譯過程中各個(gè)階段潛在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凸顯了出來,而現(xiàn)在則需要與社會(huì)中譯作以及譯者的在場(chǎng)性(situatedness)聯(lián)系起來”(Wolf, 2012: 133),也就是說,文化研究所揭示的翻譯中的文化因素,會(huì)作為當(dāng)前社會(huì)翻譯研究的一個(gè)視點(diǎn),用來和其他相關(guān)因素一起參與解釋,研究譯者及其他參與者在翻譯這項(xiàng)社會(huì)生產(chǎn)活動(dòng)中的行為。
從廣義上來看,翻譯始終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活動(dòng)。因此,任何語境下的翻譯研究都脫離不了文化因素,也就是說,文化是翻譯過程中各種因素互動(dòng)的交流場(chǎng)所,它為翻譯這種社會(huì)活動(dòng)提供了一個(gè)宏觀的背景,居于每個(gè)翻譯行為者潛在的思想認(rèn)識(shí)層面,所有的翻譯過程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進(jìn)行的。譯者個(gè)體與社會(huì)和文化的關(guān)系具體到實(shí)踐層面便是:“文化是成套的價(jià)值和傳統(tǒng),而社會(huì)作為人際間的關(guān)系系統(tǒng),是將這些價(jià)值傳遞給每個(gè)個(gè)體的一種機(jī)制。”(Tyulenev, 2014: 23) 社會(huì)學(xué)視域下的譯者行為研究根本不可能脫離文化因素的干涉,只是研究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是在譯作生成的各個(gè)階段,如作為社會(huì)個(gè)體的譯者、他的行為以及行為背后的因素,以及他與其他社會(huì)成員、社會(huì)環(huán)境之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這些活動(dòng)包括譯者對(duì)譯本的選擇、譯本的生產(chǎn)、譯本傳播以及接受的社會(huì)因素。譯者對(duì)文化層面因素的考慮,是其作為一個(gè)社會(huì)個(gè)體,在進(jìn)行社會(huì)生產(chǎn)實(shí)踐時(shí),對(duì)融入其基本認(rèn)知語境的一個(gè)不可忽略的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此時(shí)便作為社會(huì)人的一個(gè)不可或缺的認(rèn)知要素發(fā)揮著作用。因?yàn)槟軐⑸鐣?huì)與社會(huì)區(qū)分開的標(biāo)志是文化,而每個(gè)在特定社會(huì)領(lǐng)域中生產(chǎn)實(shí)踐的個(gè)體,必然帶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受到該文化因素的影響。但是,與文化研究不同的是,在將翻譯過程視為一種譯者的社會(huì)行為之后,譯者對(duì)于文化因素的考慮,是譯者在具體的社會(huì)語境下進(jìn)行主動(dòng)選擇的行為,不再是對(duì)外在文化因素“操控”的被動(dòng)接受。
五、結(jié)語
從社會(huì)翻譯學(xué)視域下譯者行為研究來看,任何翻譯活動(dòng)都是在特定社會(huì)中的社會(huì)行為。正是作為社會(huì)參與者之一的譯者將語言操作與外部語境進(jìn)行了聯(lián)系,讓翻譯得以在外部社會(huì)文化語境的制約下,在語言層面得以實(shí)現(xiàn),翻譯結(jié)果無論怎樣,都是譯者在社會(huì)語境中抉擇的結(jié)果。語言層面的研究和外在文化層面的研究,只有通過譯者的介入,才能構(gòu)成一個(gè)完整的社會(huì)生產(chǎn)過程。因此,對(duì)譯者行為的深入研究,就成為“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與“文化轉(zhuǎn)向”之后翻譯研究應(yīng)該重視的一個(gè)領(lǐng)域。目前出現(xiàn)的翻譯學(xué)“社會(huì)轉(zhuǎn)向”則是借鑒了社會(huì)學(xué)的相關(guān)理論和方法,對(duì)譯者的行為及其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進(jìn)行考察。翻譯被認(rèn)為是一種社會(huì)行為,譯者作為社會(huì)參與者中的一員,其行為雖然首先受到外在的社會(huì)條件(關(guān)系)制約,但最終的行為則是其本身作為“社會(huì)個(gè)體”在充分考慮社會(huì)條件的基礎(chǔ)上做出個(gè)人選擇的結(jié)果。而對(duì)“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因素的區(qū)分,能夠?yàn)樽g者行為分析和解釋提供更好的“備選菜單”,有利于凸顯翻譯的社會(huì)性,厘清理論上的混淆,促進(jìn)譯者行為研究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