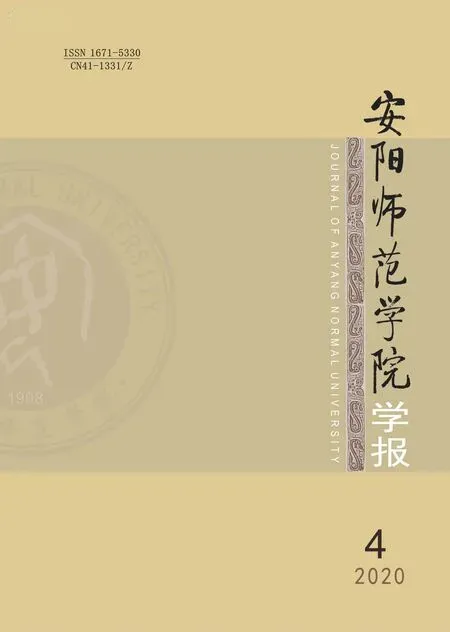明代河南府進士群體及影響芻議
劉林坤
(廣西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0)
北宋以后我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南移,中原地區(qū)的地位與前代而言已不可同日而語,但長期的歷史積淀,河南地區(qū)仍擁有豐厚的文化底蘊。河南府為河南布政司八府之一,作為河南較為發(fā)達的地區(qū),進士人數(shù)居河南前列。筆者根據(jù)《明清歷科題名碑錄》以及地方志統(tǒng)計,有明一代,河南府共有進士261名,居河南第三位。其中洛陽124人,偃師9人,宜陽5人,孟津13人,新安10人,鞏縣9人,澠池5人,永寧8人,嵩縣19人,登封8人,陜州14人,靈寶21人,閿鄉(xiāng)5人,盧氏11人。
明代河南府的人才分布極不平衡,就進士而言,洛陽的人數(shù)占據(jù)當時河南府總數(shù)的一半,其余十三個州縣占據(jù)剩下的一半。人才的地理分布上呈現(xiàn)了集聚現(xiàn)象,以府治洛陽為中心向四周輻射。洛陽在古代長期作為全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在人才的教育培養(yǎng)以及吸引力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優(yōu)勢。宋之后洛陽逐漸衰落,并且經(jīng)歷長期的戰(zhàn)亂,但相對而言長期積累下的文化底蘊尚在。因此,相比其他州縣,洛陽縣依舊擁有巨大優(yōu)勢。就個體來看,河南府下各州縣的文化水平參差不齊,除洛陽縣外其他十三個州縣進士人數(shù)較少,并且人數(shù)差別較大,其中人數(shù)較多的有靈寶(21人)、嵩縣(19人)。
有學者統(tǒng)計,明代鄉(xiāng)試的平均錄取率僅在3%至4%之間,會試平均錄取率也不到9%[1](P145),因此一名讀書人考中進士的難度極大,也更加顯現(xiàn)出進士官員的難能可貴。河南府進士除個別未入仕外,大多入朝為官。
筆者通過查閱地方志,對有明一代河南府261名進士最終任職情況進行了梳理和統(tǒng)計,除16人不詳外,有245人曾在中央或地方擔任不同品秩的官職。其中在中央任職的有124人:正一品(內(nèi)閣大學士)2人,正二品(尚書、都御史)21人,正三品(通政使、侍郎、副都御使)12人,從三品(太仆寺卿等)8人,正四品至正九品81人;在地方任職者有121人,其中正二品(巡撫)5人,從二品(布政使)13人,正三品(按察使)2人,從三品(參政、鹽運使)11人,正四品至正七品90人。
由此可知,明代河南府的進士官員,其任職品秩與職權(quán)大小有所不同,總體而言屬行政與監(jiān)察官職,擁有一定的實權(quán)。二百多名進士官員中,中央官與地方官各占一半,其中朝官以御史和尚書居多,地方官以知府、知縣居多。朝廷核心官員(從三品以上的官員)為74人,占總數(shù)的30.2%,六分之一的河南府進士官員或為七卿(六部尚書與都御使)或為封疆大吏(巡撫與布政使)。這些官吏中不乏清正廉潔、為國為民、造福一方的好官,對國家與地方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
一、為政清明,不畏權(quán)貴
河南府的進士們?nèi)氤癁楣俸螅蠖几矣谥毖约{諫,不畏強權(quán),彈劾權(quán)奸,為國為民,造福一方百姓,心系國家社稷。其中影響最大的便是洛陽劉健,為天順四年(1460)庚辰科進士,明中期名臣、內(nèi)閣首輔,輔佐孝宗“弘治中興”,歷仕英宗、憲宗、孝宗、武宗四朝。孝宗即位后,“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nèi)閣參預機務。弘治四年,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十一年春,進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為首輔。”[2](P4810)劉健主政期間,崇儒興學,興利除弊,注重實務。極陳殆政之失,指出財政困難之原因在于齋醮、織價、冗官、營造之浪費。后世評價“其事業(yè)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2](P4817)又如孟津喬允升,萬歷二十年(1592)壬辰科進士,為人剛正不阿,清正廉明,為官期間,興利除弊,革故鼎新,秉公辦案。“三十九年大計京官。允升協(xié)理河南道,力鋤匪類。而主事秦聚奎、給事中朱一桂咸為被察者訟冤。”[3](P6553)同其他東林黨人一道,力圖革新朝綱,重振大明王朝。崇禎年間,審判閹黨,平反眾多冤案,為后世所敬仰。“崇禎初,召拜故官。時訟獄益繁,帝一切用重典。允升執(zhí)法不撓,多所平反。”[3](P6554)
河南府進士還有許多堅持原則、不畏權(quán)貴之人。如靈寶許進,成化二年(1466)丙戌科進士,性格耿直,廉潔奉公,能謀善斷,大膽使用有識之士,量才而用。“陳鉞激變遼東,為御史強珍所劾,進亦率同官論之。汪直怒,構(gòu)珍下獄,摘進他疏偽字,廷杖之幾殆。”[4](P4923)因得罪太監(jiān)汪直,被構(gòu)陷下獄,遭廷杖,幾乎打死。其次子許誥,秉承父風,“尋劾監(jiān)督中官苗逵貪肆罪,進刑科右給事中。”[4](P4926)后因為得罪劉瑾,被貶為全州判官。三子許讃,亦因得罪劉瑾遭貶,“以逆瑾,矯旨謫山東臨淄知縣,罰米三百石。”[5](P343)偃師薛蕙,為正德九年(1514)甲戌科進士,嘉靖即位之初,朝中發(fā)生“大禮儀之爭”,與張璁、桂萼等人相持不下,反對世宗以生父為皇考,上萬言書,“撰《為人后解》《為人后辨》合數(shù)萬言上于朝。解有上下二篇,惟明大宗義書奏。天子大怒,下鎮(zhèn)撫司考訓。”[6](卷43)洛陽孫應奎,為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進士,嘉靖四年入為兵科給事中,時桂萼、張璁專權(quán),孫應奎上疏奏言,彈劾桂萼、張璁,不久便被下獄,貶為高平縣丞。
此外,還有為國計直言納諫、獻言獻策之人。如盧氏耿九疇,永樂二十二年(1424)甲辰科進士,為官清廉,以德行名著于世。正統(tǒng)初年,為兩淮鹽政,大膽革除弊端,“正統(tǒng)初,大臣言兩淮鹽政久壞,宜得重名檢者治之,于是推擇為鹽運司同知。痛革宿弊,條奏便宜五事,為節(jié)令。”[7](P4321)同時,為國家大計獻言納策,天順初年,耿九疇上書“陳崇廉恥、清刑獄、勸農(nóng)桑、節(jié)軍賞、重臺憲五事。帝皆嘉納。”[7](P4322-4323)陜州張九功,成化十四年(1478)戊戌科進士,為人博學負氣節(jié),積極獻言納策,“列三十余疏,皆國家大體。論孔廟從祀當黜荀況,進薛瑄。他如崇本恤民、救災儲蓄、防患抑貪等奏皆剴切,可施行。”[8](P598)靈寶李情,弘治六年(1493)癸丑科進士,“以進士授監(jiān)察御史,彈劾不避寵戚”,為人剛正不阿,因忤逆大太監(jiān)劉瑾,被貶為驛丞,“逆謹,謫其失,降驛丞。”[5](P343)洛陽劉奮庸,嘉靖三十八年(1559)己未科進士,時高拱專橫恣意,劉奮庸很是厭惡,隆慶六年三月,上疏條陳五事:“一,保圣躬;二,總大權(quán);三,慎儉德;四,覽奏章;五,用忠直。”[6](卷41)
明代河南府進士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主要在明朝中后期,有明一代河南府進士共出現(xiàn)了15位尚書,除耿九疇外,均為明代中后期。其中不乏靈寶許氏家族父子四尚書——許進,吏部尚書,次子戶部尚書許誥,三子吏部尚書許讃,少子兵部尚書許論。明末以孟津縣城為中心,四公里方圓之地,出現(xiàn)了刑部尚書喬允升、禮部尚書王鐸、兵部尚書李際期三名尚書,時人稱“孟半朝”。
二、屢立戰(zhàn)功,維護國家安定
進士為官多為文官,其中不乏在軍事上頗有建樹之人,他們在地方為官之時,充分發(fā)揮自身的軍事才能,為維護地方的安全與穩(wěn)定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明代河南府進士官員在軍事方面有建樹的如兵部尚書許論、王邦瑞、呂維祺、李際期等能臣,還有諸多名將。如靈寶許進,在巡撫甘肅期間,收復哈密。弘治十一年,吐魯番阿黑麻攻陷哈密,“尚書馬文升謂復哈密非進不可,乃薦為右僉都御使,巡撫甘肅。”[4](P4924)諸將膽怯,不敢進攻,許進便獨自與總兵官劉寧謀劃,“厚結(jié)小列禿,使以四千騎往,殺數(shù)百人。”[4](P4924)“十一月,副將彭清以精騎千五百出嘉峪關(guān)前行,劉寧與中官陸訚統(tǒng)二千五百騎繼之。越八日,諸軍俱會,羽集乜川。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僵臥。進出帳外勞軍,有異烏悲鳴,將士多雨泣。許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為!’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時番兵俱集,惟罕東兵未至,眾欲待之。許進曰:‘潛師遠襲,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及明,冒雪倍道進。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牙蘭已先遁去,余賊拒守。官軍四面并進,拔其城,獲陜巴妻女。賊退保土剌。土剌,華言大臺也。守者八百人,諸軍再戰(zhàn)不下。問其俘,則皆哈密人為牙蘭所劫者,進乃令勿攻。或欲盡殲之,進不可,遣使撫諭即下。于是探牙蘭所向,分守要害。而疏請懷輯罕東諸衛(wèi)為援,散土魯番黨與孤其勢,遂班師。”[4](P4924-4925)許進幼子許論,“幼從襄毅公,歷邊事,輒以操戈布陣為戲,喜談兵。始就外傳,善屬文,襄毅公心奇之。”[5](P568)少年之時跟隨父親許進巡歷邊防,熟悉邊境各關(guān)地形,“因著《九邊圖論》上之。帝喜,頒邊臣議行,自是以知兵聞。”[4](P4928)嘉靖三十三年,蒙古騎兵一萬余人進犯山西,被許論擊敗。嘉靖三十八年,許論奉命督薊、遼、保定軍務。蒙古人把都兒侵犯薊西,被許論擊敗。后又“分掠沙兒嶺、燕子窩,又卻,乃遁去。”[4](P4930)此舉鞏固了北方邊防,維護了京畿的安全。
宜陽的兵部尚書王邦瑞,當其尚為生員時,“山東盜起,上剿寇十四策于知府。”[9](P5270)嘉靖初年,遷固原兵備副使,適逢涇、汾巨盜李孟春,流竄劫掠河東、河西,王邦瑞發(fā)兵剿滅。而后被升為右僉都御使,巡撫寧夏。“寇乘冰入犯,設(shè)伏敗之。”[9](P5270)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發(fā)生“庚戌之變”,“俺答犯都城,命邦瑞總督九門。邦瑞屯禁軍郭外,以巡捕軍營東、西長安街,大啟郭門,納四郊避寇者。”[9](P5270)王邦瑞在兵部尚書任上,曾上疏條列安定天下的十二件事。
洛陽王冕,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進士,參與平復寧王叛亂。正德十四年(1519),寧王朱宸濠反,王冕時任萬安知縣,“長史多奔竄,冕募壯士數(shù)千人,從附王守仁攻復南昌。”[6](卷42)張松,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進士,官至都御使,總督宣大。上任之初,“任行及廣靈七寇入龍門,松以便宜召諸將,簡精銳,猝擊之,賊大潰。期年,寇復發(fā),前后十數(shù)戰(zhàn)。洗馬林之役,松躬援甲胄,破賊精騎數(shù)千,俘首甚眾。”[6](卷44)魏養(yǎng)蒙,萬歷十四年(1586)丙戌科進士,萬歷十八年(1590),播州土司楊應龍反叛,魏養(yǎng)蒙任湖廣路監(jiān)軍,指揮攻克海龍屯。
盧氏任佐,景泰二年(1451)辛未科進士,平固原叛亂,“土賊滿四據(jù)石城作亂,勢猖獗,殺傷吏民無數(shù)……佐趁勢掩殺,斬俘殆盡,遂平之。”[10](P417-418)韓鎬,成化十四年(1478)戊戌科進士,為抗倭名將,以“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撫浙江兼贊理軍務,統(tǒng)兵御倭寇。”[10](P419)多次擊敗倭寇,屢立戰(zhàn)功,倭寇聞之喪膽。永寧張論,萬歷三十二年(1604)庚戌科進士,崇禎二年(1628),升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撫四川。“時土酋奢崇明素蓄逆謀,至是據(jù)重慶以叛,墮名城四十有七,乘勢圍成都。”[6](卷41)張論剿滅奢崇明叛亂,開拓疆土兩千余里。
三、著書立說,教化鄉(xiāng)里
以科舉途徑為官的官員是明代官僚系統(tǒng)的主體,同時,他們的文化素養(yǎng)遠遠高于常人,在文化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明代河南府的進士中不乏孟化鯉、呂維祺等大儒,桃李滿天下,對社會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根據(jù)各地方志統(tǒng)計,明代河南府進士群體的著作有近70部,內(nèi)容涉及政治、哲學、軍事、地理、歷史、文化、倫理等方面,如劉健著《明英宗實錄》,喬縉著《性理辨惑》,焦子春著《登封縣志》,呂維祺著《孝經(jīng)本義》,衛(wèi)三省著《易經(jīng)正解》等。
明代北方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程度遠落后于南方,但是隨著政治的穩(wěn)定和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發(fā)展,至明代中后期,河南府的文化發(fā)展也呈現(xiàn)出繁榮景象。作為科舉制度的直接受益者,進士也十分重視文教事業(yè),他們修葺學校、創(chuàng)辦書院、著書講學,以實際行動參與文化教育事業(yè)。如陜州王以悟,致仕后歸故里著書講學,從者甚重,“與張抱初、張春宇、呂豫石諸人倡明師說,一時學者多向風。”[8](P602)著有《常惺惺稿》10卷、《解縛編》2卷等。又如新安孟化鯉,為一代名儒,在罷官歸家之后,在川上書院著書講學,一時名師云集,川上書院成為當時北方的一個學術(shù)中心,影響甚重,來自洛、澠、嵩、孟、永、汝、陜、秦、晉等地的學子,從者數(shù)百人。孟化鯉的弟子,同鄉(xiāng)呂維祺,因得罪魏忠賢,辭官回鄉(xiāng)。建芝泉書院,后又設(shè)立伊洛學會,著書講學,廣收門徒。孟、呂不僅對新安縣,而且對整個豫西地區(qū)的文教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明清之際,有數(shù)十位進士出自孟、呂二人門下,門徒遍布各地,多達數(shù)千人。
四、治理地方,政績卓著
河南府的進士,在地方任職時,發(fā)展當?shù)亟?jīng)濟文化,整頓風氣,使得政治清明、社會穩(wěn)定、百姓富足。比如靈寶許進,任山東按察司副使時,善辯疑案,被人們稱為神明,“滿三考,遷山東副使。辨疑獄,人稱神明。”[4](P4923)明末文學家凌濛初,在其小說《二刻拍案驚奇》中便有兩篇故事取自許進所斷的真實案例。“其時山東巡按是靈寶許襄毅公,按臨曹州,會審重囚。”[11](P228)“那個察院,就是河南靈寶有名的許尚書襄毅公。其時在山東巡按,見是任命重情,批與州中審解。”結(jié)案后受害者家屬慟哭“望空叩頭道:‘虧得許公神明,仇既得報,銀既得歸。愿他福祿無疆,子孫受享!’舉家頂戴不盡。”[11](P59、265)對許進極盡褒獎。在陜西任職期間,許進整飭吏治,遍訪民情,加強邊防,整治軍務,興利除弊,“關(guān)中人謠曰:‘明鏡張,許重光。’進巡撫陜西,力格彊御,不為勢怵,馭下有權(quán),吏民無不神明其政。”[12](卷51)使得陜西政治清明,百姓富足,深得陜西百姓擁戴。嵩縣李輿,巡按陜西時,整治風紀,一時陜西風紀大振,“所至奸盜屏息”[6](卷41)。董相,為金壇令時,修筑城墻,罷黜了不利于邑民的法令,“筑邑城,故事不便民者,一切罷之。”[6](卷41)趙全,“初任安陸州,以清勤聞。時賦役繁重,全歸盡有方,無不就緒。”[8](P598)
遇到災荒,傾力救助,有些積勞成疾,病故于救災第一線。如陜州王言,為人清勤,造福一方,最后為治河患積勞成疾,“知順德府,以清勤聞,民為立生祠。調(diào)大明山東憲副,時黃河潰決。言馳往巡視,以勞致疾卒。”[8](P599)當?shù)厝嗣駷槠淞⑸簦阋娡跹栽诿癖娦哪恐械牡匚弧3苫荒?1475)乙未科進士何鈞,巡撫山西之時,遇災荒,極力救助,“巡撫山西,賑貸饑民,全活甚重。”[5](P341)盧氏李作義,出任山西汾陽知縣時,“在城立瞻士社倉,澗西村立廣濟社倉。每遇歲荒,計口授食,隨時賑濟,賴以全活者數(shù)萬人。”[10](P423)
除暴安良,保一方百姓。盧氏耿九疇,景泰初年,“鳳陽歲兇,盜且起,敕往巡視招撫。奏留英武、飛熊諸衛(wèi)軍更守,招來流民七萬戶,境內(nèi)以安。”[7](P4322)保證了帝鄉(xiāng)鳳陽的安寧。 李炳,為人忠直,不畏權(quán)貴,按撫京畿時,宮中宦官外出征稅,民眾苦不堪言,李炳從中斡旋,極大地減輕了民眾的負擔。任山東巡撫時,宦官稅監(jiān)橫征暴斂,民不聊生,李炳上奏皇帝,極力彈劾。孟津喬允升,萬歷二十二年(1594)調(diào)任太谷縣,在任內(nèi)五年期間,“以除強暴,翼良善為務”“修學宮,均賦役,實倉儲,嚴保甲,禁淫汰,懲奸蠢,抑豪強。”[13](卷3)使得太谷縣社會穩(wěn)定,人民生活富足,深得太谷人民愛戴。
五、致力于家鄉(xiāng)經(jīng)濟文化建設(shè)
由于地域回避制度,進士官員大多都在外地為官,因此仕宦生涯對本地區(qū)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的影響較小。但有不少官員會因為致仕、丁憂等情況回歸鄉(xiāng)里,為這些官員對家鄉(xiāng)的社會發(fā)展做貢獻提供了可能。同時,在仕官員亦可通過自身的影響力,對家鄉(xiāng)的發(fā)展起到一些作用。
新安呂維祺,致仕歸鄉(xiāng)后,十分關(guān)注民間疾苦。崇禎十二年,河洛大饑,“維祺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以振人心。王不省,乃盡出私廩,設(shè)局賑濟。”[14](P774)李自成進攻洛陽,呂維祺分守北城,城破被俘后,農(nóng)民軍中有人認識呂維祺要釋放,而呂維祺“于周公廟,按其項使跪,不屈延頭,就及而死。”[14](P775)偃師藺完植,萬歷三十五年(1607)丁未科進士,“以病乞休歸,居林下十余年,葛巾野服,片楮不入公庭,郡縣守令非公事不相見。里邑有為民蠹者,則力除之。”[15](卷16)
孟津陳惟芝,時刻不忘鄉(xiāng)里,“孟津苦沖,而協(xié)濟邑七百金。”[6](卷41)喬允升,萬歷晚期,齊、楚、浙三黨排斥東林黨人,喬允升被迫稱病告歸。在孟津西山寺著書講學,從者甚重。賦閑期間,喬允升還率眾出資修建了黃河永賴堤,保護了沿河百姓以及光武帝原陵的安全。同時,為官期間,他也為鄉(xiāng)里做了諸多好事。比如奏報朝廷,為河南鄉(xiāng)舉貢士增加了五個名額,“任太常時有《中州廣額疏》。”[16](P204)并呈文道、院,要求免除孟津每年的三千夫差,竭盡所能為鄉(xiāng)里做貢獻,“更以津濱黃流派夫累繁,具揭道院歷請豁免。為邑人所德,令專祠西郊春秋俎豆云。”[16](P204)崇禎十三年(1640)庚辰科進士李際期,當李自成進攻河洛,黃河南岸民眾想要渡河避難,卻被守河官員所阻。李際期聞訊,以全家性命作擔保,請守河官員放民眾渡河,“邑人北竄,官令斷航,不得渡。際期以百口為質(zhì)……發(fā)舟引難民橫流而濟者三晝夜。民皆泣拜曰:‘李公生我。’”事后,百姓在李氏祠堂立“救活萬人碑”,[16](P204)李際期被祀鄉(xiāng)賢祠。登封的焦子春告老還鄉(xiāng)之后,居家編纂了《登封縣志》,結(jié)嵩陽耆社,促進了當?shù)匚慕淌聵I(yè)的發(fā)展。
明代河南府的士子不僅在科舉中取得了輝煌的成績,而且對國家和地區(qū)的社會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河南府的進士官員在其宦海生涯,盡職盡責,不畏奸邪,為國為民,積極從事地方行政事務,政聲惠聞于當?shù)亍<词故莾?yōu)游林泉,也通過自身的影響力,積極參加地方社會公共事業(yè)的建設(shè),深受百姓愛戴和人民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