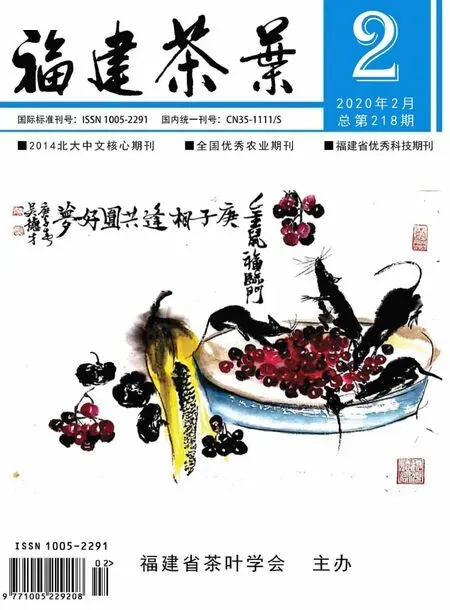包豪斯設(shè)計教育:誠實、普世與人本關(guān)懷
盧 宸
(中國地質(zhì)大學(xué)(武漢)藝術(shù)與傳媒學(xué)院,湖北武漢 430000)
戰(zhàn)后德國背景下的政治經(jīng)濟狼藉一片、亟待恢復(fù),而隨著包豪斯設(shè)計教育的出現(xiàn),其不僅在教育引導(dǎo)層面發(fā)揮了實際效用,在設(shè)計實踐層面更是影響至今,在當今設(shè)計教育領(lǐng)域仍保持著廣泛探討和應(yīng)用。進入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科學(xué)技術(shù)相較當時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國際格局和經(jīng)濟狀況也大不相同,再探包豪斯,研究這所學(xué)校設(shè)計教育思想的倫理性又能帶給我們哪些新的啟示呢?到底藝術(shù)與設(shè)計如何開展教育?包豪斯設(shè)計教育的意義和價值又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呢?本文基于這些問題作如下方面的研究與分析。
1 設(shè)計誠實:為更如意生活
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曾在其著作《建筑的七盞明燈》中強調(diào)設(shè)計誠實的重要性,“任何材料或任何造型,都不能本與欺騙之目的來加以呈現(xiàn)”。[1]在藝術(shù)批評章節(jié)的觀點中,道德意義幾乎是拉斯金衡量設(shè)計家和設(shè)計作品優(yōu)劣的唯一標準,而“設(shè)計誠實”則為重中之重,這一觀點也影響了包豪斯的設(shè)計教育思想。作為德意志制造聯(lián)盟的成員之一,魯?shù)婪颉な┩叽模≧udolph Schwarz)承擔過戰(zhàn)后德國科隆城市重建的重要工作。他曾談到在文化革新運動中德意志聯(lián)盟秉持的宗旨是“根除工業(yè)設(shè)計與手工藝生產(chǎn)當中所有的不誠實因素。”[2]在施瓦茨看來,由于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被一些不合理的繁瑣事物所困擾,因此他們的生活過得不盡如人意。究其根本,源于“不誠實”的設(shè)計。而要想建構(gòu)真實的生活,創(chuàng)建人性化的社會,唯有符合設(shè)計的誠實性才能達到這些要求,才能使之成為可能。與德意志制造聯(lián)盟的其他成員類似,施瓦茨關(guān)于設(shè)計社會功能的看法也充滿了濃重的道德色彩。把設(shè)計產(chǎn)品的質(zhì)量提升到關(guān)乎社會的倫理層面,是戰(zhàn)后德國設(shè)計師道德倫理意識的體現(xiàn),也是包豪斯設(shè)計教育的思想之一。
2 普世情懷:“逸想”還是“尋覓”
在魏瑪包豪斯時期,學(xué)校主張以教育終止人類戰(zhàn)爭,通過藝術(shù)與教育創(chuàng)建人類的自我實現(xiàn),強調(diào)作為個體的人對于國家與社會的價值,讓學(xué)生在藝術(shù)的認識和應(yīng)用上更具服務(wù)意識,增強他們對于藝術(shù)的社會責任感。[3]德意志制造聯(lián)盟(Deutscher Werkbund)產(chǎn)生于1907年,其創(chuàng)建者包括政治家、藝術(shù)家、建筑師以及設(shè)計師共同組成,希望通過設(shè)計的力量推動德國經(jīng)濟的復(fù)蘇。該組織對于戰(zhàn)后德國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意義重大,突出體現(xiàn)在對發(fā)展方向乃至具體規(guī)劃層面的推動作用上。伴隨多年的努力。該組織的設(shè)計理念研究與實踐落實到了社會經(jīng)濟的多個領(lǐng)域,尤其是住房和日用品設(shè)計方面,對于戰(zhàn)后滿目瘡痍的德國來說,此類設(shè)計即具有典型的民主性又具有社會責任感,這在戰(zhàn)后的德國顯得極其可貴。對于戰(zhàn)后的德國而言,政權(quán)的掌控者把設(shè)計作為“承諾給民眾以民主的、現(xiàn)代化未來”[4]的保障力。而實際證明了設(shè)計在日常用品中的應(yīng)用不僅實現(xiàn)了功能、美感與人性的較好統(tǒng)一,還為消費者勾勒了未來生活的美好圖景,給予民眾希望和信心。戰(zhàn)前設(shè)計理念中所推崇的“忠于材料本身”以及“形式的道德性”的價值觀被認可、被運用,在戰(zhàn)后發(fā)揮了巨大作用,推動了戰(zhàn)后的經(jīng)濟振興,并成為了設(shè)計領(lǐng)域的重要準則。對于設(shè)計師的社會角色而言,社會參與感以及社會價值的實現(xiàn)帶來的是自我認知的提升;更深層的意義則是,設(shè)計師將設(shè)計理念融入物質(zhì)生活用品當中,實現(xiàn)了實體在文化體驗上的一次升級,帶給社會價值與文化軌道一次有益重塑;相對來看,政治層面多是出于關(guān)懷式的道德倫理,是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普世情懷,設(shè)計師則是切實將理念融入社會并帶來巨變的突出個體,如貝倫斯(Peter Behrens)、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布勞耶(Marcel Breuer)、華根菲爾德(Wilhelm Wagenfeld)等代表了德國設(shè)計精神的幾位設(shè)計大師。
3 烏托邦氣氛:絲絲感動與人本關(guān)懷
包豪斯的第一任校長、著名的建筑師沃爾特·格羅佩斯(Waiter Gropius)曾說:“我的設(shè)計要讓德國公民的每個家庭都能享受6個小時的日照(圖15-20)。”包豪斯有一名叫納吉的教師曾經(jīng)有過一段這樣的自我詢問“我對自己所承擔的責任源于在戰(zhàn)爭期間對于現(xiàn)狀的思考,在那段時間我肩上所擔負的責任愈發(fā)重大。這種意識不斷地在向我發(fā)問:在這個社會劇變的時代里,我是否還要作一個悠閑的畫家,在朝不保夕的時候,作為一個畫家是否是一種罪惡。”并且他開始對于藝術(shù)創(chuàng)造進行了富有哲理的獨特個人反思“過去的100年間,藝術(shù)與生活各不相干。我們是否只是沉醉在自己的所謂藝術(shù)構(gòu)思和創(chuàng)作中,而遠離了擁有世界最珍貴藝術(shù)來源的廣大人民”由此可見,他們的設(shè)計理念都非常關(guān)注每個公民的日常生活,進行的是“大眾性、關(guān)懷性的設(shè)計活動”,即對大眾,對每個家庭的關(guān)懷,設(shè)計有著濃濃的人情味。他們進行的設(shè)計活動不是對形式考慮的結(jié)果,而是解決問題、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結(jié)果。
如上所述,一方面,包豪斯設(shè)計理念對于當時德國的影響不僅在設(shè)計領(lǐng)域改變了戰(zhàn)后德國,還對德國設(shè)計文化的諸多元素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其中最顯著的影響就是其改變了人與物之間的關(guān)系。德國民眾開始以“消費者”的身份親自參與到設(shè)計之中并體驗它。人民所有日常瑣碎生活的體驗與物件在設(shè)計的重造下,逐漸成為精致生活的符號。大眾不再滿足于日常用品在基本功能方面的實現(xiàn),而開始轉(zhuǎn)向關(guān)注卓越的工藝、造型的美觀及平易近人的價格等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經(jīng)歷戰(zhàn)爭的德國設(shè)計范圍和重點發(fā)生了偏移。設(shè)計的最佳場所轉(zhuǎn)移到世俗與大眾生活產(chǎn)品設(shè)計方面。基于當時情況,二戰(zhàn)對德國本體的創(chuàng)痛深入骨髓,戰(zhàn)后重建的任務(wù)艱巨。而最終的成果喜人,很大部分源于設(shè)計層面的變革帶來的積極影響。在原有的設(shè)計結(jié)構(gòu)中,“社會”與“國家”的理念與結(jié)構(gòu)貫穿始終,而變革過程中“家”與“家庭”理念結(jié)構(gòu)的進入使得個體和微觀得到重視,原有的德國設(shè)計文化發(fā)展巨變。正因如此,日用與家用設(shè)計讓德國民眾獲得了設(shè)計新體驗。
從魏瑪包豪斯開始所影響的德國設(shè)計講究“真實性”、“人情味”注重設(shè)計的“真、善、美”,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蒙德·羅維(Raymond Loewy)在美國被視為民族英雄,在羅維的設(shè)計理念當中,追求流線型風格特點,并崇尚銷售曲線的實際價值,其受到美國的廣泛推崇并帶來美國經(jīng)濟的蓬勃,而在德國設(shè)計界卻遭受到強烈的抵觸,被視為美國設(shè)計腐朽面的典型代表。美國風格設(shè)計的主要特點是要“刺激”消費者的眼球,實現(xiàn)感官層面的刺激從而刺激消費者非理性的消費行為,這在德國設(shè)計界看來只是一種偏離了設(shè)計誠實性、虛偽、不負責任的非道義行徑。從“流線型”風格在美國的應(yīng)用來看,泛濫式應(yīng)用和過分追求商業(yè)利益,使得該設(shè)計風格的本真價值被掩蓋,裝飾與外觀的表面化使用造成設(shè)計理念的架空,消極意義遠遠大過積極意義。從包豪斯設(shè)計教育角度來看,該設(shè)計理念當中功能和人本關(guān)懷的缺失,極大地背離了戰(zhàn)后德國設(shè)計的時代追求。
4 結(jié)語
在今天回望包豪斯,從其設(shè)計教育的誠實、普世、人本關(guān)懷等倫理性的視角挖掘并剖析包豪斯設(shè)計教育的思想精髓,可極大幫助設(shè)計教育在理念與實踐上的同步革新,為設(shè)計者的創(chuàng)新培養(yǎng)打造根基,將大眾需求作為設(shè)計的風向標,這樣的設(shè)計師必定會獲得和擁有作為設(shè)計者的真正尊嚴。而就設(shè)計尊嚴的實現(xiàn)來源來看,是以設(shè)計倫理為基礎(chǔ),以設(shè)計道德為規(guī)范,兼顧兩者的自我探索與實踐作為設(shè)計行為的前提,因為,“道德是惟一能使一個有理性者成為目的自身的條件;惟有通過道德,他才可能在目的王國中成為一個立法者。因此,道德以及有能力擁有道德的人,是惟一擁有尊嚴者”[5]。這也是我們再研究包豪斯設(shè)計教育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