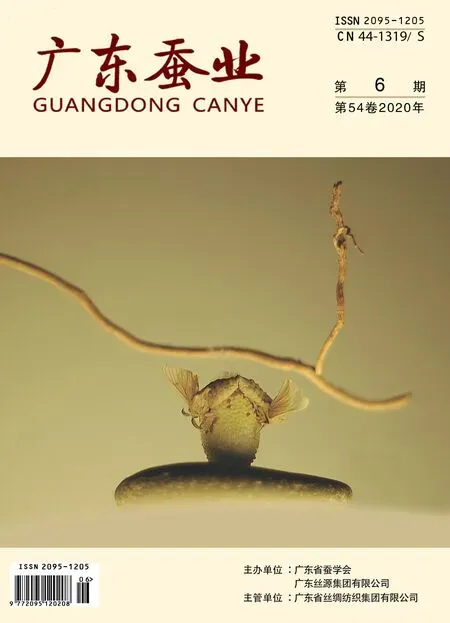微生物降解DDT的研究進展
劉橦昕 葉嫣然
(河南大學邁阿密學院 河南開封 475004)
重金屬、農藥等嚴重損害了環境,并且污染帶來的影響還在持續,污染類型也在向復合型污染轉變[1]。DDT 相對穩定且生物可降解性相對較弱,屬于環境里十分多見的相對復雜的有機氯農藥類污染物,因此它比簡單的有機物更難降解,半衰期也更長。
1 DDT 的毒理性
DDT 曾廣泛在全國范圍內使用,但由于它的難降解性和富集性,即使在1983年已禁止使用,現如今我國各個地區土壤中的DDT 含量還是嚴重超標。如果DDT 和其他物質結合,造成的危害更大。殘留的DDT 跟隨食物鏈進入機體,不利于機體健康。動物DDT 中毒后,會表現出對恐懼的異常敏感性,對正常的閾下刺激產生劇烈反應。隨著中毒次數的增加,會產生像士的寧中毒一樣的過敏性,如果保持食物攝入,那么震顫可能持續數周或者數月。DDT 會導致人體的生殖系統受到影響,生殖能力減弱、行為異常、荷爾蒙紊亂、免疫受限與中樞神經及各器官組織的紊亂等[2]。所以,處理被污染的土壤是我們現在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2 DDT 的微生物修復方法
現如今,物理法和化學法的缺點明顯,DDT 土壤修復重點借助生物法。比如植物修復、微生物修復及植物微生物聯合修復等三大方式,文章具體說明微生物修復法的研究情況。
微生物修復表示微生物通過有機污染物給僅有碳源與能源,或和別的有機物質開展共代謝等手段完成污染修復的方式。微生物降解DDT 還包括細菌與真菌兩大類降解。細菌降解主要通過還原脫氯降解DDT、脫氯化氫之后開環降解DDT、直接開環降解DDT 三大手段。真菌利用還原脫氯手段或借助羥基化反應完成DDT 的降解[3]。
2.1 專性降解菌
這類微生物包括在環境影響下具有降解能力的土著菌,但土著菌有生長緩慢、抗干擾能力弱等特性,對DDT土壤沒有顯著的修復作用。潘淑穎了解到,比較在土壤里分離所得的土著微生物來看,白腐真菌更能夠降解土壤[4],也能夠通過基因工程方式開展培養,但這項技術是否被應用和發展在國際上還存在爭議。在被DDT 污染的區域也可獲得對DDT 有抗性或者有分解能力的微生物。研究人員可在被污染的土壤、污水中分離出專性降解菌或在實驗室培養獲得[2]。
現在學術界十分關心污染區對專性降解菌的分離。李紅權等在化工廠收集土樣、分離、篩選好1 株可以于好氧環境中有相對可觀的DDT 降解率的菌株DH-7,且進行深入分析,發現該菌株對DDT 10 d 的降解率是73.6%,改善培養環境滯后,發現該數值提高至 81.4%[3]。Adi Setyo Purnomo 等從牛糞堆肥中分離并鑒定了14 個真菌菌株,這些真菌在馬鈴薯右旋糖肉湯培養基中,在30 °C 和60 °C 時均具有很高的降解DDT 的能力[5]。
2.2 植物根際促生菌
植物根系對于微生物的強化影響表現在給微生物帶來氧氣保障其在根系位置的好氧功能,并給其帶來影響,確保根系的相關菌群有良好的環境且促發對微生物的降解,提高降解水平[2]。鄭學昊利用加入根際促生菌與木質素對“鼠李糖脂強化油菜-專性降解菌聯合修復 DDTs-PAHs 污染土壤”展開調控,發現根際促生菌與木質素聯合調控方式能顯著祛除DDTs,甚至有27.48 %的去除率[6]。
2.3 表面活性劑
表面活性劑表示尾端包括了非極性、疏水性基團,頭端包括了極性、親水性基團且能夠讓表面張力減小并存在表面活性的物質之一。疏水性有機化合物 DDT 能滲透到非極性內核,水體里的溶解水平就會明顯增強。表面活性劑包括了離子型(陽離子與陰離子)、非離子型、兩性型、復配型與其他型等各類。且于20世紀70年代研究所得的生物表面活性劑備受關注,它一般是由微生物或者植物生長發育或繁殖過程中培養所產生的[2]。在降解DDT 的過程中,表面活性劑是常常使用的,并且產生了較好的效果。
不同的表面活性劑往往有不一樣的洗脫成效。章瑞英等了解到因為洗脫液里 Tween60 與SDS 質量水平不斷增加,土壤里的DDTs 的總洗脫效率慢慢提高,一次性洗脫時最大洗脫效率各自是43.60 %與34.62 %。土壤里六種DDT的洗脫情況差異明顯,Tween60 對2,4’-DDD 有55.12 %的洗脫率,而對4,4’-DDD 可以達到54.09 %;SDS 對2,4’-DDD 有 59.99 %的洗脫率,而對4,4’-DDD 的數值是57.10 %[8]。這說明一樣的洗脫劑會對不一樣的DDT 產生不同的洗脫成效。
2.3.1 表面活性劑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微生物降解DDT的程度
肖鵬飛等對非離子表面活性劑Tween60 和陰離子表面活性劑SDS 在單一與聯合兩大手段降解人工污染黑土里白腐真菌Phlebia lindtneri GB1027 的DDT 的效果進行了分析。數據顯示Tween60 與SD 對于DDT 的降解水平均存在相應的影響,特別是兩類表面活性劑具有 1.0mg/g 的數值時,土壤中里DDT 能夠完成62.9%與53.9%的降解率。Tween60 和SDS 以相應比例聯合之后對DDT 的去除率次序為:Tween60 -SDS(3:1)>Tween60 -SDS(2:1)>Tween60 -SDS(1:1)[11]。
2.3.2 生物表面活性劑
從微生物中獲取的生物表面活性劑也有非常好的洗脫效果。Wang 等發現化肥+高羊茅,化肥+高羊茅+假單胞菌的去除率分別為59.4%、65.6%,肥料控制(40.3%)[10]。
生物表面活性劑和不同的表面活性劑混合在一起,可以取得更好的降解效果。楊慧娟等使用20 mL 濃度為20 g/L的AGP0810 和皂角苷以及10 mL 濃度為5 g/L 的AGP1214超聲振蕩 30 min,DDT 的去除率為21.79 %~91.63 %[7]。陳蘇等借助混合表面活性劑十二烷基苯磺酸鈉與吐溫 80(Tween80),份額是2∶3 和生物表面活性劑-鼠李糖脂(RL)當成供試表面活性劑,進行5 個月處理的混合表面活性劑-降解菌后發現H70 +N 對DDT 的降解率最高,數值為63.98 %;生物表面活性劑-降解菌的處理中最顯著的是RL20 +N 對DDT 的降解率為45.64 %;混合表面活性劑-降解菌的處理情況比生物表面活性劑-降解菌好,H70 +N 最優秀,為63.98 %[11]。
3 外界環境對微生物降解DDT 的影響
在微生物降解DDT 時,外界環境不同,對DDT 的降解效果也會產生影響,例如pH、溫度、降解時間、外加碳源物質、土壤結構等方面。
3.1 外加碳源物質
在微生物降解過程中,DDT 難以成為唯一提供能源和碳源的物質,代謝活動所需要的碳源往往需要其他物質來提供。植物-微生物共同對DDT 進行降解便屬于利用植物根系分泌物給專性菌的共代謝反應帶來足夠的碳源來促進DDT 進一步降解。Hua 等了解到,加入葡萄糖,將DDT 作為唯一碳源和能源培養出的D6 菌株對DDT 的降解在統計學上顯著增強(p≤0.05)[12]。王婷研究外加藥劑(還原劑和有機碳源混合物料)和不加藥劑的循環序批式厭氧-好氧生物堆制技術對土壤有機氯的降解,發現添加藥劑的DDT降解率為40.38 %,未加藥劑的降解率為31.22 %,降解率提高了9.16 %[13]。潘淑穎等了解到進行 DDT 降解的時候,添進有機質當成共代謝底物,能夠讓其產生足夠可觀的降解水平[14]。
3.2 pH、溫度和反應時間
在微生物降解DDT 的過程中,不同的pH、不同的溫度和不同的反應時間也會對降解效率產生影響。蔣金會分離所得的高效降解細菌分析了不一樣的時間、pH、溫度和底物水平影響細菌降解水平與生長量的情況。數據顯示,這一菌株5 d 可以對 10 mg·L-1DDT 實現55.0%的降解率,而對10 mg·L-1DDE 達成39.88 %;pH6.0~8.0 有最高的降解率,細菌的生長量能夠于中性與偏堿性環境實現最高水平;底物水平是10 mg·L-1 時降解率最顯著,細菌的生長與降解均需合理的溫度,30 環境中的降解率與生長量[15]最可觀。
3.3 降解菌株的濃度
趙煜坤了解到降解菌與土壤里的菌體水平會對其降解農藥殘余情況產生明顯作用,降解菌會因為土壤里農藥殘余數值減少慢慢消亡。土壤里的降解菌大部分是進入土壤里1d 之后消亡的。如此表示通過降解菌劑的土壤農藥殘留原位生物修復作用最顯著[16]。
3.4 土壤
土壤也會對微生物降解DDT 有很大影響,不一樣的土壤代表不一樣的有機質、溫度與水分數值,所生長的植物根系分泌的醇類、酶類、糖類也會對土壤的各項指標產生影響。Zhang 發現就系統發育多樣性和系統型豐富度而言,總體微生物多樣性與土壤中六氯環己烷和二氯二苯基三氯乙烷的含量以及其他土壤特性(包括總氮、溶解有機碳、pH 和植被)相關。多元回歸樹(MRT)分析顯示,植被明顯影響土壤微生物的種類,在總變化里占比31.8%,其次是OCPs(28.3 %),總氮(12.4 %),溶解性有機碳(6.3 %)和pH(2.4 %)[17]。
蚯蚓是大型土壤生物分解者里很關鍵的結構之一,土壤的改造能力很顯著,能顯著消耗有機物并加速反應,被叫做“生態系統工程師”,對于土壤生態的保護與優化存在顯著價值。蚯蚓利用吞食、挖穴等活動,改善土壤理化性質,增加微生物與有機污染物的接觸機會,提高其生物有效性。蚯蚓代謝物除了能被土壤微生物當成碳源,也可以進一步增加其數目與活性[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