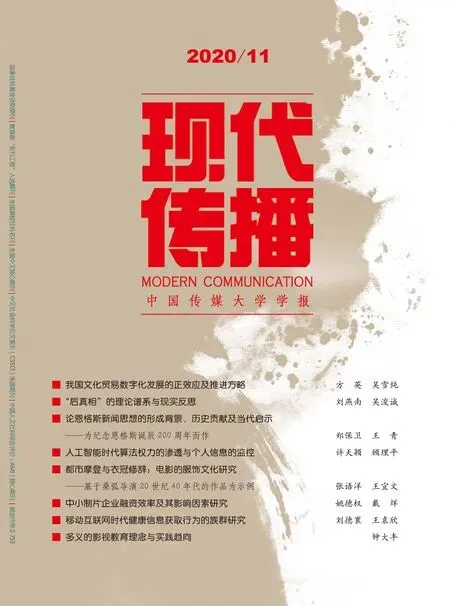新感性的重構:當代中國文學“欲望書寫”的電影改編
■ 陶賦雯
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的基本主題多與“欲望”關聯,承載了新中國成立后到“文革”結束被壓抑的深層文化心理,并在文本創作和類型演繹上將“欲望書寫”貫穿下來,電影改編也一直呼應文學的“欲望書寫”,在“文”與“影”的循環互動中擴展邊界。如第五代導演改編的莫言《紅高粱家族》(1986)、蘇童《妻妾成群》(1990)、《紅粉》(1991)、余華《活著》(1993),呈現著傳統勢力對欲望的壓制和個體的反抗;第六代導演改編的畢飛宇《推拿》(2008)、葉彌《天鵝絨》(2004),轉向關注弱勢階層和邊緣群體的欲望,并將之置放在改革的時代背景下;新生代導演改編的路內《少年巴比倫》(2017)、魯敏《六人晚餐》(2017)則瞄準普通平民階層所經受的靈魂振蕩。目前學界對文學電影改編研究主要集中在具體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塑造、歷史文化意識等,也涉及文壇地域影像風格的比較研究,但文學電影改編中凸顯的“欲望書寫”主題和鏡像表達還未得到深入研究。
電影文學作為文體的成熟和發展,與當代的文化焦慮契合,呼應了欲望這一獨特的社會心理現象。弗洛伊德最早從心理學角度探究身體感知的“欲望本能”問題,將人類生物學上的性本能即欲望本能視為人類進步發展的永恒動力,認為欲望控制是文明得以建立的前提,該學說也構成了精神分析學的理論基石。保羅·薩特建立了“欲望本體論”,將欲望視為意識轉變的核心動力。吉爾·德勒茲則將電影分為側重精神的“大腦電影”與側重欲望的“軀體電影”①,欲望、機器和生產共同構成了世界上不同的生命現象。
在西方美學中,對于感性價值的貶低是其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相對于傳統理性,感性被視作“靈魂的低級部分”②,是混亂、貪婪、變動不居的負面存在。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赫伯特·馬爾庫塞首次提出了通過藝術的“新感性”來獲得人性解放的問題。在當代中國美學研究中,高建平、丁國旗、何光順等較早探討了“新感性”的學理話語及其藝術實踐。如高建平指出:“在當代美學的復興和轉型中,有必要提出美學的意義在于感性的提升,在一個感性充盈從而造成麻木的時代,重新恢復健康的感性。”③丁國旗將感受力 、反省力、審美力作為馬爾庫塞“新感性”的三個重要特征,認為這三個特征處于一種逐漸遞增的順序中。④何光順認為:“20世紀現代藝術的感性激蕩,常常和潛意識、無意識的問題聯系在一起,并延伸到了傳統感性學所視而不見的領域,因而我們可以稱其為‘新感性’”,即一種“原始精神非常強烈的現代情緒,是消解現代文明理性機制的生命原欲”⑤。顏純鈞也提出“新感性”電影概念,闡述了轉型期中國電影舊理性的鈍化與新感性的激發。⑥可以說中國學界的“新感性”思想不僅限于感官欲望刺激,而且追求藝術與審美,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使生命體進入更大的統一體”的欲望理論,借鑒了馬爾庫塞“新感性”的相關論述,注重愛欲、幻想夢境及生命力的彰顯。筆者認為,當代文學電影改編的“欲望書寫”,與停留于感官或感性沉溺的傳統欲望不同,而是呈現具有反抗傳統道德禮教以及表達兩性特別是女性生命體驗的“新感性”表征。“新感性”是欲望的情境性源動力,目光(攝像機)的投射即“生命原欲”的投射,這其中有現代處境和原始欲望的內在矛盾與緊張,并生成了從小說到電影鏡像表達的分叉和延異,促進了“新感性”的生發。
一、“新感性”的生發:“欲望書寫”改編的鏡像表征
1.感性生命視覺化的文影連通
面對文學文本的電影轉化,改編者以身體和欲望作為電影改編重要的敘事成分與表征符號,引領觀眾在鏡頭跳轉間捕捉人物內心情緒流,揭示人物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文化情境下的欲望生發。在對欲望的重新詮釋和建構中,改編是其中連通“文”和“影”的密鑰,而關鍵則在于實現感性生命的視覺化表達。《現代小說美學》的作者利昂·塞米利安曾提及:“技巧成熟的作家,總是力求在作品中創造出行動正在持續進行中的客觀印象,有如銀幕上的情景。”⑦以蘇童小說為例,無論刻畫人物還是描繪場景,字里行間將人物鮮明的欲望特征彰顯,呈現出極富戲劇效果的蒙太奇鏡頭感。
小說《妻妾成群》有一段描述:“午后陽光照射著兩棵海棠樹,一根晾衣繩栓在兩根樹上,四太太頌蓮的白衣黑裙在微風中搖曳。雁兒朝四處環顧一圈,后花園間寂無人,她走到晾衣蠅那兒,朝頌蓮的白衫上吐了一口唾沫,朝黑裙上又吐了一口。”⑧小說文本主要依靠讀者心理想象和藝術建構完成,丫鬟雁兒對四太太頌蓮的衣服用“吐唾沫”的行為表達憤慨,這份妒性來自頌蓮到來后自身的失寵,老爺對其欲望“落空”而帶來雁兒的主體性焦慮。其改編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沖突相較于文學文本愈加集中強烈,鏡像中雁兒將頌蓮的衣衫放置在洗衣盆里,端到后院清洗,她步行急促,臉帶慍色,發現四周無人時,忽然停下腳步,怒啐手上端著的衣衫。這一連串表情動作訴諸于視覺,更凸現在感性生命場景中人物活動的立體感和沖擊感。正如巴魯赫·德·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所言:“好勝心不是別的,正是我們內心產生的對某個事物的欲望,我們之所以對它有欲望,是因為我們想象到其他與我們相仿的人有著同樣的欲望。”⑨鏡頭中呈現的欲望,其本質是“對欲望的欲望”,作為欲望的介質之一——肉體消隱不見,而構筑為一種好勝動力的情感游戲,通過精神上的欲望法則,介入第三者心理建構的“模擬欲望”,來實現欲望的生發與焦慮呈現,描撰出人物妄圖宣泄的跋扈和主仆間無法彌合的欲望矛盾,并衍生出模仿、攀比、嫉妒、競爭等荒誕行為。
作家葉彌的短篇小說《天鵝絨》曾被姜文改編成電影《太陽照常升起》,以銀幕鏡像承載特殊年代的文化記憶,傳遞出對“文革”閉鎖時期壓抑欲望、扭曲人格的抗議。影片通過對“什么是天鵝絨”的欲望探詢,以少男的性啟蒙、成熟男性的性尊嚴等符碼承載“欲望書寫”敘事,開啟一段男性對女性“身體所有權”爭奪失敗的悲劇敘述。影片由陳沖飾演的林大夫一角,在片中一直以濕漉漉的護士服造型、溫柔嬌喘的少女般聲線、“摸屁股”的戲謔遭際,成為電影里一個流動的、高度欲望化的實體投射。通過大膽的身體展演,彰顯其主體意識伴隨身體情欲的復蘇,傳達原著中特殊年代女性被遮蔽的欲望渴求和內心世界。而另一位女主角唐妻在原著小說中有段自述:“我家老唐說我的皮膚像天鵝絨。”在電影里這句話被姜文導演改編為:“我家老唐說我的肚子像天鵝絨。”把“皮膚”置換為更有顯性肉欲意味的“肚子”,其間的欲望表達更加明晰,實現改編中感性生命的視覺化體驗。
2.感性生命向原始神秘的返歸
在改編中,文本投射的欲望既可通過摹狀人物性格行為、心理變遷、情節發展等藝術技巧體現,也可通過獨特的意象表達和場景設計來承載,其中所折射的隱蔽欲望和不可知命運的糾葛也構成了現代藝術向原始藝術“他性”(神秘性)的返歸,呈現出“宿命論”與輪回觀念的籠罩。例如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將原著小說《妻妾成群》中充滿南方陳腐糜幻氣蘊的江南深宅,置換成山西的喬家大院,以一種中規中矩、與世隔絕的封閉式構圖,在電影框鏡中呈現對欲望的閉鎖隱喻,承接了對神秘欲望的鏡頭窺癖,暗示人物所處的壓抑生存狀態。電影中啟用了“點燈”“捶腳”等神秘又帶性暗示的民俗儀式,將深宅大院中禁錮扭曲的房事、算計傾軋的爭寵大戲欲望化呈現,通過紅燈籠的點燃、升起、懸置,象征為欲望的興起、燃燒與壓抑,將原始生命的幽深欲望不斷溢出,視覺化呈現人性的陰森黑黢。張英進曾指出這些影片中呈現了“被壓抑的性欲……在意識或其他類型農村習俗中可看到的性別行為和性展示”。⑩欲望也在現代藝術的跨領域改編中,發生了溢出、復調和變奏。
同樣,被改編過程中,文本時隱時現的線索,即作品的神秘性維度,也是欲望“止溢”的寫照。正如葛紅兵指出:“他(蘇童)更看重的是人作為本在的根本性欠缺,這種欠缺是與生俱來的、無法回避和改變的,因此,蘇童常常不能為自己筆下的人物的遭際提供一個社會學的解釋,蘇童筆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在小說《妻妾成群》中曾設置了一口作為線索的“古老兇井”:“頌蓮聽見自己的喘息聲被吸入井中放大了,沉悶而微弱、有一陣風吹過來,把頌蓮的裙子吹得如同飛鳥,頌蓮這時感到一種堅硬的涼意,像石頭一樣慢慢敲她的身體。”這一文學場景設計體現了頌蓮對圍繞這口陰森的井所流傳的不祥傳說的恐懼,對“宿命”的堪憂,對不可把控的命運、隨時可能被幽黑深井般生活所吞噬的欲望抵抗。在改編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里,場景設計被置換成了一間頂樓的黑屋子,并數次以遠景方式出現,成為三姨太的死亡歸宿和最終頌蓮的幽閉歸宿。電影通過三姨太被挾制掙扎的肢體動作和頌蓮偷偷遠眺窺視的眼神表演,詮釋出人物的深懼及其與命運的抗衡,使得觀眾產生對其悲劇命途的共情。通過改編,將小說中的兇井置換為電影里的黑屋子,呈現這看似細小的場景線索在欲望情節中牽持故事發展起落的作用,同時暗示主人公宿命般的命運輪回,將這份無奈森冷的可怖情感表現得入木三分。電影改編后,山西的喬家大院、大紅燈籠、樓頂的小黑屋成為藝術形象被觀眾所記憶,它們既被看作是欲望敘事本身,也是欲望敘事的線索,是“有意味的形式”,是現代藝術向原始藝術的感性回歸與緣域生成。
3.感性生命被壓制的女性符碼
布萊恩·特納曾強調身體的政治性和社會性:“我們主要的政治和道德問題都是通過人類身體的渠道進行表達。”底層、女性、身體、欲望,被攝影機緊密粘連在一起,將當代文學中眾多被壓制的底層女性形象“轉譯”為銀幕上欲望的符碼表征,以非暴力的欲望書寫來實現一種軟性反抗。于是,身體(尤其是女性身體)描寫滿足受眾的窺視和幻想,就成為視覺上的“內部殖民化”(Interrior Colonization),塑造出一批具有抗爭氣質的女性形象。如莫言筆下的戴鳳蓮(我奶奶),陳忠實筆下的田小娥,范小青筆下的萬麗,葉兆言筆下的沈三姐,蘇童筆下的頌蓮、秋儀、織云,畢飛宇筆下的筱燕秋、玉米、玉秀、玉秧等。這些女性都帶有外在樸質之美與受儒家文化影響的“表面的馴服”,但骨子里充斥著人性的復雜和抗爭氣質,在欲望與禮數沖突中掙扎,爆發出被壓制的身體原欲。銀幕上這些女性欲望的符碼表征,成為展示當代社會變遷、情感欲望及倫理道德的場域。雖然她們性格迥異,經歷不同,但銀幕上演的卻是一幕幕動人心魄的欲望悲劇。
勞拉·穆爾維在《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中提出:“女人更密切地被聯系到圖像的表層,而非其幻覺的縱深處,那個被建構出來的三維空間注定要由男人占據并控制。”蘇童筆下的女性多呈現出對男性的欲望崇拜,隨著深宅大院里妻妾爭寵的畸形發展與欲望的過度膨脹,當頌蓮們的自身力量無法滿足超乎能力的欲求時,唯有死死抓住男性的“留夜權”及其欲望認同,以實現自我價值指涉。但在其電影改編中出現了權力的暫時反轉,女性的“欲望的自我”(moi-du-desir)被實現出來。在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女主人公頌蓮獨自靜坐在光影里等候陳老爺的到來,鏡頭里冷艷的藍紅對比色調,形成了劇烈反差,顯得女主角更為孤傲決絕,并讓女性由“欲望客體”走向“欲望主體”。而在對男主角的“鏡像期待”方面,導演張藝謀反其道而行,將男主人公陳老爺的刻畫消隱,甚至他的臉都未曾在鏡頭里出現。這種改編可看作是訴諸女性主體視角的“軟性反抗”,它表達了電影制作者對作為被壓制對象的女性的同情,也揭示出男性無處不在的壓制力量,表現了兩性結構的更大內生張力,凸顯了頌蓮們的欲望悲劇,以及她們最終被驅逐到歷史的狹縫邊緣,或沉默、或失語、或瘋癲的狀態。蘇童曾談及“喜歡以女性形象結構小說”,因為女性身上凝聚著更多小說因素。“小說中,我對女性的觀照主要是人性上的觀照,雖然有時候她是陰暗的,但她是高大的,她不是受苦受難的,也不是被男權包裹起來的,她們都是獨立的。我在表現女性的時候盡量讓她真實化,我從來不會去把她們無休止地美化,她們是怎么樣的我就寫什么。”
二、“新感性”的沉淪:“欲望書寫”改編的審美誤區
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傳統倫理道德的基礎被逐步蠶食,造成了文化領域的欲望流回歸和反抗機器宰制的粗鄙化與功利化傾向,正如汪民安指出:“欲望生產著現實。”在現代藝術中,欲望成為最現實的寫作維度,文學作品的“欲望書寫”改編承載了人物內在欲望的鏡像化表達,并主要通過具象的身體形象來傳載。然而,這種過度身體化或具象化的欲望書寫,造成了屏幕現實的單向度和貧瘠化,導致部分改編電影作品先天營養不良,文化語境閹割、風格囿于脂粉、商業化導向,造成了“新感性”的沉淪,呈現去理想性、柔靡化、低俗化的審美誤區。
1.理想性文化語境的缺失
欲望研究歷史可謂悠久,但在哲學、心理學層面得到充分探討卻是近現代工商業文化發展的結果。“欲望或欲望流實際是主體與社會存在拆解后的互動性實體,是對現代再現論、總體論、主體論等意識形態思維的疏離。”這種從西方近代社會開啟,蔓延到中國人文領域的“欲望”主題也強烈影響了改編,并在電影藝術的綜合媒體效應中被放大。諸多文學作品雖然在身體或欲望感官寫作中強調理想性和超越性,“講述個人經歷的生命故事,通過個人經歷的敘事提出關于生命感覺的問題,營構具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但由于電影注重工業化流程的切割與拼接,故在改編實踐中,那種被文學家所看重的某種作為僭越指向的理想性文化語境喪失了,一種更為“蒼白化”“肉身化”的導向被凸顯——銀幕為觀眾帶來快感并作為情感激發功能的外在裝置被重視。正如改編自劉恒小說《伏羲伏羲》的電影《菊豆》,在銀幕上充當了“男性凝視”(Male Gaze)者身份,透過他的眼睛替代了攝像機的窺視,觀眾們看見了楊青天所看到的一切,這使觀眾也變成了“雙重窺視者”。菊豆是楊青天的欲望對象,也變成了觀眾投射自我欲望的對象。誠然欲望是文本的戲核與推動力,是使得觀看者獲得掌握被觀看者的愉悅快感,但部分電影改編為追求視覺直觀化效果,降格、置換、偷換了文學的文化語境,弱化閹割了文化主題,忽略作家注重“欲望書寫”背后的文化語境與批判精神,從而使得電影顯得空心化,并致使改編失敗。
2.囿于脂粉的柔靡化導向
值得肯定的是,部分作家在面對社會急遽發展中,始終秉持現實主義創作風格,注重用藝術改編來傳達處于社會欲望漩渦中人的情感困惑與心靈掙扎,其中不少作品都承續著本源的地域文化風韻。如長三角一帶,人文底蘊深厚,其文學創作本身帶有濃郁的煙花脂粉味和傳統文人才子氣,形成了欲望書寫的女性崇拜情結。部分江南地域風格明顯的文本在改編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被賦予了柔媚細膩的女性化特質,缺乏了深刻思考與凌礪粗蹈的氣質。作品里“有一種總是消解不去的‘秦淮情結’,過于‘脂粉氣’,輕靈虛美有余,高遠深邃不足”。因此這種以人物形象支撐的欲望“柔靡化”改編和制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電影的敘事框架、主題原型與故事圖式,限制了構建鴻篇巨制的能力。
短篇小說《婦女生活》充分詮釋了人性的情感渴求和欲望掙扎,但其改編電影《茉莉花開》則摒棄原作中乖謬異常、人性逼仄的命運遭際,刪改了原作中人物刻畫的部分特征,如性格倔強、冷漠等,添加了更為溫暖真實的成分,表現出濃烈的母性和親情關懷,“影像”給予了人物最終的情感歸宿,讓觀眾得到情感宣泄和補償性滿足,引起強烈的內心共鳴。但精神式微過于“柔靡化”的欲望書寫框架,削弱了作品本身的批判性力量與思想深度。誠然,換一視角,這種脂粉氣濃重的欲望書寫也可看作南方地域文化特色,是江南文化承載的“記憶之場”,突顯當地作家及其電影改編的地域性維度。在堅持“欲望書寫”的同時,汲取北方文學的陽剛氣質與南方文學的開放精神,或應是當代文學與電影改編的重要方向。
3.商業導向的低俗化發展
近代商業資本讓整個世界流動變化速度加快,制造了龐大的大眾階層,解放了欲望,讓身體得到充分展現和出場,但也消解了古典階級固化中隱藏的靜止和恒定的生命深度。20世紀80年代,中國作家開始構建具有啟蒙和現代意義的愛欲自覺,一種具有原始情感和理性精神平衡的欲望書寫,主要體現在海子、王蒙等作家寫作中。90年代后,由于劇烈的市場經濟沖擊和文化變異,文學藝術家難以適應社會轉型,其主體性被市場利益劫持,社會文化從啟蒙轉向娛樂消費,在文學中引入強烈低俗的商業化元素,出現了對“身體寫作”的曲改,以迎合影像時代的閱讀趣味。那種在80年代尚可維持原欲和理性平衡的“新感性”,其愛欲維度開始遭到破壞,人性內在平衡被打破,并在文學電影改編中得到強烈體現。
在市場經濟席卷下,改編行為不可避免受到以市場為導向的價值取向影響,“商業邏輯對各個文化生產場域進行了侵蝕和滲透”,出現了大量以文化娛樂為旨歸的商業化作品。其中“身體作為色情和欲望的能指,作為消費對象,開始被較多地呈現于銀幕上,表現出中國電影視覺主題的某種轉向,或者可以成為視覺意義上的‘身體轉向’”。一些改編電影作品過分追求市場利益與商業眼球效應,忽視作品應具備的人文意涵和對人性欲望的理性節制,銀幕上充斥著肉體之欲和對感官的極度開放,重視情欲描摹的視覺呈現,導致改編的膚淺化,成為影片營銷的手段。
三、“新感性”的重構:“欲望書寫”改編的路徑拓延
“欲望是一種文化現象。欲望不是一種主動、本能、自然的產物。人對某人或某物產生欲望,是因為他者作用,這個他者成為欲望者與欲望對象之間的中介,所以欲望實際上是對他者的模擬,是被中介化的。”文學是通過文字中介作用于讀者的想象力,但電影是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更多依賴于不同的地域風格、經濟考量、文化素質、接受能力等,導致創作主體在改編程度和內容把握上千差萬別。電影想要表現的這種內在隱秘的“欲望”,卻又真切地進入人的感知系統,與影像系統融合成一體,呈現出一種未經理性認識,卻朦朧敏銳地對事物作出反應(包括興趣、好惡、取舍等)的“新感性”的重構。
1.發掘“欲望書寫”影像的精神自覺
在德勒茲看來,感性生命可能在這種消費化、媒體化和偽治療化的社會被抹平,視覺的統治可能造成現代藝術感性生命豐富性的喪失。研究現代藝術,就需要充分了解其內在的文化精神及問題矛盾,此在/他在、自性/他性,既親近而又爭執的共構性緊張關系構成了現代藝術的二元性分裂,這種二元性分裂在當代文學電影改編中,體現為藝術性和商業性的沖突,既需在文學寫作中堅守藝術純粹性,又不得不接受作品面向市場所經歷非藝術的商業導向。從某種意涵上來說,文學作品電影改編的“欲望書寫”,終極意義上是對人性深度的探幽與展演,是人的精神情感世界的宣泄與釋解。
面對理想性文化語境的沉淪,諸多文藝作品反思了在物質繁榮中生存環境的驟變、精神壓力的疊壘以及欲望的延展。回溯20世紀初的中國文學,是以“人的覺醒”為發軔,以底層解放為表達訴求,以創作社會劇表達覺醒的個體對傳統禮教政治的反抗。這樣的創作曾給電影改編帶來了原型母本,而“欲望書寫”也是當代政治權力與兩性權力的濃縮化表達,這種集中交織著權力隱喻的現代藝術,易于受到銀幕上觀眾的歡迎,但迎合普通大眾感官需要的欲望一旦表達過度,則喪失了更高的精神維度。因此電影在對文學作品中欲望矛盾和痛苦處境做出藝術表達時,仍要守護一種尺度,將欲望合理化表達,承載銀幕之上的現代性精神。
2.開拓“欲望書寫”影像的空間構置
電影藝術是工業文明和商品經濟時代的典型藝術,它在一定程度上既承接了文學內在的純粹性,但更增加了觀賞性和娛樂性,適應了快節奏的現代都市人進行欲望投射和精神釋壓的需要。在影像表達階段,“影”在其美學意義上是與“意象”一致的,是藝術視知覺復合在作家靈魂空間的產物,是憑借主觀情緒攝取的人生現象,是人性之光折射的結果。文學文本和電影改編在“欲望書寫”的具體方式上有著較大差異,文學的敘述更加細膩化、心靈化,是面對那些相對更熱愛文字推演的小眾群體而寫作的,而電影的敘述則更加視覺化、形象化,具有非理性激蕩的“新感性”特質。“攝影機前的現實不同于人眼前的現實,之所以不同,關鍵是因為它用一個受制于無意識的空間替代了人的意識所主導的空間。”
針對影視改編囿于脂粉的柔靡化風格,我們需要探討“欲望書寫”建立在虛擬性和假定性基礎上的某種具體化情景,以重構欲望化身體的敘事元素與表征符號。針對電影主要面對娛樂化吸納的普通觀眾,為制造情感激蕩,要利用新的欲望空間,以調動觀眾的新感受力。在電影《大鴻米店》中,米倉成為一個封閉性欲望耦合的承載場景。導演黃建中用升格鏡頭表現出欲望主體五龍在米香中交織的生命氣息。一場飛米中交媾的戲份將黑與白的世界對立起來,當五龍躺在潔白的大米中時,欲望就承載在銀幕空間方寸中。“米”的影像在這里有多種對于欲望的呈現方式,人最初的欲望是能飽食二兩米,而五龍的淪落,不僅是社會環境和個人命運遭際使然,更是其欲望承載主體意識的覺醒。電影中彰顯五龍在米堆里扭曲變形的身體,源于其對性、對生存的饑渴,整個空間充滿著強烈的原欲與吊詭的原罪感,增加了影片對現實的批判力度,揭示人物在不同歷史時期與空間情境下的欲望生長及命運走向,向社會提供了一份多棱鏡式的人性觀察與思考。
3.加強“欲望書寫”影像的政策引導
近年來社會文化語境日益轉向以影像為中心的感性主義創作,強化了作品的商業性和市場性,造成了對文學作品藝術性和純粹性的挑戰。譬如,作家們注重鏡頭描寫的語言,體現其應和未來電影改編的某種兼容性,在深化人物形象時往往強化小說“欲望生產”的鏡頭感。電影文學最大特點就在于它的表達需要通過視覺和聽覺兩種方式,以動態具體形式呈現,并給人以感官的致極享受與震撼,但身體敘述往往容易迷失在追尋消費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的需求大潮中,用低級趣味、媚俗煽情的手段改編,“貶損化”“娛樂化”人物形象,使得審美崩塌,歪曲歷史事實。同時由于缺乏必要的審核把關,受眾在暴力與色情的文化中膜拜欲望介體,變成無能的窺視者,其視覺沉浸于他人虛假的激情。當個體過多載入這種媒介污化敘述,會產生對身體欲望書寫的異化及刻板印象。
鑒于商業導向的低俗化現實,電影改編要注意在國家政策層面的引導力,特別是關注兒童/青少年的媒介接受途徑,設置“性“的倫理表達分區,建立合理的電影審查分級制,化解社會規范與自由表達的沖突,避免“眼球經濟”時代“流量至上”思想,呼吁創作團隊將文學原著中不利于視聽表達的感官內容加以驅除剪裁或轉化,融入更加符合時代意蘊的新視像表達。既維護原著藝術上的完整性和純粹性,又適應市場導向的商業性與娛樂性,以推動電影行業的制度改革。
從小說到電影改編“欲望書寫”的視覺化表達,呈現了電影這一現代裝置機器對于人的身體和欲望的雙重延伸和聚焦,它不同于原始藝術中感官欲望的直接表達,而是更加注重在身體的感知覺視野和欲望具象化敘述中“新感性”權力話語的建構和發掘,形成了兩性、同性間以及不同地位間展開權力爭奪的實踐之地。
注釋:
① [法]吉爾·德勒茲:《時間—影像》,謝強等譯,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頁。
② [德]赫伯特·馬爾庫塞:《工業社會和新左派》,任立編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18頁。
③ 高建平:《新感性與美學的轉型》,《社會科學戰線》,2015年第8期,第131頁。
④ 丁國旗:《尋找“新感性”——馬爾庫塞“新感性”的諸種形式》,《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年刊》,2010年,第281頁。
⑤ 何光順:《感性的抗爭——從王蒙〈神鳥〉看現代藝術的他在》,《鄭州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第77頁。
⑥ 顏純鈞:《“新感性”電影:中國電影舊理性的鈍化與新感性的激發》,《現代傳播》,2018年第8期,第87頁。
⑦ [美]利昂·塞米利安:《現代小說美學》,宋協立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頁。
⑨ [法]奧利維耶·普里奧爾:《欲望的眩暈:通過電影理解欲望》,方爾平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頁。
⑩ [美]張英進:《影像中國——當代中國電影的批評重構及跨國想象》,胡靜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