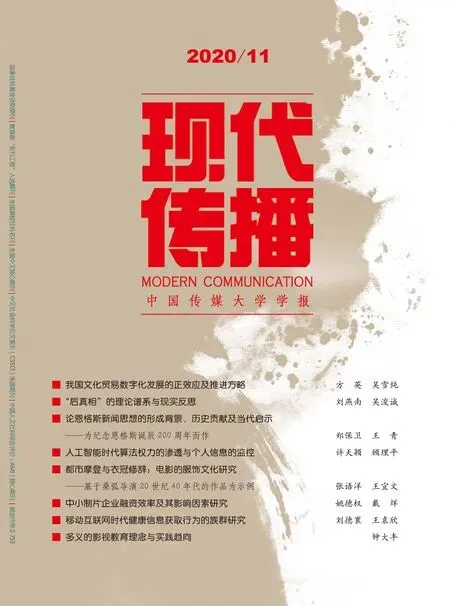“后真相”的理論譜系與現實反思
■ 劉燕南 吳浚誠
“后真相”是一個令人困擾的痛點,也是一個日新又新的論題。2016年,隨著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脫歐等黑天鵝事件的發酵,西方民主社會面臨著一個解構性的難題——“后真相”(post-truth)。同年11月,牛津詞典將該詞選為年度第一熱詞,指稱一種特殊情形:即訴諸情感和個人信念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公眾輿論的情形①,將客觀事實與主觀情感、信念等進行對立式闡述。時隔數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橫行引爆了更為復雜的信息生態,殘酷的疫情背后是輿情的爭奪與拉鋸,“造謠者”的正名、雙黃連搶購風波的興瀾乃至撲朔迷離的陰謀論論調等等,不斷刺激著本就緊張的公眾神經。顯然,在此次疫情中,公共事件的輿情發展往往難以追究真相與謠言之間的絕對分野,而是在撲朔迷離的事件進程中頗具后真相的曖昧色彩。因此,站在今天的視角重新審視后真相及其表征,是把握現代輿情脈絡以及復雜信息生態的題中應有之義。
仔細思忖“后真相”這一組合詞匯的涵義,其既蘊含了后現代主義等后學思潮中(post-x)解構與顛覆現有秩序的寓意,又將真相、真理或稱事實這些一百年來哲學論戰的焦點重新推到公眾面前。有關后真相的探討綿延至今,復雜的動因也使得該概念牽一發而動全身,衍生出涵蓋哲學、政治學、新聞傳播學、社會學等多領域的思辨與求索,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學術態勢;而其概念表征、成因及影響更是涉及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
作為對目前社會信息形態的概括性描述,“后真相”一詞因其模糊、復雜、多元等一些非排他性特征而充滿迷思。首先,從一種學術話語看待“后真相”,該概念覆蓋了哪些問題焦點與辯證關系?又存在什么樣的立場與價值預設?其次,在多學科闡釋中,作為信息社會嬗變中出現的新興現象,后真相與真相的關系呈現怎樣的形態?最后,以今天的現實立場考察“后真相”,我們又將何去何從?
一、哲學爭鳴:從關于真相的省思出發
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真理或真相這一關乎事物本質及表現形式的探討綿延數百年,衍生出了本體論、認識論等多元復雜的認知體系。然而,關于后真相的哲學探討并未執迷于真理或稱真相本體論意義上的實在性,而是將視角聚焦于認識論層面的比較維度:真相是否擁有普遍的客觀版本?又是否存在相對主義?本質而言,這是哲學意義上如何認識“真”的問題。
長期以來,在西方后形而上學的時代里,對應于后真相存在的所謂“真相”體系大抵踐行一種符合論(correspondance theory)與共識論(consensus theory)相結合的真相觀。符合論要求真相必須符合外部世界而存在,提供一種求索事實的客觀依據,通常被視為新聞求真的主導理論。②共識論則以普遍的主觀性來檢驗所得真相的有效性,同時將客觀事實轉化為經驗真相。換言之,前者作為真相的定義而存在,后者在此之上扮演著標準檢驗者的角色。英國哲學家羅素(Russell)曾揭示過其中的一致邏輯:盡管對真實的判定取決于是否與事實相對應,但普遍的聯系將為其提供一種最高的自證性(self-evident)。③顯然,在一個共識充分形成的時代里,雙方具有較高的互惠性與一致性。前者為后者提供真相的依據,后者維護關于前者的基本價值、認識意愿與表達程序。然而,“后真相”所帶來的主體多元、意義復雜、語境林立等演進趨勢,無疑突破了原有客觀性與普遍主觀性的調和,以挑戰者的姿態沖擊傳統共識,亦即所謂的客觀性瓦解與主觀意見不斷擴張的狀態。在這種對立的框架下,推崇上述真相觀的哲學家們開始對后真相現象的風行提出尖銳的批評,有忌于共識的消解與客觀事實的流逝,重建客觀以及重返社會共識和經驗真相也因此成為一種主流的社會呼吁。④然而,社會學家史蒂夫·富勒(Steven Fuller)卻對這種主流批評提出了質疑。在他看來,所謂“事實”永遠都是需要打上特殊引號的存在。⑤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哲學家口中的事實合理性只能在特定的假設框架內獲得特殊含義,而非一種歷經完全公共討論所形成的事實形態。事實上,這樣一種反精英、反共識的論調逐漸形成了一股對于后真相的反制趨勢。
當我們擺脫上述真相觀的桎梏,致力于尋找真相更廣泛的價值,后真相或不再面貌可憎。悉尼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基恩(John Keane)在與柯林·懷特(Colin Wight)在2017年悉尼民主節的一場辯論中提出,所有真相離不開語言環境的詮釋,其本人則用真相的歷史學與地理學(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truth)來描述不同時空下的詮釋差異。⑥就該層面而言,后真相提供了質疑所謂絕對真相(hard truth)的新機遇。⑦這種觀念大體源自于哲學解釋學的視角。在伽達默爾看來,理解已然超越了認識與方法,本身即為存在。作為理解立足點的“視域”(horizont)是融合生成的,蘊含了歷史與共時、自者與他者、主體與客體的整體統一,語言則被視為貫穿始終與通達理解的存在。⑧因此,在解釋學視角下,真相不可能是純粹的客觀呈現,而必然在歷史、語言、實踐等理解要素中差異生成。在這個層面上,相對主義(relativism)或稱視角主義(perspectivism)顯然走得更遠。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在其《腳踏實地:新氣候體制下的政治》(Down to Earth: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一書中強調,在全球化的氣候、政治、經濟危機之下,建立于共享文化之上的真相已經瓦解。人們應該走向地方尋求經驗支持,而非重建具有精英色彩的全球共識。⑨作為一種頗具解構性的意涵,相對主義強調真相及其相關價值由視角制造,在不同立場與經驗中有不同的闡釋。⑩基于此,盡管后真相仍然在重重爭論中疑云未解,本身也尚未增加任何有關真實的認識論論據,但至少帶來了一種開放的契機來審視何以為真。站在多元主義的立場上,有學者表達了一種較為包容的態度:后真相自身就是當代真理的表達方式,應該將多元公共意見納入真理體系之內,而不是將其視為有待克服、規訓的情景。
事實上,以一種去蔽的哲學視角來考察后真相,會發現其并不等同于“無真相”或“真相已死”的悲觀論調,而是指向了真相的多元價值重構問題。英國哲學家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在詮釋了真相的多元認識后,用一個隱喻揭示了真相體系的意涵:我們往往認為真相是花園中的眾多礫石,它們閃閃發光、清晰明朗且不可改變。事實上,真相更像是一個有機的、完整的真實花園,其中有些特征將持續永恒,有些品質則會隨著時間交替成長、改變與消亡。因此,要重拾對真相的強大信念,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該系統的復雜性。在這個體系內,多元真相觀共同形塑了完整的真相有機體,而并非截然對立的哲學抽象。正如學者潘忠黨所言:不同意義體系下有不同的“現實”與“真相”,它們不可完全通約(但不是完全不可通約),亦不可簡單地以優劣排序。一種樸素的經驗判斷是:一篇紀實報道未必比一本個人日記更加真實;同理,集體記憶也難說就比個人書寫離真相更近,哪怕前者是媒體構建的碾壓式主流表達,后者只是個體視角的獨白式個性觀察。因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簡單地質問真實與虛妄,也不在于誰能收獲所謂絕對公理的青睞,理解二者書寫真相的認識論意義及差異并由此展開公共對話,才是求真實踐的應有之義。因此,當我們面對充滿爭執與對立的“后真相”世界時,不妨嘗試以一種更為包容的認識論立場來理解其中的真相體系與表達程序。
當然,懷特對基恩的現實回應也提醒我們,應該謹慎對待方法論層面的價值:既然真相不能武斷確定,那么我們該如何甄別謊言?需要辯證的是,開放的認識論立場并不意味著個體原子化的方法論準則。歷史的經驗已經提示了無度秩序的嚴重惡果——“個人理性的結果幾乎總是集體非理性的”。如果不希望看到謊言橫行、野蠻叢生,需要我們思考的是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重構:即如何在新技術語境下求索真相?人們擁有多少自由的裁量權,又應該在哪些層面受到制約?總體而言,后真相的哲學進路暗含了一條關于權力的線索:以共識為基礎的真相觀轉化為一種多元主義的價值取向。真相價值的失衡總會讓人無所適從,但也使得人們能夠動態反思真相的真正意涵,并在多元認知與對話中捍衛關于真相的共同意義。事實上,這種由一到多的權力變遷,與當今技術賦能下民主政治形態的更迭不無關系。
二、政治異動:權力與權利的博弈
在政治場域中,“后真相”似乎已經構成一組復雜的組合詞項。假新聞(fake news)、民粹主義(populism)、右翼運動(right-wing movement)、部落政治(tribal politics)、黨派偏見(partisan bias)等一干詞匯與后真相一道,沖擊著嬗變中的政治生態。但顯然,我們要做的不是執迷于這種快速且確切的斷言,而是探究后真相與這些詞匯的聯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2017年,第53屆慕尼黑安全會議發布了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Post-Truth,Post-West,Post-Order)為主題的報告,其中直指后真相的關鍵威脅:“后真相”文化的風靡侵蝕了自由民主制度所賴以為繼的基石——理性的公開辯論。作為西方民主政治的根基,開明辯論的意義早在古希臘城邦演講與自由辯論興盛的時代就已經確立。亞里士多德就曾經以用事實公開論戰的呼聲回應智者派的煽動言論。直至近現代,即便是對公眾力量感到悲觀的李普曼也承認,自由的公開辯論至少能夠幫助公眾辨明黨派偏見與私利維護者并形成可追隨的公共意見。就這點而言,政治在公開辯論過程中彰顯了其天然本性:建構、維護和捍衛超越任何“個人”和“私域”的公共秩序。
然而,公開辯論的呼喊也無法解決協商主體本身的難題。在個體身份的輾轉變化中,一系列古老的問題也始終困擾著民主政治生活的堅實擁躉:公眾將在公共政治中扮演何種角色?其公共與私人的身份界限又該如何辨明?顯然,這事關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民主。從傳播政治學的角度來分析,甘惜分先生曾經將該問題置于更宏大的人類文明史中思考,提出傳播權力與權利概念的出現以及兩者之間的沖突和爭奪,是民主對抗專制的法律表現,二者在歷史長河中交替演進,此起彼伏。事實上,只要存在階級或階層差異,關于傳播資源的權力與權利的斗爭就將不斷延續,公共政治的邊界以及民主形態的流變則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相應生成。
在網絡化語境下,權利主體突破了通過大眾媒介及組織參與公共政治的藩籬,轉而以原子化的身份投身政治活動。這種民主實踐的轉化主要有兩大特征:首先,隨著精英政治與代議制民主的衰落,精英政治與底層政治之間搭建起了直接對話的橋梁,促進了監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與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等大眾政治模式的崛起,公民能夠以對話的形式廣泛地監督、參與公共政治。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政治參與主體享有同等的地位。其次,社交媒體為公眾構造了快速且普遍的聯結方式,尤其體現于近年來以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主導的社會運動中。通達了這兩點,就不難理解后真相作用的現實場域:權利的彌散與權力的失落。雙方的此消彼長似乎本是歷史斗爭中的常態。
1.政治謊言:當權力左右權利
在第一個特征上,當政治領袖繞過傳統公共媒體直接與公眾對話,似乎一竿子插到底,那么一種必然的路徑是,將修辭和話語技巧作為政治人格化與吸引選票的優質策略,特朗普的推特執政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語言學家羅賓·拉科夫(Robin Lakoff)指出,為了贏得選民與影響力,特朗普更多基于語用(pragmatics)層面的考量來發表言論,跳過了與事實相關的語義(semantic)層面。在馬丁·蒙哥馬利(Martin Montgomery)看來,正是這種本真(authenticity)取代真實(truth)的混談幫助特朗普贏得了美國大選。按照一些學者的說法,這些言論中包含以情緒化路線主導的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為利益編篡事實的胡扯(bullshit)、社會階層差異所制造的系統性謊言(systematic lies)以及閃爍其詞的誤導信息(misinformation)等等。總體而言,這種科學理性的分析還算中立客觀,另一種更為偏激的表述是:這是為了操縱公眾而編織的謊言。有研究者用“武器化謊言”(weaponized lies)形容這種頗具殺傷力的修辭包裝。本質上,武器化謊言或說謊言的武器化,其重點不在于粗淺地衡量真實與否,而在于揭示這種話語方式的殺傷性和俘化力,即能夠獲得公眾的善意支持與包容。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林奇(Michael Lynch)在其文章中有過這樣的論述:當我們把目光從特朗普身上挪開,才能意識到后真相所面臨的真正困難——站在他以及另類事實背后的另類支持者。基于此,學者們普遍表達了一種擔憂:權力操縱了權利并從中獲益。
2.民粹主義:當權利壓制權利
當公眾得以廣泛聯結,第二個層面的表征開始顯現:社會行動者們基于底層價值以建立等價鏈接(equivalential links)的方式為民粹主義提供溫床。瑞典智庫機構Timbro2019年的數據顯示,在已經開展的歐洲大選中,有26.8%的選民選擇投票支持民粹主義政黨,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持率持續上升。對于西方后真相語境下民粹主義的抬頭趨勢,學界也產生了多維度的解讀與分析:本質上,這是市民社會興起背景下無限制的主觀性發展的必然結果,具體可以表現為平民公共領域的崛起及其與精英公共領域的價值斷裂。同時,在西方經濟下行的本土趨勢下,對精英價值的文化反沖(Cultural Backlash)與強調精神實現的后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價值轉型等因素為民粹主義的孕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盡管民粹的成因機制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因素,但是,學者們卻都毫無例外地表達了一種“托克維爾式”的擔憂:民粹主義的泛濫或將讓大眾政治走向“多數暴虐”,壓制理性聲音的表達。需要辯證的一點是,民粹主義本身夾雜多元訴求與觀點紛爭,是一定社會情緒的出口,同時也具有反精英、平權化的期許;但是,民粹主義浪潮中所表現出的反理性、反建制與排他性的一面,又暗含著反多元、反民主的內在特征。因此,在大眾政治的新一輪崛起中也潛藏著黨派偏見與政治部落化的新型癥候。
后真相所引發的擔憂不無道理,集中反應了西方現代文明發展的矛盾表征。然而,以一種動態的權力與權利觀來考察民主,會發現現代民主的可貴之處在于建立起的是一種制度意義上的平衡路徑,而非依賴于權力引領權利的精英治國,抑或是權利驅動權力的直接民主。甘惜分先生也曾指出權力與權利的關系是相互拉鋸、相激共生的,二者共同維護著制度生態的平衡。一些現行體系中的危險傾向已經引起了西方知識共同體的普遍警覺,對權力與權利的失衡進行反制,這未嘗不是積極的一面。因此,從辯證的視角來理解民主,需要注意的是現代民主體系在處理權力與權利問題中的復雜機制與糾錯能力。正如郭小安所述:公眾的情緒、自私與偏見在民主中雖然導致了一些不良后果,卻也在相互博弈中形成了“隱形”的權力分散機制,發揮著不易察覺的功能。
事實上,真正需要我們思考的是立足當下如何重新定義公眾角色在民主中的作用。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人們會時常提及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所描繪的令人失望的公眾形象,但是我們應該明白這并非要回到民主必然精英的保守信念中,而是要反思當上下力量能夠擊穿制度性層級時,我們能夠做些什么?
三、傳播生態:后真相與真相市場
在哲學與政治的爭鳴中,真相與權力這兩組核心概念看似不可通約,卻又在后真相語境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我們揭開附著于真相之上的權力迷霧,如何求真的問題又將重新浮現。事實上,傳播生態作為社會信息流動的環境,不僅承載了呈現真相的使命,也往往是權力與權利爭奪的現實場域。因此,哲學與政治所反映的后真相問題都不可避免地要在傳播領域中尋找現實出路。
1.權威消解:走向談判桌的真相
新聞社會學告訴我們:作為傳統的事實調查機構,新聞業一直以對客觀事實的追求維護著它們言說真相的權威,保證其對收集和管理信息的合法地位。與此同時,新聞實踐所確立的客觀準確、平衡報道、公正無私等一系列共識性的操作準則,維系著基本的公共交往秩序,具有天然的公共性特征。因此,傳統信息生態的共識也主要存在于上述兩個層面:一是專業新聞業建構的職業權威,二是由客觀性主導的內生價值。二者共同維護共識社會中的事實標準與交往規范。
然而,后真相所引領的解構浪潮不斷沖擊著傳統新聞業主導的信息生態。大多數學者對此采取的是一種技術性歸因,即依托網絡技術的社會化分發和分享式民主給專業新聞業帶來了沖擊。面對大環境的沖擊,專業新聞業與新聞價值卻擁有著截然不同的境遇。在普遍公信力危機的侵蝕下,專業媒體的權威地位備受挑戰,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其原有真相界定者及其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公眾與傳統真相界定者之間原本穩定的聯結關系也變得飄忽不定。”然而,新聞價值卻在一種連接受眾的語境中被賦予了更為樂觀的期待。有學者認為,后真相是西方奉為圭臬的客觀新聞學轉向以“后現代主義”思維指導的以多元化、去中心化、碎片化為主要特征的“對話新聞學”的具體體現。在這個層面上,關于新聞求真的標準與價值將不再囿于傳統權威。另有一些學者指出,新聞將由此擁有更廣闊的實踐空間,得以在公共生活實踐中以交往性原則重新詮釋價值倫理與交往規范。從上文所提及的權力與權利觀展開分析,這或成為一次可能的歷史契機:在歷經權力去蔽之后,真相的價值與標準才得以擺脫教條,在談判桌上獲得新生。
當然,所有談判桌上的“籌碼”分配都并非公正無缺,權力與權利的拉鋸形塑了其中的微妙關系。首先,權利正在向權力拓展邊界。作為權利的表達一旦獲得普遍認同,那么往往能在新的信任機制中生成權力。因此,新的多元權力與信任機制正在介入真相表達。美國學者杰森·哈爾辛(Jayson Harsin)就曾指出,后真相所反應的傳播生態是“真相市場”(truth market)繁榮的體現,以參與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為代表的新興權力正在參與、傳播與表達。本質上,作為一種流動的權威,新的事實機制賦予了受眾更多的主觀自由,選擇什么事實、相信什么事實以及如何闡釋事實都將由個體把握。信息生態由此在不確定的聯結關系中完成了比爾·科瓦奇與湯姆·羅森斯蒂爾所指稱的從信我(trust-me)時代到秀我(show-me)時代的轉變。其次,權利主體的認同來源也由階級差異泛化為種族、性別、文化甚至興趣愛好、生活方式等等與主體身份休戚相關的各類維度,尤其是在社交媒體語境中,廣泛的情感與主觀聯結成為可能。在主觀自由與情緒作用的加持下,后真相對于公共討論的遮蔽作用開始顯現:人們根據預設立場與偏好來選擇他們所愿意接受和表達的信息。主觀自由指導下的碎片化建構逐漸消解了完整事實的嚴肅意義,轉而在討論中追求觀點的表達與闡釋。最終,事實也被簡化為觀點與主張在意識形態場域內的辯論。
后真相也因此游離于一種去蔽與遮蔽的復雜狀態中,既帶來了更為廣泛的真相探討,也有可能造成情感層面上的顛覆與扭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傳播權力的嬗變與以往頗具顛覆性的斗爭方式有所不同。權力與權利主體所爭奪的對象不再以作為集合體的受眾為目標,而是面向一個構成多元、屬性多重、身份多樣、功能復雜的后受眾生態。因此,多元權力主體與交錯的認同機制勢必長期共存。認識到表達權體系中多元主義的必然性,就應該看到拯救真相意義的方式是尋求更積極的對話解蔽,而非大而劃一的真相共識與權力壟斷。后真相的尷尬狀態就像是笨手笨腳的人們剛剛站上岌岌可危的談判桌,而學習交流碰撞,省思“我”和傾聽“他”,也是探尋真相的傳播活動。面對不確定性的真相迷霧,對話與辯論至少能幫我們更確信地接近真實。
2.重構傳播:符號學視角的對話
基于此,本文一以貫之的認識論立場是:真相是一個多元的有機整體,體系中思想的碰撞與活躍維系著真相作為整體而存在的意義。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為人類尋找一種超越性的客觀價值,賦予其先天正確的神話意涵,站在權力的角度上,這樣的傾向總是危險的。一種更為真誠的路徑是:在對話中理解多元、建立規范以及糾正偏誤。換言之,人不應成為被某種假定的“真相”所制約的人,而是在解蔽過程中不斷開放的人。
正因如此,傳播過程中需要破除的是一種二分的對立思維——真實與虛假、事實與價值、主觀與客觀,而應理解語境化、多元化真相的復雜性,正視后真相語境中真相與價值的普遍互構的可能性。甚至,當我們將真相的未來置于對話中闡釋時,就應該對不同主體的差異境遇抱有理解。當然,對話中所還原的真相必然不是生而完整的。有學者指出,社交媒體殲滅時間與空間的同時也消滅了確定性的新聞文本。當真相不再一尊,我們該如何求索真相?又該如何在碎片化的文本拼湊過程中制衡偏見?
面對這個問題,傳播符號學提供了方法論思路。沿著建構主義道路摸索,符號學將對真相的追求投射于符號文本、意義生成(能指)及其與對象事物(所指)的聯系之中。多主體下多元歧義的符號文本,意味著真相(意義系統)愈發撲朔迷離。秉持著再現真相而非還原真實的信念,符號學者選擇了一條“再現之真—對話之真—歷時之真”的動態述真路徑以平衡主客觀性,符號再現真實、形成事實文本;對話糾正偏誤、通達公共合意;而歷時則加以檢驗并還原整體事實。可見,符號學所追求的并非絕對真實抑或是絕對非真,而是在兼具客體性、主體間性、符號性和歷史性等因素的“對話真相”中尋求平衡。此外,在事實意喻不明的后真相語境中,圍繞對話展開的傳受主體意圖也被視為述真的檢驗條件。
符號學所提供的是一種基于還原與整體的對話視角:事實的碎片式還原為整體提供信息,整體則為還原提供視角以及對話的空間。該視角的特殊性在于呈現了一種動態發展的求真模型,且能夠容忍事實還原過程中所存在的個體差異乃至相對性,并在整體層面予以制衡。事實上,制衡偏見的方法并不源于道德層面的個體審判,而取決于社會述真與知識體系的良性互構。當主體積極參與事實再現,整體關于事實的價值與網絡不斷擴張,編織盡可能多的真實路徑,信念與事實的一致壁壘才可能走向土崩瓦解,還原活動也得以生成自適應、一致性的意義與規范。在這種狀態下,謊言與謬誤能夠被廣泛糾正,事實網絡的強大意義才得以真正彰顯。而實現良性互構的充分條件是:一個更為開放的對話體系與意見市場。
四、現實反思:后真相語境下的問題表達
當我們把視野從眾多表象中拉開,“后真相”大體可以被描述為這種狀態:在客觀與主觀、權力與權利的拉鋸中,圍繞真相展開的公共價值正在重構,真相、事實以及新聞都在重塑自己的表達方式與求索標準。此次新冠疫情的發生及其世界性蔓延,呈現出了關于真相與事實的新態勢。
除了媒體或專家發布疫情信息和解析,吹哨人李文亮醫生最早在微信群里披露了關于疫情的傳染性信息,自媒體賬號丁香醫生也率先推出疫情地圖與實時通報平臺,以及海內外各種輸入輸出疫情動態;無論是醫護、患者還是公眾,圖片、錄音、視頻、聊天記錄等都可以成為記錄一線及疫情場景真實情況的形式,而社群的線上聚集則為信息的流通提供了傳播空間。毫無疑問,在公共交往與普遍聯系中探尋事件的真實性已經成為一種時代趨勢。
由這一視角觀之,后真相所反映的問題將是常態化和全球性的。在權利開放與權力失落的趨勢下,后真相的出現意味著真相市場的再繁榮,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意見建構與情緒渲染的可能,甚至寓于書寫事實的符號方式中。核心問題在于我們如何看待這些可能的偏誤。總體而言,客觀事實難以完全還原,新聞本身也并不具備傳遞客觀事實的全部屬性,而更多表現為一種建構主義的取向。因此,試圖以一種經過打磨的“客觀事實”來統攝多元現實的方式是不可行的,也是不現實的。無論是真相價值還是書寫方式,未來的必然取徑都是“共繪”而非“獨唱”。宏觀嚴肅的歷史書寫中也應該存在隨筆或日記一類的個人觀感,包容疫情中不同視角的真實記錄與還原。盡管這些表達未必絕對客觀,未必純粹理性,但總體上構成了現實社會的真實圖譜。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Arendt.H)曾經提出過“真相是專制者”的箴言洞見。今天看來,所謂“專制者”的真正意義不在于維持一種不容分說的強制性與暴力體系,而在于啟發人們思考如何在意見表達過程中秉持對事實與真相的專注信念。某些外在力量的強權邏輯往往會讓人們偏離真相的軌道,而一個世界永遠無法容忍兩個“專制者”的統治。當然,同樣不能排除的另一種可能的壓制是,當權利成為“專制者”。
從中國的現實語境出發,中西方關于真相的價值文化難以完全貫通,關于權力與權利的關系亦有不同的辯證表達。在全球性主體崛起的趨勢下,后真相問題在當代中國的傳播生態中有其特殊的顯現形式。比如,圍繞某些不確定或敏感問題,由“禁果效應”引發的膨脹的好奇心與擦邊意識,以及由“寒蟬效應”激發的報復性話語反彈,兩者實際上互為表里,每每帶來濃重的后真相迷霧。當傳統信息市場上單向性、宣導性話語仍居主流,普通公眾難以有效參與公共事務的進程時,人們向網絡信息場的流溢和恣意擴張技術賦權便在所難免;而在具有“高選擇性”的信息環境中,紛繁的信息對沖不僅使傳統的信任機制有陷入失靈的危險,情緒化、非理性話語也會對真相表達形成嚴重沖擊。
面臨全球性疫情蔓延,世界各國在面對這一人類共同的挑戰時,卻絲毫沒有減縮意識形態領域的爭斗,反而愈演愈烈。一些國家的“甩鍋”指責和說辭使得真相問題由一地一國演變為國際沖突話語,并由此展開了頗具后真相色彩的信息戰。在網絡信息流中,有“遞刀論”“賣國賊”和“愛國賊”“義和團”等各種標簽和“帽子”紛飛,話語推波助瀾。面對“疫情”和“輿情”的雙重擠壓,我們堅持改革開放大目標,堅持基于科學客觀公正的真相理念殊為關鍵,而更重要的是要警惕外部刺激下民族主義情緒的內爆式高漲,并防止其滑向更具破壞力的民粹主義。歷史的經驗表明,民粹主義泛濫不僅會模糊事物的焦點,還會綁架和裹脅民意,更別說被某些政治力量所操控的威權民粹主義,其更具殺傷性。這種傾向與上述兩種效應一樣,都會讓真相市場被泛濫的情緒和觀點所壅塞,導致真相不斷后撤,乃至湮沒,走向另一種意義上的“后真相”。
專業(專家)話語進入信息市場,接受挑戰、爭論和征詢,是此次疫情中后真相問題的新特征。對于來勢兇猛的新冠疫情人們所知甚少,希望傾聽專業的聲音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人類對于未知領域的探索大多是在已有知識坐標內進行,而坐標本身卻在不斷變化。疫情落幕的預言被一再證偽,藥物特效也不再篤定,專家權威不是萬能的,也沒有萬應良方。在知識(所謂客觀確定性)與信仰(所謂主觀確定性)的混雜和對抗中,信息也在確定與不確定性中掙扎和爭辯。對世界性難題的攻關創新,或許我們需要更多時間、耐心和信念,以及必要的容錯機制,這未嘗不是開放多元的“后真相”題中應有之義。而面對專業性、新聞性和意識形態話語的雜糅如何分辨,在現實利弊和歷史得失之間如何權衡,仍然值得省思。
一種基于現實的紓解路徑,或許寓于傳播體系的創新和再造中:立足中國實際,建構良性互動、相輔共生的對話型傳播生態,既著眼于權力的制衡,也要看到權利發聲的必然趨勢,賦予兩者更多的對話與耦合空間,尊重關于真相表達的新興文化,共建良好的有關真相的公共價值體系,而非試圖一勞永逸地替代人們去思考。
(本文系中國傳媒大學“雙一流”學科建設項目“融媒體前沿創新研究”〔項目編號:YLTS180505〕的研究成果。)
注釋:
① 原文為“Relating to or denoting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Oxford Dictionaries:https://www.oxforddictionaries.com/press/news/2016/12/11/WOTY-16,2016.12.
② 楊保軍:《如何理解新聞真實論中所講的“符合”》,《國際新聞界》,2008年第5期,第47頁。
③ Bertrand Russell.TruthandFalsehood:ProblemsofPhilosophy.New York:Henry Holt.1912.p.210.
④ 參見藍江:《后真相時代意味著客觀性的終結嗎》,《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第13頁;汪行福:《“后真相”本質上是后共識》,《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第16頁。
⑤ Steven Fuller.Post-Truth:KnowledgeasaPowerGame.London:Anthem Press.2018.p.17.
⑥ Sydney Initiative for Truth:https://sydneyinitiativefortruth.org/2017/10/26/for-and-against-truth-prof-john-keane-and-prof-colin-wight,2017.10.26.
⑧ [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洪漢鼎譯,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8頁。
⑨ Bruno Latour.DowntoEarth:PoliticsintheNewClimaticRegime.Catherine Porter trans.Cambridge:Polity Press.2018.pp.23-25,100-103.
⑩ 參見劉擎:《共享視角的瓦解與后真相政治的困境》,《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第25頁;Higgins,K.Post-truth: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nature,vol.540,2016.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