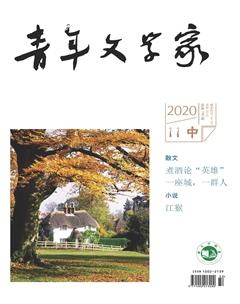一座城,一群人
作者簡介:盛潔(1997-),女,漢族,江蘇江陰人,揚州大學在讀法學碩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連日冰涼刺骨的陰雨過去之后,太陽才出現,不濃不烈地照耀著瑟縮在寬厚棉衣之下的行人。唯有溫暖的晴天,人們才肯慢下腳步,生活也就多了有條不紊的煙火氣。我遇見老趙的時候,也是在這樣一個陽光燦爛的好時候。
那時候我拖著和我一起逃學但是膽小怕事的妹妹半拉半扯地從正在施工的工地經過,兩個人吵吵鬧鬧,好不熱鬧。他蹲在廢棄的木料旁,沐浴在陽光下,“吧嗒吧嗒”地抽著香煙。亮光之下,我只看見他幽黑的眼珠子,一動不動地看著我們兩個,似笑非笑的神情在煙氣后不甚分明。
我氣急敗壞地扯了一下妹妹,發狠叫道:“若你再拉拉扯扯,回去我告訴家人就說是你逃的學。”力度大了一些,她跌在了布滿灰塵的工地旁。“喲,別看著小,脾氣還挺大的。”他在妹妹聲嘶力竭的哭聲中終于發了話。他剛想站起來,頓了頓,在地面上按了按自己的香煙,火紅的星子閃了閃,熄滅了。
煙氣慢慢散開,我看清了他的臉。
很典型的農民工的樣子:黝黑的皮膚,皺巴巴的臉,一笑起來滿臉布滿了溝壑,陽光仿佛也瞬間被“吸”了進去,黝黑的臉龐便不是啞光的黑,而變為高光的黑了。他的褲子臟臟的,從褲腳至膝蓋布滿了大塊小塊的黃泥,就連膝蓋往上也被濺上了星星點點的泥土。他好笑地看著我,伸手扶起了妹妹。“帶妹妹不是這么帶的。”他左摸右掏,掏出來一塊包裝紙鮮艷但皺巴巴的糖果,明顯已經放了許久。我有些嫌惡,但仍惡作劇般地迅速塞進了妹妹的口中。嘴里被塞了東西,她迫不得已地停止了哭泣。“對嘛,小孩子最愛吃甜了。”他洋洋自得地笑了起來,這一笑露出了因為抽煙而牙漬斑駁的牙齒,更加丑陋了。我拉著妹妹想要離開。
“喂,丫頭,這次我抓到你逃課,你就想這么走了嗎?”他自作調皮地朝我眨眨眼,我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
“那你想怎么樣呢?”
“我家有個像你們一樣大小的兒子和女兒,但我認字不夠,給他們寫寫信也不能,好不容易你我有緣,你幫我寫寫信件如何?”
“我憑什么幫你?”
“就憑你高中校服胸口的校徽,我便認得你哪個學校。”
我瞬間如泄了氣的皮球,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答應了下來。他又嘿嘿地笑了,伸出寬大而粗糙干硬的手掌摸了摸妹妹的頭,然后掏出另一塊糖果送給了我。
在回去的路上我便丟了。
第二天中午,陽光燦爛,我如約來到工地臨時搭建的用餐棚中。他在吃著泡面。“哧溜哧溜”的吸面聲混雜著工地外“叮鈴哐啷”的收拾鋼板聲,人聲鼎沸的交流聲,他在別人的煙霧繚繞下,心無旁騖地吃著面。陽光照射下,周邊的浮沉清晰可見。他看見我便將我帶了出來,遠離了吸煙的人群。他隨意地在地上鋪了報紙,讓我席地而坐,搭起了幾塊木板,隨后小心翼翼地將塑料袋中嶄新的信紙拿出鋪開,手掌在上面摩挲了好幾下,告訴我說可以寫了。他邊說邊為我打了一份三菜一湯的飯,很貼心地在飯菜上蓋了一層塑料蓋。他說工地塵土飛揚,怕飯菜被污染。然后他在我旁邊,依舊大口大口嘬著熱氣騰騰的泡面。
他在信里向家里問好,主要關心自己的兒女是否好好學習,問及自己的父母和妻子是否安好,在信里也提到了我,只是說我是好孩子,愿意為他寫信,希望兒女能向我學習,今后努力考到大城市來。寫好之后,他將泡面盒拿開了些,手在衣角上擦了幾遍,拿起信紙,告訴我字寫得很好,他非常滿意。然后我們一起封了信封口,他前后將信封摸了數遍,終于依依不舍地將信封給了我,讓我放學之后投遞。接過寫好的信時,信封里上還帶著他胸口的余溫。
夕陽逐漸西下,落日的余暉溫暖地照耀在我們的全身,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他說他姓趙,很普通的姓和名,就像普通的蕓蕓眾生一般,容易消失在人海里。“當然,好歹我的姓是《百家姓》中的第一位啊。”他樂呵呵地打趣道。家在銅川,妻子是個老實的農民,在家里帶著一對兒女,兒子上著中學,女兒還小,大齡得子,父母康健。
“那你為何還背井離鄉在外面那么拼?”我有些不解,畢竟他不出來打工,家里溫飽還是不成問題的。
“因為想像城里人一樣,讓女兒多開闊開闊眼界,然后給兒子買個房,讓他也走出來看看外面的世界。”說到激動處,他點燃了一根煙,又可能忽然想到我還在旁邊,瞬間按在地上掐滅了,但是他黝黑的臉頰上犯出了通紅的色彩,在余暉的照射下,更加熠熠閃光。
“你看,這背后即將建好的高樓,都是我們這些人蓋的。我從陜西蓋到了江蘇,”他不無驕傲地說道,隨后聲音突然低沉了下去,他重重嘆了口氣,“可是什么時候,我才能讓自己的孩子住進我蓋的樓呢?”他自言自語道,隨后大概覺得我這個小孩子也不懂,朝我擺了擺手,連聲道“不談嘍,不談嘍。”夕陽的余暉繼續溫柔著,美中帶著點憂傷,也許美里總是包含著淡淡的憂愁。
我只幫他寫過兩三次信,都是絮絮叨叨地在說些瑣事和向家里問好。而等高樓建好,這幫工人這一階段的任務便也完成了,他們仍舊像往常一樣,消失不見了。沒人記得高樓建好前的這一群忙碌的、在塵土飛揚里工作的人,更不會有人記得這一群人里有個姓趙的陜西銅川人。
我也只是偶爾看著沖入天空的高樓才會想起這樣一個人。
后來,也是機緣巧合,我在火車站與他見過一次。大學放了寒假,我拉著行李箱,準備回家過年。人群之中他背著大包小包,肩頭扛著碩大的麻袋,肩膀微微向下傾,依然是風塵仆仆的普通農民工的樣子,只是褲腳少了黃泥。我大聲喊了喊他,他仍舊像當初一樣對我笑了笑,隨即掐滅手中的香煙。
“這回回家我就不出去打工了。兒子青春期叛逆得厲害,女兒倒是很乖順,只是成績不好,升學還是有點問題。我想回家陪陪他們,畢竟他們的成長中已經太多時光缺少了我的參與了。”
“銅川現在建設得不錯,我心里也有愧,建設了外鄉這么多年,還沒有好好建設過家鄉。”他不緊不慢地說到,聲音有些嘶啞,但是眼睛仍然清亮,像我當年初次見他一樣我不知該從何說起,而離別的時刻也來得異常快。他朝我揮了揮手當作告別,涌入上車的人群之中,我的視線便逐漸模糊,再也看不到他了,他仍然像相見的時候一樣,來之于眾生,然后又消失于眾生。而我,又何嘗不是眾生中的一份子?有時候我想:大概人的出生環境是最難更改的,人與人之間的命運到底不同。但即使人的出生環境無法選擇,像老趙一般的普通工人不一樣充滿著熱血去奮力一搏嗎?像老趙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是存了美好的愿望才會愿意背井離鄉去建設別人的家園吧。也正因為有了他們,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的各個城市才會越來越好。
大學畢業后,我去陜西玩了一趟,也到達過銅川。銅川仍在快速發展著,一座座高樓等待著拔地而起。我看著忙碌的工人,他們的臉上洋溢著干勁,我心想這里一定有像老趙一般的農民工說不定也有老趙。
冬日正午的太陽即使猛烈也讓人洋溢著幸福。我相信他們也是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