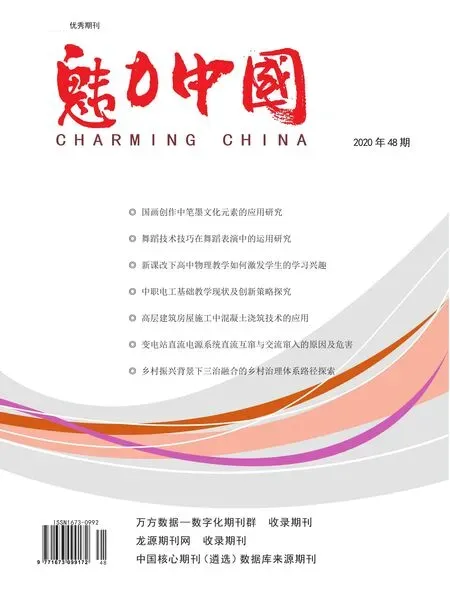近代衛生觀念對我國體育事業的影響
王少陽
(重慶文理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402160)
中國古代并不存在可以概括所有體育活動的“體育”概念。近代西方體育輸入以后,中國所使用的“體育”概念主要有“體操”和“體育”兩種,而它們都是從日本引入的。其中“體操”一詞于洋務運動后期傳入中國并被開始使用,至五四運動之前,它實際上就是近代體育的代名詞。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清末學制改革期間,隨著近代教育制度的初步確立,“體操”開始被當作學生的必修課而普遍開設,不僅更加強調體操對于增進人體健康和促進身體發育所起到的積極作用,還有意強調體操在精神與品德訓練方面所具有的積極意義。然而,清朝統治者之所以提倡和普及體操運動,其根本目的在于培養符合維護自身統治所需要的“軍國民”,而在體操普及過程中則存在過度強調“嚴整紀律”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弊病。
而“體育”一詞則直接從日本引進,與之相對應的英文詞匯Physical Education起初被日本人譯為“體育教育”、“身體教育”或“有關身體的教育”,直到1883年才被近藤鎮三簡譯為“體育”。“體育”一詞于1897 年從日本傳入中國后開始屢見報端,從20 世紀初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前,該詞主要被部分知識分子所使用,但遠非“體操”一詞的普及程度。五四運動后,尤其在1922 年北洋政府頒布實施“壬戌學制”后,隨著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學說和體育理論的引進與傳播,我國此前的“體操”課才逐步被改為“體育”課,其內容也由之前的兵式體操和普通體操改為球類、徒手操、田徑、技巧運動及各種體育游戲等項目。2
隨著近代衛生觀念的引進與傳播,國人對“體育”內涵的理解也日益深入和全面,對“衛生”的理解更加科學和全面,對身體健康的追求也更加積極和主動,而參與體育活動即為實現強身健體目標的一條極為有效的途徑。如1923 年10 月15 日,蔣湘青在《申報》上發表的《體育究竟是什么》一文中詳細論述了自己對“體育”的理解,他說:“‘體’是什么,照習慣說就是肉體,按解剖學講就是骨格、肌肉、血腋、神經所構成的有機體。‘育’是什么?就是‘養育’的意思。由此可知體育的范圍極廣,凡足以強健筋骨,發達神經,涵養德性的都可納入之,既不是單練身體的運動所能包括,更不是專門修養精神的方術所能范圍。”3
而對于近代體育衛生與道德建設間的關系,戴季陶則說:“我因為在歷史上發現出這幾件大事,再加之以自已幾回受到身體疾病的痛苦和因疾病而障礙事業工作的痛苦,所以愈覺得體育衛生的重要。的確,一切深遠偉大的智識都要有強健的身心才能獲得了,也才能應用。至于道德的意義,我以為能獲得強健的身體精神的方法就是道,能夠自已努力不懈去作,并且幫助他人去作就是德,能夠使團體有強健的組織和主義的方法就是道,能夠努力不懈去作,并且幫助他人和其他團體去作就是德,所以道德的意義簡直和體育衛生相通,并且有時竟可以作為一個解釋,尤其在中國專講道德的道家是完全把體育衛生看成一切道德的本體。”4
早在開埠之初,體育就作為一種租界生活方式為我國上海、重慶等地民眾所領略。20 世紀初,上海更是成為西方近代體育傳入中國的主要擴散地。近代體育始終伴隨著上海的近代化進程,是見證者更是參與者。開埠通商后,旅滬洋人將西方近代體育帶進上海等地,并逐漸帶動當地民眾踴躍參與體育運動的新風尚。可以說,近代上海是體育文化最大的舞臺。5上海近代體育最初主要來源于以在滬的外僑群體為媒介的輸入,其中主要包括基督教青年會和一些教會學校的體育活動以及外僑體育,而外僑體育又比基督教青年會和一些教會學校開展的體育活動要早很多。他們對生活在周邊的上海民眾產生一種深刻且廣泛的影響,不僅給此前一些只進行傳統體育運動的上海民眾帶來了猛烈沖擊和洗禮,還給他們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生活觀念和文體信息。據載,當時每逢僑民開展體育運動會時,便會引來眾多市民前來觀看,他們起初以驚異的目光注視著那些來自異國他鄉的奇特舉止,而隨著對西方近代體育了解的深入,他們又逐步完成了從排斥到調和,并最終吸納西方近代體育的全過程。6
福柯的身體規訓理論認為,無論何種社會的人的身體都受到權力的嚴密控制,并通過體育等控制模式來掌握它,所提及的控制對象指的是機制、運動效能以及運動的內在組織,控制模式則意味著通過對時空與活動進行編碼來給身體施加壓力、限制與義務。7這可能使人們對人體運作進行控制,并征服人體的各種力量,同時將柔順、功利的關系強加給這些力量。福柯認為一個與眾不同、自我封閉的場所是對身體進行規訓的最佳場域,而這種封閉原則并非永恒不變的,而是要創造一種更加靈活和細致的方式,以便將空間進行分段,從而讓空間內的階層流動更有效率。運動時間表的制定是一種旨在通過嚴謹的時間排序對身體行為進行控制的手段,在這種強制且精細的節奏中,身體自然而然地習慣于對權力的服從,從而形成制式化的行為模式。8規訓是一種權力形態,是一個由一整組的工具、技術與程序、應用層級與目標所組成的運作模式。規訓是身體政治技術學的一種方式,將身體視為一個可以被分解的集合體。頭、手、四肢都可以分開對待,并強制其作為。而身體規訓機制中的考核,可被視為一種最主要的方法。考核是將人體置于權力的凝視之下,作為一種不斷被權力所窺見的客體。考核發揮了客體化的作用,將人視為一個具體的個案物件來精讀和分析,用知識對其進行分類、拆解和重組,這些知識并不局限于科學,還應包括日常生活對人體行為和施為進行控制的程序與技術。9在近代體育運動中,運動員的培養正符合福柯所提及的身體規訓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在某個具體口令、具體動作的支配下,身體行為表現越好的運動員,就越容易被收編在這個特殊的權力場域之中,這一馴化工程一旦發展到了極致,此前柔順的身體就變成了一個被嚴格約制的載體,并成為一種追求比賽勝負的工具。10
近代體育不只是為了民眾強身健體那么簡單,它還被當時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們賦予了強烈的強國強種的任務和使命,同時也為精英們干預和規訓國民的身體提供了極好的理由。具體言之,近代以來,在內憂外患的特殊歷史背景下,精英們將國民體質的強弱視為國家實力的表現,將提倡體育運動以改造國民身體作為實現其救國目的的一個重要手段,在此過程中,體育對國民身體的規訓正是通過身體國家化來實現的。
近代中國要實現民族富強,不僅需要在教育上培育新民,更需在體育上訓練出體格健壯的新國民,以擺脫“東亞病夫”的屈辱。這就使得近代體育不僅具有娛樂健身的功能,而更多的承載了“強國強種”的歷史使命。近代中國的體育在國家危亡之際和優勝略汰的社會進化論影響下已經成為國人用體育塑造身體,從而達到拯救國族的一種手段。近代中國的精英們借助體育對國民身體進行規訓所產生的影響首先是通過對中國重文輕武的傳統思想進行批判來開啟的,并進一步促使中國體育文化的向前發展,與此同時,以尚力和對抗為主要特征的西方競技體育也得以傳入中國,并得到快速發展。此外,盡管中國的民族傳統體育發展存在一些問題,但也得到了較大發展。通過對中國重文輕武的傳統思想進行批判,促使尚武思潮在當時社會十分流行,極大地改善了國民的精神風貌,尤其是使知識分子也開始尚武,展示出一種積極的豪俠氣概。其次,使近代體育教育日益受到普遍重視,并得以不斷發展進步。近代以來,體育教育逐步開始走入課堂,地位也隨之日益提高,影響也越來越大,是對國民身體進行文化規訓的一種重要手段。再次,近代以來的國民身體規訓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國民因陋習所導致的精神萎靡狀態,并解放了婦女的身體,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對國民身體健康的改善起到一定作用。11此外,在近代國民身體訓練的體育項中,中國傳統武術、日本體操、歐美現代體育運動是同時存在的,但它們在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中所承載的不只是簡單的身體鍛煉和娛樂功能,更多的是提高和增強國民的身體素質,以達到強身強國的歷史追求。就像汪民安所說的那樣,“身體在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目標內,既是為了生成,也是為了同他國競技既是為了提高效率,也是為了提高民族的身體質量既是國家強化自身目標的一部分,也是抵御外來侮辱的基本技術要求。國家理性實踐的宗旨和目的就是身體。現代國家,它的最大使命就是要保護身體。完善身體和強化身體。因此,身體既是對象,又是手段既是目的,又是方法國家政治經濟活動深陷于目的論的陷阱中。”12近代中國把身體納入體育運動這個社會場域之中,并用其獨特的手段和技術不斷對身體進行規范、訓練、強化和控制,從而達到國族救亡圖存的最終目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