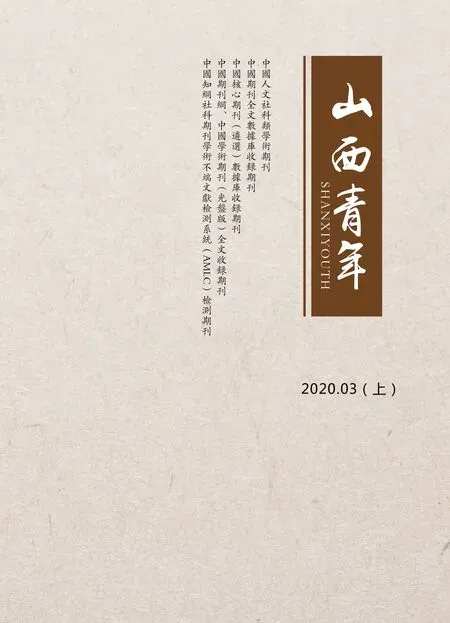必然性在作為基因決定論的社會生物學中的體現
李曉明 謝露露
1.太原科技大學,山西 太原 030024;2.山西大學,山西 太原 030006
一、作為“基因決定論”的社會生物學
“基因決定論”歷來被各界學者批判,這是由于傳統(tǒng)的基因決定論過分強調基因單項維度所致。進而衍生出來所謂的“優(yōu)生學”、“血統(tǒng)論”。過去的學者在批判基因決定論時也往往是站在環(huán)境主義的角度對此進行批判。其實基因決定論是奠基于進化論的,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寫道:“我所謂的‘自然’只是指許多自然法則的綜合作用及其產物而言,而法則是我們所確定的各種事物的因果關系。”[1]所以,“基因決定論”就其語境意義來說,其實已經涵蓋了環(huán)境這一元素。1975年,愛德華.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面世,標志著社會生物學理論的誕生,完備的“基因決定論”亦隨之產生。路翁亭曾公開表示“社會生物學就是一種認為人類的社會組織是由經過環(huán)境選擇的基因所控制的基因決定論。”[2]考慮到環(huán)境是物質的,而基因是分子生物學概念。所以,社會生物學與機械決定論本質上也是相容的。
但機械決定論統(tǒng)攝的是整個物質界,所以其并未就生物界與非生物界進行區(qū)分。而社會生物學作為基因決定論在生物界則是將決定論的邏輯演繹得極為通透。而且作為決定論,二者在“決定性”或必然性上表現亦有所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二、必然性作用的客體不同
機械決定論的主要組成因素是還原論與因果律。其中因果是人類的先天認識能力。而從古希臘的德謨克利特到拉美利特,只要持有還原論的主張,多半其理論都會導向決定論。在拉格朗日整合了牛頓力學之后,機械決定論在認識論的維度發(fā)展為波普爾所謂的“科學決定論”,即強調了人類對于世界預測的能力。科學決定論起因于用按照理性的科學的可預測性的更明確的觀念取代可能的預支的模糊觀念的嘗試。[3]就宏觀現象來說,只要給機械決定論的還原論組成部分設定一個不與宏觀現實相矛盾的臨界點(比如原子),該理論仍然具有充分的解釋力。而這個節(jié)點所在就是機械決定論必然性作用的客體。
社會生物學作用的客體是行為模式。而行為模式的載體與進化論所討論的自然選擇的最小單位是一致的。進化論在其發(fā)展過程中,生物學家曾就自然選擇的最小單位是什么進行了長達一個世紀的爭論。上個世紀中葉,日本學者木村資生提出了“中性理論”,與該理論最為兼容的是把種群當做選擇最小單位的綜合進化論。社會生物學研究的是社會性動物的行為模式,加之其是立足于綜合進化論的,所以社會生物學中的必然性的作用客體正是種群的行為模式。
三、必然性的來源不同
反駁科學決定論的學者曾拿出了許多可以證明預測行為的不可行性,比如微觀的不確定、系統(tǒng)科學等,但并不能對形而上學的機械決定論構成威脅。在機械決定論者看來,混沌的世界在人類看來即便不可解是認識能力的不足,決定是本體論意義上的。真正能反駁機械決定論的是證明因果律失效,即事物之間是斷裂的,沒有普遍聯系的。但如此一來,類理性的價值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因果律是機械決定論作為本體論的必然性的來源。
而社會生物學作為新版本的基因決定論中的必然性,因為基因決定論統(tǒng)攝的是生物界,其自然不可避免地與生物所具有的獨特性相關聯。薛定諤在《生命是什么》中指出“生命以負熵為生。”熵是用來衡量物質的有序性的,生物的獨特性也正是體現在了其所具有維持低熵的能力上。熵與信息密不可分。我們熟知的米勒實驗證明了無機物向有機物轉化的可能性,而后者則可以形成核酸。脫氧核苷酸雙鏈的半保留復制則使得基因可以將信息傳遞下去。在生命形式由簡單到復雜的發(fā)展過程中唯一不曾發(fā)生過變化的是“基因存續(xù)”這一事實。即道金斯所謂的“復制基因為了保證自己在世界上得以存在下去而采用的技巧和計謀也在逐漸改進。”當然社會生物學的研究對象是動物的行為模式,即行為模式是與基因協(xié)同進化的,優(yōu)勝劣汰的法則同樣作用于種群。進一步,如果對行為模式的進化做目的論分析的話,則無論何種行為模式,其著眼點必須是基因的存續(xù)。
四、客體與必然性的關系不同
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本質上就是對機械決定論中的因的認識,包括牛頓力學、分子生物學都是如此,即認識必然性。但對這一必然性我們能否選擇違背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還原論把人的思維還原為了神經元之間的信號傳遞,人類并不具備與物質界的區(qū)分特征,所以人類和其他物質一樣都是不能違背機械決定論的必然性的。這也是決定論與絕對自由不能相容的原因所在。
文化是人類的行為模式,其作為基因決定論的客體遵循上述的必然性,即不可以違背基因的存續(xù)機制。生態(tài)學對種群的定義是:在特定的時間內分布在同一區(qū)域內的同種生物個體的集合。基于認識能力考量,單個的人與種群在面對上述必然性時對必然性會有不同的把握。
就群體來說,文化的發(fā)生遵循第一后成法則與第二后成法則。即基因規(guī)定了一套生物學過程(后成法則),指導著心靈裝配的順序。這二者使得今天的我們不管看到什么樣的文化,其必定是與基因的存續(xù)相關聯的。故而威爾遜在《社會生物學》中討論人類時才會說“并不存在一套單一的道德標準可以用于人類所有群體。”需要注意的是,社會生物學里所討論的文化發(fā)生機制考察的始終是自然狀態(tài)下的情況。
文化與基因固然關聯,但其傳遞卻不同于基因,并非完全通過遺傳,“習得”才是主要途徑。與群體的文化必須符合基因存續(xù)的必然性有所不同。作為個體的人在面對自己所在群落的文化是可以有所選擇。既可以遵守,也可以違背。所謂遵守即循規(guī)蹈矩地踐行該群落的文化教條,成為了該群落的組成部分。如果個體選擇違背既有的行為模式,那么可行性依舊存在,但勢必受到該群落其他個體的攻詰。之所以個人有能力這么做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社會生物學的必然性來自于基因存續(xù)機制的慣性而非單純的強因果性。其二,人類的認識能力在把握了生物界的必然性后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即擁有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相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