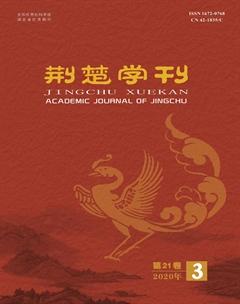中國當代青年的媒介素養及其文化認同
秦洪亮
摘要:新媒體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當代中國青年人,其媒介素養與文化認同有些駁雜,有必要到具體的文化現實中尋求答案。在多元的媒體文化環境下,青年群體對官方主流文化既積極擁護也存有建設性意見,對于大眾文化的審美化和浮躁化傾向缺少清醒的認識,而對作為深度范式的精英文化同樣缺少認同感。面對大眾文化和新媒體文化的消極影響,作為主要參與者的青年人若只慣于接受低質的媒介資訊、作戲謔化的形式抵抗,雖有助于釋放壓力、放飛自我,卻無益于自身的茁壯成長,青年人應時刻保持清醒,學會拒絕淺薄,回歸現實。
關鍵詞:新媒體;青年媒介文化;淺薄;文化認同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2-0768(2020)03-0082-05
一般將當代中國文化劃分為官方文化、大眾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四大類,但鑒于新媒體環境下崛起的草根文化對青年群體產生了超出民間文化的影響力,因此,針對青年群體的探討,可從官方文化、大眾文化、精英文化和網絡草根文化四種形態著手,而更進一步,針對新舊媒體文化影響的延續性,探討青年問題可簡至從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媒體文化(包含舊媒體的大眾文化和新媒體的分眾文化)三個層面入手。具體來講,不同文化施加于青年群體的影響強度不盡相同,官方文化、精英文化著眼于青年人的教育問題,新舊媒體文化多為青年人主動接受和參與,而隨著網絡和新媒體的飛速發展,新媒體的影響日漸突出,顯影于傳統媒體的官方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影響有所減弱,精英文化沉于書齋相對疏于媒體權力,影響力長期有待加強。青年人與新媒體文化具有天然姻親性并深受其影響和塑性。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在搶灘文化格局的較量中,雖不一定占據上風,卻很大程度地搶占了青年人的注意力。
這些不同的文化力量,在不同程度的媒體參與中形成強弱差異的權力話語,而混合文化、媒介與權力的信息體系,能夠大范圍地影響和沖擊當代青年人的知識體系和認同話語,這就對他們的媒介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媒體的出現,對媒介素養的要求增加了參與實踐中的創造、讀解以及傳播信息的能力。我們注意到,這更需要參與者特別是青年人具備較高的媒介素養,在參與性的接受、創造和轉發中辨別不良信息,并對有深度的優質信息保持認知熱度。媒體文化越來越強勢地占據當代青年人的文化接受盤局,而精英文化及其深度話語存在被邊緣化的風險,此消彼長之間會深刻影響到青年人的媒介素養和文化認同。
一、自主性地認同官方主導文化
伴隨著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官方積極引導消費市場,主導文化的優勢地位也不斷得到鞏固。同時,新媒體文化在一定層面沖擊官方文化,既可能促成兩者的良性互動,也可能拉出兩者之間的某種距離感。
首先,官方文化持續地正面引導新舊媒體的輿論方向。官方文化借助報業、廣電和教育等國家意識形態機器,自上而下集中式支配和影響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在趨向官方文化的同時,各成體系并持有別于官方文化的相對獨立性。異軍突起的網絡新媒體文化,在匯聚民間文化的狂歡元素、亞文化抵抗元素的同時,對其他文化樣式構成了某種消解。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強勢的經濟實力為國富民強的盛世圖景奠定堅實基礎,各級部門積極順應發展潮流,推動經濟發展,致力于社會的穩定和諧與人民的安居樂業。以傳統媒體為主要陣地的官方話語,成為這一發展潮流的堅定詮釋者和維護者,并在新媒體環境中依舊保持著正面引導,營造出有別于某些浮躁和媚俗的媒體文化的崇高與嚴謹。這種高峻嚴謹的官方話語,通過整治衛視綜藝與網絡綜藝的不良風氣,實施限娛令、限薪令以及抵制三俗演員等舉措得以強化,并由此促成行業內部形成自覺、自律的底線。官方文化在維護崇高形象的同時,進一步整合媒體文化、精英文化,并與青年人倚重的新媒體文化碰撞出一定的互動空間。
其次,官方文化在新媒體環境下積極求新求變。不斷翻新花樣的新媒體,不同層次地沖擊依附于傳統媒體的官方文化和大眾文化,為文化的多元發展注入嶄新活力。在傳統媒體框架下,大眾文化對官方文化的沖擊是相對的,其娛樂至死精神一定意義上消解官方的崇高文化,但官方崇高文化始終高度保持著支配地位,而兩者作為傳統媒體環境下的強勢文化,也需在新媒體環境中不斷調試并謀求新生。一方面,與謀求社會長治久安和人民安居樂業的執政理念相一致的官方傳媒,積極探索與不同媒體形式合作,通過官辦娛樂節目等豐富文化產業,及以開通各種微博賬號、便民公眾號等方式拉近與普通民眾的距離。就是說,在自媒體的渲染下,官方文化開始學著轉變角色,積極地與民互動、與民同樂,在政務宣傳中加入自媒體元素,融入“給力”“你懂得”“扎心”“呵呵”等網絡詞匯,展現出吸納民眾聲音的親民性。同時,網絡空間傳播的奢侈品等特定圖片、高考頂替信息等成為反腐或強化社會公信力的重要觸點,顯示出官方對于自媒體聲音的重視。另一方面,相比于官方傳統媒體穩固的主導地位,電視主導的大眾文化近年來雖取得長足發展卻面臨危機,除去一些喜聞樂見、雅俗共賞的節目持續贏得老百姓喜愛之外,一部分節目遭到網絡節目和海外制作的沖擊,網絡綜藝節目的年輕卡位、多元內容、碎片化時間以及互動性和靈活性等特點,往往更能奪人眼球,大眾文化需要不斷吸收新媒體元素來完善自身。
再者,青年群體對官方文化以認同為主,并與之保有一定距離。一方面,在網絡和新媒體中,青年人積極響應國家和人民號召,自覺抵制西方無良媒體、捍衛中國聲音。社會對青年文化的基本期許是相對恒定的,主要包含:“年輕人是充滿著生命力的、象征著人類世界未來希望的存在,與此相關聯,他們在精神、肉體上應該是純潔的、純粹的。”“青年必須是學習的,為擔當社會現代化的特殊角色而做準備。”“在個人—社會關系中,青年必須是奉獻性的。為民族、國家而戰斗、獻身,是青年的崇高義務。”“他們必須順應支配價值,接受成年人為他們設計的文化式樣,并服從成年人社會為他們制定的所有的規范的、制度的要求。”[1]純潔、奮斗、奉獻和順從等特質,中國青年人并不陌生,我們可以在五四運動中的熱血青年、積極參與抗擊新冠疫情的青年醫護人員和志愿者群體中,強烈地感受到這些美好特質。另一方面,青年人的網絡新媒體實踐,使其成為重要的媒體監督力量。近些年來飛速發展的網絡技術促使自媒體從有限的渠道中擠迸出來,凸顯為具備較強監督屬性的第四權力。網絡媒體監督的主要參與者并非來自中產階級、新型媒介人或精英群體,而是臥爬于新興媒體的青年或非富群體。他們大都尚未掌握有分量的資本,處于社會整體金字塔層級的底層,但他們對數字裝置表現出超越其他階層、其他年齡的興趣和參與度,在響應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的同時,堅持自我獨立并充當著權力監督的角色。在特定事件發生后,他們能夠借助聲勢浩大的網絡人群,迅即點染事件并形成強大的輿論合力和社會關注,促成問題或事件的合情合法處理。再者,由于青年人身處親近新媒體而相對疏遠傳統媒體的文化環境,導致他們不會一味沉浸于大眾文化,也不會廣泛接觸傳統媒體的官方文化,如此也會產生一種距離感。諸如學習強國等主旋律應用的推出,讓這一局面在一定層面得到改觀,但是,讓青年人從大眾文化和網絡文化的習有傳統中適度抽身出來,加入主動和自覺學習主導性文化的平臺隊伍中,仍舊任重道遠。
二、無意抵制媒體文化的消極面向
消費文化渲染下的日常生活呈現出審美化與虛浮化,這在大眾媒體中得到直觀映現。作為媒體文化主要參與者的青年人,不只在追逐大眾文化,而且沉迷于甚或比大眾文化更媚俗的網絡文化。
學界的大眾文化研究相對比較成熟,并對此存有批判和肯定的不同聲音。對大眾文化的批判,一般源自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馬爾庫塞等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場上,無情地批判大眾文化的強制性、齊一性和平均化等特征,認為它們貽害無窮、乏善可陳。而英國文化研究往往采取肯定態度,威廉斯和霍爾等學者致力于發掘大眾文化消解主流話語的面向,肯定受眾的抵抗力量而非只是文化工業的消極附庸。中國學界以往對于大眾文化的態度,主要受法蘭克福學派影響而展開批判,近來涌現出一些持肯定態度的學理分析。在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的先期膨脹中,人們已經開始感到焦慮的是它們對于青年認知的腐蝕作用。當然,針對大眾文化乃至后起的網絡文化的負面影響,也都存在不同的聲音。大眾文化對觀眾具有超強的操控力,以至把觀眾改造為受眾雇傭,受眾雇傭指個體在觀看電視節目時,雖身處自家客廳消遣卻如同在工廠操作間勞作,并非只是獲得身心愉悅,而且受控于消費社會的虛假意識形態。針對網絡新媒體的批判聲音更進一步,指認個體不止是客廳中的家庭雇工,而且在時空不受限的網絡和移動裝置使用中成為數字勞動者,遭遇的是比家庭雇工更嚴重的數字異化勞動,個體在裝置操控中獲得快感的同時,可能日益陷入資本文化的數據圈套。作為新媒體主要參與者的青年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負面影響。因為新舊媒體從業者,面對媒體與消費文化茍合之態往往認識不足并宣揚物欲現實,而當下消費文化吸納新媒體在攫取受眾注意力方面的主導性,時常利用人際傳播、電商平臺的優勢擴大營銷范圍,新媒體參與者則在各種自我炫示中主動吸納這種虛浮觀念且越陷越深。
青年人對媒體文化的溫和抵抗,并不能形成強力的反思性或革命性力量。承接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對大眾文化的肯定姿態,青年人對媒體文化中的消極面向雖往往缺少足夠的應對能力,卻也不是絲毫沒有自身的話語空間。青年人不會任憑大眾文化和網絡文化將自身蠶食掉,他們總歸對此操持著一定的協商話語。胡疆鋒認為:“青年無疑是大眾文化最重要的受眾群體,大眾文化從來不加掩飾的愉悅性和商業性,對當代青年的審美觀念、價值觀帶來的沖擊和影響,是怎么估計也不過分的。隨著新媒體技術的普及和消費主義的盛行,當代青年有了更多的創造新文化的機會,大眾文化從來沒有、也不會終結青年文化。隨著全球化和網絡時代的到來,大眾文化的蔓延速度越來越驚人,其解構和建構的能力與日俱增,也越來越明顯地催生或改變著中國的青年文化和文化版圖。不過,大眾文化與青年文化的關系似乎遠非侵蝕與被侵蝕那么簡單。”[2]青年人自然不會一味地接受大眾文化和網絡文化,他們會在相關文本的自我發揮中成為盜獵者。一方面,傳統媒體主導的大眾文化已成為青年亞文化改寫、拼貼和戲仿的對象,而新媒體出現之后,社會生活無處不在的媒介化現象,展現出不同于大眾文化的傳播效果,青年人不再熱衷于傳統媒體自上而下的單向傳播,而是投身于自下而上甚至平等的雙向傳播,在網絡空間的惡搞、表情包、火星文和彈幕等亞文化的刺激把玩中,消解其他主文化的傳統地位。但這一切的消解是相對溫和的,沒能改變媒體文化的固有地位,不能因此將其認定為是青年人有意識的、積極的抵制行為。
媒體文化將物欲觀念和娛樂至死的理念灌輸給青年群體,要說沒有絲毫的侵蝕作用是不現實的,針對這種侵蝕的憂慮也無可厚非。新媒體或自媒體文化至今尚未展現出高于大眾文化的價值和趣味,但對青年的腐蝕作用相比大眾文化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就如抖音的腐蝕性不是《天天向上》所能比擬。德國哲學家沃爾夫岡·韋爾施在《重構美學》(1992)中宣告審美泛濫時代的到來,時至移動與互動媒體時代,數字化存在日益深刻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審美理想,人人成為新聞攝影記者和生活藝術家,數字化另類審美以更加碎片化的方式嵌入現實世界,甚至使崇尚外觀的日常生活審美化,轉向推崇強刺激的日常生活粗鄙化。當代青年人大多心懷家國,擁護各項方針大略,并時常在網絡空間針砭時弊、嫉惡如仇,大力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狼子野心。但也有一部分人時常激憤互懟、臟話連篇,更有甚者附庸于社會浮夸風氣而不自知,或沉于網絡海洋而無藥可救。一部分相對處于弱勢的青年群體,不滿于自身的現狀,對資本富足者“羨慕嫉妒恨”,甚至在現狀暫無法改變時消極厭世,然而他們對消費特別是裝置消費熱情非凡,很多時候正是因為裝置消費得不到滿足而表現消極。盡管青年人的經濟承受力相對是有限的,卻絲毫阻攔不住他們購買數字設備的狂熱,有的甚至一味沉浸于數字裝置的虛擬游戲、虛擬交際空間,漠然于周遭真實世界的人和物。
在國內,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時常以青年人為主要目標群體,卻沒能給予青年人足夠的文化給養,從精英主義視角來看甚至有拉低他們認知水平的風險。放眼中國各地大小影院的觀看坐席,青年人滿為患,其他年齡段則為少數,因為當前中國的電影市場,往往以青年觀者為目標接受群體,但參差不齊的影片質量將之引向拒絕思考的面向。他們對影視藝術的欣賞,沉迷于“小鮮肉”的身體景觀,對“老戲骨”的深情達意不以為然,不顧及思想內容,稍顯復雜的情節便表示看不懂。瘋狂于《捉妖記》《小時代》《西游記女兒國》的矯揉造作,卻直呼看不懂《聶隱娘》的慢調敘事,更鮮為問津《地久天長》等好口碑文藝片。如此拒絕深度思考、沉迷視覺奇觀或媚俗的行為,被德布雷視為“集體的不思考”[3],但在國內更準確地說是“青年的不思考”。在移動與社交媒體的影響之下,“淺薄”(尼古拉斯·卡爾),“愚蠢的一代”(馬克·鮑爾萊因)更加成為青年人的代名詞,沉迷于消費文化、表象美學和網絡刺激的他們,被認作不尊重傳統、缺乏社會歷史責任感、不具備前人的公民意識,無法以合格的組織者和責任者應對社會價值體系和指導公共政策。“最愚蠢的一代的病根就在于此,不是學校,也不是工作,而是他們鐘情的游戲、社交網絡以及消費支出。”[4]165這就將責任直指網絡新媒體文化,認為它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互聯網的確改變了我們閱讀和書寫的方式。沒多少人想在電腦上閱讀《戰爭與和平》,電腦不適合深入長期閱讀。長期閱讀更適合在線下,不論是在線上還是在電子設備上,當對著一臺連著網并且網速很快的電腦,我們最不想做的就是停止上網、放慢速度或專注地做一件事情。”[5]當然,多數青年人并沒有腐朽掉,仍是社會正義力量的積極傳播者,仍保有刻苦向上的認知態度,但在浮躁與淺薄的路途上,確實有不少青年人接踵而至。當網絡在不斷地切割人們的注意力,長期慣于屏幕閱讀的青年人,往往缺乏全神貫注的閱讀能力、縝密深刻的思維能力,以至對深奧的文章敬而遠之,可見從大眾文化階段到網絡文化階段,媒介對個體的影響存在由不思考轉向淺薄之嫌,相對有深度的精英文化能否力挽狂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