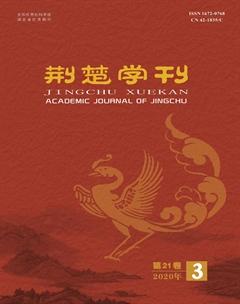從林黛玉形象塑造看《紅樓夢》“互文性”寫人之道
李桂奎
摘要:《紅樓夢》之寫人雖然存在取自文本外部的所謂社會“原型”甚至“自敘傳”跡象,但更不可忽視的是它還廣泛地來源于文本與文本之間的借鑒吸收,即以歷代不斷累積的“互文性”見勝。作為一部經典文學名著,《紅樓夢》的“集大成”性質除了體現為對以往形形色色的文化元素的兼收并蓄,還突出體現為其寫人文本多由各個不同的“集眾為一”而成。就拿頗具代表性的林黛玉形象塑造來說,她既是歷代無數富有畫感的名媛嬌娃意象的積聚,又是眾多以傷心為主調的詩性符號的集結,蘊含著而今人們所謂的“互文性”寫人之道。這種“互文性”既有宏觀層面的,又有微觀層面的。即使那些通過文本內部賈寶玉、薛寶釵以及晴雯等人物與林黛玉之間的對照、映照寫法所傳達的各種影像,也常常除了與前人文本有諸多關聯,還具有文本互生性質,同樣可視為一種富有特色的“互文性”寫人之道。總之,從林黛玉這一“獨一無二”形象塑造看,《紅樓夢》之文本創構中含蘊著多元化的“集眾美為一體”“合諸情于一身”的寫人之道。
關鍵詞:互文性;詩性形象;集大成;嬌美意象;傷情心象
中圖分類號:I207.41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2-0768(2020)03-0005-07
關于小說的敘事寫人之道,現代作家魯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講過這樣一番很有影響的話:“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1]513后來,他還在《〈出關〉的“關”》一文中進一步提出,“作家的取人為模特兒”,除了“專用一個人”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一種,即“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1]519此即為人耳熟能詳的所謂“雜取法”。在社會批評、文本外部研究風行的年代,魯迅的富有權威的寫人之見自然受到追捧,并不斷地被拿來論證當年紅極一時的“典型化”理論。然而,現在看來,他所謂的“雜取”或“拼湊”云云,只是顧及了取材或反映現實的“反映論”一面,而沒有特別重視文本與文本之間所存在的彼此承繼關聯的“互文性”一面。事實上,大凡經典小說寫人,常常除了依靠對現實人生追蹤躡跡,還要依托對歷史文化文脈的沿承,尤其是離不開文本形成過程中相關意象的不斷滾積。這種通過“層層累積”“集眾為一”的寫人之道,以重新創造出新的人物,就像把小的物體揉滾成大的圓球那樣,故不妨用“團揉”“摶揉”等俗語視之。《紅樓夢》寫人不企求一氣呵成,更非一次性兜售,而是層層加碼,步步為營,最終達到渾然天成。此正是這種寫人之道的經典演示。在這種筆法之下,林黛玉等人物形象便成為一個個讓人感覺似曾相識而又耳目一新的“熟悉的陌生人”,紛紛以“意象集”“角色叢”“影子的影子”“鏡像的鏡像”“箭垛式的人物”等“集大成”的面貌出現。由于上世紀尚未引入“互文性”理論,故而人們多采取“匯集”“會聚”“集大成”等觀念論說之。正如紅學家王昆侖《紅樓人物論》所指出的:“黛玉以前,中國原有著千千萬萬個局部的黛玉;到了黛玉出現,那許多不完整的人物之情、之才、之貌,就都匯流在這一個人身上。”[2]沿著“集大成”“互文性”這個思路,我們還可通過這一經典形象的塑造,進一步深入探討《紅樓夢》的寫人之道。
一、“集眾美為一體”及其意象化育之道
從文本敘述和相關評點來看,《紅樓夢》關于林黛玉的塑造中卻采取的是循序漸進、不斷完善之道。庚辰本第十六回寫林黛玉面對賈寶玉將北靜王所贈的“鹡鸰香念珠”轉送給她,質問道:“什么臭男人拿過的!”并擲而不取。對此,脂硯齋評語曰:“略一點黛玉情性,趕忙收住,正留為后文地步。”[3]260這一“略點”,突出的是其“質本潔來還潔去”。“留為后文地步”既含有敘事余漾不斷的意味,也體現出逐步展開的意圖。每逢寫到人物,作者總是略一點染,適可而止,以便為實現整體上的“集眾為一”留有余地。此正是《紅樓夢》作者所著意采取的一條重要的寫人之道。作者筆下的林黛玉之所以與她的搭檔賈寶玉、薛寶釵等角色一樣,令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乃至達到一千個讀者會產生一千種審美感覺,主要就是因為他們均是“集眾為一”的結果。
毋庸置疑,在人們心目中,《紅樓夢》中的林黛玉首先是一道精彩絕倫的“美品”。根據作者曹雪芹自己在小說文本中的表態以及其近距離的評點者脂硯齋傳達的信息可知,由于作者曾對當時小說中千篇一律的寫人弊端有著清醒的認識,因而厭棄“滿紙‘羞花閉月等字” “滿紙紅拂、紫煙”[3]15“滿紙皆是紅娘、小玉、嫣紅、香翠等俗字”“滿紙‘千伶百俐‘這妮子亦通文墨等語” [3]67這類生硬刻板的寫人套路,致力于借助各種前人文本中的有生元素,讓一批少男少女在紙上復活。其中比較亮麗的一道風景是,通過賦予林黛玉以紅顏薄命、多情短命等嬌美多情形象,使之成為古往今來無數女性“病態美”的化身。
在黛玉身上,到底集聚了多少個文化符號?對這個難以數計的問題,紅學家馮其庸曾有過這樣的概括:
林黛玉這個藝術形象,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中國傳統文化、傳統美學理想,經過曹雪芹嶄新的思想而孕育化生出來的。析而言之,她有藐姑仙子的仙和潔,她有洛水神女的傷,她有湘娥的淚,她有謝道韞的敏捷,她有李清照的尖新和俊,她有陶淵明的逸,她有杜麗娘的自憐,她有馮小青的幽怨,她有葉小鸞的幼而慧,嬌而夭,她更有白身幼而喪母復喪父的薄命……總之,在她的身上,集中了傳統性格和傳統美學理想的種種特點和優點,镕鑄成一個完美的活生生的獨特個性。這個個性是孕育化生而成的,不是集合而成的。[4]
從這里提供的線索看,林黛玉由《莊子》《洛神賦》《湘夫人》《世說新語》《牡丹亭》等文學文本所塑造的各色文學人物和謝道韞、李清照、陶淵明、葉小鸞等各種才女逸士“集中”“熔鑄”“化生”而來,而非簡單的“集合”或“疊加”。我們盡管無法也不宜憑著基因解剖的方式對林黛玉身上的文化細胞進行“互文性”驗證,但卻可以通過審美聯想來洞察或發掘這一形象塑造的“互文性”淵源。這本身是一項很有興味性的審美工作。
近年,隨著“互文性”理論的引進以及相關理論方法的深入人心,已有學者開始有意識地用這一理論觀照林黛玉形象塑造。如陳洪《從“林下”進入文本深處——〈紅樓夢〉的“互文”解讀》從“可嘆停機德,堪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掛,金簪雪里埋”出發,引劉義慶《世說新語·賢媛》所載一尼姑對王夫人謝道韞、顧夫人張玄妹妹兩位名士夫人的點評之語:“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指出謝道韞有才情,并有“林下之風”,而“林下之風”與“閨閣之秀”相對應。通過自然與名教的對應,揭示出林黛玉身上的謝道韞氣息;并進而指出第五回關于林黛玉的“堪憐詠絮才”判詞,更是直擊《世說新語·言語》所載一段文字:“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紅樓夢》依隨東晉才女謝道韞塑造黛玉,正映現出其才華橫溢、詩風靈秀的特點。[5]如此這般關于林黛玉形象的追蹤,用的是“互文性”觀念,闡發的是寫人之道,給人以很大啟發。
《紅樓夢》的作者不僅別具匠心地遣用謝道韞等各歷史人物以喻說林黛玉,而且還隨機將其他“病態美”的形象及其性情投射到她的身上。毋容置疑,在關于“病態美”的形象中,若論與黛玉形似和神似之高,首先當數由來更久的美女西施。作者于第三回正面呈現其面貌,除了前述“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那兩句,更用了這樣的筆墨:“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嬌花照水,行動時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這些筆墨傳達出眉清目秀、多愁善感、嬌美多態、聰明伶俐、體弱多病等多重信息。在作者筆下,林黛玉聰慧靈敏,乖巧可愛,又有些敏感多心,故以傳說中擁有“七竅玲瓏心”的比干和常于蹙眉捧心的西施來比襯凸顯。描寫林黛玉“病如西子勝三分”,正與“西施捧心”典故構成互文。而“西施捧心”典故與“東施效顰”典故皆見于《莊子·天運》,說的是,春秋時美女西施有心痛病,經常捧心而蹙眉,更添媚艷。鄰家丑女效仿其捧心皺眉,反而愈顯其丑。自此,人們把捧心蹙眉視為女性的一種嬌柔之美。宋代馬永卿《嬾真子》卷一《屈言之妙》云:“仆讀至此,始悟莊子之言曰:西施捧心而嚬,鄰人效之,人皆棄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嚬,無不佳者,如屈子以笑為宜,而莊子以嚬為美也。”[6]《紅樓夢》在寫黛玉出場時,即通過一路下來的一系列文本互涉賦予其以病態美。接下來,小說又借寶玉與黛玉之間的一番對話,強化了黛玉的善顰秉性:“寶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道:‘何處出典?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妹妹眉尖若蹙,取這個字豈不美?”寶玉見黛玉生得“眉尖若蹙”,便靈機一動為其取字“顰顰”,不僅盡得西施顰眉之美的風韻,而且還將其關聯到《古今人物通考》的石黛典故,陡然又增出一層文本意義。年少的寶玉未必有此博識,而博學的作者卻能信手拈來,不斷地給黛玉增添文化氣韻。作者在行文中對黛玉的纖腰裊娜之姿,走起路來如弱柳扶風之態反復點染。
細心的讀者也許早已覺察到,《紅樓夢》寫黛玉之美往往不是直接描摹夸飾,而是常常借其他人物的觀議來達成。第五十五回寫王熙鳳對平兒說林黛玉“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第六十五回寫仆人興兒口中的黛玉“姓林,小名兒叫什么黛玉,面龐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這樣的天,還穿夾的,出來風兒一吹就倒了。我們這起沒王法的嘴都悄悄的叫他‘多病西施。每常出門或上車,或一時院子里瞥見一眼,我們鬼使神差,見了他兩個,不敢出氣。”如此對“西子顰眉捧心”之美、被稱為“多病西施”等等反復強化,再加林黛玉自小有不足之癥的交代,便使得“善顰”的病美人西施像一個幽靈,附體還魂于黛玉身上,揮之不去。
另外,《紅樓夢》還著意寫林黛玉常為寶玉傷心落淚,故又把她比作為虞舜淚灑斑竹的娥皇和女英兩位妃子,并在第三十七回借助寫探春跟黛玉開玩笑時說的幾句話道出其中究竟:“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這無形之中又賦予林黛玉以劉禹錫詩歌所謂的“淚痕點點寄相思”的“斑竹”意象。這里借鳳姐與寶玉兩個人物的口耳來展演林黛玉的絕世之美,為其增添了另一重瘦弱傷心之美。
當然,《紅樓夢》并不滿足于此,其第二十七回的回目“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冢飛燕泣殘紅”,再度把林黛玉比作知名度較高的漢代能輕飄于掌上舞蹈的寵妃趙飛燕。據漢代伶玄《趙飛燕外傳》載:“宜主(趙飛燕)幼聰悟,家有彭祖分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7]結合前述小說所寫林黛玉“行動似弱柳扶風”,便可見出其體態之輕盈,真宛如翩翩起舞的趙飛燕之美。
在關于黛玉的塑造中,《紅樓夢》作者不僅“舉一反三”,更在于“集眾為一”,直至“以眾美證成一美”。對此,傅憎享也有過這樣的分析:
他(曹雪芹)把美的單體置于眾美叢集的群體之中,不僅以美與美感、美的效應,更以眾美證成一人之美。連環不是循環,迭加不是簡單相加;不是組合混合,而是融合化合生成一個新生象。在共變鏈中,美的群體是單體賴以產生的母體,而單體又是必不可少的環節。通過叢集鏈環節間的變換易位交互作用,通過往返流動的共變因果,人們逐漸地認識了人物,人物的實象在心目中漸次生成。[8]
所謂從“單體”到“群體”的“叢集”,所謂“眾美證成一美”“融合化合生成”云云,都道出了《紅樓夢》“互文性”寫人之“集大成”本真。可以說,這位從歷史文化的千山萬壑中走來的林黛玉,絕對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速之客,也并非是現實某一人物原型的追攝,而是一種“多而一”的“互文性”會聚。
二、“合諸情于一身”及其詩性化合之道
按照第一回的說法,《紅樓夢》“大旨談情”,而林黛玉是“情”的化身。這個“情”不僅僅是一般的兒女常情,而且還包括各種各樣的人生情操和情感。小說所寫林黛玉身上的“情”錯綜交會,卻不是大雜燴。第三回寫林黛玉亮相,便以“兩彎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笑非笑含情目”兩句為其定格,以“愁眉”“淚眼”為其奠定“含情”基調,從而確定了其籠而統之、大而化之的多愁善感的“傷心人”面貌。
首先,從詩稗跨界視角來看,《紅樓夢》作者繼承發揚了傳統詩歌賦比興,尤其是《離騷》以來運用“香草”比喻“美人”的寫作風尚。除了以前人文本其他人物作鏡像來映照,作者還賦予林黛玉“詩魂”與“花魂”秉性,使其身上集結了多種人情物理之意象與神韻。脂硯齋于第八回在反復感嘆小說所寫黛玉含酸處“不知有何丘壑”之余,進而概括道:“用此一解,真可拍案叫絕,足見其以蘭為心,以玉為骨,以蓮為舌,以冰為神。真真絕倒天下之裙衩矣。”[3]159指出作者是在不斷地借前人文本中不斷運用的“蘭”“玉”“蓮”“冰”等高潔意象來形容黛玉的超凡脫俗、能言善辯等品質,可謂集天下美女性情之大成。
且不說《紅樓夢》作者筆下的林黛玉雖然年紀輕輕,但其才情不僅已隱約含有秦觀、晏幾道以及李清照等“古傷心人”之心影,而且還兼具辛棄疾等“豪杰”之孤高情懷。梁啟超《飲冰室評詞》評價辛棄疾《青玉案·元夕》所言:“自憐幽獨,傷心人別有懷抱。”[9]同樣也可以用以言說林黛玉。第二十六回寫道:“越想越覺傷感,便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黛玉秉絕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這一哭,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棲雞,一聞此聲,俱成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作者如此忽前忽后地一路寫來,寫出了黛玉的孤苦無依及其心中的孤寂凄涼。黛玉正是一位清雅淑女,所以她擇“竿竿青欲滴,個個綠生涼”的瀟湘館為居。古人有言: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瀟湘館被安排給黛玉居住,也許包含著某種深意。第二十六回寫寶玉來到瀟湘館,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用這八個字形容滿院翠竹,不是相當奇巧嗎?黛玉的別號“瀟湘妃子”則取義于:“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她住的是瀟湘館,她又愛哭,將來她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后都叫她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前面以鳳喻之,后面又以娥皇、女英喻之,且又號曰“妃子”,妙合無垠。同時,也回應了第五回“世外仙姝寂寞林”那句用以為人物定性的曲辭。
《紅樓夢》中的林妹妹年齡雖小,才能和學問倒是非同小覷。眾所周知,一切景語皆情語,小說寫花即寫人,作者筆下黛玉的《葬花詞》《桃花行》《唐多令·柳絮》等詩詞足以見出她的哀傷凄婉性情;《問菊》則頗顯出其清高情操。她的詩詞創作本身就是經過“吸取”“融化”的意象積聚和符號集結,不是生拉硬扯,硬性捏合,而往往是水乳交融的“互文性”的。紅學家呂啟祥曾經說:“林黛玉不僅是《紅樓夢》的第一女主人公,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做整個中國文學史的第一女主人公。她是凝聚著本民族文化的華粹精英……《紅樓夢》的作者明白昭示這是一部為閨閣傳真的作品。如果說,他把天地間靈秀之氣所鐘的女兒喻之為花,那么,林黛玉就是花的精魂;如果說,他把生活心靈化而流瀉為詩,創造了充滿詩意的真正的藝術,那么他所創造的林黛玉形象最富于詩人氣質,是詩的化身。”[10]《紅樓夢》作者也許有借寫人物題詠、聯詩等各種活動為自己留存原創詩詞曲賦的初衷。的確,作者借鑒前人文本而創作的作品得以有賴小說傳世而被有效地儲存起來。尤其是,作者賦予林黛玉以多才情,頗有幾分將自己才情寄托于文本人物的意圖,也可以說是作者“借稗傳詩”的重要策略。
與此同時,除了顰眉捧心的西施,金圣嘆以元代王實甫之作為基礎評點的《西廂記》中的鶯鶯(間或紅娘)也是《紅樓夢》寫林黛玉用以比附的對象,甚至讓林黛玉時常索性以鶯鶯自居。曹雪芹寫黛玉在與寶玉感情交流過程中,反復直接引用《西廂記》鶯鶯與張生的唱詞,這不僅意味著作者對這部戲曲之熟稔,信手拈來,令其筆下的人物“活學活用”,而且也表明《紅樓夢》中的寶玉、黛玉以及紫鵑時常自覺扮演張生、鶯鶯以及紅娘角色,以他們為自我人生角色扮演的“影像”。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是靈活機變式的“互文性”應用,“《牡丹亭》艷曲驚芳心”是感同身受式的“互文性”接受。寶玉讀《西廂記》后心有所感,用戲曲中的原話和黛玉交心:“我就是個‘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寶玉如此套用《西廂記》第一本第四折張生唱詞,不料惹惱黛玉;而他在賠禮道歉時,卻又反被黛玉借用《西廂記》第四本第二折紅娘唱詞中的語言取笑:“呸,原來是苗而不秀,是個銀樣镴槍頭。”寶黛對《西廂記》曲詞賓白的這種活學活用不僅使兩部作品的人物發生勾連,而且直接使得兩部文本發生互動。《紅樓夢》不僅將鶯鶯的才情寫到林黛玉身上,而且還接受《牡丹亭·離魂》寫春香演唱的曲詞的影響,將杜麗娘“連宵風雨重,多嬌多病愁中。仙少效,藥無功”等性情寫到林黛玉身上,使黛玉詠出“連宵脈脈復贍贍,燈前似伴離人泣”詩句,大概是《牡丹亭》寫春香的曲詞的轉換;而“多嬌多病愁中”無疑正是黛玉嬌弱生命的最好寫照。從這個意義上說,林黛玉仿佛是鶯鶯之再生,杜麗娘之再世。該回的庚辰本批語有言:“以《會真記》文,后以《牡丹亭》曲,加以有情有景消魂落魄詩詞,總是急于令顰兒種病根也。看其一路不跡不離,曲曲折折寫來,令觀者亦自難持,況瘦怯怯之弱女乎!”[3]402脂硯齋這幾句評點揭示出《紅樓夢》是如何寫《西廂記》《牡丹亭》曲詞熏染林黛玉這位嬌弱女子的,而且也告訴讀者前者是如何將后兩者的人物附會到林黛玉身上的。再如,第二十六回寫寶玉將臉貼在紗窗上看時,忽聽得黛玉細細的長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此乃《西廂記》第二本第一折鶯鶯唱詞。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寶玉掀簾子進屋后,面對紫鵑端茶倒水的周到服侍,寶玉脫口而出:“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舍得疊被鋪床?”乃活用了《西廂記》第一本第二折張生唱詞。如此這般,《紅樓夢》寫寶玉、黛玉受到《西廂記》感染,時常自覺不自覺地扮演起張生、鶯鶯角色來。還有,第四十九回寫寶玉注意調解黛玉和寶釵矛盾,卻不知她們早已以同胞姐妹共處,就情不自禁地借用《西廂記》紅娘的一句唱詞來問黛玉其中究竟:“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是在引用《西廂記》第二本第一折張生唱詞說事。在聽了黛玉的解釋后,寶玉才恍然大悟,并且用《西廂記》中的另一句唱詞“小孩兒家口沒遮攔”,取笑黛玉說錯酒令之事。由此可見,許多《西廂記》文本曲詞貫穿于寶黛二玉的“戀愛史”中,也表明他們口無遮攔,有著心心相印的共同語言。有趣的是,每當寶玉運用《西廂記》淫詞艷語調情逗趣,林黛玉總是會一時間難以接受這種突如其來的直露表白,表現出對他“看了混賬書”,拿她“解悶”的指責,并擺出要向長輩告狀的姿態,頓時回到《鶯鶯傳》中大家閨秀鶯鶯那般的矜持;而每當寶玉那張生般的狂情不得不有所收斂,只好發誓再不敢說“這些話”時,林黛玉又反倒像《西廂記》中的紅娘那樣大膽。
《紅樓夢》與《西廂記》文本關聯度甚高,脂硯齋自然也經常予以涉筆評批。如針對第四十三回所敘茗煙不知寶玉底細,含淚施了半禮,跪下代祝一段文字,乃從《西廂記》所寫雙文降香,紅娘代祝數語那段文本而來。再如,針對第二十六回所敘“瀟湘館春困發幽情”一節,庚辰本有眉批曰:“方才見蕓哥所拿之書,一定見是《西廂》。不然,如何忘情至此?”[3]453針對第四十五回寶玉與黛玉一番對話,脂批曰:“妙極之文,使黛玉自己直說出‘夫妻來,卻又云畫的、扮的。本是閑談,卻是暗隱不吉之兆,所謂‘畫兒中愛寵是也,誰曰不然?”[3]732這意味著,《紅樓夢》對《西廂記》的文本師法既駐足于局部敘事,也草蛇灰線般地隨時閃爍于字里行間。特別是第三十五回,寫黛玉自比鶯鶯,是作者把鶯鶯當作黛玉描寫的鏡像。黛玉回瀟湘館,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第二本第一折所寫紅娘唱的“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兩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雙文,誠為薄命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懦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并連孀母弱弟俱無。”總之,元代王實甫《西廂記》中的鶯鶯已被寫得富有才情,纏綿悱惻;明代湯顯祖《牡丹亭》繼而又把鶯鶯的多情發揚光大到杜麗娘身上,使之柔情繾綣。經過清人金圣嘆的評點,鶯鶯更是被賦予以“至尊貴、至靈慧、至多情、至有才”等秉性,《紅樓夢》將其脫化到林黛玉身上。
其次,《紅樓夢》在反復展演林黛玉的詩才,在反復表現其博學、卓識的過程中,正是為了不斷地突出其特立獨行、多情多才品格。第三十七回寫大觀園起詩社時,探春給自己起別號“蕉下客”,黛玉借機挖苦她是一頭鹿,眾人都不解其意,黛玉解釋說,古語有云“蕉葉覆鹿”,惹得眾人哈哈大笑。今人已考察出這個古語淵源在《列子·周穆王》。試看,連林黛玉開個玩笑,作者也借助“互文性”策略增添其妙趣。更能顯示黛玉詩詞才情的是第六十四回所寫黛玉悲題《五美吟》一節。《五美吟》依次吟詠了西施、虞姬、王昭君、綠珠、紅拂五個人物。按照林黛玉自己的說法,“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嘆者甚多,胡亂湊幾首詩,以寄感慨”,自然是“互文性”的用典而成,是作者感慨“古史”所載才色絕佳而命運不幸女子之作,這些所謂“古史”,包括詩詞、小說在內。在作者筆下的黛玉筆下,《西施》中的美女西施依托于《莊子》所載東施效顰故事,首句“一代傾城逐浪花”寫西施傾國傾城之美乃化用自漢代《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明妃》中的王昭君的故事,參照的是西晉葛洪《西京雜記》中所寫昭君不肯賄賂畫工以致不為元帝所知被詔使出塞的傳說。《綠珠》中的富豪姬妾綠珠,主要根據《晉書·石崇傳》,并借鑒《世說新語》所載潘岳《金谷集作詩》等相關記載附會而來。而《紅拂》中的紅拂形象,則取意于唐代小說家杜光庭《虬髯客傳》所寫英雄李靖與大官僚楊素姬妾紅拂以及奇俠虬髯客之間的風云際遇。作者的高明之處還在于借寶釵的一番評賞,道出小說中的黛玉之詩如何翻意出新的奧妙:“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詠昭君之詩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后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所謂“翻古人之意”“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云云,正是而今所謂“互文性”寫作的重要密諦之一。
至于林黛玉所賦如泣如訴的《秋窗風雨夕》,更是直接模擬唐代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詩意,更形成情韻兼備的互文。是文本之中林黛玉之作,更是文本之外作者采取“互文性”策略襲擬而來。就文本效果看,它既渲染了審美氣氛,又助益于深情寫人。
當然,小說還特別注意通過寫林黛玉對前人詩歌的愛好,來巧妙地傳達其心境。如第四十回寫林黛玉表示最不喜歡李商隱的詩,而偏偏只喜歡“留得殘荷聽雨聲”一句。這句詩所隱含的冷寂、孤高意境正是與林黛玉當時的性情吻合的。
《紅樓夢》善于化詩意為稗家敘事,其文本之美,不僅美在作者經常于行文中根據情節需要插入大量詩詞,而且美在其敘事寫人文墨中往往含有豐富的詩韻。于是,林黛玉也成為天下無數傷心人的詩意化身。
三、“對映互影”及其鏡像化成之道
《紅樓夢》所采取的文本內部人物與人物之間的對照、映照進行寫人策略,著意以“鏡像”“影子”等方法寫人,從賈寶玉、薛寶釵、晴雯等人物身上鏡照出林黛玉的影子,而作為鏡像的各人物影像又往往并非文本自足的,同樣含有意象積聚和符號集結因素。也就是說,由于鏡像人物或影子人物也是有文本淵源的,對“互文性”寫人形成有效呼應,再加文本人物之間的彼此相生,因而這種行筆策略屬于西方文論不曾有的另一種中國特色的“互文性”寫人實踐方式。
從出場率看,寶玉無疑是黛玉形象塑造的第一鏡像。作者不僅通過敘述他們之間“相生相克”式的吵吵鬧鬧,反射出黛玉的小心眼、多愁善感,而且還通過他們之間的朝朝暮暮,演繹人間悲歡、傳達審美況味。第二十七回,作者筆下黛玉《葬花詞》,源于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是一場凄楚悱惻、抑郁孤苦之悲鳴。如僅寫黛玉一人自怨自艾,也無可厚非,但作者卻將寶玉拉到同一場域,不僅使之成為一個聽者,而且還使之成為一個情感共振的鏡像。寶玉時時關心林黛玉,一不見她即趕著尋覓,于是才有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直奔而來尋黛玉。于是才有了聽到她邊數落邊哭泣的“嗚咽之聲”,才有了因聽《葬花詞》的悲吟而引起的一連串推想:由林黛玉的花容月貌到無可尋覓,推之于寶釵、香菱、襲人等,再由人及已,由己及物,因而不勝悲傷。這種悲情渲染同步的、共振的,二者的詩性形象是同一色調的。至于第三十七回寫寶玉題詠《詠白海棠》之詩曰:“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也暗示出寶玉心中也只有終不忘世外仙姝的黛玉一人而已。總之,《紅樓夢》通過寫寶黛之間的小兒女恩怨爾汝,年齡漸長后的心心相印,使之達到“一而二”“二而一”的境地。這種文本相生的“寶黛合一”筆墨,不但文字經濟有效,而且之于寫人效果則是相輔相成。
相對于人們不太關注的“寶黛合一”,《紅樓夢》中的“釵黛合一”寫人之道常被人提及。作者反復以寶釵影像對照之,使釵黛二者合則為一體,分則為兩立。第五回《終身誤》曰:“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所謂“山中高士”“世外仙姝”應該是由明代高啟《詠梅》詩中的“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二句化用而來。其文本間際的關聯自不待言。作者把兩個關鍵人物置于同一曲子中,其意旨頗值得尋味。第四十二回,脂硯齋在總批中提出“釵黛合一”之說:“釵、玉名雖兩個,人卻一身,此幻筆也。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余,故寫是回,使二人合二為一。請看黛玉逝后寶釵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謬矣。”[3]679再回頭結合《終身誤》曲辭,我們不難感受到其中蘊含著這樣的寓意:兼美方得完美,互補才能圓滿。然而,世間本來沒有十全十美,任何人任何事皆會美中不足。因而,“釵黛合一”只能以虛妄的審美“幻象”形式而存在。
另外,《紅樓夢》以文本內部其他人物來比照林黛玉,形成“影子的影子”“互為影子”等寫人之道。如第七十四回寫王善保家的對王夫人說:“別的還罷了,太太不知,頭一個是寶玉屋里的晴雯那丫頭,仗著他的模樣兒比別人標致些,又長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樣了。”先將晴雯與西施勾連起來,繼而再寫王夫人聽了這話,就對鳳姐表白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罵小丫頭,我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樣子。”眾所周知,“眉眼”是一個人物內在特征的標識,從晴雯的眉眼再次傳達了林黛玉的眉眼。隨后,小說又寫王夫人到了鳳姐房中細看,那晴雯“因連日不自在,并沒十分妝飾,自為無礙。及至王夫人一見她釵蟬鬢松、衫垂帶褪,有春睡捧心之遺風,不覺勾起火來:‘好個美人兒,真像個病西施了!”在此,作者借助王夫人之言,接二連三地將歷代文史文本中的西施與小說文本內部的晴雯、黛玉聯系起來,達成意象和符號的多元會聚。這種“影子的影子”寫人筆墨,層層加碼,不僅是在步步凸顯晴雯之病態美,更是在不斷強化黛玉之病態美。
概而言之,“美”與“情”本是文學文本創構的兩大關鍵要素,《紅樓夢》中的林黛玉不僅兼而有之,而且深厚絕倫。從當今風行的“互文性”理論視角看,作者在這一形象塑造中,靈活機動地采取了“集眾為一”“合眾于一”等策略,既對香草美人等前人文本中詩情畫意進行了靈動的攝取與化合,又對歷代名媛嬌娃等相關成分進行了廣泛的吸納與團揉。另外,這部小說還別出心裁地借助文本內部人物之間的“對映”“互影”策略來寫人,使賈寶玉、薛寶釵、晴雯等人物與林黛玉互為鏡像,直至合二為一。如此下來,《紅樓夢》之“互文性”寫人不僅成就了其整體的“雅馴”“典重”審美格調,而且還使其文本顯示出“多而一”式的“集大成”性質。
參考文獻:
[1]?魯迅.魯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
[2]?王昆侖.紅樓人物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241.
[3]?曹雪芹.紅樓夢[M].脂硯齋評改,黃霖校理.濟南:齊魯書社,1994.
[4]?馮其庸.啟功先生論紅發微——論紅樓夢里的詩與人[J].紅樓夢學刊,2002(2):1-23.
[5]?陳洪.從林下進入文本深處——紅樓夢的互文解讀[J].文學與文化,2013(3):4-14.
[6]?戴錫琦,鐘興永.屈原學集成[Z].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43.
[7]?徐訐.小說錄要[M].臺北:正中書局,1988:55.
[8]?傅憎享.等閑識得東風面—從鳳姿與風貌的共變關系看紅樓夢一組女性肖像描寫[J].紅樓夢學刊,1985(3):155-164.
[9]?辛棄疾.辛棄疾全集[M].徐漢明,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4:476.
[10]?呂啟祥.花的精魂 詩的化身——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蘊含和造型特色[J].紅樓夢學刊,1987(3):41-60.
[責任編輯:黃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