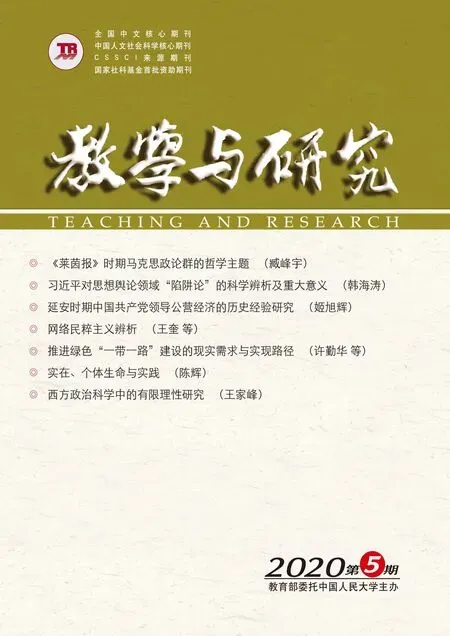《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政論群的哲學主題*
臧峰宇
1842年5月,馬克思開始為《萊茵報》撰稿并參與編輯部的工作,不久先后擔任該報編輯和主編,直至1843年3月17日該報被普魯士當局查封。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連同寫于1842年2月與之主題相似、內容相聯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等,馬克思撰寫了政論、按語或聲明等35篇,其中大多數在《萊茵報》發表,這些文本可被視為馬克思《萊茵報》時期政論群。正是在這時,他“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頁。由此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開始思想的第一次轉變。他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哲學的世界化與世界的哲學化處于同一進程,并在觀念層面確認了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政治哲學視域。
一、闡揚啟蒙理念與公共精神
馬克思這一時期政論群開始于對普魯士新書報檢查令的評論,這篇本來為《德國年鑒》撰寫的文章因書報檢查令的限制而發表于瑞士出版的《德國現代哲學和政論界軼文集》第一卷。面對體現浪漫主義精神的書報檢查令和檢查官的“脾氣”,馬克思指出:“你們贊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頁。這項限制新聞出版自由的法令使報刊缺乏公共精神,使一種主觀的、敏感的、不確定的情緒蔓延,“給哲學方面的書刊帶上新的枷鎖”,“賦予純粹的偶然性以空想的精神,并以普遍性的激情宣布了某種純粹個人的東西”,(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因而失去了客觀標準。此外,它將專橫和獨斷偽裝成客觀的邏輯,沉湎于無定形的意見中不負責任,所以應當廢除。(4)作為馬克思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此文得到盧格和《萊茵報》主編榮克的高度評價,榮克認為“文章寫得非常之好”,盧格將其視為“至今”關于出版自由的“文章中最優秀的作品”。(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頁。這篇捍衛言論自由的雄文力透紙背,“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只有洛克的《論寬容的信》和密爾的《論自由》可以與之媲美”。(6)參見[俄]尼·拉賓:《馬克思的青年時代》,南京大學外文系俄羅斯語言文學教研室翻譯組譯,三聯書店,1982年,第63、130頁。
隨后,在分六期發表在《萊茵報》的《關于新聞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級會議辯論情況的辯論》這篇長文中,馬克思進一步闡發了上述觀點。他以歷史觀察者的身份論述萊茵省議會“關于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進程,批判《國家報》“斷言現實的國家生活沒有政治精神,政治精神不存在于現實國家之中”。(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在這里,馬克思以具體的政治觀念考察新聞出版問題。由于反對新聞出版自由的論戰主體是等級,他從諸侯等級的一位辯論人談起,他回顧在實行嚴格書報檢查制度的1819—1830年間普魯士新聞出版界的“墮落”,指出“當時著作界中唯一還有充滿生機的精神在躍動的領域——哲學領域,已不再說德語”,因為這時德語已淪為“一種無法理解的神秘的話語”。(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當新書報檢查令頒布,這位諸侯等級的辯論人抹殺了書報檢查制度的精神屬性,表明等級制的邏輯在社會責任面前失語。面對這種邏輯,必須彰顯自由報刊的人民性,以之促進總體性的人民革命。
馬克思認為自由報刊體現了人民精神,反對新聞出版自由“駁斥的是人的自由”,問題的實質是新書報檢查令體現了特權而非社會普遍權利。省議會本應體現普遍意識和社會精神,騎士等級的辯論人卻體現了特權和特殊精神。“以近乎滑稽的嚴肅、近乎憂郁的尊嚴和幾乎是宗教的熱忱闡發了關于省等級會議的高度智慧以及它的中世紀的自由和獨立的假想”,而“真正的政治會議也只有在公眾精神的密切保護下才能昌盛”。(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這種特殊精神否定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維護人類永遠不成熟的論點,實則是一種停留于啟蒙時代之前的壟斷的批評。馬克思在這里倡導以法律形式存在的自由,因為“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在這些規范中自由獲得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理論的、不取決于個別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同時,面對城市等級的辯論人“天真”的意見,馬克思強調“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進而在現實領域強調普遍精神的價值,走出等級政治智慧的世俗租佃者們的幻覺,讓自由報刊為人民精神代言。
與此相應,還有一篇分五期發表在《萊茵報》的《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與關于新書報檢查令的評論都是圍繞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展開的。這個辯論圍繞的問題是,窮人撿拾枯枝是否違背林木盜竊法?馬克思著力強調這兩種行為本質上的差別,因而在法律上具有不同的意義。如果將撿拾枯枝的行為看作是犯罪,那么“人民看到的是懲罰,但是看不到罪行,正因為他們在沒有罪行的地方看到了懲罰”。(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枯枝不是林木所有者的財產,理應由撿拾枯枝的貧民所有。在馬克思看來,法律應當體現人民的心聲,而不能淪為純粹的動物假面具。他為窮人吁求普遍的習慣法,力圖滿足最底層的、一無所有的群眾的利益和愿望。現實的情形是,“不自由的世界要求不自由的法,因為這種動物的法是不自由的體現,而人類的法是自由的體現。封建制度就其最廣泛的意義來說,是精神的動物王國,是被分裂的人類世界”。(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馬克思認為窮人既不想與法的習慣相抵觸,而只是想讓合理的基本要求合法化,但這種基本要求與特權者的習慣相抵觸。
馬克思對法的差異進行深入比較,他認為貴族的習慣法與普通法律的形式相對立,與貧民的習慣法大相徑庭。撿拾枯枝是貧民的權利,他們在獲取自然界的布施,“在貧苦階級的這些習慣中存在著合乎本能的法的意識,這些習慣的根源是實際的和合法的,而習慣法的形式在這里更是合乎自然的”。(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馬克思強烈指責私人利益的空虛的靈魂,認為為其代言純屬詭辯,實則違背了公共精神。“盜竊林木者偷了林木所有者的林木,而林木所有者卻利用盜竊林木者來盜竊國家本身。”(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這實際上是將壞原則作為議會通過的法律的出發點,使林木所有者像夏洛克希望通過法律割去對方的一磅肉一樣。省議會將行政權、行政當局、被告、國家觀念等都降為私人利益的物質手段,“不僅打斷了法的手腳,而且還刺穿了它的心”;(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徹底地將不自由的形式賦予不自由的內容。這種維護特殊利益的行徑是“下流的唯物主義”,違背國家理性和一般精神,因而不值得公眾期待。
此外,馬克思還批判了當時一些報刊缺乏公共精神的蒙昧筆調。例如,在批評《科隆日報》的“‘政治性社論’主要是促使讀者厭惡政治的一種絕妙的手段”(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時,他回到“問題本身”,在分析問題的過程中得出答案:“德國哲學,愛好寧靜孤寂,追求體系的完滿,喜歡冷靜的自我審視;所有這些,一開始就使哲學同報紙那種反應敏捷、縱論時事、僅僅熱衷于新聞報道的性質形成鮮明對照”。(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報紙若要避免糟糕的、輕薄的形式,就不能停留于草率、咒罵和恐嚇,而要像哲學那樣求助于理智、許諾真理和恰當的安慰。要認真研究問題,還要思考“應該怎樣進行這種研究”,進而“從理性和經驗出發”,形成“自由理性的行為”, 以“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觀點”,“根據整體觀念來構想國家”,“實現法律的、倫理的、政治的自由”,服從“人類理性的自然規律”。(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
二、法哲學的最初闡述與《萊茵報》的思想立場
擔任《萊茵報》編輯后,馬克思首先在《共產主義和奧格斯堡<總匯報>》中回應奧格斯堡《總匯報》指責《萊茵報》同情共產主義,首次公開表明自己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他的文風幽默而辛辣,將《總匯報》的指責描述為“奧格斯堡女人的這種不像樣子的幻想”,同時指出“共產主義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法國和英國當前的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31、143、149、162、176、187、245頁。馬克思意識到這時德國化的共產主義已經淪為非現實的理論,他從當時德國社會實際出發,提醒《總匯報》要以自己的智慧充分研究問題,不應使評論陷入空談。應當研究時代思想的現實性,將貧民的實際利益作為問題的出發點,“絕不能根據膚淺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長期持續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253、277、287-288、206、219、222-228、292、295頁。同時,應當意識到理論的力量,要以符合時代精神的理智、見解和良心影響現實,使之發揮深刻持久的作用。相關思想在《<萊茵報>編輯部就有關共產主義的論證所作的說明》一文中得到了補充。
1842年10月15日,馬克思就任《萊茵報》主編,當天普魯士內務與警務部得到的報告中提到:“《萊茵報》的傾向特別惡劣。它帶著年輕人所特有的那種傲慢態度攻擊國家和教會的現存制度,卻提不出可以代替它的任何更好的辦法。”(22)[法]奧古斯特·科爾紐:《馬克思恩格斯傳》,第1卷,劉丕坤等譯,三聯書店,1963年,第400頁。可以說,馬克思在擔任《萊茵報》編輯和主編的過程中,時刻面臨普魯士當局查封報紙的危機,并為此不斷申訴和駁斥。“馬克思作為新聞工作者,主要關心的是政治問題。”(23)Allan Megill, Karl Marx,The Burden of Reas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p.83.他在這一時期的思想戰斗是多方位的,既要抵制一些報刊編者或作者的中傷,也要反駁當時輿論界的各種錯誤言論,同時要認真回應書報檢查機關的各種指責,進而投入到對普魯士政治現實的實際批判之中。正如這一時期他寫給盧格的信中所說:“不要以為我們在萊茵這里是生活在一個政治樂園中。要把《萊茵報》這樣一個報紙辦下去,需要不屈不撓的堅毅精神。”(24)[法]奧古斯特·科爾紐:《馬克思恩格斯傳》,第1卷,劉丕坤等譯,三聯書店,1963年,第240頁。
這一年10月底—11月初,馬克思針對格魯培在《布魯諾·鮑威爾和大學的教學自由》中攻擊鮑威爾的《符類福音書作者的福音史批判》一書和為波恩大學解聘鮑威爾辯護的觀點,撰寫了《再談談奧·弗·格魯培博士的小冊子<布魯諾·鮑威爾和大學的教學自由>1842年柏林版》一文,諷刺這個小冊子不過是“一部門外漢的喜劇”,在“一知半解、淺薄無知”的筆觸中透露著“他的叵測的意圖、昧心的歪曲和卑鄙的陰險手段”。(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1、306、313-314頁。在這篇發表在《德國科學和藝術年鑒》上的文章中,馬克思指責格魯培曾是一個天真的無賴,后來失去了天真,成為一個沒有任何精神和優點的人。盡管批判波恩大學解聘鮑威爾的行徑,但馬克思這時與以鮑威爾為首的轉向“自由人團體”的青年黑格爾派部分成員漸行漸遠。因為“自由人團體”越來越陷入抽象的自我意識,沉湎于缺乏現實性的批判世界,與馬克思向往的將理論批判與現實政治聯系起來的思路分道揚鑣,這引來“自由人團體”對《萊茵報》的批判,導致書報檢查機關對《萊茵報》的檢查更加嚴格,馬克思認為他們不研究具體的政變社會的現實條件,只是將批判本身視為進步的標志,陷于草率的高談闊論之中,他為此撰文嚴厲批判了這些昔日的同仁,實際地選擇與他們決裂。
在以“《萊茵報》編輯部”名義發表的《<萊茵報>編輯部為<評《漢諾威自由主義反對派的失誤》>一文所加的按語》中,馬克思分析了“自由主義反對派”這一用語以及漢諾威反對派何以被稱為自由主義反對派,闡述了1837—1838年漢諾威憲法沖突中資產階級反對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觀念和行為,指出“漢諾威的真正的自由主義今后的任務,既不是維護1833年的國家基本法,也不是退回到1819年的法律。它應該爭取實現一種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識相適應的嶄新的國家形式。”(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1、306、313-314頁。從而揭示了合理的人民意識與嶄新的國家形式結合的必要性,為自由的追求提供了符合公共精神的路徑。
針對當時圍繞普魯士政府打算在萊茵省城鄉實行地方管理機構改革進行的激烈辯論,馬克思撰寫了《區鄉制度改革和<科隆日報>》三篇通訊,反對實施普魯士的等級原則,維護區鄉權利平等,揭露了《科隆日報》對《萊茵報》的誹謗。他認為《科隆日報》的猜疑和告密做法“再一次使我們相信,智力的貧乏最終企圖靠性格的軟弱,靠道德敗壞的無聊的魯莽行徑來維持自己。”比較而言,《萊茵報》強調城市和農村權利平等,《科隆日報》“做出某種空泛的、不說明任何理由的對城市和農村權利平等的承認”。馬克思指出當時萊茵省城鄉沒有分開的實際情形,認為“法律只能是現實在觀念上的有意識的反映,只能是實際生命力在理論上的自我獨立的表現”,(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1、306、313-314頁。因而不應當頒布不符合實際的法令。該文的主要觀點在隨后發表的《<科隆日報>的一個通訊員和<萊茵報>》一文中得到進一步強調。
1842年2月,歷史法學派的代表人物薩維尼被威廉四世任命為法律修訂大臣,著手起草新離婚法草案。該草案的準備和討論在當時均屬不允許公開發表的秘密,但《萊茵報》在當年10月20日發表了這個草案并展開廣泛討論,普魯士政府要求編輯部提供草案投寄人的姓名被拒絕。馬克思發表了《論離婚法草案》一文,批判薩維尼和萊茵法學家的觀點,從五個方面提出對新草案的反對意見。在他看來,“立法者應該把自己看作一個自然科學家。他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識的實在法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律表現出來。”(28)同時,他強調“只有當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的時候,才會有確實的把握,正確而毫無成見地確定某種倫理關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質的那些條件,做到既符合科學所達到的水平,又符合社會上已形成的觀點。”(29)此外,他還以“《萊茵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為《論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語,明確指出萊茵法學的根本缺陷在于二重化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由于用膚淺的方式把信仰同法的意識分開,不是解決最麻煩的沖突,而是把它劈成兩半;它把法的世界同精神的世界,從而把法同精神割裂開來,這樣也就把法學同哲學割裂開來了。”(30)他還明確批判邦法的缺陷在于建立在理智的抽象上,“這種理智的抽象本身是無內容的,它把自然的、法的和合乎倫理的內容當作外在的、沒有內在規律的質料加以吸收,它試圖按照外部的目的來改造、安排、調節這種沒有精神、沒有規律的質料”,(31)從而彰顯了批判邦法的本質。
在這一時期,馬克思認識到社會利益決定不同的政治立場,他對等級差別問題進行了深刻闡述,認為問題的關鍵不是等級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而在于其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延伸到國家生活的最高領域。他對普魯士封建等級制度做出尖銳的批評,指出“智力不僅不是代表制的特殊要素,而且根本不是一個要素;智力是一個不能參加任何由各種要素組成的機構的原則,它只能從自身進行劃分。”(32)他將問題聚焦在“到底是特殊利益應當代表政治智力,還是政治智力應當代表特殊利益”,(33)強調應當把代表權理解為“人民自身的代表權,理解為一種國務活動,這種國務活動不是人民唯一的、獨特的國務活動,它跟人民的國家生活的其他表現不同的只是它的內容的普遍性”,應當將其“看作最高力量的一種自信的生命活動”,(34)倡導人們獲得在國家事務中的發言權。
當得知《萊比錫總匯報》在普魯士遭查禁,馬克思為《萊茵報》寫了社論《<萊比錫總匯報>在普魯士邦境內的查禁》,指出報紙對普魯士的批評是政府采取全面制裁的根本原因。隨后他寫了一組論及相關主題的文章,包括《<萊比錫總匯報>的查禁和<科隆日報>》《好報刊和壞報刊》《答一家“中庸”報紙的攻擊》《答“鄰”報的告密》《駁奧格斯堡<總匯報>編后記》《<科隆日報>的告密和<萊茵—摩澤爾日報>的論爭》《萊茵—摩澤爾日報》。他充滿激情地認為,“凡是報刊年輕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輕,而剛剛覺醒的人民精神公開表達出來的日常政治思想,同那種已經在政治斗爭中成長壯大并充滿自信的人民精神所表達的政治思想相比,就顯得不夠老成、不夠確定、不夠周密。……人民看到自己這種本質在它的報刊的本質中反映出來……成為現代荊棘叢中一棵道德精神的玫瑰。”(35)在馬克思看來,對人民報刊的指摘就是對人民政治精神的指摘,捍衛人民報刊的權利,就是捍衛人民的權利。為此,必須尊重報刊的發展規律。“要使報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須不從外部為它規定任何使命,必須承認它具有連植物也具有的那種通常為人們所承認的東西,即承認它具有自己的內在規律,這些規律是它所不應該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擺脫的。”(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7、349、316、316-317、343、343、344、352-353、397頁。這時馬克思認為報刊應當啟發人們的頭腦,其使命在于促進歷史的發展。
為《萊茵報》駐摩澤爾記者科布倫茨揭露摩澤爾地區農民貧困狀況的兩篇文章辯護,馬克思寫了《摩澤爾記者的辯護》及其續篇《摩澤爾記者的辯護。C 摩澤爾河沿岸地區的種種主要弊端》,續篇因被書報檢查機關刪去而在當時未能發表。《摩澤爾記者的辯護》由五個部分組成,馬克思在這里批判普魯士的官僚制度和管理弊端,認為在普魯士官員看來,“只有當局的活動范圍才是國家,而處于當局的活動范圍以外的世界則是國家所支配的對象,它絲毫也不具備國家的思想和判斷能力”。(37)摩澤爾河沿岸的貧困狀況在馬克思看來正是普魯士管理工作的反映,問題的本質是政治性的。“這種本質的關系就是既存在于管理機體自身內部、又存在于管理機體同被管理機體的聯系中的官僚關系。”(38)相比而言,人民報刊是社會輿論的產物,是“具有公民頭腦和市民胸懷的補充因素”,(39)書報檢查機關同人民報刊的沖突只是表明它是多余的存在,是與人民政治精神相背離的。
為駁斥普魯士三位負責書報檢查的大臣頒布關于查封《萊茵報》的指令,馬克思寫了《評部頒指令的指控》,抗議普魯士政府的無理譴責。因為這種譴責沒有“證據”,而只有強加的“明顯企圖”。《萊茵報》的觀點是,不把君主限制在個人范圍內,而將其視為國家的軀體,“各種機構是他賴以生存和活動的器官,而法律是他用來觀察事物的眼睛”。(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2、377、378、426、203頁。馬克思強調,《萊茵報》遵循普遍原則和公共精神,關心合乎倫理和理性的政治共同體,它在德國是態度最認真和最了解實情的報紙,至于指摘它與其他報刊進行論戰,則根本不能成為查封的理由,這只不過是《萊茵報》為了免受污蔑和攻擊而進行的自衛。遺憾的是,這樣的評論并沒能改變《萊茵報》遭到查封的危險,馬克思為此采取的最后努力是,聲明“因現行書報檢查制度的關系”,退出《萊茵報》編輯部。不到半個月后,《萊茵報》被當局查封。
三、重塑時代的觀念與開啟哲學的世界化視域
可以說,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對黑格爾的王權、行政權和立法權思想的批判均進行了前提性研究。“在這些文章中,馬克思已經初步認識了社會的階級結構。”(41)Allan Megill, Karl Marx,The Burden of Reas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p.6.這時他的理論批判更明顯地表明,他并非青年黑格爾派的不疑因循者,而是新理論的開創者。(42)[美]湯姆·洛克莫爾、臧峰宇:《啟蒙的路徑與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觀念資源》,《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6期。
《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力圖重塑時代的觀念。哲學作為時代精神(zeitgeist),與黑格爾所謂“哲學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有關,在馬克思看來,思想中的時代是現實中的時代的反映,體現為一種生成性的過程。“時代”是一種富于現實性的時間性規定,這種規定使哲學參與乃至塑造現實的能力得以凸顯。哲學不只是思想中的時代,還是引領時代的思想,因而,它主要是一種可能性的敞開。黑格爾意識到哲學與時代的內在關聯,認為哲學屬于時代并受限于時代,思想不應當也不可能跳出時代。同時,黑格爾強調哲學對實體性內容的追尋,并避免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興趣中,避免意見的空疏淺薄,正是在具有現實性的反映時代主題的哲學中,我們可以煥發青春化和強有力的內容,構成具有內在質感的上層建筑。馬克思強調哲學的現實性,以“高盧的雄雞”彰顯哲學引領時代的英姿。他在物質生活的創造中建構精神生活形態,提出了一種超越既往的政治哲學主張。
馬克思認為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對時代的把握必須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他在《集權問題》一文中指出:“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4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2、377、378、426、203頁。時代的命運所系不是答案,而是現實的問題,關鍵在于敏銳地提出問題并找到答案。“哲學家并不像蘑菇那樣是從地里冒出來的,他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都匯集在哲學思想里。”(44)對哲學問題及其實踐內涵的研究必須做出當代的自我闡明,我們只能在時代條件下認識現實,現實的意識以時代發展為基礎。后來馬克思的時代觀與思維方式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時代精神作為哲學的本質特征之一并未走出他的理念。如同旅行中的導游,哲學在時代之中,同時在時代之前。
理解時代,必然需要深刻地認識歷史,認識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問題。馬克思在這一時期批判了歷史學派的“輕佻”,質疑該學派將研究起源極端化的做法,這種做法很可能在研究中“編造虛構”。在《歷史法學派的哲學宣言》中,馬克思主要關注該學派的創始人胡果,批評他“是一個否認事物的必然本質的懷疑主義者”,這個懷疑主義者曲解了其理論出發點康德哲學,否認理性的現實性,他“力圖證明,實證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45)該學派將同理性相矛盾作為原則的方法,其論據是非批判的,“只是為了不把合乎理性的事物看作實證的事物。”(46)馬克思摘錄并解讀了胡果的著作《作為實在法、特別是私法的哲學的自然法教科書》,對導言和書中各篇幾乎逐一做了批駁,揭穿其中“那些非歷史的臆想、模糊的空想和故意的虛構”,否定“舊制度的啟蒙思想家的那種齷齪而陳舊的怪想”。(47)為此必須以現代理性確認一種新啟蒙觀念,強調合乎理性的實證研究。
從哲學角度把握時代,關鍵在于關注現實問題,在于轉向塵世的批判。塵世中的現實既不是現象,也不是現存,而是一種合乎理性的過程,以常識為路標。馬克思對德國在當時歐洲的時代錯位的批判,正是基于對現實和常識的把握,鐫刻與之同時代的現實和常識印記的哲學才是時代的哲學。哲學對常識的超越應當建立在尊重常識的基礎上,為此應豐富經驗理性,達到對事實有生命力的自然理解。因而,不僅要審視哲學發展的理論邏輯,也要確認哲學發展的實踐邏輯。哲學與時代的關系由此合理地表現為,在思想竭力體現現實的同時,使現實更好地趨向思想。馬克思強調哲學的時代性和世界性,認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因此,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時代:那時哲學不僅在內部通過自己的內容,而且在外部通過自己的表現,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那時,哲學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體系相對的特定體系,而變成面對世界的一般哲學,變成當代世界的哲學。各種外部表現證明,哲學正獲得這樣的意義,哲學正變成文化的活的靈魂,哲學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學化,——這樣的外部表現在一切時代里曾經是相同的。”(4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220、230、232、238、220頁。在這樣的時代視域中,哲學沖破了令人費解的體系,“以世界公民的姿態出現在世界上”,因而成為一種具有現代公共精神的世界的哲學,一種以人民精神為底色的面向未來的哲學。
綜上所述,《萊茵報》時期的政論群是青年馬克思面向現實問題展開的重要著述,他在報紙編輯的生涯中從事哲學實踐,以筆為武器參與改變現實的實際工作,力圖培育一種普遍的公共精神,形成一種高揚啟蒙理念的自由的倫理國家觀,創造一種從根本上否定官僚制度的理想社會。不僅反映了“馬克思已開始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49)《列寧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9頁。而且反映了青年馬克思政治哲學理路的轉換。馬克思對它們頗為珍視,后來于1851年再次出版(50)Richard N.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4,p.34.這些文章。他在這一時期對利己的、原子式的個人的批判,對一種基于社會共同性的積極自由的倡導,對國家與法的關系問題的研究對其后來形成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哲學做了思想上的準備,鐫刻了重要的思想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