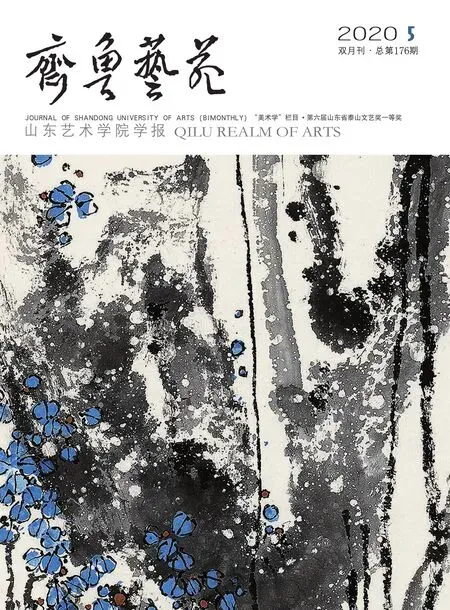《哪吒之魔童降世》:游戲化敘事、重構式人物與想象力美學
張明浩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北京 100871)
回顧與梳理2019年上映的中國電影作品,可以發現,《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簡稱《魔童降世》)可謂名利雙收,成為了該年度的最大贏家。一方面,它是“電影工業美學”的現實佐證:“影片在美學層面進行中國藝術精神的現代影像轉化,呈現出典雅又不失‘靈氣’的美學圖景;‘接地氣’的現實感和話題性及民間亞文化的開掘,又傳達了喜聞樂見的世俗之美,共鳴了普泛性的世俗人倫之情……影片在工業層面努力進行‘工業化’、規范化、系統性、協作性的制作和運作,體現了電影工業觀念……影片所呈現的‘工業化’特點與所表露的‘工業缺陷’,都為中國動畫電影未來的工業化發展提供了有益的鏡鑒,懸擬了高遠的未來指向”[1](P25-30)。
另一方面,基于中國傳統神話故事進行文本重構與現代性改編的它,在劇作結構、敘事方式、人物塑造等方面均表現突出,為國產動畫電影的未來發展提供了可借鑒藍本:《魔童降世》基于受眾以往對《封神演義》《哪吒鬧海》等作品中故事建構、家庭組合的互文記憶,進行了大刀闊斧且頗具現實感、話題性的改編與文本重構。影片不同于以往類似作品中重點講述哪吒與家庭的悲歡離合及其矚目的生平事跡,而是把戲劇沖突集中為“反抗天命”與“自我救贖”等方面,講述了因身份而被自幼歧視的哪吒,在父母、師友的幫助下突破自己、打破狹隘、回歸社會、成為英雄的故事。毋庸諱言,這樣的改編,無論在藝術方面,還是在商業方面,亦或是在未來中國動畫電影的取材、制作等方面,都頗具借鑒意義與價值,值得我們進行深入探析與研究。
一、劇作策略:互文敘事基礎上的文本重構
德國學者卡爾-海因茨·施蒂爾勒(Karl-Heinz Stierle)曾言“任何文本都不始于零”[2](P70-80),“因此,所謂互文性是指,每個文本都處于已經存在的其他文本中,并且始終與這些文本有關系”[3](P258-273)。哪吒的故事可謂流傳千古,當下受眾所熟知的關于哪吒的故事內核、人物形象,多來源于明代小說《封神演義》。中國影視行業中有諸多作品對哪吒這一形象及其故事進行過書寫,如《梅山收七怪》(1973)等;在動畫界,則是1979年的動畫電影《哪吒鬧海》最為經典,該片“手持火尖槍、腳踏風火輪”的哪吒“龍宮復仇”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正是因為關于“哪吒”的文本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才為《魔童降世》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記憶互文根基:影片取材中國傳統神話故事,但在文本、人物、敘事、主題、美學等諸多方面,與受眾以往的文化記憶體形成了強烈反差,進而打破了受眾的定向期待視野,增加了話題性與新鮮感。
(一)“傳承”與“重構”:標準劇作結構下的游戲化敘事
美國編劇布萊克·斯奈德在《救貓咪——電影編劇寶典》中,曾在剖析電影劇本后,劃分出15個關鍵節拍[4](P57),用以指導類型電影劇作,即開場畫面、呈現主題、鋪墊/建構、推動/轉折、爭執/掙扎、第二幕銜接點、B故事、游戲時間、中間點、敵人逼近、一無所有、靈魂的黑暗、第三幕銜接點、結局、終場畫面,這一電影劇作結構范本,可以在諸多好萊塢主流商業類型電影中得以印證。《魔童降世》雖非好萊塢電影,但在參照布萊克·斯奈德節拍表后,我們不難發現,該片在劇作結構上,對好萊塢商業類型電影的模式,進行了借鑒與創新。
以該片“開場畫面”為例,其內容為太乙真人與申公豹兩人在元始天尊的幫助下,收服混元珠,并介紹其來歷,在此之中,雋永的畫面呈現、高飽和的色彩,確定了影片古典美學的氣韻風格,并起到了介紹故事前史的作用。再以“B故事”為例,在影片第30分鐘時,影片開啟了另一個故事,山河社稷圖出現,哪吒進入山河社稷圖,開始與師傅修身養性、學技藝,而這便是促使哪吒轉折的節點,在這里哪吒不同于以往的“小魔頭”,而是逐漸開始把自己真實的一面展現出來。又如“靈魂的黑暗”這一節點,在這里哪吒孩童的身份被喚醒后,因為愧疚、不甘而離開大家,前往森林,一人獨處,這與節拍點作用不謀而合:即主人公處于深淵、找不到拯救自身及周圍人的辦法、看不到希望……《魔童降世》的劇作結構頗具好萊塢商業類型劇作特質,從“開場畫面”到“終場畫面”無不緊扣受眾心弦,并一步一步促使其進入影片,與主人公共同經歷“啟、承、轉、合”。與此同時,在敘事方面,影片有著經典三幕劇、英雄之旅式的敘事結構,也融合了西方“戲劇體”電影與東方“敘事體”電影的特征(1)“戲劇體”電影是指“一切進展都奔赴沖突的爆發”,而“敘事體”電影則是指“形成單元間均衡起伏的節奏”,《魔童降世》中在“生日宴”沖突爆發的設置,具有“戲劇體”電影的特征,而三幕中分別的起承轉合,又形成了單元間的均衡節奏,具有“敘事體”電影特質。參見楊健. 拉片子:電影電視編劇講義[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44.。無疑,正是影片對標準化劇作結構的借鑒、對經典化敘事模式的傳承,才保證了受眾的情感調度,加固了影片的地基、促進了影片的傳播。
值得強調的是,影片在傳承的同時,根據現代“網生代”受眾群體的審美喜好(如游戲、夢幻等)進行了“游戲化敘事”[5](P31-34)的嘗試,此敘事方式亦為“影游融合”“既電影、亦游戲”式跨媒介敘事(2)陳旭光教授曾提出“跨媒介敘事”的概念,此種敘事方式形成了“既電影、亦游戲”的敘事美學。參見陳旭光,李黎明. 從《頭號玩家》看影游深度融合的電影實踐及其審美趨勢[J]. 中國文藝評論,2018,(7):101-109.的重要方式。此種“影游融合”敘事模式,表現為人物設計、場景設計的游戲奇觀化[6](P31-34)與“游戲線性故事”[7](P155)設置,它不但可以滿足受眾視覺奇觀性想象的需求,而且可以使受眾體驗到“過關斬將”的游戲快感。如《白蛇:緣起》便“具有游戲化的場景設置”[8](P116-120),而《魔童降世》更是在場景制作、故事講述、人物塑造等方面,進行了“游戲化敘事”的嘗試。
首先,從影片人物來看,人物(角色)作為影片敘事過程中的關鍵,具有連貫敘事、代入受眾等方面的作用,而動畫電影的人物天然與游戲中角色有著密切聯系:同作為技術生成的三維虛擬體,并且在形態、動作等方面有著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影片在人物外在造型、人物動作、人物服裝變化、人物技能等方面體現出了“影游融合”的特點,而這些小細節又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影片總體的游戲化基調,成為影片“游戲化敘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
一是影片中形色各異的人物造型,給受眾一種玩家選擇角色的快感。影片開頭便是太乙真人與申公豹“打怪升級”的橋段,混元珠在此似如游戲中“終極大Boss”,而太乙真人、申公豹、元始天尊則如可以供受眾選擇進行此次戰爭的角色。同樣,影片中的哪吒、敖丙、李靖、李夫人等人,亦表現出不同的外在形態與核心技能,供玩家(受眾)選擇,如果受眾選擇李夫人,那么要完成疏導孩子、抵御外來入侵的任務;如果選擇李靖,則要完成保護哪吒、維護陳塘關的重任;如果選擇敖丙,則要承擔攻打陳塘關、幫龍族翻身的任務……無論受眾代入(選擇)哪個人物,都可以在該片(游戲)中體會到過關斬將、完成任務、贏取獎勵的快感,這無疑拓展了受眾感官體驗的范圍,使之體會到“選角”的游戲感。
二是影片中人物的動作呈現,具有游戲的實踐體驗感。哪吒從家庭到街上,從街上到海邊的游走過程,極似游戲玩家在“游戲中的奔跑”“選擇地圖”“走出營地”“走向戰地”的過程。哪吒大幅度的動作,也極似游戲人物“發技能、出大招”的指示。哪吒的打斗過程,更與游戲中的打斗升級場面極為相似,如哪吒、敖丙二人最后的比拼,二人各發技能,從內到外,從手、腳到法器、技能都與“拳皇”等拳擊、格斗類游戲人物的動作不謀而合……從人物行走方式、打斗程式等諸多動作中,受眾都似乎會不自覺產生記憶互文、游戲文本互文,想到以往自己所玩過、所見過的游戲,并在觀影過程中再次體驗到游戲的刺激感。
三是影片中人物技能隨服飾變化的設置,具有游戲代入感。片中哪吒從兒童時期變身到青年時期的服飾、外形、技能等都發生了顯著變化。敖丙在“初遇哪吒”“抵抗哪吒”“成為反派”的各個時期,外在服裝也有明顯不同。李夫人居家與上戰場的服裝也有較大差異……影片通過人物服裝變化,來進一步代表人物性格、技能的變化,而此種邏輯與游戲中的“換皮膚”“換裝備”等互動性設置極其相似。當敖丙穿上“裝備”“萬龍麟鎧甲”時,便可以抵御強攻擊;而哪吒在換上“混天綾”“乾坤圈”的裝備后,便可以增加技能;太乙真人在乾坤圈“法寶”(武器)的幫助下,可以壓制哪吒……諸如此類通過更換“皮膚”來更改技能,通過安裝裝備來提升技能的設置,都較為符合游戲玩家的互動性、體驗性心理,極具游戲感。
其次,在場景制作與呈現方面,和傳統線性敘事電影不同,游戲化敘事的電影故事空間,更表現為一種“游戲發生的空間”[9](P31-34),在這一空間內的工具、場景等,都為觸發游戲環節打下基礎。導演建構的山河社稷圖、陳塘關、地下龍宮等空間,為玩家(主人公)提供了一種可游戲化空間,在山河社稷圖中,哪吒可以通過“筆”來改變整體內容,空間隨著玩家(哪吒)的意念而變化,極具游戲化與想象力;在陳塘關內,玩家要經過各種關卡(哪吒要面對不同村民的歧視等)才能獲得重生。同樣,導演也在李府中設置了諸多類似的游戲類關卡,如哪吒想要出門,便必須要騙過守門的兩個仙童,他故意驚嚇村民及出逃李府時所選擇的面具、石頭等工具,以及影片中的樹林、瀑布、沙灘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玩家(哪吒)可以用何種資源闖過關卡、觸發下一步劇情,贏得勝利。此種游戲化的空間設置、工具設置,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敘事的前進與轉折,而受眾也于此代入到哪吒這一游戲玩家角色之中,跟隨其一起探險、成長、闖關,而其也令受眾產生如游戲操作的體驗感與互動感。
最后,在故事講述方面,影片呈現出一種游戲線性“英雄闖關式”的關卡樣式。影片以“魔丸轉世→外逃李府→報復村民→被關畫作→大戰水怪→被人誤解→不出家門→大鬧宴會→拯救蒼生→承受天劫”為故事總線,講述英雄自我成長、自我認同的過程,亦具有“闖關”色彩。一方面,哪吒從“被偏見”到“被認可”的故事線索,本身就帶有一定程度上的突破性與闖關感。另一方面,影片中哪吒收服水怪、結交朋友等支線,也具有游戲質感。在收服水怪的過程中,哪吒從村頭到村尾,不斷用技能攻打水怪,而水怪則用毒泡泡回擊哪吒,在這一支線敘事體系內,哪吒與水怪形成游戲中的二元對立關系,并最終以玩家(哪吒)勝利告終。在哪吒、敖丙相識過程中,二人在隔離人群的沙灘(對應游戲中特定的、與世隔絕的結拜場景)相知相識,并最終結交好友,與游戲中團隊生成的方式相似。此外,山河社稷圖中的敘事亦具游戲風格,哪吒在畫作中修身養性提高技藝,并最終接受模擬戰爭考核的設置,與游戲中玩家“回家修煉”的程式相似,也與單機游戲中玩家通過“人機模式”提升自己技能的設置不謀而合。縱觀《魔童降世》的故事構設,主人公(玩家)不斷需求認同的闖關過程與最終攻打終極大Boss、對抗天劫的環節,本身便帶有游戲風格。與之同時,影片中的支線敘事,又在一定意義擴展了影片游戲世界的維度,使其實現了“影游聯動”的效果。
綜上所述,我們或許可以得出結論:影片標準化的劇作結構與游戲化的敘事創新,為其打下了堅實基礎,它在傳承以往哪吒故事的同時,又進行了文本重構與劇作創新,不但吸取了西方劇作模式的經驗,而且加入了現代青少年受眾所喜聞樂見的游戲元素,在傳統與現代之間走出了一條康莊大道。
(二)“解構”與“顛覆”:對經典神話人物譜系的現代化、立體式重塑
在全媒體時代,人物性格是否鮮明,人物造型是否新穎獨到,都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動畫電影的傳播與發展。[10](P58-64)毋庸諱言,《魔童降世》的成功,離不開其新穎獨到的人物塑造。該片在保留以往《哪吒鬧海》主要人物設置的同時,對其進行了“顛覆式”塑造,此種對受眾互文記憶中人物的大膽解構與顛覆性重構,無疑在打破受眾定向期待視野的同時,加強了影片的傳播力度。與《哪吒鬧海》的人物形象、人物行動動機相比,《魔童降世》的形象設計更具現代化特質,多為立體、生動的圓形人物(3)福斯特曾在《小說面面觀》中,將人物類型分為“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扁平人物”又稱性格人物或漫畫人物,即自始至終人物性質單一而純粹、平面化,甚至可以用一個句子概括其特點。“圓形人物”則是立體的、復雜多面的——“一個圓形人物必能在令人信服的方式下給人以新奇之感……如果他無法給人新奇感,他就是扁平人物;如果他無法令人信服,他只是偽裝的圓形人物……圓形人物絕不刻板枯燥,他在字里行間流露出活潑的生命”。參見(英)E·M·佛斯特. 小說面面觀[M]. 蘇炳文譯. 廣州:花城出版社,1981:63-64.,行動動機也都有現實溯源可尋,受眾不僅可以對正面人物產生認同,而且能夠了解反面人物背后的心酸苦辣。
與此同時,影片在塑造反面人物時,也做了游戲化、現代性的處理。如說話口吃、做事糊涂的申公豹,因為自己“妖怪”身份被元始天尊歧視,所以才想報復天尊、自己封神,但是他每次在設計計謀時都會“出糗”,令受眾哭笑不得,而其在最后時期也未曾想傷害過陳塘關百姓,并且還為避免戰爭屢次提醒敖丙不要前去“多管閑事”(正是因為敖丙在哪吒成魔時拯救了百姓,才被百姓鄙視,最后釀成大錯)。故此,我們不難看出,申公豹也有一顆愛民之心,他也只是一個被歧視而走向報復之路的“天涯淪落人”。又如影片中的黑暗大Boss——龍王,雖極其陰險、手段毒辣,但也曾經是幫仙家打下江山的重要成員,卻因人們猜疑而被封鎖數年。于此而言,孰好孰壞似乎并不是導演的設計一錘定音,而是想讓受眾于主人公現況中細品。再拿敖丙來說,導演給這一“反派”一幅驚世容顏與溫柔之心,但也卻因人民的鄙視、偏見而走向末路,但最后與哪吒同仇敵愾、共迎天雷的選擇,又表現出他的大愛、善良之心。亦如李靖這一人物形象,雖然愛民、護民、愛子、愛妻,但也有著偏見、狹隘之心,當他看到拯救自己的是龍族后,立刻反擊并讓敖丙真實身份暴露于眾,此時,他把敖丙從善良的英雄一下拉到了邪惡的罪人,這無疑是壓垮敖丙的“最后一根稻草”,進而直接導致了敖丙的殺戮……如上,我們似乎可以發現,導演并沒有給人物或好或壞的固定形態,而是以“事出有因”的出發點塑造人物,讓受眾在每個人物經歷中去體會角色的內在,這種塑造方式與價值觀念立場,無疑是對《哪吒鬧海》的一次突破與顛覆。
此外,《魔童降世》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有其獨到之處。以哪吒這一角色的塑造為例,影片保留了《哪吒鬧海》原有的身高比例與出生契機等引發受眾產生記憶互文的關鍵點,但對哪吒的總體命運、外在造型等方面進行了大膽地現代性重塑。一方面,“尋求認同”代表“網生代”受眾想要融入社會的內心所想。另一方面,“乖張造型”與“反叛性格”也一定程度上意在彰顯當下青少年與眾不同的個性。此外,“煙熏妝”“大眼睛”等外在造型也頗具現代玩偶造型、游戲角色造型風格。此外,《魔童降世》中的敖丙、太乙真人等人也都在性格、造型等方面一反以往、顛覆受眾審美,此種基于受眾互文記憶的大膽創新,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影片的話題性與吸引力、增強影片的傳播力、保證作品的受眾數量。
綜上,通過文本對比、劇作解讀等方法,對影片的劇作結構、敘事方式、人物塑造等方面進行分析梳理后,我們或許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魔童降世》是基于受眾互文記憶的一次充滿想象力的文本重構,一方面,影片的成功與精準的劇作結構密不可分,合理的劇作節拍拉動受眾情愫,進而帶動了影片口碑;另一方面,影片游戲化的敘事方式充滿想象力,為影片錦上添花,同時也代表了其對“想象力消費”(4)參見陳旭光. 關于中國電影想象力缺失問題的思考[J].當代電影,2012,(11):98-101. 陳旭光,陸川,張頤武,尹鴻. 想象力的挑戰與中國奇幻類電影的探索[J].創作與評論,2016,(4):123-128. 陳旭光. 類型拓展、“工業美學”分層與“想象力消費”的廣闊空間——論《流浪地球》的“電影工業美學”兼與《瘋狂外星人》比較[J].民族藝術研究,2019,(3):113-122. 陳旭光. 中國電影呼喚“想象力消費”時代[N].南方日報,2019-5-5(7). 陳旭光. 論互聯網時代電影的“想象力消費”[J].當代電影,2020,(1):126-132. 陳旭光,李雨諫. 論“影游融合”的想象力新美學與“想象力消費”[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37-47.陳旭光,張明浩.論電影“想象力消費”的意義、功能及其實現[J].現代傳播,2020,(5):93-98.的實踐,頗具游戲感的人物塑造、空間設置與故事講述,使受眾產生帶有游戲感覺的互動感與體驗感;最后,影片對以往受眾互文記憶中人物形象的大膽顛覆與現代化創新也極具想象力,增加了影片的話題感與現實性,進而保證了影片的傳播效果。
二、想象力美學:視覺奇觀的呈現、超現實情節的設置與溫情世界的營造
歷經5年、60多家制作團隊、1600多位制作人員、20多家特效公司團隊制作……種種特質下的《魔童降世》具有一定的工業化屬性,但也表現出了小作坊式生產的弊端,如協作不完善、工業化制作流程不規范等問題[11](P25-30)。同時,作為魔幻類電影的《魔童降世》,也是“想象力消費”(5)在互聯網時代,“所謂的想象力消費,就是指受眾(包括讀者、觀眾、用戶、玩家)對于充滿想象力的藝術作品的審美欣賞和文化消費的巨大需求。顯然,這種消費不同于人們對現實主義作品的消費需求,我們也不能以類似于‘認識社會’這樣的相當于‘電影是窗戶’的功能認知來衡量此類作品。在互聯網時代,狹義的想象力消費則主要指青少年受眾對于超現實、后假定美學類、玄幻、科幻、魔幻類作品的消費能力和消費需求”。互聯網新媒介時代下,“想象力消費”類電影具有四種形態:其一是具有超現實、“后假定性”美學和寓言性特征的電影;其二是玄幻、魔幻類電影;其三是科幻類電影;其四是影游融合類電影。參見陳旭光. 論互聯網時代電影的“想象力消費”[J].當代電影,2020,(1):126-132.類電影的力作,我們似乎可以從中窺見并再次論證魔幻類電影“想象力消費”的具體策略:一種是滿足受眾外在奇觀化審美需求的想象力美學呈現與具有“超現實”“無中生有”等想象力特質的情節、形象設置;一種是滿足受眾內在心理化需求的“情感共鳴式”想象表達。(6)參見陳旭光,張明浩. 論電影“想象力消費”的意義、功能及其實現[J].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5):93-98.
(一)想象力加持下的奇觀異境呈現: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現代影像轉化
《魔童降世》在立足傳統、發揮想象力的基礎上,對中國傳統藝術精神(如意境美學、寫意精神、樂舞精神等)進行了現代影像轉化[12](P25-30),并通過營造一幅幅視覺奇觀與幻想靈境圖,彰顯出了“想象力消費”的外在形式策略:滿足受眾外在奇觀化審美需求的想象力美學呈現。
首先,影片為受眾營造出了一幅幅飄逸靈動、鳶然而深、并且充滿想象力的意境空間圖,呈現出一種“天人合一、虛實相生、情景交融、時間空間化的意境美學精神”[13](P11-18)。影片“開場畫面”便給受眾一種“寧靜致遠”式“悠然見南山”之感,在大遠景、高飽和度的視野下,在對稱型、開放式的構圖中,受眾仿佛立足于仙界、腳踏祥云,前方是層巒迭起的山峰,后景是一望無際的云層與漫天燦爛的霞光,實可謂給其一種虛實相生、天人合一且頗具“霓為衣兮風為馬”的體驗,在營造典雅之境的同時,表達出了其精妙絕倫的獨特想象力與創造力。
自“開場畫面”勾勒出影片整體基調后,淡雅、幽深并且頗具“桃花源”質感的陳塘關便展現在受眾面前,伴隨著CG長鏡頭與搖鏡頭,位于山水之間、立于彩霞之處的地形圖呈示于眾。在此之中,村民生活井然有序、周邊環境寧靜悠然、建筑質樸大氣,似“清明上河圖”一般熱鬧非凡,卻又似“山水圖”一般寧靜自在,靜與動之間表露出一種“時間空間化”之感,呈現出天人合一、情景交融之勢。另外,影片中的“山河社稷圖”亦充滿靈動之氣,顯現了導演豐盈的想象力與卓越的創作才能,在哪吒“入畫”后,導演先以遠景牽引出哪吒面前雄偉壯闊、高雅別致的宮殿,表現了哪吒與畫作融合的意味,后用拉鏡頭,為受眾呈現山水相間、淡雅別致的畫作全貌……哪吒與畫作于此融為一體,而其在此之中的修行、玩耍也別有一番天人合一、物我相融、虛實相生之感,而蘊含著意境美學或寫意精神的傳達。除此之外,影片中陰森黑暗的龍宮、余輝照耀的海灘等場景,都與主人公相輔相成,形構了動靜結合的二元質感,為受眾營造出一幅幅意境悠遠的靈動之景,既滿足了想象之需,也彰顯了影片清新雅致的美學特質。
其次,影片總體基調呈現出獨特、靈動、飄逸、悠揚,并且蘊涵著些許“流動性”“運動感”[14](P11-18)的樂舞氣韻。一方面,影片的構圖、景別與鏡頭呈現出別致的流動感,而其較多運用長鏡頭,搖鏡頭也較為緩慢,在鏡頭流動轉化之間給受眾呈現出如泉水細流一般的“運動感與流動性”;另一方面,影片中的山水、草木、房屋等呈現出“線之美”,以哪吒剛入畫的宮殿為例,在給人以崇高質感享受的同時,其流暢的弧度、對稱的構造與四周飄逸的云層,也帶來了似乎獨具東方韻味的舒緩感;再以“山河社稷圖”的湖面為例,湖中的山水草木,靜態暗流的泉水、仰天長嘯的荷葉、立于葉上的層山、飄渺靈動的祥云,都在外部形態與內里構造之處,勾勒出了一幅“清泉石上流、蓮動下漁舟”的風景。虛靈的空間、流動的鏡頭、雅致的景別……種種特質下的《魔童降世》,不僅對中國傳統樂舞氣韻進行了現代影像轉化,而且為受眾呈現出了一幅幅、一個個靈動飄逸的圖景,極具想象力與創造力,滿足了受眾“視聽震撼,奇觀夢幻”式的審美需求。
(二)情節、敘事的想象力美學彰顯:怪誕、夸張、超現實、出乎意料
如前文所述,《魔童降世》呈現出一種游戲化敘事與互文記憶基礎上的文本重構設置,影片夸張怪誕的主人公造型、超現實的敘事場景呈現及出乎意料的情節設置……都體現出影片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也都呈現著想象力美學、彰顯著想象力消費的內在策略。
首先,影片基于受眾互文記憶的文本重構,體現出其獨到且卓越的想象力。影片對以往“哪吒鬧海”故事的顛覆與現代性改編極具話題性與創造力,一方面它從“魔王降世、收服魔丸”為故事的出發點,不但重新想象了哪吒的前世,而且二度創造了他的今生,大膽重構了人物性格與人物關系(如敖丙性格、敖與哪吒的關系等),給受眾以出乎意料的審美體驗;另一方面,影片敘事呈現出游戲化“闖關”特點,與以往“哪吒因過失而失去生命,復活后選擇復仇”的故事設置相比,《魔童降世》采用“哪吒為贏得認同,而不斷突破自己、突破社會、突破命運”式的闖關設計,以出乎意料的改編,打破了受眾定向期待視野,極具創新價值。
其次,影片的諸多情節設置呈現出超現實、出乎意料的想象力美學風格。哪吒“入畫修行”,作為實體進入到虛擬空間,在其中修煉、嬉鬧的情節,超乎現實邏輯,亦表達出一種虛實相生、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哲學色彩。同時,“山河社稷圖”中哪吒“以筆運景”的情節設置,亦具想象力與創造力:通過一只筆便可以改編世界、移花接木、扭轉乾坤……這無疑是諸多受眾閑暇之想。另外,影片中哪吒敖丙共抵天雷、地下龍宮共鑄萬麟甲、哪吒敖丙海邊相遇、李靖殷夫人共抵龍族來襲、申公豹設計陷害、太乙真人吃酒誤事等諸多情節,都一反受眾定向思維,超乎現實、出乎意料。
最后,值得強調的是,除情節、敘事外,影片中夸張、怪誕、一反以往的人物造型也頗具想象力與創造力,給受眾以出乎意料的審美體驗。“黑眼圈、大齙牙”的丑哪吒、“鞋拔子臉”的申公豹、“油膩大叔”樣式的太乙真人、英姿颯爽的殷夫人等作為敘事的行動者與接收者,在自身呈現想象力的同時,也表現出影片整體的想象構設。
(三)溫情世界的呈現與人文訴求的表達
魯迅先生把《封神傳》列為明代神魔小說一類,評論其為“實不過假商周之爭,自寫幻想……較《水滸》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遜其雄肆”[15](P187),盡管此中表現出了魯迅先生對此類作品“自寫幻想”的批判,但時至今日,尤其對于魔幻類作品而言,“自寫幻想”似乎已經演化為一種敘事方法與表達方式:基于原始神話故事進行現代性轉化,并借古喻今,“把人性、愛情、人與自然事物的原始情感推向幻想世界進行‘詢喚’,完成大眾對魔幻和超驗想象世界的消費”[16](P41-44),進而表達出影片獨到的人文訴求,為受眾呈現出一個溫情世界。《魔童降世》便是如此。
首先,影片為受眾勾勒出了一個充滿親情、愛情、師生情的溫情世界。受“身份之因”而飽受偏見之苦的哪吒在父母、師友的幫助下走出陰霾、重獲新生的故事,本身便帶有溫情之意味。相對于哪吒所面對的偏見與狹隘,因其之過失而不斷受村民指責的李靖與李夫人,所承受的辱罵、責怪、謠言等與之不相上下。但盡管如此,李夫人依然在妖怪入侵陳塘關時,呈現出放棄骨肉至親時而深入骨髓的創痛,李靖也不斷放下身段為哪吒求情,二者對職業、對百姓的尊重,也在無時無刻溫暖著受眾之心靈;當哪吒屢次闖禍回家后,二者語重心長的教導,無不流露著至上之親情;面對哪吒的誤解與反抗,二者雖表明氣憤,但卻多次心疼而憐惜,表面嚴厲的李靖甚至以身為契,代替哪吒承受天雷之刑……無論是李靖、李夫人對陳塘關百姓的保護,還是對哪吒的寵愛,都在為受眾呈現出類似現代父母所承受的社會壓力:一邊是在外應酬、掙錢養家、處處小心謹慎,一邊是在內持家、保護孩子、照顧老人、時時不敢懈怠。此種借古喻今的情節設置與人物塑造,在使受眾感受溫情的同時,已讓其產生認同與代入感,呈現出影片獨到的人文關懷。此外,影片中敖丙、哪吒一同抵御天雷,哪吒說服敖丙,敖丙應邀參會等設置,也在想象重構而豐滿情節架構的同時,為受眾呈現出了二者亦敵亦友的純粹情感,溫馨無比;同時,影片中太乙真人對哪吒的不離不棄、認真負責、隱忍寬容、精心照料也充滿溫情,代表著當下含辛茹苦、不畏辛勞的教師精神,亦不難讓受眾產生認同、達到共鳴。
其次,影片對“偏見”進行了審視與反思,極具人文關懷與現實價值。縱觀影片的主要沖突,我們不難發現,把主人公“逼向梁山”的往往是大眾的成見。哪吒因“魔丸”身份而自小被鄙視、被孤立,就連小朋友都對其言語攻擊。哪吒在救人后被誤認為打家劫舍、搶走小女孩。哪吒在出門玩耍時,被定義為出來禍害村民……被鄙視、被孤立、被妖魔化的哪吒,也曾想通過拯救人們、入畫修煉等方式融入社會,但村民對哪吒的成見,一步步地讓哪吒走向了深淵。一句妖怪來了,不僅刺痛哪吒的心,更指向了受眾的心。同樣,出生“靈丸”的敖丙,也因其龍族身份而備受煎熬,善良大度的他,拯救了即將要被哪吒毀滅的陳塘關,但只因村民得知其為龍族異類后,便對之大開殺戒的選擇,引發了敖丙的報復。與其說是哪吒、敖丙傷害陳塘關,不如說是陳塘關百姓因自我的成見而引火上身。哪吒、敖丙所經歷的一切,也正指向了現代受眾所經歷的:當下人們為贏得別人認可,而不停改變自己,甚至違背內心,社會也經常以“出身”“家庭”“學歷”“背景”“過往史”等標準來評價個體。哪吒、敖丙通過自己的反抗,進行自我救贖的設置,無疑頗為契合諸多受眾意圖對抗不公、做回自己的情感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釋放了大眾在工作、生活、學習、人際交往中的壓力與苦悶,給其以片刻的精神復歸與解放。誠然,哪吒、敖丙通過犧牲自己的形式,回歸社會、成為英雄、得到認同的設置,具有浪漫色彩,但此種溫情處理,也促使身份代入的受眾獲得快感:“身份邊緣的我,也是可以作為英雄拯救那些當初看不起我的愚昧之人的”。此中,哪吒、敖丙由“被邊緣”到“被英雄”的弧度性人物設置,無疑是一種富有想象力、創造力的連接和轉化,也頗為符合受眾想要成為“平民英雄”的未來之想象。我們可以通過此種結局設計,感受導演“期待每個生命個體得到認同、渴望每個個體成為自己的英雄”的美好期盼與人文關懷。我們更可以從此種假定中,窺見影片想象力消費的內在策略:將原始情感推向奇觀異景的幻想世界進行“詢喚”。
結語
就一定意義而言,作為一個具有“合家歡”性質的電影片種,動畫電影的發展是頗具前景的。它在好萊塢占據重要地位,以《獅子王》為代表的諸多票房與口碑雙豐收的佳作,都在直接證明發展動畫電影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縱觀中國動畫電影發展的歷程,不難發現,我們的作品,在票房和口碑等許多方面,與好萊塢相比,都有著不小的差距。但自《西游記之大圣歸來》(2015)取得斐然成就后,我們便可以看出趨勢,即動畫電影在中國是有光明的發展前景的、是符合受眾審美需求的。2019年的優秀影片《白蛇:緣起》《羅小黑戰記》,尤其是《魔童降世》的成功,更是直接佐證了動畫電影未來勢不可擋的發展勁頭。
誠然,《魔童降世》的成功具有偶然性,與2019年暑期檔其他影片狀況、自身排片及精準宣發密不可分。同時,相較于好萊塢動畫大片的強視效、大體量、泛共鳴而言,它在體量積累和視聽呈現等方面均有所欠缺。但是,所謂瑕不掩瑜,我們應該看到,《魔童降世》對于國產動畫電影發展的推進作用,它的成功不但給予了中國動畫電影在未來創作上的廣闊空間,也給予了“電影工業美學”在未來理論建構與實踐道路上的極大自信。就此而言,我們應該大力呼吁、大量創作此類充滿想象力、具有奇觀化視聽、飽含趣味性與游戲性、滿足受眾認同心理與“想象力消費”需求、傳遞普適價值觀念且擁有票房號召力與話題性的動畫大片。
無疑,中國動畫電影應在包容、創新、發展的過程中,充分發揮想象力與創造力,大膽突破、精心制作,滿足互聯網受眾日益增長的“想象力消費”之訴求,傳達中國精神與中國夢的核心內涵,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增加文化自信與自覺。筆者相信,未來國產動畫電影將在踐行“電影工業美學”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好,將在扎根國內的基礎上,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