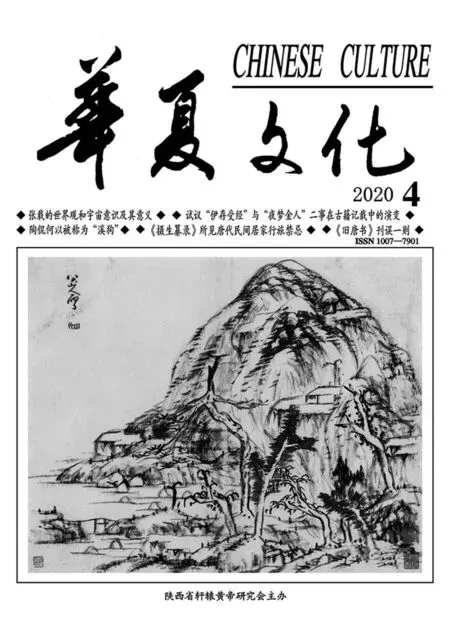《論語》“何必讀書然后為學”章探賾
□程澤陽
《論語·先進》有一章:“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在此章中,孔子不同意子路推薦子羔出仕,而子路應之以“何必讀書然后為學”之語。由此出發,對于孔子何以批評子路,為學、讀書、出仕之間是什么關系以及相關問題,都值得深入探討一番。
一、子羔為宰之地考
子羔,原名高柴,又作子皋、季羔、季子皋、高子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又說:“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比《先進》篇所記多一“郈”字,東漢王充《論衡·藝增》也作“子路使子羔為郈宰”,由此生出異說。劉寶楠引戴望的觀點:“《史記》‘費’字后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郈在鄆城宿縣,未言費所在,知所見本無費字……子路以墮郈后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他不僅斷定高柴所任為郈地宰,還點出了子路任職時間在孔子“墮郈后”,并加按語認為“戴說頗近理”。(劉寶楠:《論語正義》,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2頁)。但是筆者認為此種說法并不合理。首先,戴望根據《史記正義》此處只釋郈不釋費,斷定“費”字為后人所增,此觀點就站不住腳。因為在《史記》其他出現費地之“費”的地方,如《孔子世家》“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于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等處,《史記正義》都是不釋費,只釋郈,則可知《正義》默認“費”字不出釋文,戴望所認為的不釋“費”字則本無“費”字的觀點不成立。并且根據日人水澤利忠的考證,南化本、楓山本、三條本、梅本四種宋元版《史記》校記都“無郈字”(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四,廣文書局,第2410頁),卻沒有校記說無“費”字的。
其次,王充《論衡·藝增》云:“子路使子羔為郈宰,孔子以為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此一處雖作“郈宰”,但記載十分簡略。而《問孔》、《量知》、《正說》三處均記載為“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并且引用得比較詳細,其中《正說》篇所引與《論語》相差無幾。雖然黃暉《論衡校釋》認為正作“郈宰”,凡作“費宰”皆后人據今本《論語》而改。可是他的說法也有不合理之處:第一,若是后人據《論語》妄改“郈”為“費”,何以獨《藝增》篇未改?第二,《問孔》篇引文作“有社稷焉,有民人焉”,而《正說》篇卻作“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前后不相統一,若經后人竄改,必嚴絲合縫,無此紕漏。所以這些紕漏恰恰證明應是王充憑自己記憶所寫的“傳聞異辭”。同時代的《白虎通義·社稷》引用此段,亦作“季路使子羔為費宰”;劉寶楠又說“《論語集解》亦不釋郈,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則同一時代諸家與王充《論衡》所本相同,都作“費”。
最后,仔細品味此章語氣,子路使子羔為邑宰似乎頗為容易。再參之以《論語》:《雍也》篇“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罕》篇“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張》篇“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在這幾例中,“使……為……”均表示前者對后者擁有某種指派、任命的權力。但是“仲由為季氏宰”,子路是季孫氏的“總管”(楊伯峻語),而郈地卻是叔孫氏十分重要的采邑,是“三都”之一,那么即使子路在“墮三都”之事中再有功勞,也不可能很輕松地以季孫氏家臣身份指派子羔做叔孫氏重要都邑的邑宰。又根據《論語》記載,叔孫氏這一代家主叔孫州仇,即叔孫武叔,他曾多次詆毀孔子,意必之前對孔門弟子無好感,不會任用孔子門人。事實的確如此,《左傳·哀公十七年》云“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武伯問于高柴”,《禮記·檀弓下》“子皋將為成宰”、“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可見高柴是受到孟孫氏的重用,當過成宰(成即郕)的,所以有理由認為《仲尼弟子列傳》中“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的“郈”是“郕”字之誤。
二、出仕、為學與讀書的關系
子路舉薦子羔當邑宰,孔子以為不可。子路說:“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王充《論衡·正說》云:“五經總名為書。”子路認為為學不一定只是讀《詩》、《書》等典籍,治民、事神亦是為學。而孔子說:“是故惡夫佞者”。梁章鉅注曰:“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程樹德說:“自夫子惡夫佞者,而佞乃為不美之名。”孔子為什么批評子路“佞”?為學與讀書是何關系?
據余英時考察,春秋末期,宗法分封制度被破壞,社會階層的流動——即上層貴族的下降和下層庶民的上升,使得處在“上下流動的匯合之所”的士階層人數大增,士出現了從最低層的貴族到最高級的庶民的轉化。瞿同祖也認為,處于四民之首的士民是士的預備階級,他們以學問為事,不耕不作,“學未成不為官,便是庶民;被擢用時,便可進而為士”。因此,私人講學的風氣在此時十分興盛,儒家、墨家都大規模的收徒講學,傳授士民做官的知識。《論語·為政》“子張學干祿”,《衛靈公》“學也,祿在其中矣”;《墨子·公孟》:“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而不經過學習則不能出仕,《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載子皮想要讓尹何主管一邑之地,在管理中學習,而子產說:“僑聞學而后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此行,必有所害。”《新序》也記載:“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后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 為學熟習成為了出仕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當子路讓子羔出仕去當邑宰時,孔子認為子羔“學未熟習”,會害了子羔。
在《論語》的記載中,孔門對“學”是非常重視的。《論語》開頭就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孔子自述“十有五而志于學”、“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孔子對季文子、顏回的評價也都是“好學”,其他關于學習方法、學習意義的論述也比比皆是,茲不贅言。既然學是為了出仕做準備,那么所學、所教就十分重要。首先應當是學習各種實用技能——即“藝”。孔子也說:“吾不試,故藝。”藝指多才能,大體是指禮、樂、射、御、書、數六種官吏的常用技能。《左傳·昭公七年》記載“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于是臨終時使其子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是貴族不知禮而向孔子請教;《論語·子罕》云:“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孔子曾致力于樂;同篇又云:“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是孔子嫻熟射與御;孔子又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程樹德《論語集釋》考證“古謂字書為史”,是孔子對書有研究;《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是孔子于數亦能“會計當”。因此當季康子問子路是否可以“從政”時,孔子說:“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掌握“藝”是庶人為“士”最基本的要求。
若只是要學會一項或數項“藝”,自然不一定要學于“仲尼之門”。而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亦不僅僅是因為他教授弟子射、御之技能,更在于他教授與傳承禮樂文化的典籍。《述而》篇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這是有關孔子教人最直接的表述。《先進》篇則將孔門高弟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分為四科。北宋劉敞《公是弟子記》將二者對應起來:“文,所謂文學也。行,所謂德行也。政事主忠,言語主信。”他還認為:“古之教者,《詩》《書》、禮、樂。至仲尼,益之以《易》《春秋》,樂自此沒矣。禮者,徳行之本也;《詩》者,言語之本也;《書》者,文學之本也;《春秋》者,政事之本也。”又將孔子四教與儒家典籍聯系起來。《史記·孔子世家》亦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此處的“六藝”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詩》、《書》等典籍在春秋時代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無論是在宗廟會同、諸侯朝聘,還是勸諫君主、貴族宴飲,這些場合都需要賦《詩》、引《書》來表達意見,或為自己的觀點提供依據。據統計,《左傳》中引詩、用詩多達一百多處,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這些都是重視《詩》交際功能的體現。
但是也有不同觀點,元代《四書辨疑》引王若虛云:“夫文之與行固為二物,至于忠、信,特行中之兩端耳,又何別為二教乎?”將“忠、信”納入“行”中,把孔子所教歸為“文”和“行”兩類。事實上,這種看法才是比較全面的。隨著王官之學失守,“道術將為天下裂”,士階層不僅嫻熟于贊禮、治政等具體技能,還掌握了傳承禮樂文化的上古典籍。他們面對禮壞樂崩、“肉食者鄙”的現實局面,要求改變,并以“道”自任,“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自覺地承擔起了弘道的責任。因此,一部分人為學不再是為了出仕、求祿:“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論語·雍也》)顏回好學,卻未曾仕進,而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士志于道”、“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君子謀道不謀食”成了更高層次的要求。因此“為學”內容的本末就發生了變化,具體技能的掌握、《詩》《書》等典籍的諷誦固然重要,但對“道”的踐行、傳承才是為學的終極目標。而儒家的“道”是仁、是孝悌,都是側重于“行”。故而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在“文”和“行”的關系中,孔子認為學文是“行有余力”才可以從事的,先“行”而后“文”,這一思想在孔門后學亦引起了討論。有若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子游批評子夏的門人只能“灑掃應對進退”,有末而無本。為學次第、本末的爭論已經有了分歧。
至此,對孔子批評子路“是故惡夫佞者”可以全面地理解:子羔“學未熟習”,對典籍的理解、應用不夠,自然不可以出仕;但子路之言若單獨拿出來亦無不當,為學當然不僅僅只是讀書,至少包括力行;所以孔子只說他“佞”,而對他的意見并沒有正面否定,此處的深意值得注意。
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的后世影響
自子路以“何必讀書,然后為學”應孔子,此語很長一段時間都用作掩飾不讀書的遁辭,如《魏書·伊馛傳》崔浩云:“何必讀書,然后為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能大建勛名,致位公輔”。及至宋代,學術風氣大變,心性之學興起,子路之言才又被置于學術討論的語境之中。
“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從范圍上講,是說為學不僅僅包括讀書;從為學次第上講,則是認為讀書不在為學之前,不是為學所必備的。因心學一派主張“心即理”,認為為學應當“發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故而主要從為學次第的層面上理解此語。如陸九淵說:“學茍知本,六經皆我注腳”,又說:“學者須是打疊田地凈潔,然后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凈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為學,即‘讀書然后為學’可見。然田地不潔凈,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赍盜糧。”(《陸九淵集》,中華書局,1980年,463頁)與陸九淵來往密切的曾豐亦有詩云:“……心融口笑先儒泥,一萬余言解三字。粹精還我聞未聞,糟粕從渠味無味。懸知書者古之余,稷契皋夔讀何書?猶期立腳群賢上,更請回頭萬物初。”(《題李師儒上舍稽古堂》)明代陳獻章更說:“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陳獻章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20頁)這引起了朱熹學派的極大反對,鵝湖之會上朱熹與主張“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覽”的陸九淵激辯;王應麟考證稷契皋夔之時,亦有書可讀;明儒黃佐批評說:“學必讀書,然后為學,問必聽受師友,然后為問。駕言浮談,但曰‘學茍知本,則《六經》皆我注腳’,則自索之覺悟,正執事所謂野狐禪耳。”(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五十一)但正如全祖望所說,陸王之學并不教人不讀書,而是“深戒學者騖高遠而不覽古今”,他認識到“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黃宗羲也說:“然陽明亦何嘗教人不讀書?第先立乎其大,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德性之知也”。他們的思想對于轉變繁復的章句訓詁之學自有其積極意義,只是流弊以致“世之談道者,每謂心茍能明,何必讀書”,亦非象山、陽明所知也。
心學發展到后期,出現了“未嘗讀書而索之空寂杳冥”、“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的局面,儒生對于經史典籍早已束書不觀,只致力于與帖括之文有關的程、朱注疏。隨著明朝滅亡,有識之士如王夫之、顏元等人認識到這種空疏的學風與之有莫大的關系。顏元說:“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所以他認為為學不僅僅是讀書,甚至不是讀書,“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力主實行、實干之實學。他解釋此章云:“‘賊夫人之子’,蓋謂道未明,德未立……非謂必使之先讀書也”,又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將讀書視為“吞砒霜”。他重新詮釋儒家之道與學:“蓋吾子之所謂道,即指德行兼六藝而言;所謂學,即指養德修行習六藝而言”(《顏元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222頁),要求儒生躬行“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身習“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之屬”,為有用之學,做有用之人。
陸王心學贊同“何必讀書,然后為學”,而反對陸王心學的顏元亦贊同此語,這種現象值得更加深入地探討。在今天,我們對于子路“何必讀書,然后為學”之語仍要作辨證地理解,即既要廣泛地讀書、博覽,又不可只將讀書看作為學而鉆入故紙堆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