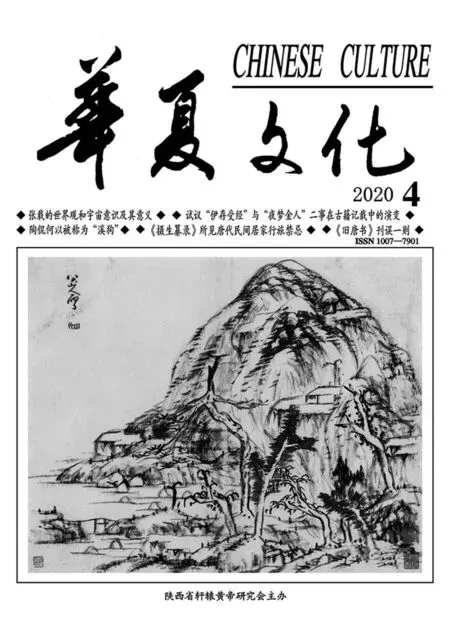史學確立為官學不由石勒始考
□華迪威
《晉書·石勒載記》云趙王二年“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并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胡寶國先生在其《漢唐間史學的發展》中認為這標志著史學在教育中成為了一個獨立的門類,標志著西晉以后經、史區分在教育上的體現。
此條史料是襲自北魏崔鴻撰寫的《十六國春秋》,一向被認為是“史學”二字第一次并稱在史籍中,史學似乎已經與經學、律學一樣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但我們檢視史料,發現《晉書》中除此之外再無“史學”二字出現,這里的“史學祭酒”是否就是我們所認為的歷史學呢?
我們先看看負責擔任經學祭酒的裴、傅、杜三人。《晉書·裴憲傳》云其“修尚儒學”且在石勒初開創制度、制定朝儀時出力甚多,由其擔任經學祭酒自然再合適不過;《晉書·傅暢傳》云其“諳識朝儀”也在制定制度等方面出力甚多,其儒學修養也足以讓其擔任經學祭酒一職;《晉書·石弘載記》云其“受經于杜嘏”。可知三人都有深厚的儒學功底,讓他們擔任經學祭酒是人盡其才。
再看續、庾二人。《晉書·續咸傳》云其:“修陳杜律,明達刑書”,庾景則無其他記載,但可以推知應該也是對律法之事頗為精通之人,可知石勒都是以有相關知識儲備的頂尖人才充任祭酒的。
接下來看擔任史學祭酒的任播、崔濬。《晉書·石弘載記》云石勒“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前文中有石弘“受經于杜嘏,誦律于續咸”之記載,而石勒之所以讓任播授石弘以兵書是因為他認為“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經學、律學自然為文業,而任播卻并不被石勒認為是文人,如果“史學祭酒”是歷史學,自然也屬于文業,而從石勒的態度又可以明顯看出任播并非一般的文人。
按照石勒以個人知識結構與體系劃分官職的一貫方式,這里的“史學祭酒”或許并非歷史學,而是與兵學直接相關,與任播一起授石弘以兵書的劉徵更是石勒手下的大將。或許劉徵負責傳授其行軍打仗之具體經驗,而任播在兵學理論方面對其進行傳授,崔濬則除此之外并未再出現在史籍中。
從整體來看,有關“史學祭酒”的相關材料或無法證明其與我們如今認知的歷史學有直接的關聯性,從為數不多的史料所呈現出的擔任史學祭酒的任播,其知識體系更接近于兵學而非文業。故我認為這條史料并不能證明歷史學在石勒時已經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對于證明經、史已經分離也未必那么有說服力,更無法確認此時之史學學官是否就是我們所熟知的與歷史學相關的官職。
誠然,大多數文獻中出現的“史”、“史學”就是我們認識的歷史學,但在好兵的石勒眼中,是否史學含義近似于過往歷史中行軍打仗的相關理論與實踐呢?這也是有可能的。如《漢書·宣元六王傳》載東平王劉宇上書求《史記》,被大將軍王鳳以“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為理由拒絕,可知《史記》中存在戰略權謀或關兵學之事,故不許諸侯王閱讀,也可從側面看出史學與兵學確實存在著一定聯系。
既然我們無法確認石勒設立的史學祭酒與歷史學直接相關,那么之后宋文帝劉義隆以儒學、玄學、文學、史學四學并立就尤其值得考察。《宋書·雷次宗傳》云元嘉十五年“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何承天負責史學一門。《宋書·何承天傳》云其“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元嘉十六年何承天“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沈約《宋書》的基礎便是由何承天等人陸續修成的南朝宋國史。《宋書·禮志一》提到“史學生山謙之”,應當是何承天門生無疑,《宋書·徐爰傳》又有:“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則山謙之繼何承天之后繼續修史,與上文相對照我們可以確認山謙之確曾就學于何承天學習史學相關知識,故能繼承其學,繼續完成修史大業,可知劉義隆所立史學學官培養的確實是史學人才,這應該是史學被立為官學的鐵證。